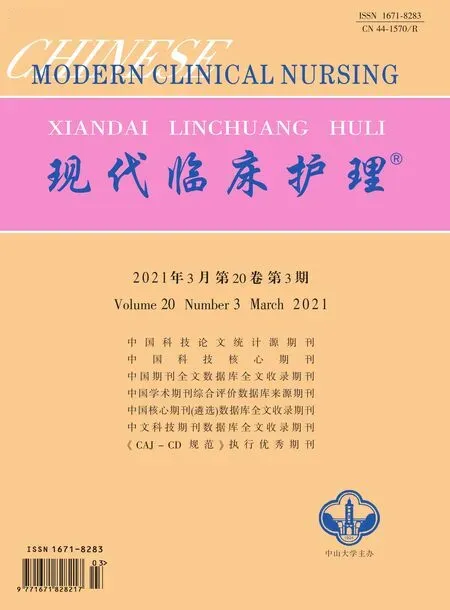临终患者预先护理计划实践研究现状
阳佩,张春华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1 放化疗腹部肿瘤一病区,2 护理部,湖北武汉,430071)
预先护理计划(advance care planning,ACP)又称预立医疗照护计划,是指患者在意识清楚时,在获得病情预后和临终救护措施的相关信息后,凭借个人生活经验和价值观,表明自己将来进入临终状态时的治疗护理意愿,并与医务人员和(或)亲友沟通其意愿的过程[1]。预立医疗指示(advance directives,ADs)是ACP 的表现形式,即患者在意识清楚的前提下为自己将来的医疗决策作出的指示,包括指令型和代理型ADs[2],它是ACP 沟通过程中的一部分,强调具有患者自主权的法律文本。ACP 的实施不仅能有效保障临终患者的自主权,提高终末期生活质量,还可以减少过度医疗,节约医疗成本。在我国人口老龄化和慢性病发生率持续上升的社会背景下,实施ACP 具有重要的社会和经济效益。然而,在国内受传统文化和社会伦理的影响,ACP 的发展与国外存在着较大差距。美国于上世纪70年代就提出了生前预嘱概念并于1976年正式赋予了生前预嘱法律效力,随后英国、澳大利亚等其他国家也建立和完善了相关法律法规。我国在2010年—2013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了推广生前预嘱和建立政府指导下的生前预嘱注册中心的提案[3]。在实践研究方面,我国还处于ACP 文化价值探讨和接受度、态度等[4]现状调查层面,在实践应用方面涉及较少,仅在晚期或终末期患者中应用[5-7]。本文将从国内外ACP 实践的流程步骤、干预要素与模式、评价指标、实施障碍和促进因素等方面进行综述,以期为开展本土化ACP 实践提供参考。
1 实施ACP 的流程步骤
1995年EMANUEL 等[8]最初提出ACP 的实施过程可分为5 个步骤:对ACP 展开讨论、促进ACP的讨论、签署ACP 文件、对签署的ACP 文件定期审核与更新、在临床中落实ACP 文件。2014年欧洲肿瘤内科学会[9]发布的《ESMO 姑息治疗临床实践指南》提出了ACP 的实施流程,该流程包括两个层面,首先是个人层面(包括专业健康照顾提供者、患者、替代决策者):告知病程→确保患者理解→考虑制定预立医疗指示→确定预立医疗指示→记录预立医疗指示(指定并通知替代决策者)→重新评估和更新预立医疗指示→记录预立医疗指示的变化; 其次是机构层面: 转述预立医疗指示→执行预立医疗指示(认可替代决策者的角色)→对预立医疗指示程序和实施进行评估。2020年王硕等[10]总结了国外晚期癌症患者ACP 实施的主要内容:评估患者及其家属参与意愿,讨论并确定首选代理决策者,了解患者对自身健康状况的掌握程度和未满足的信息需求,了解患者的价值观、目标、优先事项、希望、恐惧以及担忧,告知其他相关治疗方案,了解患者对生命末期医疗照顾的期望,记录患者意愿等。目前,我国ACP 实践干预[5-7]主要体现在满足晚期或终末期肿瘤患者对ACP 和各类临终照护方式的了解需求、引导患者主动表达临终治疗意愿并拟定临终医疗照护计划两个方面,未提及是否和如何按照患者意愿提供临终照护。
2 ACP 的干预要素与模式
2.1 ACP 发起者
ACP 的完整实施需要依靠多学科团队协作进行,通过ACP 培训并考核合格的医生、护士、社会工作者、健康教育师以及研究助理等人员均可以发起ACP。BERN-KLUG 等[11]调查显示,超过1/3的老年人愿意与其代理决策者而不是医生讨论临终护理意愿。但是LUCKETT 等[12]和SHARP 等[13]的系统评价结果表明,患者和照护者更倾向于由医生或者医疗团队发起ACP,而不是非正式的看护人员。其他系统评价[14-16]还强调人际关系的重要性,患者倾向于由熟悉病史、了解患者和其家庭状况的医疗专业人士发起。开展ACP 讨论需要花费较多时间,临床医生可能不具备这一条件,因此安宁疗护护士作为ACP 发起者已经越来越普遍[17],这与她们的职业特点有关。护士作为专业的医疗照护人员,通过与患者频繁互动和沟通,不仅有利于建立持久的照护关系,还能敏锐发现患者和家属之间的决策矛盾以及ACP 需求,并通过非正式沟通方式向患者宣传ACP,评估患者的参与意愿,是非常理想的ACP 发起者[18]。但是我国目前并没有明确的流程和职责分工指导护士如何在临床中开展ACP。
2.2 发起ACP 的时机
关于发起ACP 的适当时机,目前没有统一标准。有研究者建议应该尽早开始,尤其是在痴呆患者和照护者中,因为需要在患者认知功能完好的时候开始ACP。另有研究者则认为在患者疾病的后期会更有用,例如在肿瘤患者中,患者和照护者一般倾向于尝试完所有方案后才开始考虑是否参与ACP[16]。我国肿瘤医务人员也认为在患者终末期即告病危时发起ACP 会比较合适[19]。ZWAKMAN 等[20]研究发现,患者对疾病性质缺乏了解不利于ACP 开始时间的确定,例如慢性阻塞性肺病等呼吸系统慢性病,患者缺乏对该类疾病终末期性质的了解,确定合适的讨论时间对他们来说比较困难。因此,确定ACP 讨论时机应该根据疾病类型和患者意愿而定,随着人们传统观念的改变以及对ACP 了解的深入,在健康状态下开始ACP 讨论也会成为可能,ACP 不是一次性事件,ADs 文件的签订需要经过反复讨论、沟通和修改才能确定[15,21]。
2.3 ACP 干预模式
2.3.1 结构化干预模式 结构化干预模式,即干预者与患者、家属面对面沟通,沟通内容已成体系,一般包括患者疾病信息、患病体验、生命价值观、临终治疗意愿等,该模式正逐步被接受并应用于临床实践中。陈裕丽等[22]在实践中总结了适用于中国香港地区社会背景的ACP 四步模式,后来他们将该模式运用于居家终末期患者时,发现大部分患者体力和注意力低下,于是将四步模式简化为了三步模式。中国台湾学者[23]通过文献回顾和专家评审等方式,筛选出适合本地文化的ACP讨论主题,包括生命故事、目前的健康状况和健康习惯、目前遭受的疾病痛苦以及关于临终照护的医疗决策。这种结构化的干预模式方便了ACP 干预的实践推广,但是在运用该模式时必须结合当地的社会文化背景,不可照搬照抄。邓仁丽等[24]认为,在家庭观念根深蒂固的中国文化背景下,应该构建以家庭为导向的ACP 沟通模式。邱业银等[7]对晚期肿瘤患者和家属共同实施名为“杏林晚语”的干预项目,提高了患者和家属的决策确定性,但并没有改变患者和家属的临终治疗意愿。
2.3.2 决策辅助干预模式 决策辅助干预模式通过视频、宣教手册、网站、计算机等工具,客观地向患者和家属提供有关各种治疗方案的信息,促进患者和家属对各种治疗方案利与弊的理解,它主要从明确需要考虑的问题、提供基于证据的信息以及使患者明确其选择意愿,促进医患交流这3个方面帮助患者做出决策。该模式通过决策辅助工具来实现,视频是教育患者并影响患者ACP 行为的重要辅助工具,它具有形象生动、可视化、传播性强等优势,视频干预并非单独进行,它往往与其他辅助工具联合使用。BAKITAS 等[25]通过使用ACP 学习册、DVD 视频等辅助决策工具,并联合护理人员电话辅助决策指导等措施,大大提高了患者满意度。肖兴米等[6]在晚期肿瘤患者中通过沟通技巧手册、宣传册和视频、医护当面解答患者疑惑等方式开展ACP,提升了肿瘤终末期患者的尊严水平,改善了其生命质量和死亡质量。这启示可以联合使用多种途径和形式向患者、家属展示各项临终照护方式,帮助他们制定合理的临终照护决策。
3 ACP 评价指标
ACP 既注重沟通过程,也强调将讨论共识记录成文本,之后再根据患者意愿决定是否进行法律公正,所以最终不一定签署ADs[2]。但是开展ACP 讨论却可以起到播种的效果,因此不能把ADs 文件签订率作为ACP 实施效果的唯一评价指标[22],应该使用多方面、多维度的评价方法。WENDRICH-VAN 等[26]通过对RCT研究和系统评价的概括总结,把ACP 效果评价指标分为了五类:第一类是ACP 和临终结局指标,包括临终治疗与患者意愿的一致性、是否在患者意愿的地点死亡、ADs 文件的签订率、ACP 讨论数量、接受姑息治疗和疼痛治疗的患者人数、对患者意愿的了解;第二类是医疗资源使用情况,包括住院率、住院天数、是否管饲、急救车呼叫数量、临终关怀使用、维持生命的治疗数量;第三类是患者结局,包括焦虑、抑郁、综合健康状况、生活质量、决策冲突、医疗保健选择的稳定性、照护满意度等;第四类是照护者结局,包括决策冲突、对制订治疗决策的信心、情绪问题、生理问题、生活质量、照护满意度、对ACP了解程度;第五类是费用,包括健康照护费用、住院费用、人均费用。
4 ACP 实施的障碍和促进因素
4.1 患者和家庭照顾者方面
患者对参与ACP 准备不足[17],将临终护理决策交给专业健康保健人员,而自己不愿意预先制订决策[27],这阻碍了ACP 的开展。家庭照顾者参与度不高,也会使ACP 的开展陷入窘境,廖佳芮等[19]发现,家属在ACP 沟通中占主导地位,肿瘤医务人员认为要首先获得家属的同意和认可才能与患者进行ACP 沟通。DENING 等[28]调查发现,患者年龄较大、受教育程度高或者健康状况比较严重时更愿意参与ACP。例如,与非癌症患者相比,癌症患者的ADs 文件签订 率更高[29]。ACP 不仅仅适用于患者,它也适用于任何健康阶段和任何成年人,鼓励人们“未雨绸缪”,提前思考临终治疗决策。目前,我国民众对ACP 的知晓率和接受度均较低,且经济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差异很大。张继元[30]的研究结果显示,不同特征人群如年轻人、老年人、机关事业单位人群等对ACP 的传播偏好存在着差异,因此为了普及ACP 知识,提高患者、家属和普通民众对ACP 的参与度,需要采取多样的传播方式和途径。此外,患者死亡地点和死亡类型也影响着ADs 的制订,在养老院死亡的患者和预期内死亡的患者制订ADs 的人数分别是在医院死亡和意外死亡患者人数的3 倍和2 倍[31]。这提示,随着我国老龄人口的增多和养老政策的相继出台,未来选择在养老机构临终的患者会越来越多,患者及家属的ACP 需求也将随之增加,养老机构的健康保健人员必须具备相应的知识和技能,满足患者对ACP 的需求。
4.2 健康保健人员方面
健康保健人员对患者疾病转归与预后的不确定会阻碍ACP 的进程[29]。例如,充血性心力衰竭或慢性阻塞性肺病等慢性疾病与死亡没有直接联系,健康照顾者在不恰当的时间与患者开始ACP讨论可能会引起患者和家属的负面反应。健康保健人员对待ACP 的态度至关重要,一项关于澳大利亚全科医生的调查显示[32],全科医生对ACP 的积极态度与迅速启动ACP 息息相关。在社区环境中,社区长期照顾提供者的个人特征如护理经验、既往ACP 经验以及对ACP 的态度等会对社区患者是否制订ADs 产生极大影响[33]。健康保健人员的谈话技巧也不容忽视[34],为了指导医师在临床环境下开展ACP,美国哈佛大学癌症研究中心专门制订了《严重疾病对话指南》,由此可见谈话技巧的重要性。该层面的促进因素还包括健康保健人员具备评估患者参与ACP 意愿的能力、具备丰富的ACP 知识[35]。然而,我国大多数医务工作者虽然对ACP 态度积极[36],对其知晓率却很低[37]。因此,为了提高医务人员的ACP 知识和技能,促进临床ACP 的有效开展,必须制定并实施系统、有效的ACP 教育和培训计划。
4.3 系统层面
目前,我国医疗卫生体系尚未嵌入ACP,缺乏清晰的流程和制度以及职责分工; 我国大陆地区有关ACP 的立法还属于空白,法律制度上的缺失可能成为了医护人员不予实施ACP 的关键原因之一。因此,需要在法律和卫生系统层面采取强有力的政策倡议,为ACP 的实施保驾护航。关于实施ACP 系统层面的支持要素,JIMENEZ 等[35]通过对80 篇系统评价综述进行整合,总结出了三个主要因素即系统的策略方针、成功ACP 项目的特征和创新ACP 的支持系统,具体支持要素见表1。

表1 实施ACP 的支持要素
5 小结与建议
ACP 是医护、患者、家属共同讨论临终治疗方案的过程,为医护、家属、照顾者等多方人员了解患者临终治疗意愿提供了很好的机会,有利于对患者临终治疗方案达成共识。虽然,我国相关法律制度尚未建立,医护人员在临床工作中仍然可以借鉴ACP 理念和方式,帮助患者、家属清晰地知晓各种临终治疗方式的利与弊,提供机会让患者充分表达、让家属充分聆听,减少家属之间的决策冲突,缓解患者和家属面对死亡的焦虑、恐惧情绪,提高患者临终生活质量。我国群众死亡观念保守、医护人员ACP 知识与技能缺乏、ACP 尚未被纳入医疗体系等因素影响了我国ACP 的发展,未来需要要针对不同人群采取不同的传播途径和方式,提高群众对ACP 的了解和接受度; 为医护人员提供系统的培训,在医学院校增设相关课程;将ACP纳入现有医疗体系,利用信息网络技术提高患者实际临终治疗与意愿的一致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