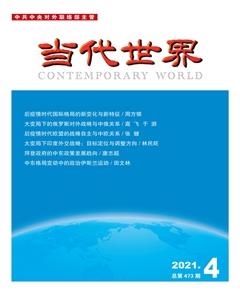大变局下印度外交战略:目标定位与调整方向
林民旺
【关键词】印度外交战略;中印关系;国际格局;不结盟;多向结盟
【DOI】10.19422/j.cnki.ddsj.2021.04.004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印度方面也认为,世界正处于一个大变局之中,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世界大变局的发展态势。作为当前国际政治的重要力量之一,印度在大变局中趋利避害,因势利导,谋求实现莫迪政府提出的“新印度”愿景。过去数年,在莫迪及印度人民党(以下简称印人党)的强势执政下,印度在外交战略上进行大调整,对全球局势及地区稳定都产生较大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将随着时局的发展进一步呈现出来。
印度对大变局的基本认知
2020年9月,印度外长苏杰生(S. Jaishankar)出版了《印度道路:不确定世界下的战略》(以下简称《印度道路》)一书,[1]系统阐述了对国际大势和印度战略的思考。苏杰生深受莫迪倚重,虽然其声称书中所阐述的思想仅为个人观点,但事实上代表了印度政府的外交战略取向。[2]结合对《印度道路》相关阐述的分析,以及印度自身的利益与战略关切,印度视野下的世界大变局至少包含以下三个重要维度。
第一,世界正处于新一轮巨变之中。印度战略界普遍认为,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是当前这一轮世界巨变的起点或拐点时刻,当今世界发生的一系列变化都是这一巨变的具体表现。发达国家开始拒绝全球化,全球民族主义加强,大国冒险主义上升,世界多边主义被削弱,国家间关系表现出更多的冲突性。[3]
冷战结束后以美苏争霸为特征的两极格局终结,全球化进程高歌猛进,给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社会与安全带来了巨大影响。特别是全球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改变了很多国家的国内生态。在互联网等新技术的推动下,传统政治制度出现失灵,表现出来的是全球范围内的民粹主义兴起和国内政治极化。特别是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公开抱怨国际贸易不公平、移民过度,并且要求盟友分担更大责任。上述政策举措体现了美国保守主义和孤立主义的倾向,其他发达国家也出现了与美国类似的“拒绝”全球化的现象。
第二,多极化是世界大变局的发展趋向。全球化导致国际政治力量对比发生了改变。从当前全球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Nominal GDP)分布比重来看,亚洲占世界的33.84%,北美占27.95%,欧洲占21.37%。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保持了大致稳定,欧洲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快速下降,亚洲则逐渐在世界经济中占据关键地位。在此背景下,西方世界的主导地位正在被整体性地削弱,世界排名前20的经济体中有一半已经不是西方国家。同时,印度方面认为,随着一大批新興国家跻身世界经济体前列,其对自身国家利益和国际地位有了更高要求,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全球原有的国际规则基础。
就印度战略界的理解而言,当前世界并没有明显朝着两极化的方向发展。苏杰生认为,世界并不会走向完全的两极体系。美国仍旧是世界科技领域的领导者,中国在贸易和资金上有实力争取世界第二的位置,欧洲的工业基础和制造能力仍然备受赞誉;俄罗斯恢复实力后,依靠自己的意志力能够重新成为关键玩家;加上大量第三方势力的存在,全球的权力等级排序并不是那么容易回答的问题。[4]中美双方在战略竞争中将努力争夺第三方的支持,这样反而会推动多极世界加速实现。[5]印度前国家安全顾问梅农则认为,全球化打破了全球力量的平衡,世界在经济维度上表现为多极化,军事维度上仍是单极的,而政治上则是模糊的。[6]
第三,中美战略竞争走向成为世界大变局发展的关键。印度是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理解中美关系变化的。苏杰生认为,一般而言,随着中美实力越来越接近,两国间竞争和冲突的一面不断上升,导致双方合作空间大幅收窄;而且中美竞争具有长期性,只有在技术领域出现重大突破,中美战略竞争的最终结果才能更加清晰地显现。在大变局下,印度既迎来发展良机,也面临战略挑战。具体而言,一个朝着多极化和更加均衡发展的世界有利于印度崛起。例如,美国早在21世纪初就表现出与印度携手的意愿,现在两国正在进一步加速推进各领域合作。俄罗斯仍然是印度的特殊伙伴,即便当前国际战略环境趋于复杂,俄印在地缘政治上的共同利益依然主导着两国关系。在英国“脱欧”后,一个不确定性更加凸显的欧洲越来越希望发展与印度的战略关系,并且将印度看作亚洲稳定和发展的重要力量。此外,随着中国的崛起,日本和东盟希望印度作为构建多极亚洲的关键要素,印度在亚洲的存在有利于地区力量的平衡分布。印度方面认为,中美战略竞争不仅对印度是利好,对中等国家来说也是如此。中美在战略竞争中将会努力争夺第三方的支持,这样反而扩大了后者的利益空间。印度同样也面临着挑战,在一个中美“脱钩”的世界中,印度要想顺利推进自己的战略目标,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是否能够处理好同两个大国的关系。[7]
“新印度”愿景与领导型大国外交
在印度看来,世界已经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开始了新的结构性转型,其发展趋势仍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但是国际权力格局的多极化和中美战略竞争的长期化是最为核心的方面。在此背景下,莫迪政府提出并构建了一套宏大的战略设想。在2017年8月15日的印度独立日演说中,莫迪首次阐述了建立“新印度”的愿景,而其所在的印人党于2018年明确将“新印度”愿景列为本党党纲内容。印度国家转型委员会(NITI Aayog)则专门制定了印度建国75周年的国家战略文件。[8]这一战略文件的核心内容就是将印度建设成为世界经济强国,而实现该目标的第一步是到2022年即印度建国75周年时,印度发展成为4万亿美元体量的经济体,到2025年成为5万亿美元体量的经济体。换言之,印度决心在短期内实现赶德(国)超日(本)的目标,使自身经济体量跃居世界第三。
莫迪政府的这一“新愿景”固然有为国内选举造势的诉求,但也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和现实基础。自2014年莫迪政府执政以来,印度GDP平均增速高达7.3%,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增速最快的国家之一。而莫迪提出的名目繁多的发展口号,如“数字印度”“技能印度”“清洁印度”“创业印度”等都是其“新印度”愿景的一部分。
如果说“新印度”愿景是印度对内的整体国家战略,那么面对印度崛起后要成为什么样的国际力量这一外交战略的核心问题,莫迪基于印度历史和传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即印度要成为领导型大国和世界领导者(Vishwa Guru),在全球范围内发挥领导作用,而不是仅仅作为国际体系中的一种平衡力量。基于领导型大国的目标定位,印度在外交战略中提出了一系列政策主张。
在国际多边层面,印度倡导所谓的“改革的多边主义”(Reformed Multilateralism)。莫迪早在2018年7月第十届金砖国家峰会时就提出了这一概念,其核心思想是现有的国际多边机制已经不符合时代要求,需要进行改革;改革的主要方向是将印度这样新崛起的大国纳入多边机制的“领导国”行列,或者至少要给予其更大的发言权和决策权。对印度来说,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最重要的诉求。除此之外,印度还努力将“印度元素”推广到全球。在莫迪政府的推动下,2014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正式将6月21日设立为国际瑜伽日。同时,印度积极以所谓领导国身份,构建以印度为主导的国际组织。如2018年3月,在印度总理莫迪、法国总统马克龙的领衔下,30多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以及近百个国家和组织的代表团齐聚印度首都新德里召开太阳能峰会,正式宣布成立一个全新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国际太阳能联盟”(ISA),旨在为贫穷发展中国家筹措资金,通过技术分享和能力建设,力争2030年前为这些国家新增1000吉瓦的太阳能光伏装机。
在大国外交方面,印度明确以多向结盟(Multi-Alignment)政策取代不结盟政策。在战略实质上,不结盟和多向结盟都意味着印度没有明确表明要选择一方,而是寻求保持同大国的等距离外交。但相较于不结盟政策,多向结盟秉持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寻求同时与多个大国发展关系。在这一政策思路的主导下,印度不是仅仅消极地避免卷入到美俄、中美之间的矛盾,而是选择同时推进印美、印俄、印日、印中等大国关系,并在不同的国际组织中“纵横捭阖”。例如,2017年印度加入上海合作组织的同时,与美日澳重启了四国安全对话并于2021年举办了美日印澳“四国安全对话机制”首脑会议;2018年印度与中俄召开三国领导人会晤的同时,与美日领导人也召开了三国领导人会晤。
在南亚及印度洋的直接邻国方面,印度仍奉行传统的地区“门罗主义”政策,针对南亚国家推行“邻国优先”政策,针对印度洋岛国则推行“萨迦构想”(SAGAR),将地区各国的互联互通作为重要内容。2014年莫迪在举行总理宣誓就职仪式时,邀请了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南盟)国家领导人集体参加,相当于组织了一个微缩版的南盟峰会(Mini-SAARC)。2019年莫迪的总理就职仪式邀请了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BIMSTEC)的国家領导人观礼。以上种种举动都显示出印度对地区“门罗主义”政策的重视。在实际政策举措中,印度仍然摆出一副不容任何国家染指南亚地区的姿态。除了抹黑并抵制中国 “一带一路”建设有关项目在这一地区的推进,印度还联合美日等国在该地区搞出各类平行的项目,作为战略上的平衡。
在东亚及亚太区域的延伸邻国(Extended Neighbourhood)方面,印度借助美国的“印太战略”,推进印度版的印太战略。尽管印度试图以“战略自主”来掩饰其在亚太地区的多向结盟政策,但其外交政策越来越偏离了自主方向。印度在军事防务上逐步同美日澳的印太战略捆绑在一起。2016年8月印美签署《后勤交流备忘录协定》(LEMOA) 、2018年9月签署《通信兼容和安全协议》(COMCASA)、2020年10月签署《基础交换与合作协议》(BECA)、2020年印澳签订《相互后勤支持协定》(MLSA)以及印日签订《相互提供物资与劳务协定》(ACSA),再加上美日澳彼此之间签订的相关协议,美印日澳四国之间构建了一个以共享军事基地和后勤相互支持为主要内容的防务体系,标志着相关国家在地区军事合作问题上迈出了实质性步伐,对现有地区安全秩序产生了影响。
简言之,在大变局中,印度将自己重新定位为世界领导型大国,以多向结盟为外交核心理念,并据此在国际多边外交、大国外交和周边外交中突出积极性、主动性、进攻性的一面。这一战略调整是冷战结束后印度外交战略的一次重大转变。
印度外交战略调整及其影响
纵观印度自1947年独立以来的外交政策,大致可以分为6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47—1962年,这是印度外交的不结盟阶段。印度在美苏两极的世界里保持等距离外交,并在国际舞台上积极为广大亚非拉国家发声。在此期间,印度不仅获得了较高的国际地位,也得到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同时拉拢。第二阶段是1962—1971年,这是印度逐渐抛弃不结盟、走向现实主义结盟的阶段。1962年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之后,印度转向美国寻求军事保护,并于1964年与美国签订了防务条约。但随着美国约翰逊政府、尼克松政府相继看轻印度的战略重要性,加上印度内政变化,美印双边关系很快遇冷。第三阶段是1971—1991年,印度与苏联结成事实上的联盟,[9]并积极推进地区“门罗主义”。印度不仅肢解巴基斯坦,吞并锡金,还出兵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牢牢确立了地区霸主地位。第四阶段是1991—1998年,印度因“无盟可结”,不得不选择战略自主。1991年对印度外交来说是最具灾难性的时刻,苏联解体以及俄罗斯向西方靠拢,降低了俄印结盟的战略重要性,印度自1971年以来的外交基础消失了。更具挑战性的是,1971年以来,与苏联结盟的印度就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处于较为对立的位置。为此,1991年开始,印度在保持与俄罗斯关系的同时,逐步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接触,并与中国主动交好。[10]1992年,印度正式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通过借助美以关系来打开改善同美国关系的大门。[11]第五阶段是1998—2014年,印度逐渐找到了一个平衡大国的定位,在各种议题上同各个大国合作并左右逢源。[12] 2005年7月,时任印度总理辛格访问美国,印美发表了《民用核能合作联合声明》,两国关系实现了较大转圜。同时,印度保持了同俄罗斯的传统战略关系,还改善了与中国的关系,并逐步融入东亚经济圈。上述外交成果,加上印度在经济上的崛起,给莫迪政府打下了奉行多向结盟的政策基础。第六阶段则是2014年莫迪执政至今,印度明确以领导型大国定位推进外交战略。
莫迪政府的这一外交战略调整,延续了冷战结束后印度外交战略转变的基本趋向。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印度外交战略指导思想发生了五个方面的变化:一是从国内封闭的计划经济转向面向全球化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二是对外政策转向服务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三是抛弃“第三世界主义”和一直潜藏的不结盟情结;四是拒绝反西方主义,并开始拥抱西方;五是理想主义逐步退却,并淡化了外交说辞中的道德主义色彩。[13]
印度外交战略开始从不结盟走向结盟、从战略自主走向多向结盟。印度方面认为,不结盟政策通常呈现的是犹豫不决、模糊和超脱的姿態,那样得罪各方的风险更大,一个期望成为领导型大国的国家在变动的世界中不能够一直墨守成规,将成规抛弃是印度开启领导型大国征程的起点。[14]多向结盟基于现实主义,并在准确把握国际大势的同时,认清机遇与挑战以及最大化自身选择空间,更重要的是敢于冒险。[15]冒险不仅是外交政策取向,也是实现大国雄心的必要组成部分,低风险的外交只能带来有限的回报。[16]
多向结盟政策可以说是印度试图保持自主性的一种战略对冲方式。事实上,它并非没有政策偏好,而是有清晰的国别地区政策,归结起来包括:交好美国、应对中国、深耕欧洲、安抚俄罗斯、调动日本、整合邻国、影响更广泛的周边、扩大传统的支持者。[17]就大国关系而言,印度不是在各个大国之间进行等距离外交,而是有明确的战略诉求。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印度外交战略的主要目标之一是与其他国家携手平衡并牵制中国的崛起。印度方面认为,中国崛起带给印度巨大挑战,主要包括双边领土边界争议长期存在、中国在印度周边地区的影响力不断上升、印度对华贸易逆差拉大两国经济差距以及双方在全球治理问题上的矛盾逐渐凸显。[18]因此,在中美战略竞争越发激烈之际,印度对中国进行战略遏制的表现日益明显。例如,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印度不仅试图在生产链、供应链方面抢占中国的国际市场份额,甚至同美国等西方国家共同打压中国的高科技企业,其外交战略中针对中国的意图凸显。
同时,在推进印太战略方面,印度也有自身的打算。印度前外交秘书顾凯杰认为,在亚太区域内,中国在贸易、技术和金融领域有建立独立于美国的“平行世界”的可能性,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正在构建以自身为中心的完整体系。[19]对于印度而言,一方面不愿看到中国实力和影响力逐渐增强,另一方面强调只有构建多极亚洲,印度在全球中的战略重要性才能得到彰显。正是基于这一战略诉求,印度不断地配合美国并升级其印太战略。
在大变局背景下,印度的外交战略调整延续了其冷战结束后外交理念的转变过程,增加了战略上的主动性和冒险性,并充分表现出利用国际格局变动的契机壮大自身力量的意图。在国内政治议程上,印度不会轻易接受国际社会的压力,会不断彰显自身的民族主义和大国自信。就国际影响而言,印度外交战略的变化使得国际社会多了一个更加积极进取甚至敢于冒险的玩家。
整体而言,印度多向结盟战略仍然有别于“一边倒”或者清晰的结盟政策,其仍然在宏观战略上保持了一定的模糊性,以便从大国战略竞争中渔利,在同各大国谈判中获得最大议价空间。不过,正因为如此,印度外交战略也时刻面临着如何取得平衡的问题,这对印度方面的外交操作能力提出较高的要求。印度多向结盟战略虽然并没有明确将中国视为对手,但其实质上正在不断加大对中国的战略平衡和牵制,并且毫不忌惮地在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谋利,即在经济上试图逐步取代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地位,战略上拉住美国以对中国形成长期消耗,同时稳住俄罗斯,使其不与中国更加走近。在印度相关战略趋向的影响下,后疫情时代的中印关系将面临更多不确定性。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建立全方位的中印战略互信研究”(项目批准号:19ZDA139)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苏童)
[1] S. Jaishankar, The India Way: Strategies for an Uncertain World, Noida: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2020.
[2] 苏杰生是莫迪最为欣赏的外交官。在莫迪第一任期(2014-2019年)时,时任印度驻美大使的苏杰生成功安排莫迪访美(2014年9月)和奥巴马访印(2015年1月)而得到莫迪的高度赏识。就在他即将退休前两天,印度总理办公室任命他为印度外交部的外秘,为此不得不让当时的外秘苏嘉塔·辛格(Sujatha Singh)提前退休。苏杰生担任外秘3年(2015-2017年),超龄延期一年。在2019年5月莫迪赢得第二次大选后,旋即任命苏杰生为外长。这无不显示出苏杰生与莫迪在外交理念上的契合。
[3] 同[1],p.3。
[4] 同[1],p.38。
[5] 同[1],p.33。
[6] Menon Shivshankar, “Indias Foreign Affairs Strategy,” Brookings Institution India Center, May 2020, https://www.brookings.edu/wp-content/uploads/2020/05/India27s-foreign-affairs-strategy.pdf.
[7]同[1],pp.26-33。
[8] NITI Aayog, “Strategy for New India at 75,” January 2019, http://niti.gov.in/sites/default/files/2019-01/Strategy_for_New_India_2.pdf.
[9] 同[1],p.26。
[10]同[1],p.88。
[11] Sumit Ganguly and Rahul Mukherji, India Since 198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25.
[12] 同[1],pp.75-78。
[13] C. Raja Mohan, Crossing the Rubicon: The Shaping of Indias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Palgrave, 2004.
[14] 同[1], p.105。
[15] 同[1],p.26。
[16] 同[1],pp.97-101。
[17] 同[1],p.10。
[18] D. Jaishankar, “Acting East: India in the Indo-Pacific,” Brookings Institution India Center, October 2019, https://www.brookings.edu/wp-content/uploads/2019/10/Acting-East-India-in-the-INDO-PACIFIC-without-cutmark.pdf.
[19] Vijay Gokhale, “Chinas Vision of Hegemony: the View from India,” February 2021, https://www.aspistrategist.org.au/chinas-vision-of-hegemony-the-view-from-ind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