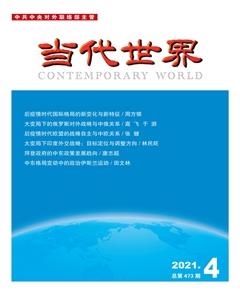拜登政府的中东政策发展趋向
唐志超
【关键词】拜登政府;美国中东政策;伊朗核问题
【DOI】10.19422/j.cnki.ddsj.2021.04.005
自上任以来,拜登政府在中东地区采取了一系列新动作、新举措,引起外界对美国新政府中东政策走向的普遍猜想。从拜登本人及其团队的发言表态和已采取的政策举措看,拜登政府将延续前两任政府从中东进行战略收缩的政策,聚焦结束战争、达成新伊核协议和推行价值观外交三大任务,以恢复美国在中东的领导力和信誉。不过,拜登政府要想实现这些政策目标,前景并不乐观。
拜登政府中东政策的主要内容
自就任以来,拜登政府已就中东问题多次发声,在进行政策宣示(主要是针对伊朗核问题)的同时,还烧了“五把火”:一是宣布愿意重返伊核协议;二是宣布结束也门战争,停止支持沙特的进攻性军事行动;三是空袭叙利亚境内受伊朗支持的什叶派民兵,强硬回应驻伊拉克美军基地遭袭;四是公布沙特记者卡舒吉遭杀害的美国情报评估报告,指控沙特王储穆罕默德,并对相关人员实施制裁;五是叫停对沙特和阿联酋的军售。这五大行动既有被动回应之举,也体现了主动谋划之意。
在拜登政府看来,当前美国在中东面临的主要挑战涉及四个层面:一是中东地区持续动荡,美国因领导力缺失而在该地区的声望和信誉有所下降。美国在中东地区实施战略收缩,其留下的权力真空被各种势力填补,这进一步加剧了地区动荡,进而动摇美国的地位。二是美国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使得中东地区面临的威胁不断增大。美伊关系日趋紧张且对抗持续升级,严重影响美国战略东移。伊朗以部分不履行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作为回应,加快核技术的发展步伐,日益逼近“拥核”门槛,美国的紧迫感骤然上升。伊核问题导致中东地区核扩散形势日益严峻,沙特、土耳其、阿联酋、埃及等国也纷纷加快了核技术的发展步伐。三是地区“民主化”进程和“人权”状况出现“倒退”,人道主义危机严重。特朗普政府在这方面的政策以及美国地区盟友的“独裁化”趋向损害了美国的国际形象,并对西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产生威胁。四是中东地区冲突不断,“无休止的战争”牵扯了美国大量的精力、人力和资源,使得美国始终难以摆脱中东泥潭,进而迟滞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拜登明确指出,“在无法取胜的冲突中固守根基,只会削弱我们在其他需要我们关注的问题上发挥领导作用的能力,也会阻碍我们运用重建美国力量的其他工具。”[1]
基于对中东地区挑战的基本认识,拜登政府明确了中东政策的基本目标:纠正特朗普政府的中东政策,恢复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领导地位和信誉;结束中东战争;确保核不扩散,重新与伊朗达成核协议;捍卫“民主”和“人权”;维护地区盟友的安全。围绕这些目标,拜登政府中东政策将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结束战争。拜登多次明确指出要从阿富汗和伊拉克撤军,只保留少部分兵力用于反恐,同时提出了结束也门战争的新任务。二是聚焦伊核问题,与伊朗重新谈判,以达成新的伊核协议。三是推行价值观外交。以下围绕具体地区问题来分析拜登政府的政策趋向。
一是伊朗问题是拜登政府中东政策的重中之重。奥巴马政府将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视为最大外交成就,特朗普政府则称之为“史上最糟糕的协议”并退出该协议,同时恢复和加强了对伊制裁。对拜登政府而言,伊朗问题具有多重意义,不仅事关核扩散和美国全球战略调整,而且关乎美国国际形象,还涉及奥巴马政府的外交遗产以及美国国内两党政治斗争。拜登政府多次明确提出,如果伊朗遵守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美国将重返该协议;宣布允许伊朗动用在韩国的资产缴纳联合国会费;同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伊朗贷款助其缓解新冠肺炎疫情。目前看,美国重返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仍存在诸多障碍:美伊两国为谋取谈判筹码相互较劲、加大对抗,谁也不肯率先让步;美国不仅未首先解除部分制裁释放善意,反而提出新条件,希望达成新的伊核协议,而不是简单重返旧协议;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盟友以色列和沙特强烈反对拜登政府的伊朗政策,反对美国重返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并要求将弹道导弹和所谓伊朗破坏地区稳定两大议题纳入谈判。为威逼拜登政府并恫吓伊朗,以色列还释放出军事打击伊核设施的强硬信号。
二是在也门问题上以结束战争为主要目标,缓解也门的人道主义危机。近年来,也门战争在美国国内的关注度日益提升,主要归于四个因素:沙特发动也门战争事先未与美国协商;战争造成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和大量平民死伤,酿成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战争导致也门陷入长期动荡,恐怖主义势力抬头,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特朗普及其女婿库什纳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的关系过于亲密。拜登以及民主黨人一直对沙特主导的也门战争持批评态度,指责特朗普政府支持沙特的军事行动,呼吁结束也门战争,停止对沙特军售。拜登在上任后的首次重要外交政策讲话中明确提出要结束也门战争,强调战争造成了“人道主义和战略灾难”。拜登政府宣布了一系列措施以推动结束战争,包括支持联合国领导的停火以及恢复和谈的倡议 ;任命职业外交官蒂姆·伦德金为也门事务特使,推动外交解决也门问题;撤销特朗普政府对胡塞武装的“恐怖组织”认定;要求交战各方停止侵犯平民的行为;宣布停止对沙特在也门进攻性军事行动的支持;暂时叫停对沙特和阿联酋的军售;宣布新增1.91亿美元人道主义援助,使2021年美国对也门的援助达到3.5亿美元。
三是推行价值观外交,关注“民主”与“人权”问题。拜登政府将“民主”“人权”问题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与奥巴马、特朗普两届政府有着明显不同。针对“民主”在全球范围内“退却”,拜登发誓将采取一系列步骤来“纠正”外交政策,把“民主”价值观与外交领导力更好地结合起来。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更被视为奉行自由主义的国际干预派,在“民主”和“人权”问题上十分强硬。拜登和布林肯多次发声批评伊朗、埃及、沙特和土耳其等国的民主人权政策。2019年12月,拜登指责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是“独裁者”,甚至呼吁“支持土耳其反对派领导层通过选举击败埃尔多安”。[2]2020年7月,拜登发推特批评埃及政府“逮捕、拷打、驱逐人权活动分子或威胁他们的家人是不可接受的”,声称“再也不能对特朗普‘最喜爱的独裁者开空白支票了”。2020年10月,布林肯称拜登政府计划对美国和沙特关系“进行战略评估”,“以确保这一关系真正推进了我们的利益,符合我们的价值观”。[3]
拜登上任后,在“民主”“人权”问题上向中东地区国家发出了一系列强硬信号:宣布结束对也门战争的支持;公布被特朗普一直扣押的卡舒吉遇害案调查报告,指控沙特王储是责任人并对沙特实施制裁;批评土耳其政府镇压博斯普鲁斯大学抗议活动;在与土耳其、埃及、沙特等国领导人和外长通话时强调“民主”“人权”问题的重要性,并要求对方改变政策。布林肯和沙利文在与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和土耳其总统首席顾问卡林通话时表达了拜登政府对支持民主制度和法治的广泛承诺以及民主体制、包容性治理和尊重“人权”的重要性。[4]布林肯在与埃及外长舒克里通话时指出,“人权”问题是美埃关系的“中心问题”。拜登政府对沙特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立场更为强硬。拜登致电沙特国王萨勒曼时强调了“美国对普世人权和法治的重视”。[5]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莱斯称,美方已向沙特领导人明确指出,“人权”问题会破坏美沙关系和两国间合作。美国公布卡舒吉案旨在“重新校准”美沙关系,确保此类犯罪不再发生,并使两国关系在“正确基础”之上实现可持续发展。美国强调将督促沙特继续改革,释放“人权”分子。
四是巴以问题将重回旧轨道,拜登难以全盘否定特朗普的中东政策。特朗普是近70年来最亲以色列的美国总统,在“两国论”、耶路撒冷地位、定居点、戈兰高地归属、美国驻以大使馆迁馆、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地位、对巴勒斯坦援助等问题上,突破了美国历届政府的诸多政策红线,从根本上动摇了巴以和平以及中东和平进程的根基。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主导的“世纪协议”对以色列一边倒,将约旦河西岸约三分之一的土地划归以色列。拜登对特朗普的巴以政策持批评态度,指责特朗普削弱和破坏了中东和平进程。拜登政府或将继续坚持“两国论”,在耶路撒冷地位、定居点、戈兰高地等问题上回归传统立场,恢复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地位并继续提供援助。不过,拜登政府也明确表示不会再将大使馆从耶路撒冷迁回特拉维夫,对阿以关系正常化也予以肯定。总体上,鉴于巴以问题边缘化趋势和巴以僵局日益难以破解,拜登政府可能不会在该问题上投入过多精力,除政策宣示外,恐难有所作为。
五是在叙利亚问题上将继续维持美军小规模存在,加大对反对派的政治支持,但不会大规模军事介入。拜登对奥巴马政府的叙利亚政策基本持支持态度,不愿大规模军事介入,对推翻叙利亚巴沙尔政府心存顾忌。拜登政府批评特朗普政府不负责任地从叙撤军、放弃叙反对派、容忍俄罗斯主导叙利亚事务、纵容土耳其镇压美国的反恐盟友库尔德武装,还批评土耳其、沙特、卡塔尔和伊朗等地区国家在叙利亚搞代理人战争。拜登政府提出要加大支持叙利亚反政府组织参与叙利亚政治进程的力度,提高美国的地位和影响,避免叙利亚问题被巴沙尔政府和俄罗斯完全主导。美国副总统哈里斯称,拜登政府将与叙利亚公民社会和支持“民主”的伙伴站在一边,为“叙利亚人民有发言权”的政治解决方案而努力。拜登政府将继续保持在叙利亚的驻军,继续支持库尔德武装。2021年2月27日,拜登下令空袭叙利亚,但意在威吓伊朗,无意扩大对叙利亚的军事干预。
此外,在利比亚、东地中海、伊拉克等地区问题上,拜登政府也将投入更多精力,力求发挥更重要作用。
拜登政府中东政策是奥巴马政府中东政策的“2.0版”
拜登以及布林肯、沙利文等人皆是奥巴马政府的旧臣,曾在奥巴马政府中东政策制定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他们主张淡化反恐色彩,强化多边主义和对话外交,避免对中东地区进行大规模军事干预,强调与伊朗达成核协议等。因此,拜登政府将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与发展奥巴马政府的中东政策,并且要纠正特朗普政府在中东地区问题上推行的有损美国领导地位和利益的政策,实现美国中东政策的“去特朗普化”。不过,三届美国政府的中东政策虽然个性鲜明、差异不小,但共性也较为明显,都强调战略收缩、避免再次卷入中东地区的大规模军事冲突。美国中东政策的避战慎战怕战心态日益凸显。
奥巴马执政时期,对美国的外交政策进行战略性调整,提出要结束小布什政府开启的全球反恐战争,把主要精力转移到应对中国崛起上来,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因此在中东地区进行战略收缩。奥巴马政府的中东政策基本可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结束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并从中东撤军,以改善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二是缓和与伊朗的矛盾,与伊朗达成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三是推行多边主义,强调发挥“幕后领导”作用,督促盟友承担更大责任;四是降低“民主”在其中东政策中的地位,结束对中东的“民主改造”。奥巴马政府认为,其最大外交成就之一就是于2015年与伊朗达成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奥巴马本人还因推崇多边外交和在中东促进和平的努力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但是,奥巴马政府也因其中东政策而饱受质疑,反对者批评他为收缩而收缩,在中东“不作为”:对伊朗采取绥靖政策;在支持英法推翻利比亚卡扎菲政权后对利比亚弃之不顾;放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崛起;应对“阿拉伯之春”不力等。特别是2012年极端分子杀死美国驻利比亚大使克里斯托弗·史蒂文斯被视为奥巴马和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外交上的“滑铁卢”。
特朗普政府虽然表面上推行“去奥巴马化”的中东政策,但在精神上却继承了奥巴马政府中东政策的衣钵,即“结束中东战争,从中东战略收缩”。特朗普政府坚持“美国优先”理念,推行孤立主义和保守主义,自私自利特征鲜明,在国际上四處“退群”,并且明确表示不想承担国际领导者责任,不愿继续充当“全球警察”,这在其中东政策上表现得最为明显。特朗普政府力避卷入中东冲突,虽多次遭遇伊朗的重大挑战但仍竭力避免与伊朗发生大规模军事对抗,不顾美国军方和盟友的反对两次急切宣布从叙利亚和伊拉克撤军,对也门战争、利比亚战争、叙利亚战争、东地中海危机、卡塔尔—沙特外交危机等地区热点问题大都置身事外,更无意关注中东地区的“民主”“人权”和国家建设问题,大幅削减对地区国家(以色列除外)的援助。特朗普的中东政策以战略收缩为中心,以维护以色列的安全和孤立、打击伊朗为重点,带有明显的内卷化、个人化、利益化(兜销军火)和“以色列化”的特征。特朗普政府的中东政策可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恢复并加大对伊制裁,全面遏制伊朗;二是在巴以问题上推出严重偏袒以色列的“世纪协议”,推动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和解;三是增兵伊拉克和叙利亚,加大对“伊斯兰国”的打击力度;四是积极向海湾国家兜售军火,让地区盟友为反恐买单,以谋取经济实惠。与奥巴马政府相似,特朗普政府将其中东政策视为任内最大的外交亮点之一,如击垮“伊斯兰国”;促成《亚伯拉罕协议》签署,推动以色列与阿联酋、巴林、苏丹和摩洛哥四个阿拉伯国家实现关系正常化;推动以色列与沙特、阿联酋等国建立“中东战略联盟”,组建反伊朗的地区阵线。然而,与奥巴马政府一样,特朗普政府的中东政策也在美国内外招致广泛批评:在伊朗问题上,不顾国际社会反对,执意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恢复并持续加码对伊朗的制裁,不仅未达到让伊朗屈服的目标,反而加剧了美伊对抗,引发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在巴以问题上严重偏袒以色列,在“两国论”、耶路撒冷地位、戈兰高地归属、非法定居点、边界划分等重大问题上采取了一系列打破常规、颠覆国际社会共识的行动,如承认以色列对耶路撒冷、戈兰高地的主权并将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由特拉维夫迁至耶路撒冷,承认以色列建设的大部分非法定居点的合法地位,断绝与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交往;颁布“穆斯林禁令”,公开歧视伊斯兰国家,等等。
总体而言,拜登政府将大体延续奥巴马政府的中东政策,但也会依据形势发展作出相应调整。拜登和布林肯都一再强调,时代和环境已发生改变,政策需因时而变。这既是拜登与民主党人必须与特朗普进行切割的政治需要,也是美国的国际国内环境剧烈变化使然。拜登认为,特朗普上台后,美国的国际信誉和影响力都不断下降。特朗普贬低、削弱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抛弃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在应对来自中国、俄罗斯、朝鲜、伊朗、叙利亚、阿富汗、委内瑞拉等国的安全挑战上几乎没有任何表现,放弃了美国动员盟友集体行动以应对新威胁的领导地位,背离了美国的民主价值观。[6]
2021年3月3日,拜登政府颁布了《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方针》,指出“我们的世界正处于一个拐点。全球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需要关注新的危机”。“我们不能假装世界可以简单地恢复到75年前、30年前甚至4年前。在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方面,就像在国内政策方面一样,我们必须制定新的路线。” [7]《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方针》列出了当前美国面临的一系列挑战: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和其他生物风险、不断升级的气候危机、网络和数字威胁、国际经济中断、旷日持久的人道主义危机、暴力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以及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等。对拜登政府而言,当前最主要的问题是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拯救因疫情而陷入困境的美国经济、恢复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和信誉。就外交政策而言,拜登政府的中心任务是恢复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让美国重新回到世界舞台的中心并发挥领导作用,扭转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式微趋势。拜登上任后首个重要外交政策讲话的主题就是如何恢复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8]
从拜登政府的全球战略布局看,印太地区仍将是其全球战略的重心,欧洲的地位也明显回升,但中东地区不是优先选项。2020年美国大选时,拜登的竞选纲领中有三处提及中东:一是停止“无休止的战争”;[9]二是核扩散问题,其中核心之一是伊朗核问题,提出要重返伊核协议;三是与盟友关系,明确提出确保以色列的安全。而2021年3月3日,布林肯在其上任以来首场重要讲话中列出的拜登政府八大外交重点并未触及中东地区,只是点出了美国为军事干预中东地区付出的代价过高,但也提及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是奥巴马政府取得的两大外交成就之一。
近年来,美国国内已基本就中东地区形势达成三点共识:一是不应该在中东地区发动新战争;二是不应通过大规模军事干预来推动反恐和促进“民主”;三是中东对美国的战略价值已经下降,美国应将全球战略的重点转向大国竞争,而非继续深陷中东泥潭。虽然目前美国国内围绕中东地区对美国是否还有战略价值、美国应该在多大程度上撤离该地区这两大问题上仍有争论,但主要是做多做少的问题。因此,拜登政府中东政策的总基调仍是战略收缩,这是由美国全球战略调整以及美国在中东利益下降所决定的,不会因政府更替而发生变化。2021年2月17日,拜登在上任后第三周才与其在中东地区最紧密的盟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2月24—25日才分别与伊拉克总理卡迪米、沙特国王萨勒曼通话,迄今尚未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穆罕默德、埃及总统塞西三位领导人通话。这既传达了拜登对中东地区领导人的复杂情感,也反映了其希望与中东地区保持距离的心态。
概而言之,拜登政府既要回归奥巴马政府中东政策的基本路线,但又不会全盘继承,比如拜登政府强调要加大在中东地区“民主”“人权”问题上的干预;虽然强调“去特朗普化”,但又难以与特朗普政府的中东政策遗产做彻底切割。奥巴马政府中东政策的缺陷是理想主义色彩过重,过于担心继续深陷中东泥潭和与“伊斯兰世界”关系恶化,对中东地区局势的干预犹豫不决。与之相较,布林肯强调强硬外交,支持对利比亚的军事干预,主张向叙利亚反政府武装提供武器装备,认为“若事关阻止暴行,应实施强硬外交政策”。特朗普政府中东政策的缺陷则是孤立主义和功利主义色彩太浓,个人化外交取代了机制化外交,加上特朗普本人行事鲁莽、作风粗暴,美国中东政策的传统和基石遭到破坏,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信誉和形象一落千丈。除了理论和路径差异外,作为后来者的拜登对前两届政府的政策得失也有比较深入的认识,将会从中汲取教训。
拜登政府中东政策的前景
拜登政府的中东政策侧重于防止核扩散、价值观外交,有选择地恢复美国在地区事务中的领导地位。目前,除利比亚局势有所缓和外,中东地区其他冲突并无明显停息迹象。也门战争不仅未停,反而有所扩大,美国与伊朗依然处于僵持之中,双方剑拔弩张。各方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博弈加剧,红海和地中海的地区角逐依然非常激烈。未来,拜登政府能否如期从中东实现战略收缩、完成在中东地区三大任务(结束战争、重返伊核协议、推行价值观外交)的前景并不乐观。拜登政府的中东政策面临着一系列内外挑战。
第一,美国的精力与能力问题。在聚焦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大国竞争和振兴经济三大任务的背景下,拜登最终能拿出多大精力投入到中东地区是个疑问。另外,自奥巴马政府以来,美国掌控、塑造和影响中东能力的持续下降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维持美国在中东地区领导地位的重要支柱——地区盟友体系也已遭重创。
第二,美国国内政治的巨大掣肘。美国国内政治极化和外交内卷化日益严重,拜登政府希望恢复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可能是一厢情愿。同时,民主党在参众两院优势并不明显。除了共和党人的反对外,民主党内部、犹太人在议会之外的游说集团以及左翼团体对拜登政府中东政策的制订和实施也形成了巨大制约。如在对伊朗、土耳其、沙特和以色列的政策上,拜登政府就面臨来自党内外的巨大压力。再如,拜登下令军事打击叙利亚境内目标在美国国内遭遇强烈反弹,面临来自国会要求限制总统对外动武的巨大压力。
第三,美国与中东地区盟友和伙伴的利益与政策分歧日益加大。当前,美国与沙特、土耳其、以色列三国矛盾最为突出。来自以色列的挑战主要在巴以问题、伊朗核问题上;来自沙特的挑战主要在伊朗问题、也门战争、“民主”“人权”政策上;来自土耳其的挑战主要在于库尔德问题、东地中海问题、“民主”“人权”问题和土俄关系等。美国与中东地区盟友关系的疏离既是全球大变局和美国的全球战略大调整使然,也是中东变局下地区国家战略自主性不断增强的结果,这不是拜登政府所能改变的。
第四,拜登政府的中東政策缺乏新意,既难为美国解套,也无助于解决中东地区问题和缓解地区动荡局势。布林肯强调,美国不再会用军事干预来推进“民主”,简单地将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失败归因于动用军事手段太多。沙利文提出,军事失败后“民主”将成为美国在中东地区取得成功的机会。[10]这些认识反映出拜登政府对美国在中东的失败依然没有根本反思,在思想理念和方法路径上都无重大创新性突破,并且没有认识到美国中东政策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霸权主义政策和过时的教条思维。美国国内已有学者警告拜登不要重演当年卡特在中东推行“民主”导致伊朗巴列维政权垮台、美国在中东地区安全利益严重受损的那一幕。[11]2021年2月,兰德公司发布的研究报告建议美国政府重塑中东政策,将长期以来拉一派打一派的策略转向减少冲突与紧张局势,支持增长与发展;将长期过度重视军事和制裁转向投资经济、治理、外交和以人为本的项目。[12]
结语
拜登政府上台至今,在作出中东政策宣示的同时也采取了一系列行动。从结果看,拜登政府的政策宣示与实际行动之间存在不小差距,政策并未到位,成效也不明显,这与其执政时间长短并无必然联系,实际上是由美国中东政策的内在矛盾决定的。在伊朗问题上,美国一方面宣布要重返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缓和与伊紧张关系;另一方面又强调要遏制伊朗,打击伊朗破坏地区稳定的行为,阻止伊朗发展弹道导弹。这不但没有使美伊之间的紧张关系降级,双方还在伊拉克、叙利亚爆发了间接军事冲突。在价值观外交上,拜登政府虽然调门较高,但跟特朗普政府一样继续“开空头支票”,一方面宣布停止支持沙特在也门的进攻性军事行动,向沙特施压结束也门战争,另一方面宣布继续支持沙特的防御性军事行动;一方面公布卡舒吉案调查报告,指责沙特王储应对卡舒吉遇害负责,另一方面又不敢针对沙特王储实施制裁,只象征性地采取其他制裁措施。在埃及“人权”问题上,拜登政府在对其表示关切的当日宣布向埃及出售价值1.97亿美元的导弹,声称例行军售“丝毫不会阻止我们继续坚持对民主和人权的关注”。为此,拜登政府刚上任就在美国国内遭到不少批评。这种内在矛盾反映出美国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价值观与利益、长远挑战与当前威胁及国内两党理念政策相互冲突的传统难题。
中东事务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突发性。奥巴马和特朗普两届政府都致力从中东进行战略收缩,但实际上无时无刻不被中东事务缠身,耗费大量精力和资源。拜登政府延续了前任的大国竞争战略,聚焦印太地区,亦希望从中东地区实现战略收缩,但拜登恐怕亦难逃其前任的历史宿命。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约翰·博尔顿在其自传中吐槽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被迫每天应付来自中东的各种危机。2021年3月初,英国《经济学人》刊文称,前两任美国总统都认为美国过度卷入中东事务,希望摆脱中东,但中东拒绝让其离开,拜登政府同样如此。[13]这应该是对拜登政府中东政策较为中肯的评价。
(责任编辑:甘冲)
[1] Jr. Joseph R. Biden, “Why America Must Lead Again, Rescuing U.S. Foreign Policy After Trump,”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20,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0-01-23/why-america-must-lead-again.
[2] “Turkey Condemns Bidens Criticism of ‘Autocrat Erdogan,” Al Jazeera, August 16 2020,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0/8/16/turkey-condemns-bidens-criticism-of-autocrat-erdogan.
[3] Jacob Magid, “Top Biden Foreign Policy Adviser ‘Concerned Over Planned F-35 Sale to UAE,” The Times of Israel, October 29, 2020.https://www.timesofisrael.com/top-biden-foreign-policy-advisor-concerned-over-planned-f-35-sale-to-uae/.
[4] “Secretary Blinkens Call with Turkish Foreign Minister ?avu?o?lu,” State.Gov, February 15, 2021, https://www.state.gov/secretary-blinkens-call-with-turkish-foreign-minister-cavusoglu/.
[5] “Readout of President Joseph R. Biden, Jr. Call with King Salman bin Abdul-Aziz Al-Saud of Saudi Arabia,” State.Gov, February 25,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2/25/readout-of-president-joseph-r-biden-jr-call-with-king-salman-bin-abdulaziz-al-saud-of-saudi-arabia/.
[6] 同[1]。
[7] “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 March 03,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3/03/interim-national-security-strategic-guidance/.
[8] Jr. Joseph R. Biden,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on Americas Place in the World,” February 04, 2021, https://joebiden.com/AmericanLeadership/.
[9] 同[1]。
[10] Daniel Benaim and Jake Sullivan, “Americas Opportunity in the Middle East”, Foreign Affairs, May 22, 2020,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middle-east/2020-05-22/americas-opportunity-middle-east.
[11] Christina Pazzanese, “Biden May Regret Releasing Report on Khashoggi Murder,” Harvard Gazette, February 27, 2021, https://news.harvard.edu/gazette/story/2021/02/biden-may-regret-releasing-report-on-khashoggi-murder-says-expert/.
[12] Dalia Dassa Kaye, Linda Robinson, Jeffrey Martini, Nathan Vest, Ashley L. Rhoades, “Reimagining U.S. Strategy in the Middle East,” February 23, 2021, https://www.rand.org/pubs/research_reports/RRA958-1.html.
[13] “Can Joe Biden Get America Out of the Middle East?” Economist, March 03, 2021, https://www.economist.com/united-states/2021/03/03/can-joe-biden-get-america-out-of-the-middle-ea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