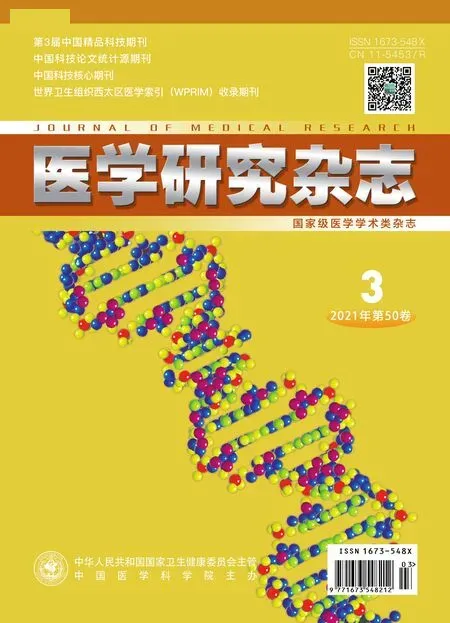宫颈癌肿瘤相关巨噬细胞的研究进展
彭思可 蔡 晶 张 媛
宫颈癌(cervical cancer,CC)是世界范围内第2常见的女性生殖道恶性肿瘤,发生率逐年上升,发病年龄趋于年轻化。尽管宫颈癌疫苗、根治性手术和放化疗已广泛用于预防和治疗宫颈癌,但全球每年仍有50多万新增病例[1]。耐药、复发和转移是病死率高的主要原因,这与肿瘤微环境(tumor microenvironment,TME)有关。TME主要由肿瘤细胞、骨髓源性细胞和宿主间质细胞组成,它们相互作用,形成免疫抑制微环境,从而促进肿瘤进展[2]。众多研究表明,肿瘤相关巨噬细胞(tumor-associated macrophages,TAMs)在宫颈癌进展中起关键作用,并在肿瘤细胞增殖、侵袭、血管生成、免疫抑制等方面与不良预后相关。本文将对巨噬细胞的来源和分类、宫颈癌中参与TAMs形成和活化的分子、巨噬细胞的生物学标志物、TAMs上PD-1的表达情况以及在CC研究中针对TAMs治疗的研究现状展开综述。
一、巨噬细胞的来源与分类
1.组织驻留巨噬细胞:参与宫颈癌病理生理过程的巨噬细胞有两种:组织驻留巨噬细胞和浸润巨噬细胞。在胚胎器官发育过程中,来自卵黄囊和胎儿肝前体细胞的巨噬细胞驻留在正常、未受伤或发炎组织的上皮内或上皮上[3]。这些巨噬细胞作为常驻的、自我维持的群体存留至成年。出生后,骨髓或脾脏来源的单核细胞可在损伤、感染或炎性反应后补充组织驻留的巨噬细胞。组织驻留的巨噬细胞被认为是分化的单核细胞,其驻扎在组织中执行免疫哨兵和维持稳态的功能。然而,组织驻留的巨噬细胞并不是一个同质群体,而是一组具有相似功能和表型的细胞。目前已有研究证明,组织环境本身是巨噬细胞表型的主要控制因子,并且可以影响巨噬细胞许多基因的表达,而不受其来源的影响[4]。这些巨噬细胞在调节代谢和介导免疫炎性反应中发挥重要作用。骨破骨细胞、脑小胶质细胞、肝脏中的库普弗细胞和肺泡巨噬细胞具有共同的功能,但也高度适应于它们的器官特异性用途[5]。
2.浸润巨噬细胞:与组织驻留巨噬细胞不同,浸润巨噬细胞来源于骨髓,它们的寿命相对较短,需要从循环单核细胞中不断补充。循环单核细胞被多种炎性介质招募到肿瘤、炎症或感染组织中,从而获得浸润巨噬细胞的特性。与组织驻留巨噬细胞相似,浸润巨噬细胞可以感知局部环境的变化,并分化为特异性巨噬细胞群,促进组织稳态、免疫和炎症。肿瘤免疫抑制微环境破坏了新招募单核细胞的正常生理功能(抗原递呈和细胞毒性功能),使其分化为肿瘤相关巨噬细胞(TAMs)。组织中单核细胞来源的巨噬细胞在经历生长因子、代谢需求、局部氧张力、组织细胞和基质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后往往具有高度的异质性[5]。浸润巨噬细胞主要分为M1型和M2型。Th1细胞因子IFN-γ、IL-2、IL-3、IL-12、TNF-α、细菌成分如脂多糖和Toll样受体(TLR)激动剂等可诱导M1型巨噬细胞的极化[6]。M1型巨噬细胞分泌促炎性细胞因子,如IL-1β、IL-6、IL-12、IL-23、iNOS、TNF-α、CXCL-9和CXCL-10等,并表达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Ⅰ类(MHCⅠ)和Ⅱ类(MHCⅡ)分子[7]。因此,M1型巨噬细胞参与炎性反应和抗肿瘤免疫。相反,M2型巨噬细胞由Th2细胞因子IL-4、IL-10、IL-13、TNF-α、TGF-β、GM-CSF、免疫复合物和TLRs等诱导形成,分泌多种抗炎性细胞分子,如IL-4、IL-13、IL-10、TGF-β、维生素D3、糖皮质激素和精氨酸酶1等,发挥抗炎和促肿瘤活性[6,8]。巨噬细胞可以同时具有杀瘤和致瘤的特性,这取决于细胞类型和信号微环境。在癌症背景下,M1型可通过细胞毒性和吞噬作用发挥杀伤肿瘤作用。而M2型与不良预后相关,其血管生成和免疫抑制功能促进肿瘤生长。
二、TAMs的形成
肿瘤组织间质中的巨噬细胞增殖形成TAMs的一部分,循环单核细胞的招募也是TAMs积累的必要条件。来自肿瘤和宿主细胞的信号共同形成了TAMs的功能表型。在CC中,TAMs的形成主要与肿瘤源性分子、T细胞源性分子、精浆源性分子、厌氧微环境和其他来源的分子有关[8]。
1.肿瘤源性分子:TAMs的形成与肿瘤及肿瘤源性分子关系密切。Colegia等[9]研究证明了肿瘤细胞产生的乳酸,作为有氧或无氧糖酵解的副产品,可以诱导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的表达和肿瘤相关巨噬细胞的M2型分化,并对肿瘤细胞与巨噬细胞之间的信号传递具有重要意义。此外,有研究发现,用宫颈癌细胞的上清液培养单核细胞时,其趋化、吞噬和调节T细胞增殖的功能被显著抑制,且M1型巨噬细胞出现M2型特征,CD163、TLR-3、TLR-7、TLR-9和IL-10等的表达也上调[10]。核磷脂蛋白β1(karyopherin β1)是一种核导入蛋白,参与转运含有核定位序列的蛋白。如图1所示,转录因子NF-κB和AP-1通过启动与炎症和癌细胞生物学相关的多种因子的表达,调控TAMs的分化[11]。抑制HeLa细胞karyopherin β1的表达可降低NF-κB和AP-1的转录活性,减少宫颈癌细胞的迁移和侵袭[12]。Th2细胞分泌的细胞因子如IL-6、IL-1β、TNF-α、GM-CSF等也是NF-κB和AP-1的靶向基因,而这些细胞因子可诱导巨噬细胞M2型分化[6]。这些结果提示karyopherin β1可能参与诱导M2型巨噬细胞分化。
CCR2-CCL2通路是肿瘤中单核细胞募集和功能定位的重要决定因素。趋化因子CCL2可以影响巨噬细胞的极化程度,因为CCL2增强了脂多糖诱导的IL-10的产生,而CCL2的阻断可导致人巨噬细胞M1型分化相关基因和细胞因子的表达增强,M2型相关标记的表达减少[12,13]。CC细胞中CCL2 mRNA表达水平与TAMs数量呈正相关[13]。宫颈癌进展与血清中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M-CSF)水平升高有关。研究表明,CC细胞表达GM-CSF的水平与TAMs的数量呈正相关,且GM-CSF可以激活TAMs释放促肿瘤因子[14]。IL-10可由多种细胞产生,包括HPV转化的宫颈癌细胞。IL-10可通过上调IL-4Rα和IL-4R依赖性精氨酸酶1的表达来促进巨噬细胞M2型活化。此外,IL-10可促进精氨酸酶在脂多糖中的表达,使巨噬细胞发挥免疫抑制功能[15]。
癌蛋白可促进细胞中参与TAMs形成的分子的产生。研究数据表明,HPV感染后,HPV E2、E6、E7蛋白可促进IL-10的表达,而IL-10又会刺激HPV E6和E7的表达[16]。IL-10参与细胞向M2型巨噬细胞的分化,而M2型巨噬细胞表达高水平的IL-10[10~13,16]。因此,HPV癌蛋白和IL-10之间的相互作用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可能有利于宫颈癌组织内免疫抑制微环境的形成。此外,王军等[16]研究发现高危型HPV16 E6蛋白可上调宫颈癌细胞外泌体中热休克蛋白HSP70的表达,进而促进巨噬细胞分泌IL-6、IL-10,并介导宫颈癌细胞增殖、迁移和侵袭。
2.T细胞源性分子:T细胞通过分泌特异性分子,可能影响单核细胞向巨噬细胞的分化。巨噬细胞活化途径分别为经典活化途径和选择性活化途径。经典的活化途径被定义为Th1细胞因子γ干扰素 (IFN-γ)或细菌产物如脂多糖刺激巨噬细胞M1型分化。 Th2相关细胞因子IL-4、IL-13、IL-10、TGF-β、糖皮质激素、维生素A等抗炎性细胞因子作用引起的巨噬细胞M2型分化属于选择性活化途径[17]。M2型巨噬细胞在被T淋巴细胞受体激动剂激活后,共刺激分子的表达降低,IL-12p70和IL-10的平衡改变,以及刺激T细胞增殖和IFN-γ生成的能力下降,这就形成了肿瘤免疫抑制微环境[18]。肿瘤浸润淋巴细胞可组成性表达IL-4,IL-4已被证实可以通过诱导转录因子kruppel-like factor 4 (KLF4),促进骨髓源性巨噬细胞向M2型分化[19]。激活的CD4+T细胞产生的IL-17可增加宫颈癌细胞系IL-6的分泌,而IL-6对M2型巨噬细胞的分化具有重要作用。IL-17引起的肿瘤生长增强与IL-6的表达增加以及肿瘤部位巨噬细胞的招募有关[20]。以上结果提示IL-17可能参与了浸润巨噬细胞的分化。

图1 TAMs的招募与分化调控[11]
3.精浆源性分子和厌氧微环境:由于男性伴侣的精液是免疫调节前列腺素和细胞因子的复杂混合物,精液暴露可能影响女性生殖器炎症微环境。用正常精浆对宫颈细胞进行体外刺激,发现IL-6、IL-8和GM-CSF的分泌浓度显著升高,PGE2和IL-6对M2型巨噬细胞分化也有作用[20,21]。这表明精浆可能通过前列腺素影响宫颈癌巨噬细胞的分化。
TME缺氧启动宫颈癌细胞中神经纤毛蛋白(neuropilin-1,Nrp-1)的过表达,从而招募并使巨噬细胞向M2型分化。Nrp-1和M2型TAMs已被证实与宫颈癌FIGO分期和淋巴结转移相关[22]。
三、TAMs的生物学标志物
科学家发现,宫颈癌CD68+TAMs呈CXCL10(M1型)/CD163+(M2型)混合型,但大多为M2型[9]。CC肿瘤间质中存在M1型巨噬细胞,其IL-6、TNF-α和iNOS等M1型标志物表达下降,并在肿瘤细胞的影响下易于向M2型转化。CC研究中,用于M1型巨噬细胞的生物学标志物有CD163-、CD163+pSTAT1、CD68+pSTAT1+、IL-6、TNF-α、iNOS、IL-12p40、CD80+、HLA-DR和CXCL10(图1);M2型最常见的标志物是CD163+,其他标志物有CD206+、IL-10、CD14+、CD11b+、CD204+、CD163+c-MAF+、CD68+c-MAF+、HIF-1α、PPARγ、Arg-1、Ym1、CD14+PD-L1+和CD163+CD14+[11,17]。
四、PD-1在TAMs上的表达
程序性死亡受体1(programmed cell death protein-1,PD-1),也称CD273,是一种免疫检查点受体,主要表达于活化的T淋巴细胞和前体B细胞,可介导机体免疫耐受。肿瘤细胞则通常过表达PD-1的配体,即程序性细胞死亡配体1 (programmed cell death ligand 1,PD-L1),促进肿瘤细胞免疫逃避。虽然PD-1/PD-L1阻断激活T细胞已经得到证实,但该通路在TAMs上的作用尚不清楚。相较于活化的T淋巴细胞,PD-1在巨噬细胞上的表达水平较低,且需要脂多糖、NF -κB和α-干扰素等的刺激[23]。此外,PD-L1在TAMs上强表达,这可能导致T细胞耗竭和介导肿瘤的免疫抑制。因此,阻断PD-L1对巨噬细胞的作用,增加T细胞的活化,从而增强抗肿瘤作用[24]。Gordon等[25]在小鼠模型中研究发现TAMs上PD-1的表达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并且在原发性人类癌症中随着疾病的进展而增加。PD-1+的TAM可表现为M2型,而PD-1-TAM的表达谱则与M1型相似。TAM PD-1表达情况与对肿瘤细胞的吞噬能力呈负相关,体内阻断PD-1/PD-L1通路可以增加巨噬细胞的吞噬能力,减缓肿瘤生长,延长肿瘤模型小鼠的生存时间,并呈巨噬细胞依赖的模式。研究结果表明,PD-1/PD-L1疗法也可能通过对巨噬细胞的直接影响发挥作用,且2020年NCCN指南已将抗PD-1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派姆单抗列为复发或转移性PD-L1阳性宫颈癌首选二线治疗方案,这对宫颈癌的免疫治疗具有重要意义[26]。
五、靶向TAMs的宫颈癌治疗
巨噬细胞是肿瘤炎性微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巨噬细胞的可塑性使肿瘤免疫治疗过程中改变肿瘤微环境和重建抗肿瘤免疫成为可能。靶向TAMs的主要治疗策略包括抑制M2型巨噬细胞的活化,阻止单核细胞向肿瘤组织募集,激活巨噬细胞吞噬活性,阻断PD-1/PD-L1通路对巨噬细胞的作用以增加T细胞的活化[27]。
现有研究数据表明,代表所有活化巨噬细胞的CD68+巨噬细胞并不是预后标志物,而M2型巨噬细胞与CC的关系具有特异性[28,29]。宫颈鳞状细胞癌组织标本中肿瘤内M2型TAMs的数量显著高于非肿瘤样宫颈标本中上皮内M2型TAMs的数量,宫颈鳞状细胞癌瘤周M2型TAMs的数量高于宫颈非肿瘤组织[28]。此外,宫颈腺癌中肿瘤浸润CD204+M2型巨噬细胞密度较高,与较短的无病生存显著相关[29]。
由于M2型TAMs被证明有致瘤作用,而M1型TAMs在CC中具有抗肿瘤作用,一些研究者开始关注M2型向M1型的转化,认为这可能是治疗上的突破。Gordon等[25]研究发现当PD-1敲除后,用酵母聚糖诱发炎性反应,可使巨噬细胞向M1型分化,这可能与PD-1敲除后胞内STAT1/NF-κB活化增强以及STAT6信号通路活化减弱相关。Heusinkveld等研究发现,宫颈癌细胞诱导的M2型巨噬细胞与CD4+Th1细胞相互作用后,可转变为活化的M1型巨噬细胞,同时表达高水平的共刺激分子,获得淋巴归巢标志物CCR7,从而形成抗肿瘤微环境[20]。然而,M2型巨噬细胞与Th1细胞作用的具体机制暂不清楚。Saito等[30]研究发现,重组人血清素-干扰素(rIFN-γ)对宫颈癌细胞系具有直接的剂量依赖性抑制作用。此外,他们还发现,用rIFN-γ处理后,人腹腔积液细胞(>80%的巨噬细胞)对卵巢癌和黑色素瘤细胞株的集落生长均有很强的抑制作用。虽然缺乏直接证据,但这些结果暗示TAMs可能在rIFN-γ的影响下产生一种可扩散物质,在CC中成为杀瘤物质。此外,Nrp-1在宫颈癌缺氧TME诱导的巨噬细胞M2型分化和促肿瘤作用中起关键作用,干扰Nrp-1可能是治疗宫颈癌的一种潜在的治疗策略[22]。
六、展 望
综上所述,循环单核细胞受多种炎性细胞因子调控被招募至宫颈癌局部病变组织中,并分化为M1型和M2型巨噬细胞,参与肿瘤免疫和免疫逃避。在肿瘤进展过程中,来自CC细胞的分子如HPV癌蛋白,特别是E6和E7,是影响巨噬细胞分化的初始因素。此外,T淋巴细胞、精浆和厌氧微环境等的相关分子也在巨噬细胞分化和选择性活化中起着重要作用。由于M1型巨噬细胞在CC中发挥抗肿瘤作用,而M2型巨噬细胞有致瘤作用,故M2型向M1型巨噬细胞的转化引起了研究者们的关注,这或许将成为肿瘤治疗的新方向。PD-1+TAMs与M2型巨噬细胞表型相似,在抗PD-1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宫颈癌中发挥着重要作用。TAMs作为新的免疫治疗的靶点,具有巨大潜力,将对宫颈癌的治疗产生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