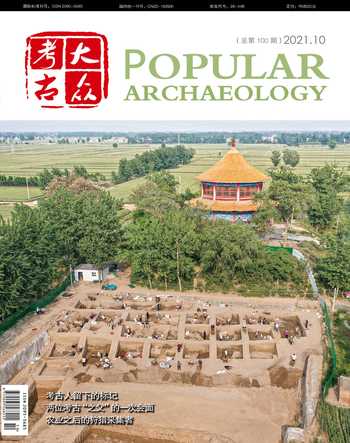明代货币资本发展的见证 高凌烟墓志铭
张国勇 张倩

《明敕封文林郎河南彰德府安阳县知县高公墓志铭》,为明万历时期(1573—1620)的一方墓志铭,1967年出土于河北邢台地区宁晋县曹伍疃乡曹伍疃村,原存于曹伍疃小学。20世纪80年代后期,河北省墓志普查工作领导小组开展调查时,该墓志志盖已佚,因此《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北卷)》仅收志石。墓志青石质,正方形,边长71厘米,厚15.5厘米,在邢台地区所见的明代墓志中属于中等体量规格。阴刻楷书,44行,满行45字。志石左上部有小片石花,缺损少量文字,除此外大部分文字清晰可辨。
墓主高凌烟,生活于嘉靖(1522—1566)中后期至万历时期,在万历时期从事商业活动,主要是信贷业务。明代商人的墓志铭,在河北境内较为少见,在国内也并不多得,高凌烟墓志铭是研究明代信贷问题不可多得的一手资料,其事迹和遭遇、成功和失败,为考察明代后期商品经济,尤其是货币资本的发展情况提供了区域性的样本和视角。
墓志录文
明敕封文林郎河南彰德府安阳县知县高公墓志铭
赐进士翰林院检讨征仕郎高邑李标撰
赐进士征仕郎工科给事中建言钦调贵州布政司添注都事前奉命巡视陵工典试浙江邑人刘文炳书
赐进士文林郎陕西道钦差巡按直隶苏松常镇四府兼督沿海综核将领监察御史邑人冯英篆
万历四十七年三月,封文林郎、安阳县知县、文豪高公以疾终正寝。时子侍御君及次子进士君痛欲绝,已而苏曰:“府君已矣,吾属不能起死者而生耳。惟是府君一二懿行表表为人传诵者,冀得勒贞珉而垂不朽焉。”乃卜仲冬十一日,安厝公祖茔之次,而侍御君自为状求余志铭。余与侍御君乡举升第皆同籍,而又属肺腑交,且公行谊固夙所耳而目之者也,曷得辞?按状:公讳凌煙,字子英,别号文豪,世为宁晋之奇唐城乡人,盖今曹古疃是也。始祖讳□用者,胜国时官承务郎,温州路同知瑞安州事,卜居于此,云仍迭起,至公称累盛云。公生而倜傥,不屑问家人生事。少习举子业,学已成,乃三试督学不偶。公翻然曰:“大丈夫生身当世,何术不可为,安能俛首帖括,日效诸生佔毕为?”竟去之学农,属屡岁大?,无所获,公又翻然曰:“古云力田逢年,今终岁勤动,而至不能赡人口,又安能捲捲老畎亩间也?”□去之学贾,贷子母钱,逐什一之利,嗣是家稍进。时两尊人俱在堂,公以所获奇赢,具滫瀡之奉,极其洗腆,两尊人甚欢。母张先逝,痛之几不欲生。又奉继母如母,无少闲。而公性恬顺,事事务主退让,不与人争。族人有携人资贾于京者,会公亦自京归,族人令责主仆携资同行,仆人乃匿资携女子去。族人不知,以为公加害,竟诬于官,已而得其人,乃在河南货布。人谓公必有后言,族人遂皇恐欲死,冀得公稍宽以赎前误,公竟不较。族富人有谋公之产者,不遂,阴假以事,率无藉之辈詈骂,三日夜不绝,公杜门若罔闻,人皆服其雅量。然公无它营时,专精于贾,而又数奇,后皆不获所利。顾其意恒思所以佐人之急。衡水赵姓者,拥巨资,重公谊,不惜千金贷之。同族大父贾,族大父曾代邑人李姓者货麦于京,得资二百金,携至中山,为盗抉扄窃去,易以瓦砾。其人鸣之官,比盗获而金亦尽。公遂以所贷赵资代偿之。讼事久不结,其费皆于赵氏金取办,急人之厄,不复知非己有也。族大父竟物故,而赵氏金已去其半。公尽鬻产以偿,家遂茫然矣,然犹振人之急不怠,诸凡衣寒哺饥、药疴棺?,为德之事不可殚述。恻隐之心,公盖得之至性,非有所矫也。嗣是,两尊人相继捐帷舍,敛葬皆如礼,不以丧资累仲弟,家益窘。公乃抗志益厉,不复与里中坚肥辈齿,或劝之:“以公食贫,稍贬以借资,何不可?”公曰:“嗟来若可食,当不饿死。且吾不贷千金行贾乎?今拓落至此,又乌能缓颊向人,以枉寻直尺为也?”其人惭愧退而是。时侍御君及进士君皆以次补弟子员,文藻英英出众,公见之为色喜。癸卯,侍御君举于乡。丁未,成进士。公乃辗然曰:“吾识尔于童稚时,以尔在约无酸鄙气,今果显,然勿忘□□年前生计也。”侍御谨受教。试宰淄川,调繁安阳,皆大有声,绩三载最,竟用安阳秩封公。□□□□,章服辉映,贵矣!越十年,而次君亦举于乡,长君业拜御史,叔子虽隐于闾里乎,然善治生,循循德让长者,公□□□颜。公春秋高,渐不耐人事,乃卜城隅隙地为舍,日坐卧其中。每暇,则约一二亲知,煮茗小集为笑乐,不设酒,□□□饮,所结皆不能饮者,如是以为常,陶陶然甚欢也。生平故无恙,忽一日为族人寿,中席遽昏瞀,侍御亟呼之,□□□疾作。今年上元步中庭,忽复昏瞀如前,侍御又亟呼,复醒,自是竟不起。弥留之日,次君成进士,报至,公自榻上笑颔之,然益剧。次君甫释褐,即请告归,兼程至里,乌纱袍带,犹及拜公榻前。越翌日,乃卒。卒之日,正襟危坐,绝不及家人生事,但睹两君贵显,孙枝世茂,则曰:“吾愿足矣!”其达如此。公生于嘉靖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卒于万历四十七年三月二十九日,得寿七十有六。配王氏,封孺人,王君燮女。子三:长推,即侍御君,娶王氏,封孺人,王君汝弟女;次捷,即进士君,娶刘氏,赵州刘君士彦女。继李氏,李君学诗女。郑氏,赵州庠生赵世乾女;次拔,娶柳氏,庠生柳色先女。女四:长适庠生鲁惟忠子鲁一言;次适王君士英子王律;次适庠生王堡子王振古;次适太学生王士贤子王泌,邑庠生。孙三:曰去奢,邑庠生,娶王氏,武举王元化女,推出;曰去靡,邑庠生,娶闫氏,闫君嘉谟女。曰去伐,未聘,捷出。女孙五:长适柏乡举人白允升子白珙,庠生。余未适。曾孙六:曰光祖,聘举人李之萼女。曰光猷,聘柏乡庠生魏柏祥女。曰光祉,未聘。去奢出;曰光宗,聘庠生贾瑗女。曰光国,曰光治,俱未聘。去靡出;曾孙女一,未适,去靡出。
李子曰:自纯古之□还,而人情日薄,往往不心竞,而力争于朝、于市,恬不知耻,其在于今,为尤甚。高公起家布衣,又值不绌,而事务退□务□,其于人世机变倾巘之事,不惟身所未尝,亦且念所不涉。知雄守雌意,有得于老氏之训者耶?天道张弓,宜食其后,报未艾也。因既志而铭之。铭曰:
谓公儒耶?而薄胶庠。谓公贾耶?而啬箧筐。非儒非贾,晦迹徜徉。处顺安排,何用不臧?爰启哲嗣,天路翱翔。华封舄奕,有赫纶章。瘿陶之墟,凤山之傍。为公窕穸,如斧如坊。蜉蝣世宙,今古沧桑。猗维硕人,何存何忘。
墓志特点
经检视《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北卷)》中所收邢台地区墓志,相对于北魏及唐代,明代墓志纹饰大幅度减少。这反映出唐代以后墓志铭文化的盛极而衰,以及墓志铭在明代丧葬文化中所扮演角色的变化。首先,明代墓志铭所附着的宗教色彩已大为减弱,在唐以前,这主要是通过墓志上雕刻的纹饰来体现的。其次,在元代以后的丧葬文化中,本应该体现的虔诚性和严肃性受到一定冲击,葬礼过程的重点更多体现在作为外在形式的排场的讲究与铺张上,如堪舆、佛事等的盛行。这使得明人不再刻意追求墓志的表现形式,进而忽略了墓志铭本来所具有的深刻意义,如巫鸿先生所认为的,墓志发明的初衷是象征死者,并通过纹饰“将死者置于一个象征性的宇宙的中心”,而在明代,墓志的“叙事性”几乎成为它的全部价值所在。最后,随着宋代以降平民社会的到来,使用墓志的群体日益扩大至一般民众,对于墓志需求量的增多,必然会增加墓志作为商品的属性,为迎合平民社会而删繁就简是难以避免的。
在志文的行文格式上,作为国号的“明”字独占一行,这在明代乃至以前的志文格式布局中很少见。邢台地区出土的明代墓志铭中,只有1978年威县出土的《董威母刘氏墓志铭》有类似情况,“明故”两字独占一行,更加贴近当时八股文和公文的体例。
从志文看明代货币资本
虽然志文对高凌烟生前从事商业活动的详细介绍不多,但却构成此墓志铭的核心内容,是研究明代货币资本发展不可多得的一手资料。对此,可至少作如下解读:
明代后期,信贷业已经成为河北一带助推传统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经济形态。明代后期,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孕育的商品经济异军突起,快速发展,开始深刻改变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也促使社会思潮和人们的价值观发生变化。在这种环境下,商业作为营生手段受到重视,商人地位提高,弃农从商或者商而儒、儒而商,士商相杂、士商相混者,不乏其人。高凌烟一开始遵循的是读书仕进的人生道路,几次碰壁后,毅然转变方向,其发出“大丈夫生身当世,何术不可为,安能俛首帖括,日效诸生佔毕为”的人生宣言无疑在晚明社会是有一定思想基础的。在学书、学农失败后,却在经商方面获得成功。其经营的并非是普通商品,而是“贷子母钱,逐什一之利”,即商业借贷,收取利息。“什一之利”并非为利率标准的确数,明代货币借贷利率因人、因地、因事而异,根据学者的研究,正常的利率在二分至三分之间,有的低至一分五厘,有的高达四五分乃至十分。我们无法从墓志中了解高凌烟放贷的利润,但是从“家稍进”和“具滫瀡之奉,极其洗腆”看出,回报还是相当丰厚的。正是由于此,才使得参与经营的人进一步增多,高凌烟族人“携人资贾于京”、衡水赵姓“千金贷之”等,说明该时期社会上的信贷经营绝非个别现象,已经具有了一定的规模。这也反过来说明明代后期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规模,客观上需要有货币资本的支持。河北一带为北直隶属地,密迩京师,对于本区域包括货币资本在内的商业发展是一个有利的条件。因此,从事信贷经营的人不在少数,是晚明商人中的一个重要子群体,也是人们积累财富的重要方式。
货币资本对于社会的积极作用。明代的货币资本以信贷为具体业态,在追求利润的同时,信贷商人还拿出一部分财富积极参与社会事务,做了不少有益的事情,对于明代基层社会的稳定和贫苦民众生存条件的改善发挥了积极作用。以高凌烟为例,他在放贷经营获得成功后,“振人之急不怠,诸凡衣寒哺饥、药疴棺?,为德之事不可殚述”,诸如此类善举,基本事实是可信的。而这不是个别现象,很多当时的方志都会提及士绅对农田水利、学校和宗教建筑的修造、重建的资助。在明代后期社会儒、商,士、商身份日益交织的背景下,士绅的队伍中无疑也包括了像高凌烟这样的商人群体。信贷商人所属的明代货币资本,以其相对雄厚的实力,在基层社会的公益活动中自然会占据瞩目的地位。特别是商人对家族内部成员的帮助上,更显示出明代资本的温情一面,例如志文叙述的高凌烟帮助失盗的“同族大父”解决偿贷危机一事。在明代后期商品经济兴起的时代背景下,某种程度上,信贷资本对于社会事务的热心参与,于己而言,起到了搏取名誉、赢得社会认同的作用;于社会而言,显示了民间商人作为一个阶层和社会耦合度的加深,以及其日益增长的社会地位。不过,考虑到晚明社会竞相奢靡的风气已为当时精英阶层诟病,这可看作明代商业资本向社会舆论的主动回应,是商业向儒家思想主流社会加深渗透的一个表象,具体说就是“用贵金属的花费量来测定道德功善的这种可能性为在儒家道德经济中给银钱一个正当的地位开辟了道路”。
明代商业资本的“围城”。明代虽然实现了商品经济前所未有的高度发展,但却并未如西欧那样顺利过渡到更高一级的社会形态,个中原因十分复杂。除了“以商致富,以宦贵之”的官本位意识盛行外,其他一些不利的社会因素,也都形成了明代商品经济发展的桎梏。这些因素在高凌烟墓志铭中同样可以看出端倪:
一是糟糕的治安环境。高凌烟经商所在的万历时期,虽然还未出现崇祯年间(1628—1644)的动荡局面,但是治安环境同样不容乐观。无论是志文中所说受人所托携带银两的仆人轻易地、私自地“匿资携女子去”,还是高凌烟族大父所携二百金在中山“为盗抉扄窃去”,都一再表明明代后期治安的弱化,在这种没有充分安全保障的社会环境中,商品经济要想正常运转,是非常困难的。
二是商品經济的要素还不健全。明代后期的商业经济虽然具备了劳动力、市场、资本等要素的支持,但对于一个高度运转的商业社会来讲,这些要素还是远远不够的,仅站在商业和市场层面来观察,商业的持续发展,是离不开完善的金融系统支撑的,特别是从事信贷行业的商人,他们需要一个稳定的金融汇兑市场,以保证他们能安全、顺利地将大量的银子从一个地方运送、传输到另外一个地方。在清代票号开创之前,这些工作不但费时耗力,且极不安全。高凌烟墓志铭中为我们提供了现实的案例,无论是“携人资贾于京者”的族人,或者是高凌烟“族大父”,这些信贷商人的不幸,恰恰说明了没有通汇通兑的技术性支持,没有成熟统一的金融市场的托底,明代商品经济形态,尤其是信贷这种行业是多么脆弱和不稳定。高凌烟本人虽然未遭逢偷盗困扰,但是他在帮助族大父度过偿贷危机的同时,也将危机转嫁到了自己身上,耗尽数百两银子,无疑也成了他走向破产的重要原因。
三是宗族的牵制。传统中国是宗族社会,宗族是一个人无法脱离的基本单位,一个人可以从宗族中得到扶助,同时宗族也可能成为个人的束缚。当商业因素在明代后期社会生长时,传统的宗族与宗法的精神不但没有被冲淡,反而有所强化,个人与宗族的纽带进一步密切起来,明、清时期徽商借助宗族势力兴起,反过来用财力回馈宗族的案例,学者们进行过充分的研究。但高凌烟墓志铭所呈现的个例,却是一个反面的、更为发人深省的样本。我们在志文中看不到宗族势力对于高氏经商活动的支持,而是更多观察到它的反向作用。当他经商稍有所得时,就遭遇了“族富人”倾陷谋财之事,虽然未果,但族富人接下来“率无藉之辈詈骂,三日夜不绝”,则势必会影响到高氏个人的名誉及其与宗族的关系,这很难说与高凌烟随后的“数奇”“皆不获所利”没有关系。在“族大父”一案结案后,高凌烟“不复与里中坚肥辈齿”,说明“里中坚肥辈”在导致案子久拖不结中起到了相当的掣肘作用,而正是这个案子,造成高氏“鬻产以偿,家遂茫然”,走向破产。接下来有人开导高氏的话“以公食贫,稍贬以借资,何不可?”则让我们隐约看到,这个(些)“稍贬以借资”的对象,正与“族富人”和“里中坚肥辈”的影子有着某种重合。可以说,高氏经商之旅诸多波折和不幸,是有他背后的宗族因素的。
《高凌烟墓志铭》作为碑刻文献,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不算成功的明代后期商人的样本,而这个样本应该不是偶然的,它无疑是一个镜鉴,照出了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条件下,旧的文化和社会形态对于新的商业因素的牵制。
(作者张国勇为邢台市文物管理处副研究馆员;张倩为邢台市图书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