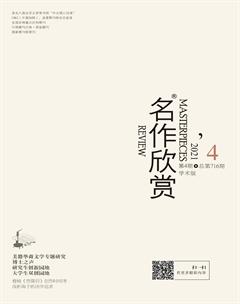简·爱的身份困境与身份认同
摘 要:《简·爱》是19世纪英国文学中的经典之作,其中塑造的女主人公简·爱以强烈的女性反抗精神闻名于世,其形象是否具有矛盾性也引来了颇多争议。从青少年时期的自我同一性危机到步入社会后的身份抉择,简·爱不断面临身份困境。作为男权社会主流价值体系中的一员,简·爱对社会不平等准则的反抗并非以打破现有社会秩序为目的。简反抗的原动力是其身份困境,斗争的最终目标是获得身份认同。当简的自我身份认同与社会身份认同达到平衡统一后,简的个人反抗也达到了终点。
关键词:简·爱 身份困境 身份认同 矛盾性
夏洛蒂·勃朗特所著《简·爱》是19世纪英国现实主义文学的经典之作,国内外学界有关这部作品的研究角度多样,成果颇丰。简·爱一向被看作文学史上具有反抗精神的女性形象,她敢于争取自由、平等的性格为其在文学史上赢得了显著的地位。但同时,也有学者对简·爱的形象的反抗性持怀疑态度,认为这一形象在进行反抗的过程中暴露出矛盾性的特征。简·爱这一形象的自觉意识不可否认,但其还不具备清晰的性别意识、阶级意识,更遑论明确的女性主义、阶级反抗思想。a
身份认同涉及对自我的确认,其基本含义指个人与特定社会文化的认同。b身份认同又是主观与客观的共同作用,包括自我身份认同以及社会身份认同这两个对立统一的方面。个体认同是个体在时空上确立的自我意识;社会认同则指个体积极追求社会群体成员身份及在群体中的认可后实现社会化。c简·爱自身作为男权社会主流价值体系中的一员,其对社会不平等准则的反抗并非建立在打破社会秩序的目的之上。简·爱反抗的原动力是其身份困境,简斗争的最终目标是在现有社会秩序下获得身份认同。简最终回归家庭,回到社会既定价值的轨道上,不只是因为简·爱个人反抗力量的有限性,也是由于简在获得了自我身份认同以及社会身份认同后个人奋斗已达到终点。
一、青少年时期的自我同一性危机
自我同一性理论创始人埃里克森认为,自我同一性的形成是青春期的核心任务,青少年面临着自我定义具体化的任务。d简·爱幼年生长在盖茨海德府,十岁进入劳渥德学校学习,直至十八岁离开学校。青少年时期的简因自我同一性的危机而造成了身份困境,这种自我同一性危机是心理层面身份认同即心灵归属的危机。在盖茨海德府,简是寄养的孤女,她的家庭身份为其带来困境;在劳渥德学校,简于入学之初与离开学校之时两度陷入身份困境,对这两次身份困境的化解也是简人生的转折点。
(一)寄养儿童的身份困境
简·爱的幼年时期在盖茨海德府度过,她被寄养在舅妈里德太太家。寄养儿童这一身份的内在矛盾使简在幼年便陷入了身份困境:简不是一家之主的直系亲属,她并非盖茨海德府的小主人;简在家中也不从事劳动生产,她与盖茨海德府也非雇佣关系。简的自我与他者眼中的身份存在矛盾。
1.自我认同:盖茨海德府的小主人
简原本与盖茨海德府有着血缘关系,盖茨海德府的主人里德先生是简的亲舅舅。然而,当里德舅舅去世后,简与盖茨海德府的联系发生了质变:舅妈里德太太成为盖茨海德府的主人,其与简之间没有血缘关系。里德太太既没有抚养简的义务,也没有抚养简的情分,坚持抚养简只是在履行里德先生死前被迫许下的承诺,而这一承诺违背了里德太太的本心。自此,简与盖茨海德府失去了亲缘关系,其在盖茨海德府安逸生活的根基倒塌了。
显然,简并没有认识到自己在家庭中身份的变化。里德舅舅的疼爱使简产生了惯性,在她看来,自己始终是盖茨海德府的孩子,理应受到与约翰少爷、两位小姐同等的待遇。基于此,简对自己的处境感到不满,认为里德舅妈苛待了自己。对于约翰·里德的打骂、里德小姐的蔑视、里德舅妈对待亲生骨肉与对待简的双重标准,简耿耿于怀;对于自己衣食无忧的生活,简认为是理所应当的。
2.他者眼光:盖茨海德府的多余人
“妈妈说你是个靠别人养活的人;你没有钱;你父亲没给你留下钱;你该去要饭,不该在这儿跟我们这些绅士的孩子一起过活,跟我们吃一样的东西,穿我们妈妈的钱买来的衣服。”e通过约翰·里德的话语,读者可以发现,里德太太并未在物质生活上苛待简。简对自我身份的认知存在偏差,這一点不仅引起了主人的不满,雇佣关系下自食其力的仆人们也对简颇有微词。在仆人看来,简并非小主人却享有着和少爷、小姐们同等的吃穿用度,简没有为她的物质生活付出任何劳动。阿葆特认为简“比用人更没有权利住在这儿”,白茜也说出简几乎从不干活这一事实。简对自己的家庭待遇不满,但也不愿放弃盖茨海德府的物质条件与贫穷的父系亲属一起生活。
简的幼年在身份困境中度过,由此造成了自我同一性危机。当这种身份困境随着简的成长演化为身份焦虑,终于以殴打里德少爷、辱骂里德太太的形式爆发,无论是简自身还是他人都认为简不再适宜留在这个家庭。
(二)求学时期的身份认同
简·爱于十岁来到劳渥德学校独立生活,在这里简先后成为学生和教师。这一阶段简对于自身的认同于一定程度上建立在他者的认同之上,简的自我身份认同向社会身份认同靠拢。
1.他者眼光下的自我认同
对于简来说,劳渥德学校是一个全新的环境。初入学校的简努力寻求认同——“我是想做个那么好的孩子,是想在劳渥德做那么多事;是想交那么多朋友,去博得尊敬、赢得爱。”这里没有人纠结于她的过去,简很快赢得了老师的赞扬、学生的平等相待。然而,布洛克尔赫斯特先生的突然出现打破了简刚刚适应的新生活。他听信里德太太的一面之词,认定简是个坏孩子,并不加分辨地在全校师生面前指责简为撒谎者且对简进行体罚。自幼缺乏关爱的简十分看重新环境中他人对自己的态度——“要是别人不爱我,那我宁可死掉,也不要活着——我受不了孤独和别人的憎恨。”面对布洛克尔赫斯特先生公然指控:“她有孩子的一般外貌……魔鬼已经在她身上找到了一个仆人和代理人”,简很可能自暴自弃地走上成为小恶魔的道路。
在简·爱的这场身份危机的化解中,谭波儿小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谭波儿小姐以师长的身份引导简为自己辩护,并告诉简自我意识的重要性——“你自己证明是怎么个孩子,我们就认为你是怎么个孩子。”在耐心聆听了简·爱的诉说后,谭波儿小姐主动写信求证,继而当众澄清了对简的指控。谭波儿小姐的教诲与善行帮助简完成了一次救赎,这使得简在劳渥德学校逐渐找到了自我身份与社会身份的平衡,成为学校优秀的学生、教师。
2.成年之际的自我怀疑
简·爱入校八年后,谭波儿小姐离开劳渥德学校步入婚姻的殿堂,她的离去使简又一次陷入了身份危机:
从她离开的那天起,我就不再是原来的那个人了;一切稳定的情绪,一切使我感到劳渥德有几分像我的家的联想,全都跟她一起消失了……我忠于职责,遵守纪律;我安静;我相信我是满足的;在别人看来,常常是在我自己看来,我似乎是一个受过训练的、克己的人。
简发现几年来保持的诸多品性只是“从谭波儿小姐那儿借来的”,随着谭波儿小姐的离去,简失去了进入劳渥德学校以来心灵的平静。尽管在他人看来,此时的简是劳渥德学校出色的毕业生、受人尊敬的教师,但简已经察觉自己的内心不再满足于她的社会身份,她开始希望冲破现有身份的束缚,寻找可供灵魂安歇的新身份。
简·爱在成年之际再次陷入身份认同危机,即他者对其福利学校教师身份的一致认同与其自身对社会身份不满之间的矛盾。简的身份认同危机导致了自我怀疑,这种内心矛盾外化为行动,促使简渴求新的社会职位,开始走上新的生活道路。
二、身份抉择中的社会认同
成年后简·爱对身份认同的追求更多是一种对身份或角色在社会中合法性的确认。不论是对家庭教师、乡村教师等社会身份的选择,还是对妻子、情人等伦理身份的抉择,简的目的都是在自我认同的基础上获得身份认同。
(一)社会地位与身份困境
简·爱对于社会身份的态度充分反映了维多利亚时代的价值观念。在简看来,工作是她获得独立地位与社会认可的基础,靠工作谋生、自食其力是她的责任。f离开劳渥德学校后简有过三次工作经历,职业在为简在赢得社会地位与社会尊重的同时也造成了身份困境。
1.家庭教师的身份困境
简·爱在桑菲尔德府的职位是家庭教师,这一社会身份地位尴尬。家庭教师有知识,自尊心强,但也同仆人一样受到雇佣关系的束缚,所受的待遇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雇主的主观意愿。简也不例外,她在桑菲尔德府同样面临着身份困境。
来到桑菲尔德府,简受到了客人般的待遇,女管家菲尔费克斯太太在初次见面时与简说:“约翰夫妇俩也都是很正派的;不过,你知道,他们只是仆人,不能用平等身份同他们说话,还得跟他们保持一定距离,因为怕失去自己的权威。”可见在女管家心中,家庭教师简·爱是有知识的、受人尊敬的,而非雇佣关系下应给予管教的仆人。桑菲尔德府的男主人罗切斯特先生虽不时摆出男主人的架子,但他对待简从开始便不同于对待府上的仆人,甚至一度忘记简是他付佣金雇来的。
简在桑菲尔德府获得了足够的自由与尊重,但这一切平衡被贵族客人们的来访打破了。简应罗切斯特先生的要求,与客人们共同处于休憩室。在这个贵族聚集的空间,贵族太太、小姐们当着简的面羞辱家庭教师这一社会群体,使自尊心极强的简受到了伤害。这次聚会最令简绝望之处在于,她意识到自己爱上了罗切斯特先生,却也发现他们的爱情之间隔着的鸿沟——“要是上帝赐予我一点美和一点财富,我就要让你感到难以离开我,就像我现在难以离开你一样。”毫无疑问,尽管简相信她与罗切斯特先生在精神上是平等的,但她也无法否认贫穷与相貌平平使得她在爱情中处于劣势。
简有着丰富的精神世界与崇高的精神追求,她甚至对贵族妇女枯燥乏味的精神生活表示轻蔑。然而,缺少美貌、财富与门第的简社会身份低微,她那向往自由平等的灵魂不得不受制于社会规则。这一切使其陷入身份困境。
2.乡村教师的身份困境
从桑菲尔德出走的简·爱来到沼屋,机缘巧合下成为一名乡村女教师。在简看来,这份工作虽然卑微、辛苦但并不下贱,这是一个独立的职业,不似在有钱人家做家庭教师一般依附于人。精神上的独立自由扫除了简此前作为家庭教师在经济上依附于他人所带来的屈辱感,但正如圣约翰所说,这是一份“贫穷、卑微的工作”。简在接受这一职位后不得不承认,简略粗劣的生活条件与缺乏教养的粗鲁学生无法使自己感到安定与满足,她感到“降低了身份”。 简·爱不否认物质的重要作用,她一向认为精神上的平等不能超越物質上的不平等达到人格的自由和平等。乡村教师的社会身份使简陷入了物质与精神之间矛盾造成的困境,她开始认真思考在依附于人的衣食无忧与自由自在的贫穷落魄之间该作何种选择。
(二)文化塑成的性别身份
简·爱作为女性这一性别身份的抗争与保守集中体现在她对爱情的抉择上。正如波伏娃认为社会性别是“建构”的,女性角色由社会文化塑造。g简在男权社会中抗争难免会遇到认同困境,从而表现出保守的一面。
1.妻子或情人:女性的身份认同
当简·爱与罗切斯特先生确立了恋爱关系后,简对即将获得的“罗切斯特夫人”这一身份感到抗拒——“这种宣布给我带来的感觉,是一种与快乐不相适应的更为有力的东西——它使人不安,使人震惊;我认为几乎是一种使人恐惧的东西。”这种恐惧源于罗切斯特先生订婚后显现出的男权思想与简自由意识间的冲突,即女性性别身份带来的焦虑。在19世纪初期的英国,简·爱一类自食其力的女性生活在男权社会中,正处于社会对妇女“房中天使”形象认知与自身独立形象认同的夹缝中。罗切斯特先生希望“完全抓住”“占有和保持”简,企图用珠宝服饰等财富“这样的链条拴住”简;而简自尊自立——“永远也受不了让罗切斯特先生把我打扮得像个玩偶”。简对罗切斯特夫人这一身份的抗拒是对传统妻子“房中天使”形象的反抗,在简看来夫妻双方应当是平等的,妻子并非是丈夫的所有物。
在婚礼举行之际,罗切斯特先生有一疯妻子尚在人世的消息公之于众。如果说此前简的身份危机是妻子身份下不同价值标准之间的冲突,那么伯莎·梅森的出现则消解了简作为妻子的身份。伯莎的存在使得简再也无法成为罗切斯特先生的妻子,而与罗切斯特先生表明了爱情的简显然无法再以家庭教师的身份留在桑菲尔德府。可供简选择的只有两条路:以情人身份留在桑菲尔德府,或离开此地重新踏上探寻自身独立身份的道路。简选择离开桑菲尔德府,不仅是因为社会伦理观念的威慑,也是由于罗切斯特先生在订婚期间就表现出的强大控制欲。简意识到如果此时屈从于罗切斯特先生的意志,自己极有可能沦为附庸。想要保持自己独立自尊的平等地位,简就必须离开桑菲尔德府。h
2.内心情感与道德约束:女性的道路选择
对于简·愛来说,在沼屋的时期是人生的转折点。于极富浪漫主义色彩的情节中,简的社会身份发生了很大变化:她找到了失散多年的亲人——圣约翰兄妹,不再孤苦伶仃;同时,简获得了叔叔的遗产,成为财务自由的女继承人。
在此时,简·爱面临着人生道路的选择:跟随内心情感与罗切斯特先生相守,或服从圣约翰的道德约束做一名传教士的妻子。简对圣约翰的拒绝是对于无法带来自我认同的社会身份的拒绝,简认为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遵循内心情感才是对婚姻与爱情的尊重。在简动身返回桑菲尔德之时,她并不知道当初逼迫她离开的障碍已被清除,她依然面临着是否成为情妇、成为附庸的两难选择。简对回到桑菲尔德一事有过犹疑,但依然没有停下脚步。简在逃离圣约翰为她安排的命运,她意识到要讨圣约翰喜欢,就必须“抛掉我的一半天性,扼杀我的一半才能”,引导简选择人生道路的是对自我身份认同的探寻。
三、自我身份认同与社会身份认同
身份认同是主观与客观认同的组合,包括自我身份认同以及社会身份认同这两个对立统一的方面。自我发展理论认为自我状态是逐步发展的,个体认同指个体对自己独特性的意识,是个体在时空上确立的自我意识;社会认同理论认为,个体积极追求社会群体成员身份及个体在群体中的认可,最终实现社会化。i
简·爱与劫后余生的罗切斯特先生在芬丁庄园重逢,并决定建立婚姻关系。对《简·爱》一书结局的解读众说纷纭,有人认为一系列巧合塑造的大团圆结局违背了真实性,也有人认为回归家庭的简是女性反抗的失败。但不可否认的是,简·爱在芬丁庄园获得了自我身份认同与社会身份认同的统一:
现在我已经结婚十年了……我认为自己极其幸福——幸福到言语都无法形容;因为我完全是我丈夫的生命,正如他完全是我的生命一样。没有一个女人比我更加同丈夫亲近,更加彻底地成为他的骨中骨,肉中肉……我全部的信任都寄托在他身上,他全部的信任也都献给了我;我们性格正好相合——结果就是完美的和谐。
简走入婚姻,成为所爱之人的妻子,符合主流社会对她的身份期待;同时,简受到丈夫的尊重与依靠,获得了实现自我价值的成就感,得到了自我身份认同。简在社会既定规则中反抗,又在反抗中寻求社会规范的认同。当简找到了自我身份认同与社会身份认同的平衡,她步入婚姻,定居于芬丁庄园。至此,简漂泊的前半生画上了句号。《阁楼上的疯女人》一书提到,天使与妖妇是出现于男性笔下的两种极端女性形象,却在文学中无处不在,成为男性强加于女性的形象枷锁。j而夏洛蒂·勃朗特笔下的简·爱无疑为我们呈现了一个与文学史上所有女性都不相同的形象:简既不是天使也不是妖妇,她不再是符号化、概念化的女性,而是有自我意识的有血有肉的人。在自我意识的支配下,简不断化解身份困境,最终获得了身份认同。
结语
本文运用身份理论对简·爱形象进行阐释,从而反思简·爱形象的矛盾性及其原因,对简·爱身份变化过程与探寻历程进行观照。简·爱的人生历程是寻求身份认同的过程,对身份认同的渴望促使简在不同身份之间做出抉择。从幼年开始,简不断遭遇身份危机,陷入身份困境。简·爱是一个有独立思想的女性,性格中的反抗精神使简拒绝委曲求全,一次次踏上探寻身份认同的道路;同时,根植于简内心的社会文化使简的抗争限定在社会规则的框架下,使其反抗行为不至于超越社会容忍。面对鬼堡般的盖茨海德府,简选择寻机离开,而非采用如伯莎烧毁桑菲尔德府一般的极端方式。简·爱性格中反抗与保守的调和正是其形象独特性与同一性之所在,也正因此,简·爱最终能够达到了自我身份认同与社会身份认同的统一。
a 肖瓦尔特在《她们自己的文学》一书中将女性写作分为三个阶段:出现男性笔名的19世纪40年代到1880年乔治·艾略特去世的时期被定为“女性阶段”(the Feminine phase),这一时期女作家模仿主导传统的流行模式并把它的艺术标准和对社会角色的观点国际化;1880年—1920年争取妇女选举权的时期被定为“女权阶段”(the Feminist phase),女作家对传统标准和价值观进行抗议,提倡少数群体的权利和价值,要求获得自主权;1920年后被定为“女人阶段”(the Female phase),是女性作家的自我发现阶段,寻求身份认同,1960年左右进入自我意识的新阶段。出版于1847年的《简·爱》是女性文学不自觉时期的产物,以女权主义的性别意识来谴责简·爱反抗行为之中存在的妥协显然是一种苛责。
bcdi 张淑华、李海莹、刘芳:《身份认同研究综述》,《心理研究》2012年第1期。
e 〔英〕夏洛蒂·勃朗特:《简·爱》,祝庆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6页。(下文有关该作引文均出自此书,不再另注)
f 程巍:《伦敦蝴蝶与帝国鹰:从达西到罗切斯特》,《外国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
g 〔美〕朱迪斯·巴特勒:《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宋素凤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41页。
h 刘慧英:《走出男权传统的藩篱:文学中男权意识的批判》,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30页。
j 〔美〕桑德拉·吉尔伯特、苏珊·古芭:《阁楼上的疯女人:女性作家与19世纪文学想象》,杨莉馨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59页。
参考文献:
[1] 肖瓦尔特.她们自己的文学[M].韩敏中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
[2] 张淑华,李海莹,刘芳.身份认同研究综述[J].心理研究,2012,5(1).
[3] 赵一凡等主编.西方文论关键词[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4] 夏洛蒂·勃朗特.简·爱[M].祝庆英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
[5] 程巍.伦敦蝴蝶与帝国鹰:从达西到罗切斯特[J].外国文学评论,2001(1).
[6] 朱迪斯·巴特勒著.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M].宋素凤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
[7] 刘慧英.走出男权传统的藩篱:文学中男权意识的批判[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
[8] 桑德拉·吉尔伯特,苏珊·古芭.阁楼上的疯女人:女性作家与19世纪文学想象[M].杨莉馨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作 者: 范予柔,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2018级在读本科生,研究方向:文艺学。
编 辑:水涓 E-mail:shuijuan393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