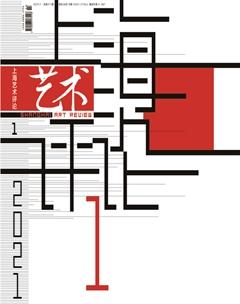“我”该如何进入现场
史晓丽
“我”该如何进入现场?是征询,也是质询。
关于“现场”的界定,总与事件或行动相关,无论已然发生或是尚未践行,事件或行动的地点即为现场。进入现场,意味着逼近真相,意味着贴近更多的细节和内情,从而获取真相的更大可能性。戏剧的现场,亦需进入,尤其是精神和情感层面的深入。事实上也只有观众深度进入戏剧现场之后,良好的观演关系才能得以形成,与观众结成戏剧共谋的创作期许才能达成,戏剧的三度创作才能愈臻完美地实现。根据翟永明同名长诗改编的诗歌剧场作品《随黄公望游富春山》,虽然其表现内容和形式与传统戏剧完全不同,编创方也并不以“戏剧”作品自称,但是,若按英国导演彼得·布鲁克在《空的空间》中的观点:一个人在他人注视之下走过一个被选取或指定的空间,那空间即是舞台,那场景便形成一幕戏剧,那么,《随黄公望游富春山》被剧院、媒体宣传成戏剧作品甚至话剧作品,也并无不妥。因为这里提到的戏剧、舞台(或剧场),显然不同于常规意义上的戏剧及舞台,其内涵及外延都被有意放大,更多带有泛戏剧等人类表演学的意味。
这里我们权且凭此观点将这部诗歌剧场作品界定为戏剧,或者根据其剧场特征更进一步明确其为小剧场戏剧:更加被缩短的舞台和观众席的距离,演员甚至直步逼入观众席;更加被强调的观演互动,台词 “你们,准备好了吗?”一经喊出,顿时逼起观众无端被喝问的紧张心理。舞台被淡化,剧场被凸显,剧场空间中,每一个人都在戏剧发生的现场,观众和演员一起被纳入表演,其颇具烧脑意味的现场对观众实则具有更高的期待。
众所周知,戏剧《随黄公望游富春山》改编自翟永明的同名长诗,而翟永明的长诗又源自元代画家黄公望的传世名作《富春山居图》。所以,进入剧场的“我”大致可分为两种:了解画作和长诗的,和不太了解画作和长诗的。“我”能否顺利进入《随黄公望游富春山》的现场?把握其意旨、感受其灵魂,尽可能最大限度地完成剧场同谋?
首先败下阵来的是未做攻略的“我”。如果“我”对现代舞略有所知,那么,《随黄公望游富春山》对“我”来说,就会是一场现代舞的晚会版串烧,台词(诗句)被“我”拍在背景板上,音乐凸显,舞姿带给“我”无限的挣扎、纠结、苍凉和忧伤。虽然该剧的真相远不止此,但这样的“我”,至少还能捕捉剧中的情感,做出自己对该剧的解读。可是,如果对现代舞一无所知呢?那么置身于该剧的现场,“我”几乎只能是一具空壳。剧中的肢体、影像、装置纷至沓来,“我”的精神高度紧张,眼睛紧紧盯住一切能看到的,耳朵也努力捕捉一切能听到的,极富特色的实验性音乐、带有明确音乐性的诗歌诵读……很累很努力,却依然无法捕捉到所有细节。更无奈的是,即使捕捉到细节,却未必能瞬时心领神会,生出令人惬意的深度共鸣。于是,“我”明明坐在剧场中, “我”的感官也都在现场,但“我”的精神却在现场外悲鸣,无法体察细节背后的隐情,难以和该剧的内涵意蕴邂逅、交会、契合,更无法企及与戏剧编创演者共谋的快感。基本可以斷定的是,进入《随黄公望游富春山》的现场,领略其中纽结的内容,无论时空、人物、艺术,还是社会、政治、人生,全然不做攻略显然是走不通的。
于是,我们首先需要以感性之心裹触介质。如同开篇诗人踩着纸张铺就的路径入场,纸张或代纸张实为我们看画、读诗避之不开的介质,观剧也同样需要了解其介质。黄公望用了六张宣纸,耗时4年以上,画画云游两不误,随意、洒脱、自在、淡然;翟永明的长诗印了几十页,完成它,也花费了三四年的时间,沉醉、沉思、自省、孑然。手卷慢慢展开,我们随着黄公望的笔触漫游于山水之间,感叹着黄公望晕染于画绘中的大家风范、浑融于水墨间的生命体验,由山峰雄奇见高士风骨,以水天润阔窥仙家气度,这些需要介质;诗句徐徐诵出,我们陪着翟永明驰骋于时空之间,感佩着翟永明娓娓诉诸笔端的情感、思绪、哲理,在说画,又不局限于画;在神游山水,也不局限于山水;对历史的反思、对现实的批判、对人生的体验,都凝聚在翟永明多重时空、多种人群、多层意蕴的诗句中,这些,同样需要介质。一切无形的依托于有形,一切意蕴,依托于形式。《随黄公望游富春山》这部作品也使用了诸多介质,如与剧场氛围、戏剧主旨、演员情绪相辅相成,合二为一的实验音乐和现场声响;随着舞者对音乐、对诗句的领会从心淌至肢体表达的现代舞;能够将画内画外、历史与现实隔断的同时又纽结并维系起来的那面高挂垂落的幕布,多媒体的手段也在其上展开演绎;从来都由戏剧本体生发,但又始终保持独立语汇的舞美灯光;代表着《富春山居图》的两部残卷、诗人沦陷于现实生活中的困境、女性话语在古代与当今的生存空间等多重含义的两幅白色卷轴;甚至每一个演员或舞者的每一处表达……这些介质如果得到感性之心的包裹与融触,那么,“我”应该已经做好了进入该剧现场的基本准备。但是,这些还不够。
我们还需要启理性之神体悟该剧的精神,这同时也是观剧的终极目的。义理?主旨?情致?意趣?这些存在于精神层面的意识形态,都寄托在各种有效的介质中,亟待表达。说到底,戏剧是一种表达,具体到《随黄公望游富春山》这部脱胎于长诗的戏剧,这种表达可能是双重甚至是多重的,该剧精神因此也会更富多义性。从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到翟永明的《随黄公望游富春山》,水墨的浓淡点线幻化为字词句点,从此,水波不再静止,山峦季节变幻,黄公望的生命之河在山水间流淌,时间空间突破了维度的界限。很难说是画比诗更明确,还是诗比画更浓郁。但从赏画到读诗,在当下的时间维度中回顾历史,在现代城市一隅中冥想山水,从而反观历史、反思当今,诗歌意蕴的丰厚若斯,确实需要调动更多的想象力和艺术感觉。从山居图到游富春山,即使并未发生真正的物理位移,但心动神移,却已在画卷、历史、山水、丛林中游走。翟永明用字词垒起的不单是诗歌的形式,更砌起了诗人的精神,并凭着这样的精神,直入1350年,与黄公望相谈甚欢。而得出这些体悟,我们才刚刚从手卷走到诗歌前面。
从手卷到诗歌,无边的想象力在受到文字解读抑或生发的同时,也开始进入一种受限的范畴;而从诗歌到戏剧,从纸张到剧场,时间从凝固变为短时流动,空间从二维走向多维,鲜活灵动的同时意味着易逝,升维拓展给了观众更多满足的同时,也呈现出想象的边界。如前所述,大量的介质被调动起来辅助表达,但因为剧场作品自身的现场感、时限性,除非所有或主要的表达被观众立时捕捉,否则,表达的真相,只能在转瞬间与我们擦肩而过。
作为一部非常规的剧场作品,戏剧《随黄公望游富春山》创作之初就注定了其不可能具有大众性。但是,即使小众,即使阳春白雪和者寥寥,知己可遇难求,但只要有,就已然可以算作一种成功。而该剧2014年面众以来,参加了不少展演活动,也收获了不少赞誉,2016年底豆瓣评分7.2分,即使现在也还有6.8,比起很多同类来说,委实不低。只是,在这一片赞扬及肯定声中,很难说没有夹杂人云亦云、皇帝新装般违心的称颂。因为确有很多熟稔画作及诗歌,或者观剧前认真做了攻略的“我”们,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真正进入该剧现场,无法达成共鸣、生发观剧喜悦。坐在剧场中,不断涌现出来的各种观演阻隔,挠拨出“我”无奈的憾叹甚或质询:“我”,该如何进入现场!
阻隔之一,主体不明晰
我们知道,改编是基于原作基础上的再创作。原作者的思想固然重要,但改编者的意志更加关键。设若,在手卷面前,我们感受到了黄公望;在诗歌面前,我们感受到了翟永明;那么,在戏剧现场中的我们,是否应该充分感受到编创者?可事实上,我们在剧中更多感受到的是翟永明,或其代言人。大量的翟永明诗句被直接诵读推送到观众面前,虽然辅以现代舞者的肢体语汇,多媒体手法在实验音乐中渲染,甚至翟永明的声音直接出来声情并茂地为大家读诗,但这些都只是翟永明。翟永明的诗歌、翟永明的困惑、翟永明的思辨、翟永明的批判,翟永明与黄公望跨越时空的会面,翟永明穿越古今的女性身份反思……虽然剧中那个具有串场功效的,样貌声音甚至表演都非常不起眼甚至败笔的女诗人,一直在强调诗人的普遍和普通,但全剧最为凸显的意志,却始终都是翟永明,而非这位诗人,亦非该剧编创。
诚然,翟永明的诗歌始終带有其特有的气韵流动,主观、客观,有形、无形,有生命、无生命,其身份也在不断地变换或幻化。因此,作为翟永明诗歌作品的剧场呈现,将翟永明作为剧作的主体,不仅并不简单,而且还有利于更多的观众了解诗人和诗歌。当然,编创者意志的隐形有些可惜,但对于熟稔翟永明长诗的“我”们来说,强调“翟永明”也许更有利于“我”进入该剧现场。可惜的是,即使是“翟永明”,也并未贯穿始终。很多人都津津乐道的相声读诗一节中,男逗,女捧,大家听得津津有味,不停爆以善意及会意的笑声,但是,在翟永明的长诗中,这两节一改之前“渔樵耕读”的那些男性话语方式,第一次刻意凸显出翟永明一贯的女性意识……显然,这里的主体不是翟永明,那么,又是谁?
阻隔之二,手法显粗糙
编剧周瓒在一次被采访中说,出于戏剧性的考虑,增加了一场人演皮影戏,介绍黄公望那件传世画作的传奇身世。且不说编剧下意识将戏剧性等同于故事性是否正确,只看这一表现手法,却是做得很不精致。那块兼具画布、时空分割线、多媒体投影屏的白色幕布,这一节中充当的是皮影表演必需的隔亮布。布后的“影人”表演,很多动作都显粗糙,有的甚至不像影人,只是真人在幕布后自娱自乐。白幕后刚讲过爱画如命的吴洪裕临终前要求其侄将《富春山居图》“焚以为殉”,幕前的演员又讲述了一遍“焚以为殉”的传奇,也许不能算作粗糙,但至少显得表述不简洁,衔接不精准。
另外,《随黄公望游富春山》中大量使用现代舞解读现代诗歌。剧中的五个演员中,至少有三个是专业的现代舞者。剧中不乏使用精到的现代舞桥段,但那段一个现代舞者在幕布后以舞姿描摹倒流人生或进化论的手法,却因过于直给,感觉非常粗粝。
戏剧主体不同也许并不容易被人发觉,表现手法的粗糙却是触目而惊心的。好在戏剧虽是遗憾的现场,却也具备了不断修订和进步的可能。如果编创团队调整好心态,稍稍假以时日,解决掉这些问题应该并不算难。遗憾的是,心态是另一个“我”进入现场的阻碍。
阻隔之三,心态欠沉稳
或许是编创者受翟永明影响太深,或许,从诗歌到戏剧,这个过程沉淀得还不够充分,再或许,面世以来得到热情的关注和广泛的赞誉影响到编创者的冷静,该剧呈现出来的编创心态很不沉稳。戏剧主体不够明晰,表现手法上的粗糙,归根到底都是编导心态不稳的体现。说是90分钟的表演,100分钟过去还没有结束的意思,戏剧结构中各部分内容的设置是否需要调整?表演者对戏剧节奏的掌控是否还存在问题?这些不仅体现出编创者对节奏的把控存在问题,更需要反思的是编创者们的心态。
作为一部演出时,诞生已逾两年的剧场作品,其戏剧主体、表现手法,以及戏剧节奏方面体现出来的种种问题,即使加入演员更换等客观因素的考量,也依然令人质疑该剧的创作态度不够精益求精。于是,台上演员表演越卖力,“我”可能反而觉得越造作。这种质疑和反感一旦产生,就很难遏制,很可能溃成汪洋。除非“我”是专业戏剧人,一般观众很难冲过汪洋继续保持进入该剧现场的渴盼或热情。
“我”该如何进入现场?提出这一问题也许会促生观众和作品的融合,作品实现有效表达,“我”顺利进入了现场;也许更激起观众对作品的不满或质疑。但是,每一部文艺作品都有其相对的局限性,所有人都喜欢未必是好事,很多人不喜欢未必是坏事。尤其对于《随黄公望游富春山》这部以戏剧表现诗歌的戏剧作品或者剧场作品,泛戏剧也好,大戏剧也罢,尝试、探索、勇于追求使用更多介质,承载更多层次的表达,这部作品在戏剧本体上的意义已经超过了其作品本身。
所有问题的提出,都意味着解决的开始。观剧“反感”,总强过观剧“无感”。“如何进入现场?”这一问题固然体现出“我”的困惑和质疑,却同时更表现出“我”的挣扎和努力。征询也好,质询也罢,若没有对戏剧的喜爱甚或热爱作支撑,一切,都不可能存在。
“我”该如何进入现场,不只是《随黄公望游富春山》,答案依然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