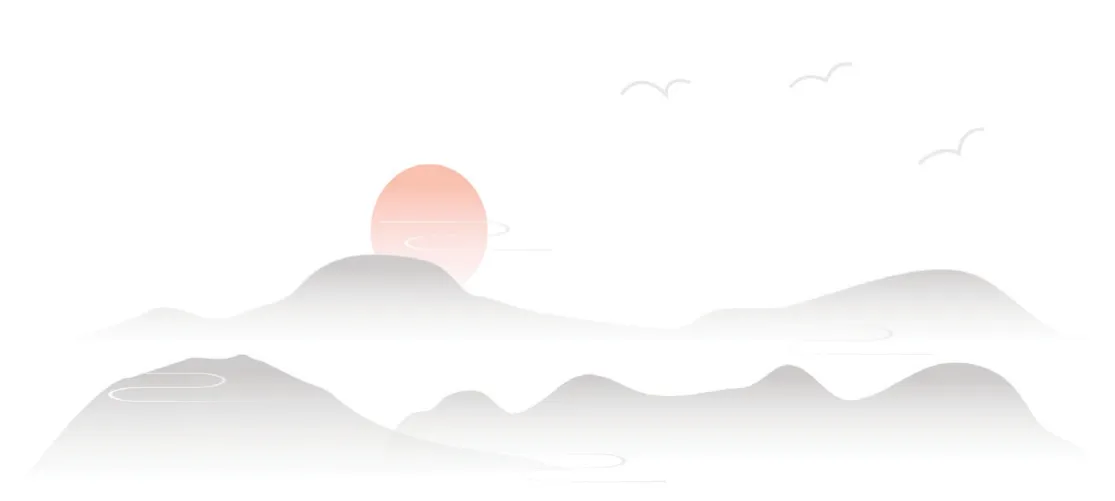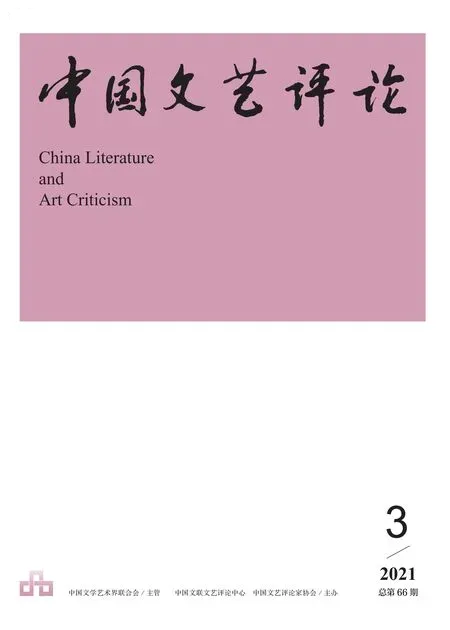钟嵘“滋味说”批评标准的生成与启示
余开亮 张 烁
刘勰的《文心雕龙》与钟嵘的《诗品》是齐梁年间文学理论著作的双璧,二者都在坚守儒家传统思想的基础上呼应时代的变化,提出了更具合理性的新美学观念。本文试图立足于钟嵘《诗品》“滋味说”的具体内涵,在晋宋时期美学经验与诗风新变背景下,阐释钟嵘是如何将诗学传统与时代新变相结合而提出“滋味说”诗歌批评标准的。通过对历史个案的梳理,以期给当前文艺批评推进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供一条可能的思维路径。
一、钟嵘“滋味说”与传统儒家诗学
钟嵘以“味”论诗源自先秦的味觉文化,更具体地说是来自于儒家以“味”论礼乐的思想传统。许慎《说文解字》云:“味,滋味也,从口,未声”。“味”作为一个哲学美学概念在先秦就较为普遍。在老庄那里,“味”是体道的一种方式与境界,表现形式是一种“淡味”;在儒家那里,“味”在饮食文化的基础上引申出两种主要内涵:一是指大飨之礼乐的“大羹遗味”之感,表现形式是一种体现至敬之情的简素“本味”;二是指礼乐形式多样性统一及其带来的生命和谐感,表现形式是一种“和味”。从味觉隐喻上讲,儒家最理想的人文世界和生命世界都应是五味的调和,是一种几种味道相成相济、“以他平他”的“和味”。相较于道家味觉思想,讲究多样感性形式统一与内在情理中和体验的“和味”当为儒家味觉论的特性。《论语·述而》所载的孔子闻韶乐,所体验到的“三月不知肉味”之味,实来自韶乐尽美尽善的和谐。《论语·学而》也载有子云:“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
“味”这一概念大量进入文学理论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一方面,刘劭、王弼、嵇康、阮籍、玄言诗人、宗炳等发展了道家的“淡味”“无味”思想;另一方面,陆机、刘勰、钟嵘等人则发展了儒家的“和味”思想。陆机《文赋》论及文章之病云:“或清虚以婉约,每除烦而去滥。阙大羹之遗味,同朱弦之清氾。虽一唱而三叹,固既雅而不艳。”“阙大羹之遗味”源自《礼记·乐记》的“大羹不和,有遗味者矣”。不过,陆机引用时已脱离了《乐记》“大羹不和”“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的伦理教化语境,只是认为简约清虚的文章缺乏一种余味,并将“雅而不艳”视为文病之一。继陆机在《文赋》中以“味”论文之后,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也屡次使用“味”来品评诗文,如“余味”“可味”“遗味”“道味”“辞味”“义味”“滋味”“味之必厌”“味飘飘”等。陆机与刘勰虽以“味”论诗文,但“味”并未在他们那里自觉成为一种范畴,而更多的是在评论时附带谈及。到了钟嵘的“滋味说”,“味”与诗文之美的密切关系始得以根本确立。
钟嵘的“滋味说”作为一种批评标准,其提出的目的乃欲对当时诗坛盛行的五言诗予以“辨彰清浊,掎摭利病”。其《诗品序》(《诗品·总论》)云:
夫四言,文约意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耶!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
因《诗经》的典范效应,四言诗往往被儒学思想家视为雅言正体,所谓“雅音之韵,四言为正”(挚虞),“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刘勰)。与视四言诗为诗文正体的保守理论家不同,面对“云会于流俗”的新五言诗体,钟嵘不是予以打压与漠视,而是积极主动地肯定了其“居文词之要”“众作之有滋味者”的存在地位。钟嵘将五言诗抬升到比四言诗更高的位置,足显其面对新文艺的胆识魄力。不过,这种胆识魄力并不意味着钟嵘走向了儒家的对立面。相反,从《诗品序》对气化宇宙观、物感论、诗言情志等观念的论述可以看出,钟嵘是一位明显具有儒家思想倾向的理论家。其“滋味说”的提出,既坚守了传统儒家精神的基本内核,又以一种新的内涵发展了传统儒家诗学。
钟嵘的“滋味说”对传统儒家诗学的继承与发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针对“诗刺道丧”“兴义销亡”的诗坛现状,钟嵘再次高扬了儒家的“兴”“比”“赋”三义,并赋予了三者不同于儒家旧说的新内涵。《诗品序》言:“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兴”“比”“赋”源出于先秦两汉以来的儒家《诗经》六义。儒家《诗经》六义讲“风”“赋”“比”“兴”“雅”“颂”。《诗大序》云:“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以郑玄为代表的汉儒对六义诠释道:“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郑玄以“美刺”释义比兴,从政治教化的角度阐释诗之六义。钟嵘则从诗之六义中直接截取了“赋”“比”“兴”,将其重新排序为“兴”“比”“赋”,既继承了传统儒家诗学的诗学手法,将其作为五言诗的三义,又赋予了三者不同于儒家旧说的新内涵。钟嵘指出:“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可见,“兴”即“因物起兴,言尽意余”。“兴”使得诗文中蕴含“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的无穷情味;“比”即“因物喻志”;“赋”即“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这里,钟嵘对“兴”和“比”的解释都直承儒家起情言志的诗学传统而来。只不过相较于《诗大序》的“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的“诗言志”面向,钟嵘更强调比兴皆“因物”而起,并在其“滋味说”理论中突出了“物感”之“物”的形象性美学价值(“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物感”之“物”不再仅仅作为“仁智比德”的道德象征,而是注重二者的贴切性(“因物喻志”)。“物感”之“感”也借由对物的直接感受而更显切实与生动(直书其事,寓言写物)。“滋味说”对“兴、比、赋”的弘扬与酌而用之,对物象形象性、直感性的注重都表明了钟嵘对传统儒家诗学精神的继承与发展。
其二,钟嵘所言的诗之“滋味”为一种多样丰富性的美感,是对儒家“和味”思想的进一步审美化。在钟嵘看来,一首诗好不好,品第高不高,关键在于作品是否有“滋味”。可以说,“滋味说”既是一种作品论,又是一种鉴赏论。《诗品序》言:“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五言诗“滋味”的达成需要“兴”“比”“赋”三种诗文创作手法,外加“风力”和“丹采”的配合。在诗歌手法上,钟嵘要求作者对“兴”“比”“赋”根据情境兼而用之。因此,他既批评了“专用比兴”而导致诗歌情意晦涩、文辞不直接(意深词踬)的问题,又批评了“但用赋体”而导致诗歌情意粗浅、文辞散漫(意浮文散)的问题。在诗歌情感内容上,钟嵘要求诗歌蕴含有“感荡心灵”的情志力度。在文辞方面,钟嵘要求用优美的辞藻来实现诗意的传达。这里,钟嵘从情志内容、辞采形式、诗歌技法方面,较为综合地对诗歌作品是否有“滋味”进行了规定。唯有在内容、形式与技法上做到有机统一的诗歌,如兼具优美的文采、鲜明的意象、动人的情志、深长的意味等,方能给人一种隽永动人的美妙滋味。在鉴赏论上,钟嵘的诗之“滋味”,正是源于诗歌作品的这种丰富多样性统一而带来的一种综合性美感。显然,钟嵘的“滋味”属一种五味调和的儒家式“味”美,是文与质、情与志、感性与理性统一的中和之美。
钟嵘对“兴”的文外余味的重释,对“比”“赋”的“物”的形象性、直接感受性的强调,对诗歌情志感染力与对诗歌辞采的重视,都使得“滋味说”真正成为一个足以批评诗歌艺术的美学尺度。可以看出,钟嵘提出的“滋味”是个美感经验极为鲜明的美学范畴。他既坚守了儒家诗学重情志兴发的比兴传统,又扭转了儒家诗教、乐教传统重道德政治性而轻诗歌形象性、直感性、辞藻性的弊端。钟嵘“滋味说”的这种新意蕴是时代诗风所带来的,明显受到了晋宋山水诗“寓目美学观”的影响。
二、“寓目美学观”下的诗学新变
相较于传统儒家的“和味”论与“诗言志”说,钟嵘以味觉经验论诗,凸显了诗给人带来的形象性、感官性等审美性内涵。这些审美性内涵与魏晋南北朝时期注重感性经验的时代背景是分不开的。也就是说,除了立足传统,钟嵘“滋味说”批评标准的生成还紧密结合了时代的文艺新貌。特别是,钟嵘以“寓目辄书”来评价谢灵运所引领的新诗风,显示了其对时代文艺新貌所带来的审美新经验的卓越把握。从根本上说,正是钟嵘对“寓目美学”的理论提炼,才使其“滋味说”成为了一个美感经验鲜明的批评标准。
自晋伊始,“寓目”感官经验开始在诗中被广泛书写,如潘尼的“驾言游西岳,寓目二华山”(潘尼《游西岳诗》)、庾阐的“拂驾升西岭,寓目临浚波”(庾阐《登楚山诗》)、王羲之的“寥朗无厓观,寓目理自陈”(王羲之《兰亭诗》)、谢万的“肆眺崇阿,寓目高林”(谢万《兰亭诗》)、谢灵运的“以为寓目之美观”(谢灵运《山居赋注》)等。正如萧驰所指出:“在庾 阐 的 诗 里,‘目 散 ’、‘盻 ’、‘观 ’、‘目 翫 ’、‘寓目’、‘运目’、‘仰盻’、‘睨’、‘眺’等词语大量出现。‘寓目’这个词也是自晋开始与赏玩山水的诗有了关联。”台湾学者郑毓瑜首次提出了“寓目美学观”,其这样定义道:“那是以物色形象先于情理概念,并以为目光所及就足以成就意义;换言之,耳目观聆不但成为创作首要步骤,甚且是主要活动,因此所见所闻的声色形构直为创作的主题内容,而不必须被重塑、归类以便成为情志之借代品,即此身观眼见即是所欲表现(包括对象与作者)的整体实存与价值”。可见,“寓目美学观”尤其强调亲历身观的当下活动,强调耳目见闻等感官感受的直接性与鲜活性。
实际上,“寓目”这一观看方式在以谢灵运为代表的山水诗中最为典型。陈昌明索性将山水诗称作“一种运用眼耳感官的视听文学”。通过运用视听感官,谢灵运的诗歌呈现出了更加逼真可亲、绘声绘色的山水场域和官能世界。钟嵘亦注意到了谢灵运山水诗作背后的“寓目美学观”。对于谢灵运及其山水诗,钟嵘评价道:“嵘谓若人兴多才高,寓目辄书,内无乏思,外无遗物……名章迥句,处处间起;丽典新声,络绎奔会”。可见,钟嵘对谢灵运“寓目辄书”的诗文运思颇为赞赏。纵使谢诗“尚巧似”时“颇以繁复为累”,但“寓目辄书”却也避免了“繁复”的诸多弊端,而使得谢诗如“青松”“白玉”一般清丽。可见,“寓目辄书”确是谢灵运诗歌的精义所在,其最美妙的诗句(往往是写景句)基本都是在“寓目”的当下得出的。钟嵘以“寓目辄书”来评论谢灵运,切中了时代诗风注重形象性、直感性与辞藻性的新特色。试看谢灵运《石壁精舍还湖中作》:
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晖。清晖能娱人,游子憺忘归。出谷日尚早,入舟阳已微。林壑敛瞑色,云霞收夕霏。芰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披拂趋南径,愉悦偃东扉。虑澹物自轻,意惬理无违。寄言摄生客,试用此道推。
谢灵运这首诗写的是他从北山石壁精舍经巫湖返回南山居所的经历与感受。这种进入山水亲身游历、身观眼见的过程,使得谢灵运所感知到的山水更为真实、更为立体,对景物的描写也十分鲜活生动。日斜欲暮,诗人归舟过湖,从昏旦光影的稀微、山光水色的辉映,到林壑、云霞的逐渐褪色,乃至芰荷倒映、蒲稗相依,诗人目观身历了一系列景物变换。经由诗人对其“寓目”“体物”审美经验的书写,景物的本然形姿不再模糊不清,一个真实不扭曲、活泼不僵化的本然世界如在目前。由此“寓目”的审美经验,谢灵运感叹“虑澹物自轻,意惬理无违”。这“理”不是别的,正是由“寓目”所开显的自然之理。由此自然之理的开显,诗人返回自然的本真性情,对身外之物无所计营;景物敞开本然形容,不再被情志道德所淹没;即便“昏旦变气候”,诗人也无需感时叹逝。诗人与景物不复相互投赠之婉转,而是彼此既相互独立又相因玄同。谢灵运的多数写景诗可谓长于物色与丽辞,但其“以理代情”却也有“酷不入情”之偏颇。
“寓目美学观”对物象感知的直接性与物象的鲜明性“直书”“辄书”,直接导致了山水诗“尚巧似”“重辞藻”的美学特色。刘勰与钟嵘都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刘勰对山水诗评价道:
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文心雕龙·明诗篇》)
自近代以来,文贵形似,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吟咏所发,志惟深远,体物为妙,功在密附。故巧言切状,如印之印泥,不加雕削,而曲写毫芥。故能瞻言而见貌,即字而知时也。(《文心雕龙·物色篇》)
钟嵘《诗品》中也认为“元嘉三雄”的诗文创作有着“尚巧似”的共同特点:
上品谢灵运条为:杂有景阳之体。故尚巧似,而逸荡过之,颇以繁富为累。
中品颜延之条为:尚巧似。体裁绮密,情喻渊深。
中品鲍照条为:善制形状写物之词……然贵尚巧似,不避危仄,颇伤清雅之调。
由上可知,最为晋宋时人所津津乐道的就是刻画景物、善制新辞的山水诗。以谢灵运为代表的山水诗在晋宋之际蔚然成风,“每有一诗至都邑,贵贱莫不竞写,宿昔之间,士庶皆遍,远近钦慕,名动京师”。在刘勰看来,山水诗对形似的追求,对景物“巧言切状,如印之印泥,不加雕削,而曲写毫芥”的精细刻画必然是以一种新型“体物”的审美经验为基础的。换言之,刘勰和钟嵘并不排斥“密附”“巧似”的体物之文。钟嵘更是将“指事造形,穷情写物”作为其“滋味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在注重藻采美文的时代潮流下,刘勰与钟嵘也都对“丽词”“丹采”在诗文创作中的重要性进行了强调。
由此可以看出,钟嵘对五言诗所带来的新的感官审美经验与典型特征无疑是深有体会的。结合这一新的体物经验,钟嵘“滋味说”的理论再创性得到了进一步的具体说明。
三、钟嵘“滋味说”批评标准的具体生成机制
钟嵘的“滋味说”体现了传统儒家诗学与新型诗学美感经验的调和。钟嵘站在历史与时代双重视域交融的高度,超越了传统与时代的局限,在诗学历史、时代与理论的语境下实现了新观念的具体再创。“寓目美学观”强调诗歌创作的“即景会心”与“寓目辄书”。“当钟嵘把‘寓目美学观’倡导的‘即目’‘所见’‘直寻’‘尚巧似’观念引入五言诗创作时,其关于五言诗的‘滋味说’评价标准就应运而生了。”可以说,正是由于诗学领域“寓目美学观”的出现和晋宋之际山水诗的兴起,嗣后钟嵘五言“滋味说”新意蕴的开拓才有了可能。
“寓目美学观”对钟嵘诗论的冲击是有迹可循的。钟嵘在《诗品序》中有言:“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对比陆机《文赋》的“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以及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的“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无论钟嵘,还是钟嵘之前的陆机和刘勰,三人都强调物、情、文的相互感发过程。这一感发过程便是“物感”模式的集中体现。“物感”的缘情创作模式直承《乐记》“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与《诗大序》的“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的言志创作模式,体现了从“诗言志”到“诗缘情”的言志缘情诗学观念的连贯性。言志缘情的诗学观念是以先秦两汉以来儒家气感类应的哲学观作为思想根据的。自《易传》的“阴阳交感而化生万物”至《乐记》所代表的先秦儒家乐教模式,一直到两汉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囊括“阴阳”“四时”“五行”等的气化宇宙图式,先秦两汉以来儒家的气感类应哲学都以气的交感类应来阐述万物之间的相互关联。总之,先秦两汉以来儒家气感类应的哲学观为“吟咏情性”的诗学传统奠定了基础。钟嵘的五言诗诗学理论也主要立足于气感类应的哲学观和“吟咏情性”的诗学传统基础之上。不过,钟嵘已然感受到了晋宋之际的诗风新变。故而,其“滋味说”在儒家言志缘情的主流诗学观念的基础之上,亦吸纳了晋宋之际的“寓目美学观”和山水诗“尚巧似”的体物诗学新变。
“滋味说”对“寓目美学观”的接纳和创造性阐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体现在钟嵘对“专用比兴”和“但用赋体”的批评上。比兴二法多用于儒家言志诗歌的创作。钟嵘对“专用比兴”的批评,表明了他对传统儒家诗学为服从道德政治性阐释而过度乃至附会式的引譬连类是颇有微词的。赋法则多用于晋宋之际以谢灵运为代表的山水诗文创作。钟嵘对“但用赋体”的批评,表明他对山水诗缺乏情志与社会担当也有不满。故而,在山水诗及其背后“寓目美学观”的冲击之下,钟嵘的“滋味说”要求对“兴”“比”“赋”酌而用之,既强调了赋法的重要性,又为比兴二法增添了“因物”的要求。显然,“滋味说”实现了言志诗学与寓目诗学两种审美经验的美感调和。
其二,体现在钟嵘对诗歌创作“即目”“亦惟所见”以及“直寻”的强调上。钟嵘在《诗品序》中曾直接标示出“即目”“亦惟所见”以及“直寻”的重要性,其论述如下:
夫属词比事,乃为通谈。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
钟嵘首先指出,“吟咏情性”的诗文不同于“经国文符”“撰德驳奏”的应用文。而“吟咏情性”的诗文中的古今胜语,又皆由“即目”“亦惟所见”“直寻”而来。钟嵘列举了一些秀句、胜句以作例证,譬如徐干的“思君如流水”(徐干《室思诗》)、曹植的“高台多悲风”(曹植《杂诗七首》)、张华的“清晨登陇首”(张华《诗·清晨登陇首》)、谢灵运的“明月照积雪”(谢灵运《岁暮》)等。正因为钟嵘对诗歌创作中“即目”“亦惟所见”“直寻”的重视,故而,其批评了当时诗坛“务为精密,襞积细微,专相陵驾”的诗风以及“用事”、“补假”、“殆同书抄”、过于注重声律等拘挛补衲现象。在钟嵘看来,缺乏真情实感而勉强硬作诗文,结果只能是“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拘挛补衲,蠹文已甚”。钟嵘曾在《诗品》中援引汤惠休的话评价谢灵运和颜延之二人的诗歌:“谢诗如芙蓉出水,颜如错采镂金”。这既是汤惠休对谢灵运、颜延之二人的评价,亦表明了钟嵘本人对二人诗作的态度。谢灵运“寓目辄书,兴多才高”,颜延之则“喜用古事,弥见拘束”。相较而言,钟嵘更赞赏谢诗的如“出水芙蓉”一般的自然清新以及“寓目辄书”的直接感受性,并将谢诗列为上品。颜延之则缺少“自然英旨”而位列谢灵运之下。清代袁枚曾作《仿元遗山论诗》一诗云:“天涯有客太詅痴,错把抄书当作诗。抄到钟嵘诗品日,该他知道性灵时。”由此可见钟嵘对后世文论重视性灵的影响。
这样,钟嵘的“滋味说”就在“言志—缘情”美学与寓目美学之间开辟出了一条中间道路。这条中间道路在萧纲那里亦有所体现。萧纲言:“寓目写心,因事而作”(《答张缵谢示集书》)。此正表明了写心与寓目的折中调和。钟嵘的“滋味说”一方面要求赋法的创作和“寓目辄书”,即在“指事造形”“直书其事,寓言写物”的过程中强调“穷情写物”、贴切刻画物象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要求“因物起兴”和“因物喻志”,即在“言志—缘情”的创作模式中强调“因物”当下喜怒哀乐与志气的鲜活呈现。故而,写景写事须得融主体情志于其中,写情志又须得借景借事来自然感发。这种自然之情志必不是依“用事”“补假”“殆同书抄”而来,不是一种拘挛补衲、牵强附会的生硬情感,而是由当下感受而带来的自然情志之抒发,此正是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说的“感物吟志,莫非自然”。
由此,在钟嵘的“滋味说”中,“寓目美学观”的直感经验被儒家“诗言志”的诗学传统所收编与调和,并在后世殷璠的“兴象”、司空图的“醇美”、严羽的“兴趣”、王夫之的情景交融等诗学理论中持续回响。由物的宏大式(道德的、政治的、宇宙的)的类应关联到物的情感化拟代(情的独立),再到物的寓目式直观(景的独立),最后复归心物交融(情景统一),中国诗学在总体上也有着一个“正—反—合”的理论发展过程。这一过程是物的诗性不断彰显的过程,也是物与个体审美品味、个体生命体验不断贴近与契合的过程。钟嵘的“滋味说”和刘勰的“情景交融”一样,算得上是儒家诗学发生艺术化、审美化转折的核心关节点。
四、余论:历史个案与文论创新
作为一种“流俗”诗体的批评标准,钟嵘的“滋味说”是具有创造性的。他在保持传统儒家诗学精神内核的基础上,又吸纳了新诗体的艺术新貌,实现了传统诗学的理论再创并发挥了切实的批评效果。钟嵘“滋味说”这一新理论生成的历史个案,对当下传统文论如何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而言不无借鉴作用。
在对待时兴的文艺新风方面,作为儒家诗学价值的坚守者,钟嵘对流行的五言诗持一种积极的态度。钟嵘在高度肯定其艺术特性与美学价值的同时,也看到了其中的缺失。新文学艺术的出现,是与时代的社会背景、人的精神需求等因素紧密关联的。文学艺术作为人类生活和生命精神的载体,始终通过感性符号的形式承载着、探寻着、反抗着人类现实生存的命运。文学艺术面貌的每一次创新和变化都是和人类生产、生活世界的变化息息相关的。要创造、欣赏、阐释文学艺术,都离不开对人的生活史的把握。这就表明,面对时代的文艺新潮,首先要积极面对而非拒斥与打压。只有在深入品评与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其典型的艺术特征、美学观念乃至时代背景,才能对文艺新潮有全面而系统的认知——既看到新文艺的时代性、先进性又看到其时代局限性。立足于文学艺术自身,是文艺理论创新的基点。
在对待传统诗学方面,钟嵘并未一贯守旧,而是用历史动态的眼界既看到了其所具的人文性、现实性精神内核,又看到了其有待发展与有待提升的感官性、审美性层面。文学艺术的发展与阐释是离不开历史以及历史理论的,任何文学艺术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时空中产生并被一定历史时空中的人来欣赏的。只有在艺术史与艺术理论中,人们才会知道每一种新的文艺运动实际上都是对原先文艺运动的创新,也才能把握人类文艺精神的演变历程。缺乏艺术史与理论史的知识,我们将无法理解文艺复兴时期的“复兴”所指何在,更无法对杜尚艺术的意义做出判断。艺术史与理论史提供给人们的是人类感性生活的开拓领域与反思诉求。只有立足于已经开拓的领域与已经具有的精神反思之上,才能进一步开拓新的领域以及实现感性经验的有效性扩展,让人类的感性生活更加完满。中国传统文论与美学承载了历代中国古人的艺术经验,为塑造悠久绵长的中华文明作出了贡献。这种最切近国民心理、生存状态的民族文化,在历史的多次洗礼中依然焕发着自己的生命力。只有以当代的眼界去回视传统,在历史事实与人文价值相统一的评价下,对传统文论与美学进行合理定位,才能对当今社会该弘扬什么、发展什么乃至放弃什么有较清晰的判断。
在理论创新方面,钟嵘的“滋味说”完成了传统诗学合理内核与新诗风新经验的辩证统一。这种辩证统一不是杂糅与随意叠加,而是有针对性的互补。五言诗的形象性、感官性、文采性正是传统儒家诗学的缺失处,而传统诗学的情志观、现实关切性也正是五言诗的短板。二者之间取长补短,恰能实现新理论的自然圆融,并在批评实践中生发切实之效。传统文论的当代转化与发展,需要在传统文艺精神与当代审美经验的对比、互看中寻找互融互通的可能性,并以此为基点来实现新理论的再创。
时代新变、历史传统、艺术理论构成了当代文论创新的重要基点。在时代语境中,积极主动地去感受新的文艺经验;在历史文化语境中,深入地去体验文艺变迁带来的审美精神的历程性与多元性;在艺术理论语境中,开放性地去反思文艺新旧范式的内在转换。也许,只有置身于一种多重语境交互的文艺框架或丹托意义上的“艺术界”中,才能对过去、现在乃至未来的文艺现象有一种较为清醒的辨识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