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面与空间
胡弦
画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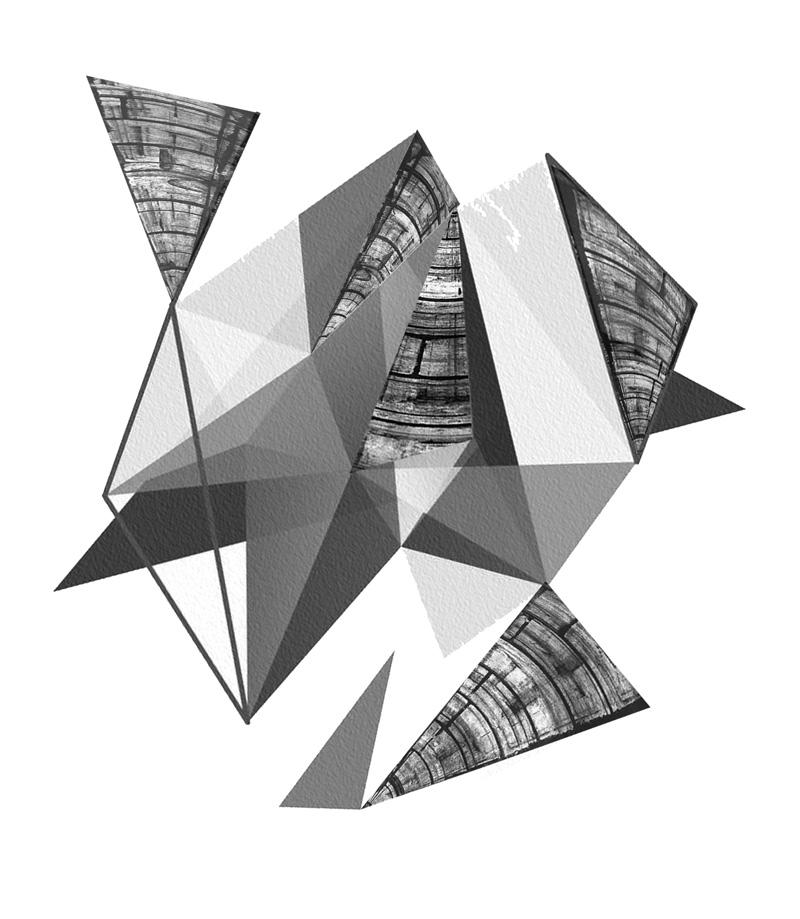
插画/陈俊
小巷里,一棵蔷薇开得红硕。它靠在老墙上,爬藤占据了一大片墙面。墙砖已有些剥蚀,刷的白粉也褪去了大半,连同老屋,已经带上了些许废墟的特征。但一大片繁花看护着它,仿佛世间最美好的心愿在那里。我站在这样的画面前,有点愣怔。美到极致的事物,会让人有些许伤感。我想,若须用漫长的伤感换取眼前这花开的一刻,也是值得的。
是的,你必须相信,花朵选择什么时候开放,选择和什么在一起,此中自有涵义。你不能仅仅用“一株靠墙的蔷薇在开”来表达这画面的意义。我在想,什么才可以称为“画面”?什么样的画面可以使一个细节成为故事性的存在?卞之琳说:“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写的是画面的生成。我还看过另外的一首诗,一个身居异国的诗人的作品,她写到有个来自老家(中国上海)的亲戚来看她,在地铁上,亲戚突然问她,出来那么多年了,是否想念老家?其时,她忽然瞥见对面车壁的广告牌上是一幅长城的图片,于是她凑近去,仔细端详烽火台,看到那烽火台的砖竟是红色的。她为何如此专注地端详几块砖?我想,那砖应该是她忽然找到的救生筏,她以此平静地呼吸着车厢里正在起伏的东西,而且能让人看上去仿佛处于无动于衷的静止状态,从而避免了失态。接下来,诗人说感觉随着车行的晃动,画里的野花和长城也都晃动起来。但读这首诗给我的是另外的触动,我忽然觉得,她观看的姿势,与长城广告画重新组合成了一个新的画面,在那画面里,她在不自觉中找到了新的角色。
画面,是一种诞生——它正是我们寻求、并希望从茫茫世界中出现的样式。它不是点缀,而是一个确立它存在的真理,它在呈现的过程中含着它的行动:它实际上是一个小的戏剧,不管它是视觉定格,还是一幅摄影或画在纸(布)上的作品,都如此笃定,因为它知道,观看者会补充,恢复其完整的情感动态。
生活中的场景随时会成为画面。沿着这巷子走下去,走到运河边,能看到一座古粮仓。我曾看到它的老照片,墙体斑驳,有反复粉刷又剥落的痕迹,还有旧标语的痕迹,残破,沧桑,被废弃已久。而现在,它被改装成了一座饭店。一切都变掉了,粉刷一新,配上了水车和木质的门斗,挂着红灯,在画面中,那红色照着砖青色,有深宅大院的感觉,古旧里泛着新鲜。就画面和其文化感看,一切都顺理成章,仿佛一座粮仓里本来就藏着一个饭店,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而一座粮仓的前后两幅照片,差距如此之大,仿佛拍的不是同一座粮仓。作为画面,它们各有讲述,如果前一座沉浸于记忆,并在对现实的陪伴中有些窘迫,后一座,则更专注于现在——它正离开粮仓,努力使自己成为另外的东西。
现在来讲讲有次我们去粮仓里吃饭的事。这是个雨天,又是傍晚,灯亮了。因为内外的灯都亮着,粮仓的笨重感消失,变得轻盈,甚至有点半透明的感觉,像一只大灯笼。雨也是透明的,但在黑暗中看不见,只有靠近粮仓时,雨丝才显现,一片片红光被分给雨,仿佛世界上的雨正围绕一座房子在落下。进到内部——很少有人真的进到一座古粮仓的内部,虽然很多人都已落座,且墙上有介绍这座粮仓的文字和图片——它们既是介绍,也是装饰。但我们——是的,我们仅仅是来到了一座饭店的内部。
从图片介绍看,这座粮仓有六百年多年历史了,它还曾是避难所、兵器库、废墟……但现在这些都已无关紧要,偶有人去瞄几眼那些图片。我从注释上注意到,这些图片(多为文字和绘图)大都来自古籍。它们平时静静地躺在纸上,现在,出现在饭店的墙上,仿佛没有美味相佐,历史也是难以消化的,这让人觉得,粮仓,改成一座饭店真的是太合适了。
我有点恍惚,也许是喝了一点啤酒的缘故,在现场,有点走神的时候又像坐在历史深处,有些话说出来时,像是给不在场的人听的。墙上的文字多看几眼,周围的喧嚣就仿佛小了很多,图片在讲述,但还是有很多地方被漏掉了,比如穷人的胃,富人的味蕾,国家的消化系统。当有个声音在讲述,仿佛有种秘密的职责一直存在,就像我们的咀嚼那样自然,而此刻,因为有所察觉,窗外的雨也像一种讲述——多少建筑消失后,雨穿过它们曾占用的空间,那被目睹的雨,并不讲述从前。只有在傍晚的灯光中,它们才像一种声音,讲述无数消失的雨夜,以及在古老的时代,那些连夜入城的船,以及许多人难以下咽的命运。一座粮仓,属于遥远的世代,但要取消和我们之间的距离,总是轻而易举。文字、手绘,一旦化身图片,就试图在我们的味觉中不断下沉。
回来时再次路过那条小巷,看见那架蔷薇,已没有花朵,绿沉沉的,墙角还放了一辆自行车。这已是路灯下的另一个画面。地上有些滑,砖墁地和墙根都有绿苔。这些微小的植物在雨中生长,也许有我们不熟悉的食欲。
空间
1
直视的时候,我们出现在对方的眼睛里:一个小人儿。
只有直视的时候,眼睛里的水才稳定下来。它曾是流动的,漂移不定的,或者像旋涡,像因为被丢失而变得茫然的水,现在,它清澈,安静,是从所有水中抽身而出、返回此地的水,记起了它深泉的出身。“是的,你在那儿,所以,这水如此明亮而纯净。”
但那小人儿只是成像,只是一个影子。他并不真正生活在那里。相对于恋爱的人。影子是平面的、二维的,它本身并不发生和傳递感情,它从三维空间而来,但它感受不到三维世界的存在。它可以落在任何地方,但对那里也没有任何感知。
那么,我们的爱恋从哪里来?我们会不会是谁的影子?当我爱你,另一个空间里的人也恋爱吗?而如果有某种联系存在,我们是否就是另一个空间中正恋爱的人?作为四维的人,他们的爱是什么样子?当我们拥抱——是否就是他们的影子拥抱在一起?
长时间凝视对方的眼睛,会让我们有点不舒服,所以,我们还是拥抱吧——我发现,在我们因拥抱而产生的姿势中,总有不舒服的姿势产生,当然,和甜蜜相比,这根本不算什么。这是情不自禁的结果,一如凝视那样。我们拥抱,我们把自己从眼睛里拯救出来,这时,我们的影子也拥抱,并消失在彼此中——只有影子能真正叠加在一起,且不占用任何空间。如果它们也在爱着,那一定是和我们完全不同的爱。而影子的影子又是什么呢,有没有一种一维的爱,隔着消失的空间,我们永不可能望见它。
执手相看,此一瞬间,被从无数的动态中提取出来,被固定于记忆中。相比于滑动的生活,我们更喜欢存在于那被固定的瞬间。但那瞬间也会变化。“我多么爱你呀!”这声音在我心里回响。而你眼睛里的我,正像个溺水者。另外一些时候,我的心并不发出声音,而那小人兒,像一片枯叶落入你的心灵,我望不到它,我们彼此都失去了它。
2
他人讲述的黑暗,总类似盲人的眼讲述的黑暗是另一种黑暗。
在小花园里,在一棵高大松树的下面,他知道那异样的黑暗,和它含有的内容。有时它认为,如果时间中毒了,空间也会扭曲,比如接吻时,特别是他的唇第一次碰到她的唇时,他觉得周围的时间忽然中毒一样,像碎屑般纷纷掉落身旁。那种黑暗,带着渴念,仿佛是黑暗的源头,吸走了空气中所有的振动,令人吃惊。天穹深广,但真正的黑暗只存在于一棵松树下,它在膨胀,又因受到挤压而使处身其中的人有些眩晕。木椅光滑,露水从一片树叶滴落到另一片树叶上。蛐蛐在鸣叫。一种一切照旧的氛围像一个真空般的黑暗空间是最好的陪伴。后来,他的背倚靠在树干上,那时他就意识到,树干那粗糙的感觉会一直留下来。若干年后他才发现,那粗糙,其实已成为他后背的一部分。若干年后,他仍清晰地记得那树下的情景:一个秘密的空间。当他们离去,那空间并没有跟随他们离去——它一直在那里,带着它保存的内容。像一种苦行,一个空间重新创造了它自己。
3
雷声远去,天地间,似乎比原来空旷了许多。
现在,雨正穿过那空旷。和雷声在一瞬间对自我的完成不同,细雨是缓慢的,透明,几乎无声,它是及物的,能准确地找到最细小的花瓣的嘴唇,它爱着密闭在花瓣里的尚未被打开的空间。
旧雨新枝,光,顺着草尖滑行到很远。而宅院素朴,有最小的家神流连的温暖。窗玻璃上斜挂着雨点,纸上是一只刚画好的蝴蝶。岁月空旷、自由,我们说着不着边际的话。风吹向芒果,像吹着一种不真实的香气。窗外,是峰峦、丹枫、老工厂、白杨树小径。郊区的生活,像一只陶罐那样完美无缺。而在更远的地方,连绵细雨催发了山的暴力,溪流冲撞着深涧,犹如你的躯体在薄衫内颤动。我熟知那暴力,——仿佛在另外的空间中,我学会处理闪电的方法,以及如何向你轻声细语。
4
门前,海棠开得绚烂,香气没完没了,像我们小区里漂亮的女邻居。当她走动,总像带着一个迷人的空间。
她的老公像块茎一样强壮。块茎,我曾怀疑,他即便被埋在地下也不会死掉。
几个人在演奏,这是一个草台班子吧,很多有红白事的地方,他们都会出现。邻居去世,所以,我才确认那是哀乐。看客们沉默着,他们的沉默像音乐的支流。
我仔细听那乐声,跟随它们,似乎可以越过某些界限,窥见另外的空间。后来我明白过来,我跟随的不是乐声,而是我自己的情绪。有人在谈论那个世界,以及壮汉的死因。是的,它们都已在人间存在很久了,在我们的描述中有了不同的面孔,有人,以悲伤地描述它们为生。而艺人们对此从不开口,他们给所有人送去的是同一支曲子。他们弹拨的手指、凑向笛孔的唇,还是对这边的情景知道得多一些。
乐声一阵一阵响着,它们在讲述什么。对于人类的生死观,它赶到时,是不是已经太迟了?我倾听那乐声,它仿佛在无所事事地响着。要多听两遍,才能感受到它想变成我心灵回声的强烈欲望。
海棠花开着,依然绚烂。我忽然觉得,那些花朵对于我们的处身之地,知道得也许比我们要多得多。
色·戒
1
他经过珠宝店。灯光璀璨,变幻,像未知的爱情。他看见招贴画上的“克拉”一词。前面就是电影院了,他转头寻找,女友似乎还没到,至少他没有看见她。街上人来人往,重建这样一条具有民国风情的街道是正确的吧,几乎是全天候的,这里总是挤满了人。他再次转头,仍没有找到要找的人。他忽然有种像在一个旧时代做暗探的感觉,不觉笑了一下。他盯着“克拉”一词几秒钟,觉得那词其实是一个声音,因为当他转头走向电影院的瞬间,他听见自己的颈椎骨里“克拉”,轻轻响了一下。
而她却正在珠宝店里。她喜欢首饰,喜欢透明或半透明的东西。她有一只玉镯,戴了太久,内有云絮状的东西若隐若现升起,她觉得那是她轻盈的灵魂偷偷逸出了身体,跑到美玉中玩耍。她喜欢玛瑙的红艳,翡翠的冷碧,唯独看见切割精美的钻石就有些迷惑。据说,所有的珠宝中,只有钻石能代表纯净和恒久,其它的,都不能。钻石,那就是最好的爱吗,或者,是比爱情更好的东西?跟随着她目光的移动,机灵的店员敏锐地转换着描述的对象,以确保在他的赞美中,她的目光停驻、审视的每一件东西都是动人的。她观察着钻石,一个放大镜递到她手中。是的,这是电影外的镜头,男友还没到,电影中的钻戒,还要再过几个小时才出现在镜头中。她很奇怪,为什么距离每一座电影院不远的地方都会有一家珠宝店,而每一粒钻石看似相同,其实都是不一样的。店员调整了光源,放大镜下是一个迷人的世界。她看到,钻石的每一个陡峭的棱面上,都有光在跌倒。但更多的光随即簇拥着补充进来。而在钻石内部,耀眼,沸腾,是一个光的浩大墓场。她并不知道,几个小时以后,另一个女子——彼时,她觉得那仿佛是她本人——于那光中费力地抬起头来,找到了自己那两片毁于一旦的嘴唇。她借助那嘴唇朝男主角说:快走!
2
他想回忆起小说里的章节,可全忘了,像电影开始之前银幕上出现的空白。“电影,是小说做的一个梦。”——他有点走神,看看身边的女友,如此专注,仿佛已沉入旧时代深处。她的手曾握在他手里,不知道什么时候已被她抽走了。
“听说这个地方被删了不少。”他偏着头朝她小声说。
“嘘——”他醒悟到,他们正坐在一群观众中间。
其实,没人受到打扰。所有的眼睛都紧盯着银幕,盯着人体叠成的曲别针。
他有点羞愧。他一直改不掉容易走神的毛病,特别是,女友那么专注的时候。胶片正在放映机里无声滑动,一些细小的光斑正从那里轧过(其实,现在的电影院早已不用胶片了,只是他没有察觉。他记得的,是一种联系新旧时代之间的东西)。他有时甚至觉得,自己也是一个死者,扁扁的,就像胶片那样,被卷起来,放进一个黑暗的匣子里。某些特定的时刻,它被打开,借助一种特殊的设备来救活中,并从中取出他的一生。
没有谁被饶恕,一种可以重复的时间,总是无情地轧过,并再来一遍。
3
交换一个眼神,然后,又出错牌了。麻将稀里哗啦响着,她想用手指肚触摸到麻将凹槽里的凉意。他们刚才碰撞过的目光,还滞留在空气中,粗糙地摩擦。
據说来过这条街的人,每个人都曾去过民国,并在那里有不同的遭遇。无论在电影院、成衣档、咖啡店,还是一些收集并出卖古董和假古董的店铺,每个人都曾在恍惚间变成过另一个人,仿佛遇见了自己的前世。一些店家,也会用旧时代的图片、繁体字等来营造这种氛围。你究竟想生活在哪里?打麻将,哦,那太out了,但是,如果只是一个短暂的幻觉,就像电影中的一个镜头那样,闪现,旋即就回到现实中,则有种类似自救的快乐。而且,如果再沉浸一下,并稍稍延长一会儿,隔壁酒吧的嘈杂,听上去也许就饶有趣味。然后,她去打电话——由于只是代入,她不必探究数字里的隐患和她的嗓音拖动的情节,她说着,隐语中的人在转移位置,甚至,她发现自己内心里隐藏了很久的一座审讯室。这有点吓人,但不是真的。现在,作为一个观众,一个局外人,她似乎又瞥见了另外两个男人,一个在倾听牌局的变化,另一个面孔阴晴不定,躲在一座日式房子里。他们眼里都藏着火焰,一个的在倾倒出灰烬;另一个的,在远方铁屋子里女囚的伤口上燃烧。
4
他一直试着去理解那里:一个潜伏在房间深处的大海。他能肯定的,是自己曾在其中死去过,只是想不起每次都是怎样生还的。他感觉到身体里在慢慢涨水,窗外,大街喧嚣,话匣子响着,无轨电车在行驶,但不发出声音。窗帘落下来,灯线、衣架、电视机,和有点儿木讷、笨重的床,像一群种属不明的海洋生物。水开始起伏,然后是波浪拍打——他制造波浪又承受那波浪。那是欢畅,又带着点儿喜极而泣的悔恨般的拍打,就要把他身体里的青春与中年清晰地分离出来。那是些因意识到自己存活太短才陷入疯狂、不想去理解任何东西的波浪。在这样无法自控的拍打中他试图确立他对一个大海的权威。他加速,仿佛有了一颗类似一艘蒸汽轮机的轰鸣的心。床很结实,也许是一张清朝的床。黑暗浩瀚,而光在尖叫,——他像有了起飞的能力,一次次冲撞、犁开海水,扣住了海平面那翻腾、灼热的肩胛。哦,真的像一个极乐的幻觉,野蛮的快感在传递,在掠夺陌生地理的动荡。是的,他也放弃了去理解什么的打算,身体,掠过一片片不熟悉的海域,然后,又拐进一条隐秘通道的内部。那一定是不属于此生的另一个世界,柔软而湿润,像一个梦境,像是由另外陌生的时间构成。他释放的力,仿佛可以改变它的结构,令人幸福的错觉,他认为身体里有某种从不知道的东西,正离开他逃向黑暗深处。后来,像在一个港口,本打算经过的他,靠了岸,带着放松下来的海水。闹钟滴答,世界回到身边,已是黄昏,空气里带着点儿感恩的气味。房间静了,那种静,浑浊、温热,带着远洋归来的疲惫与惬意。
5
她渴,但手边的饮料无能为力。
有一刻,她察觉到了男友心中的异动,自己也稍有不安。银幕上的光在男友的发际、镜片、肩膀上闪烁。她的感觉是,原本习惯了的依靠,竟消失了。
她笑了一下,仿佛整个人被一个笑容送回尘世。
6
“那一次,你可以的。”
一个埋伏在他心中的人,仿佛是恋人。他记起了公共汽车上,冰凉的雨点,和随着他的话语吹在脖子上的热息。
只要走神,你就是一个有秘密的人,仿佛有两个他在平行生活。他记得向女友说“我爱你”时的感觉,仿佛又是说给另一个人听的。因为他记得,在旧时代,他的确曾向另一个女子这样说过。有时他宽慰自己说,在那样的时代里,那个人还不是自己,并以此稍稍减轻歉意。但一部电影总是给人这样的感觉:它无意展示未知,只是在帮助你恢复记忆。他甚至记起了那反复出现的第一次。“不会太疼的,就像窗户纸一捅就破……”——他转过了脸去,不想看那凭空出现的唯有他一个人能看得见的画面。
颤抖和生疏总会再来——当然,如果在另一个空间的时间走得快一些,它们就早已过去了。他让手指安静地穿过她的头发,并自然地落到她白皙的肩膀上,或者熟练地调一杯糖水给她,让她重新学习呼吸,让她在他的抚爱中,把散掉的身体重新找回,并拼在一起。他说,“转过来。”他们的脸出现在镜子里。他感到,转身时如果携带的故事太多,就会有些费力,而自己的面孔也会有些陌生。这一次,出现在镜中的,是她两片刚刚涂好的嘴唇,明亮,鲜红。她佩戴着首饰,但没有钻石——他还不是那个有了权势、能给她买起钻戒的人。那时候,时间好像也稍稍放慢了脚步,房间内是让人感动的安静,薄薄的玉蝴蝶别在她的旗袍上,柔和的光与影正流过,像一阵若有若无的音乐,在绸布上起伏。
7
跋涉了许久,悬崖终于出现了。电影镜头突兀的处理,仿佛把早已消失的过去突然幻化成了让人心惊的现实。
他们的手握在一起,体会着各自心中的悸动,甚至忘掉了自己正坐在电影院的座椅上。
但当他们震惊的时候,银幕里的人已镇定下来。他们跪着,他们相互看了一眼,回到了刺客的身份。两个失败者,后者,已从她心底浮出,挨着他,如此真实。他在她心底躲藏太久,以至于看上去有些陌生。他们甚至觉得,她从镜头中向电影院里张望了一下,仿佛看见了他们,看见了带着点儿青涩气息的大学岁月。
悬崖黑乎乎的,他们发现,那黑暗是垂直的。长长的黑暗,会让随后的坠落找不到结尾。“放映一旦结束,你就再也找不到他们。”——最后,他们变成了永远的失踪者。
而他们,则变成了受到枪声恫吓的恋人。有什么样的问题从电影院里被带了出来?走出电影院的时候,他们听到有人在争执。
天早已黑下来。他们默默走着,不说话,有种类似枕骨被抽走后的安宁。他们从珠宝店前走过,沉浸在电影的某个情节中,没有察觉到珠宝店已关门了,直到拐过街角,一回头,看到珠宝店的飞檐翘在夜光中,侧墙的装饰灯线,一根一根亮起,又一根一根暗了下去。
脚印
1
雪刚落下来的时候,毛绒绒的,踩上去没有声音。等雪停了,天晴了,往往一两天过去,雪上就会结一层冰壳,再踩上去,就有了晶体断裂的声音。
已是连续两天的好阳光,原野上的雪像还没有被动过。河边是一条小路,现在在雪下消失了。我散步,已走出了村子,沿着河继续往前走,发现前面是一行隐约的鞋印。我熟悉这种情况,许多天前有人从这里走过,那时,雪下得紧,他在雪上踩出的脚印旋即被雪掩盖,现在,阳光准确地找到了它们,使这些脚印露了出来。有的脚印里的雪化得快,已率先露出了泥和草根。
我继续走,想起多年前,我也曾这样往前走去,那时,没有雪,我也意识不到村庄正被我抛在身后。
脚印不见回头。再朝前,拐个弯,穿过废弃的砖瓦厂,是通往县城的路。从村子到大路,这是一条捷径。大路上由于车辆来往,已没有雪。大路边没有专设的站点,但去县城很方便,那些客车,招个手就会停下来,把人捎上。
——我不再跟随。生活,只是偶尔把我带回到这河边,带到这雪后的散步中。我往回走,脚下的雪,不断发出骨折的声音。那些脚印已和我的行走相反,望着它们,总像有个人在迎面走来。我停下来往后看,又仿佛能隐约看见一个人远去的背影。几天前,风雪正紧,那是一个什么人在雪中走出了家门,赶往远方?
几天前,我还在南方的城市。冷,但没有雪,天是蓝的,银河大厦也有严峻的蓝,大厦间,是城市高天切出的峡谷。广场边摆放的小菊花,有薄薄的雪意。我从那里路过,几个农民工在埋管道,其中一人在指挥,我从口音听出他是我的老乡。我们聊了几句,抽烟,他是我邻县的。其他人一直在忙碌,他们刨地,使劲地刨出沥青、石块、不明之物的根须。走出几条街,我似乎仍能听到那洋镐的声音,仿佛庞大的城市有人在动它的趾骨。
而乘列车回故乡,雾气笼罩的清晨,那么多山峰破雾而出,像要闯进窗口里来。它们那么熟悉,又那么陌生,仿佛仍有需要确认的今生。
2
树林整齐,挂着雪。夕光,粘连在树枝和雪上。这树林,全是意大利杨树,在现在的苏北已是广为种植,因为它长得快,属速生树,多数被用来制作板材。我记得这里早年也是一片树林,杂木甚多,有刺槐、土桃子、苦柳、酸枣、臭椿……那时也有杨树,品种与意杨完全不同。杂生的树林,每当有人走过,会惊动老鸹、黄鼬,或者某只假寐的野猫。高高低低的林子,那时我为何并不觉好?而现在,这林子来自新的种植法,有严格的株距,树干都笔直,万千小枝指向天空。我察觉到,即便是在山中,在大野深处,也没有一座村庄是隐秘的,一直以来,一种紧跟时代的不为人知的力量在作出决定。此中,有我似曾熟悉的渴望和陌生的安静。站在这样的林子里,有时空气中仿佛总会飘来记忆般的声音,可只需一阵北风,就能把所有事物的嘴唇合上。意杨笔直的树干和整齐的枝条,仿佛已变成某种象征,不会附和我对岁月的浅薄领悟。整齐,仿佛磁力线,再造了我们胸中的磁场。
河里芦苇苍黄,顶着雪。河边有个板材厂,被剖开晾晒的意杨树木板,也白花花的,像雪。厂子里电锯嘶鸣,那尖锐的声音,并不能给乡村带来热闹,相反,现在的乡村越来越寂静了,因为青壮年大都已进城务工,还要等上一段时间,到了年关,他们回来过年,才好带给村庄短暂的热闹。
几只鸟巢在树杈上晃动——只晃动,不把任何东西传递。现在的鸟儿,似乎也比过去少得多,几只乌鸦在林子里飞来飞去,仿佛是岁月淘汰后剩下的品种。相比于麻雀等鸟儿,乌鸦很少进村,所以,在我们的印象中,它一直都是神秘的。在本地的一个传说中,乌鸦在旷野里建造过宫殿。但没有人到过那悲凉之乡,乌鸦,仿佛只为某种预感而存在。一个鸟类学家告诉我,乌鸦是无法接近的,它也从不接受问询和请教。每当我们以为自己参透了尘世,乌鸦就会盘旋着,像一道幻影,天际,传来它怪模怪样的哇的一声。
在故乡,也许只有我这样偶尔返乡的人更能察觉到不安。所有岁月,都是已被珍惜过的岁月。但激越的天空下,仍有难以抚慰的艰辛。一行隐约的脚印在推敲我们的过往。雪不会无缘无故落下和消失,只要它还没有化尽,就会有脚印把一个人的现在和过去连接在一起。而那些被混淆的日子,就仍然是可以区分的。
地铁
1
我有时觉得,一列地铁知道一个人心中的孤寂,而喧嚣,是用来簇拥沉默的。
地铁在运行中,迅捷,呼啸,强大而有力,但仍然不能用它来处理命运,也无法用来处理一个人在人流中的身影。
大部分人都在看手机,行李箱颤动着,它也孤单,但没有人留意它的孤单。有时候人太多,人们挤得紧紧的,生活,像一个被压缩、无法展开的游戏。当地铁进站,更多的光涌进车厢,随着它停稳时的一下颤动,所有人,都在自己的角色里松了口气。
地铁停一停就会开走。地铁站的灯光是明亮的,如果有人相遇,一定要在那明亮的光中。如果有人告别,也是在那里,启动后迅捷加速的地铁,也许能带走一部分感伤。
地铁停一停就会开走。它的行程里有分段的黑暗。它的灯明亮又温暖。有个人在地铁站发呆,一列列地铁,一定给他捎来了不为人知的东西。另一个人拉上套衫的拉链,戴上耳机,沉入音乐中,但要在歌声里遇见他,不容易。
离地铁口不远有个烧烤摊,我晚上加了班回来,出了地铁,会在摊子上坐坐,吃一点烤肉。摊主油光满面,总是笑眯眯的。这是郊区的地铁站,摊主的车子后面有时会拴一只活羊。“血债累累呀!”从这只羊的角度想一想,该杀的人太多。
摊主的老婆不识字,信耶稣。她晚上在烧烤摊熟练地数钱,谈起赞美诗一脸虔诚。她是幸福而满足的。地铁,正在烧烤摊下呼啸而过,但面对人间难题的时候,它好像并不比一个烧烤摊更有办法。是的,这是个难题:绵长余生,我们该怎样面对呼啸而行的地铁(它大过了个人命运的需要,又或者,它对我们的命运毫无兴趣),和一个飘溢着香气的烧烤摊,尤其是,面对摊主夫人那满足、幸福的赞美诗。
2
另有一次,加班到很晚,我在站内等最后一班地铁。由于疲惫和困倦,候车的人都不怎么说话。灯光也像倦了,比平时似乎昏暗了些。人群出现在挡板玻璃深处。而那玻璃,现在像一面镜子。在那镜子里,我们仍旧站在地板上。那地板不是真的,是我们脚下的地板在玻璃内的投影。那地板下面,是两条冰冷幽暗的铁轨。我看了看指示牌,还有几分鐘地铁就要进站了,我忽然意识到,那么多人正处于危险之地而不自知。这让我想起另外的一些场景,我的影像曾悬浮在公交车、高铁、摩天大楼的窗外,或某个重大事件运行的呼啸中。我总是在不经意的一瞥中,看到自己处于危险之地。在生死攸关的世界里,我曾凝视过自己,并忧心如焚于周围那些不知灾难将至的人。而那灾难真实地存在着,但当你想开口说出它,它马上又消失不见了。
现实就是这样,总在验证着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它的真实存在,这一生,我都苦于无法论证出它的存在。现在,又是这样的时刻,一道强光解开了我的焦虑。这是进站的地铁的灯光,它一瞬间剖开了玻璃里的映像,真实地停在我们面前,带着庄严的凉意。它停稳,我们挪动脚步,它即将装走这个城市里最后一批回家的人。
责任编辑 吴佳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