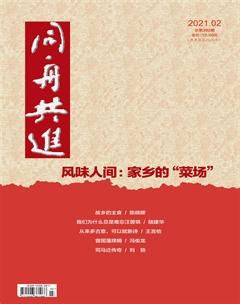故乡的主食
陈晓卿



人的口味就是这样,有时像岩石般顽固,有时又像流水一样豁达。
【回乡,一场碳水的狂欢】
清明时节,是我近些年几乎每年一度的期待。走走亲戚,见见故旧,说起很多往事……当然,口舌之欢也必不可少。
老家地处淮北,著名的粮食产区,肥沃的平原一望无际。但这里历史上一直战事不断,水患频仍,饥荒的年景甚多。因此,精细菜肴没有系统传承,百姓的日常食物,也无法和长江流域的富庶之地相提并论。更多见到的,是刚刚能够带来温饱的主食。老家人在这些主食上,可谓下足了心思。
主食,对现在的我来说,更多的时候像敌人——因为要面对不断衰退的消化能力,以及日益增长的体重,尤其是晚餐的主食,我是尽力回避的。但回了老家,要保持淡定很难。人就是这么奇怪,食物非常简单平常,但只要是小时候吃的,它就自然拥有另一种味道,不时萦绕在你脑际,反复考验你的意志。更要命的是,即便经受住了主食的考验,在老家的很多家常菜中,碳水化合物照例“明目张胆”地出现在那里。
比如清明时节,正是所谓青黄不接之际,那是吃野菜的当口。樗不揪(樗树花)、香椿芽儿、榆钱儿、槐花等渐次登台亮相,尝个鲜吧?
蒸榆钱,先焯水,然后撒上面粉拌匀蒸透,就着蒜汁一起吃,别有一番清香。但此时,你再理性也不能分清,到底吃的是野菜,还是面粉。即便是种植的蔬菜——芹菜、豆角,也被老家料理成了野菜的样子,当然还有鱼汤里“潜伏”的,用蛋清和精粉做出的水疙瘩……看到这些,不免自暴自弃,既然全部菜肴已经主食化,也就不去想什么戒断。回乡,不免成了一场碳水的狂欢。
同学聚会,酒酣耳热。有人高声问大家:“吃馍?吃米饭?”这是主食准备登场的标志,接下来理应是小麦的二黄或者稻米的流水。吃馍……”我笑着说。同学老邱站起来,一脸嫌弃:你哪有脸吃馍!”老邱对我拍美食纪录片这么久,却还没有把故乡的食物介绍给全国观众耿耿于怀:“吃馍,你应该去阜阳,不要回家。”《风味人间》团队曾在阜阳拍摄了“枕头馍”,节目播出当晚,他就发微信表示抗议——在他眼里,只有我们老家的东西才是最好吃的。这种朋友我认识不少,理论上我把他们称作食物的“故乡沙文主义者”。
其实,我自己也觉得老家的手工馍好吃,圆圆的,松软清甜。一般来说,馍就是指发面馒头,但老家分得细:圆馒头叫“馍”,而刀切馒头则被称为“卷子”——用老面让面粉发酵,醒两三小时后,等面膨胀起来,加碱水反复揉制,搓成长棍状,用刀从中均匀切开,上笼屉蒸,出锅便是松软而有弹性的卷子,也叫“白面卷子”。
称它“白面卷子”,可能是为了区别于当地的花卷——和好发面,用擀面杖擀成两尺见方的大饼,涂抹上少许葱花、猪油渣和芝麻酱,卷起,切块来蒸,剖面上有好看的螺形花纹,味道也好吃得多。白面(小麦粉)价格略贵,也有人家擀两张饼,一张白面的或一张玉米面(或红薯面)的,贴在一起卷起切,口感和味道都不如前者,但视觉上黄白相间,也很好看,叫“素卷子”,是巧妇的作品。
在老家人看来,给和好的面粉赋予味道,有各种各样的方式,也配得上各种各样的智慧。我最喜欢吃的一种叫“菜卷子”,面无需发酵,用大擀面杖擀成薄薄的饼,抹上猪油,撒上肥瘦各半的肉末、葱花、芝麻和花生,卷成大大的长条,切开后贴在柴灶的铁锅边,下层放水,很快,饱含油脂的菜卷子便出锅了。上层松软、鲜香,呈半透明的诱人光泽,下层焦黄酥脆。有了它,根本不需要做菜。
还有更简单的,那就是“喝饼子”,北方也叫“贴饼子”。
幼时家境不好,有客人不期而至,蒸馒头显然来不及,喝饼子就是最好的选择。在面盆里和好面,最好偏软一些,放在那里醒一下,让面的口感更筋道。同时也腾出手做菜,接下来的菜可能是烧干豇豆或者萝卜土豆烧肉,偶尔也烧一只小雏鸡——大灶旺火,葱姜爆炒,添酱油、水和八角焖烧。加锅盖之前,把和好的面分成小剂子,拿清水蘸湿了手,把面剂子挤压到很薄的状态,用力迅速齐整地贴在锅边。偏软些的面,表面持续保持下垂,一直延展到烧菜的汤里。加盖后改小火,一刻钟后即可起锅,这时,菜和饼子同时熟了。薄薄的喝饼子已经被锅边炕得起了迷人的锅巴,而伸到菜汤里的部分又吸饱了肉香。制作喝饼子,对火力的控制不能着急,加锅盖之后,一定要改用文火。
喝饼子的技术含量并不高,我小时候就做过多次,而且也很喜欢吃。记得二十多年前,在广西龙脊大山深处拍片,摄制组每天三顿主食,都是当地出品的红米饭,就是那种没有去除苞衣,吃起来非常剌嗓子的米做成的饭。半个月后大家开始抗议,红米饭口感很差,更关键是对我们这些电视体力工作者来说,它不“扛饿”。所以,我一直惦记着,写信托人到山外买点米面,计划给大家换换口味。
后来有朋友从桂林来探班,果然带了一袋五斤装的面粉。那天,组里有厨师证的老李,准备用蛇肉段加青蒜,做一个灵川干锅,我劝他不如改作红烧,而自己准备就着这个蛇锅,直接做喝饼子。
村子里的小朋友围在我们的驻地外面,看见我们吃蛇就已经十分惊诧了,更绝的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面粉这种麦子磨成的白色物体。我剪开塑料袋,开始和面,窗口边一帮小姑娘哇哇叫着散了去,我赶紧叫住她们询问究竟,一个叫乾梅的一年级女生,挠着头不好意思地翻译着同伴们的瑶族话:“陈叔叔你好可怕,连洗衣粉都要吃呢!”
黄淮海地区,几乎每个和我差不多年纪的人,大都贴过饼子,这种粗粝便捷的主食制作方法,带着物质匮乏时期深深的烙印。有一天,当我们依然像从前那样,对着这種简单美味的食物大快朵颐,却隐隐觉得,这些死面疙瘩,居然那么难以消化?嗯,应该是我上了年岁了。
【父亲的“缸贴子”】
家父是个烧饼爱好者。
有回吃披萨,全家都吃得很欢乐,只有他,手捧着一牙儿,眉头紧锁:要是把上面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去掉”,他嘟哝道,“兴许就好吃了”。我常年出差拍片,每到一地,都会寻找当地的面食,尤其是烧饼——这是受我父亲的影响。
烧饼吃久了,慢慢也摸索出一些规律。在我们广袤的国土上,这种烘烤而成的面饼,尽管制作手法大同小异,但从天山脚下的脸盆大小,一路向东,逐渐缩小,到长江下游时,已经手可盈握。新疆的烧饼叫馕,制作方法相对简单粗放,而到了苏杭一带,小小的蟹壳黄已经有很多细密的分层,工艺以及辅料也复杂一些。如果从西向东,把各地的烧饼摆成一排,看上去更像由大到小的一串行星,从中不仅能够看到面食流变的痕迹,也和地域物产的丰饶程度大体相关。
我的老家,理论上属于大中原地区,因此在烧饼这件事情上,能够看到来自东和西两个方向的影响。从烧饼制作的方法到它的外观,老家的烧饼分两大类:油多,起很多层酥的,我们叫“油酥烧饼”;以面为主,很少放油,有点甜咸各半的,则叫做“缸贴子”。
老家的油酥烧饼,需要一个水缸当内膛。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水缸是过去人家用来盛放清水的容器,司马光砸缸的道具,开口大,收口小,粗陶制成。把水缸倒扣,锯掉底部,下方生火,缸壁的弧度让炙烤非常均匀,尤其是上层封盖了以后。
做油酥烧饼的面要醒得足够,在案板上反复揉制,轻轻一抻,不致断裂,在擦了油的案板上一扯,一摔……我小时候以为这就是打烧饼中“打”字的由来,后来才明白,在中文语境里这种说法比较普遍,新疆叫“打馕”,陕西做月饼也叫“打月饼”,有部讲陕北故事的电影《啊,摇篮》,其主题歌就有这样的词:八月十五月儿明呀,爷爷给我打月饼呀,月饼圆圆甜又香呀……”
每次摔打和抻开后,都要用小面杖擀成长条儿,然后涂上厚厚的调料,调料的主味是盐、猪油、葱花和胡椒粉。再搓成卷,最后擀成饼状,沾上芝麻,一手相托,由下而上快速贴紧缸壁。贴好的烧饼起酥后出炉,还要在炉边继续用较低的温度烤制,直到它外表焦酥,一口咬下,碎末飞溅。宿州南乡祁县镇,烧饼用驴油打底,状如马蹄,谓“马蹄烧饼”,在我老家最为有名。其实,这种做法在苏、鲁、豫、皖各省都能见到。
比油酥烧饼更极致的是一种叫“油酥馍”的,在我出生地安徽灵璧县称之为“火食”,我猜测,这或许是中原官话“火烧”的变异。它是在一个平底的鏊子上不断刷油煎制,待蓬松起酥之后,再刷油,置于炉膛内和炉口边分两次烘烤,结果是由里及外的酥脆。这种油酥馍最好吃的方法,是起酥后用铲刀从中间一分为二,灌上生鸡蛋继续烤,那种香是让人垂涎欲滴的。、
不过,比起油酥烧饼和火食,我父亲更偏爱“简版”的烧饼,也就是缸贴子。望文生义,面饼在水缸内一贴就成。这实际上和西北地区的馕,长江流域的“草鞋底”(江阴的一种烧饼)大同小异。缸贴很瓷实,一个大约二两(100g)左右,用发面制作,长方形,沉甸甸的,大小可以遮住孩子的脸。发好的面,醒透,摔打成细长的条,只抹一点点混合着油的葱花,卷起,用手按扁,再用小擀面杖往两头轻推。面饼贴进炉膛内,遇热迅速膨胀,有巴掌这么厚实,外表焦香,内瓤却不分层,但底部会被缸壁炙出诱人的焦壳。
尽管操作简单,缸贴子也有油酥烧饼没有的工艺环节。那就是烘烤之前,打烧饼的,会在生面上用刷子轻轻扫上一些糖浆水,再敷上几粒芝麻。糖水和面遇热,散发出炙烤的香气,这就是一百年前法国化学家发现的“非酶褐变反应”,也叫“美拉德效应”,它能刺激享用者大脑分泌多巴胺,产生快乐的感觉。在我后来制作的美食纪录片里,“美拉德”这个词被反复提起,烤鸭、烧猪……凡是靠热辐射制作的食物,几乎都存在着美拉德效应。
但我坚信家父并不知道美拉德是何物,他偏爱缸贴子的理由,除了他自己解释的“火食油大,太腻”之外,我分析可能也有价廉物美的因素。对于他这一代人来说,缸贴子显然更实在,耐饥,能迅速带来温饱的感受。
童年时代的记忆里,家父十分严厉,但在外面,他又从来谦卑随和、谨小慎微、与世无争。上世纪90年代初,我和妹妹们都大学毕业,分配在北京工作,父母身边一下清静了许多。为了我们方便回家,父亲作出了一个决定:奔波长达一年,把工作调动至铁路沿线的宿州市。那时,他已经年过半百,突然改变工作和生活环境,现在想来是需要勇气的。
当时,新单位还没有解决住房,父母暂时租住在宿州市府巷一个逼仄的民房里。我们几个子女,不免开始后悔,或许当初不应该有回家路途漫长的抱怨,也担心他们人地两生的各种不便。一向乐观的父亲,在来信里,却把新家描述得非常舒适,同时,他还特地注明:一出家门的巷口,就有一个卖缸贴子的小摊,“每天都能吃到刚刚出炉的烧饼”。我后来还特地去看了那个地方,烧饼摊儿已经改成了煤气烘烤,味道大不如前。但父亲还是很激动地买了一只,很烫,一边走,一邊换手,边吃边吹。我站在一边看着,心里想,也许他确实太喜爱这种东西了。
从美食的角度看,油酥烧饼或者火食,无论口感、香气、质地、外观,都应该属于高一个层级的食物,但这并不能改变父亲对缸贴子的热爱,曾经的一段经历,或许更能够解释其中原因。
我父辈家境清贫,兄弟姐妹甚多,父亲是七兄妹中唯一的幸运儿——18岁那年,他考上了合肥师范学院(今安徽师范大学),这意味着生活费用由国家负担。那是1959年,大学的饭菜非常寡淡,曾有史书这样描述当时的学生食堂:早上洪湖水(可以见底的粥),晚上浪打浪(菜汤),中午小二黑(两个红薯面窝头)。当时他每月的菜金是9元钱,而当时合肥市区,计划外的猪肉价格,议价每市斤8元。
大二那年,父亲去安徽纺织学院看望同学,路上看到一个打烧饼的小摊儿,一个面饼,没有粮票要卖到6角,这相当于他整整两天的菜金。踌躇再三,父亲最终买了一个。“这是我一生中吃过的最香的烧饼,每一口都香”,父亲如此说道。
父亲多次说起的这段人生中的烧饼故事,我是不久前才听到完整的版本。1960年,横穿合肥市区的那次看望同学的路上,他还有一个同伴,一位来自大别山区的同班同学,恰好这位女生也有一个高中同窗在纺织学院就读。两个学校之间有十几里路,食堂的伙食几乎支撑不了这段行程,在遇到那个烧饼摊的时候,父亲犹豫了半晌,买了一只烧饼,然后分成了一大一小两块,把大的那块递给了女生,自己很快吃完了小的部分后,咬着嘴唇,静静的,看着女同学一点一点吃完。
如你所知,这个女生后来成了我的母亲。
半个多世纪后,我的儿子乐乐决定去海外念大学。临行前,母亲自然准备好了一些反复打过草稿的叮嘱。祖孙间谈到了学业,谈到了生活,也谈到了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比如恋爱。奶奶拉着孙子的手,乐乐温驯地坐在那,用非常大的耐心,听老人讲完了这个完整故事。奶奶最后总结说,分烧饼的那一刹那,她觉得爷爷一定是个好人,会一辈子对自己好。“将来,无论你找一个什么样的对象,其他都是次要的”,奶奶说,“一定要心好”。
【故乡滋味与“世界胃”】
十七岁那年,我北上求学。站台上,全家人给我送行。我面前是一个大旅行包,还有一个硕大的包袱,用背包带捆得很紧,里面是我的衣物和一床新被子。我媽站在一旁,又递过来一个书包,里面鼓鼓囊囊。天气很热,我一面示意他们回去,一面把装满食物的书包递还给我妈,“北京什么吃的都有,用不着这些”,我显得很不耐烦。
“为什么不报考南方的学校呢”,她总是轻声地嘟囔,“听说北京的粮食供应里,还有四分之一的杂粮呢”。母亲是中学教师,对学生说的是艰苦奋斗建设四化的大道理,但归结到自己家里,她还是希望儿子有更好的生活条件。
母亲出生在江淮之间的六安县,大学毕业时,为了爱情,和父亲一起来到了皖东北的小县城教书。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她总会用很长的篇幅,怀念大别山区我外公外婆家的小山村,风景有多秀丽,腊肉有多解馋,糍粑有多香甜,蔬菜的种类有多丰富。甚至连简单的用糯米面制作的饼子——糯米粑粑,都被她形容得神乎其神——要用什么样的米和糯米搭配,泡多久,怎么磨,怎么蒸,怎么放到石碓里面舂,最后要放到冬水里保存……说起来,她如数家珍。
妈妈关于故乡的表白,我们习以为常。其实我去过外婆家,小村子并没有像母亲描述的那样山清水秀,外公家的房子也非常低矮,家中的饭食种类更是少得可怜。童年时的我认为,淮北平原无论是地形上、气候上,还是物产上、食物上,都比大别山区好。我小学的乡土教材里,有这样一首诗:
有人说它是南方,
有人说它是北方,
南方和北方手拉手,
坐在淮河的岸上。
看看,南北适中,不冷不热,多好的地方。几乎我身边的所有人都告诉我,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
不过,外婆的山村,也以另一种形式存在于我们淮北平原的家里。每年冬、夏两季,父亲都会拿着包裹单去邮电局,在高高的绿色柜台后面,有外婆定期寄来的包裹。夏天会是一种节梗很粗的茶叶,叫“瓜片”,味道奇苦,但非常耐泡。冬天寄得更多,咸肉、咸鱼、腊鸭、腊鹅,还有“传奇”的糯米粑粑。外婆家的糯米粑粑不是我的最爱,一个个实心儿的、呆头呆脑的圆饼坨坨,比粮站供应的用糯米做成条状的年糕,颗粒感要粗一些。但我大妹妹在外婆家长到了五岁,她比较爱吃,我妈则更是甘之如饴。
粑粑简单蒸一蒸,立刻会变得软糯,蘸上白砂糖,可以直接吃。我妈还喜欢把粑粑切成块,放在菜汤或肉汤里煮,口感也不错。即便是用火钳夹着它,在灶膛里轻轻地烤一烤,也有奇异的谷物的香气。每次看到孩子们吃粑粑的时候,流露出对食物的渴望,我妈都会特别得意,并为她是一个“南方人”而深深自豪。
南方富庶,北方贫瘠,这是母亲的逻辑。其实,这种直觉判断大体符合事实。翻开中国农业发展历史,有文字记载的农作物栽培记录可以证实,大约在春秋时期,齐国出现了两年三熟制的小麦耕种技术,这使得山东在很长时间里,一直是中国最富裕的地区。物产和人口是农业社会最显性的标志,尽管秦、汉均建都长安,但关中平原的人口密度一直都不及齐鲁大地。而自汉代以后,中国的农业GDP高点,慢慢开始向南移动,将近一千多年的时间,一直没有离开过长江三角洲。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江南一直是中国的经济中心,人的生活也就更富足一些。
当然,这并没有影响一个十七岁的高中毕业生的选择。这一年的九月,我到了北京,在崭新的环境里开始了大学生活。然而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开始感到哪里不对,剔除想家的因素之外,最主要的就是食欲不振。按说,广播学院食堂在北京高校里算做得不错的,我和同学们也偶尔凑份子“进城”去吃北京的馆子,但这些,都没有办法平复我对家乡食物的思念。
一个人,确切地说,只有当他离开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离开自己的家庭,到了完全陌生的地方,才会理解:所谓的故乡不仅仅意味着熟悉的人群,也不仅仅意味着熟悉的景物,熟悉的味觉习惯,显然也是故乡重要的组成部分。
我有一位科普作家朋友,叫土摩托,他对美食家笔下所谓的“故乡滋味”,或者“妈妈的味道”是这样解释的:除了人在童年时代养成的味觉习惯之外,每个人的消化系统菌群都像自己的指纹一样,有着独特的组织方式。长时间吃惯了一种或几种食物,肠道的菌群就会相对固定下来,只要遇到类似的食物,就能熟练地进行各种分解。而遇到了陌生的食物,它就会手足无措,甚至会闹情绪。
在北京读大学的第一个学期,我的肠胃一直在闹情绪,直到我寒假回到家里,报复性地吃喝了一整天,世界才逐渐安静下来。等再次踏上去往北京的列车,我的包里已经放满了各种故乡的食物:烧鸡,酥糖,腊鹅……还有我妈妈特地留出来的糯米粑粑。
说到这次糯米粑粑,还有一个小故事。大学同宿舍有一位维吾尔族同学,看到我挂在床头网兜里的粑粑,几次欲言又止。终于,他说这个东西,听说是大油做的……其实,外婆家的粑粑是纯素的,除了米没有添加任何的东西,不过为了维护我们的友谊,我决定改变每天消灭一块粑粑的节奏。与别的同学分享吧,一来不舍得,二来别人也很难理解其中的美妙。那天晚上,我买了点儿大白菜,和着方便面调料,煮了一饭盆汤,把剩下的五块粑粑全部放了进去,全部吃完后,撑得我直翻白眼。
至今想来,十七岁那年的离家,是我成长过程中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它让我切实感受到了一个叫“故乡”的东西,不仅从心理层面,也从生理的层面。与此同时,我开始主动尝试和接纳更加丰富的食物——读大学之前,我甚至不能吃辣椒。假如没有十七岁的远行,我现在会不会也会像母亲一样,成为一个口味界线非常清晰和狭窄的人呢?会不会是一个“故乡口味沙文主义者”?真的说不好。
后来我成了一名纪录片导演,职业需要我不停与人打交道,而食物恰好是人与人之间交流最便捷的媒介,用现在流行的话说——没有什么是不能用一顿饭解决的。为此,我不得不带着好奇心,品味各种匪夷所思的吃食。渐渐地,我变成了一个“世界胃”,可以出国十几天不吃一顿中餐,心安理得地享用几乎所有的在地食物。
更难得的是,我开始从餐桌上发现,食物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慰藉肠胃的物质,它身上富集的信息既有鲜明的个性,又有非常强烈的生活气息。即便是同一种食物,在地球上不同的地方出现,它既会有同一性,又会有差异性,有时异曲同工,有时又南辕北辙。所以我总结:吃百家饭,行千里路,等同于读万卷书。食物与所在地区气质的某种勾连,以及食物自身流变的秘密,一直深深吸引着我。
就拿粑粑来说,这种稻米制品,通过不同的加工手段,居然能演变出那么多美食——粉、圆、粽、糕、糍、丸、糟、糜、堆……即便是和粑粑性质类似的年糕,也有不同的称呼。仅在广东一地,客家人称之为“粄”,潮汕人称之为“粿”,而粤西人则叫它“籺”,这一切,是多么有趣的现象。
游走在故乡和世界之间,寻找风味,寻找人和食物之间的关联,这一切,都开始于十七岁那年的远行。回顾这些年吃过的饭,走过的路,《风味人间》有句旁白很能代表我的感受:人的口味就是这样,有时像岩石般顽固,有时又像流水一样豁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