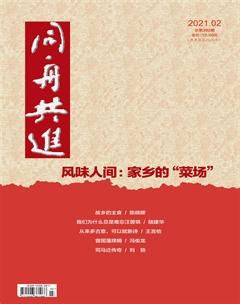菜市场:人间烟火气,最是抚人心
黄馨慧


每到一座新的城市,建议你不妨去三个地方看一看——博物馆、夜市和菜市场。如果说认识一座城的风格是不带目的地四处溜达,想了解一座城的历史可以去博物馆走一遭,要领略一座城市的灵魂,去夜市和菜市场则再适合不过,是它们,使一个城市更有温度。
汪曾祺老先生曾在《食道旧寻》中提到:“买菜,也多少是运动。我是很爱逛菜市场的。到了一个新地方,有人爱逛百货公司,有人爱逛书店,我宁可去逛逛菜市。看看生鸡活鸭、鲜鱼水菜,碧绿的黄瓜、通红的辣椒,热热闹闹,挨挨挤挤,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
陈晓卿老师也说:“我们去一个城市,一般就会去名胜古迹、所谓的地标建筑。其实了解一个城市的最好方式,是去看它的菜市场。用我的话来说,这样才和这个城市有了肌肤之亲。名胜古迹都是‘西装革履的,装扮得很好。但是菜市场装不了,它想装都装不了。”
美食家陆文夫每次请客人吃饭,都会坚持自己去菜市场买菜。他觉得买菜、切菜、做菜,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别人不能代劳。袁枚在《随园食单》也写过,一桌好菜,买菜功居四成。、
很多人喜欢去菜市寻寻觅觅,只为那一口滋味。也有人起个大早赶个早市,就喜欢那股子最新鲜的“朝气”。在观察摊贩和客人买卖间的互动中,我们可以看到人性的趣味;从亲手触碰的各式肉类和蔬果中,我们学会了辨识食材的好与坏。孤独的时候去菜市逛逛,还能感受到久违的人情味儿。
【菜市场里才有“意外”】
一个城市最有朝气的地方,可能就是早晨的菜市了。宛如连接都市人与大自然的一个中介,在那里,“鲜活”是一项重要的商品竞争标准。从一葱一叶,到辣椒、茄子、西红柿……在有限的空间里,一个个摊位紧密相邻,缤纷多样的农副产品被密集地陈列,这是一幅高度浓缩又有序的图景。赤橙黄绿青蓝紫,丰富的色彩与线条相间交织,活色生香,顿时让人的心情开朗起来,这让买卖双方的兴奋和愉快都溢于言表。
要想快速了解一个城市的胃口,就得来这里。比如云南的菜市上就有很多鲜花和菌子,东北的菜市到冬天会摆上大箱的冻梨和冻柿子,在广州的菜市里很容易看到各种生猛海鲜,成都的菜市里往往有一个专门卖各类火锅调料的窗口。
除了特别精品的超市,在主流的超市里,其实可供选择的食材算不上特别丰富。现代超市讲究成本和效率,从价格、货品、供应链到物流,背后是一套完整的核算系统。超市看似全面,挑选的却往往是稳定而大量的单一品种。而在菜市里,总能遭遇到很多产量不高、也不算大众需求的品种。这还不只是单纯种类多少的问题——一个能卖七种姜的市场,比如有高良姜、南姜、沙姜、红爪姜的,跟只卖五种姜的市场相比,所带来的幸福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别看只差了一两种姜,幸福感强的人,才会分出这么多细致的味道来。
更特別的出现在朝露一般的早市里——多半只在早上7到10点之间开启,会随机出现一些“流动摊贩”:他们往往是附近的乡镇居民,随着时令不同,带着各色产品进城售卖。有新采的野菜,比如南方的扣子菜、菊花菜,自家院里树上开的槐花、榆钱,或是自给自足又稍有富裕的口粮……
它们可遇不可求,多半得靠碰运气。这便是菜市场带来的乐趣,去超市是有目的地“寻”东西,而去菜市场则是“相遇”,这些特殊的食材,也往往最让人念念不忘,广东话里这叫“食过返寻味”。
随着季节流转,菜市场总有小小的食材变化,但只要这个城市这个地区具有活力,居民有所需要,这些变化就会永远延续下去。
【每个菜贩,都可能是一位隐藏大厨】
去菜市场,总会感到“方便”和“快捷”,摊主们往往会帮你把食材处理了,因为卖家们各显神通,方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制胜。
老板们仿佛个个身怀绝技:抓一把韭菜,就是半斤,分毫不差;斩一段肋排,两斤左右,正合买家心意。水产摊前,鱼头往砧板一拍,刷子一刮,鱼鳞尽数脱落。手起刀落,在鱼肚上剖一刀,内脏除尽。门庭若市时,分工合作,鳝筒、鳝片、鳝丝,根据买家要求分类宰杀,有条不紊。古时有“庖丁解牛”,菜市场上的纯熟技艺与之相比,并不逊色几分,不由得让人心生“技近乎道”的感慨。
除了熟练的技巧,卖家们还有各种吸引顾客的招数,比如叫卖。萧乾笔下,老北京的吆喝声有的声音厚实、词儿朴素,有的细而高,有的低而深沉,有的忽高忽低,有的合辙押韵,可以说是“带戏剧性的叫卖艺术”。(萧乾《吆喝》)
什么人懂食物,什么人懂吃?我们一般都觉得是厨师和美食家。其实我们还忽略了菜贩,那些卖菜卖肉给你的人。
如果对某种食材感到疑惑,去问菜贩准没错。这个东西怎么做好吃,他们往往都能说出个八九不离十来,有些热心肠的,还会给你分享详细的烹饪秘诀。譬如我们可能觉得板筋是烧烤用的,但卖牛肉的摊主会介绍说,带板筋的部分,炖起来要更好吃。
这都是常年与食物打交道积累下的熟知。有些菜贩开始只是做加工,慢慢地也做成了厨师,他们对某种食材的理解力,甚至不输给真正的大厨。
比如著名的筑地市场,原本是批发水产的东京都公立批发市场。早在江户时期,这里就是水产交易的地方,挑着扁担的货郎们在这里卖寿司和天妇罗。筑地市场有着东京最新鲜的水产,慢慢积累了很多刀功极佳的师傅。
随着名气愈来愈大,许多专门做寿司和刺身的餐馆便开始在周边营业,还有海鲜烧烤餐厅等等。要去筑地吃海鲜,往往得赶个大早,六七点再往后,最新鲜的一批货就都不剩什么了。在筑地做了几十年水产批发生意的伊藤宏之看来:一直以来我们都直接和鱼、和人打交道,面对面的真实感,是面对电脑做买卖永远无法企及的。没有交流,哪里来的信任。虽然新事物的渗透谁都无法拒绝,但这并不代表可以摒弃传统的面对面买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反而应该更加重视这种传统。”
即便不是这样著名的旅游景点,普通的菜市场里也总是“埋伏”着很多好吃的东西。这里离新鲜食材近,人流密集,藏着很多不起眼的熟食和小吃,也往往能寻觅到一个城市最地道的美味。
比如位于广州市老城区的“东山肉菜市场”,常常登上老广的美食榜单。在这里,花30元就能吃撑。新鲜滚烫的猪红汤,一碗只要2元,咬下去细腻爽滑,腥味全无;煎堆、蛋散、春卷、沙琪玛、干蒸、饺子、萝卜糕……都是地道的老广美味,甚至一些茶楼里已很少见的点心小吃,在这里还能找到。当然,作为一个肉菜市场,也少不了叉烧、酱油鸡、烧排骨这样的粤味烧腊。光顾者也大都是附近的街坊邻居,在口味挑剔而竞争激烈的广州,只有这样物美价廉的店铺,才能存活下来。
而柳州螺蛳粉,据比较公认的传说,也是从菜市里发源的。上世纪80年代,民间商贸开始复苏,谷埠街菜市逐渐成为柳州市内生螺批发的最大集散地。当时夜晚流行吃用骨汤打底的酸笋煮螺,柳州人爱吃米粉,故螺蛳摊上也常常经营米粉。当时,人们尚未有今日我们这般丰盛美味的菜式可选,肚内油水无多,那些饥肠辘辘的食客们,不免有意或无意间地要求在点的米粉里加入几勺油水颇多的螺蛳汤,一同享用。于是,慢慢地就形成了螺蛳粉的雏形。
如果在三四线城市,还能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许多小吃店做大后,出于更多人流量的考虑,会从菜市里搬出来,但仍会打着“某某市场老店”的名号,这或许正是菜市场所带来的底气吧。
【“沒有人会在菜场里自杀”】
古龙曾在《多情剑客无情剑》里写过,一个人如果走投无路,心一窄想寻短见,就放他去菜市场。一进菜市,此人定然厄念全消,重新萌发对生活的热爱——这话虽有夸张的成分,但意思是对的。
早晨走在大城市的路上,上班通勤的人常常神色紧张,而在菜市里的感觉全然不同,人们往往有一张比较松弛的面孔。逛菜市场是闲适、市井的日常生活实践,拖鞋、裤衩在这里再寻常不过,西装革履才会被视作另类。
卸去了职务与社会身份,菜市场里的买家们更类似一个个漫游者,他们不仅要为生存层次的“口腹之欲”而选择和操心,还要与卖家、与其他买家交流互动甚至是博弈。
货比三家,讨价还价,抹掉零头,争取一点葱姜之类的“小恩小惠”……如果说叫卖是带有戏剧性的艺术,那么,菜市场里的每一笔交易,就像是一幕幕不乏戏剧冲突的舞台剧:老太太买菜是一种学问,一场战斗,她进了菜场就像上了战场,脚步飞快,眼看八面,讨价还价,刨去零头;假装要走,三步回头,称好了菜还要抓一棵放在篮里:你小气的啥呀,反正是自家地里长的!”(陆文夫《井》)
那些对谈和吆喝声、砧板和菜刀碰撞的声音,混合着泥土的青菜气味、蔬菜瓜果的飘香、肉类的腥、海鲜的咸、滋滋作响的油烟……每一种都是真实的存在,都是大千世界最鲜活的一隅。
与传统的乡镇不同,现代化的大都市是一个“陌生人社会”,菜市场却是城市中的小型“熟人社会”,菜市场不仅仅是购物的空间,而且是社会交往的空间,这里的寒暄问候、消息传递甚至是八卦闲聊,和产品交易一样频繁而蓬勃。有缤纷的物,有市井的人,有人与物、人与人的互动,才有了菜市场的“烟火气”。
烟火气往往和一个词分不开——人间。在菜市场总能观察到形形色色的人,但最让人感叹的往往还是摊贩。摊贩们多是夫妻店,需要在凌晨两三点就起床,到几十公里外的批发市场进货,而后开启一整天的备菜和售卖,两人中间轮流抽空休息一会儿。问起他们一天的生活,“挣的都是辛苦钱”,几乎是每个人都会说的话。
但在平时,他们不会主动对人说这些,也很少有抱怨和不耐。知足常乐和随遇而安,是在摊贩们身上看到的最多的神情。
与其说,菜市上的每个摊位是每一个个体生意,倒不如说是每个小人物的活法。他们借此在这里存活下来,当小菜摊越来越有特色,就不仅养活了自己,也丰富了这一整片街区。
刚到香港时,举目无亲的窦文涛,就经常一个人到菜市场里待着。“实际我什么都不买,就走来走去,看着这些鲜艳的蔬菜的颜色,红红黄黄绿绿白白,红罩子里的灯光。虽然没人搭理我,但就有一种人情,抚慰了我的孤独”,“超市你看的是货架,看的是冰柜,但是你在菜市场呢,看的是人”。
这种人情味,或许正是我们留恋菜市场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