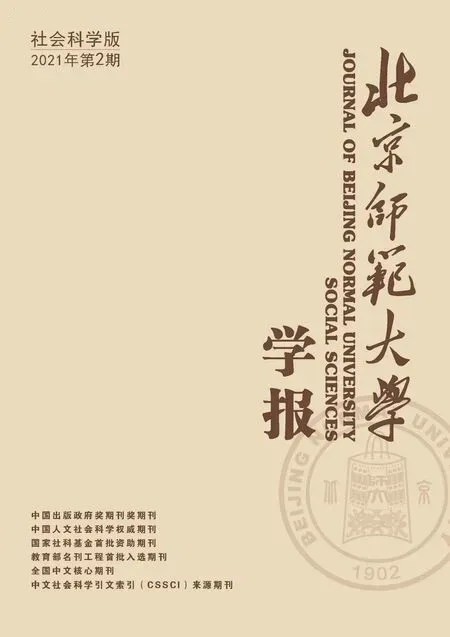“燕丧威仪”与殷商亡国
桓占伟
(河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开封 475001)
殷商王朝修建了庞大的城邑,使用着成体系的甲骨文,拥有无可匹敌的军事力量,取得了处于时代前沿的物质和精神文明成就,周人也称其为“大邑商”,声威之隆,达于天下万方。然而,这样一个泱泱大国,竟然不堪一击,一战而亡于“小邦周”之手。殷商亡国带给人们的震撼相当巨大,即使作为胜利者的周人,也谆谆告诫后人“殷鉴不远”。因商朝灭亡形成的这一成语至今广为流传,足见殷商亡国事件影响之深远。历代学者持续关注殷商亡国原因问题,传统认识把殷商亡国主要归因于纣王的荒淫残暴,自顾颉刚先生提出有力质疑之后,专家又提出了对夷战争亡国、改革激进亡国、贪欲腐化亡国、迷信宗教亡国、多重原因亡国等诸多新观点(1)参见顾颉刚:《纣恶七十事的发生次第》,《古史辨》,第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82-85页;丁山:《商周史料考证》,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64-166页;郭沫若:《中国史稿》,第1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66页;罗林竹:《纣克东夷与牧野之战》,《学术研究》,1982年第5期;胡厚宣、胡振宇:《殷商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19页;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84-286页;黄奇逸:《历史的荒原——古文化的哲学结构》,成都:巴蜀书社,1995年版,第646-662页;孟世凯:《商史与商代文明》,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132-143页;罗祖基:《对商纣的重新评价》,《齐鲁学刊》,1988年第3期;宫长为、徐义华:《殷遗与殷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4页。。前贤研究丰富深化了我们对殷商亡国原因问题的认识。当然,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是由许多复杂原因所导致的,但在众多的原因分析中,人们似乎忽视了一个方面,那就是,殷周贵族上层都曾把酗酒视为殷商衰败之因,周公甚至把“燕丧威仪”与殷商亡国直接联系了起来。“燕丧威仪”也应是需要重视的殷商亡国的原因之一。令人费解的是,喝酒如何会与殷商王朝败亡形成关联?“燕丧威仪”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些问题还有进一步研究之必要,以期对殷商亡国原因作出一点补证。
一、殷周贵族上层对殷商败亡的共识
商王盘庚曰:“邦之臧,惟汝众;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罚。”(2)孔颖达:《尚书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70页。这说明殷商王权已经形成。商王自称“予一人”,拥有最高决策权和最终决定权,殷商灭亡,纣王理当要承担主要责任。殷周可信文献中,殷末贵族上层及周初武王、周公、成王在不同场合,都曾提及殷商败亡原因,我们试分析如下:
《尚书》的《西伯戡黎》与《微子》两篇文献,保存有殷商末年社会动乱、王朝危亡的可信史料。其中有殷人自身对王朝危亡原因的认识。《尚书·西伯戡黎》载:“天既讫我殷命,格人元龟,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后人,惟王淫戏用自绝,故天弃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3)孔颖达:《尚书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第177、177-178、183、183、220、229页。《尚书·微子》载:“微子若曰:‘我用沈酗于酒,用乱败厥德于下……卿士师师非度。’……父师若曰:‘王子!天毒降灾荒殷邦,方兴沈酗于酒,乃罔畏畏,咈其耇长旧有位人。’”(4)孔颖达:《尚书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第177、177-178、183、183、220、229页。这两段话出处不同,基本内容则大体一致。《西伯勘黎》是周文王战胜位于河东的黎国,殷商政治统治出现重大危机,殷臣祖伊奔走告纣的记载。很可能纣王把危机原因归咎于祖先神不加保佑,故祖伊才直陈问题出于纣王自身,指出不是先祖不襄助子孙,而是纣王过分戏怠,逆天道而废典刑,自绝于先王,故遭弃于上帝。祖伊虽未明言纣王“淫戏”的具体表现,但纣王曾“以酒为池……为长夜之饮”(5)司马迁:《史记·殷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04-105页。,说明酗酒应为纣王“淫戏”的主要内容。微子与箕子均明确指责纣王“沈酗于酒”。关于纣王酗酒导致的问题,三人认识高度一致:所谓“不虞天性”、“乃无畏畏”,均指纣王不敬上帝;而“不迪率典”、“咈其耇长旧有位人”,则指纣王丢掉了既定的政治准则。可见,在殷末贵族上层看来,殷商危亡与纣王酗酒有直接关系。
武王征商,需要战前动员。《尚书·牧誓》作为可信的西周文献,记载了武王在牧野之战前的动员讲话,其中言及纣王诸多恶行:
古人有言曰:“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6)孔颖达:《尚书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第177、177-178、183、183、220、229页。
武王提到的“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隐含着纣王酗酒之意。《尚书正义》曰:“为长夜饮,妲己好之。”(7)孔颖达:《尚书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第177、177-178、183、183、220、229页。它说明纣王为讨妲己欢心,故纵情于酒;而“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亦指纣王不敬上帝,丢掉了既定的政治准则。
西周建国后,周人统治着数量庞大的殷遗民,武王、周公经常对这部分特殊群体加以训诰。不少训诰也涉及殷商败亡原因:
《逸周书·克殷解》载:“殷末孙受,德迷先成汤之明,侮灭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彰显闻于昊天上帝。”(8)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354-355,454、461页。
《逸周书·商誓解》载:“今在商纣,昏忧天下,弗显上帝,昏虐百姓,奉天之命。上帝弗显,乃命朕文考曰:殪商之多罪纣……今纣弃成汤之典,肆上帝命我小国曰:革商国。”(9)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354-355,454、461页。
《尚书·多士》载:“在今后嗣王,诞罔显于天,矧曰其有听念于先王勤家?诞淫厥泆,罔顾于天,显民祗。惟时上帝不保,降若兹大丧。”(10)孔颖达:《尚书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第177、177-178、183、183、220、229页。
《尚书·多方》载:“乃惟尔商后王,逸厥逸,图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时丧。”(11)孔颖达:《尚书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第177、177-178、183、183、220、229页。
武王、周公对殷遗民的训诰,重心虽在于强调殷商灭亡是上帝的威罚,但也或隐或显地指出纣王迷乱于酒、过分逸乐的问题,而“侮灭神祇不祀”、“弗显上帝”、“罔顾于天,显民祗”、“不蠲烝”,是说纣王不敬上帝;“德迷成汤之明”、“弃成汤之典”、“矧曰其有听念于先王勤家”、“逸厥逸,图厥政”,均指纣放弃了既定的政治准则。
《尚书·酒诰》是康叔赴卫就国前,周公代表成王对他的训诰。这是西周统治阶级上层的内部谈话,所谈内容可信度比较高。有意思的是,周公不但明确把酒与邦国丧亡联系起来,而且把“燕丧威仪”视为殷商灭亡的重要原因:
天降威,我民用大乱丧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丧,亦罔非酒惟辜……在今后嗣王酣身,厥命罔显于民,祇保越怨不易。诞惟厥纵淫泆于非彝,用燕丧威仪,民罔不衋伤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庶群自酒,腥闻在上,故天降丧于殷,罔爱于殷,惟逸。(12)孔颖达:《尚书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第206-207、222、207页。
周公指责纣王“酗于酒德”(13)孔颖达:《尚书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第206-207、222、207页。,“淫泆于非彝”。“彝”与《尚书·洪范》所称“彝伦”同义。顾炎武云:“彝伦者,天地人之常道……不止《孟子》之言‘人伦’而已。”(14)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秦克诚点校:《日知录集释》,长沙: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55页。纣王“淫泆于非彝”,意指纣王带头酗酒,丢掉了既定的政治准则。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酗酒之风迅速蔓延,成为殷人族群性的“污俗”,出现了“燕丧威仪”情形。“燕丧威仪”又使得“民罔不衋伤心”。《尚书正义》将其释为“民众无不衋然痛伤其心”(15)孔颖达:《尚书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第206-207、222、207页。,似非达意。此处之“伤心”,应作“失去民心”解,实际是《孟子·离娄上》所载“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的来源(16)孙奭:《孟子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721页。,是周公首次把王朝兴衰与民心向背建立了关联。“燕丧威仪”四个字承上启下,极其重要,既是纣王“淫泆于非彝”的严重后果,又是“天降丧于殷”的直接原因,隐含着殷商亡国的关键信息。
由上可知,微子、箕子与武王在谈及殷商败亡原因时,不约而同地突出了纣王酗酒、不敬上帝与丧失既定的政治准则等三个问题,几乎形成了共识性认识,值得我们高度关注。那么,周公所言的“燕丧威仪”究竟有什么涵义?是否也与这三个问题有关?“燕丧威仪”又能够造成什么样的危害?还需要进一步条分缕析。
二、“燕丧威仪”解析
“燕丧威仪”四个字当中,“丧”是动词,即“失去,丢掉”之义,无需过多解读,需要深究的,是“燕”和“威仪”的涵义。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燕”字。“燕”本身有饮酒燕安之义,只是,饮酒也分“燕私”与“燕礼”不同场合。如果商王在私下场所燕饮娱乐,即使醉酒不省人事,也只会被极小范围的侍者知晓,不会产生太大政治影响,更不会导致身死国亡的历史悲剧。周公既以“燕丧威仪”为殷商败亡之因,则“燕”必非“私燕”,应为官方性质的、含有政治象征意义的“燕礼”。“燕丧威仪”是指纣王在正式燕礼上丧失了“威仪”。

燕礼多在帝王正殿举行。《仪礼·燕礼》载:“膳宰具官馔于寝东……燕朝服于寝。”(20)贾公彦:《仪礼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014、1024,1022页。许维遹先生认定,燕礼在路寝举行(21)许维遹:《飨礼考》,《清华学报》,1947年,第14卷第1期,第141页。。《礼记·玉藻》载:“君日出而视之,退适路寝,听政。”(22)孔颖达:《礼记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687-1688、1474页。《周礼·天官·宫人》载:“掌王之六寝之修。”郑玄《注》曰:“六寝者,路寝一,小寝五……路寝以治事。”(23)贾公彦:《周礼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75页。可证路寝是王处理国家大事之所。在正殿举行燕礼,既有表示相亲昵的意思,又象征着在燕礼上明确的各项准则具有官方背景。西周燕礼的传统,理应有从殷商传承的成分。
来宾参加燕礼,要醉不及乱,始终保持和乐有序。《仪礼·燕礼》载:“君曰:‘无不醉。’宾及卿大夫皆兴,对曰:‘诺,敢不醉?’皆反坐。”(24)贾公彦:《仪礼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014、1024,1022页。表面看来,这是国君让来宾不醉无归,喝个尽兴,来宾也向国君表白不敢不尽欢。实际上,这只是君臣之间表达亲昵的礼仪性唱酬罢了。《诗经·小雅·宾之初筵》载:“既醉而出,并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谓伐德。”(25)孔颖达:《毛诗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87、421页。宾客醉了一定要离开,这是礼的要求。但常识告诉我们,喝醉还能不丧失控制,需要强大的定力,非常人所能为之,故“既醉”多为“佯醉”。这样既可以落实国君要求,领受国君盛情,又能保持自身体面,心照不宣地维持燕礼秩序。《诗经·小雅·湛露》云:“湛湛露斯,匪阳不晞。厌厌夜饮,不醉无归。”毛《传》:“夜饮,燕私也。宗子将有事,则族人皆侍。不醉而出,是不亲也;醉而不出,是渫宗也。”(26)孔颖达:《毛诗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87、421页。燕私作为非官方场合的礼仪仪式,还要保持醉不及乱,何况具有政治礼仪背景的官方燕礼呢?《左传·宣公二年》载:“臣侍君宴,过三爵非礼也。”(27)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867页。臣子陪国君宴饮,过三爵就被认定为非礼,怕的就是喝醉丧失礼节。因此,君臣在燕礼上饮酒作乐,只是为了烘托气氛,双方之意均不在酒,而在于维系、确认并强化君臣之间政治关系的各项准则。《礼记·燕义》载:
诸侯燕礼之义。君立阼阶之东南,南乡尔。卿大夫皆少进,定位也。君席阼阶之上,居主位也。君独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莫敢适之义也。设宾主,饮酒之礼也。使宰夫为献主,臣莫敢与君亢礼也。不以公卿为宾,而以大夫为宾,为疑也,明嫌之义也。宾入中庭,君降一等而揖之,礼之也。君举旅于宾,及君所赐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明臣礼也;君答拜之,礼无不答,明君上之礼也。臣下竭力尽能以立功于国,君必报之以爵禄,故臣下皆务竭力尽能以立功,是以国安而君宁。礼无不答,言上之不虚取于下也。上必明正道以道民,民道之而有功,然后取其什一,故上用足而下不匮也,是以上下和亲而不相怨也。和宁,礼之用也,此君臣上下之大义也。故曰:“燕礼者,所以明君臣之义也。”席,小卿次上卿,大夫次小卿。士、庶子以次就位于下。献君,君举旅行酬,而后献卿;卿举旅行酬,而后献大夫;大夫举旅行酬,而后献士;士举旅行酬,而后献庶子。俎豆、牲体、荐羞,皆有等差,所以明贵贱也。(28)孔颖达:《礼记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第1690、1692页。
这段文献记载了周代燕礼包含的三项准则。首先是君尊臣卑。君主独尊体现在燕礼的方方面面,如君“居主位”、“独升立席上,莫敢适”,传递出君王处于“予一人”的独尊地位;而“臣莫敢与君亢礼”,君王只需举杯象征性地向宾客敬酒,臣子则需要“降再拜稽首”,强化着君尊臣卑的王权意识。其次是君臣有义。臣子的礼敬,君主需要一一答谢,象征国君不会虚取于臣下,双方以“义”相互约束:君“明正道以道民”,担负起应有统治责任;臣竭力尽职,建功立业,然后有资格接受君赐予的爵禄。君臣各自都有需要担负的责任与义务。再次是贵贱有等。君、卿、大夫、士、庶子旅酬有严格的先后顺序,提供的俎豆、牲肉、脯醢、菜肴也各有等差。这些都是为了明确不同等级贵贱之别。
据《仪礼·燕礼》记载,燕礼程序有“祭脯醢”、“祭酒”、“坐祭”等祭祀祖先的活动,说明燕礼还具有宗教性质。这种宗教植根于祖先崇拜,彰显着长幼有序、上下有节、贵贱有等、君臣有义的社会准则。因此,燕礼的目的,本质上在于强化君主独尊,巩固君臣政治关系的基本准则,明确臣子的等级贵贱。当然,燕礼也可以联络君臣感情,并使这种感情在仪式程序上得到升华,产生一种超越于日常生活的神圣感。《礼记·聘义》载:“贿赠飨食燕,所以明宾客君臣之义也。”(29)孔颖达:《礼记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第1690、1692页。周礼与殷礼有继承有损益,周代燕礼与殷商燕礼相比较而言,在仪式程序上也许会有一些新变化,但其功能却不会轻易改变。殷商时期的燕礼,理应也是商王用来明确既定政治准则的手段,在殷商政治统治中占有重要地位。
纣王在燕礼上丧失的“威仪”是什么?春秋时期卫国大夫北宫文子的解释最具代表性:
有威而可畏,谓之威;有仪而可象,谓之仪……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爱,进退可度,周旋可则,容止可观,作事可法,德行可象,声气可乐,动作有文,言语有章,以临其下,谓之有威仪也。(30)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016页。
北宫文子把威仪视为贵族君子外在的形象举止,并被后世学者奉为圭臬。阮元视威仪为德之隅,威仪者,人之体貌,“后人所藐视为在外最粗浅之事,然此二字古人最重之”(31)阮元:《揅经室集》,邓经元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17页。。侯外庐先生指出,威仪暗示着古代社会统治阶级的威风(32)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5卷,《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02-603页。。裘锡圭先生以威仪为礼容(33)裘锡圭:《史墙盘铭解释》,《文物》,1978年第3期。。张岂之先生以行礼者之身份地位的举动谓之“威仪”(34)张岂之:《中国思想学说史》,先秦卷(上),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9页。。日本学者竹添光鸿指出:威者,和顺中积,英华外发,自然之威德风采也;仪者,正衣冠,尊瞻礼,动容周旋中礼者也(35)〔日〕竹添光鸿:《左氏会笺》,成都:巴蜀书社,2008年版,第1592页。。不过,北宫文子的解释应代表春秋时期的威仪观念,不一定能反映殷周之际威仪的本质。那么,殷周之际是否存在威仪观念?如果存在的话,威仪的本质又是什么?
尽管在现有甲骨文材料中没有发现“威仪”一词,但周公言及“燕丧威仪”之时,尚去殷商未久,且殷周所用文字体系又相同,似可推定,晚商时期燕礼应存在周公语境下的“威仪”。刘翔先生指出,殷周时期还没有出现“仪”字,迄今发现最早“从人义声”的“仪”字出现在甘肃居延汉简中(36)刘翔:《中国传统价值观诠释学》,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12-113页。,故“威仪”一词,在殷周时期应为“威义”。在现有西周金文文献中,“威义”凡四现,并被认为来源于先王:
《虢叔旅钟》铭:“旅敢肇帅型皇考威义”;
《叔向父禹簋》铭:“肇帅型先文祖,恭明德,秉威义”。(37)张亚初:《殷周金文集成引得》,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870-871页。
西周习见文、武、成、康、德、礼、恭、敬、刚、柔等单字形式的观念词汇,以合成词形式出现的“威义”,显得很不寻常。上述彝器的主人宣称要效法皇考“威义”,要秉持“威义”,用“威义”奉事先王,“威义”显非贵族礼容。晚商“威义”究竟所指为何?还需要分而述之。甲骨文中已经出现了“畏”(威)字:
癸未卜,王贞:畏梦,余勿御。(《合集》 17442)
辛卯…畏至不?(《合集》 19484)
《逸周书·商誓解》:“予来致上帝之威命明罚。”(41)黄怀信:《逸周书校补注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25页。
《尚书·西伯戡黎》:“天曷不降威。”(42)孔颖达:《尚书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第171、177、198、219、223页。
《尚书·大诰》:“天降威。”(43)孔颖达:《尚书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第171、177、198、219、223页。
《尚书·多士》:“将天明威,致王罚。”(44)孔颖达:《尚书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第171、177、198、219、223页。
《尚书·君奭》:“我亦不敢宁于上帝命,弗永远念天威。”(45)孔颖达:《尚书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第171、177、198、219、223页。
商王作为上帝所降之监,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可以传达上帝的威命,也可以代表上帝对违命臣民实施惩罚。在殷人全体族众尊崇神灵的时代背景下,商王假上帝之威,才能“有威而可畏”,为自身政治行动寻找到神圣性依据,使人们相信他的各项安排来自于上帝意志。因此,“威”是保障手段,是商王实施政治统治的前提,其最终目的是要确立“义”。

弜用义行,弗遘方。(《合集》 27979)
□即义。(《合集》 31051)
…丑用于义友…。(《合集》 38762)
于义…。(《屯南》 03040)
《说文》载:“義,己之威仪也。从我、羊……臣铉等曰:‘此与善同意,故从羊。’”(46)许慎:《说文解字》(附检字),徐铉校订,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67页。许慎的解释代表着汉人对“义”的理解,不一定是商代原始意义。专家对“义”字原始意义的考释分歧也较大,形成了“杀”、“善”、“地名”、“仪仗”、“人名”等不同解释(47)参见庞朴:《儒家辩证法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0-30页;徐中舒:《甲骨文字典》,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0年版,第1382页;刘兴隆:《新编甲骨文字典》,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865页;毕秀洁:《商代铜器铭文的整理与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289页。。不过,“叀义行用”、“勿用义行”的“义”字,以上解释都很难说得通。若把“义行用”释为“推行义的准则”,似较为通顺。实际上,甲骨文“我”、“羊”组合成为“義”字,极具符号象征意义,在商代就与祭祀有关,带有浓厚的宗教政治准则特征。“羊”是商代重要的祭祀牺牲,“我”是祭祀时用于杀伐的刑器,“义”也可以解释为商王在宗教祭祀中以“我”杀羊,献祭祖先和神灵;并以“我”解羊,给参与祭祀者分肉。用“我”杀羊的目的是祭祀神灵和分肉享众,这在观念上是一种“善”;先秦文献中,义经常与内外、上下、远近、贵贱、君臣之“分”相对应,是政治准则和等级秩序的代表(48)桓占伟:《从宗教神性到政治理性——殷周时期义观念生成的历史考察》,《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4期。。在重要的国家祭祀中,主祭者往往是商王,故主祭权即是最高权力象征。尤其是在宜祭上帝这种带有族群共同神灵性质的祭礼上,商王借助与上帝沟通交流的惟一性,为自身“予一人”的独尊地位涂上了神圣色彩。商王在国家层面拥有独尊地位,各级宗族长在自身宗族中同样拥有独尊地位,他们在宗教祭祀中拥有主祭权。这样,殷人宗教领域的“尊神”,根本上落实为世俗领域的“尊尊”。不难想象,能够亲临祭祀现场者必然身份特殊,他们或者是王室成员,或者是深受商王信赖与倚重的贵族勋旧,带有“亲亲”性质。这样,义就同时具备了“尊尊亲亲”两大特征,而“尊尊亲亲”,也是对中国后世具有深远影响的宗法精神的基本内核。义蕴含着殷商政治统治的各项准则,其植根于氏族血缘关系,发端于原始宗教背景下族群首领对所获物的分配,生成于殷商祭祀中“杀牲”和“分肉”的程序,与燕礼所要确认和维系的君王独尊、君臣有义、贵贱有等的观念恰相一致,亦当为殷商政治统治的观念基石。
“威”来自于上帝,在宗教仪式上凸现出神圣性;“义”出自于商王,在政治统治中表现为准则性。“威”与“义”合并为“威义”一词,正是商王神道设教,通过仪式性语言及行为确立殷商政治准则的历史印记。因此,商王在燕礼上秉持“威义”,事关王权的神圣性和政治准则的确定性,事关统治群体内重要成员身份地位的确认和群体认可,是一件极其庄重严肃的事情。如果因宾主酗酒而言行失当,屡丧“威义”,就会使燕礼上的宗教祭祀和政治礼仪失去神圣性和取法意义。《诗经·小雅·宾之初筵》是有关西周时期燕射礼的诗歌,其中形象地记载了宾客醉酒后场面失控的混乱局面:“曰既醉止,威仪怭怭。是曰既醉,不知其秩。宾既醉止,载号载呶。乱我笾豆,屡舞僛僛。”(49)孔颖达:《毛诗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第487页。宾客东倒西歪,狂呼乱叫,丑态百出,把那些象征身份地位的笾豆都搞乱了。燕礼饮酒,目的是“维其令仪”,即维护那些美好的政治准则,可场面一旦失控,竟至于“不知其秩”,连最起码的秩序也丧失了。
燕礼仪式上有宗教祭祀和政治礼仪的不同环节。在宗教祭祀环节上,如果商王醉酒轻慢于神灵,就意味着对神灵的亵渎,会使人们不再对上帝的威严产生敬畏,继而对商王政治统治的神圣性产生怀疑。这将导致“尊尊”之义沦丧,消泯祭祀仪式中所固着的族群凝聚力和共同情感,带来内部分裂的危机。前引文献中纣王的一大罪状,就是放弃了宗教祭祀,不敬上帝:“昏弃厥肆祀弗答”、“侮灭神祇不祀”、“弗显上帝”。纣王对上帝轻慢,遭到了上帝抛弃,这可以称之为“丧威”。在政治礼仪环节上,纣王如果因醉酒而行为举止失当,破坏了俎豆、牲体、荐羞这些“人格的物化”的分配规则,贱者取得贵骨,贵者分到贱骨,分配的礼器和食物没有遵循亲疏贵贱的地位等差,失去了准则和秩序,那么,寓于燕礼中的长幼、内外、亲疏、贵贱等关系就会随之出现混乱,使得“亲亲”之“义”不存,既定政治准则丧失。殷商时期,血缘纽带对政治统治至为关键,来自族群内部的支持是王权的基石。这个基石一旦被抽空,就意味着王权成为空中楼阁,再坚固的堡垒也会从内部坍塌。
“燕”有燕礼上饮酒之义,“威”又与上帝相关,“义”乃是殷商时期的政治准则。这样看来,周公所言的“燕丧威仪”,是对纣王酗酒、不敬上帝和丧失既定政治准则的高度概括,实际上与微子、箕子、武王的认识保持着内在一致。“燕丧威仪”使纣王政治统治的神圣性和权威性荡然无存,使朝野上下共识性、普遍性和通行性的政治准则陷于混乱,纣王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也必然随之出现严重的认同危机。一旦王朝的宗教认同出现危机,政治秩序陷入混乱,就会使统治群体内部众叛亲离。殷商亡国前夕,“殷之大师、少师乃持其祭乐器奔周”(50)⑧ 司马迁:《史记·殷本纪》,第108、105页。;“殷内史向挚见纣之愈乱迷惑也,于是载其图法,出亡之周”(51)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梁运华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96页。。侯外庐先生指出:“伯夷叔齐就曾向周人上过太平策,也有的向周人供奉自己祖先的典册,去献媚周人。”(52)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中国思想通史》,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1-72页。《诗经·大雅·荡》载:“侯作侯祝……内奰于中国、覃及鬼方。”(53)孔颖达:《毛诗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第553页。殷商统治阶层内部离心离德,不但族人非难,民怨沸腾,而且波及到遥远的鬼方。在这样的情势下,也就注定了牧野之战前徒倒戈,殷商一战而亡的悲剧命运。
三、“燕丧威仪”何以可能
《礼记·檀弓下》载:“墟墓之间,未施哀于民而民哀;社稷宗庙之中,未施敬于民而民敬。”(54)孔颖达:《礼记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第1313页。这是讲特定场所会带给人特定情感体验。让人难以置信的是,纣王何以能在庄严隆重的庙堂之上,在众目睽睽之下,屡屡做出“燕丧威仪”这样匪夷所思的举动呢?我们认为,失去约束、极度膨胀的王权,才会导致“燕丧威仪”的混乱局面。

……麓获白兕,丁酉……。(兕肋骨,《殷契佚存》 427)

之所以说这些甲金刻辞特殊,是因为它们具有为商王歌功颂德的共性。上引甲骨刻辞文风统一,且多采用珍稀的绿松石装饰,显得特别精美,似着意彰显商王的勇武无匹;作册般铜鼋器形写实,射进鼋身的四支箭仅余尾部,箭身大部分没入鼋体,且四发皆中,无有废矢,似在特别炫耀商王射艺超群。司马迁说纣王“手格猛兽”,看来所记不虚。不过,回头细思,殷商人才济济,能够猎获猛兽的武士应很多,但自武丁以来,只有纣王获虎、获兕、射艺高超、获鼋之事被特别记录下来,或用宝石装点,或用吉金铸器,刻意渲染的成分相当突出。这自然会令人联想到纣王对自身勇武的洋洋自得,也可以体察得到纣王近臣对他的着力吹捧。这些文物记载,从某种角度来看,也是显示纣王自命不凡的实物证据。《史记·殷本纪》载:
费中善谀,好利,殷人弗亲。纣又用恶来。恶来善毁谗,诸侯以此益疏……西伯滋大,纣由是稍失权重……王子比干谏,弗听……祖伊反,曰:“纣不可谏矣。”……纣愈淫乱不止。微子数谏不听……比干曰:“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争。”乃强谏纣。纣怒曰:“吾闻圣人心有七窍。”剖比干,观其心。箕子惧,乃详狂为奴,纣又囚之。(58)司马迁:《史记·殷本纪》,第106-108、1241页。
纣王自视甚高,且重用费中、恶来等谗谀之人,故宗族近臣虽多次进谏、强谏,但纣王“弗听”甚而发怒,最终王子比干被杀,箕子被囚。宗族近臣下场尚且如此,一般臣子自保不暇,何敢直言进谏呢?《荀子·解蔽》载:“昔人君之蔽者,夏桀殷纣是也……纣蔽于妲己、飞廉,而不知微子启,以惑其心,而乱其行……纣县于赤旆,身不先知,人又莫之谏,此蔽塞之祸也。”(59)王先谦:《荀子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第388-389页。在荀子看来,纣王纵然自视再高,但毕竟是人不是神,对重大危机不能未卜先知;加之谗谀之臣极力吹捧,宗族近臣又畏祸不敢进谏,终至蔽塞视听,落得个头悬“赤旆”的可悲下场。
其次,对夷战争的胜利使其自我陶醉,膨胀的王权轻视准则约束。卜辞中有不少帝纣征伐人方、尸方的记录,说明殷商与东夷常有战争冲突,且持续时间长,战争规模也比较大,涉及地域比较广甚至深入到淮河流域。不少文献记载,帝纣有突出的军事才能,对东夷的战争也取得了最后胜利:
《左传·宣公十二年》:“纣之百克,而卒无后。”(60)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第1880、2035、2060页。
《左传·昭公四年》:“商纣为黎之蒐,东夷叛之。”(61)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第1880、2035、2060页。
《左传·昭公十一年》:“纣克东夷,而陨其身。”(62)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第1880、2035、2060页。
《吕氏春秋·古乐》:“商人服象,为虐东夷。”(63)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梁运华整理,第128页。
一般认为,以上文献表明纣王穷兵黩武,消耗了大量国力;且牧野之战爆发时,其主力部队来不及调回,所以才给周人以可乘之机,导致了身死国亡的悲剧。实际上,殷人对东夷的战争,早在牧野之战前五年就已结束;加之纣王大胜而归,俘虏了大量夷人,掠取的财富自然也不在少数,国力自当空前强大。按司马迁的说法,帝纣“百战克胜,诸侯慑服”(64)司马迁:《史记·殷本纪》,第106-108、1241页。。纣王自身也正值声威远播之际,何以“纣克东夷,而陨其身”呢?最有可能是军事上的胜利加剧了纣王的自负心理,使其陶醉于“老子天下第一”的幻象之中。在王权不断膨胀的情况下,纣王具有俯视一切的神圣权威,能够作威作福,为所欲为;甚至通宵达旦酗酒,“靡明靡晦,式号式呼,俾昼作夜”(65)孔颖达:《毛诗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第553页。,达到了丧失理智,丧失时间意识的地步。燕礼上丧失一下“威仪”,又有什么大不了?谁又能怎么样呢?这样,“威仪”的既定政治准则自然形同虚设,可以肆意突破,失去应有的约束力,沦为纣王眼中不值一提的小事。而这样的行为,就为纣王其后“陨身”埋下伏笔。
再次,信“有命在天”使其丧失最起码的忧患意识,丢掉对天命的敬畏之心,无视迫在眉睫的危险,沉溺于歌舞升平之中:
好酒淫乐,嬖于妇人。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于是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巨桥之粟。益收狗马奇物,充仞宫室。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慢于鬼神。大冣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县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66)司马迁:《史记·殷本纪》,第105页。
这极有可能是在西伯兵锋迫近,王畿西境的黎国已经不保的危险情势下纣王的所作所为。《尚书·西伯戡黎》记载了大臣祖伊与纣的一段对话:
“今我民罔弗欲丧,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挚?今王其如台。”王曰:“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呜呼!乃罪多参在上,乃能责命于天?殷之即丧,指乃功,不无戮于尔邦!”(67)孔颖达:《尚书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第177页。
民众都盼望着上帝降下威罚,纣王早日倒台,形势已经变得岌岌可危。祖伊奔告纣王,寻求应对之策,纣王却反问祖伊:“我生不有命在天?”从语境分析,纣王这句话不是随意调侃,而是传递着他对自身“有命在天”的深信不疑。纣王确信,既有“天命”在身,王位自会永固世享,“小邦周”即使侵犯了边鄙属国,也算不上什么大不了的事儿。毕竟,历史上殷商王朝边境经常遭到土方、邛方、盂方等方国袭扰,这些入侵事件从未对王朝带来真正威胁。某些小邦即使发展壮大了,但其再强也赶不上“大邑商”。纣王自认为战争主动权永远掌握在他手中,不率先对天下万方发难就是一种恩惠,怎么可能会有小邦不自量力,敢来挑战他的神圣权威呢?故“大邑商”不需要什么忧患意识,倒是应抓住平定东夷后天下太平的闲暇时机及时行乐。这自然是对天下局势的误判。为人臣子的祖伊尚能对此保持清醒,何以纣王却执迷不悟呢?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缺乏谏诤匡正的批评,“商邑翼翼,四方之极”式的颂声就会充盈朝庭。纣王只能听到对其圣化、神化的信息,蔽塞日久,“予一人”的天之骄子形象就会自我确认;发展到极致,会目空一切,甚至不再敬畏上帝鬼神,自己崇拜自己。谢文郁先生指出,纣王的悲剧在于对“天命”的敬畏情感在其言行中逐步减弱,以至于随后走向自以为是,敬意尽失。没有敬畏情感,把自己的想法等同于天命,从而无视天命(68)谢文郁:《“敬仰”与“信仰”: 中西天命观的认识论异同》,《南国学术》,2017年第2期。。
美国历史学家威尔·杜兰曾深刻地指出,一个伟大的文明国家,其灭亡,常非由于外力的摧毁,而是其内部的腐蚀所造成的(69)〔美〕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3卷,幼狮文化公司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493页。。纣王极度自负导致极度蔽塞,引发王朝上下离心离德的政治危局,堡垒先从内部崩坏了。故荀子曰:“鼓之而纣卒易乡,遂乘殷人而诛纣。盖杀者非周人,因殷人也。”(70)王先谦:《荀子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第136页。他把牧野之战失败的原因归结到殷人自己身上。
四、威仪之丧,纣所以亡也
《史记·乐书》载李斯之言曰:“轻积细过,恣心长夜,纣所以亡也。”(71)司马迁:《史记·乐书》,第1177页。李斯的认识独到而深刻,轻视积累的细小过失,耽于燕安之乐,确与殷商亡国有脱不开的干系,也是需要引起重视的殷鉴。纣王酗酒,“燕丧威仪”,就会不断造成政治过失,产生君臣矛盾。这些被轻易忽视掉的过失和矛盾,经过不断积累,会系统性放大,从根本上腐蚀掉殷王朝的政治准则,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其实,对于细节问题引发大的灾难,古人也保有清醒的认识。《史记·宋微子世家》载:
纣始为象箸,箕子叹曰:“彼为象箸,必为玉桮;为桮,则必思远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舆马宫室之渐自此始,不可振也。”纣为淫泆,箕子谏,不听。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为人臣谏不听而去,是彰君之恶而自说于民,吾不忍为也。”乃被发详狂而为奴。(72)司马迁:《史记·宋微子世家》,第1609页。
箕子从纣王用象牙筷子而预见到亡国的命运,深具忧患意识,可谓见微知著,深谋远虑。只是纣王已陶醉在天下太平的假象中难以自拔,箕子也只能装疯卖傻以求自保。
周公也极为重视政治细节,要求避免积累细小的政治过失。《尚书·康诰》载:“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尚书正义》曰:“人之怨不在事大,或由小事起。虽由小事起,亦不恒在事小,因小至大。是为民所怨,事不可为。”(73)孔颖达:《尚书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第203、215、232、245页。《康诰》与《酒诰》本为一篇,故周公此言,正与前述《酒诰》所载之“燕丧威仪,民罔不衋伤心”前后呼应。不惟如此,成王迁洛前夕,周公再次教诲成王重视细微之过。《尚书·洛诰》载周公之言曰:“无若火始焰焰,厥攸灼叙,弗其绝。”(74)孔颖达:《尚书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第203、215、232、245页。意思是细小的政治过失,刚开始只是一星一点,微不足道,一旦形成灼然洞烧之势,就没有办法遏止了。小问题引发大灾难,也屡屡见诸史册,《吕氏春秋·察微》载:
楚之边邑曰卑梁,其处女与吴之边邑处女桑于境上,戏而伤卑梁之处女。卑梁人操其伤子以让吴人,吴人应之不恭怒,杀而去之。吴人往报之,尽屠其家。卑梁公怒,曰:“吴人焉敢攻吾邑!”举兵反攻之,老弱尽杀之矣。吴王夷昧闻之怒,使人举兵侵楚之边邑,克夷而后去之。吴、楚以此大隆。吴公子光又率师与楚人战于鸡父,大败楚人,获其帅潘子臣、小帷子、陈夏啮。又反伐郢,得荆平王之夫人以归,实为鸡父之战。(75)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梁运华整理,第419-420、418页。
两个小女孩游戏误伤,这自然是再平常不过的小事。可这件小事经双方不断升级,最终发展为国家之间的大规模战争。无独有偶,《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记载了一场类似的政治风波:“季、郈之鸡斗,季氏介其鸡,郈氏为之金距。平子怒,益宫于郈氏,且让之;故郈昭伯亦怨平子。”(76)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109页。昭公出奔,是春秋晚期鲁国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祸端源于郈氏与季氏的一场斗鸡比赛。由于双方矛盾冲突不断升级,最终兵戈相见,导致昭公丧失君权,出逃齐国,落得个客死异乡的结局。
一场游戏引发国家战争;一次斗鸡致使国君出奔。当然,这些重大灾祸的发生,背后的原因往往很复杂,但是,如果没有导火索,再大的火药桶也难以被引爆。发生重大灾祸的原因如此细微,以至于人们往往难以察觉。问题不知不觉地扩大,矛盾无声无息地加剧,积微成巨,如人体生疮,终有溃时,故《吕氏春秋·察微》曰:
使治乱存亡若高山之与深溪,若白垩之与黑漆,则无所用智,虽愚犹可矣。且治乱存亡则不然。如可知,如可不知;如可见,如可不见。故智士贤者相与积心愁虑以求之,犹尚有管叔、蔡叔之事与东夷八国不听之谋。故治乱存亡,其始若秋毫,察其秋毫,则大物不过矣。(77)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梁运华整理,第419-420、418页。
国家治乱存亡的原因极其隐晦,即使人们处心积虑地去探求,也苦于难以把握,但其发端却如秋毫可见,只要洞察并规避细微过失,就不会引至大的灾祸,故贤哲们多强调要注重细微问题:
《尚书·立政》:“自一话一言,我则末惟成德之彦,以乂受我民。”(78)孔颖达:《尚书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第203、215、232、245页。
《尚书·毕命》:“克勤小物,弼亮四世。”(79)孔颖达:《尚书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第203、215、232、245页。
《管子·权修》:“微邪者,大邪之所生也。微邪不禁,而求大邪之无伤国,不可得也。”(80)黎翔凤:《管子校注》,梁运华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56页。
《礼记·中庸》:“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81)孔颖达:《礼记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第1625页。
《春秋繁露·二端》:“夫览求微细于无端之处,诚知小之将为大也,微之将为着也……贵微重始。”(82)苏舆:《春秋繁露义证》,钟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55页。
无论“一话一言”、“克勤小物”,还是“君子慎独”、“贵微重始”,都重在强调政治家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是关乎国家兴亡的大事,必须注重“嫌疑纤微”,做到“别微绝纤”。《韩非子·喻老》载有一段高度理论化的论述,剖析了政治统治必须注重细微问题的道理:
有形之类,大必起于小;行久之物,族必起于少。故曰:“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细。”是以欲制物者于其细也。故曰:“图难于其易也,为大于其细也。”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此皆慎易以避难,敬细以远大者也。(83)王先慎:《韩非子集解》,钟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60-161页。
“千丈之堤,溃于蚁穴”,是为不易之论。认真处理容易的小事,方能避开大的困难;敬畏细微的过失,才能远离大的灾祸。就此而论,李斯关于纣亡之说,可谓一语中的。如果再将其具体化,那就是本文的结论:威仪之丧,纣所以亡也!
五、结语
日积月累,常被忽视掉的小过失,往往能够导致重大政治危机。综合文献考察,殷商之亡,“燕丧威仪”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殷商燕礼上设置饮酒环节,本是为了维护既定的宗教政治准则,纣王却使之蜕变为无度的宴乐,丧失了政治统治的神圣性与合法性,导致统治集团内部分崩离析,从而给周人以可乘之机,最终酿成亡国的历史悲剧。这与纣王极度自负导致的极度蔽塞有关。极度自负使其自我神化,拒斥谏言,进而目空一切,迷信天命;极度蔽塞又使其错判形势,纵情逸乐。两者的合力,使殷商王朝这个强大的堡垒从内部崩坏了。国不突亡,惟逸亡之;政不立息,惟慢息之。纣王忽视对政治准则的细微关照,而最终压死骆驼的,却正是那一根根看似微不足道的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