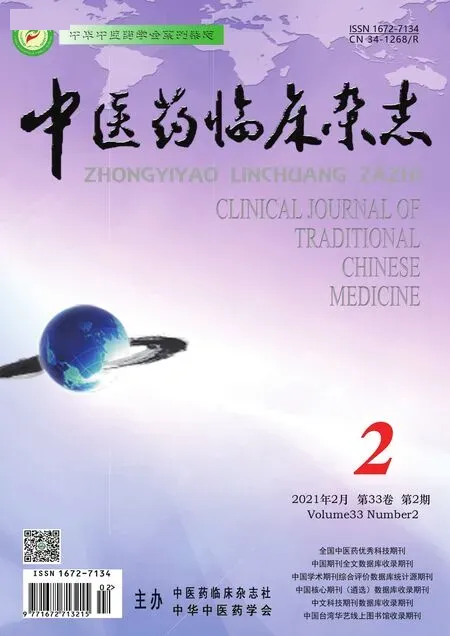陆曙“双心同调”论治心血管疾病经验*
夏成霞,陶国水,2,陆曙,2
1 江苏省无锡市中医医院 江苏无锡 214071
2 江苏省无锡市龙砂医学流派研究院 江苏无锡 214071
在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下,“双心医学”应运而生,要求临床医生不仅要关注患者的心脏疾患,更需关注患者的心理,以期达到“心身”协调,体现疾病诊疗过程中“以人为本”的理念。而中医学对于心身疾病的关注已积累了数千年的经验,“心主血脉”,“心主神明”,二者密不可分,《素问·调经论》载“五脏之道,皆出于经隧,以行血气,血气不和,百病乃变化而生”,《灵枢·平人绝谷》有云“血脉和利,精神乃居”,《医林绳墨》说:“夫人身之血气也,精神之所依附者,并行而不悖,循环而无端,以成生生不息之运用……故血乱而神即失常也。”可见双心疾病应为“神明之心”与“血脉之心”功能异常所导致的形神合病。吾师陆曙教授为第六批全国名老中医专家学术经验指导老师,从医三十余载,在临床工作中也践行“双心同调”理论,在治疗心血管系统疾病的同时着力于对患者情志状态的调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辨治思路
《素问·灵兰秘典论》提出“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肝者,将军之官,谋虑出焉”,《素问·举痛论》言:“百病生于气也”,肝气失于疏泄,则气机逆乱,而百病始生。若情志不遂,肝气失疏,会出现抑郁焦虑等负性情绪,且肝气郁久,则可化火,火扰心神,会出现心悸等症状。《素问·灵兰秘典论》又载“心主身之血脉”,而肝气失于疏泄,则会影响脾胃运化和升降功能,进而造成水湿不运,形成痰饮;气滞日久可致血行瘀阻;以上病理产物均易致脉络不通,心脉失调,引发胸痛、胸闷等症状。故“心主血脉”、“心主神明”的功能均赖于肝气的调畅。
历代医家在治疗肝气郁结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柴胡疏肝散、逍遥散等都是常用方剂。陆师在临床上则发现多数气郁者常夹杂痰火、血瘀等,证型复杂,其实早在元代朱丹溪就提出:“气血冲和,万病不生,一有怫郁,诸病生焉。故人身诸病,多生于郁”,并在书中首次提出“六郁”,且云:“郁病多在中焦,中焦脾胃也,水谷之海,五脏六腑之主,四脏一有不平,则中气不得其和而先郁矣”,可见六郁之成,与肝脾密切相关。肝气失于疏泄则为气郁;气机不畅导致血行瘀滞而为血郁;气郁日久,化热生火而为火郁;肝气失于疏泄,则会影响脾胃运化和升降功能,进而造成水湿不运,停滞为湿郁;湿聚成痰而为痰郁;脾胃腐熟水谷的功能失常,运化失职,则饮食积滞而为食郁;故气郁、火郁、血郁主要责于肝,痰郁、湿郁、食郁主要责于脾[1]。基于此,朱丹溪立越鞠丸治之。此方中香附疏肝解郁,以疗气郁;川芎活血祛瘀,以治血郁;栀子泻火除烦,以解火郁;苍术燥湿健脾,以治痰湿郁;神曲健脾消食,以消食郁。诸药配伍,使气畅血行,湿去热清,食化脾健,六郁俱除[2]。费伯雄 《医方论》云:“凡郁病必先气病,气得流通,郁于何有? ……气郁者香附为君,湿郁者苍术为君,血郁者川芎为君,食郁者神曲为君,火郁者栀子为君”,可见方中的五味药,根据“六郁”的侧重不同,都可为君药。故而陆师在临证辨治也常从“郁”论治,化裁运用越鞠丸,收到良好效果。
药理研究
越鞠丸是治疗郁病的常用方,故对其方中五味药的药理有深入研究。川芎的主要有效成分为阿魏酸钠和川芎嗪,针对心血管系统疾病的临床治疗,体现在抗血小板聚集,改善冠状动脉血流,抗动脉粥样硬化,镇静、镇痛,拮抗钙离子,减轻机体毛细血管通透性等[3]。苍术的主要化学成分为倍半萜及苷类、烯块类等,现代药理研究显示,苍术具有促进胃肠运动及排空,抗菌抗炎,利尿,心血管保护等多种药理作用[4]。香附的有效成分主要为挥发油类,具有镇痛,抗抑郁,促进胃肠蠕动,改善血液流变性,降压等作用[5]。栀子的主要有效成分为栀子黄色素、环烯醚萜等,在降血糖、胃功能保护、降压、调脂、抗炎、抗血栓、抗抑郁等方面具有一定的活性[6]。六神曲含有丰富的挥发油、消化酶等多种成分,有保护和调节肠道菌群,提高胃肠动力的作用[7]。对全方药理研究发现,越鞠丸有抗抑郁、保护心脏、调节肠胃功能、防治代谢综合征等作用[8]。
临床应用
1 高血压病
高血压病是以体循环动脉压升高为主要临床表现的心血管综合征。2019 年的《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提出长期精神紧张是高血压病患病的危险因素[9]。过往研究也显示,高血压病的发生、发展及其转归与心理行为因素有密切的联系,焦虑情绪与高血压病风险的增加存在一定的相关性[10]。高血压多属中医学“眩晕”范畴,《素问·至真要大论》载“诸风掉眩,皆属于肝”,《丹溪心法》又云“故无痰不作眩也”,清·李中梓《证治汇补》中言“七情所感,脏气不平,郁而生涎,结而为饮。随气上逆,令人眩晕”,并总结道“以肝上连目系而应于风,故眩为肝风。然亦有因火,因痰,因虚,因暑,因湿者”,另则眩晕迁延不愈,久病入络,致瘀血阻窍,发为眩晕。周训杰等[11]研究发现加味越鞠丸对降压有辅助作用,能改善胰岛素抵抗,并可缓解患者的症状,且有效改善患者焦虑或抑郁的状态。可见高血压病患者多存在紧张、焦虑的精神状态,且从辨证上气郁、痰湿郁、火郁、血郁者居多,陆师临证时痰湿重者常合用半夏白术天麻汤,肝阳偏亢则加用天麻、钩藤平肝潜阳,百合地黄汤多用于阴虚有热者,气郁明显者常合用柴胡疏肝散,血瘀明显的合陆师自创之交泰调脉方[12]。
2 冠心病
冠心病是指冠状动脉(冠脉)产生粥样硬化引起管腔狭窄或闭塞,导致心肌缺氧或坏死而引起的心脏病。有报道发现,合并焦虑抑郁的冠心病患者,其精神压力诱发心肌缺血发生率明显高于无焦虑抑郁的冠心病患者[13]。有资料表明,约有1/5 的患者,其心绞痛发作以情绪波动为诱因,激怒可以导致交感-肾上腺髓质兴奋,进一步引发冠脉痉挛,心肌细胞电位进而改变,以致心肌耗氧量增加,从而诱发心绞痛[14]。冠心病属于中医学“胸痹”等范畴,以胸部闷痛为主要症状,汉代·张仲景《金匮要略》将其病机归纳为“阳微阴弦”,清李中梓总结前人经验,在《证治汇补·胸胁门》心痛篇中载“而方论复分曰痰,曰食,曰热,曰气,曰血,曰悸,曰虫,曰疰,曰饮者,亦常见之候,均宜力辨”。胡蓉等发现越鞠丸可以降低大鼠血清中肌酸激酶(CK)、乳酸脱氢酶(LDH)的活性,增高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SH-Px)、超氧化物歧化酶(SOD)的活性,提高心肌抗氧化能力,以对抗心肌供血不足的诸多症状[15]。毛拉提·努尔沙德克等研究发现,越鞠丸可使老年不稳定型心绞痛(UA)患者PCI 手术后白细胞介素(IL-6)、超敏C 反应蛋白(hs-CRP)水平降低,白介素10(IL-10)水平升高,从而改善预后,并提高生活质量[16]。越鞠丸可疏气郁,化痰郁,调血郁,解食郁,从而达到“通则不痛”的目的,血瘀重者陆师常合用丹参饮、交泰调脉方,瓜蒌薤白半夏汤常合用于寒痰甚者,气郁明显则加柴胡疏肝散、四逆散。
3 心律失常
心律失常是指心律起源部位、心搏频率与节律以及冲动传导等任一项的异常。大量研究显示,心律失常患者常合并一些心理障碍,如焦虑、抑郁等,其可相互影响,形成恶性循环[17]。刘桂梅等[18]对360 名合并抑郁、焦虑症的老年心血管病患者进行动态心电图的检查,发现心律失常检出率明显偏高。心律失常可以归为中医“心悸”、“怔忡”、“惊悸”的范畴,其病位在心,《灵枢·百病始生》“忧思伤心”及《灵枢·邪气脏腑病形》篇的“愁忧恐惧则伤心”,都体现了“心主神志”功能异常而出现的不良情志活动对心的生理功能产生影响。肝郁气滞,气郁日久,瘀血内停,心气失畅,发为心悸;或气郁化火,炼液成痰,痰火扰心,心神失宁而心悸。从中可提炼出瘀、痰、火、气等病理因素,陆师临证时血瘀重者常合用丹参饮,痰热明显的加用黄连温胆汤,气郁化火者常合用栀子厚朴汤,收效甚显。
4 血脂异常
血脂异常指血浆中脂质量和质的异常,通常指血浆中胆固醇和(或)甘油三酯升高,也包括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降低。随着人们饮食及生活方式的改变,高脂血症现已严重危害人类健康。已有研究表明,抑郁症与高脂血症之间存在相关性[19-22],血脂异常中医可归于“血浊”范畴。在当今社会环境下,人们承受着来自各方的压力,导致气机不畅,浊气内生,蓄积于血液之中,发展为血浊。《血证论》有:“木之性主于疏泄,食气入胃,全赖肝木之气疏泄之而水谷乃化”,若肝气失疏,气血津液运行障碍,聚而成痰,痰阻血脉,瘀血内停,产生血浊的状态。李玉波等[23]研究发现越鞠丸能降低TC 和LDL-C,其机制与辛伐他汀不同,越鞠丸可能通过抑制红蝽菌科等4 类细菌和促进双歧杆菌科等5 类细菌的生长来降低TC 和LDL-C。故而陆师常用越鞠丸加减治疗,疗效显著。
典型案例
患者薛某,女,63 岁,2018-03-31 初诊,主诉:头晕5 年余。查体:血压 160/90 mmHg,心率 68 次/分,律齐,未及杂音。刻诊:头晕,口干,偶有心慌,大便溏,小便调,纳可,夜间难以入睡,苔白,质紫暗,脉弦细。中医诊断:眩晕病(肝郁脾虚、心脉痹阻证)西医诊断:原发性高血压、高脂血症、动脉硬化。治拟柔肝健脾,通络宁心,处方:川芎10g,醋香附10g,焦栀子10g,六神曲10g,炒苍术10g,炒白芍10g,生地黄10g,当归20g,紫丹参10g,楮实子10g,肉桂(后下)3g,黄连3g,百合干10g,7 剂,水煎服,每日1 剂。04-10 二诊:头晕、心悸好转,夜寐、纳食改善,血压:150/90mmHg,苔脉如前,继拟前法,前方去生地黄、当归、百合干、炒白芍,加葛根30g,14 剂,水煎服,每日一剂。后以前方适当加减变化1 月后头晕明显好转,血压稳定。
按:该患者以肝郁脾虚为基础,表现为头晕,大便溏;进而脾虚生化不足,血不养心,出现口干、心慌、失眠等症状;另外肝郁气滞,气郁日久,瘀血内停,心脉痹阻,也可出现心慌的表现,故辨证属肝郁脾虚、心脉痹阻,陆师以越鞠丸疏肝理气、健脾助运,合用四物汤养血,百合地黄汤养阴清热,交泰调脉方调畅血脉,宁心安神。二诊时患者头晕、心悸好转,但测血压仍偏高,故去生地黄、当归、百合干、炒白芍,加葛根是取其降压的药理作用。
结 语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居民生活、工作压力倍增,加上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多因素作用下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逐年升高,防治任务任重道远。虽然西药治疗仍占主流,但“双心医学”模式的提出,给了中医中药治疗更广阔的空间,结合心血管疾病的特点,陆曙教授从“六郁”,以越鞠丸为主方,但此方虽对“六郁”均有兼顾,但因疾病侧重不同,需有所加减,陆师常以“三从”为原则,“从病”者,乃不同疾病有其自身的特点,如冠心病的血瘀理论需贯穿治疗的始终,故血郁当为其重;“从证”者为根据疾病特有阶段的表现,辨证论治;“从时”是依据特定时期的运气特点,结合疾病本身,加减用药;加之陆师精通中药药理学,衷中参西,常能做到精准用药,疗效甚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