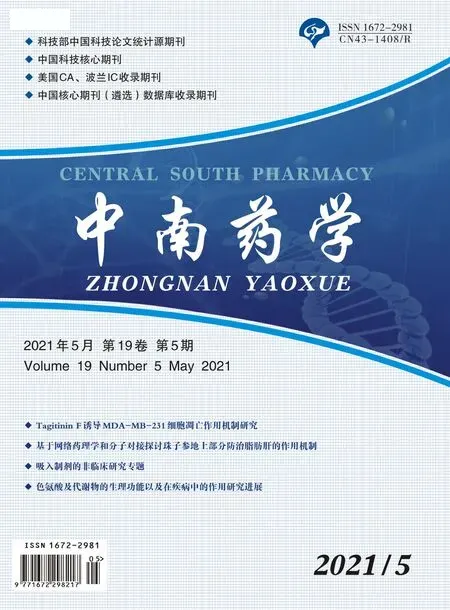金诺芬在卵巢癌中的作用机制及研究进展
刘小平,王铭远,2,肖彩艳,王劲进*(.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附属株洲医院妇产科,湖南 株洲 42000,2.中南大学基础医学院病理生理学教研室,长沙 40008)
卵巢癌是常见的妇科肿瘤,全球统计数据表明,每年约有30万例新诊断的卵巢癌病例,其中60%以上因该病死亡[1]。由于卵巢癌早期症状隐匿,缺乏特异性肿瘤标记物等,超过70%的卵巢癌患者确诊时即为晚期;经正规治疗达到临床完全缓解后,约70% 的人在两年内出现肿瘤复发[2]。目前治疗方案以手术为主,铂类为基础的联合化疗为辅,但铂类药物毒副作用大且易产生耐药,成为卵巢癌治疗失败的主要原因[3]。因此,寻找和开发新型药物联合应用以降低铂类药物毒性和耐药性、增加抗肿瘤疗效是卵巢癌治疗的迫切需求。
金属配合物(如铂、金和铜)已显示出巨大的抗肿瘤潜力[4],其中,金诺芬(auranofin,AF)是第一个被发现有抗肿瘤活性的一价含金化合物,有治疗潜力但目前缺乏系统研究。已有研究表明AF有广泛的生物学活性,包括抗菌、抗病毒、抗炎、抗肿瘤[5-9]等。AF可通过阻滞细胞周期、诱导凋亡、诱导氧化应激等发挥抗肿瘤作用,由于其存在多种氧化态及多种结构的配体,抗肿瘤作用机制较复杂,具体作用机制尚未完全阐述清楚[10]。本文就AF在卵巢癌中的研究现状进行综述,为AF的进一步研究和临床应用提供参考。
1 AF抑制卵巢癌细胞的生长增殖
正常细胞遵循G0/G1-S-G2-M的周期顺序,细胞周期紊乱是癌变的重要起因及基本特征。AF能将肿瘤细胞阻滞在细胞周期的不同阶段,从而抑制肿瘤无限增殖。在Calu-6细胞和SK-LU-1细胞中,低浓度的AF即可将其分别阻滞在G2/M期和G1期,从而抑制肿瘤细胞增殖[11]。Gandin等[12]发现不同AF衍生物处理卵巢癌细胞后Sub-G1期细胞(常代表凋亡细胞数目)较对照组增加6~14倍,进而影响DNA合成,抑制卵巢癌细胞的增殖。Park等[13]指出AF治疗组肿瘤细胞的存活数约为对照组的1/13,且AF呈剂量和时间依赖性地抑制卵巢癌细胞的存活和增殖[13-14]。Wang等[14]首次证明AF可能通过抑制癌基因——蛋白激酶C1(PKC1)信号转导,影响具有自我更新能力的肿瘤起始细胞(TICs)从而抑制卵巢癌细胞增殖。在动物模型中,AF也发挥强大的抗肿瘤活性[14-16]。研究发现AF治疗组小鼠肿瘤细胞的有丝分裂指数较对照组降低,小鼠瘤体积也明显减小。27 d后对照组小鼠因出现临床症状而终止实验,AF治疗组则没有出现任何临床症状[14]。
此外,研究表明AF能不可逆地抑制卵巢癌顺铂敏感细胞系(2008、A2780-S)和顺铂耐药细胞系(C13、A2780-R)的增殖和集落的形成能力[16-17]。AF对卵巢癌顺铂耐药细胞同样能发挥抗肿瘤效应。在OVCAR8细胞中,AF的IC50值约为0.34 μmol·L-1,而顺铂的IC50值约为8.95 μmol·L-1,这表明更小剂量的AF即可发挥抗肿瘤作用[18]。
2 AF诱导卵巢癌细胞凋亡
细胞凋亡(即Ⅰ型程序性细胞死亡)是严格受基因调控以维持机体内环境稳态的过程。细胞凋亡途径包括死亡受体介导的外源性途径和线粒体介导的内源性途径,AF可通过调节凋亡相关蛋白、线粒体等多个环节诱导凋亡。
2.1 AF影响B细胞淋巴瘤-2(BCL-2)蛋白家族诱导凋亡
BCL-2家族是一类调控细胞凋亡的关键因子,其中BCL-2和BAX分别是BCL-2家族中最主要的抑凋亡蛋白和促凋亡蛋白。AF可通过上调促凋亡蛋白BAX和BIM,下调抑凋亡蛋白BCL-2和IκB激酶(IKK-β)的表达诱导卵巢癌细胞凋亡[13]。
2.2 AF影响半胱氨酸蛋白酶(Caspase)家族诱导凋亡
Caspase家族能选择性切割某些蛋白从而诱导凋亡,其中Caspase-3起着核心诱导作用[19]。Marzo等[15]研究发现AF处理A2780细胞后,Caspase-3表达量几乎是对照组的10倍,凋亡显著增加;在小鼠模型中,AF显著减少瘤体积的同时不影响治疗组小鼠的行为、活力及体重。Gandin等[12]的研究结果也表明,AF通过诱导Caspase-3激活从而介导细胞凋亡,其中AF处理组细胞凋亡特征较对照组更为显著,主要表现为细胞染色质浓缩和核DNA片段化明显增加。与此同时,Park等[13]发现AF可能通过调控IKK-β/叉头框蛋白O3(FOXO3)途径诱导SKOV3细胞凋亡。转录因子FOXO3有促进凋亡、抗氧化、延长寿命等多种生物学功能。在卵巢癌细胞中,沉默FOXO3可显著减少Caspase-3介导的凋亡,AF可通过下调IKK-β使FOXO3转录活性增加,从而诱导卵巢癌细胞凋亡。
2.3 AF影响线粒体细胞色素C(Cyt-c)诱导凋亡
Cyt-c从线粒体释放到胞浆和线粒体膜电位丧失是线粒体凋亡途径的关键步骤[20],研究表明AF可引起Cyt-c的释放和线粒体膜电位的改变[21]。在顺铂敏感和耐药的卵巢癌细胞中,AF与曲美替尼联用均能诱导Cyt-c释放,增加凋亡标志物DNA片段化,从而显著诱导细胞凋亡[22]。在肝癌[23]和肺癌[11]细胞中AF通过诱导线粒体膜电位损失,引起线粒体功能障碍从而诱导其凋亡。但Hyter等[24]发现在卵巢癌细胞中,经AF治疗后的线粒体膜电位没有发生明显变化。故AF能否通过改变卵巢癌细胞线粒体膜电位从而诱导凋亡仍有待进一步研究证实。
3 AF诱导卵巢癌细胞氧化应激
细胞内各种生理生化反应的顺利进行,都需要一个氧化还原平衡的稳定内环境,当生物遭受到环境压力时一般会伴随活性氧(reactive oxygen species,ROS)的大量产生。AF可通过诱导肿瘤细胞氧化应激发挥抗卵巢癌作用。硫氧还蛋白还原酶(thioredoxin reductase,TrxR)是硫氧还蛋白(thioredoxin,Trx)系统(体内重要的抗氧化系统)的关键酶,Trx系统维持机体内氧化还原稳态的前提是Trx处于还原状态,而TrxR是细胞内部唯一已知的可以将Trx还原的物质[25]。AF是TrxR的特异性抑制剂,通过靶向抑制TrxR氧化还原活性中心[26],使得氧化应激产物ROS在体内过度蓄积从而引起细胞氧化损伤[27]。研究发现,TrxR在许多肿瘤中过表达[23,28],高表达的TrxR会促进肿瘤发展[29],这可能与其抗凋亡、促进新生血管生成和转移有关[30]。在卵巢癌细胞中,AF同样通过抑制TrxR的表达,诱导ROS产生,发挥抗肿瘤作用。Oommen等[31]还发现AF可剂量依赖性地增加DNA双链断裂(DNA DSB),减少细胞克隆,诱导DNA损伤和细胞凋亡,从而发挥抗肿瘤活性。而应用抗氧化剂N-乙酰基半胱氨酸(NAC)可显著减少AF诱导的卵巢癌细胞DNA损伤和凋亡。由此推测AF可能通过抑制TrxR导致ROS蓄积,影响细胞氧化还原稳态。
研究还发现化疗耐药的卵巢癌细胞中往往显示出更高的TrxR水平[17],并且纳摩尔级别的AF即可抑制TrxR活性[16]。Yamada等[32]证实顺铂耐药的卵巢癌细胞系中耐药程度与TrxR表达水平成正相关,并且AF比顺铂能更有效地降低细胞活力[16-17],故AF可有效逆转卵巢癌细胞顺铂耐药。在紫杉醇耐药的卵巢癌细胞A2780/PTX中发现Trx1和FOXO1较敏感细胞过表达,而沉默Trx1后FOXO1活性降低,细胞对紫杉醇的敏感性增加[33],AF逆转卵巢癌细胞紫杉醇耐药的机制之一可能是通过抑制Trx1/FOXO1信号通路实现的。此外,Landini等[34]研究表明,TrxR的高表达是细胞产生AF耐药性的原因之一,而对AF耐药的A2780/AF-R细胞对顺铂不耐药。
综上,AF在顺铂和紫杉醇耐药的卵巢癌细胞中均可能通过抑制TrxR,诱导氧化应激而表现出良好的抗肿瘤活性,同时A2780/AF-R细胞对顺铂敏感,这表明AF与顺铂不存在交叉耐药。故AF有望与化疗药物联合应用于卵巢癌的治疗。
4 AF与其他药物联用抑制卵巢癌
许多研究表明AF与其他药物联用时可更有效地发挥抗肿瘤作用。Kato等[35]发现AF与无毒剂量的MI-463(Menin混合谱系白血病抑制剂)联用后显著增加血红素加氧酶-1(HO-1)的mRNA和蛋白表达,从而诱导卵巢癌细胞铁死亡,发挥抗肿瘤作用。Bae等[36]发现单用AF或沉默黏蛋白4(MUC4)不影响SKOV3细胞中凋亡相关蛋白的表达,但协同使用后BAX和BIM上调,BCL-2下调,PARP1和Caspase-3裂解增加,抗卵巢癌作用显著增加。Papaioannou等[37]发现AF在卵巢癌细胞中抑制Trx系统后可显著增强双硫仑(一种活性氧诱导药物)的细胞毒作用。此外,AF与曲美替尼的组合可能通过诱导ROS促进肿瘤细胞中p38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APK)的磷酸化,从而诱导线粒体应激,随后通过释放凋亡诱导因子来促进肿瘤细胞凋亡[22]。因此联合用药可能更进一步增强AF的抗卵巢癌作用。
5 展望与结语
AF于1985年经FDA批准用于类风湿关节炎的临床治疗[38],但尚未作为抗肿瘤药物进入临床。“老药新用”不仅可以节省时间和成本,还可为药物作用机制和疾病生物学提供新思路。金属配合物的中心金属离子具有多种配位数和几何构型,这些构型赋予其广泛的生物活性,而金属离子独特的性质又赋予了配合物特有的理化性质[39];此外,配合物中的配体还能以协同作用方式发挥重要的药理作用。AF的配体——三乙基膦基(R3P)增加了AF的稳定性及脂溶性,有助于其渗透进入细胞膜,而去除R3P后AF的细胞毒性降低了150倍[40]。顺铂主要以DNA为作用靶点[41],而肿瘤细胞对DNA损伤具有修复能力,因此容易出现耐药性。与顺铂不同,AF的主要作用靶点包括线粒体和蛋白酶体,这可能与其特异性抑制含硒蛋白TrxR有关[42-43]。主要作用靶点不同可能是AF与顺铂无交叉耐药的原因之一。AF的给药途径为口服,与静脉给药的铂类药物相比,药物不良反应相对较少,患者依从性高。顺铂及其代谢产物主要经肾脏排泄,故肾毒性明显,而AF主要经粪便排泄,主要表现为胃肠道不良反应,且不良反应较少。
大量研究表明,AF能有效逆转卵巢癌细胞顺铂耐药[15-17],这可能还与肿瘤细胞的膜流动性相关。肿瘤细胞的膜流动性通常大于正常细胞,并且膜流动性与肿瘤细胞恶性程度及化疗耐药成正相关[44]。顺铂处理的卵巢癌细胞膜流动性迅速增加[45],但AF对卵巢癌细胞膜流动性没有明显影响[46]。因此与顺铂相比,AF可能不易产生化疗耐药。进一步研究发现卵巢癌细胞系中膜流动性与AF敏感性之间存在正相关,即恶性程度高的肿瘤可能对AF更为敏感[46]。因此,AF对于恶性程度高和顺铂耐药的卵巢癌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AF因其重要的抗肿瘤作用已被纳入多种疾病的临床试验阶段,如卵巢癌(NCT01747798)、肺癌(NCT01737502)和白血病(NCT01419691)。在卵巢癌的临床试验中,纳入10名CA-125升高的无症状卵巢癌术后患者,进行为期28 d的口服AF治疗。结果发现4名患者在AF治疗后的第一个月内CA-125趋于稳定(即升高或降低程度低于50%),1名患者在经AF治疗后的3个月内CA-125逐步降低,而停用AF后CA-125显著增加。在这项试验中,大多数患者对AF的耐受性良好[47]。这些临床研究均表明有必要进行更多的临床前和临床研究,以证实AF的潜在抗肿瘤活性及治疗剂量和安全性。
综上,卵巢癌因其恶性程度高、复发率高已成为妇科肿瘤的治疗难题,铂类化疗药物的肾毒性、骨髓抑制及消化道等不良反应严重限制其在临床的应用,且许多患者在初始化疗后产生铂耐药。故寻找新型抗肿瘤药物以克服铂类药物的不足之处显得尤为重要。AF以其重要的抗肿瘤作用及逆转顺铂耐药为卵巢癌患者的临床治疗带来希望。目前AF在卵巢癌中的作用机制研究主要集中在抑制细胞增殖、诱导凋亡和抑制TrxR等方面,是否存在其他相关机制仍有待进一步研究。AF具有一般金属配合物的共同特性,同时与顺铂无交叉耐药,且不良反应较少。但其用于治疗卵巢癌的临床使用剂量及安全性仍需更多临床试验证实。随着人们对AF抗肿瘤作用机制及研究进展的不断深入,其有望成为有效的抗肿瘤药物,为临床治疗带来希望。
- 中南药学的其它文章
- 小檗碱抗肿瘤作用机制研究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