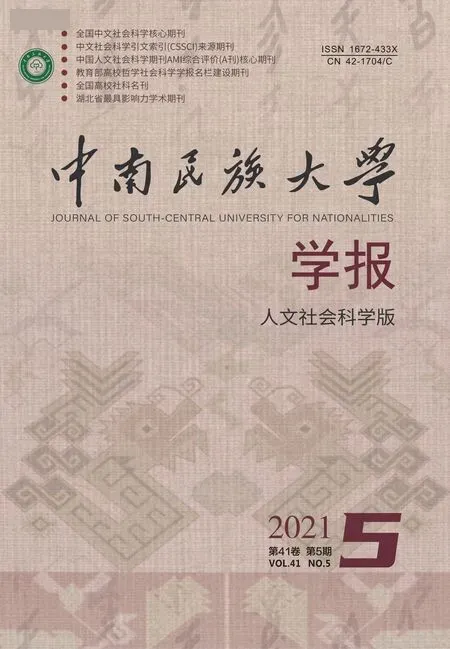近三十年来清代中俄政治外交问题研究述评
叶柏川,于白昆(中国人民大学 清史研究所,北京 100081)
中俄关系是清朝时期重要的双边关系。现实中两国间的很多问题,都要从清朝追根溯源,尤其是两国领土边界奠定于清朝时期。受时代背景影响,包括领土边界在内的政治外交问题历来是清代中俄关系史研究的重点。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中俄致力于建设新型的国家关系,中俄关系史研究也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随着中俄划界问题的解决,出现了一批总结性的研究成果,有关政治外交的专题讨论更加深入。本文拟对近30年来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回顾总结。
一、中俄东段边界及相关问题研究
1991年苏联解体后,中俄边界主要集中于东段地区,长约4200公里。2004年10月,两国签署《中俄关于两国边界东段的补充协定》,2005年完成换文,从而在法律上彻底解决了划界问题。伴随着中俄划界的进行和解决,双方都出现了一个讨论边界问题的小高潮。因现实中俄边界主要集中于东段,这方面的成果明显更为集中。
中俄东段边界历经几次大的变化:第一次是中俄《尼布楚条约》划界,两国由无边界到有边界;第二次是《瑷珲条约》签订后,额尔古纳河一段变成东北地区西段中俄边界;第三次是中俄《北京条约》签订之后,把乌苏里江以东中俄“共管之地”变为俄国独占,出现了东北地区东段中俄边界,北起乌苏里江口,南至图们江口[1]4。
1689年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划分了早期中俄东段边界。因条约文本及后世文献记载的差异,中外学界在条约的法律地位及其规定的界河、分界点,以及约后立碑情况等问题上存在诸多争议,即使在一国学界内部,也有不同认识。近年来学界对满文舆图及档案的解读,为相关问题的讨论提供了新的重要论据。
1.清后期东北地区东段中俄边界研究。中俄《瑷珲条约》与《北京条约》签订之后,中俄东段边界发生重大变革,形成西、北、东三段。其中东段中俄边界,由于江河多变,界牌容易腐烂,故“界务纠纷之复杂,勘界次数之多,涉及范围之广,是东北地区西、北段边界所少有的”。双方间大的纠纷有黑瞎子岛、“耶”字界牌,通江子、白棱河及兴凯湖问题。中俄《北京条约》(《续增条约》)规定:“自松阿察河之源,两国交界,逾兴凯湖,直至白棱河口,自白棱河口顺山岭至瑚布图河口,再由瑚布图河口顺珲春河及海中间之岭,至图们江口,其东皆属俄罗斯,其西皆属中国。”[2]但无论是吉林省所藏地图还是伊格纳季耶夫来京时所进地图都未标示白棱河。1861年中俄兴凯湖会议勘界时,俄方代表强调“奎屯必拉迤北之分支小河”为白棱河,中方代表则认为“白棱河应在兴凯湖西南,与伯珍河(即白珍河)及白志河部分尚属符合”。刘家磊经过实地考察和考证认为,俄方强指奎屯必拉迤北的分支小河为白棱河,“是另行选择将兴凯湖边界的西南改为西北走向的方案”,而中俄《北京条约》所载白棱河指的是兴凯湖西南的缐河,也叫西颜(满语“细”的意思),因为根据《北京条约》及其附图,“只有缐河,不仅河身在兴凯湖西南,河口也在该湖的西南岸,而且在河口附近即伊利英卡西南有一西南走向的山岭,与中俄《北京条约》的规定相符合,与其附图所划边界线的西南走向一致”[1]122。
黑瞎子岛是黑龙江与乌苏里江的冲积地,刘家磊认为,“在1860年签订中俄《北京条约》之前,整个黑龙江流域都是中国领土”,即使划分中俄边界的中俄《北京条约》也将黑瞎子岛划归中国”[1]206,距黑瞎子岛最近的“‘耶’字界牌原立于乌苏里西岸黑瞎子岛东北端的莫勒密或乌苏里江口迤上三里左右的高阜上,后被俄人潜移私挪,至1886年换用石碑时已被移至通江子东口迤上五里左右的乌苏镇”[1]202-203。1886年重勘吉林东界,吴大瀓只勘查自图们江至白棱河口的边界,并未勘查松阿察河至乌苏里江口的边界,而三姓副都统顺林不谙地理,不知边界莫勒密在何处,将“耶”字界牌换立在俄人潜移之处,即卡扎克维赤沃村对岸,通江子东口以上,即今乌苏镇东北。他指出,“不管‘耶’字界牌立在何处,它都标志着从乌苏里江口开始以乌苏里江为界,并非以界牌的所在地为界”[1]205。吕一燃指出,“1861年双方共同设立的‘耶’字界牌的位置在乌苏里口以上三里许的高阜上,而不在乌苏里口近岸的莫勒密”[3]211,原因是俄方代表提出“乌苏里口近岸莫勒密地方低洼,立牌恐被冲没”,中方负责立牌官员副都统福尼扬阿“恐距岸较远,仍于莫勒密地方多立界牌一面,以为印证”,但后被“江水涨发冲没”[3]211,亦未补立。
他还指出,由于“俄方官员包办一切,以及中方官员的无能,致使设立的界牌并不完全符合中俄《北京条约》的规定”,如没有设立位于图们江口左岸的“乌”字界牌,错立了“土”字和“倭”字界牌;中俄东界的终点在图们江口左岸,这里有一个本应设立而未设立的“乌”字界牌,“土”字界牌并不是中俄边界终点的标志;兴凯湖勘界会议签订的《中俄东界交界道路记文》相较于《北京条约》之规定15座界牌,少了7座[3]209。
2.中俄逃人问题。边界与逃人问题密切相关。逃人、通商、划界问题交织在一起, 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构成17、18世纪中俄关系的主要内容。“中俄两国在订立边界条约以前, 对毗邻土地的控制权往往是通过对当地部族的控制取得的”,“因此,中俄两国针对各自的逃人问题均采取针锋相对、穷追不舍的态度”[4]。1667年清属索伦部首领根特木尔率部众五百人逃往俄国事件,引起双方政府高度重视,也成为雅克萨战争和《尼布楚条约》签订的重要因素[5]。根特木尔事件促使清政府重新审视原有的东北边疆政策,做出一系列改变,影响了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进程[6]。
此外,惠男利用满文档案及俄国驻北京传教团的见闻资料,讨论了1764-1780年间在新疆、蒙古和黑龙江等边疆地区被清朝卡伦守卫所缉获的俄罗斯逃人的命运,展现了自《尼布楚条约》和《恰克图条约》签订以来有关逃人遣返条款的执行情况[7]。金鑫利用《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考证了第一次雅克萨之战后清军所获的各项人口、身份、数量、处置结果等问题[8]。 刘亮、张海林从涉外法律角度探讨了清朝交涉越境事件的法理依据、具体操作方式、实际效果等问题[9]。 姚敏、王聪从移民视角讨论了清前中期中俄俘虏、逃人问题[10]。
二、中俄西段边界、边疆及相关问题研究
1991年苏联解体之前,中苏西段边界涉及地域相当广阔,而苏联解体之后,原中苏边界成为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四国的共同边界,其中中俄共同边界仅余54公里。与中俄东段边界研究相比,近年来西段边界研究成果相对分散。
1.唐努乌梁海问题。唐努乌梁海原为清朝版图上的一个行政区,清末民初被俄国所占,1921年在此地建立由苏俄控制的图瓦共和国,1944年成为苏联俄罗斯联邦的一个自治州,后成为自治共和国。因资料匮乏,该地区向为大陆与台湾学者少有涉足的研究领域。樊明方的系列成果,大大推动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其所著《唐努乌梁海》以大量原始档案为基础,以唐努乌梁海的主权归属为重点,考察了历代对乌梁海地区的设置、管辖,清朝时期中俄对该地的交涉,以及中俄边界条约对乌梁海地区的规定等问题。吕一燃称该著为“这一领域前所未有的力作”[11]。 樊明方指出,从1727年到1911年的180多年中,清政府对唐努乌梁海地区的管辖突出表现在编旗设官、征收贡赋、司法管辖、内务民政管理,边界保卫等方面[12]39;《布连斯奇界约》在唐努乌梁海地区的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该约签订后,“唐努乌梁海是中国领土这一点是确定不移,无可动摇的了”[13]。
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将原属中国的阿穆哈河划归俄国,因此关于嘉庆年间游牧于阿穆哈河一带归定边左副将军直辖的唐努乌梁海十佐领的下落引起学界关注。《沙俄侵略我国蒙古地区简史》和《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两书认为,这十佐领与阿勒坦淖尔乌梁海二旗一样,由于《勘分西北界约记》的签订而并入俄国。台湾学者李毓澍在其长文《唐努乌梁海佐领考》中提出,同治年间中俄划界后,原游牧于阿穆哈河一带的十佐领唐努乌梁海人即自动内徙。樊明方认同李毓澍的内徙说,但时间上认为这十佐领在同治年间中俄划界之前就已迁入了克穆齐克河一带[12]89-92。此外,谈汀利用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军机处录副奏折,通过考察乾隆朝君臣对汗卡屯俄属乌梁海人越界问题的处理,讨论了清朝统治者传统边界观念与近代边界意识之间的碰撞。
2.中俄科塔谈判及《科塔界约》。中俄科塔边界谈判, 是光绪七年 (1881)《中俄改订条约》签订之后进行的西部三段边界谈判中最为重要的谈判。何星亮于1983年在阿勒泰市地委档案馆发现清光绪九年 (1883) 勘分中俄科塔边界大臣等写的五件札谕,分别以哈萨克察合台文、满文和汉文三种文字写成。“五件文书内容相关,但又自成一系,均写于清光绪九年(1883) 中俄勘分科塔边界前后。其内容既谈及当时所定中俄科塔边界, 也谈及当时安置哈萨克族的有关情况和勘分边界前后的一些问题。”[14]何星亮对五件文书和《中俄科塔界约》进行了详细考证和校注,包括相关人名、地名、部落名称,勘界大臣和相关人员额尔庆额、升泰、堆三伯特的生平简历及其有关历史,界约着重提到的三个哈萨克部落等内容。他认为,这五件文书中以察合台文文书,价值更大,具有很高的语言文字价值和历史价值,文书中所述的有些条约内容为清实录和清代外交史料所无[15]。他还指出,清政府之所以每次勘界均遭沙俄圈套, 除了沙俄伎俩狡诈之外, 其自身原因在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对边疆地理不详,测绘技术落后,勘分边界之际中方无测绘地图之人,自咸丰、同治以来中俄勘界地图均出自俄人之手,以及对边疆地区重视不够[16]。
3.卡伦问题。中俄《北京条约》将清朝设在境内城镇附近的常驻卡伦指为分界标志,使中国丧失西疆大片土地,因此卡伦问题自清朝以来就备受官学两界人士的关注。百余年来,大量成果用来论证清代中国边疆地区的卡伦并非边境哨所,亦非边界标志。清代中国西北国界的标志是边界鄂博,卡伦线并非边界线。沙皇政府强行以常驻卡伦划界,就是要把边界划到塔城城郊[12]79。 近年来学界对卡伦设置的时间讨论有所深入。李之勤认为,卡伦设置的时间绝非何秋涛所说的“始于雍正五年”,在清朝初入北京尚未统一中原时,在所属北方游牧、狩猎各部地区,就已经有卡伦设置,并且卡伦的设置可能不限于清代[17]。 宝音朝克图则提出,“蒙古地区的边境卡伦和内地卡伦之设置时间均可以追溯到康熙朝初期”,“已有国界概念的清朝政府,在康熙朝初期就将卡伦运用到漠北地区边防建设中”[18]。马长泉、张春梅认为,“早在中俄两国签订《恰克图条约》之前,卡伦存在北部边疆已是不争的事实”,《恰克图条约》及其子约将卡伦和鄂博一起作为划分双方边界的标志或者标示物,突破了《尼布楚条约》签订时期主要以自然环境作为标志物的做法,加入了人工标志的因素,条约受到了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划界原则的影响[19]。
4.准噶尔蒙古与俄国关系。清前期中俄关系中,准噶尔问题与边界、逃人、贸易问题一样,是牵制中俄关系的重要因素。讨论的焦点在于噶尔丹与俄国关系的性质及其后果。准噶尔蒙古首领噶尔丹17世纪中叶征服天山南北,雄踞中国西北,对入主中原的清政府造成威胁。以往研究强调噶尔丹勾结俄国分裂祖国,噶尔丹在1688年清朝代表准备与俄国进行谈判期间突袭喀尔喀蒙古,导致清政府不得不改变谈判战略,对俄国做出让步。对于噶尔丹是否分裂祖国,蒙古族学者黑龙提出不同观点,认为清朝对俄准关系判断有误,没有看到俄准之间出现的激烈矛盾,片面认为噶尔丹勾结俄国,而实际上是噶尔丹虚张声势,向清朝方面发出虚假信息。他指出,准噶尔部历代统治者从未臣服俄国,也从未将任何一块土地让与俄国[20]。
5.伊犁交涉问题。中俄伊犁交涉,在20世纪70-80年代是热点问题,但是近年来学界对该问题的关注减少。学界评价最高的成果是吕一燃主编《中国近代边界史》一书中的伊犁交涉部分,被认为“其研究的确切、深入、详尽程度大大超过了以往的有关著述”[21]。厉声所著《中俄伊犁交涉》是对伊犁交涉问题的专题总结[22]。不少成果专注于对伊犁交涉人物曾纪泽、崇厚的讨论,对其评价不再整齐划一。吴保晓通过查阅曾纪泽和军机处往来电报,发现由于曾纪泽及时报告俄国动向,使清政府逐步改变原定谈判目标,并授予曾纪泽某些临机处置的权力,这也是促成谈判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23]。米镇波则提出,伊犁收回是“以武力支持外交”的结果,“曾纪泽虽有功劳,然其功远在左宗棠之下”[24]。王建华、孙君琪也认为,曾纪泽在伊犁交涉界务、赔款、商务等方面存在若干失误[25]。杨红、孟楠认为,“由于左宗棠所采取的军事行动对俄国的威慑,曾纪泽在交涉中基本能坚持立场”,“但曾纪泽对形势缺乏正确的估计,又受到李鸿章的影响,在某些方面一味让步,从而使条约仍然具有不平等性”[26]。但朱昭华指出,从当时情况出发,要求曾纪泽在伊犁交涉中“商界并重”看似对中国主权有利,实则难以达到,清政府在中俄陆路通商交涉中节节失利,事实上是晚清政府边疆危机在经济上的表现,不能因此而苛责曾纪泽的修约交涉[27]。关于崇厚的评价,以往学者多批判其无能误国,蒋跃波则认为,首次伊犁交涉失败既有崇厚作为外交人员的个人缺陷,也与当时的客观环境与清政府的决策有关[28]。此外,汤仁则另辟蹊径,讨论了谈判期间清流派的活动,认为中俄伊犁谈判崇厚签约后,经历了严惩崇厚、改派使臣、改定条约等过程,每一次改动,都与清议有关,但清流派对风云变幻的世界形势认识不足,存有一定的局限性,并不能真正挽救危局[29]。
6.俄国与西藏问题。清季西藏问题是近年来研究的热点,俄国与西藏问题研究也受到关注。最重要的两部著作是王远大撰《近代俄国与中国西藏》与周伟洲主编《英国、俄国与中国西藏》。王著利用了大量一手档案,如英国“F.O.535”档案和俄国来华探险家撰写的论著,此外,还包括汉、藏、法、德文等多语种史料。该书的关键性结论是西藏自古以来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并且通过档案证实,俄国并没有霸占西藏的想法,但想要通过西藏打通通往印度洋的通道,进一步称霸世界[30]。史料方面最为重要的成果之一,是陈春华编译的《俄国与西藏——俄国档案文件汇编 1893-1914》,该汇编除包括别洛夫等俄国学者编辑的《俄国与西藏——俄国档案文件汇编(1900-1914)》外,还收入关于巴德玛耶夫档案汇编《在沙皇制度幕后》中涉及中国藏蒙的档案19件,以及《帝国主义时代国际关系》一书中涉藏档案32件,是目前涉藏档案汇编最完整的版本。此外,还有英国“F.O.535” 档案,即英国政府已公布的有关中国西藏的外交档案汇编。2005年,这部档案史料中约280万字的汉译文由中国藏学中心《西藏通史》课题组内部印制,供研究者使用[30]。
论文方面,许广智、艾虹、李晔、阎小骏等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讨论了英俄侵藏问题。星全成讨论了沙俄及日本对我国西藏的渗透活动,并对二者的渗透渠道与方式,渗透领域与效果进行了比较[31]。 梁忠翠认为,20世纪初英国政府在前进政策鼓吹者的推动下,武装入侵西藏,其军事外交方面的软硬兼施,颇显技高一筹[32]。冯建勇则认为,从实际效果来看, 似乎俄国更占优势,俄国人利用英俄协定,限制了英国对藏政策,并为其随时过问英国对藏政策提供了条约保障[33]。李冠群介绍了俄罗斯学者安德烈耶夫著《沙俄、苏俄、后苏联时期的俄罗斯西藏政策》一书。安著认为,无论是沙皇还是苏联时期的国家领导人都没有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计划,19世纪末之前的俄国同西藏地方之间的联系主要是出于宗教的原因,19世纪末至1914年间的沙俄及其后的早期俄国苏维埃政权在1918-1929年间处于同英国在中亚地区进行大博弈的阶段,当时的苏俄将西藏视为同英属印度、英国帝国主义展开斗争,向印度方向推行革命的基地[34]。
7.帕米尔问题。帕米尔问题自民国时期就受到学界关注,但对该问题的研究似乎始终未能达到足够深入,近30年来的成果更是相当有限。吕一燃讨论了清政府对帕米尔地区的管辖[35]。许建英认为,“帕米尔问题是英俄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结果。有必要就早期关于帕米尔的有关协议、英俄私分帕米尔的原因、英国入侵坎巨堤及其影响以及瓦罕走廊的法律地位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36],讨论了清政府中俄帕米尔交涉各阶段的对策[37]。朱新光讨论了英俄私分帕米尔,瓜分中国领土的经过,“并对清政府为捍卫国土主权,与英俄据理力争的严正立场予以新的阐释”[38]。
8.俄国探险家问题。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第九款明确规定:“英国民人准听持照前往内地各处游历、通商。”[39]此后,大量东西方探险队借助于不平等条约的保护,进入中国进行考察,以西北、西南和东北地区最为集中。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与当时边疆地区普遍出现危机,特别是与英法、英俄、日俄在边疆地区的角逐有密切关系[40]。俄国探险队也参与其中,且“成就卓著”。俄国探险家多为军官出身,受派于皇家地理学会。该学会由俄财政部资助,具有明显的官方性质。探险队深入中国边疆地区,对沿途山川地理、风土人情做了详细记载,将大量资料与照片发表在皇家地理学会通讯或单独出版。这些成果现存于俄罗斯联邦地理学会档案馆。近年,一些俄国探险家的著作被翻译成中文。这些成果对于研究中国边疆地区以及当时的中俄关系,意义重大。马大正撰书对此有详细介绍[41]。目前学界对于普尔热瓦尔斯基、波塔宁、谢苗诺夫、鄂登堡、科兹洛夫等热门人物的考察活动及学术成就,都有不同程度的讨论。张艳璐利用19世纪以来俄国出版的有关俄国地理学会、俄国东方学史的资料以及俄国考察队的考察报告和旅行日记,对十月革命前该学会的中国考察与研究活动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并对《俄国地理学会公报》和《俄国地理学会年报》所刊登的以及单独发行的研究中国的论著进行了编目[42]。
三、中俄遣使及礼仪之争
1.中俄遣使。中俄遣使包括派遣临时使节与驻外公使。在中俄互派公使之前,中俄双方交涉主要通过遣使或俄国驻北京传教团解决,清前期主要是俄国使节来华,中方只有两次因准噶尔事务直接向俄国派遣使节。《恰克图条约》签订之后的一百余年间,俄国驻北京传教团实际履行俄国驻华非正式外交机构的职能,直至1861年总理衙门成立后,俄国开始正式派遣驻华公使。1878年崇厚受命赴俄交涉伊犁事务,是首位中国驻俄公使。
关于早期中俄通使肇始于何时,迄今尚无定论,成为学界一桩悬案。不仅俄国学者对此争论百余年,国内学者间也存在分歧。宿丰林讨论了该问题[43]。郭蕴深以宿丰林的研究为基础,对相关讨论进行了梳理[44]。 第一种说法是1567年俄国沙皇伊凡四世派遣伊·彼得罗夫和布·亚雷切夫首使北京说。最早提出这一观点的是俄国著名历史学家卡拉姆津,很长一段时间内该说在俄国影响甚广。但余绳武认为,“历史上不曾有过所谓彼得罗夫和亚雷切夫使团,虽然历史上确有其人,但他们从未到过北京”[45]。张维华、孙西指出并未在中文史料中寻找到彼得罗夫和亚雷切夫出使中国的证据,“看来此次使华的事件,不是事实有误,就是这件事在中国未被记载下来,终致湮没无闻”[46]12。第二种说法由当代学者米亚斯尼科夫提出,认为首次来华使团为1618年佩特林使团,他与另一位学者杰米多娃在档案馆发现了佩特林的使华报告,该说近年来在俄罗斯学界占有优势。《沙俄侵华史》和《清前期中俄关系》两书支持该观点[47]。第三种说法由郝镇华提出,认为佩特林使团也不存在,1656年的巴伊科夫使团是首个来华使团[48]。第四种说法由宿丰林提出,他认为1655到达中国的彼得·亚雷什金使团才是首使中国的俄国使团。他指出,《1567年彼得罗夫使华见闻录》是半个世纪后来华的佩特林所写,所谓彼得罗夫使华没有任何可靠证据,不能作为中俄外交史的上限;1619年佩特林首使北京说虽有佩特林本人撰写的《见闻记》作证,但无相应的中文史料印证,且并无史料证明佩特林到达的中国城市就是北京;而据《清实录》记载,顺治十二年到京先行通报巴伊科夫使团即将来华的俄国商队首领彼得·亚雷切夫,是清政府按照正式使节高规格接待的首位俄国使臣,俄文史料对此讳莫如深的原因在于“彼·亚雷日金在中国行了跪拜礼,犯了俄国的大忌”[43]。
早期中俄关系的另一桩悬案,是原苏联科学院远东所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档案与文件集所收两封明朝皇帝的国书是否存在问题。宿丰林认为,这两封争论了几十年的“国书”真伪问题还有继续研究的需要,不宜轻易下结论。他举例说明,现有的俄文史料尼古拉·班蒂什-卡缅斯基编著《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 (1619-1792)》和斯帕法里出使报告都对此提出否定;斯帕法里在其出使报告中四次提到,清朝政府根据“国书”原文判别,该“国书”不是中国明朝皇帝致俄国沙皇的国书,而是明朝皇帝给边吏的任命“诏书”[49]。
嘉道时期的中俄关系前承康乾盛世,后连鸦片战争,是中俄关系即将发生巨变的酝酿时期,对于探讨近代以来中俄关系的转折具有重要意义,但这一时期的中俄外交向来为学界所忽视。得益于俄文史料《19世纪俄中关系》档案与文件集的翻译出版[50],学界对嘉庆年间来华的戈洛夫金使团(1807)进行了细致考察。戈洛夫金使团是清代规模最大的俄国来华使团,与马戛尔尼使团及阿美士德使团来华时段大致相同,其主要目标都是进一步扩大对华贸易,其结果皆是无功而返,其历史意义也大致相同,但因该使团未能走出库伦便被遣返,长久以来为学界所忽视。但俄国学者米亚斯尼科夫指出:“戈洛夫金使团同其以前派往中国的所有其他俄国使团相比,不同之处在于它与其说是要解决双边关系问题,倒不如说是要确立俄国的远东新政策,我们完全有理由把这一政策称之为亚洲和太平洋政策。”[50]5而戈洛夫金使团遭遇的戏剧性结局,甚至受到当时远在流放地的法国皇帝拿破仑的关注。这位皇帝认为:“如果俄国使臣确实想完成自己的使命,那他就应该服从接待他的国家所规定的外交礼节。”[50]1米亚斯尼科夫则提出:“综合导致使团失败的各种因素……所谓使臣的固执,根本不是最主要之点。政治优先地位和经济利益之间的巨大分歧,民族文化方面的缺乏相互理解,满人实行的闭关锁国政策,清朝当局对于向俄国偿还历史债务——即把阿穆尔河左岸和卡尔梅克人归还俄国的担心——所有这一切造就了一种态势,使俄国使团必遭失败。”[50]18笔者认为:“仅以文化碰撞还不能从根本上解释戈洛夫金使团被拒事件……此次使团的失败,从深层次讲,是随着准噶尔问题得到根本解决和边界逃人问题的困扰相对减弱, 清政府对俄国的国家利益诉求相对弱化所致。”[51]
关于此次出使的意义,陈开科认为,“通过这次外交事件,俄国基本形成了整个19 世纪的对华政策,并逐渐获得对华外交优势,而清朝则慢慢丧失了对俄外交的优势,为 19 世纪中叶丧权失地的外交悲剧埋下了伏笔。在这次外交事件中,俄国失败的只是一个使团,而中国失败的则是整个外交”[52]。叶柏川认为,戈洛夫金使团所担负的使命,是俄国远东战略的重要内容,也是19世纪下半叶俄国在对华关系中转为绝对强势后迫切攫取的利益,如果嘉庆皇帝没有遣返使团,并且答应其某些贸易要求以作为回报,清政府有可能在争议土地问题上与俄国签订新约,也许就不会致使俄国在半个世纪后从中国东北再掠走100余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至少这项新约会对俄国有所约束,然而在嘉庆皇帝的谕旨中,却从未提及划界问题[53]104-105。曹雯则认为清朝欲借戈洛夫金使团访华之机“理清中俄关系”,“将俄国导入朝贡国行列,然而由于俄国的强烈抵抗,清朝很快放弃了上述引导,却拒绝与俄国继续进行政治往来活动。这是清朝处理与互市国关系的定式:可以参与符合中国对外体制的经济活动,但无须政治往来”[54]。
关于清前期赴俄使节,张维华、孙西与王希隆都有所讨论。继民国学者陈复光之后,王希隆首次考察了托时、德新奉使俄国及相关问题[55]。阿拉腾奥其尔撰《清朝图理琛使团与<异域录>研究》一书,对图里琛使团出使土尔扈特始末做了“突破性补充”,作者汉译、考释和研究了不同文本《异域录》以及《康熙帝谕土尔扈特阿玉奇汗敕书》和《沙克都尔扎布致阿斯特拉罕军政官》的两封托忒文信函,并译介了《瑞典人施尼茨克尔关于1714-1716年清朝使团赴卡尔梅克阿玉奇汗处的报告》,充分体现了该学者的多语种研究能力。关于赴俄使臣及驻俄公使的个案研究,对崇厚、曾纪泽、李鸿章、杨儒的讨论比较丰富,对缪佑孙、王之春、刘瑞芳、洪钧等人的中俄交涉研究则相对较少。现有研究成果中,除了阿拉腾奥其尔的著作,皆未能充分利用俄文史料,不得不说是一个重要缺憾。
2.俄国驻北京传教团与中俄外交。除了俄国派遣来华的正式外交使节,在清朝心脏北京,还长期驻扎着一个俄国非正式外交机构——俄国驻北京传教团。1727年《恰克图条约》规定,俄国政府可定期派遣传教士和留学生来华,此后俄国传教团便合法进入北京,至清末共有18届传教团来华。在俄国正式派遣公使驻华之前,传教团俨然作为俄国驻华的非正式外交机构,集外交、宗教、文化、商务等功能为一体,“虽无使馆之名,而有使馆之实”[56],成为俄国政府对华外交的重要助力。“中俄两国间的公文传递、谈判交涉,都离不了传教团的参与。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成了俄国驻伊犁、塔城和天津的领事,直接参与对中国的瓜分。”[57]蔡鸿生指出,俄国东正教会在彼得一世后彻底沦为为国家服务的工具,传教团出身的俄国驻华总领事孔气,为保住俄商在通商各口之总口天津的地位,在处理教案时灵活采用了“缓决”策略。清后期,由于俄罗斯文馆的中国学生无法胜任俄文文书翻译,两国交涉文书皆由传教团学生承译。蔡鸿生考证发现第八届传教团随团学生“四贴班”遗稿中存有理藩院致枢密院咨文抄件,是其参与1805广州俄船事件的证据[58] 168-191。陈开科讨论了第13届传教团大司祭卡法罗夫接受俄外交部和东西伯利亚总督的指示,在《中俄瑷珲条约》和《中俄天津条约》的提前签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46]385-462。据他分析,耆英因和谈失败获罪后,其子竟往俄罗斯馆请求卡法罗夫施救。虽然“俄罗斯馆最终也没有真的以官方身份出面干涉耆英的生死”,但作者揣测“这恐怕正是外人干涉清廷内政在当时尚处于萌芽状态的表现”。他还提及“耆英与俄罗斯馆的关系源于俄罗斯馆在京城展开的民间外交攻势”[59]。肖玉秋对此也有深入讨论,谈及俄国政府1818年给传教团发布指令,“要求传教团成员以令人称赞的道德和行为博得清廷官员的尊重,伺机建立密切联系,同时继续结交在北京落脚已久的耶稣会士”[60]。
3.礼仪之争。礼仪之争曾是清朝对外交往的重要障碍,该问题同样出现于中俄交涉之中。尤其在清前期,俄国频繁遣使来华,礼仪问题成为双方争执的焦点之一。学界聚焦于礼仪之争的原因、内容、礼仪之争与国家利益的关系等问题。宿丰林认为:“专制主义的皇权至上思想在17世纪的中俄两国社会意识形态中都占支配地位,这种情况使得初交的中俄两国权力机关在处理相互关系时,采取了各不相让的态度。”[61]王开玺则认为:“清廷的上述天朝大国思想及某些礼仪要求,绳之当今外交惯例,的确是错谬当改的,但此为当时历史的局限及封建阶级本质所致,且并非清廷独然的历史现象。在这一方面,俄皇决不逊色于清帝。”[62]“但是,随着交往的深入,受到边界、逃人、准噶尔和贸易问题的诸多牵绊,国家利益成为两国最高代表首先考虑的因素”,“在其他西方国家无法解开礼仪之争的死结时,中俄两国实际上已经进入正常的国家关系发展时期”[53]143。而随着两国政治诉求的变化,双方对待礼仪的态度再次发生变化。1807年,戈洛夫金使团来华时,“在维护天朝礼仪方面,清政府的态度是固化的,不容商量”,“俄国政府的态度却是弹性的”,“只有在不影响国家利益的前提下,才需要坚持反对天朝礼制”[63]。
事实上,中俄礼仪之争主要发生在俄国使节来华期间,清朝使团赴俄时双方并未就礼仪问题发生大的争执。每当使节出使,清朝执政者对觐见俄皇的礼仪都要进行慎之又慎的考量。如雍正皇帝谕令托时(1729)、德新使团(1731),为避免礼仪问题,若俄国方面不提及觐见俄皇,中国使臣也不必提及;如需觐见,不得以叩拜皇帝之礼觐见,只能以王爷之礼行之,最终使臣对俄皇行了觐见王爷的叩拜礼[55]。到清后期,清政府不得不遣使出洋时,同样因礼节问题踌躇许久,最终,“当1866年斌椿最先率众出访时,只是立于门前,并未行礼。之后,清政府为了避及礼仪纠纷,干脆用了美国公使蒲安臣作为清政府的钦差大臣出访西方国家”[64]。
四、晚清时期中俄外交政策
晚清时期的对俄政策,尤其联俄政策,一直是学界讨论的热点。蔡鸿生首次提及,19世纪70年代后,沙皇政府以贿买政策施用于中国,华俄道胜银行理事、俄国驻华公使璞科第通过贿买白云观高道士,搭上慈禧身边的太监李莲英,从而建立起一条“李、高、璞”秘密勾结通往清宫的内线,可见清廷内部的联俄氛围早已有之[58]216。陈开科、潘晓伟等学者,将中俄关系置于东北亚国际舞台的大背景之中加以检视。陈开科认为:“皇太子东游与俄国外交战略‘双头鹰’关注远东的时机一致,再加上俄国‘东方派’的渲染,使尼古拉东游不可避免地成为俄国东方外交战略向远东倾斜的表征。”[65]他还讨论了甲午战争前后,李鸿章与俄国驻华代办拉德仁在天津五次会谈,达成口头“君子协定”,“从战略上建构和协调了彼此的朝鲜政策,对维持甲午战前东北亚局势的相对稳定起了一定作用”[66]。潘晓玮指出,19 世纪80年代,清朝在对朝鲜政策上经历了从“防俄”到“联俄”的转变,“防俄”作为清朝对朝政策的首要目标持续至 19 世纪 80 年代中期, 清朝切实感受到日本对中朝藩属关系的威胁,开始视日本为最大对手,对朝政策由 “防俄”转为“联俄”[67]。除东北亚视角,贾小叶从中德外交角度详细考证了胶州湾事件中清政府联俄政策的失败。德占胶州湾事件发生后,清政府将联俄视为解决“胶案”的重要筹码,然而俄国围绕“胶案”的决策却始终未曾顾及过中俄同盟[68]。
除了清朝对俄政策,有关俄国对华政策的考察使得中俄外交研究更加完整,但相关成果非常有限。徐万民从俄国政策的角度讨论了清政府在庚子中俄之战中的失误,指出“这场给东北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严重损害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中俄之战”是可以避免的。当时俄国政府并非只有一个选择,以财政大臣维特为首的一派,主张在中国东北实施铁道与经济征服政策,反对轻易诉诸武力。但是由于清政府贸然对列强宣战,东北三将军又缺乏统一的战略,导致局面最终失控,维特也从反对出兵东北转为与主战派同流合污[69]。维特是晚清时期与李鸿章、伊藤博文同样活跃于东亚国际舞台上的风云人物,也是《中俄密约》的始作俑者。张丽系统讨论了维特的远东外交政策、侵华策略,以及他在是否出兵东北和进军北京、是否吞并满洲和留兵护路等问题上,与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之间的争执与妥协,认为由于沙皇在维特和库罗巴特金之间摇摆不定,导致俄国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对华政策呈现出矛盾性与多变性[70]。
综上所述,近三十年来,关于中俄政治外交问题的研究,意识形态色彩明显淡化,论战性的话语减少,双方能够回到学术研究本身进行讨论,这得益于和平的时代环境和开放的学术氛围。现有研究在很多议题上有所拓展和深入,如对边界问题的讨论深入到界河、界点、界碑及清朝疆域观念问题的研究;对唐努乌梁海、19世纪初俄国远东战略等问题进行了拓荒性考察;对涉及中俄科塔谈判的多语种文书及《科塔界约》进行了细致考证;从不同角度讨论了晚清时期的联俄政策及俄国对华政策等。从史料方面来看,在边界研究中加强了对满文舆图及档案的利用,编译出版了《19世纪俄中关系》俄文档案集,《俄国与西藏》俄文档案以及俄国探险家的论著等。现阶段的研究成果从数量上看,与1970-80年代的研究高潮时期不可同日而语,但从质量上看,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尤其是考证性成果十分有限。主要原因在于:一是因国际形势变化,自1990年代起中俄关系史研究迅速变冷,研究人员大量流失;二是受到社会大环境影响,一些学者转向中俄贸易与文化关系史研究,政治外交史研究的绝对核心地位被打破;三是中俄划界问题解决后,对政治外交史研究的现实需求不再迫切。但是,中俄是拥有长约4300公里共同边界的大国,领土边界问题关乎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并且在未来很长时间内仍将是影响两国关系走向的潜在因素,因此以领土边界为核心的清代中俄政治外交史研究绝对具有持续下去的必要性。
笔者认为,未来的研究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史料上加强对多语种档案的利用。一是强化对满文档案和满文舆图的利用及互证研究。满文档案和满文舆图对于清代中俄边界研究意义重大。因为直至清末,边疆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往来文书,依然使用满文,并且很多文书并没有相应的汉文文本。满文舆图的情况也是如此,现今留存的满文舆图中包含了大量汉文舆图未曾涵盖的信息。二是加强俄文档案文献的利用。在俄罗斯的各大档案馆中,收藏着卷帙浩繁的清代中俄交涉档案。俄文档案对历次出使、中俄交涉都有详细记载,既包括使节报告,也包括相关人员的各类记述,与清朝官方档案种类单一、记述简略形成对比。此外,还存有大量俄国驻华领事、间谍的报告,以及传教团档案、探险家报告等。尽管老一辈学者历来重视中俄文档案的比较研究,但是以往研究所用俄文档案似乎仍是冰山一角,而近年来专心爬疏俄文档案的学者也越来越少。尤其应该注意的是,17世纪的古俄文档案和地图对研究清前期中俄边界问题十分重要,但是目前国内具备解读古俄文档案能力的年轻一辈学者可谓凤毛麟角。三是加强对边疆民族语言档案的利用。除了汉文、满文、俄文档案,也有一些边界地区民族语言档案留存,如何星亮发现的察合台文书。这些档案可能数量不多,但对具体历史问题的研究不可或缺。
其次,在研究内容上,应注重以下几方面:一是对清代中俄边界条约文本的考证研究及实地考察。中俄签订了大量边界条约,但目前只有个别条约文本得到详细解读,应对这些条约逐个进行考证研究,对界点、界牌进行实地考察。二是对中俄地方层面交涉的研究。地方层面交涉是国家层面构建的中俄条约体制的具体落实过程,更能反映中俄关系的细节,而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国家交涉层面。三是以东北亚国际关系为背景及以全球史视角考察晚清中俄关系。19世纪末东北亚地区成为多国激烈角逐的国际舞台,应考虑复杂多变的国际因素对中俄关系的影响。四是俄国驻华传教团和俄国探险家研究。这两类专题史料,是除中俄外交档案外的两类俄文档案宝藏,目前大量传教团手稿尚未充分利用,俄国探险家的个案研究也十分有限。五是晚清俄国对华政策的研究。晚清中俄外交,总体特征是俄攻清守,俄国服从于其全球争霸战略,不断调整对华政策,应考察其政策演变过程和内在逻辑。六是在研究中吸收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国际关系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有助于获得更深入、更丰富、更具体的历史认识,提高研究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