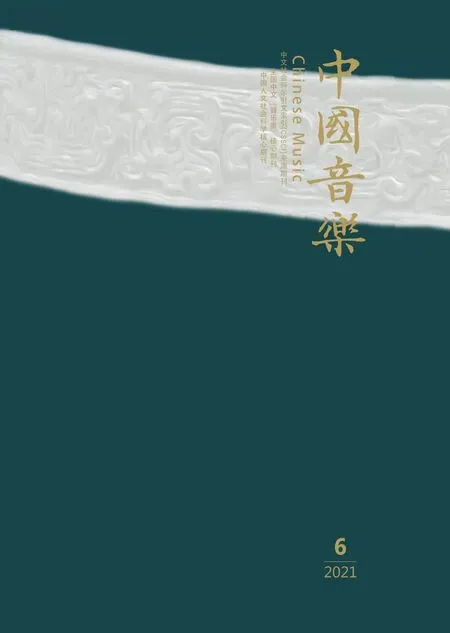话语分析
——不同研究视角下的陈其钢
○ 郭茹心
陈其钢,知名旅法华人作曲家,出生于中国知识分子家庭,生长于“文革”年代,恢复高考后求学于中央音乐学院,毕业后考取公费留学生,留法深造并开启其职业作曲家生涯。特殊的家庭环境、特定的时代背景与文化环境,加之陈其钢本人天性与个人经历,共同造就了陈其钢其人其乐。不同的学者与听众对其有不同的认识和印象,譬如中国第五代作曲家、北京奥运会音乐总监、中国音乐诗人等。作为已经形成个人风格并且仍旧在创作的作曲家,陈其钢是不可多得的研究样本。
近年来,以陈其钢为主题的学术性研究文论不断涌现并呈现出了以下三种特征:其一,大多属于作曲技术理论领域,以音高材料、音乐织体以及西方技术与中国元素的融合为切入;其二,以单个作品研究为主,并且主要集中在陈其钢最为人所知的《逝去的时光》《五行》《蝶恋花》三部作品上;其三,存在对陈其钢其人其乐进行多次解读的学者,譬如明言、景徐,涉及了陈其钢早期、中期创作的多部音乐作品。
与此同时,不同的研究者基于不同的研究身份会采取不同的研究视角对陈其钢其人其乐进行考量,在阐述音乐的同时,建构和体现陈其钢的社会身份和行为。譬如《蝶恋花》作为热门研究对象,因其描绘刻画了女人的九种情态,加之陈其钢本人的音乐风格较为阴柔,不少学者从社会性别和女性主义的角度出发对《蝶恋花》进行了研究。笔者认为,通过话语分析,我们可以窥探出不同研究者的审美取向、价值判断及其缘由。为什么研究者在研究作品的选取上更为青睐陈其钢归国前的创作而非陈其钢近年来的创作?为什么陈其钢作为男性作曲家,其音乐创作却被大多研究者形容为“阴性的声音”?陈其钢又为何被研究者定义为文人作曲家?……而当研究者以不同的研究视角观照陈其钢其人其乐时,陈其钢也在观照不同的研究视角。
本文中,笔者将主要针对作曲技术理论、音乐学这两种不同学科视域的研究及讨论进行话语分析,所涉及的文本除了目前公开可见的学术性文论,同时也包括笔者所收集到的田野资料,譬如笔者对不同学科不同研究者的采访,对作曲家本人在不同场合的录音整理以及往来邮件、聊天记录等等,主要涉及的作品均为陈其钢职业作曲生涯的代表作。
一、作曲技术理论视域下的陈其钢
时光回溯,1998年,融进了《梅花三弄》旋律的大提琴协奏曲《逝去的时光》于法国巴黎首演,在当时布列兹的音列主义和米哈伊的频谱乐派这两种主流风格的笼罩下,具有浪漫主义抒情风格的《逝去的时光》显然不被学院所看好,法国《世界报》批判道 “有旋律有调性”,似乎作为梅西安的学生,陈其钢的创作理应在先锋话语体系的范畴内:技术就是全部,旋律便是罪过。面对质疑,仅仅在一年之后,陈其钢在管弦乐组曲《五行》中调整了创作策略,将先锋性的作曲技术与抽象化的中国元素相结合,其精湛的配器与独特的结构大受好评,《五行》不仅给他带来了奖项和荣誉,更被作曲技术理论学界视为“配器教科书”。
2017年6月末,在躬耕书院短期生活写作期间,陈其钢向我和一位青年作曲家提问道,在他的音乐创作中更为喜欢哪一部作品。青年作曲家毫不犹豫地回答了《五行》,他认为作品中所蕴含的极致技术正是无数青年作曲家所追求的,而陈其钢却不置可否。笔者则从单纯的欣赏角度出发,更为偏爱展现了女人九种情态的《蝶恋花》。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初出茅庐的青年作曲家还是具有音乐学背景的我抑或是作曲家本人,都对首演“失败”的《逝去的时光》抱有不同程度的好感。在陈其钢看来,《五行》是一次不带观念的创作,仅仅描述意象而非表达情感,与之相比,《逝去的时光》与《蝶恋花》更能获得作曲家本人的情感认同。时至今日,随着人们对当代音乐创作的不断反思与反省,将东方线性思维与西方和声、功能思维相融合已不受诟病,而历经岁月沉淀与演奏试炼的《逝去的时光》也已成为国内外严肃音乐界公认的经典作品。
与此同时,有关陈其钢其人其乐,在作曲技术理论视域的研究中,主要是围绕《五行》《逝去的时光》等20世纪90年代的创作进行的探讨。20世纪以来,当代音乐创作最显著的特征便是没有完整的旋律,以音色、音强、发声方式为主要创作因素的先锋派作曲逐渐取代了以旋律、和声、调式为主要创作因素的传统作曲,音高不再是第一要义。而在作曲技术理论视域的研究中也以此为分野,针对陈其钢其人其乐,一类是以西方现代音乐技术与中国传统音乐元素的融合为切入,围绕《逝去的时光》等具有浪漫主义抒情风格的作品进行的研究;一类是以“音色—音响”为切入,围绕《五行》等具有先锋气质的作品进行的研究。当然此种分类并非绝对,仅是依据现有研究所呈现出的主要特征而言。
(一)以“音色—音响”为切入
所谓“音色—音响”音乐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形成的一种由色彩各异的单个音或单个音响构成的点、线、面、场的各种音响集结体在运动中所产生的明暗、浓淡、刚柔、强弱不等的音响流,并以这种纵横交汇音响流形成的音色频带网络,赋予结构逻辑作用于呈示、变化、对比、统一的音乐运动方式上。①张旭儒:《潘德列茨基早期音乐作品中的“音色—音响”观念及其创作技法研究》,2006年上海音乐学院博士学位论文,第6-7页。譬如利盖蒂对于音色亮度、频率密度的设计,梅西安、布列兹对于整体序列主义的探索,等等。而在陈其钢的创作中,就写作技术与音响形态而言,对“音色—音响”的追求贯穿始终,但研究者在研究作品的选取上往往会规避《二黄》《万年欢》等显性移植中国传统音乐元素的作品。在写作手法上,研究者普遍认为陈其钢受到了法国文化重视和声与音色的熏陶,同时也受到了利盖蒂、欣德米特等先锋作曲家的影响。他本人也曾言明具有繁复织体和空间配置的《源》与利盖蒂《大气》在“音色—音响”塑造上的渊源关系,提出:“虽然零散的写法说是像利盖蒂的,但是音响上和利盖蒂是一点关系也没有。因为利盖蒂的音响材料是音串,是音串一起往前进行。这里不是,而全是五声性的材料构成的,所以它有一个空间在里头,音和音之间有很大的空间。这个空间使得音响变得相对的透明或者特别透明”②连宪升:《陈其钢访谈录(四)》,《爱乐》,2002年,第9期,第85页。。而这种“音色—音响”的塑造方式也成为一种经验,流露在陈其钢之后的创作中。
在以“音色—音响”为切入的研究中,被视为“配器教科书”的管弦乐组曲《五行》是较为热门的研究对象。虽然整个组曲有一个较庞大的乐队规模,但他并没有挥霍音色,而是根据音乐表达的需要对每个乐章的乐器选用做了周密的设计,借助“五行”之“水、木、火、土、金”5种具体物质的外在特征,用音色作为一种指向性的暗示,使受众产生由此及彼的联想,从而领悟到音乐所要表达的特定意境和内蕴。③戴华丽:《音色—音响在管弦乐组曲〈五行〉中的结构力作用》,《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第41页。这种指向性的暗示主要是通过不同器乐组不同音色的呈现、消失与融合,点、线、面不同织体的对比与相交来完成的,譬如弦乐波浪线条与木管组短小持续音型在《水》中的相衬,梆子和木鱼在《木》中“噼里啪啦”的敲击,铜管音色在《土》的缺位以及在《火》中的充分展现,等等。与此同时,在《五行》中还可以探寻到梅西安色彩和声的痕迹,譬如《木》中的四度叠置和声,《金》中的全音阶材料,等等。
由于20世纪以来,以“音色—音响”为主导创作思维的作品往往建立在无调性或者瓦解调性的基础上,针对《五行》是否具有调性及旋律亦有所争论。陈其钢曾向我询问觉得他是一个怎样的作曲家,和他人相比具有什么不同之处,我当时回答道,“是个技艺高超的旋律派”(BBC乐评人斯蒂芬·沃尔也曾评价陈其钢的音乐为具有先锋意义的调性音乐),作曲家本人并不认同,并以《五行》为例进行反驳,提出《五行》没有旋律。无独有偶,当时在场的另一位青年作曲家表示在她的听觉范畴内,《五行》是具有旋律的,尤其在“水”的段落中出现了不少五声性的旋律短句。而在陈其钢看来,我们所谓的“旋律”不过是“动机”而已,具有五声性因素不等同于具有旋律。抛开作曲家自身的看法,学界对于《五行》的探讨虽然偏向于纵向挖掘,但对于其音高模式亦有所争论。一种观点认为:“五行全曲的音高模式是建立在无调性基础上的……调式因素只是局部地、孤立地运用了一次”④段伟伟:《陈其钢管弦乐组曲〈五行〉的音响结构》,《南通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第119页。。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五声调式和旋律是构成这部作品的主要素材之一……并置的五声音列虽引发出不协和音的出现,但陈其钢通过配器上音色融合的方式,避免了它们又包容了它们”⑤王尚:《陈其钢管弦乐组曲〈五行〉研究》,2010年中央音乐学院硕士学位论文,第2页。。笔者认为,在陈其钢以“音色—音响”为主要创作特征的作品中,虽然其构成方式主要是建立在西方现代作曲技法的基础上,但中国传统音乐所蕴含的五声性仍旧是音响材料的固有元素。
(二)以中国传统音乐元素的运用为切入
在以中国传统音乐元素的运用为切入的研究中,研究者较多考量作曲家的中国身份以及音乐创作中所显现的中国风格,同时考虑罗忠镕“十二音阶五声化”对于作曲家本人的影响,涉及的作品均是以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为蓝本或是以中国传统音乐音调为核心素材。其中,移植并发展了古琴曲《梅花三弄》旋律的《逝去的时光》是较为热门的研究对象。学者认为该作品旋律优美,富于情感,突破了以往偏向于噪音音群的现代音乐创作,并且标志着陈其钢的创作走向成熟。因此,作曲出身的研究者认为只要掌握了《逝去的时光》的作曲技法就摸透了陈其钢的典型创作风格。在研究框架上,各篇文论对于音高组织中乐音音群的分析都占有很大篇幅,譬如对于以纯五度为核心音程的“三弄”的完整引用以及片段引用、常规的五声性旋律以及加入变音的五声性旋律的形态分析等等。除此之外,学者普遍认为作品中“五声纵合性”⑥所谓五声纵合性和弦手法,是以五声调式中各种音程的纵合作为和弦结构基础的和声方法,它体现了五声调式的特性,属于五声调式类型的和声方法。参见桑桐:《五声纵合性和声结构的探索》,《音乐艺术》,1980年,第1期,第1页。的和声织体极为巧妙,确立了陈其钢鲜明且独到的音乐语汇。在笔者看来,如果说《五行》是一部“配器教科书”,那么《逝去的时光》一定是一部中国式的“和声教科书”,无论是四五度、二度叠置的运用还是常规三度叠置和弦的运用,都被赋予了“五声化”的色彩。研究者对于作品整体也给予很高评价:独奏大提琴的演奏除了具备《梅花三弄》旋律本身的风格特征,还通过倚音、拨奏等奏法模仿了古琴的音韵,并使这种“古琴式”的素材和音色与流动的音型化织体交替出现,时而浮于乐队音响之上,时而融于乐队音响之中……用交响化的作曲技法表达了中国式的音乐思维。⑦张艺馨:《陈其钢大提琴协奏曲〈逝去的时光〉作曲技法初探》,2019年上海音乐学院硕士学位论文,第24页。可见研究者虽然对于《逝去的时光》的探讨主要聚焦于中国传统音乐元素的运用,但并不否认西方“音色—音响”思维在乐曲中所起到的结构力作用。
此外,还有部分研究谈及了陈其钢的人声写作技术,主要涉及的作品有《水调歌头》《蝶恋花》等。20世纪以来,随着作曲家不断挖掘和探索新音色,出现了无调性、多声部、高难度的“新人声主义”,譬如勋伯格的《月迷彼埃罗》、贝里奥的《模进Ⅲ》等,前者运用了“说唱”的发声方式,后者则精心设计了“歇斯底里的笑声”等44种具有表情的音声。而在陈其钢的创作中,其人声的运用主要是从中国传统文化精粹中汲取营养,因此,研究者对于其人声写作技术的探讨除了关注乐曲中人声与器乐的融合与对比,亦关注人声音色中所蕴含的戏曲元素,譬如无具体音高的“吐字”、讲究“头腹尾”的归韵、“字少腔多”的行腔等等。中国传统音乐是活的艺术,这种即兴性与偶然性亦体现在陈其钢的人声写作中,譬如在谱面上仅标注念白声调而非音高,与具有规则的乐队背景相衬,产生了微妙的微分音效果。可以说,在人声写作中,陈其钢对于传统的运用获得了现代化的音响。
无论是以中国传统音乐元素的运用为切入,还是以“音色—音响”为切入,都只不过是研究手法而已,两者在陈其钢的成熟作品中皆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创作因素。因此,这两种研究视角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通过这两种不同研究视角的对比与交汇,我们可以发现陈其钢的创作融合了东方线性审美、西方功能和声既有经验以及法国先锋派的技术追求,正如他所言:“音和音之间是小二度、大二度,还是增四度,对他(利盖蒂)来说都不重要。可是对我来说是重要的,这个横向线条必须不是这些东西,必须基本是由五声音阶构成的线条,然后所有这些由五声音阶构成的木管线条和打击乐线条在一起的时候,它有一种漂亮的结果出来”⑧同注②。。
(三)归纳与引申
除却大量针对陈其钢归国前的创作所进行的探讨,也有少量针对近年来作品的探讨,后者由于几乎未在研究作品上形成重复,并不存在相互间的争论,同时就选题而言,更为看重作品的独特性,譬如与大提琴协奏曲《逝去的时光》创作手法相类似的小提琴协奏曲《悲喜同源》相比,打破刻板印象的乐队变奏曲《乱弹》更值得被研究。
综上所述,研究者大致将陈其钢的创作特点归纳为:1.具有五声性因素;2.以四五度的音程关系为核心发展材料;3.追求技术,重视和声与音色,并将此作为结构发展与结构布局的重要因素;4.擅长将东方器乐与西方器乐思维相糅合,譬如将独奏性的东方器乐作为乐队组织的一部分、用西方器乐演奏具有中国风格的旋律线条等。
在笔者所收集到的采访中,关于研究现状,有局内人谈道:“因为陈其钢的作品光从技术和音乐本体来说的话,实际上可说的东西并不多,他的大致音乐风格和语言在90年代中叶成型之后并没有很大的变动……他的作品我是真的挺喜欢,但光从我们专业的角度来说的话,真的不是很适合做学位论文”⑨采访时间:2018年11月1日,采访方式:微信文字聊天,采访人:笔者本人。。从中可以提取到的信息有:1.陈其钢的创作风格较为单一,20年来没有太大的变化;2.如果从学习的角度出发,研究陈其钢风格成型期的作品就已足矣,因为之后的技术都是重复;3.哪怕陈其钢曾经写作过不少前卫的作品,但就近年来的创作轨迹而言,他更适合被称为传统作曲家。这也从侧面解答了为何研究者更为青睐陈其钢归国前的创作。值得疑问的是,研究者所“期待”的变化很可能是理查德·施特劳斯从《莎乐美》到《玫瑰骑士》的变化,至于单一性,又有多少人说布鲁克纳把一部交响曲写了九遍呢?
在笔者看来,作曲家期待优秀演绎者能够对作品进行完美呈现的同时,也期待着研究者能够对作品进行方方面面的解读,他们尤其关注本领域研究者的观点,不仅是因为局内人的看法更能够观照自身的创作,也是因为很多音乐学背景出身的学者往往在作品技术层面上就会产生误读,从而导致作曲家无法对其整体研究产生认同。作为仍旧活跃于当代乐坛的作曲家,与围绕《逝去的时光》《五行》等经典作品的研究相比,陈其钢更希望看到围绕《乱弹》《江城子》等近作的研究,因为后者更能及时地帮助他照镜子。在与笔者的聊天过程中,谈及当前作曲技术理论领域的选题与研究偏好时,陈其钢说道:“一首作品的音乐与技术是密不可分的。一首经典作品无论表面简单复杂,只要是经典就有很多值得研究,甚至永远神秘莫测、不可言说的因素。比如说《春之祭》,杰作,技术有的可说,但并非技术说清楚了就能理解和成就《春之祭》。同理,《鹅妈妈》很简单,但你不容易说出它之所以神奇的地方,因为它没有给那些除了技术就不会分析的人展示自己的窗口。说到我,《江城子》《乱弹》,或者最近的新作品与90年代的自己,以及自己90年代前的作品变化有些是极大的,如果不了解,那就要多了解”⑩采访时间:2018年11月2日,采访方式:微信文字聊天,采访人:笔者本人。。一方面,针对作曲学界已有的研究,陈其钢并不满足于仅仅停留于纯粹技术层面的分析;另一方面,由于学界公认其创作风格早已定性因而鲜少研究近年来的创作,面对这一现状,他表示自己的作品并非是一成不变的,甚至在他自身看来,有着极大的变化。
二、音乐学视域下的陈其钢
与作曲技术理论视域的研究主要关注陈其钢的创作特征相比,音乐学视域的研究者更多地将陈其钢视为具有典型意义的中国当代作曲家,并将其放置到中国当代音乐社会中进行考量,对陈其钢其人其乐的探讨不再局限于音乐本体,并且常常在一篇文论中涉及多个作品,而非执着于单一作品的技术解析。在此种观照下,研究者普遍认为:1.陈其钢的音乐创作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2.陈其钢是中国当代乐坛中为数不多的文人作曲家(同样被称为文人作曲家的还有周文中、梁雷);3.陈其钢的音乐语言偏向于浪漫主义,细腻、温柔、抒情;4.陈其钢其人其乐具有一定的悲剧性;5.作为第五代作曲家,得益于当时的小环境、大环境,可谓是“时势造英雄”,同时与其他第五代作曲家相比,陈其钢大器晚成,在出国之后才逐渐成为一流作曲家。
(一)围绕“文人作曲家”展开的讨论
在这一小节,笔者并不对“文人作曲家”的边界与定义进行考究,而是将重点放在陈其钢本人身上,即对他为何被称为“文人作曲家”进行探究。
而在研究作品的选取上,与作曲技术理论视域的偏爱相同,对《逝去的时光》与《五行》的探讨较多,其次是《蝶恋花》。抛开作品技术层面的探讨,在音乐观念的阐发上,研究者大多会与“人文精神”和“文人意气”联系到一起。譬如明言认为,在《逝去的时光》的创作中,陈其钢将“梅花三弄”这个典型的中国古代文人音乐材料作为作品的核心精神旨归,并赋予时代性的新型人文精神内涵。⑪明言:《追寻人生的“本真”状态——大提琴与管弦乐队〈逝去的时光〉听觉读解》,《人民音乐》,2006年,第3期,第14页。张斌认为,“《五行》虽然没有直接引用中国五声性旋律,却在意境上铺陈浓郁的中国文化意蕴,是吐露中国古典哲学以及古代文人意气的作品”⑫张斌:《社会性别视阈下陈其钢的两部管弦乐作品〈五行〉〈蝶恋花〉的比较分析》,2012年中央音乐学院硕士学位论文,第VIII页。。笔者认为,古琴音乐是具有强烈主体意识的音乐,而阴阳五行则反映了中国古典哲学的哲理运思,因此陈其钢在作品题材的选取上很难让人不与文人相联想。而陈其钢对于音乐学学者所赞许的“人文精神”和“文人意气”往往不自知,他更为强调创作中的独立精神,在他看来,人文精神往往是在总结一个时代、一种风尚、一段历史的时候得出的某一类结论,而创作者本人在写作的时候是不需要、也不应该去考虑的问题。创作的最大屏障是自由、独立、诚实的灵魂表述,而不是什么人文或非人文精神。⑬邮件写作时间:2016年6月4日,邮件写作人:陈其钢,邮件接收人:笔者本人。
金湘曾在《陈其钢其人其乐纵横谈》⑭金湘:《〈蝶恋花〉开香飘中外铿锵〈五行〉声透古今——陈其钢其人其乐纵横谈》,《人民音乐》,2003年,第1期,第6-11页。中指出家庭熏陶造就了陈其钢独立的人格,并且在灵魂深处与中国传统文化所相连。毋庸置疑,书画家父亲陈叔亮与钢琴家母亲肖远为陈其钢提供了良好的艺术氛围与文化环境。陈其钢对于传统文化的认知以及文学上的爱好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父亲,陈滨滨(陈其钢姐姐)曾对陈其钢回忆道:我现在越想越觉得父亲这个人并不单纯是个“画家”,他身上其实是潜藏了很丰富的音乐潜质的。从家乡的地方戏曲,到后来的昆曲,再到后来的中国音乐,再到后来的京剧……你我的学习音乐完全是自然而然的事了,家里并不光是母亲,从父亲那里就是存在很强的音乐基因的。(当然父亲那里还有文学基因,具备了诗人特征。)⑮信息写作时间:2019年6月14日,信息写作人:陈滨滨,信息接收人:陈其钢。从中我们似乎可以追溯到陈其钢音乐中所流露的画面感、戏曲元素与诗性。
在笔者看来,研究者之所以将陈其钢定义为“文人作曲家”是因为:1.在作品题材的选取上与中国古代的“文人音乐”息息相关,譬如运用了古琴曲核心音调的《逝去的时光》《悲喜同源》,取材自苏轼词作的《水调歌头》《江城子》;2.作品在音高组织上具有明显的五声性,并在音响呈现上有着文人般的儒雅和诗人般的细腻;3.家庭环境的优越性一方面给予了陈其钢浓厚的人文素养,另一方面造就了其“高高在上”的性格;4.在音乐创作观念上,具有创作者的主体意识,强调“自我”。综上所述,陈其钢方方面面、由内而外都满足了大众对于“文人”的期待。
(二)围绕“社会性别及女性主义视角”展开的讨论
2018年12月26日,大提琴演奏家王健在与SSO合作的专场音乐会中选取了《逝去的时光》作为主打曲目,其演奏细腻与深刻并重,有作品分析研究方向的听众反馈道:“之前跟师姐聊的时候,她曾脱口而出陈其钢的东西很女性,我下意识是很反感这种性别的标签……听完这首(指《逝去的时光》),不光是昨天,也包括之前的录音(指马友友版),真的很想问陈其钢是水做的吗?”⑯采访时间:2018年12月28日,采访方式:微信文字聊天,采访人:笔者本人。常言道“女人似水”,而作为男性作曲家的陈其钢却获得了“水”的印象,这和他音乐语言中所展现的性别气质不无关联。从反馈中我们可以得知,哪怕是对性别标签持有保留态度的学者,也无法否认陈其钢音乐语言中如水般的细腻与柔软,与此同时,这份细腻与柔软并不是通过演绎者的二度创作所获得的,而是源于作品本身。佟新曾在《社会性别研究导论》中指出,女性气质总是与多愁善感、温柔等相关联。在笔者看来,部分学者觉得陈其钢的东西很“女性”,并不仅仅是因为他写作了《蝶恋花》,还因为他的大多作品在音响呈现上都具有“阴性的声音”。明言曾这样评价道:“陈其钢就具备男性的体魄和女性的细腻、敏感。可以说,作为艺术家的陈其钢本身,就是男女性别的复合体”⑰明言:《人生历程的感慨与关怀——陈其钢〈蝶恋花〉听觉解读》,《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第116页。。
因此,在目前可见的与陈其钢其人其乐相关的研究中,不乏以社会性别或女性主义视角为切入的探讨。哪怕是在作曲技术理论视域的研究中,亦有研究者指出陈其钢的创作具有“女性意识”,是中国当代严肃音乐作品中所少有的。而作为作曲家本人,陈其钢对于研究者就其音乐中的社会性别或女性主义的探讨一直持规避态度。似乎作为男性作曲家,他可以接受多愁善感的评价,却无法认同被冠以女性气质并和肖邦一起被类比。较为有趣的是,在《如戏人生》中国首演的讲解中,陈其钢谈到了“阴”与“阳”,他认为:“我们如果说有阴阳的话,(音乐的)第一部分就是阴,第二部分就是阳。第一部分是非常阴柔的,有内涵的、有感情的,粘着在一起的一种感受。第二部分是跳跃的、幽默的、激越的,最后是非常激情的。然后到最后一个小的结尾,是把阴阳这两部分,把它结合起来。”⑱讲解地点:国家大剧院,讲解时间:2019年10月25日,主讲人:陈其钢,整理人:笔者本人。在笔者看来,陈其钢所描述的“阴柔、有内涵、有感情”,恰恰是我们对陈其钢其人其乐的基本印象。在实际演奏过程中,我们所能感受到的仍旧是阴性的声音,甚至在同场演奏的贝多芬《第三交响曲“英雄”》的相衬下,显得更为“阴性”。音乐会后,我对他的讲解表示质疑,他回应道,“阴”与“阳”的对比只是为了普通听众更好地理解、辨别音乐,其实音乐在整体上仍然是阴性的。
作为表现了女人九种情态的《蝶恋花》,毋庸置疑是社会性别及女性主义研究视角的热门作品,研究者大多赞扬了作曲家高超、敏锐的音乐技法,但对于该作品所显现的性别观念褒贬不一。有的研究者认为,《蝶恋花》“介于理性与感性二者间的‘知性’创作状态,既使作曲家居于她者的文化代表,又将作品中的女性书写上升为社会建构的主体性别代表”⑲宋戚:《音乐中的性别建构——评陈其钢〈蝶恋花〉》,《人民音乐》,2016年,第7期,第17页。。有的研究者认为,《蝶恋花》“最基本的出发点即让女性处于被观看的位置,甚至还要揭开想象中的面纱,让男性观看者对其一览无余”⑳何弦:《被凝视的花朵——陈其钢〈蝶恋花〉中的女性性别刻板印象修辞》,《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第123页。。两种观点的聚焦所在,即女性是否在音乐作品中占据主体地位,在笔者看来,既然是“男人眼中的女人”,陈其钢的写作也并非似纳兰性德般模仿女子口吻写作,那么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必然不具备主体性。至于作品是还原了女人的本真,还是再现了男性针对女性的性别偏见,应完全由听众自行判断。
或许是出于对陈其钢多重文化背景的考量,学界对于《蝶恋花》中所展现的女人究竟是法国女人还是中国女人亦有所争论。王西麟认为《蝶恋花》中的女人不具备中国女人的特性,明言认为《蝶恋花》展现了中国女性的悲剧性人生历程,朱玫玫认为京剧青衣所塑造的是温柔似水的女性形象,西洋女高音所塑造的是神经质的女性形象,而作曲家本人认为,《蝶恋花》建构了自身想象中的女人。有青年作曲家表示,“他的音乐带有深深的良好教养和锦衣玉食以及浓厚的文人气息,也具有法国的那种情调,那种非常精细的感觉,但是实际上底蕴还是中国女性的那种感觉,含羞待放的那种”㉑采访时间:2019年2月16日,采访方式:微信语音聊天,采访人:笔者本人。。在她看来,虽然陈其钢的音乐兼具法国人的情调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但终归是中国传统文化占据上风,因此所能感知到的女性是中国女性。笔者认为,《蝶恋花》中的女人没有国籍,也没有中西界限,这就好比陈其钢的音乐创作本就是将东西方音乐思维的意志相融合,两者兼具。
除了探讨以女性为音乐表现对象的《蝶恋花》,亦有研究者独辟蹊径以社会性别视角观照了《五行》,并与《蝶恋花》相比较。张斌认为,“两部作品在主题蕴含上具有性别气质的差异,《五行》是从男性的视角去看理性,而《蝶恋花》中的女性形象虽出自一位男性作曲家之手,但作曲家试图把自己融为女性的一部分,叙写女性的生命体验。”㉒同注⑫,第111页。在笔者看来,《五行》所展现的更多的是作曲家对于作曲技法的探索,而《蝶恋花》则建构了作曲家心目中的女性形象,一个理性为主,一个受感性驱使。如果说理性代表男性,感性代表女性,那“《五行》具有男性气质、《蝶恋花》具有女性气质”的阐释未尝不可。但如果是从音响实体的角度出发,正如陈其钢评价自己创作的《如戏人生》整体上仍然是“阴”的一样,作为以抒情、细腻为标志的作曲家,哪怕它展现了陈其钢的“阳”,和其他以气势、力量见长的作曲家作品相比,也还是“阴”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部分学者觉得陈其钢的音乐很“女性”主要原因有三:1.陈其钢的代表作《蝶恋花》的表现对象是女性,并因此获得了比女性更了解女性的评价;2.陈其钢典型创作风格中所蕴含的抒情、细腻、精致、多愁善感、温柔等等,符合所谓的“女性气质”修辞;3.哪怕是在非典型的创作中,和其他时代包括同时代的作曲家相比(譬如谭盾、郭文景),仍旧是偏阴性的。
(三)围绕“历史责任感”展开的讨论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音乐学本领域研究者的研究,亦有不少作曲家对陈其钢其人其乐进行了音乐学意义的观照,譬如王西麟先生对于第五代作曲家的音乐批评,他认为他们普遍缺乏历史责任感。这种历史责任感包含了多重因素,譬如题材上民族危亡的使命感,风格上中国作曲家的独特性。王西麟指出第五代作曲家们的作品正是带着“文革”尾声的人文背景而走向国际,并正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下才形成一个文化群势的,外国作曲家写或不写抗战题材都可以,而一个中国作曲家就无法避开民族危亡的使命感。㉓王西麟:《由〈夜宴〉〈狂人日记〉到对“第五代”作曲家的反思》,《人民音乐》,2004年,第1期,第12页。与此同时,针对陈其钢《蝶恋花》的创作,王西麟认为中国作曲家所书写的女人应当是在特殊的历史人文背景下具有特殊性格的中国女人,而陈其钢在《蝶恋花》中所书写的女人却是任何一个外国作曲家都可以书写的。王西麟一来提出第五代作曲家在创作题材的选取上应具有民族危亡的使命感(包括陈其钢),二来指出陈其钢的创作虽走出了先锋话语体系,却仍不具备中国作曲家的独特性。针对王西麟对于第五代作曲家的音乐批评,郭文景在《谈几点艺术常识,析两种批评手法》㉔郭文景:《谈几点艺术常识,析两种批评首发》,《人民音乐》,2004年,第4期,第13-18页。中提出作曲家应当有选择写什么的权利,不应为树碑立传而创作,并认为不是谁“都可以做到”像陈其钢那样写《蝶恋花》,强调了作曲家的主体意识,肯定了陈其钢音乐创作的独特性。他们一位是作为第三代作曲家以历史过来人的身份对第五代作曲家的创作提出质疑和期许,另一位则作为第五代作曲家的一员对“第五代”的创作感同身受并表示认可。而王西麟对于陈其钢的《蝶恋花》是“音乐中的《金瓶梅》”的评价,也成为学界评价陈其钢其人其乐“风花雪月”的开端。陈其钢曾向笔者回应关于部分学者评价其人其乐“风花雪月”的看法,他不仅否定了这一形容与称谓,并自认为他的音乐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忧国忧民”。
笔者认为,受时代文化背景影响,对于中国第三代作曲家而言,创作中自然而然会流露出民族危亡的使命感。而对于之后的第五代、第六代以至第七代作曲家而言,在不同的时代文化背景下,自然会有不同的感触。甚至对于我们这一代自小受西方音乐文化影响并在相对平稳的社会环境成长起来的作曲家而言,创作中不仅难有民族危亡的使命感,更难有中国传统音乐的痕迹。那么中国作曲家就必须创作中国题材中国风格的作品吗?2018年,茱莉亚年度聚焦音乐节以中国当代音乐为主题,演奏了从90多岁高龄的周文中到90后王姝慈等不同时代不同生活背景的中国作曲家的作品,其中,第五代作曲家的作品占有很大篇幅,试图反思与回应是什么使中国音乐具有中国特色?创始人兼组织人萨克斯评价道:“总之,与其他地方一样,民族风格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在我看来,这个事实非常有启迪意义。它表明,至少在高水平的中国作曲家中,人们几乎可以找到任何东西,以及任何程度的‘中国特色’,包括没有。”㉕Jacob Dreyer.China Today: A Festival of Chinese Composition-article on the Focus! Festival.The New York Times,Jan.12.2018.似乎居于国际视角,中国作曲家是否具有中国特色并不是判断音乐水平的必要因素。
在陈其钢看来,优秀的作品应当在人类精神的角度建立自我,而非狭隘的历史民族主义。他曾在公开讲座中将歌颂祖国的《芬兰颂》与描绘女人的《蝶恋花》相比较,提出:“《芬兰颂》,很狭隘啊,好像很伟大,实际上不一样,但这纯粹是我的个人观点……说到《蝶恋花》,虽然所有的事是女人的事,但是这是人的事啊!这是人类的一种情感,一种精神。比如我们说到政治了,说到历史了,这就是一种社会责任感,不一定要有,这也是个人观点。”㉖讲座题目:《问题与思考》,讲座地点:浙江音乐学院图书馆,讲座时间:2017年11月22日,主讲人:陈其钢,整理人:笔者本人。这也从侧面回应了陈其钢觉得自身音乐“忧国忧民”的缘由。在笔者看来,陈其钢与王西麟的不同,不仅仅是个人的不同,也是在不同小环境、大环境下第三代与第五代群体的不同。
(四)围绕“创新”展开的讨论
虽然目前书面可见的文论大多对陈其钢其人其乐报以赞许的态度,但在私下以及微信世界并非如此,比较常见的批判是“陈其钢的音乐风格单一,经不起反复推敲”,“陈其钢的作品并没有随着他年龄的增长而成长”,“陈其钢在创作手法上满足于现状不创新”。陈其钢本人也曾经在公开场合自嘲:“我听工作坊的同学跟我讲,‘有人说陈其钢退步了’,为什么退步?‘他写《蝶恋花》,写《逝去的时光》,他没有超过《五行》,写的东西一个比一个差。’这真是我要问我自己的问题,因为我始终在想,始终在寻找,我不满足,然后我想有突破,有更新,这很不容易。”㉗讲座题目:《问题与思考》,讲座地点:浙江音乐学院图书馆,讲座时间:2017年11月22日,主讲人:陈其钢,整理人:笔者本人。可见作曲家本人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大众的批判,从他近年来的创作也可以看到一些改变,譬如乐队变奏曲《乱弹》。
2018年,陈其钢为2017年北京国际音乐节所创作的小提琴协奏曲《悲喜同源》被选为第二届艾萨克·斯特恩小提琴大赛的必选曲,决赛中六位不同国籍、不同学习背景的小提琴家进行了多个版本的演奏,吸引了无数在沪的音乐界人士观看。赛后有西方音乐史研究方向的学者指出:“头回听《悲喜同源》,称之为《逝去的时光》升级版也不过分。几乎涵盖了陈所有的典型技术风格和效果。真诚也还是在的,但六十岁就几乎完全放弃了冲破艺术天花板的可能性,对于陈这个位置的作曲家来说是很遗憾的。不过话说回来,当年同陈一代的作曲家,又有哪个‘活’到了六十呢?”㉘采访时间:2018年9月2日,采访方式:微信朋友圈互动,采访人:笔者本人。该评论虽言辞犀利,却不乏参考性,一方面肯定了陈其钢音乐创作中基本技术风格和真诚,另一方面对陈其钢等第五代在国际乐坛上具有一定地位的作曲家固步自封表示失望。但若换一种角度,典型的技术风格和效果是否也可以看成个人风格的鲜明和统一?而针对与《悲喜同源》同期创作的,取消首演并完全重写的《如戏人生》,有学者认为,“《如戏人生》抒情优美,情深意长,充满18岁美少男的飘逸……骨子里的少年战胜了(他)……没有思考,与他的年龄不匹配”㉙采访时间:2019年3月10日,采访方式:微信文字聊天,采访人:笔者本人。。
同样都是批判,不同于作曲技术理论学者的批判执着于作品中的技术“没有变化”,音乐学学者的批判聚焦于创作作品的作曲家还“活在过去”。研究者对于“好”的音乐的追求,不仅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也是作品与时代的相偕,更是音乐中所显现的作曲家对于过去的总结以及未来的展望。
结 语
反刍前文中研究者的考量,不难发现各研究视角下所集中反映的陈其钢的音乐创作特征与创作观念以及其争议所在,现总结归纳如下。
就作曲技术理论视域而言,讲究实用主义,偏好于总结归纳作曲家的主要创作手法,通过对陈其钢音乐作品技术形态的分析,主要阐释中国传统音乐元素与音色—音响在其音乐创作中的建构并认为两者是其音乐创作中的重要因素,同时由于陈其钢语汇成熟风格显现后缺乏变化,对其近年来的音乐创作鲜少有较为深入的关注。
就音乐学视域而言,更多地将音乐本体与其音乐创作观念、审美取向联系到一起。譬如陈其钢在作品题材、素材的选取上偏好词乐与琴乐,在创作中强调独立人格和独立精神,加之其作品音响呈现与作曲家本人给予他人的性格印象,符合音乐学学者对于文人作曲家的想象。此外,除了其代表作之一《蝶恋花》描绘女性形象,其大多作品都极具“阴性气质”,透露出抒情、细腻、精致、多愁善感等,极易使女性听众产生共鸣,研究者难以不与社会性别及女性主义视角联系起来。与此同时,由于其音乐题材以及音乐风格的呈现,容易被诟病缺乏历史责任感(针对第五代作曲家)、风花雪月(针对陈其钢本人)。而章节末提到的“创新”问题与作曲技术理论视域提到的缺乏变化的问题具有一定程度的同一性。
究其症结所在,对于陈其钢而言,风格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他被视为极具个人风格的作曲家并因此获得了各种标签,譬如中国音乐诗人(中国式的诗情与法国式的浪漫)、文人作曲家等;另一方面,针对其批判主要集中于“风格单一,缺乏变化”。笔者认为,曾经造就了陈其钢巨大成功的音乐理念与创作模式,同样也会深深根植于他的创作生涯中。正如前文所述,观其近年来的创作,陈其钢虽意识到要在创作风格上要有所突破,但在其一反典型音乐创作风格的《乱弹》之后,《悲喜同源》回归了旧有的创作模式,而与《逝去的时光》的相似性在极具陈其钢个人风格的同时,亦被认为音乐并没有随作曲家的年龄一同生长。就此引申开来,当作曲家还未形成成熟的创作风格时,作曲家需要几部作品,建立自己的创作风格,而在此之后,人们期待能有所不同,不再满足于之前的创作风格。联系陈其钢的音乐创作,笔者不禁疑问,对于已经形成个人风格的作曲家来说,风格上的突破或风格转型是否为必要呢?
综上所述,作为仍旧活跃于当代音乐创作的作曲家,不同身份不同视角的研究者对于陈其钢其人其乐会有不同的,甚至是动态的考量,但不可否认的是,他是一位成功的作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