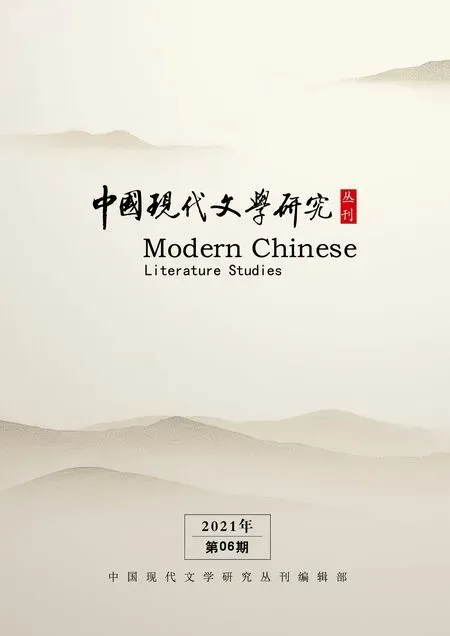“民族-人民”诗人的生成※——马克思主义视野与抗战时期郭沫若的屈原研究
唐文娟
内容提要:郭沫若抗战时期的屈原研究,是“民族-人民”诗人屈原生成过程的重要节点。首先,在民族主义催生的“屈原热”中,正是经过郭沫若的推动,“民族诗人”屈原的形象才得以确立。其次,如将郭沫若的屈原研究置于国统区的思想语境中加以考察,则郭沫若将屈原纳入“革命儒家”的脉络,虽然引发了左翼史学界内部的纷争,但也为“人民”屈原的生成奠定了基础。最后,抗战末期,随着“人民”话语的兴起,郭沫若“以人民为本位”的史观正式出场,屈原又被赋予“人民诗人”的称谓,其兼具民族性与人民性的双重内涵,既是中国革命独特性的写照,也包含了对革命中知识分子问题的另类思考。
20世纪是民族革命的世纪,也是人民革命的世纪。在世界范围内,民族革命与人民革命往往表现为相互矛盾、彼此牵制乃至对立的状态。与之相比,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划分为不同的政治区域,情况变得更为复杂。在中共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民族革命和人民革命达到了高度统一,民族解放的过程亦是人民解放的过程。然而,在国统区,随着民族矛盾的加深,民族革命的优先性被不断强调,人民革命的实践、理论与表述一度遭到抑制、排斥,如何在民族革命话语霸权中开辟人民革命理论言说与实践的空间,重构二者的一致性,成为了左翼文化人面临的迫切问题。事实上,作为左翼文化巨擘,郭沫若抗战时期的历史人物研究和历史剧创作,大多隐含着两种话语的变奏,尤其围绕屈原展开的长达十余年的研究、创作,更透露出对这一问题回应与探索的努力。
在民族危亡背景中,郭沫若起初主要着力于民族诗人屈原形象的塑造,而1942年在与左翼史学家侯外庐的论争中,郭沫若又将屈原和“革命儒家”相勾连,赋予其人民性的内涵,两者的结合最终确立了“民族-人民”1诗人的屈原形象。可以说,屈原形象的变迁过程,既包含了郭沫若对民族革命与人民革命话语统一性的持续思考,又包含了对革命中传统知识分子角色和定位的另类探索。就此而言,以往着眼于内在思想发展脉络对郭沫若屈原研究的讨论,还远未将其意义完全揭示出来。2鉴于此,本文试图在抗战时代语境和情感结构的变迁中,以及与同时代学人的对话、碰撞中,辨析郭沫若马克思主义屈原研究的独特性,揭示郭沫若如何推动民族诗人屈原的生成、传播,又如何生产出人民诗人的表述,最终促成“民族-人民”诗人屈原的诞生。这将会加深对郭沫若历史书写现实性、革命性的理解,同时深化对抗战时期国统区左翼知识分子革命话语实践复杂性、曲折性的认识。
一 抗战时期的“屈原热”与民族诗人屈原的诞生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陪都重庆出现了一个颇为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学者研究屈原身世,诗人吟诵屈原气节,作家撰写屈原故事,画家描摹屈原像,剧院上演屈原戏,文化讲座宣讲屈原,民众运动会纪念屈原,外交场合谈论屈原,传统民俗意义上的端午节已不足以盛载屈原的意义,一个崭新的节日——“诗人节”被发明出来。在这场由文化界发起、政治界助力的“屈原热”中,赋《离骚》、发《天问》、“自沉汨罗”的三闾大夫屈原,以一种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诗人形象,现身于抗战时期的历史舞台。
若追溯起来,早在20世纪初,屈原就已进入“梁启超、革命派等具有现代国家观念的新思想精英”的视野,汉代以来王逸、洪兴祖、朱熹、王夫之等推崇的“忠君爱国”屈原,开始被现代意义上的“爱国”的“文学家”所替代。3然而,在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的思潮中,胡适首先指出“忠臣”屈原是汉儒堆成的“伦理的箭垛”4,进而对“忠臣”化的屈原进行了彻底的解构,其“去政治化”的倾向使屈原不仅与“忠君”而且与“爱国”完全脱钩。受胡适在知识界如日中天的影响5,1926年游国恩就将“屈原借事神以讽谏,以寄其忠君爱国之思”看作需要扫除干净的“乌烟瘴气的谬说”。6直到1935年,闻一多仍认为,“帝王专制时代的忠的观念,决不是战国时屈原所能有的”,“说屈原是为忧国而自杀的,说他的死是尸谏,不简直是梦呓吗?”7可见,五四以后,屈原被剥离了忠臣、爱国者、政治家等身份,学界对屈原的共识主要是现代文学意义上的“诗人”。
然而,随着“九一八”事变爆发,民族危机加重,研究界对屈原的形象及作品的理解开始发生变化。曾将屈原忠君爱国之说斥为“迂腐的义理”的游国恩,目睹日本侵略行径,冀望世人受屈子之文感发,共赴国难。81935年,几乎在闻一多将屈原“为忧国而自杀”斥为“梦呓”的同时,尚在日本流亡的郭沫若应上海开明书店邀约,写下专著《屈原》,由此踏上屈原研究之路。
作为五四一代文化人,郭沫若同样摒弃了“忠臣”观念,但却肯定屈原是“爱国”的,这建立在他对屈原自杀时间及原因的重新解释上。据闻一多的总结,屈原自杀的动机历来有三种说法,即泄忿说、洁身说和忧国说。9前两者倾向于将屈原自杀看作个人悲剧,后者则将其看作爱国的最高体现。闻一多认可的是前两种说法,即屈原“自杀的基因确是个人的遭遇不幸所酿成的”,原因在于经过考证屈原的死期早于怀王丧身辱国,更不及郢都失陷。10关于屈原卒年,钱穆也持相似看法。11这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居于主流的观点。然而,郭沫若以王夫之《哀郢》篇题解为中介12,将屈原“自杀”的时间定在楚襄王二十一年秦将白起攻破郢都之际,提出了更为激烈的“殉国说”13,这无疑是忧国说的现代变体。如果考虑到传统屈原忧国说的提倡者如洪兴祖、朱熹、王夫之、黄文焕等多生活在异族入侵、朝代更替的历史情境中,那么,当民族危机再度袭来,忧国说被重新召唤回来,且被转化为更为激烈的殉国说便非偶然。只不过此时屈原所殉之“国”已从传统的“君国”被置换为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
郭沫若不仅在民族主义意义上重新阐释了屈原爱国的精神底质,而且在文学革命层面对屈原“诗人”面向进行了揭示、塑造。在1935年创作的《屈原》中,郭沫若从白话入诗、诗体解放的角度将屈原定位为“革命的白话诗人”14。他指出,“《楚辞》中使用的方言,即当时的白话”,“白话入诗已经可以说是诗体的解放”,屈原“利用了歌谣的自然韵律来把台阁体的四言格调打破了。屈原,可以毫不夸张地给他一个尊号,是最伟大的一位革命的白话诗人”。15事实上,《楚辞》“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16早为传统学人所揭示,现代学人也关注到了《楚辞》和《诗经》语言形式上的差别,并试图从民俗学、文学社会学的角度加以阐释。不同于梁启超、谢无量、游国恩、鲁迅等人将《诗经》《楚辞》的差异归为“南北文学”或“南北文化”的差异,郭沫若将其看作“雅颂”与“风”、“台阁体”和“歌谣体”、“贵族文学”和“民间文学”的不同,由此在五四白话文运动的阐释框架内肯定《楚辞》的民间性和屈原的革命性。
颇有意味的是,郭沫若的屈原殉国说以及“革命的白话诗人”的论断此时虽已成形,然而却应者寥寥,而在不多的反响中,不乏对屈原爱国说的批判。171936年,相近的说法在郭沫若的长文《屈原时代》中再次出现,依然未引起广泛关注。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挖掘传统文化中的精神资源进行抗战动员,变成了政党、知识分子文化人的普遍共识,而利用各种节庆、纪念日举行大型公开仪式则成了重要的民众动员模式。18民俗意义上的端午节被官方赋予了政治教育意义。“纪念屈原、讨论屈原本身就是一种立场、一种姿态,是一种政治的表现”。19在这一情境中,1930年代为郭沫若、游国恩等推崇的屈原,“在民族多难、国家多事的今天”,“被广泛的注意起来”。20
大约从1940年端午节开始,纪念屈原的诗文显著增加。此时既是著名学者、诗人、剧作家,又身兼第三厅厅长、负责抗战动员工作的郭沫若,时隔四五年后关注点再度回到屈原,写下了纪念文章《关于屈原》和《革命诗人屈原》。21前者强调屈原之死是为殉国而非失意,后者则强调屈原诗歌形式的革命性——这几乎是对其1930年代中期观点的“重复”。只是,这些“重复”的旧说却引发了时代共鸣。1940年端午,陪都新运总会举行大型水上运动会,会长孔融明确将屈原看作“爱国诗人”,宣告“纪念端午,就是纪念屈原”。22臧云远认为“屈原诗化了当时江南的大众语,运用了当时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民谣体”,戈茅指出“屈原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古代诗人,而且是一位富有学问的政治家,热情的爱国者”,并且率先将“民族诗人”的称号赋予屈原。23
正是由于时代情感结构转变,以屈原祭日为“诗人节”的提议呼之而出,应者云集。1941年5月30日,正值端午节,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举办了四百多人参加的大型纪念晚会。国民党元老、监察院院长于右任致辞,“文协”总务部主任老舍报告筹备经过,“文工会”主任郭沫若讲演屈原生平。24一个新的节日——“诗人节”——被隆重宣告诞生。25与此同时,重庆有影响力的报刊,无论立场左右、官办私营,几乎都刊出了篇幅可观的纪念文字。26为其供稿的既有国民党高层如陈立夫、梁寒操、冯玉祥等,也有立场各异的文艺界人士如郭沫若、孙伏园、易君左、李长之、王进珊、陈纪莹、吴组湘、老舍等。27一时间,凭吊屈原的诗词创作成为风气,以屈原为主人公的小说、戏剧、论文、随笔数量激增,“屈原热”由此到来。
在“诗人节”中,郭沫若占据着显要的位置,他不仅为屈原像题词,发表主题讲演,撰写“诗人节”专刊文章《蒲剑·龙船·鲤帜》,而且宣言性的《诗人节缘起》也经过他的修正。28更为重要的是,郭沫若在1930年代中期“翻新再造”的以白话入诗、殉国而死的民族诗人屈原形象,被呈现在《诗人节缘起》中,并经过“诗人节”的晚会仪式和媒介仪式广为传播。29当日纪念文章虽立场各异,论述角度也多有不同,且各自对民族主义内涵的理解也不乏分歧,但在屈原爱国这一点上却毫无二致。30例如,平民促进会成员堵述初不仅称屈原为“爱国的诗人”“第一位民族诗人”,还从文字通俗意义上将屈原命名为“平民的诗人”,可以说是郭沫若的观点的引申和总结。31
然而,郭沫若并未止步于此。1941年底,郭沫若在中华职教社所作《屈原考》《屈原的艺术与思想》专题演讲中,多次称屈原为伟大的“民族诗人”。321942年1月,郭沫若创作了历史剧《屈原》,2月应侯外庐的论战写下了《屈原思想》,4月将两三年来关于屈原的讲演、杂文辑为《蒲剑集》出版33,同年端午,又写下《屈原研究跋》,筹备屈原研究论著的汇集出版工作34。密集的屈原著述、公开的宣讲以及大型剧场演出,使民族诗人屈原形象深入文化人、学生群体、市民观众心中,逐渐成为了时代共识。而闻一多否认屈原自杀殉国的说法,以及质疑屈原存在的声音,此时几乎被完全淹没。35
二 唯物史观视野中的革命儒家与“人民”代言人屈原
在民族危机的“常态化”以及“屈原热”的时代氛围中,屈原研究俨然成为了抗战时期的显学。郭沫若的屈原殉国说、革命白话诗人说被广泛接受,很大程度上在于契合了民族危亡时代的情感结构。然而,郭沫若的屈原研究并没有停留在抗战动员层面,而是有着严肃的学术追求。由于首开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屈原的先河,且不断强化革命儒家的论述,郭沫若的屈原研究显得与众不同、独树一帜。
正如郭沫若所言:“屈原的作品以及整个《楚辞》,近年来已渐渐把它们的身价恢复了。学习屈原,研究楚辞,差不多成为了一种风尚。”36对于当时的屈原研究,梁宗岱有一个形象的区分,即“走外线”和“走内线”。所谓“走外线”,即泰纳派的批评方法,“对于一个作家之鉴赏,批判,或研究,不从他底作品着眼而专注于他底种族,环境,和时代”,梁宗岱批评其进入中国沦为“一种以科学方法自命的烦琐的考证”,矛头指向陆侃如的《屈原》。37事实上,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西方实证主义与传统训诂考证相结合,成为了主流的研究方法,风潮所及,当时的研究者如胡适、谢无量、游国恩、闻一多等,大都注重屈原生平、行迹、作品等材料的搜集、训诂和考证。38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闻一多《楚辞校补》与游国恩《屈原》延续的仍是这一路径。39而梁宗岱坚持的“走内线”方法,则注重文学的审美性和自律性,他所著的《屈原》不探究作家生平和事迹,也很少转引前人研究成果,而是单刀直入《楚辞》的艺术世界和屈原的精神世界。40
实际上,郭沫若的屈原研究起初走的也是梁宗岱所说的“走外线”的路子。写于1935年的《屈原》重在对屈原生平、篇目真伪及次序的考证,立论也主要从民族文化、地理环境、时代思潮等角度解释屈原思想及其诗歌特色。41然而,在1936年创作的《屈原时代》中,郭沫若开始将屈原纳入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框架中予以考察。文章开篇采用大量典籍和青铜铭文资料,证明西周至春秋时代是奴隶制社会,继而将儒家、墨家革命思潮的出现,以及白话文体改革,解释为“奴隶制向身分制的转移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应”。在厘定战国的社会性质及意识形态后,考察“他和他的作品之社会史上的意义”,指出屈原本是楚国的贵族,思想上受了儒家的影响,而在文体变革上受到的影响更为深刻,“徹底地采用了方言来推翻了雅颂诗体的贵族性”,“在诗域中起了一次天翻地覆的革命”。42由此,郭沫若将屈原及其艺术的核心要素——方言俗语的运用、儒家思想都纳入“意识形态”范畴,并从社会形态变革的角度加以阐释,唯物史观视野和方法的独特性初步显露。
无疑,此时郭沫若的屈原研究已经呈现出唯物史观的面貌,但由于典籍、甲骨、金文材料的爬梳和考证仍然占去了很大比重,因此,直到1942年,仍有人认为“郭先生的‘屈原研究’的态度和方法是‘新朴学’”43。但郭沫若的屈原研究终究不同于“新朴学”,此后不久,随着《屈原思想》的发表,郭沫若“对于屈原的整个看法”形成44,唯物史观方法全面展露,其研究的独特性逐渐为时人注意。不过质疑的声音也随之而来,同为史学家和文学家的缪钺指出:
郭君在《屈原时代》及《屈原思想》两篇中,畅论中国自殷至春秋中叶为奴隶社会,详征博引,不惮烦言(屈原时代一篇共二十二页,而论奴隶社会者占十页,屈原思想一篇共四十二页,而论奴隶社会者占十六页。)其目的无非在说明春秋战国间由奴隶制渐变为封建制,乃奴隶解放之时代,屈原之思想为此时代意识形态之反映。纵使信如郭君所言,则凡讲述战国诸子,皆可加此一大段殷周奴隶社会论,何独屈原,读《屈原研究》之书,而遇如此冗长之殷周奴隶社会论,已觉喧宾夺主,有离题过远之感。况自春秋末叶以降,王官之学,散为私家,即学术由贵族移于平民,由政府官守之保存,变为民间自由之研究与发抒,此为学者公认之事,实足以解释郭君提出屈原思想之种种特点,又何必乞灵于奴隶社会之说。45
显然,缪钺注意到郭沫若屈原研究的独特处在于“不惮烦言”地探讨奴隶社会问题,但对此甚为不解。在他看来,春秋战国“学术平民化”潮流为学界公认,钱穆《国史大纲》就将“民间自由学术之兴起”看作由春秋到战国的巨变中最重要的一个变化46,足以解释战国时代智识下移、文体变革以及屈原思想中注重民生等方面,根本不需要借助奴隶社会学说。缪钺虽然赞成从社会变迁角度阐释“屈原思想的种种特点”,但忽视了同为外部研究方法,两种解释实则有着更深层次的差别:前者把社会的精神、风俗、思潮看作“最后的解释”,后者则意识到这些因素背后还有“物质的生产力”作为基础。郭沫若的屈原研究最大的特征在于,将南北文化、社会思潮、风俗等都归拢为意识形态,并试图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角度求得最后解释,因而将很大精力放在了“看似多余的”战国社会性质考定上。显然,这种“累赘”“离题”之处恰恰是唯物史观文学批评的根基。
郭沫若将唯物史观首次引入屈原研究,遭受不同学术理路学者的质疑在所难免,然而,令人诧异的是,更大挑战来自同为唯物史观派的侯外庐。1942年初,侯外庐在看到郭沫若的讲演稿《屈原的艺术与思想》后,不同意其中关于屈原的评价,写下《屈原思想的秘密》一文,拉开了论战的序幕。针对侯外庐的挑战和质疑,郭沫若即刻答以《屈原思想》。双方不仅未能达成共识,分歧反而愈加扩大。侯外庐再次回之以长文《屈原思想渊源底先决问题》,然而,此文未及刊完,出于左翼阵营统一的考虑,论辩被《新华日报》国际版负责人乔冠华紧急打断。47
回看这场论战,同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派,郭沫若和侯外庐的屈原研究有着诸多共通之处。首先,二人都认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基本架构,坚持“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48,在他们的分析中,西周以至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性质的讨论都占据了显要位置。其次,二人都将西周视为奴隶制社会,而将春秋战国看作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时代,从而不同于吕振羽、翦伯赞、范文澜等的观点49,因此,当时学界都公认二人“是一个派别的”50。其三,对于屈原思想,当时人或视为兼具儒、道、阴阳、法等派思想的杂家,如谢无量、游国恩51,或视为道家,如戈茅52,郭沫若则力主屈原思想的主要面目是儒家,侯外庐的看法也与之相同。最后,对屈原的基本认识,二人也并未自外于时代意识,均肯定屈原是有着高尚人格、伟大诗篇的爱国诗人。
值得探究的是,二人为何会产生巨大分歧?侯外庐事后解释道,“分歧的本质在于我们对儒家思想的评价差异很大”53。早在1936年创作的《屈原时代》中,郭沫若就将儒家、墨家看作与奴隶解放运动相适应的意识形态,肯定其为“新锐的革命思潮”54。而在1942年发表的《屈原思想》中,郭沫若从伦理、政治、宗教、文字艺术、文体等多个层面,再次肯定儒家、墨家连同道家都是先秦思想革命的成果。不过,在论述中,郭沫若的重点落在儒家,例如,将儒家的核心理念“仁”解为“把人当成人”,看作“当时的一个革命的成果”,将儒家的德政大一统看作奴隶解放时代的潮流所向。在谈到儒家的古史观时,郭沫若更是明确说道:“儒家把尧舜时代粉饰得很庄严,事实上是对于氏族公产社会的乌托邦的景慕……在当时,它本质上是一种革命的、前进的思想。”55但对侯外庐来说,儒家“言仁言礼”,所谓的“仁”是“克己而达于恢复周礼”,“此一道使他一道归”56,是“仁的君子推及于不仁者小人的‘礼’治主义”,不是什么“革命的成果”。57因而,儒家虽对没落贵族有所暴露和批评,但总体上“维持周道而调和大别”,“和现状而法今古”,并不是郭沫若所说的“革命的,前进的思想”。58
然而,在唯物史观视野内,对儒家思想的评价不单是对经义的阐释,而更要向下追索到社会生产方式变革和社会性质层面。在郭沫若看来,西周是以大规模奴隶生产于“公田”为特征的奴隶制社会,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私田”大量开采,生产奴隶获得解放成为自由民,生产方式的核心要素——生产对象和生产主体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尤其随着各国进行田制、税制改革,生产关系也发生根本性的变革。59经济基础的变革反映在意识形态领域,即儒家、道家、墨家等思想的出现。60因而,郭沫若此时将儒家与道家、墨家同时看作革命的成果,并未有态度上的明显差别。而对侯外庐来说,西周社会是亚细亚式的奴隶社会,其特征在于保存古旧的氏族组织,将在农村耕作的奴隶和城市贵族维系起来。在生产方法上,“是土地国有(即氏族所有)的生产手段与集体族奴的劳动力二者间之结合关系”61。因而,奴隶社会向封建制的路径是挣脱古旧的氏族制,重在调和矛盾,而恢复周礼、维护古旧的氏族制的儒家当然是反动的,与之相比,“非现状而法上古”的道家,“不满现状而道将来”的墨家,反而具有了某种革命性。62
值得注意的是,对儒家的评价又决定了对屈原的定位。郭沫若虽然在生产方式变革的参照系中肯定儒、道、墨都是“革命的成果”,但正如王璞所言,“代表了‘人民解放’的思潮是落在儒家一边”63。在《屈原思想》中,郭沫若多处引用甲骨文、铭文资料佐证“中国古代的生产奴隶就是人民”64,由此,“奴隶解放时代”被置换为“人民解放时代”,儒家的“仁”——“把人当成人”具有了珍视人民价值的内涵,与法家的刑政大一统相对,儒家的德政大一统则是注重民生、“保卫人民”的体现。65在这一意义上,儒家思想成为了奴隶/人民普遍诉求的表达。儒家的革命性不只体现在顺应奴隶制向封建制的历史转变,更体现为在变革时代没落贵族、新兴地主、解放奴隶/人民等社会阶层中占据了人民的立场。
当“注重民生,尊崇贤能,企图以德政作中国之大一统”“重仁袭义”的屈原被确认为“儒者”时,其用民众的语言写出的诗歌,如“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衍”“汤禹严而祗敬兮,周论道而莫差。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等66,就成了内在的革命儒家思想的自然流露,成了奴隶/人民的心声的传达,在此意义上,屈原不仅是一位革命诗人,而且有意识地做了人民的代言人。与之相比,侯外庐虽也有类似的表述,如“作为人民作家的屈原,用他的歌唱,代表了人民的这喉舌”67,但由于他将儒家看作背逆时代潮流的思想,因而,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屈原,对现状的批判以及对人民的同情只是客观上的效果,而非主观上有意识的行为,本质上“他是一个三闾大夫,对于没落的公族制,反而寄着衷心的同情感”68,是崩解的奴隶社会的维护者和没落贵族阶级的代表。
需要说明的是,这场论争不只是郭沫若和侯外庐的分歧,实则隐含着郭沫若和整个左翼阵营的分歧。当时左翼阵营内部对儒家大多持否定态度,只不过否定的角度各有不同。侯外庐否定儒家主要立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论,而其他左翼史学家,如吕振羽、翦伯赞、范文澜等则从阶级史观出发,将儒家视为没落的封建领主阶级思想的代表。69更多的左翼文化人则从秉持五四新文化传统以及批判国民政府奉儒家为政治合法性来源的角度70,否定儒家的革命性。与之相关,在儒家的脉络中将屈原看作历史进步者、思想革命者和人民的代言人,郭沫若也是相当孤立的,正如侯外庐所说,1942年在重庆的革命队伍内部,不同意郭老屈原评价的同志为数不少。71例如周恩来、姚雪垠、宋云彬等,就不同意郭沫若的革命儒家论断,进而质疑其对屈原的评价。72吕振羽、翦伯赞等则抛开儒家,直接从封建领主出身推出屈原是没落腐朽的旧领主阶层代言者。73换言之,无论对孔孟还是对屈原,左翼阵营更倾向于用“落后的世界观与先进的方法论的矛盾”框架,只承认其客观上有限的进步性。
由此观之,郭沫若对儒家和屈原的评价颇有些“一意孤行”的味道。除去学理上的分歧,侯外庐多少觉得这是诗人郭沫若对屈原的“偏爱”74,而在后来左翼儒墨批判中,当郭沫若对儒家、墨家的褒贬态度完全展露时,舒芜、胡风等将其斥为“教条主义”的错误75。以后设视角来看郭沫若抗战时期的历史人物及先秦思想研究,这种“固执己见”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即他对历史人物的思考已逸出了唯物史观、阶级史观的范围,而倾向于一种新的标准的酝酿和提出。在这一标准下,儒家由于包含了“把人当成人”以及德政大一统的理念,而具有了革命性、人民性的内涵。通过儒家的中介,郭沫若不只是在诗歌语言革命层面,而更是在政治革命和思想革命层面,发掘出了统治阶级知识分子屈原的人民性。
值得一提的是,郭沫若对屈原的独特理解在历史剧《屈原》中得到了形象的演绎。以连秦和抗秦、刑政大一统和德政大一统为界,剧中人物被分为截然对立的两派:前者为南后、靳尚、子椒、怀王、子兰等楚国权贵阶层以及附庸权贵的文人宋玉,后者为屈原以及钓者、婵娟、渔父、卫士等底层民众,也即奴隶制解体时代获得自由的庶人奴隶。76屈原的抗秦、德政大一统主张代表了民众的心声,反过来,通过民众对屈原的拥护和搭救,又呈现了屈原的人民性。伴随着历史剧《屈原》的上演,郭沫若塑造的积极阳刚、代表奴隶解放精神、人民代言人的屈原形象很快为人们所接受,相反,侯外庐和大部分左翼文化人塑造的时代的落伍者和贵族阶级自我哀伤者的屈原形象,逐渐在公众视野中消失。
三 “以人民为本位”和“民族-人民的”诗人屈原
郭沫若对屈原的定位并未止于民族诗人和人民代言人,随着抗战末期“人民”话语在国统区的兴起,郭沫若“以人民为本位”的史观出场,屈原被明确称为“人民诗人”。相较于发明这一称号的闻一多,郭沫若的“人民诗人”屈原兼具人民性和民族性的双重内涵。
抗战时期,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架构内,“人民”囊括了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既是抗战的主要力量,也是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构成力量。77然而,由于国共两党始终存在的矛盾,“就在抗战初期,由南京迁到武汉,由武汉又迁到重庆的那起初的三四年,各地的报章杂志上普遍地是看不出‘民主’与‘人民’这样的字眼的”78。1944年以后,“人民”话语再次兴起,主要和两个事件密切相关。其一,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人民的世纪”这一提法在国统区流传开来,“一时成为知识分子的常用语”,并“为1944年开始的民主运动提供了话语支持”。79其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此时开始在国统区左翼文化界传播开来,“人民文艺”的相关论述被反复征引和再阐释。80
在“人民”话语再度回归的思想语境和政治氛围中,郭沫若又将屈原指认为“人民诗人”。1946年发表的《由诗人节说到屈原是否弄臣》中,郭沫若指出:“他的诗意识是人民意识,他的诗形式是民间形式,他是澈内澈外的一个人民诗人。”屈原作为偶像,“他是人民意识的形象化,人民文艺的形象化”,由此将屈原纳入新的“人民文艺”的坐标系中。81然而,这篇文章主要目的不是用新的话语范式包装屈原,与此前所写的《屈原不会是弄臣》一样,文章是对两年前那场搅动学界的屈原论争做出的迟到回应,但其触及的问题却远远超出了论争的范围。
1944年成都“诗人节”上,孙次舟从汉代艺术家仍被“倡优畜之”、宋玉是文学弄臣以及《离骚》中女性化装扮等角度,抛出“屈原是文学弄臣”的说法;这与1940年代以来普遍认同的民族诗人形象大相径庭,立即遭到了激烈的批评。在申辩中,孙次舟将这一说法追溯到闻一多。闻一多无奈作为“调人”参战,他首先肯定屈原是文学弄臣、家内奴隶,但认为奴隶具有反抗性,反而更值得敬重。82事实上,怀着这样的认识,闻一多在1945年的“诗人节”上就先于郭沫若得出屈原是“人民诗人”的结论。在闻一多看来,“使得屈原成为人民的屈原”有四重理由:“首先在身份上,屈原便是属于广大人民群中的”;其次,《离骚》《九歌》采用的是“人民的艺术形式”;其三,在内容上,《离骚》“暴露了统治阶层的罪行”;最后,屈原的“死”催生了楚国的农民革命,导致了楚国的灭亡。因此,“屈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有充分条件称为人民诗人的人”。83
付玉对他们讲发财挣钱的路子,讲买一款产品的好处,讲要花一万块钱先期投资的重要性,讲从一万块钱创业,用不了多久,就能几倍几十倍地回报。然后自己开公司,当老板。付玉讲完这些,最后举起手臂高呼,我行,我能行,我是最棒的。台下的人紧跟着高呼,我行,我能行,我是最棒的。这些口号,尽管喊得我热血沸腾,可是一到晚上,想起付玉的话,又担心起来,我就摸摸挎包里的学费,那一万块钱,硬硬的还在,它像我的希望,我的梦一样,还安安稳稳地睡在挎包的夹层里,我的心才算踏实下来。这个钱,是二叔打工挣来的,我不能乱花,这是我的学费,我要用它来完成学业。
显然,在肯定屈原“用人民的艺术形式”“暴露了统治阶层的罪行”上,郭沫若与闻一多是一致的,侯外庐也在这个层面上将屈原称为“人民作家”,这可以说是当时很多知识分子的共识。然而,在对“人民诗人”屈原的理解上,郭沫若和闻一多存在着根本分歧。
首先,屈原与人民是怎样的关系?闻一多认为,屈原“作为宫廷弄臣的卑贱的伶官”,在阶级身份上“是属于广大人民群中的”。84也就是说,由于弄臣身份,屈原本身就是人民。然而,在郭沫若看来,屈原是文学弄臣的说法并无坚实依据,弄臣而能怀抱强烈的人民意识,这样的见解“过于以意识决定存在”85。他坚持认为“屈原是三闾大夫,是楚国贵族屈、景、昭三姓中之一姓的显要”86。然而,正如刘奎追问的那样:“从阶级身份的角度否定了屈原成为人民诗人的可能……那么郭沫若又是如何将屈原命名为人民诗人的呢?”换言之,作为统治阶级的知识分子屈原又如何成为“人民的”?对此,刘奎认为郭沫若主要着眼于屈原诗歌的民歌形式及蕴含的人民思想,但又敏锐地看到人民诗人屈原和儒家诗人屈原的一致性。87王璞也注意到闻一多立足弄臣身份封屈子为人民诗人,而郭沫若的“革命诗人”“南方儒者”屈原与左翼内部革命儒家论述相呼应。88然而,需要进一步廓清的是,郭沫若的确在诗歌形式和内容层面肯定屈原的人民性,但正如前文所述,在郭沫若这一时期的论述中,屈原之所以是“人民的”,更根本的原因在于屈原有着同奴隶/人民一致的世界观,即顺应奴隶解放时代的“把人当成人”“德政大一统”等儒家观念,而《楚辞》民歌形式和人民性内容只不过是革命儒家观念的外化。人民诗人屈原之所以与儒家诗人屈原“一致”和“呼应”,恰恰在于其本身就建立在儒家诗人屈原的基础上。正是因为革命儒家的中介,屈原才能够像葛兰西所说的“想人民之所想,喜人民之所喜”,体验着人民的情感,89变成真正属于人民的知识分子。
与此同时,经常为研究者忽视的是郭沫若与闻一多的另一个重要区别,即“人民诗人”屈原中的“人民”是否包含了“民族”的内涵?在闻一多的阐释中,屈原不仅是人民群众中的一员,而且是“革命的催生者”,因为屈原通过“行义”——自杀把楚国人民的“反抗情绪提高到爆炸的边沿”,秦军到来时,人民便以溃退和叛变的方式报复楚国统治者,也即是说,屈原之死催生了人民革命。90换言之,屈原的人民性和革命性,是针对楚国统治者,而不是针对秦国侵略者。如果考虑到闻一多自始至终反对屈原“忠君爱国”的说法91,可以说,在他这里,屈原具有人民性,而不具有民族性。然而,郭沫若在民族危亡语境下首先发现的是屈原的民族性,此后通过革命儒家的中介才发现屈原“澈内澈外”的人民性。但后者并未取代前者,反而成为了前者的目标和结果。在《屈原思想》中,郭沫若指出,屈原并不是狭隘的爱国主义者,对内“他之所以要念念不忘君国,就是想使得民生怎样可以减少艰苦,怎样可以免掉离散”92;对外他眷爱楚国,不只是因为楚国是父母之邦,而是“想以德政来让楚国统一中国,而反对秦国的力征经营”93,因为以德政方式完成国家统一顺应了奴隶解放时代潮流,满足了楚国人民乃至全天下人民的渴求。1946年,郭沫若仍坚持屈原的人民性无法与民族性分离,“屈原无疑是一位政治性很浓重的诗人,而他的政治观点就是替人民除去灾难,对内是摒弃压迫人民的吸血佞倖,对外是反抗侵略成性的强权国家”94。前者指向屈原的人民性,后者指向屈原的民族性,二者结合才构成了屈原政治性的全部内容。
更准确地说,郭沫若所谓的“人民诗人”屈原,不是闻一多所谓的人民群众中产生的诗人,而是出身于统治阶级,但诗歌形式和内容兼具人民性,且有意识地占据人民立场,对内反抗腐朽统治者、对外反抗侵略的“民族-人民的”诗人。
统治阶级出身的屈原被视为人民的知识分子,郭沫若这种独特的认识,背后隐含着他在抗战后期明确表述为“以人民为本位”的史观。“以人民为本位”这一表述早在郭沫若1921年发表的《我国思想史上之澎湃城》中就已出现95,而作为一个独特概念再度出现于郭沫若的著作则到了抗战后期。但正如郭沫若所言,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以人民为本位”实际上贯穿于其1940年代全部的历史人物研究和史剧创作中。96考虑到1939年翦伯赞在《历史哲学教程》中总结唯物史观派研究时,指出郭沫若、吕振羽等史学家共同存在的问题在于,重“社会经济形态”分析,“闭口不谈个人”,在其著作中“看不见一个‘历史人物’的名字”97,那么,郭沫若以屈原研究为开端,研究屈原、曹植、万宝常、王安石、李岩等历史人物,在唯物史观框架内展开历史人物评价,就无疑具有开创性。值得注意的是,翦伯赞所谓的“历史人物”,主要指历代帝王、农民革命和民族革命领袖、反动首领、外族侵略者等98,而郭沫若选择的历史人物则是传统知识分子,“以人民为本位”史观正是用来衡量传统知识分子的标准。相对于人民史观考察历史人物时多聚焦于阶级出身,郭沫若“以人民为本位”史观主要将与人民的关系看作衡量知识分子进步与否的参照系。郭沫若始终坚持屈原的贵族知识分子身份,正是因为在“以人民为本位”的标准下,屈原的贵族出身并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奴隶/人民解放时代,屈原秉持的儒家思想是否符合历史发展潮流,他与挣脱奴隶枷锁的人民感情是否相通,他的诗篇是否代表了人民的愿望,才是决定屈原是否是“人民的”知识分子的关键。
郭沫若坚持民族性与人民性在屈原身上的统一,这很大程度上是中国革命的自身性质、任务及其对知识分子的要求使然。正如汪晖所言,二十世纪中国革命“所要完成的使命是一个混合体,既包括19世纪的课题,又包含对这些课题的批判、扬弃和超越……从孙文的‘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概念,无不体现中国革命的双重使命”99。在抗战与革命语境中,毛泽东将中国革命的性质明确表述为“新民主主义”,即“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其中,革命的主体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大众,革命的内容包括“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而最主要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100,最终目标则是建立以人民为主体的新国家。这一过程需要大量兼具民族性和人民性的知识分子发挥联系人民、教育人民、汇聚“民族-人民”的集体意志以形成新国家的功能。正是现实革命对知识分子的要求,投射到了郭沫若对历史人物屈原的研究中,使得屈原呈现出了“民族-人民”的双重面貌。
事实上,在屈原之后,郭沫若继续在“人民本位史观”下对历史人物王安石、李岩等展开研究,显示出了以新的标准重新检视士大夫传统以及重塑“人民”知识分子谱系的雄心。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及知识分子传统,在革命所需的有机知识分子尚未成形,联结政党和人民的关系、进而凝结“民族-人民”的集体意志主要依靠传统知识分子时,如何评价传统知识分子,从中辨别出革命性、人民性的元素,正是难题之所在。101在这一意义上,郭沫若的历史人物研究触碰到了革命中的知识分子难题,即如何处理革命和传统知识分子的关系。在此,更实际的关切是,在抗战时期民族革命和人民革命的框架中知识分子如何明确自身的角色和定位,以及国统区包括郭沫若自己在内的左翼知识分子如何处理与人民的关系。这构成了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无法回避的论题。从抗战时期中共尤其是毛泽东提出的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人民史观来看,以知识分子为中心的“人民本位史观”或许显得保守,但不容否认的是,郭沫若的论述避免了人民史观在处理知识分子问题时僵硬的出身论和阶级论,与之构成了意味深长的互文关系,打开了新的视野和空间。
有意味的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随着新中国成立,人民时代的真正到来,唯物史观派阐发的落后保守的屈原形象应者寥寥,而闻一多所说的“弄臣而能革命者”的人民诗人屈原也未得到承认。虽然在郭沫若新的书写中,曾作为屈原“人民性”中介和保证的革命儒家论述“富有症候性地消失了”102,但其塑造的兼具民族性和人民性的诗人屈原,被表述为“爱祖国,爱人民的诗人”,得到了广泛接受和认可。1953年端午前后,屈原逝世2230周年之际,苏联、中国举行了隆重的纪念大会,屈原与哥白尼、拉伯雷、莎士比亚一起跻身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列,屈原作为“我们民族的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伟大诗人”103形象得以广泛传播。时至今日,屈原形象仍在被一代又一代人改写104,但“爱祖国爱人民”的底质却少有改变,正如侯外庐所说,“今天,已经抹不去中国人心目中郭沫若所加工的屈原形象”105。
注释:
1 “民族-人民的”概念来自葛兰西对意大利革命中知识分子难题的表述,即意大利知识阶层脱离“民族”、脱离“人民”,不是同现实民族中占绝大多数的人民,而是同等级制度的传统保持着紧密的联系。革命所需的知识分子应该和人民休戚相关,能够发挥联系人民、教育人民、凝聚集体意志的作用(参见葛兰西《关于“民族—人民的”概念》,《论文学》,吕同六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6~54页)。但此处并非照搬葛兰西,只是借用他的说法,揭示郭沫若对屈原的定位与中国革命内在经验的联系。
2 如石云《评郭沫若的屈原研究》,《江汉论坛》1988年第4期;魏红珊《郭沫若与屈原研究》,《郭沫若学刊》1999年第2期;卜庆华《论郭沫若的屈原研究》,《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年第5期。
3 王余辉:《解构·建构·实现——近代“屈原爱国”观念生成与传播的历史考察》,《史学月刊》2020年第5期。
4 适:《读〈楚辞〉》,《读书杂志》第1期,1922年。
5 同一时期不乏学者将屈原视为“政治家”和“爱国者”,如谢无量从地理、出身和音乐角度对屈原爱国思想加以解释,只是并未引起广泛注意。参见谢无量《楚词新论》,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第60~62页。
6 游国恩:《楚辞概论》,述学社1926年版,第97页。
7 9 10 闻一多:《读骚杂记》,《益世报(天津版)》1935年4月3日。
8 游国恩:《读骚论微初集》,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216~217页。
11 钱穆也认为屈原卒年当在怀王时,至多在襄王初年。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249~252页。
12 王夫之《哀郢》篇题解:“楚东迁于陈,屈原眷念故都。”王夫之:《楚辞通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7页。
13 14 15 郭沫若:《屈原》,光明书店1935年版,《序》第2,66~67,60、64、66~67页。
16 黄伯思:《新校楚辞序》,李诚、熊良智编《楚辞评论集览》,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39页。
17 长之:《屈原》,《益世报(天津版)》1935年5月29日。
18 例如,抗战后每年举行的“一·二八”“五四”“五卅”“七七”“双十”等纪念仪式。其中,最为轰动的是1938年郭沫若在武汉领导第三厅筹办的“七七纪念周”活动。
19 70 75 黄晓武:《马克思主义与主体性》,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43,42、53,65~66页。
20 林若:《爱国诗人屈原:为纪念第二届诗人节而作》,《时代中国》第5卷第6期,1942年。
21 郭沫若:《关于屈原》,《大公报》1940年6月9日;郭沫若:《革命诗人屈原》,《新华日报》1940年6月10日。
22 《嘉陵江盛会——龙舟竞赛和纪念屈原》,《中央日报》1940年6月10日。
23 臧云远:《屈原艺术的发展和评价》;戈茅:《关于屈原》,《新华日报》1940年6月10日。
24 27 老舍:《第一届诗人节》,《宇宙风》第120期,1941年。
25 关于诗人节的筹备、设立及各方围绕屈原形象及意义的博弈与斗争,参见刘奎《诗人革命家——抗战时期的郭沫若》,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84~200页。
26 堵述初:《诗人节的重庆各报特刊》,《中央日报》1941年6月5日。
28 据老舍记述,几位朋友起草的《诗人节缘起》“由郭沫若先生修正”。老舍:《第一届诗人节》,《宇宙风》第120期,1941年。
29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诗人节缘起》,《新华日报》1941年5月30日。
30 87 刘奎:《诗人革命家——抗战时期的郭沫若》,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96、251~256页。
31 堵述初:《屈原之歌》,《中央日报》1941年5月30日。
32 《屈原考》中提到3次,《屈原的艺术与思想》中提到2次。郭沫若:《屈原考》,《中央日报》1942年12月5、6日;郭沫若:《屈原的艺术与思想》,《中央日报》1942年1月8、9日。
33 此集主要目的在收录屈原相关文字,但“还附带着收集了好几篇谈文艺或学术的文章”。郭沫若:《蒲剑集》,文学书店1942年版。
34 《屈原研究》一书收《屈原身世及其作品》《屈原时代》《屈原思想》《离骚今译》,除《屈原思想》为近作,其余皆旧作略加改动而成。参见郭沫若《屈原研究》,群益出版社1943年版。
35 在质疑屈原是否存在上,除更早的廖季平、胡适外,1930年代还出现了卫聚贤、何天行、丁迪豪等。参见卫聚贤、何天行、丁迪豪《楚词研究》,吴越史地研究会1938年版。
36 郭沫若:《关于“接受文学遗产”》,《抗战文艺》第8卷第3期,1943年。
37 梁宗岱:《屈原(为第一届诗人节作)》,华胥社1941年版,第3页。
38 如胡适《读〈楚辞〉》、游国恩《楚辞概论》、谢无量《楚词新论》、闻一多《楚辞校补》《九歌解诂》等采取的都是这一路径。
39 闻一多:《楚辞校补》,国民图书出版社1942年版;游国恩:《屈原》,胜利出版公司1946年版。
40 同时期陈适《离骚研究》(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李长之《孔子与屈原》(《文艺月刊》第11卷第6期,1941年)都可归入此类研究。
41 郭沫若与陆侃如关于屈原生卒年与作品的争论,以及对梁宗岱《屈原》的态度,参见郭沫若《屈原·招魂·天问·九歌》,《新华日报》1942年12月5、6日。
42 54 郭沫若:《屈原时代》,《文学》第6卷第2期,1936年。
43 孙伏园:《读〈屈原〉剧本》,《中央日报》1942年2月7日。
44 《屈原思想》后收入《屈原研究》,郭沫若自认为其“足以补充前两篇(按,《屈原》《屈原时代》)所论的不足”,至此,他“对于屈原的整个看法”大抵成形。郭沫若:《屈原研究》,群益出版社1943年版,第195页。
45 缪钺:《评郭沫若著〈屈原研究〉》,《思想与时代》第29期,1943年。
46 钱穆:《国史大纲》上,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93页。
47 50 53 71 74 105 侯外庐:《韧的追求》,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24,123,124,126~127,123、125,126页。
48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2页。
49 吕振羽将春秋战国置于“初期封建制”和“专制的封建时代初期”之间(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黎明书局1937年版);翦伯赞将其看作“初期封建社会的发展及其转向”(翦伯赞:《中国史纲》第1卷,五十年代出版社1944年版,第330页);范文澜将其置于“封建制度的开始时代”向“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成立”的中间阶段(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上册,大众书店1946年版)。
51 谢无量:《楚词新论》,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第57页;游国恩:《屈原》,胜利出版公司1946年版,第104页。
52 戈茅:《关于屈原》,《新华日报》1940年6月10日。
55 66 92 郭沫若:《屈原思想》,《新华日报》1942年3月10日。
56 58 62 侯外庐:《屈原思想渊源底先决问题》,《新华日报》1942年4月22日。
57 《屈原思想渊源底先决问题》后半部分单独成文,题为《申论屈原思想——衡量屈原的尺度》,侯外庐:《申论屈原思想:衡量屈原的尺度》,《中苏文化》第11卷第1—2期,1942年。
59 关于“私田”在这一时期郭沫若对古代社会变革的想象中发挥的革命性作用,参见王璞《“公”与“私”的变奏——郭沫若的“古代社会”想象的一个谱系》,李怡编《大文学评论》(1),花城出版社2015年版,第118页。
60 64 65 郭沫若:《屈原思想》,《新华日报》1942年3月9日。
61 侯外庐:《中国古典社会史论》,五十年代出版社1943年版,第63页。
63 王璞:《孔夫子与“人民”:郭沫若和革命儒家的浮沉》,2018年8月30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372365。
67 68 侯外庐:《屈原思想的秘密》,《新华日报》1942年2月17日。
69 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黎明书局1937年版,第56~60页;翦伯赞:《中国史纲》第1卷,五十年代出版社1944年版,第392~393页;中国历史研究会编著:《中国通史简编》上册,大众书店1946年版,第73~74页。
72 参见周恩来《对〈屈原思想〉的意见——致郭沫若》,《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16~217页;姚雪垠《屈原的文学遗产》,《文艺生活》第3卷第2期,1942年;云彬《屈原与儒家精神》,《青年文艺》(桂林)第1卷第1期,1942年。
73 吕振羽:《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不二书店1936年版,第378页;翦伯赞:《中国史纲》第1卷,五十年代出版社1944年版,第399页。
76 郭沫若:《屈原》五幕史剧,《中央日报》1942年1月24、25、27、28、30、31日;2月4、5、6、7日。
77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4~676页。
78 郭沫若:《民主运动中的二三事》,《新文化》第3卷第1—2期,1947年。
79 关于华莱士访华与“人民的世纪”在国统区的传播接受情况,参见刘奎《有经有权:郭沫若与毛泽东文艺体系的传播与建立》,《东岳论丛》2018年第1期。
80 例如《群众》1944年第9卷第18期组织了“文艺问题特辑”。
81 85 94 郭沫若:《由诗人节说到屈原是否弄臣》,《新华日报》1946年6月7日。
82 闻一多:《屈原问题——敬质孙次舟先生》,写于1944年12月,刊于《中原》第2卷第2期,1945年。
83 84 90 闻一多:《人民的诗人——屈原》,初刊于1945年6月《诗与散文》“诗人节特刊”,引自《诗歌月刊》第3—4期,1946年。
86 郭沫若:《屈原不会是弄臣》,《诗歌月刊》第3—4期,1946年。
88 102 王璞:《郭沫若与古诗今译的革命系谱》,《文学评论》2016年第3期。
89 葛兰西:《关于“民族—人民的”概念》,《论文学》,第47页。
91 1935年,闻一多明确否定屈原“忠君爱国说”。抗战时期,由于屈原爱国形象的教育意义,闻一多很少再提及这一话题。然而,直到1944年,闻一多仍坚持“忠君爱国”的屈原是不可靠的。闻一多:《屈原问题——敬质孙次舟先生》,《中原》第2卷第2期,1945年。
93 柳涛:《〈屈原之死〉与〈屈原〉》,《新华日报》1943年2月1日。
95 郭沫若:《我国思想史上之澎湃城》,《学艺》第3卷第1期,1921年。
96 郭沫若:《历史人物》,海燕书店1947年版,《序》第1页。
97 98 翦伯赞:《群众领袖与历史(再版代序)》,《历史哲学教程》,新知书店1939年版,《序》第6、74,74页。
99 汪晖:《世纪的诞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版,第70~71页。
100 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47、637页。
101 此处的“有机知识分子”和“传统知识分子”是葛兰西意义上的,前者指随新阶级自身一道创造出来并在发展过程中加以完善的知识分子,后者则指旧阶级中生长出来并与之保持紧密联系的知识分子。参见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姜丽等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27页。
103 游国恩:《纪念祖国伟大的诗人屈原》,《人民日报》1953年6月15日。
104 例如王璞指出,1970年代在“评法批儒”运动背景中诞生的香港左翼电影《屈原》,虽改编自郭沫若1940年代历史剧《屈原》,但电影中的屈原形象却从儒家变为了法家。Pu Wang , “The Transmediality of Anachronism: Reconsidering the Revolutionary Representations of Antiquity and the Leftist Image of Qu Yuan”,Frontiers of Literary Studies in China, 2019, 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