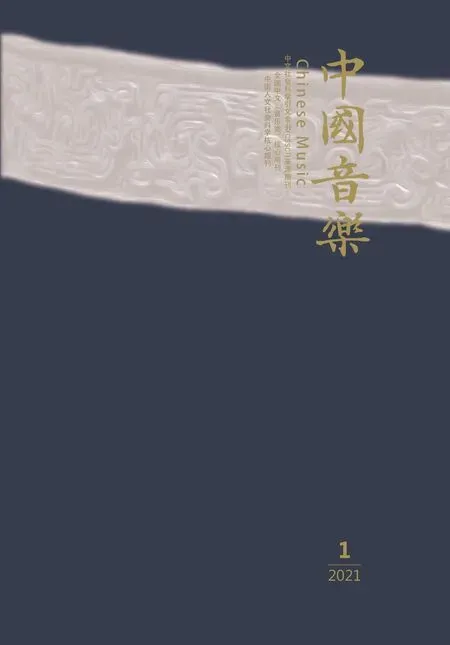冀中“音乐会”的当代传承
冀中地区的“音乐会”这一乐种主要流传于冀中及京、津地区的农村。在乐器使用上,音乐会以管子为主奏乐器,还有笙、笛子、云锣等有调乐器和鼓、铙、钹、铛子、板(小钹)等打击乐器。音乐会演奏的乐曲,其曲牌名可见于唐宋词牌和元明戏曲曲牌,与中国古代音乐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具有“中国古代音乐活化石”的性质,有着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音乐会不仅是一个民间乐队,同时还是一个乡村的公益组织,他们的活动与中国传统礼仪规范、当地民俗和民间信仰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每年,音乐会要在全村重要的祭祀和风俗性节日中演奏,在村落中常常主持与社区事务、宗教信仰密切相关的活动,主要有春节祈祥、神灵朝拜、丧葬祭祖、祈雨驱雹、中元祭鬼等。传统上,音乐会的这些活动都是义务服务性质的,因此在村落里往往享有崇高的威望,被称为“圣会”“善会”。
从杨荫浏、曹安和1952年对定县子位村“吹歌会”(音乐会的“南乐”分支)的考察开始,学术界就关注到了音乐会这一古老乐种。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中国音乐研究所从1986年对固安县屈家营音乐会的考察开始,又在20世纪90年代对冀中一带的音乐会进行了较全面的普查。此后学术界开始了对冀中音乐会旷日持久的考察,其卷入人数之众,产生的学术成果之多,为当代中国学术界所罕见,这一现象被张振涛称之为“冀中学案”。
这样一个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被学界广泛关注的民间乐种,在中国由传统农耕社会急遽向现代化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却普遍遭遇到了生存危机。今天的农村社会,已经打破了过去“农忙、农闲”的农耕社会生活规律,年轻人外出打工,以往音乐会利用农闲时节传承新人扩大队伍的传统也就难以为继了;外出打工的年轻人接触到了城市文化,受其影响,他们对家乡传统文化的亲近感也在逐渐淡漠;音乐会在传统上是义务服务村民的,可在“等价交换”的市场经济环境下,肯常年尽义务搭功夫为村民服务的人越来越少了。这些改变颠覆了音乐会旧有的传承模式,眼见着老一辈乐师渐渐逝去,年轻人接续不上来,许多音乐会因此走向了衰落和泯灭的末路。中国音乐研究所在20世纪90年代普查过的那些乐社,估计至少有约一半已经不能正常活动了。
但是在另一方面,传统文化局内人面对不容乐观的传承困境,也在积极地想办法延续自己文化的生命。他们以卓越的创造力,在与现代化社会环境的互动中探索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和走出困境之路。通过他们切实有效的努力,一个个民间乐社得以再续辉煌,甚至中断活动几十年的乐社也重新恢复了生机。冀中音乐会的局内人为努力克服传承危机复兴传统文化所做的卓有成效的努力,体现了传统文化局内人高度的文化自觉意识。一个个走向复兴的民间乐社,也印证着中国传统文化的顽强生命力。
笔者长期从事冀中民间乐社的考察与研究,与许多乐社的乐师们保持着朋友般的持久联系,对他们的传承情况也较为了解。根据长期考察所得,笔者把目前冀中音乐会这一乐种的传承方式分为固守传统的传承、师徒关系的传承、吸收女性会员的传承、吸收本村小学生的传承、校园传承、被拨款养起来的传承等几种类型。本文将对这几种传承模式各自成功的经验、不成功的原因等进行剖析,以为传统民间乐社的当代传承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固守传统的传承方式
冀中音乐会的传统传承方式,在性别上是传男不传女,在人际关系上以亲缘(亲属)和地缘(本村人)传承为主,在时间上以农闲时节为主。在年轻人纷纷外出打工,没有了以往农忙与农闲的季节更替的时候,这种传承方式日渐式微。但在今天,因为某种机缘,仍然有一些民间乐社能够固守这种传统的传承方式,且一定程度地保持了乐社的活力。
雄县韩庄村音乐会早在1993年8月就有乔建中、钟思第、张振涛、薛艺兵等学者两次前来考察,1995年9月他们又应邀为参加“首届中国民间鼓吹乐学术研讨会”的各地学者演出。2016年和2018年,他们还曾经到中央音乐学院和台湾的一些大学演出,是一个知名度较高的乐社。这个乐社目前仍然固守“传男不传女”的传统,由清一色的男性乐师构成。在会长解秋路、李法通等人的勉力维持下,现在这个乐社共有老、中、青乐师近四十人,还有固定的活动场地“菩提寺”,整个乐社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在其他同类固守传统的乐社纷纷走下坡路的时候,为什么它却能够维持并发展下去?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家族势力的强大和文化传统的悠久。韩庄村音乐会以亲缘关系作为主要传承方式,解姓族人占了乐社成员的半数左右,因此村里有“解半会”的说法,其他乐社成员之间也都有这样或那样的亲属关系。家族传承在今天能够维持,家族势力的强大是一个重要因素,许多人连续几辈人都在会里,如会长解秋路,他太爷解东洲、爷爷解福恩、父亲解永祥,以及兄弟子侄全都在会。这种传统是非常强大的,如果家中的男孩不在会,整个家族都会出来作说服工作,后生晚辈岂敢不从。在这方面易县神石庄村是个相反的例子,村里的四个大姓原来各有一道音乐会,各自伺候本宗族的各种仪式,呈现出“家会一体”的特点。可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宗族势力的衰弱,四道音乐会今天已经全不见了踪影。
二是会中的长者说话有权威,坐得住镇,能够制约晚辈一些有违传统的想法与做法。这就保证了乐社不会因为一些不同意见造成内部的纷争,这些纷争往往是民间乐社解体散伙的原因。比如韩庄村音乐会的年轻人也有参与民间丧事时要适当收费,以补偿自己误工收入的想法。可这些想法在会长解秋路、李法通等人看来就是背离传统,离经叛道,一句“我们只要死不了,传统就不能改”就把年轻人的想法堵了回去,再也不敢有非分之想,遇到民间丧事还要尽可能地赶回来义务参与。
三是与一般常年在外打工者不同,韩庄村的年轻人大多以种红薯致富,农忙时节他们在外村承包土地日夜劳作固然辛苦,但仍然有农忙与农闲的更替,这就有了在农闲时节集中时间学习乐器演奏的机会。每到农闲时节,音乐会的老人就会组织村里的年轻人韵唱工尺谱,进行各种乐器演奏的学习。总的来说这种传承方式与传统社会差别不大。
雄县常庄村音乐会虽然势力不如韩庄村音乐会强大,但是也基本上保持了家族传承为主、传男不传女的传统传承方式。近些年来,这个会有几个对家乡传统音乐有责任心的年轻人入会,并逐渐撑起了会里的各种事务。这些年轻人虽然多在城里打工,但是因为村落地处县城边缘,大家可以每天都回家,晚上聚在一起学习音乐会的韵谱与演奏。虽然传统的农忙、农闲的季节更替被打破了,但是年轻人每天晚上的相聚有效地弥补了这一变化给音乐会传承带来的不利影响。
二、师徒关系的传承方式
这里所说的“师徒关系传承”,是指打破音乐会传统的地缘(本村人)关系传承方式,采取带外村的徒弟,以有别于传统会社的方式进行人员的跨村落自由组合,并以盈利为目的的一种传承方式。以这种方式传承和组合的笙管乐组织,以天津市郊和廊坊市郊较为多见。这样的民间组织虽然有时仍然称之为“音乐会”,但是其传承方式、组织构成、行为目的已经与惯常的公益性音乐会有了较大距离,而从文化属性上更接近于冀中一带另一种盈利性民间器乐组织——“吹打班”。
传统的音乐会传承方式是以地缘(本村人)传承为主的,乐师们很少对外村的人传授本会的音乐。当然村落之间也有音乐文化的传承。如果有的村落想来拜师学习本村的音乐,那要以非常隆重的方式,郑重其事地拜师,并世世代代奉所拜师的音乐会为“师傅会”,自己则要谦称为“徒弟会”。“徒弟会”在学成后,每年的逢年过节都要来“师傅会”拜会见礼。
而师傅跨村落带徒弟,师徒好友结社相聚以艺盈利的组织,却是在以乐社之名行乐班之实。音乐只是挣来衣食、养家糊口的手段,他们从来就没有把自己的音乐神秘化,甚至以密码的方式进行“防伪”的举动。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的罗汉音乐会,因在历史上与“罗汉会”共生而得名。近些年罗汉会的表演日渐稀落,但音乐会却因民间丧事等仪式活动的实际需要一直存续下来了。这个乐社的成员由芦台镇多个村落的乐师组成,其成员之间多为师徒关系。乐社里最老的陈焕章师傅目前已经近90岁,仍然时常下场吹管子。目前,会里的主事者周百顺会长徒弟众多,又肯为会里的事务操心出力,在会里非常有威望。这个乐社约有20人,是这一带远近知名的职业艺人群体,大约每个月要应白事20多场,几乎每天都在白事上演奏,每个工(半天)有大约150元左右的收入。由于长期职业性的锻炼,这些乐师大多是多面手,笙管笛锣鼓板铙钹样样拿得起来,高手云集,技艺超群。
廊坊市的“小高禅乐社”,其核心组织者是廊坊市安次区后屯村的高建忠乐师。他本是后屯村音乐会的成员,精通音乐会各种乐器的演奏、丧事仪轨、经文念唱等。出于兴趣爱好,他还游走于附近及京津地区许多民间乐社,通过交流习得了更多的音乐会曲目。随着自己文化积累的逐渐加深和声誉的扩大,廊坊市郊的许多年轻人都前来拜他为师学习笙管乐的演奏,徒弟日渐增多。几年前以他为首,聚集徒弟、朋友多人,成立了“小高禅乐社”,在廊坊市区和市郊农村一带从事经营性的音乐演奏、经文念唱活动。这个乐社的传承及经营性表演活动,与音乐会传统的地缘(本村人)关系传承方式及非盈利的公益性宗旨已经完全不同了。
三、吸收女性会员的传承方式
在华北一带农村,年轻男性外出打工是一种普遍现象,家里只剩下“九九三八六一部队”,即老人、妇女和孩子。在大量年轻男性出走的情况下,音乐会的传承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为了使本村的音乐会能够传承下去,以往“传男不传女”的老规矩不得不被打破,各村的音乐会纷纷吸收在家妇女入会进行学习。对于这种现象,有的学者认为是由于当代女性社会地位提高而造成的,但笔者认为这更多是由于传统的传承方式在当代遇到危机情况下的无奈选择。
较早这样做的乐社,如安新县的赵北口村音乐会,这也是一个较早为学界所关注的乐社,1993年7月张振涛等人就曾对赵北口村音乐会进行过考察。到了新世纪之初的2001年,随着该音乐会老乐师的过世,传承新人的问题显得越来越突出,年轻的小伙子都在外面打工,于是就把许多五十岁左右的在家妇女吸收到了音乐会里来。这些新入会的大妈们虽然年纪大了一些,但是她们时间充裕,经过几年的学习,就撑起了音乐会的半边天。女乐师宋书苓出生于1953年,于2001年入音乐会学习韵谱和吹笙,现在是音乐会的主力乐师,2017年被评为保定市级非遗传承人。她还曾经在2015年10月去中央音乐学院教研究生韵唱工尺谱,受到了师生们的欢迎。
亚古城村是紧邻雄县县城东南侧的一个村子,村里的音乐会是这个县于2008年6月以“雄县古乐”名义共同进入国家级非遗名录的四个乐社之一。这个音乐会的会长史军平是国家级的非遗传承人,他头脑灵活,看到自己的音乐会后继无人,脑瓜一转计上心来,到聚在一起跳广场舞的大妈那里,说动了一群一早一晚以跳广场舞为乐的大妈们入会学习。他和吴保君两位乐师拿出孙武子训练女兵的认真劲儿,对这些大妈严格要求,进行全天候的严格训练(这些赋闲在家的妇女有的是时间),几年后她们中的多数就出落成了非常优秀的民间乐师。史军平带领她们参加了“第五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2018年中国民族民间音乐周”“雄安新区民间音乐赴台交流”演出,中央音乐学院、国家大剧院、台湾艺术大学等都留下了他们展示和演出的足迹,乐社的声誉也在一天天扩大。
类似的情况还有涞水县的南、北高洛村,徐水县的南城村,雄县的北大阳村,高碑店市的南虎贲驿村等许多村落的民间乐社。大量的女性入音乐会学习,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音乐会的传承危机,或如亚古城村音乐会那样彻底解决危机,再次走向辉煌。
四、吸收本村小学生入会的传承方式
因社会生态的改变而遇到传承危机后,许多民间乐社都把解决传承难题的希望转到了本村在读小学生的身上。小学生多为走读生,课业学习的压力也相对较小,因而有精力在学校学习的内容之外再学一些其他东西。在吸收小学生入会解决传承难题方面,有相当多的乐社作得非常成功。
安新县端村音乐会的省级非遗传承人田炳辉为了传承自己的音乐会,起初每天到了村中小学下课的时候,就赶到校门口去接愿意参加音乐会学习的学生。他在自己家收拾出一间房子,专供孩子们做作业,做完作业再组织他们学习韵谱和演奏乐器。这些事情告一段落后,在县城附近打工的小学生们的父母也下班回家了,学生们这才各自回家。田炳辉的家实际上成了小学生的课后托管班,他的做法既解决了学生放学后家长因尚未下班无法照顾的后顾之忧,又使得孩子们在文化课学习之外多学了一门传统音乐技艺,音乐会的传承危机也得以有效解决。
后来田炳辉又琢磨出了孩子们自己管理自己的一套办法,他请一些具有领导能力的孩子做组长,实行学习上的“自治”。孩子们都是成长之中的有灵性的个体,一旦把他们引导到传统音乐学习的这条路上,他们就会自动地探索和寻找适合于他们的学习方式。比如,以前的老乐师带新学员,在学习韵谱时都是师傅一遍又一遍地对口教唱,费时费力。今天小学生们利用手机的录音功能把师傅的韵唱和演奏录下来,可以随时反复地听和学,省却了师傅的重复劳动;以“小先生”的方式,由“闻道在先”的孩子带刚刚入会学习的孩子,实现小学生之间的互教互学,也是他们探索出来的好方法,孩子们之间的交流往往比成人教孩子沟通得更容易,学习效率也更高。
安新县的圈头村音乐会利用一所闲置的院落,专门为本村的小学生入音乐会学习而办起了一个传承基地。保定市级的非遗传承人夏满军、夏广田等人为了解决因在北京做生意而不能天天给孩子们上课的难题,他们利用QQ的视频聊天功能,把聊天的画面投影在大屏幕上,以这种方式实现了远程教学。每天孩子们下学后聚到音乐会的传承基地,先由守家在地的音乐会成员张国振老先生陪孩子们做完学校留的文化课作业,然后按照预定的时间实现北京——安新县圈头村的视频连线,由夏满军、夏广田等乐师对孩子们的工尺谱韵唱和乐器演奏进行在线指导。在孩子们的寒暑假等时间比较集中的时候,夏满军乐师则牺牲自己做生意赚钱的时间,回到村里为孩子们进行面授。在这样远程教学与集中面授相结合的教学方式下,村里的一批孩子迅速地成长为新一代音乐会乐师。
徐水县城附近的迁民庄村南乐会,在20世纪50年代曾以“跃进吹歌会”进京演出的方式而天下闻名。在新的社会环境下,迁民庄村南乐会的骨干乐师何成等人办起了南乐会的传承班,面向小学生传承南乐会的音乐文化。与安新县端村、圈头村不同的是,端村、圈头村都是由老乐师义务地组织小学生入音乐会学习,而迁民庄村南乐会的传承班却是要向参加学习的孩子们收费。县城里学习西洋乐器的孩子,每上一节课要交大约100-300元的学费,相比之下,迁民庄村南乐会的民间乐师觉得如果免费教孩子们就有些吃亏了。虽然是收费,但是由于与学习西洋乐器的单人授课不同,南乐会的器乐学习是集体授课,因此收费较低廉,孩子的家长觉得还是能够接受的。
定州市子位村的吹歌会(南乐会)的情况与迁民庄村南乐会大致相同。这个项目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王如海、张占民及其他许多乐师也都面向小学生办起了收费性质的传承班。
无论是收费还是免费,民间乐社以小学生为对象进行文化传承,一开始家长们普遍都有怕孩子因入音乐会学习而耽误了文化课的担忧,因此在起步阶段往往都是较为困难的,要做大量的说服工作,甚至以解决家庭生活的某种实际需要为交换条件,才能动员一些孩子入会学习。但是当家长们看到先期入会学习的孩子并没有因为学习音乐专长而耽误文化课,甚至这些孩子的文化课考试成绩往往还要优于一般孩子的时候,家长们的顾虑就被打消了,其态度也转变为积极支持。再加上孩子们之间看样学样的攀比心态,入会学习就成了一种孩子们争相效仿的行为。
孩子们进入初中学习以后,因为路途较远,许多孩子都要住校,再加上课业负担的加重,一般入音乐会学习过几年的孩子,这时就不能正常参加音乐会的活动了。面对这种情况,一般的乐社都以从低年级小学生里不断续招新学员的方式继续培养后继人才。这些曾经参加过音乐会学习的孩子,由于早年的文化熏陶,家乡的传统音乐都会在他们的人生历程中打下深深的烙印,无论是将来走出村落还是重新回归,他们都将是家乡传统音乐的衷心热爱者或积极参与者。
五、校园传承方式
在上级号召“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非遗进校园”的形势下,许多农村的中小学校也开始了这方面的尝试。有的学校把非遗传承人请到学校里为学生们进行展示和表演,有的学校以校本课程的方式向学生们介绍本地的乡土文化,还有的学校开设了传承班,深入传授当地某一品类的乡土文化。
河北省涞水县南、北高洛村的音乐会,从20世纪80年代末就受到了英国学者钟思第,中国艺术研究院乔建中、张振涛、薛艺兵等人的关注,钟思第和张振涛还在这里进行了长达十几年的驻村考察。2003年4月,又有亚欧二十一个国家的传统音乐学者前来考察,中央电视台等媒体也曾做过报道。在名声远播的情况下,这里的音乐会在2006年就进入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但无论是南高洛还是北高洛,两个村子的音乐会都在传承上遇到了难以为继的困境,他们也曾改变观念吸收村里的妇女入会,但是最后的效果并不太理想。
2018年3月,涞水县教育局提倡下属各个学校搞“特色办学”,北高洛村的书记闫瑞才也早就想在村里的小学传承本村的音乐会,以彻底解决音乐会后继无人的问题。在涞水县教育局、文旅局、北高洛村小学和北高洛村党政班子达成共识的前提下,他们开始了在北高洛小学传承传统音乐的实验。
为了实现在学校里传承音乐会的目的,音乐会里委派了三位市级非遗传承人头管乐师闫喜忠、笙乐师闫成和笛子乐师闫文到学校任教,北高洛村小学的李全宝校长还帮助他们根据音乐会的曲目编写了教材。农村的学校,自己安排课程的自由度较大,学校里每周二、四下午安排给全体学生各上三节传统音乐课。除了上课之外,学生们还在课外活动及家中进行个人练习。
北高洛村小学不大,目前仅有一至五年级,一共才有南、北高洛村的118名学生,13名老师(其中两位校领导)。一开始搞“特色办学”时人们是有畏难情绪的,在家长那里,许多人恐怕自己的孩子因为学习传统音乐而耽误了文化课的成绩;在学生那里,有的孩子怕因为学不会而被人耻笑;在老师那里,也有传统音乐是否真正能够在学校推广得开的疑虑。
为了使“特色办学”的意图得到彻底落实,李全宝校长号召学校的全体领导老师们要与各班的学生们一起进步,要求每个老师都学一件乐器,给学生们做出榜样。担任教学任务的三名民间乐师把传授传统音乐看作是一种神圣的责任,没有教学经验的他们经常聚在一起,琢磨怎么教学生们韵唱工尺谱和演奏乐器。他们不辞辛苦风雨无阻,到了上课的时间,无论多忙也要放下手中的活计按时赶到学校。根据学生们各自的兴趣,分为笙、管、笛三个班,由三名民间乐师分别授课,先教学生们韵唱工尺谱,待曲谱韵唱熟练后,再上手学习乐器演奏。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北高洛村小学的传统音乐学习已经见到了初步成效,每个老师和同学都掌握了至少一件乐器的基本演奏技能;音乐会的笙管乐曲牌,学生们已经学会了【翠花开】【醉太平】【青天歌】【鹅郎子】【琵琶论】【金字经】等六首;打击乐套曲【粉蝶大套】,学生们也已经学会了前三身。除了民间乐师的引导,学校的老师们也边学边教,学生们之间也互帮互学共同进步。一年多来的实践证明,学生们学习民间音乐不但不耽误文化课的正常学习,还会对文化课的学习起到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作用,这解除了家长们的一份担心,使他们对孩子音乐学习的态度由疑虑转为支持。
北高洛村小学在学校传承传统音乐的努力还得到了上级领导的大力支持,县教育局、文旅局分别为他们解决了乐器、服装、民间乐师的辅导费用等方面的问题。随着学生们表演技艺的逐渐成熟,近来他们还多次参加县、市以至国家级的大型展演活动,社会影响逐渐扩大。
此外,安新县关城村音乐会的年轻乐师张贺新和会里的保定市级非遗传承人张小庆,从2019年3月开始在村小学里进行音乐会校园传承的实验,还利用课外活动、周六日及暑假的时间,由民间乐师对孩子们进行义务辅导。在张贺新、张小庆的热心付出和孩子们的刻苦学习之下,这些小学生进步很快,现在有的孩子已经能够参加音乐会的出会活动了。
诚然,民间音乐会的校园传承有成功的例子,也有不太成功的情况。
雄县米黄庄村音乐会通过与当地小学的领导协商,共同决定在这个小学的五年级进行音乐会传承的教学。学校里每周拿出两节课的时间,由音乐会的头管乐师程志通教孩子们学习音乐会的韵谱和乐器演奏,辅之以课外的练习。但是民间乐师没有接受过专门的教育教学训练,缺少教学经验,再加上家长们对于学习民间音乐是否会干扰文化课学习的疑虑一直未打消,至今这个传承班仍然还在坚持音乐学习的孩子已所剩无几。米黄庄村音乐会校园传承的效果不彰,可能还有行政力量支持不够的原因,北高洛村音乐会的校园传承有村、乡、县各级领导强有力的行政、财力支持,可在米黄庄村只是学校和音乐会之间的合作。
本土的学校传承本土的文化,本来是责任所在。但是许多学校对此认识不够深刻,没有传承本土文化的责任担当,在行动上也就没有动力。在安新县同口村音乐会,会长韩峰、头管乐师任伯五组织村里的孩子们入会学习,几年来成效不小。但是音乐会的活动往往和学校的工作安排在时间上有冲突,于是会里就联系学校,想以“非遗进校园”的方式联合在一起进行民间音乐的校园传承。但是学校方面对这件事情不太感兴趣,总觉得这是分外之事,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
六、被拨款养起来的传承方式
河北省固安县的屈家营村音乐会是冀中音乐会这个大乐种中较早为人所知的一个乐社,在村里关心音乐会命运的林中树老先生的不懈奔走下,1986年3月28日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乔建中老师带领考察队前来这个村进行实地考察,这个乐社从此声名远播。时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赛福鼎、全国政协副主席司马义·艾买提、河北省委副书记李文珊、文化部长周巍峙、文化部副部长高占祥、音协主席李焕之、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黄翔鹏、中国音协名誉主席吕骥、中央音乐学院老院长赵沨等各级领导和专家学者都曾经来屈家营村音乐会进行过考察、观摩。
随着名声的扩大,这个乐社获得了社会各方面越来越多的物质帮助,修起了通往村里宽敞笔直的乡间公路,盖起了全国农村绝无仅有的音乐厅。从2013年起,这个村作为河北省新农村建设的样板,每年获得国家大约百万元的资助,村里的面貌由此进一步有了改观。
为了支持音乐会的传承,近些年村里规定音乐会的乐师和学员们每天晚上的活动都有40元的补助,平均每人每月1200元,2018年每人补助14400元,一年里仅这方面的支出就有40多万元。由于有了经济动力,屈家营村音乐会由原来的十几人增加到了32人,应该说这种物质刺激的效果是明显的。但在另一方面,音乐会的文化性质却也在这种经济补助的诱导下逐渐改变,原来新学员入会是以兴趣为主要驱动力的,现在则是为了挣得一份钱财。甚至目前就已经出现了有的人只是每天来会里泡一会儿,也不怎么学东西,就为报个到拿一份钱的情况;原来乐社是无偿为村民服务的圣会、善会,现在没有物质的回报再也使不动人了。
最要命的是这种来自上级拨款的资助是临时的,不是永久性的。“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参加会里的活动就要拿报酬的习惯养成了,这种报酬一旦不再有,乐社是否还能继续存续就将成为一个大问题。屈家营村音乐会的会长、国家级非遗传承人胡国庆为此忧心忡忡:“现在就有只拿钱不学东西的人了,明年再不给钱,音乐会还不散了啊!”
七、各种传承方式的比较
冀中音乐会以传男不传女,依靠亲缘和地缘关系发展新人,利用农闲时节学习为特征的传统传承方式,在一些家族势力强大,年轻人在外打工情况不是很严重的村落,仍然具有一定生命力。事实上在目前仍然有一些乐社以传统的方式进行传承,且保持了乐社的活力。但是在更多家族势力衰落,年轻人外出打工,没有农忙与农闲季节更替的村落,这种固守传统的传承方式已经越来越显露出其难以与变化了的社会环境相适应的矛盾,造成了乐社的衰落甚至消亡。
改变音乐会传统的地缘(本村人)传承关系,以带外村的徒弟的方式进行传承,以盈利为行艺目的的传承方式,在天津市郊和廊坊市郊较为普遍。虽然其传承方式、组织构成、行为目的已经与惯常的公益性音乐会有了较大距离而与盈利性吹打班相似,但是这种传承方式适应了当代社会商品经济的等价交换原则,只要民间丧仪对笙管乐有实际需要,且政府部门没有严令禁止的文化政策,这种传承方式就能够得以持续下去。
打破“传男不传女”的老规矩,积极吸纳在家妇女加入音乐会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传承难题,这是冀中地区许多音乐会的普遍做法。虽然这是大量年轻男性外出打工情况下的无奈选择,但确实使得一些乐社避免了走向消亡,甚至使有的乐社再度辉煌。一些村落的老乐师总认为女性入会使得乐社的神圣性减弱,觉得“那阵仗不雅气了”,但是在日益严重的传承危机面前,这种声音越来越弱,大家一致认识到,“不管怎么样,音乐会传下去才是最要紧的”。
吸收本村小学生入会,这些年成了越来越多乐社的普遍做法。这种做法成功的关键,是要有几个甘心为音乐会无偿付出的人,肯拿出相对固定的时间来指导和陪伴孩子进行音乐学习。在一开始时还要想出一些迎合家长及孩子生活实际需要的办法,以赢得家长对孩子学习音乐的支持,打消他们的种种顾虑。一旦这种做法实现了初步成效,得到了家长和孩子的认可,甚至形成一种村落里的新风尚,这条路就算趟开了,从此这种传承方式就踏入了坦途。现在时兴一种“……从娃娃抓起”的说法,音乐会的传承从娃娃抓起也至关重要,有了一茬十几岁的孩子入会学习,就能够保证这个乐社至少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生命力健旺,这是解决音乐会传承难题的治本之策。一个乐社就像一个家庭一样,有了孩子才有未来,没有孩子也就没有了希望。
音乐会进入校园传承,这种做法契合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和教育部印发的《教育部关于在全国中小学开展中华优秀文化艺术传承学校创建活动的通知》等一系列文件的精神。但是在一些地方的具体做法上,却显示出国家文件落实到基层学校时那种力度逐级衰减的无奈。而这种校园传承的方式,离开政府层面的强有力支持,即便是民间文化局内人再努力,往往也难以持久和见到较大成效。我们还应该看到,音乐会这种具有厚重历史文化内涵和丰富民俗文化内容的传统文化形式,在校园进行传承也是有其局限性的,即演唱、器乐演奏的内容学生可以学习,而民间信仰及其仪式、经文诵唱等内容则难以在学校进行传承。校园传承仅仅是把音乐会的音乐这种属于外形的东西继承下来,但其中核心性文化的内容却遭到了遗弃,这是有悖于保护人类文化多样性这个非遗保护最基本、最原初的目的的。
像固安县屈家营村音乐会那样被上级拨款养起来的传承方式,其实是一种饮鸩止渴的办法。这种做法既改变了音乐会的文化性质,又养成了没有钱使不动人的不良习惯。看似是“支持传承”的大量给钱行为,也许就是断送民间乐社文化生命的一道催命符。还好在冀中音乐会这个乐种里,被钱养出毛病来的仅此一例,其严重后果还不具普遍性。这个音乐会已经过世的林中树老先生曾经有一句名言:“钱是惹祸的根苗”,现在上级拨给的钱已经把这个“惹祸的根苗”种下了,2020年以后如果上级不再拨钱,这个曾经万众瞩目、名声远播的乐社,其前途堪忧。
具体到一个乐社究竟采取什么样的传承方式为好,没有标准答案,这要由传统文化局内人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因时因势随机应变地做出自己的最佳选择。众多的民间乐师们普遍都有把自己的文化传承下去的良好愿望,他们也有足够的智慧为自己乐社的未来寻找到一条光明的出路。
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几千年来穿越了朝代更迭、社会动乱、战争洗劫、政治运动的磨难,直到今天仍然生机勃勃。在今天的社会现代化变迁中,相信它也一定能够在与变化了的社会环境的互动中找到自己的生存之道。冀中音乐会的民间乐师们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传承传统音乐的各种方式,既体现了传统文化局内人卓越的创造精神,也昭示着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的光明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