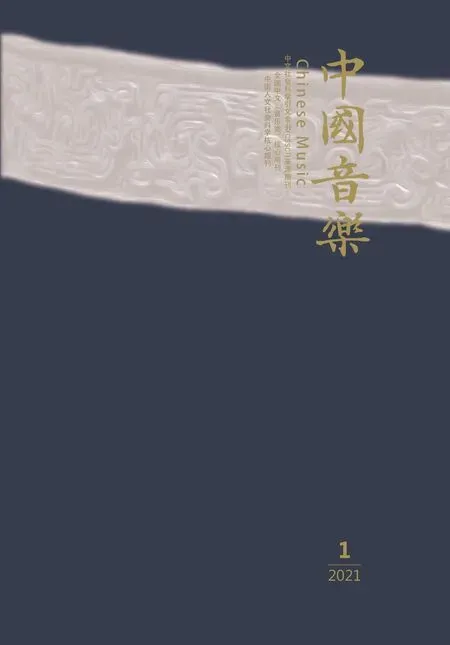艺术经济视角下的宋代“女倡卖酒”
——宋代演艺市场专题研究
一、选题界说
20世纪初,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发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率先提出“唐宋变革说”,认为“唐代是中世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其间包含了唐末至五代一段过渡期”。①〔日〕内藤湖南著,刘俊文编,索介然译:《概括的唐宋时代观》,载《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一卷“通论”,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0页。这一论断广泛影响到我国历史学诸多分支领域,音乐史亦不例外。纵观中国古代音乐史,宋代不仅是一个承上启下的组成部分,更因其特殊的“变革”意义而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黄翔鹏先生著名的“分期学说”,将中国古代音乐的发展历程分为三大阶段,并认为唐宋两代分别属于“中古伎乐”和“近世俗乐”两个不同阶段。②黄翔鹏:《论中国古代音乐的传承关系》,载《传统是一条河流》,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0年,第115-116页。这一观点指出了宋代音乐不同于前代的独特的历史面貌及其定位,可谓涉及“音乐转型”问题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学术见解,为全面认识和评价宋代音乐提供了理论依据。
此后,黄先生在《唐宋社会生活与唐宋遗音》中进一步说明:“安史之乱”以后,随着庄园经济的解体,伎乐活动渐以小型规模向商业繁荣的城市、集镇、庙会等处转移,于是煊赫一时的“大曲”便让位于市肆演出与侑酒活动了。③黄翔鹏:《唐宋社会生活与唐宋遗音》,《中国音乐学》,1993年,第3期,第20-21页。不难看出,将“市肆演出”“侑酒活动”与“烜赫一时的大曲”相对应,意在突显“安史之乱”以后音乐在形式、风格、功能、趣味等方面的显著变化,而这些正是宋代音乐有别于“盛唐之乐”的突出表现。更值得注意的是,黄先生将音乐史的视角投向广阔的社会生活,并辐射至“庄园经济”“商业”“市肆”等经济领域。
杨荫浏先生早在《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第六编中,已多次论及“工商业”“都市”“贸易”等经济因素对宋代音乐发展的影响,以及二者之间的密切联系,如“都市成为民间音乐汇集的中心”、“经济的发展……促进了音乐艺术的发展;繁盛的城市,给音乐活动以广阔的天地”、“酒肆、茶肆、卖糖者也有用器乐或声乐来吸引买客的”等。④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上下册),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年,第275、299、301页。这些论述虽未及充分展开,却为宋代音乐研究奠定了基石,更对笔者产生了重要启发。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探索与积累,宋代音乐研究已成为成果颇丰的热门领域。现状表明,“无论是在研究成果和学者的规模上,还是新视野、新史料和新方法的开拓方面,均呈现出较之以往更为自觉的学科意识和学理思考”。⑤洛秦、康瑞军:《国际化视野下宋代音乐研究的新动向与新思考(2009-2013)》,《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第73页。突出表现为,“叙事”和“阐释”成为关键词,“一方面注重涵括更多样的叙事素材和叙事方式,另一方面则在历史的阐释上下功夫,以宋代音乐一切事像为圆点,运用结构化、静态化的分析手段,阐发其对宋人、对今人、对于国际音乐史学的意义和价值”。⑥洛秦:《再论宋代音乐研究的特征分析与反思》,《音乐艺术》,2017年,第1期,第80页。可以说,宋代音乐研究正以多元的视角、开阔的视野、全面的学理思考,积极推动着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的深化及转型。
受上述研究成果与学术观念的影响,笔者尝试在宋代音乐研究中借鉴艺术经济学的视角、理论及经济史成果,关注“音乐”与“经济”的交叉领域——商业性音乐演艺,并将其视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即“音乐生产”。由文献可知,宋代酒业经营中流行一种以乐妓的音乐演艺作为促销手段的营销方式,名为“女倡卖酒”。作为音乐史与经济史的交集,“女倡卖酒”集中体现出宋代音乐的时代特色,具有较大的研究价值。基于上述,笔者把宋代的“市肆演出”“侑酒活动”置于“经济的发展”“繁盛的城市”等经济基础之中,以“女倡卖酒”为切入点,通过对这一具体而独特的音乐文化现象及其相关“音乐人事”⑦洛秦:《论音乐文化诗学:一种音乐人事与文化的研究模式及其分析》,《音乐研究》,2009年,第6期,第21页。的专题考察,管窥宋代音乐的时代风貌、文化特色,进而探寻其发展、转型的动因及表现,同时亦为中国音乐史跨学科研究作出些许探索。
二、“女倡卖酒”的渊源与契机
“女倡卖酒”之称见于宋人王楙《野客丛书》中“今用女倡卖酒,名曰‘设法’”⑧[宋]王楙:《野客丛书》,郑明、王义耀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16页。的记载。“设法”指“设法卖酒”,是宋代“榷酤”制度的一项措施,其实质便是“女倡卖酒”。⑨钱慧:《设法卖酒:“榷酤”制度影响下的宋代酒店音乐生产》,《音乐艺术》,2020年,第1期,第88页。具体说来,宋代的“女倡卖酒”是一种以乐妓为主体、演艺为手段、经济为目的的具有“音乐-经济”双重属性的“音乐生产”。
事实上,以音乐演艺为营销手段的“侑酒”“卖酒”现象并非始自宋代,早在唐代,酒店中的“音乐促销”已蔚然成风。唐人诗作对此多有反映,王建《夜看扬州市》表现出扬州酒店的彻夜“笙歌”:“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如今不似时平日,犹自笙歌彻晓闻。”贺朝《赠酒店胡姬》描绘了酒店中“弦管锵锵”的场景:“胡姬春酒店,弦管夜锵锵。”此外,更有《北里志》中浓墨重彩的“饮妓”群体,虽籍属教坊却不以从事歌舞表演为主业,而是供奉于酒席之间。⑩钱慧:《宋代酒业经营中的音乐促销活动探析》,《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2014年,第3期,第89页。可以说,唐代酒店的“音乐促销”已为宋代“女倡卖酒”做了充分的准备,但前者在形式、范围、程度等方面,较之后者尚有相当差距,不可同日而语。
“女倡卖酒”除受前代侑酒传统的影响外,还得益于“榷酤”制度下“设法卖酒”的施行。“榷酤”是我国古代的酒类专卖制度,其渊源可追溯至西汉,经历代沿革至宋尤盛。宋代的“榷酤”繁复而严苛,“设法卖酒”便是其中别具特色的一项具体措施。王栐在《燕翼诒谋录》中记述了“青苗法”期间“设法卖酒”的开展及由来:
新法既行,悉归于公,上散青苗钱于设厅,而置酒肆于谯门,民持钱而出者,诱之使饮,十费其二、三矣。又恐其不顾也,则命娼女坐肆作乐以蛊惑之。小民无知,争竞斗殴,官不能禁,则又差兵列枷杖以弹压之,名曰“设法卖酒”。此“设法”之名所由始也。⑪[宋]王栐:《燕翼诒谋录》,诚刚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3页。
照此说法,“设法卖酒”始于“熙宁变法”,在“青苗法”实施期间得到推广。结合经济史研究成果⑫李华瑞:《宋代酒课的征收方法析论》,《河北学刊》,1993年,第2期,第94页。可进一步认为,“设法卖酒”大约出现于仁宗朝,至神宗朝影响渐广。
《清波杂志》记载了“熙宁变法”及其以后“设法卖酒”的情况:“朝廷设法卖酒,所在吏官,遂张乐集妓女以来小民……官卖酒,旧尝至是时亦必以妓乐随处张设,颇得民利。”⑬[宋]周煇:《清波杂志》,刘永翔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236页。可见,因官方组织“娼女坐肆作乐”,而使“张乐集妓女”“以妓乐随处张设”成为“官卖酒”约定俗成的手段和套路,甚至引发民众斗殴等恶性事件。
“设法卖酒”至南宋更加普及、完善,势头也更为强劲。《梦粱录》有载:“自景定以来,诸酒库设法卖酒,官妓及私名妓女数内。”⑭[宋]吴自牧:《梦粱录》,载[宋]孟元老等著:《东京梦华录(外四种)》,周峰点校,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第303;255页。元人记述南宋官库时也写到:“妓女数十,设法卖酒,笙歌之声,彻乎昼夜。”⑮[元]俞希鲁:《至顺镇江志》,杨积庆、贾秀英、蒋文野、笪远毅校点,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544页。不难看出,至少自北宋后期至南宋末年,即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至理宗景定年间(1260-1264),近两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设法卖酒”政策始终贯行。⑯同注⑩。“设法卖酒”的实施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女倡卖酒”所产生的经济、文化双重效应,而政府对“设法卖酒”的推行也成为“女倡卖酒”有力的制度保障,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女倡卖酒”的普及还少不了发达的酒业经济作为前提和基础。宋代酒风大盛,酒艺精湛,在我国酒史上据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就酒店的数量及种类而言,北宋开封“正店七十二户,此外不能遍数,其余皆谓之‘脚店’”⑰[宋]孟元老撰,伊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笺注》(全二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76页。;南宋临安则不仅有“户部点检所十三库”,还有“市楼之表表者”十数家⑱[宋]周密:《武林旧事》,载[宋]孟元老等著:《东京梦华录(外四种)》,周峰点校,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第355、407页。,更有次一等“兼卖诸般下酒,食次随意索唤”的各色杂类酒店⑲[宋]吴自牧:《梦粱录》,载[宋]孟元老等著:《东京梦华录(外四种)》,周峰点校,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第303;255页。。宋代酒店虽名目繁多、等次有别,但总体上划分为官、私两大类,前者是由政府或军队直接掌管、经营的酒业机构,如北宋的部分“正店”和南宋的众多“官库”;后者则包括附属于官营酒店的各类民办性质的“脚店”“市楼”“拍户”等。因性质、级别、所属关系不同,官私酒店在规模、档次、环境、经营方式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然而无论官营还是民办,其大多对“女倡卖酒”青睐有加,从而吸引大量乐妓进入市场流通、参与市场竞争,一时成为城市经济、文化生活中一道新颖而靓丽的风景。
宋代为数众多的乐妓活跃于勾栏、酒店、茶坊、妓馆等演艺市场,通过市场流通获得经济效益、实现自我价值,其自由程度与谋生机会大大超越前代。而林立于街市坊巷的各类酒店,因群妓云集、众伎纷呈而逐渐由传统商品市场转型为新型演艺市场,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音乐的商品化、市场化、世俗化进程。正是这种转变,促使宋代音乐出现了有别于以“烜赫一时的大曲”为标志的“盛唐之乐”的显著特征。据此,可将“女倡卖酒”作为考察和理解宋代音乐及其时代风貌、文化特色的一扇窗口和一把钥匙。
三、“女倡卖酒”的类型及特色
由北宋至南宋,“女倡卖酒”不断成熟、普及且呈现多元化趋势。经分析发现,“女倡卖酒”主要包括既特色分明又互为补充的三种类型,笔者依文献所载称其为“坐肆作乐”“沿街游艺”“打座而歌”。通过对这三种类型的梳理和解读,有助于把握“女倡卖酒”的总体面貌及其特色,亦可从一个侧面管窥宋代音乐的时代风貌及历史意义。
(一)“坐肆作乐”音乐生产
“坐肆作乐”出自前引王栐之言:“置酒肆于谯门……命娼女坐肆作乐以蛊惑之”,“坐肆”表示场所明确、地点固定,“作乐”则包括演奏、演剧、演唱等演艺形式。作为一项经济措施,“坐肆作乐”由官方组织、受制度保障,因“青苗法”期间施行“设法卖酒”而兴起,是“女倡卖酒”的基本类型。
苏轼在反对“青苗法”的《乞不给散青苗钱斛状》中提及:“官吏无状,于给散之际,必令酒务设鼓乐倡优。”⑳[宋]苏轼:《东坡七集》,明成化吉州刻、缪荃孙批校本,清光绪戊申重刊本,第15页。《清波杂志》记载了北宋时潭州浏阳的情况:“方官散青苗时,凡酒肆食店,与夫俳优戏剧之罔民财者。”㉑同注⑬。可见,官方在“给散青苗钱”时,“鼓乐倡优”“俳优戏剧”等音乐演艺为酒务、酒肆必不可少的卖酒措施。
除“鼓乐”“戏剧”外,“笙歌”“管弦”等更为常见。宋元话本《赵旭遇仁宗传》借引诗词再现了汴京大酒店樊楼中豪奢的宴乐场景,《鹧鸪天》词云:“城中酒楼高入天,烹龙煮凤味肥鲜。公孙下马闻香醉,一饮不惜费万钱。招贵客,引高贤,楼上笙歌列管弦……”㉒程毅中辑注:《宋元小说家话本集》(全二册),济南:齐鲁书社,2000年,第592页。能让公孙贵客们“一饮不惜费万钱”的,恐怕绝不仅是美酒佳肴。
官库乐妓中不乏容貌出众、伎艺超群者,有些甚至被载入史册。《梦粱录》卷二十“妓乐”生动地展现了临安官库“卖酒”乐妓的绰约风姿和精妙伎艺:
自景定以来,诸酒库设法卖酒,官妓及私名妓女数内,拣择上中甲者,委有娉婷秀媚,桃脸樱唇,玉指纤纤,秋波滴溜,歌喉宛转,道得字真韵正,令人侧耳听之不厌。㉓同注⑭。
这段文字后详细列有三十多位参与“诸酒库设法卖酒”的“官妓”和“私名妓女”名号,如金赛兰、范都宜、唐安安、苏州钱三姐、鼓板朱一姐、婺州张七姐等,并称“后辈虽有歌唱者,比之前辈,终不如也”。㉔同注⑭。不难想见,所列官私乐妓皆为当时的“知名歌手”,或因服务于官库而声名大噪。
随着“坐肆作乐”的市场化、多元化,乐妓除从事专门性的音乐演艺之外,还兼及揽客、侑樽、伴宴等文娱性附加服务,并逐渐形成行业惯例。南宋时临安官库中出现一种大受追捧的特色演艺项目,时人谓之“点花牌”:
若欲赏妓,往官库中点花牌,其酒家人亦多隐庇推托,须是亲识其妓,及以利委之可也。㉕[宋]耐得翁:《都城纪胜》,载[宋]孟元老等著:《东京梦华录(外四种)》,周峰点校,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第81页。
此郡风流才子,欲买一笑,则径往库内点花牌,惟意所择,但恐酒家人隐庇推托,须是亲识妓面,及以微利啖之可也。㉖同注⑭,第203;255页。
饮客登楼,则以名牌点唤侑樽,谓之“点花牌”……然名娼皆深藏邃合,未易招呼……往往皆学舍士夫所据,外人未易登也。㉗同注⑱,第406;407页。
由“若欲赏妓”“欲买一笑”“点唤侑樽”可知,“饮客”前往官库并不仅限于酒食消费,对乐妓及其音乐演艺往往更加情有独钟,真可谓“醉翁之意不在酒”。“点花牌”的规模、形式、品质及其不可替代的“附加价值”,一定程度上成为官库“优越”性的重要标志。也正因如此,“点花牌”才成为官库音乐生产的特色品牌及专有名称。
“点花牌”的高明之处莫过于“点”,官库虽以此为“招牌”和“噱头”,但并非所有“饮客”都有机会和资格“惟意所择”,通常情况下“酒家人隐庇推托”或“名娼皆深藏邃合,未易招呼”。这表明,乐妓及其音乐生产总体上属于“稀缺资源”,必须采取“隐庇推托”“深藏邃合”的方式对消费者进行限定和分流,以缓解供求不平衡的问题。由此,官库音乐生产的商业性质及市场化程度足见一斑。同时也可看出,“女倡卖酒”至南宋已成为一种文娱风尚和消费习惯,尤其在“风流才子”“学舍士夫”群体中形成了特定的“消费者偏好”。这无疑是官库营销策略与市场实际需求之间有机互动、充分协调的结果。
相较于官库,私营酒店品类芜杂、良莠不齐,因而音乐生产形式显得更为多元。在临安著名的熙春楼、三元楼、五间楼、赏新楼、花月楼等“市楼之表表者”中,音乐生产的规格及排场丝毫不逊于官库,甚至达到“每处各有私名妓数十辈,皆时妆服,巧笑争妍……歌管欢笑之声,每夕达旦”的程度。㉘同注⑱,第406;407页。此类酒店中“女倡卖酒”已为常态,不仅“俱有妓女,以待风流才子买笑追欢耳”,其夜市更是热闹非凡:“向晚灯烛荧煌,上下相照,浓妆妓女数十,聚于主廊槏面上,以待酒客呼唤,望之宛如神仙。”㉙同注⑭,第203;255页。实力雄厚的私营大酒店在官库的影响下广泛开展“坐肆作乐”,并将其由原先的一项经济措施,发展为演艺市场中备受青睐的音乐生产。
相比之下,数量可观的中低档酒店则是另一番光景,甚至提供色情服务。《都城纪胜》提到一种惯以“红栀子灯”为标记的“庵酒店”:“有娼妓在内,可以就欢,而于酒阁内暗藏卧床也。门首红栀子灯上,不以晴雨,必用箬盖之,以为记认。”㉚同注㉕。虽然这种情况不可否认,但严格来说并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音乐生产,应作为一种“异化”现象另当别论。
“坐肆作乐”兴起于“熙宁变法”时期,因受经济制度的保障而表现出较强的制度性、稳定性、常规性特点。它以酒店为固定生产场所,以演唱、演奏、演剧为主要生产方式,属于“女倡卖酒”最基本、典型的一类。
(二)“沿街游艺”音乐生产
除在酒店开展“坐肆作乐”之外,“女倡卖酒”还包括一种“行乐”类型。官库“开沽”是官方卖酒的重大仪式活动,由点检所负责筹办,每年定期举行,规模盛大、影响深广。以迎取、宣传官酿新酒为目的的集体性音乐演艺,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头戏,因其以乐妓在街市上游行的方式开展音乐生产,故称“沿街游艺”。“沿街游艺”流行于南宋,相关记载多见于描述临安民俗风情的笔记史料之中。作为“开沽”仪式的重要部分和中心环节,“沿街游艺”的市场效应远非“坐肆作乐”所能企及,可视为“女倡卖酒”的“非常态”类型。
早在北宋,开封酒店照例于四月和八月统一出售新酿酒品。卖酒活动借助佛诞日和中秋节的节庆氛围,常出现“市井一新”“市人争饮”的场面:
四月八日,佛生日……在京七十二户诸正店,初卖煮酒,市井一新。
中秋节前,诸店皆卖新酒,重新结络门面彩楼,花头画竿,醉仙锦旆,市人争饮,至午未间,家家无酒,拽下望子。㉛同注⑰,第749、814页。
北宋的卖酒习俗延续至南宋,并进一步发展为盛极一时的“开沽”仪式。《都城纪胜》有言:“天府诸酒库,每遇寒食节前开沽煮酒,中秋节前后开沽新酒”㉜同注㉕,第81;81-82页。;《武林旧事》亦载:“户部点检所十三酒库,例于四月初开煮,九月初开清”㉝同注⑱,第355页。。中秋前后的“开沽”较之春季往往更胜,甚至出现“都人观睹”㉞同注⑭,第146;133-134;133页。的盛况。
按照惯例,“开沽”仪式须召集大量乐妓参加游艺表演,在“迎引”新酿酒样的同时开展宣传促销。“开沽”仪式自清晨开始,“先至提领所呈样品尝,然后迎引至诸酒所隶官府而散”㉟同注⑱,第355页。,身着盛装的官私乐妓按身份、形象分为三等,以器乐、杂戏、散乐等音乐演艺,为刚上市的官酿新酒大造声势。文献中对“沿街游艺”的豪华阵容及轰动效应着墨甚多:
各用妓弟,乘骑作三等装束……前有小女童等,及诸社会,动大乐迎酒样赴府治,呈作乐,呈伎艺杂剧,三盏退出,于大街诸处迎引归库。㊱同注㉕,第81;81-82页。
官私妓女,新丽妆着,差雇社队鼓乐,以荣迎引。……官私妓女,择为三等……各执花斗鼓儿,或捧龙阮琴瑟……追欢买笑,倍于常时。㊲同注⑭,第146;133-134;133页。
杂剧百戏诸艺之外,又为渔父习闲、竹马出猎、八仙故事。及命妓家女使裹头花巾为酒家保……库妓之琤琤者,皆珠翠盛饰,销金红背,乘绣鞯宝勒骏骑……所经之地,高楼邃阁,绣幕如云,累足骈肩,真所谓“万人海”也。㊳同注⑱,第355页。
“沿街游艺”是“开沽”中最受欢迎和瞩目的部分,每每引发“都人观睹”“累足骈肩”“追欢买笑,倍于常时”的消费热潮和节日狂欢,一度成为临安最具关注度和影响力的文化盛事之一,经济效益和社会影响皆不可小觑。
如果说,官库的“点花牌”属于“稀缺资源”的话,那么,“沿街游艺”就是实实在在的“全民福利”。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场声势浩大的全民性文娱盛宴中,原本以供奉官府衙署为本职的官妓、乐官等身份性乐人,暂时脱离国家制度和社会道德的规范及束缚,高调进入士庶大众的娱乐生活和消费视野,在万众瞩目中“闪亮登场”,华丽转型为“光环效应”和“眼球经济”的制造者和代言人。可以说,“沿街游艺”的乐妓在光天化日之下游走,超越了审美、道德及日常生活规范,与利益结合为一种民俗现象,进而化为一个时代的消费符号。㊴柳春雨:《宋代妓女若干问题研究——立足于身体史的考察》,2011年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第97页。
与“坐肆作乐”相比,“沿街游艺”超越了固定酒店的场所限制,将“女倡卖酒”的规模及影响拓展到更高程度。文献所示,《梦粱录》《武林旧事》分别以“诸库迎煮”和“迎新”为标题,对官库“开沽”仪式作了较为详尽的记述,而且还将其篇目位置与记录当时重要节日和民俗风尚的内容相并列。可见,宋代官方酒库所举办的大型游艺促销已突破了一般性商业营销的范畴,而升级为一种影响深广的城市文娱与民俗活动。㊵同注⑩,第90页。
乐妓参加“沿街游艺”不仅风光无限,而且有利可图,可谓名利双收。在社会商品化程度全面提升的宋代,投身演艺市场从事商业性音乐生产,已成为乐妓的重要谋生手段和职业追求。事实上,乐妓通过“沿街游艺”不仅能获得极大的自我实现及心理满足,还能得到官方丰厚的物质奖励,如“犒赏官会银碗匹帛”㊶[宋]西湖老人:《西湖老人繁胜录》,载[宋]孟元老等著:《东京梦华录(外四种)》,周峰点校,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第99页。、“州府赏以彩帛钱会银碗”㊷同注⑭,第146;133-134;133页。。虽然无法确知乐妓所获财物价值几何,但通过其“令人肩驮于马前,以为荣耀”㊸同注⑭,第133;256页。的实际行为,足见其自豪感和满足感。
“沿街游艺”可视为“坐肆作乐”的“升级版”和“扩展版”,以其显著的仪式性、规模性、开放性,成为“女倡卖酒”中独树一帜的音乐生产类型。“沿街游艺”不仅促进了酒业经济,引领了消费风尚,还打造出一个民俗文化品牌,更建构起一派极具时代特色的城市音乐景观,其意义及影响已超出“设法卖酒”的原有范畴。
(三)“打座而歌”音乐生产
相较于组织有序、规模可观的“坐肆作乐”和“沿街游艺”,灵活、简便的“打座而歌”则属于“女倡卖酒”中最易开展也最为普及的音乐生产类型。
“打座而歌”的记载出自《夷坚志》:
陈东,靖康间饮于京师酒楼,有倡打座而歌者,东不顾。乃去倚栏独立,歌《望江南》词,音调清越,东不觉倾听。视其衣服皆故弊,时以手揭衣爬搔,肌肤绰约如雪。乃复呼使前,再歌之……歌罢,得数钱下楼。㊹[宋]洪迈:《夷坚志》(全四册),何卓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57页。。
“倚栏独立”“衣服故弊”“揭衣爬搔”暗示了乐妓的身份及经济条件;“东不顾”表明酒店中的音乐生产已司空见惯不足为奇;“歌《望江南》词”明确交代了演艺品种及曲名;“音调清越,东不觉倾听”突出了乐妓的伎艺水平;“歌罢,得数钱下楼”指出音乐生产的营利性及生产方式的流动性。这段文字对“打座而歌”做了具体描述和生动展示,值得细细考究。
对于大多数普通酒店而言,既不具备官库中“点花牌”的实力,也不提供“庵酒店”中的“就欢”服务,却仍不乏有效的经营策略:
大凡入店,不可轻易登楼上阁,恐饮燕浅短。如买酒不多,则只就楼下散坐……若命妓,则此辈多是虚驾骄贵,索唤高价细食,全要出着经惯,不被所侮也……㊺同注㉕。
一道楼梯将酒店分为两个空间,楼下为“饮燕浅短”的“散坐”,楼上则是“虚驾骄贵”的“专区”,而是否“命妓”,便是区分二者的主要依据。“阁楼专区”的设置与官库“点花牌”如出一辙,以将乐妓“深藏邃合,未易招呼”的方式刺激消费。
与财雄势大的“市楼表表者”相比,本小利薄的小酒肆多以“打座而歌”为主要,可谓意趣迥然:
又有下等妓女,不呼自来筵前歌唱,临时以些小钱物赠之而去,谓之“箚客”,亦谓之“打酒坐”……如此处处有之。㊻同注⑰,第188页。
更有百姓入酒肆……有一等下贱妓女,不呼自来,筵前祗应,临时以些少钱会赠之,名“打酒座”,亦名“礼客”……如此等类,处处有之。㊼同注⑭,第133;256页。
又有小鬟,不呼自至,歌吟强聒,以求支分,谓之“擦坐”。㊽同注⑱,第407页。
“临时以些小钱物赠之”说明音乐演艺的营利性,“以求支分”更显出逐利的主动性和迫切性,而“处处有之”则表明其普及程度之高、市场需求之大。
宋元小说、话本等文学作品也不乏对“打座而歌”的描写。《水浒传》第三回写到,鲁达邀史进、李忠在渭州潘家酒楼吃酒,无意中得知金翠莲父女因受郑屠欺辱而被迫在酒店卖唱还债之事。酒保称金翠莲父女为“绰酒座儿唱的”,金翠莲则自称“赶座子”:
父亲自小教得奴家些小曲儿,来这里酒楼上赶座子。每日但得些钱来,将大半还他,留些少子父们盘缠。㊾[明]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全二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43-44页。
另外,话本《宋四公大闹禁魂张》称一个在酒店里“拍手唱一支曲儿”的妇女为“擦卓(桌)儿的”。㊿同注㉒,第157页。
“打酒坐/座”“擦坐/桌”“绰酒座”“赶座子”皆为“打座而歌”的不同称谓,其共性都表现为“不呼自来筵前歌唱”“不呼自至,歌吟强聒”。《水浒传》第三十八至三十九回,对此也有所涉及。宋江等四人在江州琵琶亭酒楼吃酒,卖唱女宋玉莲主动上前献唱:“只见一个女娘,年方二八,穿一身纱衣,来到跟前,深深的道了四个万福,顿开喉音便唱。”[51]同注㊾,第491-492页。
此外,酒店演艺市场还活跃着一种名为“赶趁”的音乐生产,亦属于广义的“打座而歌”。《武林旧事》记载,酒肆中“又有吹箫、弹阮、息气、锣板、歌唱、散耍等人,谓之‘赶趁’”。[52]同注⑱,第407页。“赶趁”一词在宋代使用广泛,本意为“追赶”,后泛指在街市上随人流动、为谋利奔走的行为及从事这样活动的人。[53]齐瑞霞:《宋代新生称谓类俗语词成词特点及其文化因素分析》,《东岳论丛》,2015年,第36卷,第3期,第57页。话本《金鳗记》中,庆奴在身无分文时决定去酒店“赶趁”:
“我会一身本事,唱得好曲,到这里怕不得羞。何不买个锣儿,出去诸处酒店内卖唱,趁百十文,把来使用,是好也不好?”……庆奴只在镇江店中赶趁。[54]同注㉒,第673页。
“赶趁”的服务对象及范围较广,遍及街市、酒店、妓馆等各类演艺市场:
街市有乐人三五为队,擎一二女童舞旋,唱小词,专沿街赶趁……或于酒楼,或花衢柳巷妓馆家祗应,但犒钱亦不多,谓之“荒鼓板”。[55]同注⑭,第302页。
上述金翠莲、宋玉莲、庆奴等本为平民女子,皆因生活窘困而依附于酒店演艺市场。她们以“不呼自来筵前歌唱”“不呼自至,歌吟强聒”等差强人意的音乐生产方式“以求支分”“得些钱来”,因而被视为“下等妓女”“下贱妓女”。迫于收入微薄、缺乏保障的现实困境,她们选择用降低成本和增加流动性的办法提高经济收益,以薄利多销的营销策略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
“打座而歌”是宋代酒店演艺市场相当普遍的音乐生产类型,多以市井乐妓为主体,个人或家庭为单位,演艺形式及所用乐器、道具也较为简单随意,总体上规模小、成本低且形式灵活、易于开展。“打座而歌”以“歌”为主要生产方式,如“歌《望江南》词”“筵前歌唱”“歌吟强聒”“拍手唱一支曲儿”“顿开喉音便唱”“酒店内卖唱”等,同时兼及演奏等其他形式。通过“打酒坐/座”“擦坐/桌”“绰酒座”“赶座子”中“打”“擦”“赶”等字眼,不难窥见市井乐妓疲于奔波、身如飘萍的生活境遇及其社会地位。总之,“打座而歌”是“女倡卖酒”中最为灵活、简便的类型,较之“坐肆作乐”“沿街游艺”更具流动性、自主性、随意性,普及程度也更高。
结 语
以音乐演艺为商业营销手段的“侑酒”“卖酒”并非始于宋代,然而将其作为经济制度确立并推广,则出现于宋代。“设法卖酒”是宋代“榷酤”制度中的一项具体措施,其实质便是“女倡卖酒”。“女倡卖酒”之称见于宋人记载,是一种利用乐妓的音乐演艺促进酒业经济的营销策略。笔者将宋代酒店演艺市场中以乐妓为主体、演艺为手段、经济为目的音乐生产,皆纳入“女倡卖酒”的范畴,并将其视为一种兼具“音乐-经济”双重属性的音乐文化现象。
通过文献分析可知,“女倡卖酒”主要包括“坐肆作乐”“沿街游艺”“打座而歌”三种类型。“坐肆作乐”因官方推行“设法卖酒”而兴起,以“鼓乐倡优”“俳优戏剧”“笙歌管弦”为生产方式,“点花牌”为特色项目,具有明显的制度性、稳定性、常规性。“沿街游艺”是盛大的官库“开沽”仪式的重要环节,官私乐妓在统一的差排调遣下,以器乐、杂戏、散乐等音乐生产方式为官酒作宣传和促销,表现出仪式性、规模性、开放性特点。“打座而歌”是“打酒坐/座”“擦坐/桌”“绰酒座”“赶座子”的统称,主要流行于普通私营酒店,以市井乐妓为主体,个人或家庭为单位,歌唱为生产方式,因其较强的流动性、自主性、随意性而达到“处处有之”的程度。上述三种类型既特色分明又相互补充,推动了“女倡卖酒”的成熟和普及,也丰富了宋代音乐的内容及色彩。
在“庄园经济的解体”“商业繁荣”“经济的发展”“繁盛的城市”的全面侵染下,宋代音乐中出现了“市肆演出”“侑酒活动”等新面貌、新品种,“女倡卖酒”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女倡卖酒”既是顺应国家财政的经济举措,也是适应文化潮流的音乐活动,它一方面表现出乐妓及其音乐演艺商业化、市场化的可能性和积极性,另一方面也折射出经济政策、商品市场、消费需求等经济因素对音乐发展的深入影响。总的说,这是音乐演艺与商品经济密切结合且有机互动的集中表现。
综上所述,作为宋代独特的音乐文化现象,“女倡卖酒”不仅顺应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还繁荣了演艺市场,促进了音乐传播,更加速了音乐的商品化、市场化、世俗化,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音乐的历史进程,为我们认识、理解宋代音乐的时代风貌及其历史意义,提供了一个有效且有趣的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