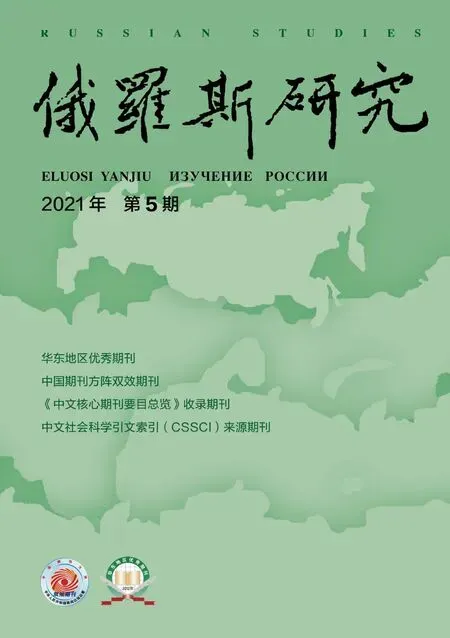格鲁吉亚的历史记忆:国家发展转型中的精神全景与细节*
石 靖 吴大辉
【内容提要】从宗教视角审视格鲁吉亚国家的发展转型时,不难发现,基督教的传承与格鲁吉亚国家的历史形成休戚相关,二者之间的关系稳定且紧密。这可以理解为悠久、独特的宗教传统已被格鲁吉亚人升华为有关国家性共同认知的重要内容。中世纪前期,基督教的传播和接纳成为重要的趋近因素,对高加索山脉南麓地域分散的不同王国产生了聚合性影响,奠定了格鲁吉亚集体记忆的历史基底。中世纪后期,特别是在国家统一繁荣的“黄金时代”之后,遭受外部影响的精神记忆仍然被视作格鲁吉亚国家独特性、忍耐力的支撑因素,并在特定历史转型时期发挥着连接传统和指向未来的特别功用。俄国时期,以维护格鲁吉亚民族和国家记忆为中心的启蒙运动,与通过包括宗教手段推行“俄罗斯化”的政策实践相互拒斥,在格鲁吉亚地域上产出了特殊的互动效果。在当前国家转型背景下,格鲁吉亚的历史记忆被再次激活,重视历史传统与强调国家独立、完整以及追求以欧洲为导向的政治实践交织在一起。精神记忆已成为当代格鲁吉亚可动用的常态化的“国家储备”,并将继续作为服务国家发展转型、体现其路标选择合理性的有效工具。
宗教,作为某个特定族群或其他共同体精神内涵的表现形式,是区别于“他者”的文化和历史标签。以宗教为主要内容开展的专门学科工作,除了在学科设置中围绕相关问题进行研究、揭示人类文化发展的逻辑脉络,在当前还更多地表现为与其他学科的平行、交叉。①在中国知网使用“宗教研究”作为关键词进行搜索,期刊文献成果的篇名中有“宗教经济学”“宗教与国际关系”“宗教民族志”以及“宗教地理学”等概念。“地区研究”,也被称作“区域国别研究”,不论是在其产生和繁盛之地的欧美,抑或是在当前将其视为“显学”的中国,均是以地理空间作为研究的限定,围绕因地域不同而衍生出的“他者”进行资料收集、整理,并开展更为专业化的学术研究。在地域限定之外,地区研究的内容却可以包罗万象并产出百科知识般的成果。但需要强调的是,地区研究的内容仍需以实际问题为导向,而在“课题”式研究之外,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特性也决定了有关地区研究方向的重点以及必须要考量的因素。“宗教”凭借其鲜明的时空特点,与文化传统以及国别政治等直接相关,可作为地区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
进一步嵌套宗教议题并限定研究地区之后,即可发现,我国当前的俄苏研究,在精神文化方面仍未给予该空间内基督教世界的“边缘地带”以足够关注。虽然位于高加索地区的国家均是当前国际体系中的小国,也不再处于各自历史发展阶段的“黄金时代”,但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却仍然稳定地对国家政治以及民众生活产生影响,而且那些可资利用的记忆资源仍是被重点强调的对象。如果选定格鲁吉亚作为研究对象却忽视了其精神记忆,那么很可能产生偏差。随着后苏联时代传统文化习俗的回归,记忆的内容成为新的国家建构不可缺少的佐证材料,因而关注精神文化的载体具有学理意义。
本文的研究场域是格鲁吉亚国家的历史演进过程,主线是作为格鲁吉亚国家传承发展线索的宗教因素:通过解析与国家绑定的东正教曲折动荡的历史,旨在呈现不同历史时段内格鲁吉亚国家的精神记忆及其在相应历史背景下所发挥的多维度功能。本文关于格鲁吉亚历史记忆的具体内容包括:格鲁吉亚历史“黄金时代”和在中世纪与异族入侵抗争的比较,俄国时期格鲁吉亚宗教因素之于国家生存的多重功能比较,以及当代格鲁吉亚政治发展愿景中精神记忆的角色。通过从历史文化到现实地缘政治的解析,本文发现,格鲁吉亚是欧亚地区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典型案例。这也说明,作为与该地区国家形成和发展历史相伴的精神文化元素,可以成为我们认识此地区对象国乃至整个区域发展现实与未来的特别切入点。
一、关于“记忆”议题的研究
在重现格鲁吉亚历史进程时,研究者往往特别选择宗教为主线,并根据记忆元素对其进行拼接贯通。由于时间跨度久远,不同对象、群体以及各类丰富载体承载的记忆,都是对格鲁吉亚绵延宗教因素的刻画,也是对该地域精神信仰以及国家历史演进的反映。因而,选取并突出记忆元素,是为了多角度且鲜活地呈现过去的故事;另外,精神信仰同时也是主观且带有情感的,这与同样具有这些特点的个体或集体的记忆形成对照。
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常引用这样一句话:“之所以有那么多人谈论记忆,是因为记忆已经不存在了。”①Pierre Nora, Zwischen Geschichte und Gedächtnis, Berlin: Verlag Klaus Wagenbach, 1990,p.11.近年来关于记忆的话题和讨论,可以通过大量的研究文献证明:除了该话题的繁荣期外,在记忆话题范畴内不同问题和兴趣交叉、刺激和密集的现象,也印证了学界对记忆的讨论。②[德]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潘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7 页。从20世纪80年代起,“记忆”开始成为西方政治文化以及人文学科里不断升温的关键词,这与历史学科中后现代主义思潮直接相关。例如历史书写中的“叙事转向”等变化,使得常被视为历史之对立面的记忆,不断进入到对历史编纂的反思中。③刘颖洁:“从哈布瓦赫到诺拉:历史书写中的集体记忆”,《史学月刊》,2021年第3期,第104 页。德国历史学家哈拉尔德·韦尔策(Harald Welzer)在总结有关“回忆和记忆现象”的研究时,发现史学家、社会学家以及心理学家等不同学科的专家都对此有所关注。同时自这一研究开展以来,也学习和区分了不同的记忆形式,例如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④[德]哈拉尔德·韦尔策编:《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李斌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 页。
学者们对于回忆和记忆现象的关注,推动了这一话题研究的进展,但是“大量研究结果和在形成理论方面取得的进步,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就是社会回忆实践的一个核心领域,是极其难以用科学手段把握的”。①[德]哈拉尔德·韦尔策编:《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虽然科学无法就回忆来自何处做出准确回答,但可以确定的是:“我们自己的回忆脱离不了客观给定的社会历史框架,正是这种框架,才使得我们的全部感知和回忆具有了某种形式。”②同上。就记忆而言,不论其形成的时间点、承载的内容是关于与当前相对的过去的事物或情境,通过不同载体,过去的许多方面会不同程度地对现实甚至未来发挥影响,这一点对于单独个体或是存在相似认同的集体都是成立的。我们生活在现实中,同时也生活在记忆里。周遭环境承载着历史和回忆,个体与环境的互动与交互,也体现了记忆和现实之间无声却坚定的联系。或许“对于我们来说,历史是记忆。我们不仅懂得记忆,而且还根据它生活。……历史就是奠定了的基础。我们继续受它束缚。”③[德]卡尔·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魏楚雄、俞新天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265 页。
在围绕“记忆”话题的诸多研究中,不难发现,在“记忆”这一词汇之前的定语十分丰富。作为记忆社会学的先锋,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在20世纪20年代提出了“集体记忆”这一概念,从此将其与“史学”意义上的“历史”彻底区分开来。④[德]哈拉尔德·韦尔策编:《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第69 页。见Maurice Halbwachs, Das kollektive Gedächtnis, Frankfurt am Main, 1985.在扬·阿斯曼(Jan Assmann)的著作中,为“文化记忆”作了如下定义:“关于一个社会的全部知识的总概念,在特定的互动框架之内,这些知识驾驭着人们的行为和体验,并需要人们一代一代反复了解和熟练掌握它们。”⑤Jan Assmann, “Kollektives Gedächtnis und kulturelle Identität”, in Jan Assmann und Tonio Hölscher [Hg.], Kultur und Gedächtnis, Frankfurt am Main, 1988, S.9. 在该著作中,阿斯曼界定了后来在专业讨论中一直使用的“文化记忆”概念:每个社会和每个时代所特有的重新使用的全部文字资料、图片和礼仪仪式[……]的总和。通过对它们的“呵护”,每个社会和每个时代巩固和传达着自我形象。它是一种集体使用的,主要(但不仅仅)涉及过去的知识,一个群体的认同性和独特性的意识就依靠这种知识。在韦尔策看来,阿斯曼的解读是对哈布瓦赫概念的细化。⑥[德]哈拉尔德·韦尔策编:《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第4 页。在区别本研究领域不同记忆概念的同时,韦尔策“试着将附带过去的无限纷繁庞大的领域称为‘社会记忆’:一个大我群体全体成员的社会经验的总和”。①[德]哈拉尔德·韦尔策编:《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第4-6 页。韦尔策关于“社会记忆”的定义基于对彼得·伯克(Peter Burke)观点的广义解释。根据伯克的观点,属于回忆社会史(Sozialgeschichte des Erinnerns)范畴的,有口头流传的实践、常规历史文献(如回忆录、日记等)、绘制或摄制的图片、集体纪念礼仪仪式以及地理和社会空间。见Peter Burke, “Geschichte als soziales Gedächtnis”, in Aleida Assmann und Dietrich Harth [Hg.], Mnemosyne. Formen und Funktionen kultureller Erinnerung, Frankfurt am Main,1991, S.392ff.此外,类似的概念还包括“个体记忆”“沟通记忆”等。在梳理总结前人关于记忆话题的研究探讨时,深刻的感受是这些带有侧重和差别的“记忆”概念的确与史学范畴中的“历史”存在显著区别。虽然记忆难以借助科学的手段进行准确测量,但记忆作为多学科学理意义的特殊性却是非常直观的。
回到对记忆内容的探讨,不论是历史学家、社会学家还是哲学家,整体的分析大多带有抽象特点,除通过案例以及记忆载体进行佐证之外,似乎还有一扇记忆的“后门”通向哲学层面的思考。就学术呈现而言,视角和内容与学者的多方面主观因素有关,甚至还不乏体现主观情感和类似非理性因素的案例。再次回到皮埃尔·诺拉的研究关注,在其著作《记忆之场》中,“记忆之场(Lieux de mémoire)②法语“Lieux de mémoire”,由场所“lieu”和记忆“mémoire”两个词组成。”是作者的自造术语。自1984年起,所出版的系列著作的内容体现出“记忆之场”的广度。③详见[法]皮埃尔·诺拉主编:《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黄艳红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III 页。在诺拉看来,历史加速消失,记忆与历史之间的距离越拉越大,记忆是“当下的、具象的、活着的、情感的现象,而历史是对过去理性的、批判性的重构”。④同上,第10-11 页。
与诺拉选择通过记忆维度叙述法国历史类似,带有记忆特点的历史和政治研究已经进入了区域国别研究的视野,并特别将俄苏案例置于近期的主要关注中,这是本领域研究的前沿。在讨论俄罗斯国家的记忆政治时,有学者认为,东正教是继国家之后的第二大记忆政治行为体,对国家的记忆政治发挥着重要作用。⑤胡巍葳:“俄罗斯的记忆政治——宗教的作用及其影响”,《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0年第6 期,第59 页。在时间维度上,有学者将俄罗斯的“二战史观”定位成涉及周边国家的共同记忆,正因为相关的教育具有世界性和人类性价值,通过“共同记忆”体现了人类反思共有历史的整体效应。①沈倬丞、高凤兰:“历史记忆与国家意志:俄罗斯‘二战史观’教育的主旨及意义”,《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 期,第75 页。在空间和时间的穿插之中,有学者对后苏联犹太人流散与记忆的研究做了较为细致的梳理回顾,展现了俄罗斯犹太人在民族学研究范畴的成果以及当代社会的具体表征。也借此,研究者总结认为,“集体身份和集体记忆成为流散的中心概念;集体记忆的危机则促成了民族身份根基的弱化和流散含义的复杂化”。②李暖:“难以摆脱的‘俄罗斯化’——后苏联流散语境下犹太人的归国难题”,《俄罗斯研究》,2020年第2 期,第165-167 页。
记忆是伴随人类自身和社会发展进程存在的内容,记忆议题受到学术界的关注理所应当,但正如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所说,“记忆是任何一个学科不能独占的”,即便是在单一学科内“也显得矛盾重重”。③[德]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第8 页。学界截至目前关于“记忆”议题的探讨,还未能展现出可以进一步聚合的趋近性和统一性。正如以上内容回顾所展现的那样,仅学研层面的记忆概念就较为复杂,互相之间存在区别,且学者即便使用同样的概念表达,赋予的内在含义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别。基于已有的研究案例,顺着“记忆”的思路打通历史与现实,在区域国别研究领域进行时间与空间维度的比较研究,将提供一个有别于传统历史视角的新路径。
二、格鲁吉亚精神记忆的历史探寻:宗教的视角
格鲁吉亚是位于区域间“十字路口”的国家,拥有悠久且独特的历史文化积淀。考察该国深厚的传统基底,不难发现宗教因素在多个维度持续发挥着独特的影响作用。作为显著的文明分界线,或可被称为“东西方文明结合部”④冯绍雷:“俄罗斯文明空间因素的基本特点”,载姚海主编:《俄罗斯文明与外交》,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作者用“东西方文明结合部”来诠释俄国现象、把握俄国千年社会发展历程的基本特征。由于格鲁吉亚与俄国、俄罗斯在历史层面的紧密性以及地域层面的近似性,因而这一概念也是适用的。,格鲁吉亚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处的特殊地理环境,是与特定认知中所谓的与异族、异教族群相互对冲的“前线”地带。因而,对精神信仰的坚守和推崇,是贯穿整个格鲁吉亚历史进程的重要内容。
在着重讨论东正教以及在格鲁吉亚土地之上东正教会的发展前,需要理顺该宗教流派的发展和演化脉络。东正教,意为“基督教的正统派”,“坚守宗教传统或是确认的信条”,在基督教信仰中,这一概念意味着“遵循初代教会(Early Christianity)呈现的基督教义”。①“What Is the Orthodox Church? History and Beliefs of Orthodoxy”, Christianity.com,https://www.christianity.com/church/denominations/the-orthodox-church-history-and-beliefs-o f-orthodoxy.html. “初代教会(Early Christianity/Early Church)”是指第一次尼西亚会议(First Council of Nicaea)正式命名为天主教会之前的基督教会。东正教的外文称呼有多种,其中出现“东方”的定语词(例如:Eastern Orthodox Church)具有明确的地域指向意义。②除在英语中“Eastern Orthodox Church”表示东正教会的含义,也存在一些东正教会的名称中带有表示“东部”含义的字眼,如前身是古罗马时代的基督教区、如今作为独立教会的“Greek Orthodox Patriarchate of Antioch and All the East”。此外,保持传统礼制但又与罗马教廷共融的“东仪天主教会”,中文的翻译也来自其外文称呼“The Eastern Catholic Churches/Oriental Catholic Churches”。“东正教(Orthodoxy)”这个中文译法,一方面考虑到信仰传播的地域,即相对于罗马教廷的东方,另外也遵循“正统、传统”的宗教理念和语言含义。③《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453 页。
按圣经所记,在耶稣基督受难与复活之后,其使徒们在不同地区建立了多个宗主教区(Patriarchate)来宣传教义思想,以亚历山大、安条克④安条克(Antioch),现土耳其东南部城市,曾是古叙利亚的首都。安条克教会/宗主教区(Church of Antioch),是1098年与罗马教会分裂之前的五个宗主教区之一。“Church of Antioch”, OrthodoxWiki, https://orthodoxwiki.org/Church_of_Antioch、耶路撒冷、罗马以及君士坦丁堡为代表的宗主教区分布,代表了当时教义传播的范围。此后,罗马帝国的分裂、政教关系、语言文化以及教义分歧等诸多因素加剧了教会内部的矛盾甚至对抗。鉴于东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九世(Constantine IX Monomachus)提出希腊-罗马统一的意愿,1054年,罗马教宗利奥九世(Pope Leo IX)派遣使者亨伯特(Humbert of Silva Candida)前往君士坦丁堡。然而之后的历史却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亨伯特与拜占庭神学家公开辩论并陷入僵局,继而在索菲亚大教堂举行的教士会议上宣布,开除牧首米恰尔一世(Michael I Cerularius)的教籍。①“Humbert of Silva Candida”,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https://www.britannica.com/bio graphy/Humbert-of-Silva-Candida这一事件标志着东西教会的分裂,罗马教会之外的基督教会组成“东正教会(Orthodox Church)”。“Orthodox”的构成来自希腊语“ορθόδοξος(orthódoxos)”,由“orthos”(延续的)与“doxa”(观念)两部分组成②“Lexico UK Dictionary”, https://www.lexico.com/definition/orthodox,意味着对正统礼制的沿袭和传承。
在基督教会发展演变的同时,传教活动也从宗教诞生的地中海东部沿岸向其他区域扩展。至11世纪东西教会分裂时,基督教的传播已经遍及环地中海地区,东部宗主教区的影响也延伸至近东以东、甚至扩展到距离更远的欧亚北部森林地带。在当今广阔的欧亚地区,最早受到基督教影响的地域是与东罗马帝国毗连的高加索地区。根据圣传(Sacred Tradition)内容,圣徒犹达(Thaddeus the Apostle)和巴塞洛缪(Bartholomew the Apostle)于公元1世纪来到亚美尼亚传布福音,并因此殉道。自此,基督教团体开始在亚美尼亚存在和发展,并于公元301年被其宣布为国教。这一独立国家教会的历史中心位于埃奇米亚津(Mother See of Holy Etchmiadzin)。③“Armenian Apostolic Church”(Mother See of Holy Etchmiadzin),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https://www.oikoumene.org/en/member-churches/armenian-apostolic-church-moth er-see-of-holy-etchmiadzin同样也是在公元4世纪,格鲁吉亚接受了来自拜占庭的基督教,作为该国宗教圣城的姆茨赫塔,至今仍然保留着格鲁吉亚正教会以及国家历史文化的重要印记。来自拜占庭的宗教也传播至更远的斯拉夫人生活地域,公元10世纪罗斯受洗,基督教作为国教取代多神教,为之后俄国千年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和文化根基。
目前,东正教作为基督教的主要分支之一,在全世界范围内共有约两亿信众。④Православные по странам//Википедия. https://ru.m.wikipedia.org/wiki/Православные по странам; Число Православных в Мире. https://pravoslavie.ru/put/worldorth.htm在欧洲东部和南部、广大的欧亚地区以及西亚北非的一些地区,作为居民的信仰和文化内容,东正教至今仍然是不少国家、民族以及个人生活中的重要元素。⑤此处将东正教的地域分布定义为“欧洲东部和南部、广大的欧亚地区以及西亚北非的一些地区”,主要是基于东正教的起源和历史发展的核心地域。据统计,目前除俄罗斯、乌克兰、罗马尼亚、希腊等国生活着众多的东正教信徒外,美国、中亚国家以及欧洲其他国家也有不同数量的东正教信徒。目前,中国国内围绕东正教的研究大多结合俄罗斯的案例,当然,这与历史上俄罗斯在东正教世界中的地位、现实中俄罗斯的国家实力以及日趋紧密的政教关系直接相关。①可以参见国内研究东正教的学者戴桂菊、林精华、马寅卯、徐凤林、乐峰等的学术成果,如戴桂菊:“中国的俄罗斯东正教研究”,《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6年第5 期,第77-80 页;林精华:“陌生的邻居:仍不熟悉的俄罗斯东正教”,《学习与探索》,2015年第9 期,第142-154 页;马寅卯:“东正教、宗教多元主义与俄罗斯民族身份”,《世界宗教文化》,2019年第5 期,第78-85 页;徐凤林:“当代俄罗斯东正教社会服务简析”,《俄罗斯研究》,2016年第4 期,第111-124 页;乐峰:《东正教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然而,东正教世界除了重要的俄罗斯以及斯拉夫因素外,在东欧、高加索、西亚北非地区仍存在更多鲜活的案例。他们往往具有悠久的历史发展进程、地域因素所致的宗教特性以及现实中的更多复杂细节。作为乌克兰危机的连锁反应之一,2019年乌克兰自主正教会(Автокефалія/Православна церква України)②在2018年末“乌克兰自主教会”成立之前,“乌克兰正教会”作为在乌克兰拥有自治权的教会,是俄罗斯东正教会的组成部分。在成立“自主教会”并得到君士坦丁堡牧首的确认后,乌克兰出现了双正教会的情形。宣布独立,并得到了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His All-Holiness Ecumenical Patriarch Bartholomew)的确认和授权③«Патриарший и Сиолальный Томос предоставления автокефального церковного устройства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Украины». Года две тысячи девятнадцатого, месяца января, 6 числа, индиктиона 12.,释放出现实中原苏东转型国家政治与宗教文化因素的联系,也说明了研究东正教世界中俄罗斯之外案例的必要性。
格鲁吉亚东正教会是世界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基督教团体之一,在当代格鲁吉亚,其作为独立的东正教团体而存在。④“Georgian Orthodox church”,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https://www.britannica.com/topic/Georgian-Orthodox-church基督教在格鲁吉亚的起源可追溯到公元1世纪,彼时,基督十二使徒中的安德烈(Andrew the Apostle)、西门(Simon the Zealot)以及马提亚(Saint Matthias)等来到格鲁吉亚地域传布基督教义。相传在公元4世纪初,来自卡帕多奇亚的圣徒尼诺(St. Nino)将基督教带到了当时的伊比利亚王国(Kingdom of Iberia,今格鲁吉亚东部地区),圣米利安国王(St. King Mirian)宣布基督教为国教,从而成就了格鲁吉亚作为最早接受基督教国家之一的历史。⑤“About Georgia”, http://gov.ge/index.php?lang_id=ENG&sec_id=193直至今日,由圣尼诺带来的“十字”,作为基督教的标志,仍被放置在与格鲁吉亚宗教圣城姆茨赫塔(也是旧都城)隔河相望的圣十字修道院内,彰显着圣徒尼诺之于格鲁吉亚宗教以及精神记忆的当代意义。
虽然当代格鲁吉亚着重强调早期接受基督教的历史,但事实却是,基督教在格鲁吉亚的传播和发展远不是这一次所谓标志性事件能够概括的。在国力、地理以及邻国因素充盈的历史中,呈现出基督教在格鲁吉亚的曲折发展进程。格鲁吉亚与基督教的联系之初,存在着显著的拜占庭因素,从教会管理到具体的礼仪形式上均有体现。在接纳基督教之初,格鲁吉亚教会归属安条克宗主教区①由于安条克在罗马帝国中的重要地理位置,诸多使徒的传教活动都是由此出发。在初代教会的历史中,安条克由于其重要地位被视为基督教世界的中心。“Church of Antioch”,Orthodoxwiki, https://orthodoxwiki.org/Church_of_Antioch#Early_years管辖。466年,安条克宗主教给予格鲁吉亚教会自治权,并提升了姆茨赫塔主教的地位,冠以“姆茨赫塔大主教以及卡尔特利大主教”(Archbishop of Mtskheta and Catholicos of Kartli)②“Catholicos”来自希腊语Καθολικός,含义是“关于全部,普遍的,通用的”。这一宗教头衔似乎是起源于罗马帝国东部边疆以及萨珊帝国的教会,时间范围约在三至四世纪,相关地区属安条克教会管辖范围。至五世纪末,几乎所有地方的主教都使用“Catholicos”的封号。但是,当时这一称号与“Patriarch”的含义不完全等同。参见“Catholicos”, Orthodoxwiki, https://orthodoxwiki.org/Catholicos. 这一概念的俄语作“Католикос”,是统领近东和中东地区自主教会的主教封号,相关自主教会并不属于早期教会体系(五个宗主教区:罗马,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安条克,耶路撒冷),通常与“патриарх”的封号等同,并经常会出现两位一体的封号“католикос-патриарх”。目前,“Католикос”仍被格鲁吉亚东正教会、亚美尼亚使徒教会、亚述东方教会等采用。例如,格鲁吉亚东正教大牧首的封号全称为“His Holiness and Beatitude, Catholicos-Patriarch of All Georgia, the Archbishop of Mtskheta-Tbilisi and Metropolitan bishop of Bichvinta and Tskhum-Abkhazia”。亚美尼亚使徒教会牧首的封号为“Catholicos of All Armenians”。“Kartli”译为“卡尔特利”,在此是一个地理称谓,是古代以及现代格鲁吉亚的核心地区,位于该国的中、东部地带。中世纪晚期出现了“卡尔特利王国(Kingdom of Kartli)”。在当代格鲁吉亚的国家区划中,有“Shida Kartli”以及“Kvemo Kartli”两个地方级单位。的封号,其主教坐堂位于姆茨赫塔。③“Diocese of Mtskheta and Tbilisi”, Orthodoxwiki, https://orthodoxwiki.org/Diocese_of_Mtskheta_and_Tbilisi需要指出的是,高加索地区接受基督教之初,其本地化的发展呈现出包容、多元以及灵活的特点,而严格的等级观念以及道统则是在此之后,特别是6世纪之后,伴随“国家”教堂的修建而产生的。④Tamila Mgaloblishvili, Stephen H. Rapp Jr, “Manichaeism in late antique Georgia?” In Search of Truth: Augustine, Manichaeism, and other Gnosticism, Studies for Johannes van Oort at sixty, edited by Jacob Albert van den Berg et al., Leiden, Boston: BRILL, 2011, p.264.
公元6-9世纪,在文化层面,格鲁吉亚的修道院主义(Monasticism)繁荣发展。格鲁吉亚的宗教建筑已经超出了现代格鲁吉亚国家的边界,同一时期在西奈半岛(Sinai)、希腊的阿托斯圣山(Mount Athos)以及格鲁吉亚历史上的陶-克拉杰伊(Tao-Klarjeti)①陶-克拉杰伊(Tao-Klarjeti,格鲁吉亚语:),是格鲁吉亚的一个历史地区,位于现今的土耳其境内,这一地区因为中世纪的历史文化遗迹而常被提及。地区建设的修道院对于宗教、文化的发展和传播起到了特殊的作用。②“Georgian Orthodox Church”, https://religion.wikia.org/wiki/Georgian_Orthodox_Church这些年代久远的宗教历史建筑,既是当时格鲁吉亚国家的呈现形式,也作为记忆载体留给了之后的世代。西格鲁吉亚曾作为君士坦丁堡牧首管辖的教区,但鉴于阿布哈兹王侯于9-10世纪的力量,西格鲁吉亚教区成为姆茨赫塔主教(Мцхетский католикос)的管辖地。③Мераб Вачнадзе, Вахтанг Гурули, Михаил Бахтадзе. История Грузии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1801 года. Тбилиси: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Интелекти”, 2014. С.65-66.1010年,卡尔特利主教(Catholicos of Kartli)的地位得到提升,并开始统领格鲁吉亚教会,其正式封号④格鲁吉亚大主教的封号为“Catholicos-Patriarch of All Georgia”。已与现代格鲁吉亚教会宗主教的基本一致。⑤“Georgian Orthodox Church”, https://religion.wikia.org/wiki/Georgian_Orthodox_Church
13-14世纪,蒙古入侵对格鲁吉亚的精神文化载体造成严重破坏。据称,在数次大规模入侵破坏之后,格鲁吉亚人最先着手建设和恢复的是教堂和修道院。⑥Giuli Alasania, “Twenty Centuries of Christianity in Georgia”, IBSU International Refereed Multi-disciplinary Scientific Journal, 2006, No.1, p.125.有些至今仍在从事礼拜活动的教堂,其建筑中的不同材料和色泽承载着跨越数个世纪的坎坷历史。15世纪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对于有着宗教文化纽带的格鲁吉亚而言并不是一件“身外事”。奥斯曼以及波斯势力的壮大,不可避免地对本地区的东正教产生负面影响。国力相对弱小的格鲁吉亚再次面临严峻的“生存”挑战。而已内化为格鲁吉亚人特质的宗教元素,也因穆斯林的到来危机重重。国家在这一时期处于分裂状态,因而东、西格鲁吉亚的教会也由不同的主教进行管辖。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格鲁吉亚的精神记忆始终与“基督教化”的国家命运息息相关。19世纪以后,俄国势力跨越大高加索山脉带来的影响,直接作用于格鲁吉亚国家以及教会在近代以来的历史演变。1811年,俄罗斯帝国取消了格鲁吉亚正教会的独立地位,宗主教安东二世(Католикос Антоний II)①1811年,大主教安东二世被召前往彼得堡,“这一事件本身就预示了格鲁吉亚教会将失去独立地位”。Теймураз Панджикидзе. Христианство в Грузино-Российской отношениях: история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и Кавказ. 2005. No.2. С.37.被停止职务、取消封号,格鲁吉亚正教会转而归由俄国正教会至圣主教公会进行管理。至1917年3月,格鲁吉亚都主教区(Грузинский экзархат)作为俄国东正教会的组成部分,在所辖主教区(епархия)范围②1885年,格鲁吉亚都主教区由5 个主教区组成,分别是格鲁吉亚主教区、弗拉季高加索主教区、伊梅列希主教区、新森纳基(古利亚-明格列尔)主教区以及苏呼米主教区。Грузинский экзархат. https://ru.m.wikipedia.org/wiki/Грузинский экзархат内从事宗教活动。
俄国时期,格鲁吉亚教会谋求“独立教会”地位的实践从未停止。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之后,宗教人士借助混乱的“窗口期”单方面重新恢复了格鲁吉亚教会的独立自主地位。随着苏俄势力的南下和继之开启的苏维埃时代,宗教议题以及所触及的格鲁吉亚教会的问题,在苏联时期总体较为沉寂。然而格鲁吉亚教会的自主地位,却在20世纪40年代卫国战争时期得到了俄国东正教会的承认,这也被视为该时期内与格鲁吉亚教会有关的重要事件。20世纪80年代末期,格鲁吉亚的局势变化也带动了社会全方位的“公开性”运动。格鲁吉亚教会一直以来争取的“独立和自治”地位,于1990年得到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的承认。③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支持格鲁吉亚独立教会,关于“格鲁吉亚独立教会”的命令于1990年1月签署。Томос об автокефалии Грузинской Церкви. 1990 спасительного года, 25 января. https://cerkvarium.org/ru/dokumenty/tserkovnye/tomos-ob-avtokefalii-gruzinskoj-tser kvi
后苏联时代,格鲁吉亚东正教会的活动进一步恢复,宗主教伊利亚二世(Ilia II)作为教会的崇高象征,时常出现在多种正式场合,也常就格鲁吉亚国内以及涉及格鲁吉亚的国际问题发声。在格鲁吉亚,88.6%④2014年数据显示,88.6%的格鲁吉亚居民信仰基督教。“Religion-Christianity-Percentage of population that is Christian”, NationMaster, https://www.nationmaster.com/country-info/sta ts/Religion/Christianity/Percent-Christian的公民信奉东正教,这样的信众基础体现了东正教在当代格鲁吉亚社会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屹立在第比利斯古城库拉河对岸的“圣三一主教座堂(Holy Trinity Cathedral of Tbilisi)”,作为当代格鲁吉亚建筑的典型代表,彰显了宗教在国家生活中历史地位的现实回归。
三、格鲁吉亚的早期国家转型与精神记忆刻画
精神文化是格鲁吉亚国家历史的组成部分,随时间积淀的东正教传统在不同历史时期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事实上,格鲁吉亚教会就是格国家精神生活的引导力量。正如伊利亚·恰夫恰瓦泽(Ilia Chavchavadze)①伊利亚·恰夫恰瓦泽(Ilia Chavchavadze)是格鲁吉亚诗人、政论家,个人生活经历带有格鲁吉亚民族主义色彩。恰夫恰瓦泽生活在俄罗斯帝国时代,支持格鲁吉亚民族独立,当代格鲁吉亚将其视为“国父”。所说:“格鲁吉亚教会总是在祝福国家,并且从未让国家的荣誉被遗忘。”②Metropolitan Anania Japaridze, Mamuka Matsaberidze ed., A Short History of the Georgian Church, Nova Science Publishers, Incorporated, 2014, p.3.很显然,格鲁吉亚教会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影响,得到了本国思想家的确认。教会不仅助力思想、文化成为国家特质的根基,而且绵延数个世纪的精神文化传统对于国家存续和发展起着特别的守护作用。
从公元4世纪被正式确定为格鲁吉亚国教,直至20世纪的漫长历史中,基督教通过宗教传播、接受度、影响力等内部因素,以及与不同时期影响其发展的外来因素的相互作用,其作为群体精神记忆内容的信仰地位逐渐上升,进而固化为传统,并持续成为格国家发展历史进程中的推动力量。按照时间阶段来看,中世纪前期,基督教的传播和接纳作为重要的趋近因素,对高加索山脉南麓地域分散的不同王国产生了聚合性影响,从而促进了格鲁吉亚作为一个统一体在历史中的呈现。中世纪后期,国家统一繁荣的“黄金时代”③格鲁吉亚的“黄金时代”是格鲁吉亚历史中的一个阶段,其发展以及所辖范围达到顶峰。具体的时间跨度为11世纪晚期至13世纪中期,随蒙古人的入侵画上句号。之后,遭受蒙古、奥斯曼、波斯因素负面影响的宗教,仍然作为格鲁吉亚国家独特性、忍耐力的支撑因素,在艰难的历史时期发挥了连接传统和指向未来的特别作用。近代以来,吞并高加索南麓地域的俄国,在宗教信仰问题上对格鲁吉亚采取统一的管理。俄国时期,以维护格鲁吉亚民族性和国家性为核心的启蒙运动,与通过包括宗教手段推行“俄罗斯化”④Theodore R. Weeks, “Managing empire: tsarist nationalities policy”, in Dominic Lieven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Russia, Volume II, Imperial Russia, 1689-1917,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37.的政策实践互斥,在格鲁吉亚地域上产生了特殊的效果。
最初,基督教的传播和接纳对于早期格鲁吉亚国家聚合、统一有着特别的促进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奠定了格鲁吉亚作为一个统一体的国家性。虽然格鲁吉亚是世界历史上最为古老的国家之一,但在古典时代以及中世纪早期,当今的格鲁吉亚土地上并不存在属于格鲁吉亚人的统一的国家形态。在数千年的历史中,其历史地域上出现过多个不同的政权形式,如位于西格鲁吉亚的科尔基斯王国(Kingdom of Colchis-Egrisi)、拉兹王国(Kingdom of Lazica-Egrisi),位于格鲁吉亚地理核心的伊比利亚王国(Kingdom of Kartli-Iberia),位于西北部的阿布哈兹王国(Kingdom of Abkhazia)。①以上不同的政权组织形式大体按照时间顺序进行排列,从公元前至公元10世纪。其中的翻译可能存在偏差,故同时标注了英文名称。关于这些古老国家的称呼,既标明了外语翻译(foreign name)也同时标明了其自我称呼的拉丁化写法。相关称呼的写法参考了英语以及俄语历史研究的文献,如Ronald Grigor Suny, The Making of the Georgian Nation,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4; Зураб Папаскири.Абхазия и Абхазы в общегрузинском этнокультурном и политико-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м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 часть 1//Кавказ и Глобализация. 2008. No.2. С.120-139.在政权组织上呈现如此分散的状态下,格鲁吉亚地区却凭借靠近拜占庭的地理优势,使基督教的传播和发展从西向东得以收获历史性的影响。中世纪初基督教在高加索山脉南麓的传播和影响,加强了早期格鲁吉亚各王国间的联系,推动了未来的融合,并逐步构建起了共同的精神文化根基。
考察格鲁吉亚的历史不难发现,国家东西部在不同时期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差异,甚至这些因历史积淀导致的差异一直延续到了今天。作为联系与弥合东西部以及其他周边地域差异的因素,宗教的地位及其传播在格鲁吉亚国家历史的演进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公元4世纪之初,位于东格鲁吉亚的伊比利亚王国国王米利安三世(Mirian III of Iberia)将基督教定为国教,这一史实被学界和大众视为格鲁吉亚接受基督教的开端。然而有学者提出不同意见,即“‘基督教化(Christianization)’并不是简单地被中央接受并由此推广,真实的情况是,国王似乎是相对较晚才皈依基督教的”。②David Braund, Georgia in Antiquity: A History of Colchis and Transcaucasian Iberia 550 BC-AD 562, London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239; Tamila Mgaloblishvili, Stephen H. Rapp Jr, “Manichaeism in late antique Georgia?” pp.266-267.国王之所以决定进行宗教变革,极为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当时罗马帝国与波斯萨珊王朝(Sasanian Empire)爆发了战争。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古代格鲁吉亚王国成为周边强大力量对抗的地带,而选择与哪一方趋近则具有政治、战略方面的关键意义。“在基督教和拜火教之间,在罗马和伊朗之间,格鲁吉亚君主选择了拜占庭式的统治作为其政治模式”①Ronald Grigor Suny, The Making of the Georgian Nation,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4, p.22.,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其推动基督教发展的行为逻辑。而一些文化人类学家关于基督教在高加索地区传播的不同观点,似乎也可以对此进行印证,毕竟国王所推行的宗教政策带有极为重要且直接的政治考量,而不仅仅是流传至今的宗教故事。②传说伊比利亚王后娜娜(Queen Nana)接受了洗礼,并由来自卡帕多吉亚的圣徒尼诺医治好了她的重病。尽管如此,国王米利安三世在多神教徒的唆使下仍决定处决圣徒尼诺。“正当宣布行刑之时,阳光暗淡,雾气在国王所处的地方笼罩”,国王因此突然失明。圣徒尼诺医治好米利安三世,之后国王和随从也接受了洗礼。几年之后,基督教的地位最终在格鲁吉亚被确立,而信奉多神教则被禁止。Православный церковный календарь.https://azbyka.ru/days/saint/2541/5613/group
在西格鲁吉亚,拉兹王国作为拜占庭的臣属国,也在4世纪初成立了基督教区(Христианская епархия)。公元523年,基督教成为拉兹王国的官方宗教。③W.E.D. Allen, A History of the Georgian People: From Beginning down to the Russian conques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ondon: K. Paul, Trench, Trubner, 1932, p.276.然而,在拉兹战争之后,波斯萨珊王朝占据了由东(Sasanian Iberia)向西(Lazica)的格鲁吉亚大部地区,基督教的发展失去了国家建制的支撑。不同于东格鲁吉亚在同时期遭受周围帝国势力的频繁侵扰,公元8世纪之后,阿布哈兹王国(Kingdom of Abkhazia)不断发展壮大,而基督教也成了其早期国家性形成的重要因素。④Абхазское царство. https://ru.m.wikipedia.org/wiki/Абхазское царство阿布哈兹教会脱离君士坦丁堡教区并承认姆茨赫塔主教的权威,从而使格鲁吉亚各个地区归属同一个主教管辖,标志着宗教实践推动了政治统一。⑤Мераб Вачнадзе, Вахтанг Гурули, Михаил Бахтадзе. История Грузии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1801 года. С.65-66.直到公元10世纪末,分散的王国才聚合成为统一的格鲁吉亚国家(Kingdom of Georgia),其目前仍在使用的格鲁吉亚语国名“”(Sakartvelo,意指“卡特维尔人/格鲁吉亚人的国家”)首次出现在历史的记载中。⑥Зураб Папаскири. Абхазия и Абзазы в общегрузинском этнокультурном и политико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м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 часть 1. С.131.基督教为格鲁吉亚国家统一发挥了独特的作用,自此也逐渐与格鲁吉亚国家绑定,对内成为国家和民众的文化依托,对外则作为特殊地理环境中区分本国与他国以及其他宗教的标尺。
格鲁吉亚历史教科书是典型的记忆载体,其中对精神文化记忆的书写是国家早期历史的重要内容。作为记忆传承的重要工具和媒介,格鲁吉亚文字与基督教早期在格鲁吉亚地域的发展密切相关。据在格鲁吉亚境内可考证的遗迹,距今最古老的文字标记发现于伯尔尼西希奥尼(Bolnisi Sioni)大教堂。在这座格鲁吉亚最古老的宗教建筑中,据称保存有公元4世纪的文化符号。①Мераб Вачнадзе, Вахтанг Гурули, Михаил Бахтадзе. История Грузии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1801 года. С.60.基于与宗教信仰记忆相联系的文化和艺术,格鲁吉亚人认为,“公元4-13世纪是基督教文化奠定基础的阶段,更高层次的发展则在之后的世纪呈现”。②Там же. С.63.但要注意的是,在高加索地域上的记忆也因族群和自然地理存在差别,国王的影响力无法到达山地,山民们接受基督教和拒绝它一样容易。③A.A. Cherkasov, et al., “The Evolution of Christianity in the Caucasus in the IV-XVIII Centuries”, Bylye Gody, 2016, Vol.41, No.3, p.556.尽管如此,格鲁吉亚土地上精神文化层面的共性逐步形成和固化,这可以被视为民族“黄金时代”记忆产出的重要积淀。
四、精神记忆中的跌宕情节:“黄金时代”的保全与复制
12 至13世纪早期,格鲁吉亚王国达到了发展的顶峰。“黄金时代”的格鲁吉亚,代表人物以及历史故事都成为史料研究的重要内容。历史学家热衷于帮助格鲁吉亚记载有关大卫国王和塔玛拉女皇的故事,编年史中融入了几乎这些领袖的所有细节。④Мераб Вачнадзе, Вахтанг Гурули, Михаил Бахтадзе. История Грузии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1801 года. С.105-106.在主要人物参与的历史进程中,精神文化因素的角色和作用是显著的。然而,与此同时,作为宗教中心的教会,其发展却不可避免地与当时的政权发生碰撞。1103年,大卫四世主持重组格鲁吉亚教会并亲自任命宗教领袖,重建了皇权位于教会之上的体系。⑤Ronald Grigor Suny, The Making of the Georgian Nation, p.35.女皇塔玛拉执政时期,教会再次与世俗政治就最高权力展开争斗。在国家作为统一整体的发展阶段,政治与宗教之间的互斥性逐渐被放大。需要强调的是,正如之前基督教服务于格鲁吉亚国家的统一,“黄金时代”的精神元素仍然镶嵌在统一国家的独特性之中。
从花剌子模进犯、蒙古入侵至被俄国吞并,格鲁吉亚在长达五个多世纪中经历了分裂、外敌入侵和俄国统治等不同历史阶段。在精神信仰层面,15世纪拜占庭的陷落使坚守基督教文化的高加索小国的处境更为艰难。分别位于格鲁吉亚东西地区的波斯萨非王朝以及奥斯曼帝国,在一定程度上加剧和固化了国家的分裂。但是格鲁吉亚教会却在艰难的环境中存续下来,位于西格鲁吉亚以及梅斯赫季(Meskheti)①梅斯赫季(Meskheti)是格鲁吉亚的一个历史区域名称,位于该国西南部。这一历史地域如今大部分被当代格鲁吉亚继承,另外一部分位于土耳其境内。的教堂也一直归属格鲁吉亚教会,甚至梅斯赫季的主教被迫发誓:“我们神职人员和执事只能由姆茨赫塔任命,并且我们会谨遵命令。”②参见Giuli Alasania, “Twenty Centuries of Christianity in Georgia”, IBSU International Refereed Multi-disciplinary Scientific Journal, 2006, No.1, p.125.18世纪40年代,格鲁吉亚贵族、地理与历史学家瓦胡什季·巴格拉季奥尼(Vakhushti Bagrationi)强调:“如果问任何格鲁吉亚人,不论是伊梅列希人、梅斯赫季人等,他们的起源是什么,他们会瞬间回答:‘格鲁吉亚人’。”③Ibid, p.126.这是“以教论族”的时代。彼时,“格鲁吉亚人”与“东正教”是代表相同含义的词汇。④Ibid.处于困境时期的格鲁吉亚国家,精神层面的密切联系和统一性,再次成为国家复兴的必要条件。18世纪末,涉足高加索的俄国人,在鼓吹宗教相近的背后则是政治扩张的野心,自此格鲁吉亚进入了记忆与现实脱节的阶段。
1783年,俄罗斯帝国与卡尔特利-卡赫季王国(东格鲁吉亚)签订《格奥尔吉耶夫斯克条约》,其中第八条规定:“为了表明对于沙俄及其人民的恩典,以及对这些具有相同信仰人民与俄国的合并,皇帝陛下准予宗主教或主事宗主教纳入俄国教会。关于格鲁吉亚教会的管理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问题,由俄国东正教最高会议负责制定特别条款。”⑤«Георгиевский трактат» от 24 июля (4 августа) 1783 г.这一条约成为之后格鲁吉亚国家被俄国兼并的前奏,而在精神文化层面也为格鲁吉亚东正教会失去独立自主地位埋下巨大隐患。从18世纪初俄国针对格鲁吉亚的实践来看,这个南高加索小国事实上丧失了独立自主。数个世纪以来为国家存续抗争的格鲁吉亚,彻底被吸纳成为周边强国的一部分,非独立状态贯穿近现代历史的绝大多数阶段。千年之前被确认的格鲁吉亚教会自主地位,也随着格鲁吉亚被纳入俄罗斯帝国版图而成为历史记忆。在经历了苏联时期的萧条,直到苏联解体后,格鲁吉亚教会才得以日渐恢复。正是在俄国统治时期,涌现了关于恢复格鲁吉亚国家的活跃思想和实践,而对基督教文化以及自主教会地位的强调则直接呼应了国家统一与独立的未来期许。
当东格鲁吉亚国王埃尔克尔二世(Erekle II)向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发出“求救”信函①«За таковые монаршия ваши милости, Обращение Ираклия II к Екатерине II с просьбой о принятии его страны под покровительство России». 21 декабря 1782 г.时,除了考虑借强国之力对冲波斯外,关于文化的趋近性②Ronald Grigor Suny, The Making of the Georgian Nation, p.64.则是选定俄国的重要原因之一。时间在推移,地区的强弱势力也在不断变化,唯有高加索作为文明分界线的历史场域仍然不变。千年之前,伊比利亚王国选择接受基督教以及拜占庭的政治模式,而再次处于关键时刻的东格鲁吉亚王国决定谋求摆脱波斯势力,其必要途径便是请求俄国人的协助。不同的历史时期,格鲁吉亚国家的选择中都包含对历史记忆的参考。抛开特定的时代特点,已固化为文化构成的精神信仰始终是格鲁吉亚国家的选择。此精神层面的记忆和遗产多次承担了挽救格鲁吉亚的重任。
1801年1月18日,东格鲁吉亚王国最终成为俄罗斯帝国的省级单位,国家的命运也预示了宗教领域即将发生的变化。虽然《格奥尔吉耶夫斯克条约》表明,“对于管理格鲁吉亚教会以及双方教会的关系将制定特别条款”,而格鲁吉亚教会人士则解读为:沙皇无权干涉宗教事务,因而(当问题将以政治途径解决时)必须解决信仰和双方教会关系的问题。③Теймураз Панджикидзе. Христианство в Грузино-Росси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ях: история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и Кавказ. 2005. No.2. С.37.格鲁吉亚教会被吸纳成为俄国东正教会的教区之后,除宗教功能外开始发挥特别的政治功效,包括通过教会的力量对民族分布复杂的高加索进行分割(管理)④Антон Рыбаков. В “Области Кесаря”: Проблема статуса и структуры грузин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после отмены автокефалии (первая половина века)//Ab Imperio.2010. No.3. C.144. 19世纪上半叶,随着俄罗斯帝国吞并格鲁吉亚的不同地区,建立了与民族地理相对应的主教区,教会传统被民族和政治原则取代。,以及与之相伴随的“俄罗斯化”,这甚至体现在中央统管宗教事务方面——第比利斯高于姆茨赫塔。①Антон Рыбаков. В “Области Кесаря”: Проблема статуса и структуры грузин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после отмены автокефалии (первая половина века). C.147.以格鲁吉亚都主教区的教区长(экзарх)为例,从1811年至1917年间所有任职的都主教(митрополит)中,只有首位也是唯一一位瓦拉姆都主教(Митрополит Варлаам)出身于格鲁吉亚。②Грузинский экзархат//Древо-открыт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https://drevoinfo.ru/articles/508.html
俄国统治时期,伴随着行政和宗教方面所推行的政策,在一些格鲁吉亚思想家、社会活动家中逐渐催生了关于格鲁吉亚民族性、国家性的思考和讨论。被誉为格鲁吉亚“国父”的恰夫恰瓦泽提出格鲁吉亚民族性(Nationhood)的三个组成因素:祖国、语言和信仰。③Ghia Nodia, “Components of the Georgian National Idea: An Outline”, Identity Studies,2009, No.1, p.88.在他看来,这三方面内容是“从祖先那里继承的,如果我们(格鲁吉亚人)不能将其好好保护,我们会是什么人?我们将如何向后人交代?”④Ilia Chavchavadze, “Oriode sitqva tavad revaz shalvas dze eristravis kazlovidgan‘sheshlilis’ targmanzeda [A couple of words on the translation of Kazlov’s The Mad Girl by Prince Revaz Shalvas dze Eristavi]” – in his Tkhzulebani, Vol.V, Tbilisi, 1991, p.30.。可见,信仰作为支撑格鲁吉亚民族性的因素之一,在俄国统治时期是格鲁吉亚人不变的坚守和倚靠。正因为如此,格鲁吉亚人关于自身、民族以及国家的讨论,逐渐拉开了被称为格鲁吉亚“民族启蒙运动”的序幕。在礼拜以及教堂唱诗时使用教会斯拉夫语,以及在创作和教学中使用俄语,引起了格鲁吉亚知识分子的关注,他们认为这会导致古老的格鲁吉亚教会传统以及文化价值消失。⑤Грузинское национально-просветитель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2-й пол. XIX в. и движение за сохранение церковных древностей. www.pravenc.ru/text/168201.html俄国末期有关格鲁吉亚宗教和传统的讨论再次印证了格鲁吉亚人长期以来对于本民族精神记忆的坚守。它与“俄罗斯化”的政策实践直接对立,催生出了俄国边疆历史的格鲁吉亚版本。
1917年3月,格鲁吉亚神职人员举行仪式,宣布恢复其自主教会地位。自主教会的首任宗主教基里翁二世(Kyrion II)表示:“提醒人们格鲁吉亚国家的名称是教会的责任。这个称呼有助于我们实现团结和统一。”⑥Giuli Alasania, “Twenty Centuries of Christianity in Georgia”, IBSU International Refereed Multi-disciplinary Scientific Journal, 2006, No.1, p.127.随后临时政府事实上对此予以承认,但命令中却表明是“依据格鲁吉亚民族,而不是依照特定领土原则”①Журналы заседаний Временног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Том 1. Март-апрель 1917 года./отв.ред. Б.Ф. Додонов. М.: РОССПЭН, 2001. С.178; Татьяна Чумакова. Вопрос об автокефалии Грузинской церкви в 1917 г. (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архива В.Н. Бенешевича)Государство, религия, церковь в России и за рубежом. 2019. C.186.。虽然在特殊历史时期仍面临诸多困难,但这一事件除了对教会本身的重大意义之外,还承载了更多格鲁吉亚国家谋求团结和自主的思想,是对其历史记忆的再次唤醒。在相对短暂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时期,当时的宪法规定将国家和宗教运行分割开来,禁止国家资助教会②George Papuashvili, “The 1921 Constitution of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Georgia:Looking Back after Ninety Years”, European Public Law, 2012, Vol.18, No.2, p.337.,体现了世俗化的倾向。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格鲁吉亚的精神坚守仍然位于记忆层面,该时间段内出现的剧烈变化见证了记忆与现实的轮转。
五、后苏联时代的转型:精神记忆与现实的再次连接
苏联末期,在“公开性”思想影响下的苏联边疆地区迅速出现“裂缝和松动”。加盟共和国将所发生的社会现象称为“民族觉醒”,而联盟中央则称为“破坏苏联社会稳定”。二者不同的界定反映出当时地方与联盟中央的对立。从苏联的视角,位于南部边疆的高加索的真实情况并不乐观,而其中谋求脱离苏联的格鲁吉亚则不出所料地再次成为地区局势变化的“驱动器”,这似乎验证了格鲁吉亚“例外”③关于苏联时期格鲁吉亚在联盟内享有的特殊地位,是笔者在进行有关格鲁吉亚问题研究时通过交谈、阅读不断得到确认的一种事实现象。政治上,当时苏共中央有不少格鲁吉亚背景的领导人,格鲁吉亚相对表现出更为强烈的政治积极性;经济上享有来自联盟预算的补助等;宗教方面,格鲁吉亚教会的社会角色在苏联时期并未被完全破坏,它仍然在保持格鲁吉亚认同和语言方面表现活跃。的特点。同一时期,属于格鲁吉亚人且已蛰伏许久的精神记忆被迅速唤醒:1990年,格鲁吉亚东正教会正式得到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的确认,重新恢复了独立教会地位。④20世纪,格鲁吉亚在不同时期坚持争取教会独立:1917年恢复自主教会身份,但并未得到广泛承认;1943年,俄国东正教会承认了格鲁吉亚东正教会的自主教会身份;直到1990年得到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的承认。在当时的背景下,格鲁吉亚东正教会得以脱离俄国东正教会。独立后的格鲁吉亚东正教会将重塑国家性和国家政治生活作为必要的任务和目标。但在现实政治当中教会则成为猛烈的社会思潮的加速器。这不可避免地将国家带向另一个充满挑战的全新阶段。在格鲁吉亚国家面临重新建构的任务时,新版的集体记忆被再次书写,而恢复地位后的宗教精神成为社会思潮中最突出的内容。
苏联末期,有关精神文化的诉求已呈现在格鲁吉亚的社会运动中。对于类似加姆萨胡尔季阿这一类带有鲜明民族主义色彩的人物而言,民族独立运动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引导格鲁吉亚国家找寻自我认同。就认同的具体内容而言,由民族情绪生发的信念认为,格鲁吉亚东正教是“真正的格鲁吉亚人”的唯一信仰。①Archil Gegeshidze, “Tolerance in Georgia: religious and ethnic aspects”, The Caucasus and Globalization, 2016, Vol.1, No.1, p.152.加姆萨胡尔季阿的意识形态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笃信宗教以及保守主义的结合,并呼吁宗教的作用。②Реваз Коява. Грузинские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повествования о конфликтах: 1991-2012 гг.Аналитический портал «Кавказского дома». 1 марта 2016. http://regional-dialogue.com/ru/грузинская-национальная-история-кас在他掌握权力后,格鲁吉亚东正教会成为国家公共生活的平等实体和重要参与者。③Beka Chedia, “The Georgian Orthodox Church in current Georgian policy”, Central Asia and the Caucasus, 2009, No.4-5, p.170.这便是过渡时期格鲁吉亚在民族主义背景下精神记忆回归和发展的特点。虽然首任总统未能成功抵挡混乱时局的影响,但对于加姆萨胡尔季阿“为格鲁吉亚独立斗争,奠定国家性基础发挥的特别作用”,格鲁吉亚东正教会给予了肯定。④Католикос-патриарх Илия II считает необходимым перезахоронение Звиада Гамсахурдиа//Русская линия. https://rusk.ru/newsdata.php?idar=4710在30年的独立历史中,作为格鲁吉亚国家性三元素(The Triad of Georgian Nationalism)之一的宗教信仰⑤Ghia Nodia, “Components of the Georgian National Idea: An Outline”, p.88.,逐渐恢复真实面貌,发展成为当代格鲁吉亚国家的精神支柱。⑥Tamara Vardanyan, “Georgia: the national identity in political programmes and in practice”,21st Century, 2010, No.1, p.68.
独立之后爆发的内战使得在格鲁吉亚暂时无法创造出适宜的发展环境,而实现真正“完整”的独立自主才是政治领导者的追求目标。由于分离问题对新生国家造成了严重威胁,成为社会新潮流的东正教会与第比利斯的政治权力核心保持一致的立场。伊利亚二世回忆在阿布哈兹担任都主教的11年间,他并不认为阿布哈兹人和格鲁吉亚人之间存在任何误解。①В абхазской войне не было победителей, заявил Илия Второй//Sputnik-Georgia. 27 сентября 2013 г. https://sputnik-georgia.ru/georgia/20130927/215915138.html内战后阿布哈兹仍处于分离状态,格鲁吉亚教会都主教离开了苏呼米主教区,也事实上从宗教层面与阿布哈兹产生了新的隔阂。独立之后,格鲁吉亚的现实政治与东正教会保持了同样的步调,也遭遇了相似的困境。然而,作为独立时代格鲁吉亚东正教会的宗主教,伊利亚二世在复兴国家宗教生活方面遇到了适宜的客观条件,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格鲁吉亚教会统领下的主教区数量进一步增加,传统的神学院、宗教学校得以恢复。②Грузин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часть 1. https://w.histrf.ru/articles/article/show/gruzi nskaia_pravoslavnaia_tsierkov_chast_1
阿布哈兹战争以签署“和平协议”③«Соглашение о прекращении огня в Абхазии и механизме контроля за его соблюдением» (Заключено в г. Сочи 27.07.1993); «Соглашение о прекращении огня и разъединении сил». Москва, 14 мая 1994 г.即政治解决的方式宣告结束,之后格鲁吉亚国家和民众生活逐渐步入正轨。1995年《格鲁吉亚宪法》的颁布标志着新独立国家法律秩序的恢复。这其中不乏格鲁吉亚精神记忆的回归:“国家承认格鲁吉亚使徒自主正教会在格鲁吉亚历史中的特殊作用,与此同时声明宗教信仰完全自由的原则,以及教会独立于国家的地位。”④“Constitution of Georgia (1995)”. Article 9.与2018年修订的现行《格鲁吉亚宪法》有关“国家与格鲁吉亚使徒自主正教会的关系”表述差异不大,即“遵循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国家认可格鲁吉亚使徒自主正教会在格鲁吉亚历史中的突出作用,并承认其独立于国家的地位”⑤“Constitution of Georgia” (Consolidated version-final), Article 8, March 23, 2018.。
美国国务院1999年发布的《国际宗教自由年度报告》指出,格鲁吉亚东正教与格鲁吉亚民族和国家认同存在紧密联系,是凝聚爱国情感的关键因素;但是东正教会游说国家议会和政府,以求授予其特殊地位并限制“非传统”宗教的活动。⑥U.S. Department of State, “Annual Report on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 for 1999:Georgia”, September 9, 1999.剥离开美国对于格鲁吉亚宗教问题的态度,教会的活动显示了其力量的回归,这是一种具有广泛基础的群体记忆的回归和确立,无法被国家和社会忽视。伴随着格鲁吉亚国家建构的推进,包含宗教内容的精神记忆正在被确立并镌刻在当代格鲁吉亚国家的立国理念之中。
新版《宪法》指出,通过宪法协议规定格鲁吉亚政府与社会中宗教活动的关系。其所提及的“宪法协议”(Concordat of 2002)①“The Constitutional Agreement between the Georgian State and the Apostolic Autocephalous Orthodox Church of Georgia”, Mtskheta, Georgia, October 14, 2002.于2002年10月由时任总统谢瓦尔德纳泽与格鲁吉亚东正教会领袖伊利亚二世签署。除强调格鲁吉亚东正教会对国家历史的重要意义外,“宪法协议”还对教产以及一系列权力做出了明确规定。格鲁吉亚政府与东正教会的这一协议,虽然重申教会独立于国家的自主身份,但同时也可视为世俗政治与宗教的相互承认,特别是确立了东正教会在国家宗教生活中的绝对主导地位。此外,这一规定国家与宗教关系的“宪法协议”的特殊性还体现在,“这份特殊的文件,囊括了教会生活的几乎全部内容,阐释了古老教规在当代国家中的设置”②Блохин В.С. История поместных православных церквей. Интернет-портал «Азбука веры». С.89.。这可以解读为精神记忆在当代格鲁吉亚被正式确认,政治权力允许宗教活动并明确为其划定范围。
加姆萨胡尔季阿时期曾把对精神遗产的坚守作为格鲁吉亚民族主义的内容,谢瓦尔德纳泽时期则延续了宗教在国家生活中的积极角色,并在法律上承认教会意义重大。作为总统,谢瓦尔德纳泽向东正教会提供补助,说服寡头在第比利斯投资建设新的教堂。1999年伊利亚二世和谢瓦尔德纳泽邀请教皇若望·保禄二世访问格鲁吉亚,在更广阔的国际场域内强调精神记忆与外部世界的联系。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格鲁吉亚东正教会最高领袖的认知也在发生变化,甚至包含其对基督教其他分支态度的变化。③Дональд Рейфилд. Грузия. Перекресток империй. История длиной в три тысячи лет.Азбука-аттикус, 2012. см.23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ная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ь.通过精神记忆的视角回顾格鲁吉亚在独立后的历史,不难发现,属于集体的精神记忆在国家生活中的确处于发展上升的势头。但与此同时,举步维艰的国家政治现实以及宗教意识回归的局限性,迫使东正教会仍需要借力政治以谋求更多上升空间。近年来,伊利亚二世关于国家政治进程的评论以及积极释放教会观点的做法,与20世纪90年代的情况形成对比,也印证了东正教会的地位在21世纪的进一步发展。
2003年“玫瑰革命”之后,精神层面的记忆更多地出现在格鲁吉亚的国家政治生活当中,政治精英充分利用宗教,并将其作为社会的凝聚力量。例如,萨卡什维利当选总统之后推行了涉及国家多个领域的大规模改革,其中新确定的国旗图案融入了基督教的“十字”元素,被议会批准的国旗方案成为新的国家象征。①Гулбаат Рцхиладзе. Религиозный фактор и конфликтный потенциал в Грузии//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и Кавказ. 2005. No.3. С.75.此外,领导人在年度重要时间点出席东正教活动,也会特意在教堂等宗教场地组织具有政治意义的活动,以此向外传递格鲁吉亚政治与宗教之间联系稳定的信号。与此同时,在公开场合通过言语、肢体礼节表达对教会以及宗主教的尊敬,逐渐成为格鲁吉亚政治精英的“规定动作”。虽然法律规定了教会的独立地位,但鉴于其在格鲁吉亚国内庞大的社会基础以及认同,政治精英自然清楚与传承记忆之载体的互动和拿捏之道。
在萨卡什维利时期,政府与东正教会的互动体现出实用主义色彩。格鲁吉亚东正教会从国家获得的预算拨款也逐年递增。据统计,教会从国家获得的财政支持从2005年的129 万拉里增加到2012年的228 万拉里②“拉里”是格鲁吉亚货币单位。Сильвия Серрано. Воплощение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единства или оппозиционная сила?//Pro et Contra. 2013. No.5. С.71.,其间虽受俄格冲突的影响存在波动,但整体来看,财政支持力度增长迅速。当然,稳定的资金来源使教会活动具备了坚实的基础,但格鲁吉亚在后苏联时代出现的“去世俗化”趋势不仅与物质保障有关,而且与国家角色弱化存在联系。这不仅源于20世纪90年代国家机构的崩溃,也与格鲁吉亚在2003年后选择了“新自由主义工程”密切相关。这虽然是西方语境的表述,但却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格鲁吉亚东正教会迅速复兴的原因。
在后萨卡什维利时代的格鲁吉亚,政党政治的发展并未实现所谓“欧洲化”的预设版本,国家议会中出现了由一党独大转变为另外一党绝对主导的情况。近几届的议会选举结果则固化了这一趋势。③据最近数次格鲁吉亚议会选举的结果,均有单一党派(团)获得半数以上席位。在政体转向议会制④“Constitution of Georgia” (Consolidated version-final), March 23, 2018.的背景下,格鲁吉亚的实际权力由实力雄厚的执政党控制。多年来,活跃在格鲁吉亚国家权力台前幕后的伊万尼什维利(Bidzina Ivanishvili),延续了政治人物对待格鲁吉亚精神记忆的传统。在重新担任执政党“格鲁吉亚梦想”领导人之后,他在更多的曝光机会中不乏涉及国家宗教历史与文化的表达。在伊利亚二世登基纪念仪式上,伊万尼什维利表示:“国家与教会都在平稳地履行各自的职能,因而能够克服各种挑战并引领国家走向成功。”①“Georgian Dream Leaders Congratulate Orthodox Patriarch Ilia II on Enthronement Anniversary”, December 25, 2019, https://civil.ge/archives/332946其他代表执政党出席这一仪式的政府官员也肯定了教会对国家恢复、发展的重要作用。这表明,尽管法律框架下国家和教会的角色保持相互独立,但宗教元素无一例外地在所有仪式性的场合体现出与政府之间的紧密联系。
纵观历史,格鲁吉亚的精神遗产持续地与国家的命运捆绑,并因其特殊性在不同时代都被着重强调。在独立以后的阶段,教会特殊角色的基底是大规模的信仰基础,②“Public opinion survey residents of Georgia”, September-October 2019, https://www.iri.org/sites/default/files/wysiwyg/georgia_poll_11.18.2019_final.pdf以及社会中始终位于前列的信赖度。③Nana Sumbadze, “Saakashvili in the Public Eye: What Public Opinion Polls Tell us”,Central Asian Survey, 2009, Vol.28, No.2, p.189.格鲁吉亚教会对国家的欧洲发展愿景表示支持,同时利用特殊的身份,借宗教渠道维持与俄罗斯的联系。在这一凸显独特性的历史时期,格鲁吉亚教会为政治尚且“够不到”或者“力不从心”的环节加力续柴。然而,带有格鲁吉亚特色的精神记忆在近年来愈发表现出传统、保守的趋向。东正教传统、国家西向愿景以及现实发展困境彼此内在制约,诸多因素共同影响着格鲁吉亚的未来发展。
六、精神记忆对格鲁吉亚内外政策转型的影响
文章此前已根据宗教的线索梳理了格鲁吉亚在多个历史阶段的精神记忆,所回溯的内容勾勒出了历史维度内精神记忆在国家发展中扮演的角色。本部分将分析格鲁吉亚的历史遗产与当代国家发展选择的关系。
(一)自由愿景与宗教保守趋势的综合呈现
在对外政策鲜明“欧洲化”特点的背景下,格鲁吉亚近年来产出的绝大多数学术成果、政策报告也体现出倾向“欧洲”的明确立场。它们强调格鲁吉亚身份认同中的精神文化因素,也将此作为现实中与欧洲联系并融合的依据。④Kornely Kakachia, Salome Minesashvili, “Identity politics: Exploring Georgian Foreign Policy Behavior”, Journal of Eurasian Studies, 2015, Vol.6, No.2, p.176.有关东正教会对待“西方”的态度,被解读为并非持续表现出完全的对抗性,对于“西方”的怀疑态度在中长期也并不处于可持续的状态。①Archil Gegeshidze, “Towards Enhancing the Role of the Georgian Orthodox Church in the Country’s Democratic Development”, Policy Study-Georgian Foundation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17, p.8.尽管分析问题的视角可以主观选择,但类似指向“欧洲一体化”政治目标的分析,却恰恰突出了格鲁吉亚传统以及精神领域愈加浓厚的保守思想。对外政治目标的自由愿景与宗教的保守趋势综合呈现,这是格鲁吉亚政教关系的鲜明特点。
伊利亚二世作为格鲁吉亚教会的最高精神领袖,在苏联时期以及当代格鲁吉亚多年担任宗教领袖,具有极为丰富的资历。他的宗教思想体现出鲜明的保守主义色彩。就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他曾公开呼吁考虑建立君主立宪制并恢复旧时格鲁吉亚的巴格拉季奥尼王朝(Bagrationi Dynasty)。②“Patriarch Ilia II(Ghudushauri-Shiolashvili)”, Canadian Orthodox Church Project, http://www.orthodoxcanada.ca/Patriarch_Ilia_II_(Ghudushauri-Shiolashvili)近年来,伊利亚二世经常在宗教活动中表达类似观点,认为“虽然无法在今天或者明天成为现实,但我们需要考虑过去、现在和未来”③“Georgia ‘may consider’ restoring monarchy after Patriarch’s sermon”, OC-media, June 19,2017, https://oc-media.org/georgia-may-consider-restoring-monarchy-after-patriarchs-sermon。此外,强调格鲁吉亚的身份认同,呼吁坚守家庭传统,促进国民生育率等,也是伊利亚二世的标签性观点。这既符合东正教传统观念,也带有鲜明的格鲁吉亚特色。
以上体现“传统、保守”思想的案例,是当代格鲁吉亚教会给外界的最主要印象,也是对整个国家产生无差别影响的客观事实。就体现“西向”的国家发展愿景而言,似乎在面对这些问题时,首先需要考虑的是当代格鲁吉亚现实的政治与宗教关系问题。而在包含政治、宗教、民众等角色在内的现实社会中,国家宪法的纲领性规定需要解释和应对的具体问题还有很多。格鲁吉亚的特殊性在于,虽为世俗国家,却承载着厚重的宗教传统。在格鲁吉亚社会当中,东正教居于绝对的主导地位。这不同于现当代其他国家实体面临的宗教纷争。同时,后苏联时代格鲁吉亚的国家建构又不得不承认包括东正教因素在内的精神遗产与西向转型目标之间存在的差别。由此来看,位于“东”“西”之间的格鲁吉亚仍处于新的过渡周期,理顺传统与现实的关系依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二)区域内国家利益纠缠中的宗教互动
伊利亚二世曾公开呼吁俄罗斯不要承认格鲁吉亚的分离地区。这可作为体现格鲁吉亚东正教会政治影响的事例,也佐证了教会因素已作为一种非国家角色出现在格鲁吉亚的对外关系中。对于两个都具有东正教传统的国家而言,虽有长时间的历史交织,但当代政治关系龃龉不断。无论怎样,在2008年后俄格政治联系中断的情况下,东正教是唯一被认同且有能力影响双边关系的角色,是承载精神记忆的行为体。2008年俄格冲突爆发后,格鲁吉亚东正教会多次呼吁停火、恢复和平,并希望有关方面通过政治协商解决问题。在8月10日的宗教活动中,宗主教表示,“呼吁大国能够尽力使这一冲突得以和平解决。我们没有和任何人战斗,我们只是试图保卫祖先的土地。我们认为(奥塞梯人)是兄弟,相信并且愿意继续保持兄弟关系”。①“As the Church defended the peace in South Ossetia”, August 8, 2018, https://incarnate wordsistershouston.org/as-the-church-defended-the-peace-in-south-ossetia虽然在停火问题上针对的对象也包括格鲁吉亚政府,但宗主教的表态实际上更多地体现出第比利斯的鲜明立场。在形势仍然危急的状态下,伊利亚二世亲往受战争影响严重的哥里地区,并与俄方军官进行了会面。在给俄罗斯领导人的信函中,教会领袖表示,“俄军战机轰炸格鲁吉亚市镇,作为东正教徒相互残杀的事件令人惋惜。并且,俄罗斯关于格鲁吉亚的屠杀指责完全是谎言”②“War splits Orthodox churches in Russia and Georgia”,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5,2008, https://www.nytimes.com/2008/09/05/world/europe/05iht-church.4.15929452.html。
虽然公开的消息大多显示,教会在危机情境下表现出投身国家事务的积极性以及推出以和平为导向的化解危机的建议,但似乎“除了一些公开表态之外,并未从宗教角度真正促成冲突的终结”③Ines-Jacqueline Werkner, “Religion and its importanc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 case study of 2008 Russia-Georgian war”, Caucasia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0, Vol.4,No.3, p.245.。这一观点来自“世界宗教会议(World Religions Conference)”时任主席汉斯·乌斯科(Hans Usko)。如果脱离涉事双方,从另外的角度看,乌斯科的表述似乎也具备客观性以及足以解释相关看法的逻辑支撑。围绕俄格冲突的案例,双方教会的表态均体现了对本国政治主张的呼应,相关做法也不出意外地成为各自政治目标的“帮手”。俄格冲突前后,俄罗斯东正教会以实际表态为国家决策“背书”,在宗教与政治融合的行为逻辑中,既充分利用宗教特点和优势,也明确表现出“政治化”的工具特点。对于俄罗斯东正教会而言,“莫斯科大牧首需要考虑政治现实,然而与格鲁吉亚教会的对话则更为重要”①“War splits Orthodox churches in Russia and Georgia”,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5,2008, https://www.nytimes.com/2008/09/05/world/europe/05iht-church.4.15929452.html,预示了双方关系未来的可能变化。
在俄格关系中,教会间的联系具有重要意义。具体来看,格鲁吉亚东正教会领袖多次呼吁俄罗斯,不要因阿布哈兹和茨欣瓦利地区②当谈到格鲁吉亚分离问题时,多语种文献中常出现“南奥塞梯”的表述,而格鲁吉亚官方对于这一地区的正式称呼习惯于采用“茨欣瓦利地区(Tskhinvali Region)”。而失去与格鲁吉亚的友谊。③Патриарх Грузии: о России, Абхазии, войне и сепаратизме. Илия II о российскогрузин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ях и последствиях войны 2008 г.//CredoPress. 11 февраля 2011.https://credo.press/118418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格方宗主教前往冲突前线的行程得到了俄罗斯教会的协助。此外,俄罗斯东正教会有关分离地区宗教事务的态度并未发生变化,即南奥塞梯以及阿布哈兹仍作为格鲁吉亚宗主教区的组成部分。④“”, https://patriarchate.ge;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ови. www.patriarchia.ru/db/organizations抛开政治层面上分离问题的固化状态,宗教层面的联络仍得以维系,这不仅涉及格鲁吉亚境内不同教区之间,也进一步扩展到俄格两国。但是限于某些问题在政治语境下仍然未能调和,因而宗教所发挥的助推作用也自然受到限制。这表现为格鲁吉亚与俄罗斯的当前关系仍处于停滞状态。
(三)精神记忆与西向愿景的相互调适
无论从地理还是历史维度,格鲁吉亚的发展都体现了介于“东”“西”之间的特点。作为当代格鲁吉亚处理与俄罗斯关系的比照,欧洲化的西向愿景是其国家政治的优先选择。事实上,无论从自然、人文地理视角,还是参考历史进程以及其中蕴含的精神记忆,格鲁吉亚案例中严格意义上的西方因素是有限的。如果一定要进行细致比较,那么来自拜占庭的传统宗教因素则毫无疑问位列第一;其虽历经千余年,但仍然在格鲁吉亚被视作认同度极高的社会存在。这可以解读为对“西方”文化基底的坚守,但不可忽视的是,东正教作为“传统”所传递出的保守思想及其与欧洲一体化存在的理念差异,将对格鲁吉亚产生长期的政治影响。
格鲁吉亚东正教会对待国家选择西向的发展道路持何种态度?基于伊利亚二世的一些表态,他也可“被视为一个带有普世思想且等同于具有欧洲心态的领导人”①Vladimer Narsia, “Church and Politics or Church in Politics: How does the Georgian Orthodox Church impact Georgia’s European Integration Policy?” Georgian Institute of Politics, Policy Brief, May 2018, No.14, p.1.。2014年3月在与欧盟负责扩大以及睦邻政策的官员会晤之后,伊利亚二世澄清了外界对其态度的错误认知,表示教会并不是格鲁吉亚实现“欧洲化”的障碍:“欧盟是格鲁吉亚人民十分熟悉的组织,我们将会努力使格鲁吉亚成为该组织的正式成员。”②Kornely Kakachia, “Is Georgia’s Orthodox Church an Obstacle to European Values?”PONARS Eurasia, June 2014.鉴于教会与国家之间存在“界线”,尽管代表格鲁吉亚教会发声的宗主教会不断在适当的时机就适当的问题发表观点——这也证明了其角色和影响力不断增加的事实,但在涉及政治领域的问题时,其作为仍然较为有限。
坚定推进“欧洲一体化”的工作,是“格鲁吉亚梦想”党作为主导政治力量的鲜明主张。因而,其对宗教团体倾注“友好”,正是谋求联动格鲁吉亚国家发展最重要的力量,并促成倾向西方路径的最大化实现。前总统马尔格维拉什维利曾公开肯定教会与格鲁吉亚身份以及历史的绑定关系,认为格鲁吉亚国家身份始于接受基督教。③“Georgian Orthodox Church celebrates 100th anniversary of restoration of autocephaly”,Orthodox Christianity, March 27, 2017, http://orthochristian.com/102211.html而伊万尼什维利掌握权力之后,与宗教代表进行了数次具有象征意义的公开会见,表示会继续资助教会事业。④“Assessments: Ivanishvili meets Orthodox Church”, April 12, 2019, https://civil.ge/archiv es/301841现任总统祖拉比什维利虽具有不同于其他格鲁吉亚政客的更为深厚的西方背景,但对教会的态度与历任总统没有显著区别。相反,其作为带有鲜明法国以及欧洲标签的总统,联想到与其家族存在关联的巴黎圣尼诺教堂⑤位于法国巴黎的圣尼诺教堂(Saint Nino Orthodox Church in Paris)于1929年由格鲁吉亚侨民所建。作为格鲁吉亚旅法侨民主席,现任格鲁吉亚总统萨洛梅·祖拉比什维利的父亲列万·祖拉比什维利(Levan Zourabichvili)对这一教堂的修建起到过关键作用。见“Georgian president: in my childhood I never thought I’d return to France as a president”,February 18, 2019, http://agenda.ge/en/news/2019/460; “Salome Zurabishvili attended the liturgy at St. Nino’s church in Paris”, February 17, 2019, https://1tv.ge/en/news/salomezurabishvili-attended-the-liturgy-at-st-ninos-church-in-paris,二者的结合似乎折射出格鲁吉亚未来的愿景,即欧洲一体化的目标与本国文化传统的契合。
支持和倡导国家“回归”欧洲式发展轨道的政治力量对待格鲁吉亚传统精神记忆内容的态度较为复杂。东正教传统与保守的一面,是欧洲主义者认知中的挑战性因素。近年来,东正教因素在格鲁吉亚当代国家发展中的角色效用被广泛讨论,重要的原因是政治精英关注格鲁吉亚东正教会广泛和稳定的社会基础。另外,东正教传统的保守特点以及当前阶段呈现出的加强趋势,也不可忽视。在地理方位上,格鲁吉亚所处的高加索地区毫无疑问在“东”“西”之间;在历史层面上,格鲁吉亚国家在不同时期面临来自“东”“西”的对手;在当前背景下,东正教会的保守成分与欧洲一体化的自由主义愿景,分别作为“东”和“西”的当代呈现,仍是格鲁吉亚需要应对的现实。
七、结语
以宗教为突出内容的精神记忆之于格鲁吉亚国家发展转型的特殊性,体现在地理、历史因素融合的多维空间,是不同时期生活在这一地域的居民在自然环境里、社会生活中以及个体认知范围内镌刻并加固的鲜明烙印。从公元4世纪正式接受基督教开始,格鲁吉亚国家的发展便与在这一地域内彰显特殊性的精神文化实现绑定。不论是在促成统一格鲁吉亚国家发展的“黄金时代”,还是在遭受外力侵扰的困境中作为族群联系的纽带,精神记忆的重要角色从未缺席。由于对宗教传统的坚守,高加索被赋予的“文明分界”意义在千年之后仍然没有发生改变。后苏联时代,精神记忆回归并参与了国家转型进程。但是,其传统的精神文化理念以及保守化的趋势,与现实国家发展的西向思维存在差别。
研究现实问题离不开对更多基础要素的梳理,当代格鲁吉亚国家发展转型中出现的困惑同样也与更为深刻的背景和根源存在关联。从历史路径追寻民族、宗教线索,是认识格鲁吉亚以及高加索地区其他地域的重要角度,而沿此路径进行的研究也验证了符合逻辑关联的解释。通过这些探索不难发现,在高加索的语境下呈现出多种贯穿历史记忆和当代现实的关联,它们的奇妙在于可超越时间维度、在同一空间内包容共生。特殊地域、丰富历史和深厚文化是高加索的特质,而从记忆的角度认识这一地域历史与现实的联系和区别,可以作为理解高加索故事的一个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