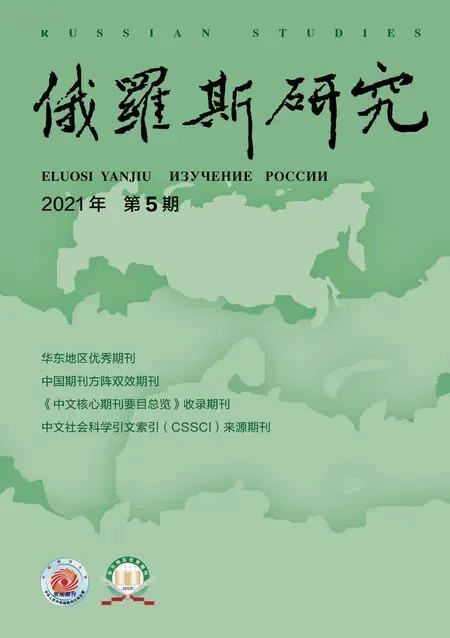文明论视角下的“俄国·中亚”空间建构及其对晚清中国的影响
黄达远 孔令昊
【内容提要】13世纪至19世纪,“鞑靼利亚”是西欧探险家和制图界对里海、乌拉尔山、西伯利亚、蒙古高原、七河流域乃至印度北部地区这一广大地理空间的笼统认识。这一词汇当时被视为“野蛮人”,带有种族、民族歧视意味。随着1492年大航海时代的到来,西欧逐渐成为文明的中心,排斥亚洲鞑靼,并将其作为文明欧洲的参照物。俄罗斯帝国的建立因与“欧洲鞑靼和莫斯科小鞑靼”具有身份关联而不被西欧认同。俄国建构乌拉尔山为亚洲边界,从而形成了欧洲俄罗斯和亚洲俄罗斯两大部分。其以“科学考察”构建新亚洲、以“中央欧亚”取代“鞑靼利亚”,来摆脱鞑靼身份使俄罗斯人彻底欧洲化、“文明化”,并基于“文明-野蛮”的合法性向中亚输出秩序。被认为属于“中央亚细亚”的还有晚清中国的西部地区,俄国通过不平等条约向该地区输出“文明-野蛮”的秩序,消解和侵蚀了中国的主权。“俄属中亚”与中国内陆边疆地区都被纳入了俄罗斯帝国文明等级秩序中,成为证明俄罗斯帝国“文明化”的牺牲品。文明论视角的研究,对于认识俄罗斯帝国的文化影响路径,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以往对俄罗斯在中亚地区扩张的历史,国内学界大多聚焦于地缘政治和殖民主义的视角。不过,英国学者奥兰多·费吉斯写作的《娜塔莎之舞:俄罗斯文化史》①Orlando Figes, Natasha’s Dance: A Cultural History of Russia,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Henry Holt and Company, 2002. 中文译本:[英]奥兰多·费吉斯著:《娜塔莎之舞:俄罗斯文化史》,郭丹杰、曾小楚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以及2006年出版的三卷本《剑桥俄国史》②Maureen Perrie,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Russia: Volume I, From Early Russia to 1689,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Dominic Lieve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Russia: Volume II, Imperial Russia, 1689-191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Ronald Grigor Sunny,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Russia: Volume III, 20th Centur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等,引入了“文明论”视角进行研究,也代表了俄国史研究的文化史转向。③参见“娜塔莎之舞:俄国史的核心意象与研究转向”,《澎湃新闻》,2020年8月29日。该文整理自张建华教授的讲座“从娜塔莎之舞说起——俄国史研究已经转向和如何转向”。“文明论”无疑是对传统地缘政治视角的一种有益补充。卡罗琳·汉弗莱就曾写道,19世纪中期,甚至更早,“俄国人就被认为肩负着一种‘天命’(manifest destiny),即驯服西伯利亚的大自然并推动东方停滞不前的亚洲社会文明化”④[英]卡罗琳·汉弗莱:“‘俄国’观念及其与中国边疆地区的关系”,袁剑、刘玺鸿译,载邢广程主编:《中国边疆学》(第七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23 页。。这从一个新的知识视角发掘了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十月革命前俄罗斯帝国的殖民者意识形态是如何通过“文明等级”来建立“殖民空间”以瓦解中国主权的。这曾经对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造成过巨大损害。到目前为止,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还相对较少,本文的初步探究,以期引起同行的关注和讨论。
一、去“鞑靼化”与欧洲化:文明论视角下的俄国国家建构
俄国历史学家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曾写道:“从8世纪大约持续到17世纪,俄罗斯人与草原地带的游牧民族、博罗维茨人以及噩梦般的鞑靼人的斗争在俄罗斯民族的记忆中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记,正如他们的叙事诗里描绘的那样,这是一段极其痛苦的历史记忆。”⑤[日]土肥恒之著:《俄罗斯:罗曼诺夫王朝的大地》,李文明译,北京:北京日报出版社,2020年,第298-299 页。尽管彼得改革使俄罗斯的文明疆域得以真正进行内涵性扩展,文明性质得到根本改造。不过,摆脱蒙古人统治以来,俄国在东、西、南三个方向的加剧扩张,形成了地跨欧亚、庞大的、多民族的殖民帝国:高加索、中亚、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等不同异质性区域,使得俄国的地缘政治形势也变得极为复杂,斯拉夫民族性、拜占庭-东正教信仰、鞑靼影响和彼得西化改革,始终没有化合成有机整体,而是形成了复杂的俄罗斯形象。①参见施展:“欧亚?帝国?欧亚合众国!——‘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叙事:俄罗斯’包头会议发凡”,载高全喜主编:《大观:第3 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年,第148-153页。这些空间扩张过程在某种程度上解构了时间性累积效应。叶卡捷琳娜大帝曾把俄国比作欧洲学校里的一名好学生,因为俄国主要就是通过模仿欧洲国家来努力实现“欧洲化”的。不过,俄国缺乏与欧洲殖民国家共同的地域结构——以大洋水体为物理分界的非洲、美洲、亚洲的海外殖民地。俄国的欧洲领土与大陆殖民地毗连这一事实,导致了地域结构差异,带来了“失序”,彼得大帝直到去世前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1725年,彼得一世时期的重臣瓦西里·塔季耶夫提出的方案得到了官方支持。他提议将帝国的领土沿着乌拉尔山分为欧洲和亚洲,这一分界是利用西欧殖民帝国模式这一基础来提供一张“新”的俄国地图。平缓的山脉在感知上有效地取代了海洋在分界时的地位和功能,借助领土在文明方面的关系对比,仿佛使山脉两侧的部分分别位于地球的两端——自然地理、气候、动植物、社会组织接受了人为的划分,成为欧洲与亚洲两部分。这样,俄国就与西欧殖民国家共同分担了将全球落后地区文明化的“责任”。而“天命”就是文明使命,将其与国家建构联系在一起,使得俄国形成了特殊的欧洲化过程。②Dominic Lieve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Russia: Volume II, Imperial Russia, 1689-1917,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49.“最初的‘文明论’,乃是近代西方人对于世界各地不同风土人情所划定的一套等级秩序,有分为野蛮(savage)、蒙昧(barbarian)、半开化(half-civilized)、启蒙(enlightened)、文明(civilized)五个等级的,也有分为三个等级的(野蛮、蒙昧、文明),还有分成四个等级的(野蛮、蒙昧、半开化、文明)。但无论是三级、四级,还是五级,这套等级秩序其实既有着空间上的内涵,也潜藏着时间上的指向,在对于不同地区和人民进行贴标签式的定义的同时,也暗藏着对这些地区当前处境和未来走向的限定。”①王鸿:“全球史、文明等级论与中国近现代史”,《中华读书报》,2017年1月25日。在这种情况下,首先需要厘清欧亚大陆上“文明人”和“野蛮人”的等级分类,从而明晰亚洲与“鞑靼”的关系。
在13世纪,欧洲人以“鞑靼人”来称呼分布于西亚、中亚和北亚的许多游牧部族。“Tar-tar原是古代一些游牧民族的部落名称,Tartarus则是希腊神话中的幽冥地府塔尔塔罗斯,13世纪中叶当蒙古人兵临欧洲之时,英国本笃会士编年史家马修·帕瑞斯(Matthew Paris)怀着恐惧与憎恨之情创造性地把这两个词联系在一起,称这些蒙古人是‘撒旦麾下令人厌恶的民族,像来自塔尔塔罗斯的恶鬼一样不断涌现,所以他们该被称为鞑靼人(Tartars)’。从此‘鞑靼人’成为欧亚大陆草原地区各游牧民族的通称。……于是在随后几个世纪的地理学想象中,鞑靼地区都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代表着威胁文明世界的蒙昧主义的温床。”②吴莉苇:“欧洲人等级制世界地理观下的中国——兼论地图的思想史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2 期,第197 页。“鞑靼”“亚细亚”或“东方”“伊斯兰”“亚洲”,成了与“欧洲”——进步的、世俗的、文明的、正面的——相对立的概念。
15世纪晚期,“欧洲理念仍然主要是地理的表达方式,附属于西方主流认同体系的基督教世界。等同于‘西方’的欧洲理念,是在‘大航海时代’的海外征服中,才开始巩固起来的。……君士坦丁堡于1453年陷落于土耳其人之手,1492年后西欧列强的殖民地扩张,作为这两件事的结果,欧洲理念与被视为特定的欧洲价值体系连接起来了,……欧洲不再仅仅指涉地理区域,还包括‘文明的’价值体系”。所以,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十字军理念复兴,“每次当欧洲受挫于穆斯林东方时,新世界的获得便大大增强了一种欧洲优越感”③[英]杰拉德·德朗提著:《发明欧洲》,陈子瑜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37-38 页。。这种由欧洲“文明的”价值体系而来的情绪,也刺激着重新定义欧亚地理分界的欲望:“1566年时,佛罗伦萨史学家出版了第一本以当代语言写成的《欧洲史》。欧洲在时间与空间中,都被定义为一个整体。这让制图学的发展成为可能。地图与书籍的到来使得欧洲有了一个明确的、可见的格局:欧洲大陆终于问世了。”①[英]杰拉德·德朗提著:《发明欧洲》,第54-55 页。而随着这种逐渐明晰的欧洲优越感,在欧亚大陆的划分过程中,一些被欧洲认为是相对落后的地区被划为“东方”:
18世纪的地图将高加索划归东方穆斯林地区,尽管从地理上来看它属于南方,而历史上它也是属于基督教西方。高加索地区的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所蕴含的基督教文明能够追溯到4世纪,比俄国皈依基督教要早500年。它们是欧洲最早信奉基督教的国家——甚至比君士坦丁大帝皈依基督教以及拜占庭帝国的建立都要早。②[英]奥兰多·费吉斯著:《娜塔莎之舞:俄罗斯文化史》,第443 页。
可见,欧洲和亚洲的地理分界,许多时候参照的是基于西方的“文明欧洲”理念,并伴随着新世界的产生而被重新定义。
到了17世纪末,欧洲学者已经开始将“文明欧洲”与“野蛮亚洲”互为参照,有古代宇宙志学者以“西徐亚”来称呼里海北边、多瑙河西边及奥克苏斯河东边的地带,被视为这段历史的源头。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Martino Martini)曾经在中国的东南地区生活,并经历了明亡清兴的历史时期。1654年,他在《鞑靼战纪》中写道:
亚洲是很多民族的发源地。鞑靼是最古老的民族,四千多年来一直是中华帝国的敌人。……
我所称为“鞑靼”的民族居住在北方,在长城的后面。长城自东向西延伸三百多德国里格,它是防止鞑靼攻入中国的堡垒。
由于中国语言中没有取“R”这个音,所以鞑靼(Tartar)自古被中国人叫作“达鞑”(Ta Ta)。在这个名称下,有我们欧洲人至今不知道的东鞑靼以及西鞑靼;撒马尔汗、蒙古、女真、奴尔干。其地域从“小鞑靼”(Lesser Tartary)和喀什噶尔王国东至日本海,到这里被连通美洲奥维奥拉(Oviora)的阿尼安(Anian)海峡所隔断。③[意]卫匡国著:“鞑靼战纪”,戴寅译,载杜文凯编:《清代西人见闻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2 页。
这份报告指出了以长城为界的鞑靼与中国内地的紧张关系,“西鞑靼”主要是指征服亚洲的蒙古人。聂仲迁(Adrien Greslon)是清初来华的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在华传教40年。1671年,他的《鞑靼统治下的中国历史》(Histoire de la Chine sous la domination des Tartares)一书出版,其中描述了清初“钦天监历狱”前后中国的教务概况、政体结构以及社会风俗民情,记录了1651 至1669年间中国发生的事件。文中的“‘鞑靼利亚’(拉丁语:Tartaria)是中世纪至20世纪初欧洲人对于中亚的里海至东北亚鞑靼海峡一带的称呼,尤指蒙古帝国没落后泛突厥人和蒙古人等游牧民族散居的区域,在当时的语境下包括中亚诸汗国、天山南北麓、蒙古诸部满洲等,因此,‘鞑靼利亚’是欧洲传教士、探险家等常用的地理用词”①张丹彤:“译序”,载[法]聂仲迁著:《鞑靼人统治下的中国历史》,广州:暨南大学澳门研究院,澳门:文化公所出版,2020年,第6 页。这里的泛突厥人指的是使用突厥语的游牧人群——作者注。。“鞑靼利亚”反映了欧洲传教士在基督教视野下的文明等级化的地理观念。
同样也是在17世纪末,参加过《尼布楚条约》谈判的法国传教士张诚(Jean-François Gerbillon)描述了“大鞑靼”的地理范围,指的是“亚洲位于日本北部的东洋、冰海(Frozen sea)、俄罗斯、里海、波斯、蒙兀儿(Mogol)、孟加拉附近的阿拉干(Arracan)王国、阿瓦(Ava)王国、中华帝国,与高丽王国之间的整个地区。所以大鞑靼西部以俄罗斯、里海和波斯的一隅为界;南部仍以波斯的那一部分、蒙兀儿、阿拉干和阿瓦两个王国、中国和高丽为界;东部以东洋为界;北部则以冰海为界”②[法]张诚:“对大鞑靼的历史考察概述”,陈增辉译,载杜文凯编:《清代西人见闻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86 页。。“大鞑靼”主要包括了欧洲以外的以长城分界的亚洲游牧地区,大部分区域都在当时的俄国和清朝的管辖下。在欧洲传教士的眼里,俄国与鞑靼的界限并不清晰,均属于“大鞑靼”的组成部分。与张诚共同参加过《尼布楚条约》谈判的葡萄牙传教士徐日升(Thomas Pereira)进一步在“大鞑靼”之内分了四种民族:满洲人属于“东鞑靼”;“西鞑靼”则包括喀尔木克人、厄鲁特人、喀尔喀人和就称为蒙古人的那些人;“回教鞑靼人”自西至东从波斯和里海一直分布到厄鲁特地区,在南面差不多一直到中国;第四种是莫斯科人统治下的民族。③参见[美]约瑟夫·塞比斯著:《耶稣会士徐日升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王立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3年,第219 页。至少在17世纪末期,已经有了莫斯科鞑靼的记录。
相较于17、18世纪欧洲传教士对“鞑靼”记载的语焉不详和混乱,到了19世纪初,德语世界最大的百科全书《布罗克豪斯百科全书》的前身《布罗克豪斯会话词典》(Brockhaus Conversations-Lexikon)第一版第六卷(1809年)的记载就明确得多,对“鞑靼之地”(Die Tartarei)进行了明确的地理划分:小鞑靼即欧洲鞑靼,大鞑靼即亚洲鞑靼。前者东、北接俄罗斯,西邻沃里尼亚(Volhynia),南濒黑海,包括克里米亚鞑靼和诺盖鞑靼(Nagaische Tartarei)。大鞑靼或亚洲鞑靼则位于亚洲境内,包括三大空间:其一为所谓鞑靼本部,居于鞑靼之地的西半部直至黑海沿岸;其二为卡尔梅克,在鞑靼之地内居中位置;其三为蒙古,居于鞑靼之地的东部直至东大洋沿岸。①Brockhaus Conversations-Lexikon Bd.6, Amsterdam, 1809, S.62-63. 资料及译文系西北大学丝绸之路研究院副研究员万翔提供。《布罗克豪斯会话词典》的解释将“鞑靼之地”分成了鞑靼本部、卡尔梅克和蒙古地区。
需要指出的是,《布罗克豪斯会话词典》在“鞑靼”(Die Tartarn/Tatarn)词条中的描述带有一定的蔑视性:这一粗暴的族群分布于中亚、北亚和俄国的欧洲部分,古时有斯基泰之称,可分为欧洲鞑靼和亚洲鞑靼两部。其中后者为由七位王公领导的七个部落,他们的勇武造成了巨大的恐惧,并于12世纪在铁木真(Temukin)的领导下,从一直统治他们的斯基泰国王王罕(Umham)麾下分离。铁木真以成吉思汗(万王之王)的名义,接管了王罕的大部分土地,从而成为如今称为亚洲鞑靼的鞑靼王国创始人。他也取得了大鞑靼可汗的称号,并带给野蛮的斯基泰人以更好的政体和法律。他的子孙后代如此强大而可怖,使周边各国乃至西里西亚(1230-1241年)都受到最具破坏性的袭击;其中很大一部分定居于伏尔加河、鄂毕河、顿河、多瑙河一带,从而成为后来欧洲鞑靼和莫斯科小鞑靼(Moscowische kleine Tartarn)的起源。②Brockhaus Conversations-Lexikon Bd.6, Amsterdam, 1809, S.62-63.游牧斯基泰人是鞑靼人的祖先,铁木真是大鞑靼可汗,鞑靼人征服欧洲以后定居在那里,并与当地人通婚和混血,结果产生了欧洲鞑靼和莫斯科“小鞑靼”——这种理解是俄国长期不被欧洲认同的巨大文化障碍,也是文明等级论的后果。
《布罗克豪斯会话词典》还记载了“鞑靼”的生活方式与人群特征:大多数鞑靼人过着游牧生活;但也有部分定居(如居住在阿斯特拉罕、撒马尔罕等著名商业都会)。大部分鞑靼人信仰伊斯兰教,也有一部分为拜偶像者(如卡尔梅克人)。他们的财富以畜群组成,主要是马,且以产良马著称,还有羊和骆驼。除了经营畜牧业,还常狩猎,善骑射,居住在便于移动的营帐之中。鞑靼人以勇武、大胆、善捕猎著称,其武器包括剑、弓和皮盾。此外,他们简朴、节俭而好客。对他们来说,马肉和马奶制成的饮品是最好的食物。①Brockhaus Conversations-Lexikon Bd.6, Amsterdam, 1809, S.62-63.鞑靼人中有游牧的鞑靼和定居的城市鞑靼;有信仰伊斯兰教的鞑靼和信仰佛教的鞑靼;游牧民是好战特征的人群,饮食以肉、奶为主。今天看,这些记载远远过时和失真了,但在18 至19世纪则是欧洲的标准词典内容。
18世纪开始,沙皇俄国因在欧亚大陆黑海区域(即上文所述的“鞑靼之地”)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经过多次战争,获得了黑海的出海口,并使黑海北岸的鞑靼地区变成了新的俄国地区,击败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一度也被西欧人视为“文明对野蛮的胜利”。随着这些俄国的扩张和现代化的过程,“东正教、专制和民族主义的三位一体——在尼古拉治下发展出来的官方意识形态的三个组成部分——巩固了教会在俄国社会生活中的中心位置、沙皇作为主权者的绝对权力,以及对于俄罗斯民族乃至泛斯拉夫人兄弟情谊抱有浪漫主义依恋的这样一种国家观念”②[美]查尔斯·金著:《黑海史》,苏圣捷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1年,第186-187页。。19世纪中期,克里米亚战争失败后,俄国转向了对中亚穆斯林鞑靼地区的征服,这些地区位于海权与陆权交汇的枢纽处,地缘位置十分重要。广大的鞑靼地区被俄罗斯帝国不断征服,在欧洲人看来更增加了帝国的野蛮性,而不是文明性。俄国为解决这一问题,则采取了“欧式”解释方法。19世纪60年代,俄国外交大臣亚历山大·戈尔恰科夫(Alexander Gorchakov)发布外交政策:俄国将如同美国之于北美,法国之于阿尔及利亚,英国之于印度一样,遵循类似的“天命”——给那些未开化的国家带来开明的社会和政治,并解决中亚人口大量流动的问题。③Alexis Krausse, Russia in Asia: A Record and Study, London: Grant Richards. Henrietta Street, Covent Garden, 1899, pp.224-225.这一时期俄国向亚洲腹地的扩张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版图扩张”,而是和欧美国家一样,获得了他们那种“天命”,从而对鞑靼之地的征服也被合法化、文明化了。
借助于乌拉尔山所象征的文化边界,将“鞑靼之地”一分为二,乌拉尔山以西的“欧洲鞑靼”和“莫斯科小鞑靼”成了“文明化”的欧洲部分,乌拉尔山以东的亚洲部分则成为俄国的殖民地、“亚洲俄罗斯”或者是被俄国文明征服的“野蛮人”地区。这成为考察19世纪至20世纪初俄国在亚洲扩张和进行帝国活动的一个文明论视角。但这是一种并不彻底的身份建构。1881年,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家日记》杂志上所发表的观点颇具代表性:
害怕欧洲说我们是亚洲野蛮人,害怕欧洲说我们与其说是欧洲人,不如说是亚洲人——这种自卑自贱的恐惧症必须摒弃。……我们这种不应有的耻辱感,我们认为自己只能是欧洲人,而非亚洲人(我们从来也没有中断过做亚洲人)的错误观点——这种耻辱感、这种错误的观点使我们在这两个世纪里付出了……极其高昂的代价。……丧失我们的精神独立性,……①《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18)作家日记(下)》,张羽、张有福、潘同珑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第971 页。
在我们转向亚洲,以我们的新的眼光观察亚洲时,在我们这里就可能出现类似欧洲在发现美洲的时候所遇到的那种情况,因为对我们来说亚洲确实是尚未被我们发现的当时那个美洲。……
在欧洲我们是寄人篱下的人,是奴隶,在亚洲我们则是主人。在欧洲我们是鞑靼人,在亚洲我们则是欧洲人。②同上,第977 页。
俄国历史学家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这样描述彼得改革以来所培养出来的“新俄国人”:“在欧洲他们被打扮成鞑靼人,在自己的祖国同胞眼中他们是出生在俄国的法兰西人。”③转引自林精华:《误读俄罗斯》,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34 页。Ключевский В. Сочинение в 12 томах. Т.2. Москва: Мысль, 1989. С.167.“去鞑靼化”而成为“欧洲人”——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的困惑长期伴随着俄罗斯帝国的国家建构。
二、文明论视角下俄国对中亚空间的等级建构
彼得大帝时期的重要理论家瓦西里·塔季谢夫明确提出乌拉尔山脉是两个地域范围(欧洲与亚洲)的天然地理边界。在全球范围内来看,这不仅是欧洲和亚洲之间的边界,同时也是另一个同样重要的边界,即将俄罗斯国内空间划分为欧洲部分和亚洲部分的“边界”。这样的划分也显示出“文明的欧洲俄罗斯”与“野蛮的亚洲俄罗斯(俄国亚洲殖民地)”的理解。他所表达的这种区分,即“欧洲的俄罗斯”和“亚洲的俄罗斯”的概念,一直沿用至今。①参见马克·巴莘:“地理的不确定性:关于俄罗斯、欧洲和亚洲的四个论题”,《俄罗斯研究》,2010年第4 期,第62-63 页。俄国地理学奠基人谢苗诺夫-天山斯基在他的回忆录《1856-1857年天山旅行记》中提出,俄国对于乌拉尔山以东的“亚洲”部分——德国地图中标识的“die grosse Tatarei”(大鞑靼地区)——的考察,与欧洲在美洲的考察具有同等的意义,欧洲人对美洲的殖民化和俄罗斯对亚洲的殖民化意义相同。同时,他还不服气地认为,现在俄国喀山附近的省份不适用于德国标识的大鞑靼地区,因为这些地方已经纳入俄国,也就是欧洲化了。②Семенов-Тян-Шaнский П.П.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в Тянь-Шань в 1856-1857 гг. Москва:ОГИЗ, 1947. С.57-58.出于对德国地理学家洪堡和李特尔的亚洲地理知识的质疑,俄国地理学家开始在亚洲内陆组织大规模的地理考察,这种科考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为亚洲地理更新、更正和补充了新的地理坐标,采集了相关的标本;另一方面,也给俄国地理学家披上了“文明发现野蛮”的外衣,并为之提供了合法性。
1870年起,俄国地理学会对亚洲内陆“鞑靼利亚”组织了系列考察,“著名的H.M.普尔热瓦尔斯基、Г.Н.波塔宁、M.B.佩夫佐夫……的考察队到中央亚细亚进行考察。……收集了各种各样的中央亚细亚地理资料。在旅行时采集了植物学、动物学、种族地理学、地质学方面的丰富的标本,并获得了完全改变关于中央亚细亚自然界概念的资料。还特别仔细而详细地进行了路线测量。这些路线测量以很多天文点和高度测量为依据。……因为正是他们的努力,才绘制成了现代亚洲大陆内部地区地图”③[苏]Н.М.休金娜著:《中央亚细亚地图是怎样产生的》,姬增禄、阎菊玲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2 页。。“地理发现”属于“文明民族”的特权,只有欧洲民族才是“文明民族”,欧洲以外的“低等人群”的地理发现都不属于“文明发现”,只有欧洲人的地理发现才算是“文明发现”。以新的文明秩序取代既有的“鞑靼秩序”,乃是俄国与西方殖民国家通约性的手段,也是俄国加入文明国家行列、解决其身份认同的有效方式。
从帝俄时期一直到苏联时期,地理大发现带来的自豪感一直被地理学家们所继承。1949年,苏联地理学家马格道维奇仍然认为,“所谓‘野人’和‘蛮族’(无文字的民族)到达无人居住的陆地或进行首次航海,对于研究原始文化的历史学家来说无疑是很有意义的。历史学家们依据他们所选用的术语,有时也将下述情况称之为‘发现’:例如有人谈到新西兰土人部落起初‘发现’了新西兰,而后又‘发现’了南大洋的一些小岛(查塔姆群岛),也有人谈到马来亚部落‘发现’了马达加斯加,北非部落(关奇人)‘发现’了加纳利群岛等等。但是大多数历史学者在经过慎重考虑以后都运用着另外一个术语:他们并不把这种第一次到达视为地理发现,而仅仅把它看作是处于社会发展低级阶段的人群迁移的一种形式。”①[苏]И.П.马格道维奇:“‘地理发现史概论’序言”,载Л.С.贝尔格等著:《地理发现与地理学史译文集》,郝克琦等译,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第3 页。按照马格道维奇的观点,所谓地理发现应理解为任一文明民族第一次到达该民族或其他文明民族皆不知道的地区。公元前2世纪,张骞出使西域,本来是人类地理大发现的重要篇章。可是,在文明论的语境里,张骞或不被承认,或被淡化,而谢苗诺夫-天山斯基在世界范围内的知名程度却要远远高于张骞。20世纪60年代,苏联地理学领域的学者休金娜依旧高度肯定帝俄时期的地理学家的成就:“如果把1840年洪堡的《中央亚细亚山脉和火山地图》与1899年的Э.久斯的《内亚山脉走向略图》作个对比,就可以得到中央亚细亚地图图形变化的鲜明概念。……只要浏览一下这两幅地图,就可以想象到我国旅行家们对绘制中央亚细亚地图所做的贡献是多么巨大。”②[苏]Н.М.休金娜著:《中央亚细亚地图是怎样产生的》,第201 页。通过加入地理大发现的“俱乐部”,俄国获得了一种与欧洲国家身份相应的认同。
站在中亚地区的立场上来看,他们则不幸成了被欧洲文明发现的“新大陆”,从而成了受害者。中亚史学家巴托尔德指出,18世纪对整个伊斯兰世界而言是一个充满危机的时期,如阿富汗的动荡和波斯的混乱。而在欧洲则恰好相反,这是一个最终确立欧洲文明的优势地位、并为欧洲人在整个世界的统治地位奠定了基础的、进步和改革的时期。①参见[苏]巴托尔德著:《中亚历史:巴托尔德文集第2 卷第1 册第1 部分》(上册),张丽译,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02 页。处于文明优势地位的“欧洲俄罗斯”名正言顺地对“亚洲俄罗斯”进行规训,19世纪60 至70年代的俄军将领把英国比康斯菲尔德勋爵对待阿富汗人的政策当作座右铭:“不要只打击亚洲人的脖颈,而且应该打击他们的想象力”②Терентиев M.A. История Завоевания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Том III). СПб.: Типолитография В.В. Комарова, 1906. С.38.。
“殖民论者”持有典型的军事殖民主义观点,从“文明等级论”衍生出的俄国中亚政策之一就是“殖民论”,主张中亚尚处于文明发展的较低阶段,短期内不可能按照欧洲俄国的模式进入帝国体系。俄国应当按照西欧殖民帝国的统治模式治理中亚。中亚民族在宗教、文化和历史方面同俄国文化有深刻区别,具有不可逾越的“独特性”。二者短期内很难相融。……只要中亚能够为帝国事业提供足够资源,政府应当尽量少干预中亚各民族的内部事务,以将力量集中于霸权争夺上。军事手段应当成为俄国中亚政策的基石。俄国的中亚政府应该区别于欧洲俄国的文官统治,而以军政府的形式存在。俄国中央政府陆军部和俄属中亚部分官员持此态度。③Daniel Brower, Turkestan and the Fate of the Russian Empire, Routledge, 2003, p.10.这种观点主要代表殖民者中的军方态度。
中亚政策之二则是“同化论”,这部分俄国征服者的意见是:“斯拉夫人”的故乡就是亚洲。他们认为回亚洲就是“返回故乡”。例如,任职于俄国突厥斯坦的地理学家文纽科夫上校提出,俄国定居者应该和中亚穆斯林部落通婚,以区别于靠种族隔离来征服的欧洲国家,通过“和平演进与同化”的方式,进行符合俄国人行为准则的扩张。④参见[英]奥兰多·费吉斯著:《娜塔莎之舞:俄罗斯文化史》,第486 页。
中亚政策之三是“进步论”,主张在中亚建立“文明秩序”(Гражданственность),提倡这一主张的主要是知识分子。其代表人物为尼古拉·伊尔明斯基,他自喀山神学院毕业后又去了喀山大学工作,“因致力于‘异族人’教育而为人所知。出于‘尊重民族性’的观点,他主张‘异族人’教育应从‘母语’教育开始,用母语讲授初级课程,使用母语版初级读本、道德教材,然后再徐徐导入俄语讲授的课程。也就是说,这种手段在不压迫、不限制民族特性的同时,带来‘非强制性同化’的效果”①[日]土肥恒之著:《俄罗斯:罗曼诺夫王朝的大地》,第244-245 页。。少数俄国知识分子对于中亚殖民政策还有一定的反思声音,如画家瓦西里·韦列夏金在圣彼得堡举办了作品展,他是俄国中亚战争的亲历者,对俄罗斯帝国在东方的“文明使命”深感怀疑。在作品中,他没有将游牧民族刻画成野蛮人,而是保卫家乡的平等的人类,对野蛮的帝国战争提出了控诉。他因此而激怒了俄国突厥斯坦总督考夫曼,这位总督甚至还动手打了韦列夏金。在各种压力下,他不得不离开俄国避难。②参见[英]奥兰多·费吉斯著:《娜塔莎之舞:俄罗斯文化史》,第483-486 页。
“穆斯林形象……是终将被东正教或工业文明取代的。”③孔源:“俄罗斯人认知中穆斯林概念的缺失”,《俄罗斯研究》,2005年第2 期,第95 页。这看起来是殖民论者心目中的认识,代表欧洲俄罗斯的“东正教-斯拉夫空间”高于亚洲俄罗斯的“伊斯兰-鞑靼空间”,意味着俄国行政当局一直在思考如何改变中亚土著的宗教信仰。1854年,西西伯利亚总督加斯弗尔德在呈报沙皇尼古拉一世的一份文件中提出了宗教改革的方案。他认为,在吉尔吉斯人(实际指哈萨克人)当中宣扬基督教是不可能的,因为游牧生活中的一夫多妻制与基督教教义相抵触。而他也担心庞大的吉尔吉斯民族加入伊斯兰教,又会与俄国的国家利益相抵触。所以,这位总督提供的方案则有些“另辟蹊径”:给吉尔吉斯人创造一种既合乎他们生活条件、又符合俄国国家利益的新宗教。也就是说改造犹太教,并推广到吉尔吉斯人当中。头脑还算清醒的沙皇尼古拉一世在这份“异想天开”的报告上忍不住批示道:“宗教不像法典的条文,可以杜撰”,然后连同报告一并退还给了加斯弗尔德。④Семенов-Тян-Шaнский П.П.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в Тянь-Шань в 1856-1857 гг. Москва:ОГИЗ, 1947. C.75-76.这件事正好被谢苗诺夫-天山斯基记载下来并写进了他的回忆录。尽管沙皇否定了加斯弗尔德的方案,但加斯弗尔德的种种担心却并非多余。巴托尔德很谨慎地指出,“伊斯兰教作为世界性宗教,几个世纪的历史已经证明了它的生命力。……任何其他宗教都不能代替它。伊斯兰教教义与其他宗教教义一样,有许多与科学结论和社会进步不相容的因素,……伊斯兰教的历史表明,它善于适应新的条件;毫无疑问,现代文明进程向所有宗教提出一个基本要求:宗教只是宗教,宗教不能要求国家和社会生活服从于宗教,伊斯兰教将要完成的这一要求,有违《古兰经》和《逊奈》的某些规定”①В.В.巴尔托里德:《伊斯兰教(概述)》,1918年,第92 页。转引自[乌兹别克斯坦]И.札巴罗夫、[乌兹别克斯坦]Г.德列斯维扬斯卡娅著:《中亚宗教概述》,高永久、张宏莉译,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15 页。。到了19世纪,伊斯兰教的改革已经成为俄国统治中亚所遇到的棘手问题。
“文明论”的等级秩序反映在物理空间上就形成了等级与隔离。中亚近代的铁路交通、现代学校、俄语区、俄国城区等新的空间中,这些都成为构筑“俄国·中亚”空间的重要方式,体现了等级观点和秩序。在俄罗斯帝国统治时期建立的城市都形成了与土著人城区分开的俄罗斯人城区。新俄罗斯城区后来成为与“土著的”或“亚洲的”城区相对立的部分,二者共同形成了一个城市。据统计,在浩罕、安集延、纳曼干、撒马尔罕、苦盏、乌拉-秋别、扎吉克和卡塔库尔干以及在锡尔河州每一座城市(突厥斯坦、奇姆肯特、奥利耶阿塔)都有类似的情况。塔什干是人口最多的城市,1865年大约有10 万人左右,作为俄国突厥斯坦总督府驻地后,俄罗斯人口曾达到5万人,是亚洲范围内俄罗斯人口最多的城市。1870年6月16日俄国颁布了城市条例,1877年推广到塔什干以后,一部分土著人获得了选举权。与俄罗斯人城区可以选出三分之二的议员相比,三分之一的议员由“亚洲城区”选举产生,而且具有选举资格的土著人是要懂俄语的。在城市照明等市政建设上最明显体现了以俄罗斯城区优先的特点。1887年年底之前,塔什干城中共有路灯606 盏,土著城区只有100 盏。从煤油白热路灯的安装情况看,1905年之前这种路灯全部安装在俄罗斯人城区。1909年,路灯共有321 盏,俄罗斯城区有297 盏,剩下24 盏灯安装在俄罗斯城区通往土著城区的道路上;从报纸看,俄罗斯人城区收到了849520 期报纸,土著人收到的报纸为24204 期。②参见[苏]巴托尔德著:《中亚历史:巴托尔德文集第2 卷第1 册第1 部分》(上册),第382-383 页。俄罗斯城区有东正教堂、俄语学校、剧院、政府机构、出版机构以及较完备的城市设施,这些公共空间的出现都代表了新的权力秩序,代表着文明进步的空间,相对而言,土著人城区则是“野蛮落后”的空间。
现代交通的发展也改变了原有的地域-空间的等级结构。沙皇政府在中亚修建的第一条国有铁路是外里海军用铁路。1880年在里海东南岸的米海洛夫斯克湾动工,陆续修到莫拉-卡拉、克孜勒·阿尔瓦特、梅尔夫、查尔朱和布哈拉,1888年修到撒马尔罕。1894年延长到克拉斯诺沃茨克。1899年,外里海铁路同撒马尔罕-安集延铁路及通往塔什干的支线接通后,易名为中亚铁路,从克拉斯诺沃茨克到塔什干,全长1748 俄里。这条铁路当时虽尚未与俄国铁路网相对接,但经里海水路可把中亚同俄国中央地区连接起来。奥伦堡-塔什干铁路是沙皇政府在中亚和哈萨克斯坦修筑的第二条国有铁路干线,全长1655 俄里,1906年1月1日起运营。奥伦堡-塔什干铁路与萨马拉-奥伦堡铁路接轨,纳入全俄铁路网。此外,俄国还鼓励修建私营铁路,如费尔干纳铁路、布哈拉铁路、特伊罗茨克铁路、七河铁路、阿尔泰铁路等。这一期间,修筑的铁路达到1500 俄里。①参见肖步升:“中亚和哈萨克斯坦铁路建设的启示”,《兰州大学学报》,1991年第3 期,第116-117 页。而铁路网的中心是俄国的欧洲部分。铁路是现代化的标志,铁路网构筑的新的工业化交通空间取代了驼队商路的交通空间,使得这些传统路线的影响下降。新兴城区令老城区黯然失色,使得地域-空间中心转到俄国新城区这边。在用欧洲技术绘制的新的中亚地图上,铁路交通网的出现,标志着空间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通过对19世纪中期俄国在撒马尔罕的统治的研究,亚历山大·莫里森认为,从经济价值角度来看,征服中亚的意义不大,对这些领土的管理成本远高于所能带来的收入。②参见施越:“评亚历山大·莫里森的《俄国在撒马尔罕的统治,1868~1910:与英属印度的比较》”,《北大中东研究》,2016年,第211-212 页。根据1868-1881年的统计数据,突厥斯坦总督区的收入约为5471.5 万卢布,支出为14059.6 万卢布,财政赤字为8588.1 万卢布。1868年至1881年间,每年的财政赤字为660.1 万卢布。如果加上俄欧地区向中亚输送武器和物资的费用,14年间的赤字达1 亿卢布。③参见[俄]M.A.捷连季耶夫著:《征服中亚史》(第三卷),西北师范学院外语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78 页。就俄国在中亚的统治而言,经济状况是收不抵支的;如果从俄国财政情况来看,整个19世纪俄国财政都是巨额赤字,危机严重。①参见裴然:《1881-1917年的俄国财政研究》,长春:吉林大学,2010年。裴然指出,俄国长期财政困难和赤字巨大,一个重要原因是非生产性支出(军事、行政债务)过高。但即便如此,俄国统治者认为,在中亚建立政区、划分疆界也是对“野蛮民族”的约束,潜台词就是欧洲人带来了“进步”,为统治当地建立合法性基础,也便于获得欧洲国家的认同。
美国学者简·伯班克和弗雷德里克·库珀在他们的著作《世界帝国史:权力与政治差异》中指出,“俄国正在把欧洲的价值观带给中亚诸民族。尤其是中亚地区被认为是这样一块殖民地,其可以通过俄国人及其他重视农业技术的民族的教化与殖民来使之‘文明化’”②[美]简·伯班克、弗雷德里克·库珀著:《世界帝国史:权力与差异政治》,柴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308-309 页。。需要指出的是,这一套新的空间秩序也解构了中国的天下观以及“西域”的地理和文化空间意义。20世纪初,曾在中国西部地区任领事的鲍戈亚夫连斯基在评述中国教育情况时所表现出的态度十分典型,他提到:
中国的教育与学科与我们西方的完全不同,毫无相似之处。在我们欧洲,除文学与抽象学科外,起很大作用的是现实的知识、有关自然与人类的知识和技术知识,或者说,主要是具有实用性质的知识,而中国人的教育内容则从下到上完全是文学与抽象性质的。现今中国的学校不讲授任何真正实际需要的东西。……只是不久前,在中国才出现了一些按欧洲方式建立起来的学校,而且仅仅是一些技术性的学校,因为中国人目前还仅认为只有这样的专业学校才对自己有些用处。③[俄]尼·维·鲍戈亚夫连斯基著:《长城外的中国西部地区》,新疆大学外语系俄语教研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225-226 页。
这位俄国领事站在“文明欧洲”的立场上指出了当时中国教育缺少实用性质的科学的方面,在“我们西方”“我们欧洲”的表达当中,似乎看不到他“欧洲鞑靼”“莫斯科鞑靼”的历史记忆。
三、“俄国·中亚空间”的形成对晚清中国内陆边疆的影响
刘禾指出,“主权这个概念sovereignty是现代国际法的根本,主权国家之间是不承认治外法权extraterritoriality的;严格地讲,治外法权违背国际法的主权原理。但有一个重要例外,这个例外是,主权国家可以对非文明国家实行治外法权。治外法权适用的非文明国家包括,半开化社会,野蛮社会,异教徒,劣等种族(非白人)等,因此,治外法权始终是在欧美国家以外实行的”①刘禾:“文明等级论:现代学科的政治无意识”,《中华读书报》,2012年7月11日。,因此,文明等级论也进入了殖民国家的法权体系中。19世纪“俄国·中亚空间”的建构,远远溢出了俄国边界,给中国边疆带来巨大的挑战,治外法权就是其中之一。在中俄签订不平等条约之前,由于天山山系都在清代中国的管辖之下,俄国探险家要考察天山的地理全貌,必须进入到清代中国的版图内,为此,他们不得不进行伪装,偷偷摸摸地进入我国边疆地区。而清朝国势衰弱后,俄国则以“治外法权”的名义公开组织科考队到新疆进行考察,因为在这样的语境中,欧洲以外的都是“野蛮民族”,无权发现地理和历史,只能“被发现”。实际上,正是援引这个“原理”,俄国科考队在中国境内的调查尽管严重损害中国主权,但是在“地理发现”与“文明发现”的名义下,披上了“治外法权”的外衣,并没有引起国际舆论的谴责,因为欧洲国家的探险队也纷纷涌入中国内陆边疆进行所谓的“科考”。
光绪年间中俄在西北两次勘界缔约,清廷勘界吃亏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缺乏精确的地图。虽然由传教士输入了经纬法,但运用不成熟,误差较大,地图上差之毫厘,实际可能丧地千里。这使边界谈判非常被动,中国丧失了大片国土。②参见郭丽萍:“西北界务谈判与西方地图使用——以光绪年间两次中俄西北界务谈判为中心”,《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2 期,第18-23 页。“俄国现代精密地图代表的是一套近代科学所理解的空间观念,运用近代地理学成果和测绘技术的产物,中国传统舆图的失败代表了天下时代的空间观念在现代民族国家博弈中的劣势。”③韦兵:“边疆形态与天下时空传统及其现代化进程”,《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 期,第108 页。俄国人发展了他们自己精心设计的“东方主义”思想,采纳了西方的观念,即俄罗斯的欧洲文化和文明对亚洲和亚洲人民的绝对优势。在科考中,俄国完全采用使用新式测绘技术得到的精密地图,在中俄划界谈判中占据优势,使得中国主权一再受损。
俄国地理学家梅彦多夫(Егор Казимирович Мейендорф)发现,“当时欧洲指称亚洲内陆的术语‘Tataria’,以及18世纪初开始流行的相关政治地理术语如‘Tartarie russe(俄属鞑靼利亚),Tartarie indépendante(独立鞑靼利亚),Tartarie chinoise(中属鞑靼利亚)、Grande et Petite Boukharie(大小布哈拉)、Grand et Petit Tibet(大小土拔特)’等概念都非常不准确”,他主张更换一个地理名称,并指出,“在地理学里,我们以某一民族之名命名某地,至少该民族应居于此地,否则定义就模糊而容易造成错乱。因此,应以‘中央亚细亚’来取代‘鞑靼利亚’这个术语,……这将更准确,更具备地理特性”①恽文杰:“19世纪初俄国对新疆和中亚汗国的探索及其影响”,《社会科学》,2018年第5 期,第159 页。。在东方学的影响下,地理的文明建构很大程度上也是服务于殖民国家的需要的,以“科学”的名义潜移默化地移植了文明等级论。
在“俄国·中亚空间”秩序下,俄国通过治外法权在中国内陆边疆城市建立的“侨民区”和“贸易圈”,在城市空间上自成一体,也是解构中国主权的一种重要的空间建构方式。“俄国侨民还享有一种特权,这就是在设有领事馆的地方,有权建立不与中国人混居的单独的居民点,这样的居民点,在中国西部地区称为贸易圈。在贸易圈范围内,中国政府当局完全不能行使权力。这样贸易圈就仿佛是俄国本土的一角。在那儿居住的是俄国臣民,行使的只是俄国的法律,遵循的是俄国的规矩。”②[俄]尼·维·鲍戈亚夫连斯基著:《长城外的中国西部地区》,第250 页。在俄国的中亚秩序中,又从“鞑靼之地”中区分出俄属鞑靼和中属鞑靼两个等级,前者是文明国家的鞑靼,后者是非文明国家的鞑靼。冯有真在《新疆视察记》中论及哈萨克人的特性时指出,“哈萨克人性极强悍不驯,但又极懒惰。除畜牧外,无其他职业”:
同光间,中俄二次划界,一部划入俄境,一部划入华境,在俄境者称为俄哈,在华境者称为华哈。双方关系殊为密切,甚至有兄为俄哈,而弟为华哈者,故彼等不问国籍,仍往返抢掠如故。①冯有真:《新疆视察记》,上海:世界书局,1934年,第22-23 页。
这种“俄哈”“华哈”是外人的划分,哈萨克人自己没有这种分别。“俄哈”和“华哈”的划分给予俄哈“先进”、华哈“落后”的观感,这种观念实际上是进一步瓦解了中国的“天下秩序”。
俄国领事鲍戈亚夫连斯基对于那些来自俄国的鞑靼人的描述和态度颇有代表性:“现在生活在中国,生活在对他们来说异常陌生的中国居民当中,这就迫使他们更加着力保持自己身上一切俄罗斯人的特点,并认为自己是伟大的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在俄国,他们对各种俄罗斯的东西也许会感到更生疏些,对于同俄罗斯居民在民族和宗教方面的差别感觉更敏锐些,而在异国,这种差别似乎是淡薄和消失了;至少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这样的。所有的鞑靼人都会说俄语。屋子里的陈设也是俄罗斯式的,比较富裕并有文化的鞑靼人甚至还订阅俄文报纸。他们中很多人还教自己的孩子学俄文,并认为这样做是很必要的。”②[俄]尼·维·鲍戈亚夫连斯基著:《长城外的中国西部地区》,第240 页。在这位领事看来,接受俄国文化就是文明民族,文明等级更高一些,俄属东干人(回族)外貌都比中属东干人好看,“只是俄国东干人似乎比中国东干人更柔顺和更坦率一些,这大概是由于俄国的政治体制更为温和,对东干人也更公正一些,对他们的性格造成的影响。他们不像中国东干人那样落落寡合,那样疑心重重。从外表上看,俄国东干人和中国东干人也不一样,中国东干人穿的是汉族服装,留着辫子,这辫子正是大清王朝国民的标志。俄国的东干人则不留辫子,穿着上模仿俄国的穆斯林鞑靼和萨尔特人,就是说,穿长袍,剃光头,头上戴着一顶小小的绣花圆帽”③同上,第241 页。。正如多米尼克·列文所指出的那样,“俄国实际上不是一个欧洲国家,而是一个‘欧洲化’的国家,既明显地领先于亚洲其他国家,也远远地落后于其他欧洲国家。……通过行使其帝国恩惠以及教化其亚洲殖民地,俄国将会增强并且发展其成为真正的欧洲国家所应具备的条件。……教化任务不仅仅是上帝赋予的、完全利他的一种责任,也是实现彼得大帝提出的欧洲化的一个重大机遇”④Dominic Lieve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Russia: Volume II, p.50.。俄国帝国形象的欧洲化包括许多方面,帝国或宗主国与臣服的殖民国家之间在地域上要存在显著差别就是其中的一个体现。俄国要看起来像海洋殖民国家,才能获得身份承认。俄国将中国边疆纳入殖民地并不一定都是通过武力手段、军事殖民以及不平等条约所取得的,其中一种隐性的殖民手段,是通过空间与秩序的建构来影响中俄边界两侧的少数族裔,如近代俄国探险家的科学考察记录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空间和地理空间的文明控制。文明等级论甚至渗透到各民族的精神空间和历史记忆中,无形中成为承认俄罗斯帝国作为文明国家的重要证据。俄属中亚近代工业化的起步,特别是铁路的修建,便利了俄国向中国内陆输出商品,俄国在空间上的某些影响和能力超过了主权国家,导致中俄之间的空间秩序出现失衡。1893年,陕甘总督杨昌浚、伊犁将军长庚、新疆巡抚陶模奏请尽快修铁路:“俟山海关外铁路工竣,即向西展筑,则秦晋驿道免重重差徭之累。新疆局势无鞭长莫及之忧,军务、矿务、赈务裨益良多。若格于浮议,日后敌人往来神速,新疆稍有疏虞,秦晋亦难安枕,似宜及早筹商。”①“光绪十九年四月十八日甘新巡抚陶模等倏议胡景桂奏新疆边务折”,《宫中档光绪朝奏折(第七辑)》,故宫博物院故宫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台北:东亚制本所,1973年,第726 页。随着俄国在中亚的铁路线不断延伸,在军事上,新疆无法与有着近代化国防的沙俄抗衡,“要把大车骆驼和火车赛跑,胜败之数,也可想而知”②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长沙:岳麓书社,1984年,第281 页。。“俄国”在近代中国长期被误读为一个全面欧洲文明化了的国家。
需要客观指出的是,俄国在中亚废除奴隶贸易,改革传统文化陋习,开办现代教育,建设现代交通……无疑是具有进步作用的;同时,俄国现代技术和物质文明体现在一些工业品上,这些工业品通过中亚的商业体系传播到内陆边疆口岸城市,如留声机、缝纫机、照相机、自行车、电讯器材、电报、电影等,使得边疆地区各族人民比内地更早接触到了现代性,体验到现代工业文明的生活方式。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俄国和东方相比确实是进步的。俄国的统治……对于黑海、里海和中亚细亚,对于巴什基里亚人和鞑靼人,都是有文明作用的”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 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85 页。,今天看来,这一分析依然十分中肯。
四、结语
诚如一些史家所评论的,俄国,正如对于西方国家一样,他们的殖民地扮演着构成帝国的重要角色,这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俄国稳定了乌拉尔山以西欧洲俄国的新兴身份认同。殖民地居民被看作具有相同而强烈的魅力、完全陌生的异国情调和民族志材料,在学习并编制帝国之巨大民族多样性方面付出了巨大的努力。①参见Dominic Lieve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Russia: Volume II, Imperial Russia,1689-1917, p.47; Y. Slezkine, “Naturalists versus Nations: Eighteenth-Century Russian Scholars Confront Ethnic Diversity”, in D. Bower and E. Lazzerini (eds.), Russia’s Orient.Imperial Borderlands and Peoples 1700-1917,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7,pp.27-57.实际上,中国内陆边疆作为俄国控制下的半殖民地性质的地区,同样成为构建俄国欧洲身份认同的重要资源。近代中国国家建构的“镜像”主要参照的是西洋(欧洲)和东洋(日本),正是以此为蓝本启动了中国从天下向“民族国家”的转型与建设。其实,“俄国·中亚空间”长期被忽略,地广人稀的内陆边疆和“中亚”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但是它构成了现代中国国家建构的第三“镜像”。20世纪早期的俄(苏)革命史固有其辉煌的一面,但是也不自觉地掩盖了“文明论”的影响,如地理发现依然深入到俄(苏)对东方社会的理解和观察中,而这一意识被近现代中国不自觉地接受,对苏联“老大哥”的认同其实也反映了“文明等级论”对中国社会的深刻影响。
实际上,今天的我们经常对中亚民族关系的变化感到困惑,常常受到19世纪俄国历史遗产——文明与空间中族群关系的等级性——的影响。因此,卡罗琳·汉弗莱指出的问题特别重要:“国家想象的角色——作为一种文明的‘俄国是什么’(what Russia is)这一不断改变的观念——在与中国接壤的东部边疆的建构中所扮演的角色,并且也尝试对这一边疆区域、其自我界定及其独特性之上的意识形态做出解释。”②[英]卡罗琳·汉弗莱著:“‘俄国’观念及其与中国边疆地区的关系”,袁剑、刘玺鸿译,载邢广程主编:《中国边疆学(第七辑)》,第22 页。也就是说,中俄双方的少数族裔对“俄国是什么”这类观念的地方性解释,通常要比国家政权中心所做的解释更引人注目。这一视角在本文中也是缺失的,拟另文分析。
马克·巴莘指出了当代俄罗斯国家的欧亚主义对早期帝国类型的反思,传统认为的俄罗斯帝国身份认同所导致的欧洲与亚洲部分的二元格局,很自然地为之后的反殖民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提供了合法性基础。而欧亚主义者则宣称,有着欧亚二分格局的俄罗斯不是亚洲的一个部分。欧亚主义者将欧亚理解为与欧洲或者亚洲完全不同的文明。为了替代这种西欧帝国模型,“欧亚主义学者阐述了一种明确的后帝国视角的俄罗斯-欧亚,它将是一种文化、历史和社会的混合体,一方面它是由多民族构成的,但同时它也是一个凝聚的、单一的和不可分割的实体,一种‘准’种族或‘超’种族单元。他们要求所有居住在这一广大区域的族群认识到并且承认这样一个客观事实,即它们都被一种共同的欧亚精神凝聚在一起”①马克·巴莘:“地理的不确定性:关于俄罗斯、欧洲和亚洲的四个论题”,《俄罗斯研究》,2010年第4 期,第64 页。。这种欧亚主义的解释力如何,以及是否会被俄罗斯的主流接受,只能拭目以待。
俄罗斯帝国正是通过去除“鞑靼”和“鞑靼利亚”的历史记忆,将其转化为中央欧亚或者中亚,成功“脱亚入欧”,转而成为新地理秩序的生产者。欧化的俄罗斯似乎切断了与“莫斯科小鞑靼”的历史联系。苏联给中亚诸民族创造出新的身份与民族认同,使鞑靼人转变成中亚民族,也塑造了新的历史过程。但是,在苏联解体后,中亚诸国在构建自身的民族主义的时候,游牧民(“鞑靼”)的历史也被民族主义激活,并进一步复苏。因此,对这一段历史要进行重新评价和整理,这关系到广大欧亚地区新区域秩序的现在与未来。总体而言,俄罗斯帝国时期国家建构的目的之一,就是使自己成功融入“欧洲”,获得文明者的身份。而这种身份的构建是以在中亚建立起“文明-野蛮”的统治秩序为重要基础的。由于俄罗斯帝国与晚清政府签订了多项不平等条约,不仅通过“治外法权”名义的科学地理考察以及建立贸易圈、侨民区的方式从空间上侵蚀了中国主权,而且还向亚洲内陆——所谓的“中央欧亚”“中亚”、中国内陆边疆各民族输出“文明-野蛮”的意识形态,以证明俄罗斯殖民帝国作为“欧洲文明”的合法性。俄国中亚历史学家斯维特兰娜·戈尔舍尼娜在自己的法文著作中指出,在西方或俄国的传统中,“中央亚洲”(Asie centrale)总是作为一个形态不定的整体出现,懂得服从于分割视野并接受所有的命名,不断被降为“文明世界”的边缘,接近“野蛮”,即使在新闻媒体报道中,“中央亚洲”也仍与西方和俄罗斯的新闻通讯社关系疏远,通常只有在灾难发生时才会被报道。①Svetlana Gorshenina, L’invention de l’Asie centrale: Histoire du concept de la Tartarie à l’Eurasie, Genève: Librairie Droz, 2014, p.551.鉴于这样的历史背景,对所谓“文明等级论”以及“中亚”“中央欧亚”等概念,从学术史和知识史视角进行研究和重新梳理是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