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名字叫城市
胡桑
帕慕克(Ferit Orhan Pamuk)在《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里设想了一类作家,他们在“天真”和“感伤”之间徘徊。他在书中写道:“天真的小说家和天真的读者就像这样一群人,他们乘车穿过大地时,真诚地相信自己理解眼前窗外的乡野和人。因为这样的人相信车窗外景观的力量,他就开始谈论所见的人,大胆提出自己的见解,这让感伤—反思型小说家心生嫉妒。感伤—反思型小说家会说,窗外的风景受到了窗框的限制,窗玻璃上还沾着泥点,他会就此陷入贝克特式的沉默。”“天真”让小说家听从经验的召唤,感受一片树叶降落的路线,感受秋日雨水在街面的轻抚,感受人与人之间的照拂。“感伤—反思”让小说家趋近智性地沉思,辨认经验的起源和限度,辨认生活的内外形式,辨认自我与他人之间的政治的、伦理的关系,甚至辨认超验的存在。他心目中的小说家试图找到天真小说家和感伤小说家之间的平衡。在帕慕克看来,一个作家,成为既是天真的又是感伤的(反思的)作家,就既忠实于自己的经验,能够穿透自己的经验,又能够对这个自己与他人共在的世界进行打量、观察、提炼和创造。

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Ferit Orhan Pamuk)
帕慕克的写作大致有两大类:一类是把伊斯兰的过去作为背景去讲述一个悬疑、神秘的故事,比如《我的名字叫红》《白色城堡》等;另一类是关注现实的、当下的伊斯坦布尔,比如《黑书》《纯真博物馆》《我脑袋里的怪东西》等。前一类小说偏于感伤,后一类小说偏于天真。当然,这只是强行的分类,其实帕慕克的写作一直在试图汇合天真和感伤两条溪流。他的每一部书都有着令人难以忘怀的个性。《我的名字叫红》的激情与开阔,《雪》的愤怒与冲突,《黑书》的幽深与敏感,《纯真博物馆》的甜蜜的忧伤与任性的欢愉,《伊斯坦布尔》则将帕慕克自己嵌入了传统的幽暗不明的版图。在这些书里,帕慕克处理土耳其,尤其是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和他自身存在之间的关系。他忠实于现实,也想象,他的大多数小说和散文采用了普鲁斯特式的写作方式,章节之间错落松散,并非环环相扣,却有着波斯细密画一样斑斓的细节和谨慎的构形。他一方面处理、安放自己的经验与记忆,另一方面又要呼应传统的光照与阴影。他的书的核心故事往往十分简略,背后卻总是安置了一个流动的、复杂的意识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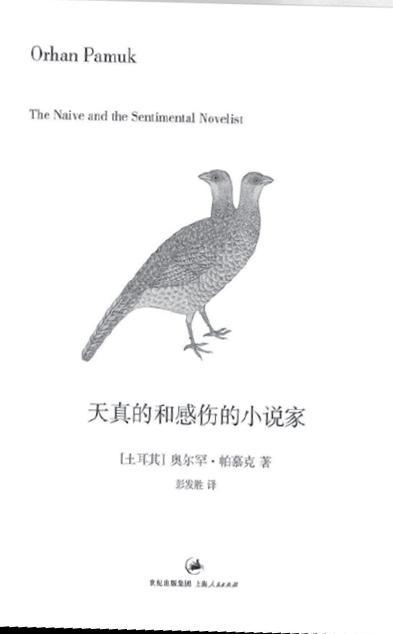
《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彭发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年版

《我的名字叫红》沈志兴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年版
伊斯坦布尔是帕慕克之城,比如在《黑书》《纯真博物馆》里。特别是《伊斯坦布尔》,让他得以深情地打量这座城市,召唤这座城市内在的魂灵。事实上,帕慕克从未离开过这座城市,除了短暂的漫游,他一直生活在这座城市的各个地区,没有离开过童年时代的房屋、街道和邻里。我们都知道,伊斯坦布尔是一座古老的城市,拜占庭帝国的都城,当年的君士坦丁堡。埃布鲁·宝雅(Ebru Boyar)的《伊斯坦布尔:面纱下的七丘之城》讲述的却是这座城市作为帝都的终结之日:一四五三年五月二十九日,那一天,奥斯曼帝国攻占了君士坦丁堡。帕慕克在《伊斯坦布尔》中是这么讲述这个日子的:“对西方人来说,一四五三年五月二十九日是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对东方人来说则是伊斯坦布尔的征服。”(《土耳其化的伊斯坦布尔》)伊斯坦布尔正是一座夹在东西方文明裂缝中的城市。帕慕克笔下的伊斯坦布尔既是一座一四五三年以来摇身一变的新的都城,“土耳其化的伊斯坦布尔”,又是一座奥斯曼帝国瓦解后的“废墟之城”,“充满着帝国斜阳的忧伤”。这是他在《奥尔罕的分身》这一篇中写下的文字。他继续写道:“我一生不是对抗这种忧伤,就是(跟每个伊斯坦布尔人一样)让她成为自己的忧伤。”帕慕克在自己的记忆之井中,一直在辨认着两股洋流交汇时的冷暖和缓急,更是在拓印自己身上的记忆失落的忧伤。

《纯真博物馆》陈竹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年版

《伊斯坦布尔》何佩桦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帕慕克将《伊斯坦布尔》视为自传,至少有一半是自传,另一半是关于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的,关于他童年眼中的这座城市,以及他在历史迷雾中搜寻而得的记忆幻景。但是,“自传”并不意味着这是一份经验的档案文献,恰恰相反,这是一个关于自我的构造物,是一座容纳复杂自我的创造性的建筑。事实上,帕慕克热爱绘画,在伊斯坦布尔科技大学所学专业就是建筑,他的祖父是建筑师,父亲从事与建筑相关的生意。不过他最终没有成为纸上的建筑师—画家,和现实中的建筑师。《伊斯坦布尔》的结尾如是写道:“‘我不想当画家,我说,‘我要成为作家。”
帕慕克在《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里面提到过一个观点,文学是第二生活。作家生活在自己创造出来的语言的构造物里,才能建构出真正的生活。他在《伊斯坦布尔》的开篇《奥尔罕的分身》里就追问过,姑妈家墙壁上挂着的自己的照片里,是不是“住在另一栋房子里的奥尔罕”,那是另一个自我的幽灵?显然,帕慕克并不觉得自我是单数的、稳定的,自我是复数的、流动的、增殖的。童年帕慕克痴迷于镜中的自己,邂逅“我的另一个陌生人”。(《母亲、父亲和各种消失的事物》)进言之,帕慕克笔下的伊斯坦布尔也在流动和增殖,甚至在被虚构。
在这本散文里,帕慕克到底如何建构起了一座城市?他说在三十五岁时曾梦想写一部《尤利西斯》风格的伟大小说,用来描写伊斯坦布尔。我们知道,《尤利西斯》就是一本漫游之书,有关漂泊、自我找寻、拯救心灵而失败。而帕慕克写的四位作家—记事录作者希萨尔、诗人雅哈亚、小说家坦皮纳、记者历史学家科丘都在伊斯塔布尔“终身未娶,独自生活,独自死去”(《四位孤独忧伤的作家》)。
《伊斯坦布尔》在两处提及了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漫游者的归来》(The Return of the Flaneur,准确的译名应是《游荡者归来》[Die Wiederkehr des Flaneurs])。这篇文章是本雅明为弗兰茨·黑塞尔(Franz Hessel)的《柏林漫步》(Spazieren in Berlin)写下的一篇书评。本雅明在其中提到一个观点,只有那些浪迹、闲荡到别处的人,才会想要去观看一个城市的异样的风景—“异国情调或美景”(《西方人的眼光》)。换句话说,本地人不能作为异乡人看到自己的城市,那么就只能成为闲荡者,与自己的城市拉开距离,才能揭示本地的别样风景。这个距离是时间的距离,而不是空间的,是时间上不可能回返的眷恋和怀念,这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思乡,而是带着由时间催生出来的陌异眼光去审视自己的城市。本雅明在《游荡者归来》中写道:“作为本地人去描绘一个城市的图景,会诉诸另外的、更深的动机。进入往昔而不是他方旅行的人的动机。本地人的城市之书(Stadtbuch)总是与回忆录有着亲缘关系,作家不是随随便便在这里度过童年的。”对于本雅明而言,他既是柏林本地人,又是一个离开了柏林的异乡人,但是,对于柏林,他只是一个离开了本地的本地人,而不能成为异乡人。他只能成为一个时间上的而不是空间上的异乡人,在回忆中将柏林转化为景观。乡愁只是来源于成长和离开,但是,还有一种时间上的追寻,即意识到了自己与童年的距离之间隔着一段逝去的历史,一个社会的流变。本雅明写过一本回忆性散文集《1900年前后的柏林童年》(Die Berliner Kinderheit um 1900)。这本书写于被纳粹帝国驱逐出境之后,身居国外,他才开始明白即将和自己的城市永别。这是他写作这本散文集的力量来源。他在序言中写道:“我试图克制它(乡愁),通过一种审视过去事物的不可追回性,是那种必然的社会性的不可追回性(notwendige gesellschaftliche Unwiederbringlichkeit des Vergangenen),而不是偶然意外的自传式的(zuf?llige biographische)不可追回性。”帕慕克说过,康拉德、纳博科夫、奈保尔这样的作家穿越了语言、文化、国家、大洲甚至文明的边界,他们的想象力来源于背井离乡的无根性。毫无疑问,本雅明的柏林书写源于无根性的痛切,因此,他笔下的事物充满不可追回的距离感,尽管这种距离感并非乡愁。然而,帕慕克与本雅明的相同之处在于,他的想象力居留在这座城市,他必须在伊斯坦布尔的根部去接受这座城市,审视、沉思和重构这座城市。“伊斯坦布尔的命运就是我的命运:我依附于这个城市,只因她造就了今天的我。”(《奥尔罕的分身》)本雅明说黑塞尔不描绘(beschreibt),只叙述(erz?hlte),帕慕克也是这么做的,他在叙述伊斯坦布尔的多重记忆,但我们很少看到他描绘让游客欣喜若狂的景观,除非是在记忆装置里重构出来的景观。
帕慕克通过本雅明发现,当地人在对城市的观看中“始终渗透着回忆”(《西方人的目光》)。《伊斯坦布尔》试图揭示给世人的正是记忆中的城市,或者说是城市赋予帕慕克的记忆。帕慕克说,伊斯坦布尔有一个“内视灵魂”。内视灵魂凝视着烟雾弥漫的早晨、刮风的雨夜、海鸥筑巢的清真寺圆顶、汽车排放的烟雾、烟囱冒出的袅袅煤烟、冬日里空寂荒芜的公园、冬夜踩着泥雪赶回家的人们。内视灵魂萦绕着“帝国终结的忧伤”,“痛苦地面对欧洲逐渐消失的目光,面对不治之症般必须忍受的老式贫困”(《黑白影像》)。于是,这座城市给帕慕克留下的记忆里盈满了冬日的寒意。这座城市在黑白影像里诉说着“失败、毁灭、损失、伤感和贫困”(《勘探博斯普鲁斯》)。

帕慕克在伊斯坦布尔,2016
记忆有着星丛的形态。帕慕克出生于一九五二年,他经历的自然是二十世纪后半期的伊斯坦布尔,但是他将记忆延伸到了十九世纪甚至更为久远的过去,延伸到个人记忆之外的历史深处。他不断回溯作为土生土长的伊斯坦布尔人的童年记忆,又一再援引十九世纪西方作家的书写记忆,同时拼贴着拜占庭帝国的记忆碎片。
在《巴黎评论》访谈中,帕慕克坦言自己是一个西化主义者,而十九世纪的伊斯坦布尔正是一个热衷于西化的城市,陆续迎来了奈瓦尔、戈蒂耶、福楼拜。有意思的是,他们都来自本雅明所谓的“十九世纪的都城”巴黎,当时的现代性中心。他们的行旅书写帮助雅哈亞和坦皮纳等当地诗人创造了一种城市形象。奈瓦尔在这座城市溃败之前来到这里,“去关心帮他忘掉忧伤的事物”(《奈瓦尔在伊斯坦布尔》)。因此,他的描述吸引了大量西方作家前来伊斯坦布尔寻找异国情调。戈蒂耶则深入城市的“侧面舞台”,深入贫民区,探索废墟和陋巷,“在脏乱之中发现了忧伤之美”(《戈蒂耶忧伤地走过贫困城区》)。当福楼拜来到伊斯坦布尔时,“和奈瓦尔一样,他越来越厌倦在这些地方看见的丑恶冷酷、神秘的东方情调—他对自己的幻想已经生厌,现实战胜了他,这些现实比他的梦想愈发‘东方,因此伊斯坦布尔激不起他的兴趣。(他原本计划待三个月。)事实上,伊斯坦布尔不是他要寻找的东方。在致布勒的另一封信中,他追溯了拜伦的西安纳托利亚之旅。激发拜伦想象力的东方是‘土耳其的东方,弯刀、阿尔巴尼亚服饰、栅栏窗户遥望大海的东方。但福楼拜则偏爱‘贝多因人和沙漠的炎热东方,红色非洲的深处,鳄鱼、骆驼、长颈鹿”(《福楼拜于伊斯坦布尔》)。更何况,福楼拜正在遭受梅毒的折磨,因此,他不能在东方获得快乐,反而感到了羞辱。伊斯坦布尔的东方异国情调在这三位法国作家身上的逐渐黯淡,让位给了粗粝的现实。正是这样一种“现实”加强了帕慕克的自我认同。他在外来者的镜像里寻见了这座城市的形象。东方经由西方而重新发现自己,发现自己身上的传统性,也遭遇了自己身上的现代性。奈瓦尔他们将巴黎的现代性目光引入了伊斯坦布尔。他们先于本地人占有了这座城市。这一点让帕慕克感到自己不属于这座城市,于是产生了一种与这座城市之间若即若离的关系。现代性就是一种目光的移植,它让传统成为碎片,并嵌入破碎不堪的现代生活,交织为景观。
“西化”正是现代性目光的聚焦,这让伊斯坦布尔在奥斯曼传统之外获得了一个新异的面目,以至于让从小生活在这座城市的帕慕克发现,外国人所描写的后宫、奥斯曼服饰和仪式与他的经验有着天壤之别,就像在描写一座别人的城市。正是“西化”,让帕慕克得以超越“民族主义和超越规范的压力”,“让我和伊斯坦布尔的数百万人得以把我们的过去当作‘异国来欣赏,品味如画的美景”(《西方人的眼光》)。凝视的目光颠倒了过来,本地变成了远方和异乡,本地生活重组为景观。这种颠倒和错位的目光,正是帕慕克的写作装置。
帕慕克让自己转变成了一个身处本地的“陌生人”。他邀请我们去陌生地凝望奥斯曼的传统及其废墟上的美景,去欣赏伊斯坦布尔的后街,那些不为人所知的角落,“贫困潦倒和历史衰退的偶然之美”。更重要的,为了看见它们、欣赏它们,我们要追随帕慕克,首先“必须成为‘陌生人”。然后我们就可以在废墟中观看如画的美景:“一堵塌墙,一栋败坏、废弃、今已无人照管的木造楼阁,一方喷头不再喷水的喷泉,一座八十年来未再制造任何产品的工厂,一栋崩塌的建筑,民族主义政府打压少数民族时,被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遗弃的一排房子,倒向一边而不成比例的一栋房子,互相依偎的两栋房子,就像漫画家喜欢描绘的那样,绵延不绝的圆顶和屋顶,窗框扭曲的一排房屋。”(《美丽如画的偏僻邻里》)这些美景是由陌生人的目光所绘制的,因为在本地人眼里它们只意味着贫穷、衰败、绝望和丑陋。
帕慕克想要写伊斯坦布尔整座城市的“忧伤”,这种忧伤有一个特殊的名字—“呼愁”(Hüzün),这个词在土耳其语里面本是忧伤的意思,“用来表达心灵深处的失落感”(《“呼愁”》)。
呼愁其实是空间中的时间装置。在这种忧伤中,时间开始重组空间。在帕慕克笔下,呼愁拥有了现代性的意味,不再只是对不可追回的过去的感伤,而是新旧的交织状态中呈现出来的废墟感—废墟感来自伊斯坦布尔的两次断裂:第一次是与拜占庭,第二次是与奥斯曼。第二次断裂对帕慕克而言最为切身。这就是他在童年时代就开始感受到的“西化”。拜占庭过于遥远,而正在失去的奥斯曼以及正在急速到来的西方就像邮戳一样镌印在帕慕克的记忆里,也成了他写作的血液。康拉德、纳博科夫、奈保尔、布罗茨基、鲁西迪都是漫游作家、流散作家,他们可以在时间和空间的距离中凝望自己的故土。但是帕慕克没有怎么离开过伊斯坦布尔,他所要思考的就是如何才能获得一种对这个城市的别样的照拂和目光?于是,他发明了“呼愁”。在呼愁的召唤下,他将过去视为陌生的影像,在记忆里四处游荡,从而与现实拉开了距离。写作,需要这样一段距离,从而构造出现实的影像。作家往往震惊于一段难以克服的时间距离。当意识到一些事物在时间中,尤其是在个人生命的长度之外,诞生和消失,“感觉就像幽灵回顾自己的一生,在时间面前不寒而栗”(《奈瓦尔在伊斯坦布尔》)。
呼愁的分量在帕慕克的书中是逐步增加的。《白色城堡》十分贴合于过去,过去的记忆成为背景。《黑书》则发现了一个切身的当下在场的城市,就是伊斯坦布尔。《黑书》被认为是小说版的《伊斯坦布尔》,其结构是双线交织的:一部分内容是卡利普寻找失踪的妻子如梦,另一部分内容是专栏作家耶拉对伊斯坦布尔这个城市的生活的全方位呈现。然而,《黑书》中的伊斯坦布尔是当下的伊斯坦布尔,本地人自己的伊斯坦布尔。到了《我脑袋里的怪东西》,帕慕克开始通过外在的目光来看待这座城市,主人公麦夫鲁特从外地逐步进入伊斯坦布尔,最后得以在伊斯坦布尔生活。当然,麦夫鲁特后来发现真正的伊斯坦布尔并不在眼前,而在虚构中。什么是虚构?每一个作家尤其是小说家都在虚构,作家职责就是虚构。但是这是老生常談。帕慕克的独特的虚构方式是在深入往昔的旅行中重构世界。《我脑袋里的怪东西》里的麦夫鲁特发现了梦幻和记忆,从而虚构出了自己想要的伊斯坦布尔。

《黑书》李佳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版
帕慕克关注童年记忆中的伊斯坦布尔,关注后街、郊区、废墟里的伊斯坦布尔,关注历史上的伊斯坦布尔—拜占庭的和奥斯曼的伊斯坦布尔,关于外来者眼中的伊斯坦布尔,关注西化进程中的伊斯坦布尔。在多重镜像中,伊斯坦布尔才变得越来越丰满和完整,这一切都是景观,却又是无从把握的稍纵即逝的碎片。呼愁就是时间锋刃上的感伤。伊斯坦布尔,这座呼愁之城,不仅承载着帕慕克的忧伤,也容纳着这个世界的记忆与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