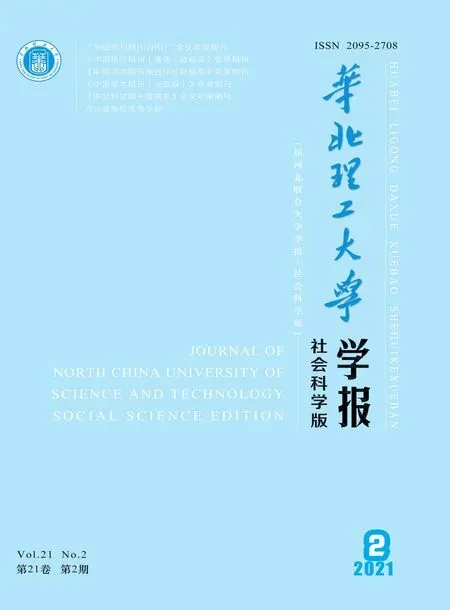《出师表》四个英译本对比研究
张 云,申连云
(扬州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扬州 225127)
引言
生态翻译学是清华大学胡庚申教授提出的中国翻译原创理论,用于描述翻译现象。该理论以生态整体主义为理念,以达尔文的“适应与选择”理论为基础,从生态视角对翻译进行综观和描述。[1]生态翻译学的翻译方法集中表现为三维转换,即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的转换。在三维转换下,优秀译文的标准不再限于忠实于原文,也不再只是迎合读者,而是要实现译文能在新的语言、文化、交际生态中生存和长存的目标。[1]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通过语言、文化、交际的三维转换,最终实现译文的最佳整合适应。[2]
《出师表》是诸葛亮北伐中原之前给后主刘禅上书的表文,表达了自己誓将完成先帝遗愿,收复国土的决心。[3]读罢《出师表》,读者便能深刻地体会到诸葛亮的人生智慧与赤诚之心,“一字不可删”!近年来王洛勇老师英文版《出师表》爆红网络,众多网友对此版本表示赞赏。“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诚然,王洛勇老师的优质口音以及恢弘的背景音让观众沦陷,但他的翻译算不上译作精品。而许多观众是通过王洛勇老师的朗诵才知道《出师表》的英语翻译。可见,如此经典的作品翻译却没有引起广泛关注。
《出师表》罗慕士译本与邓罗译本出自两位译者所译《三国演义》第91章,谢百魁译本来自其译本集《中国历代散文译萃》,罗经国译本选自其所译《古文观止精选汉英对照》。为了便于描述,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三个维度将分开叙述,但并不意味着每个维度只在该翻译过程中起作用。在具体翻译过程中,语言、文化、交际等种种因素是互相交织,互联互动,难以分割的。[4]
一、语言维转换
由于用语习惯、文化背景、社会历史发展不同,英语和汉语在语言表达的形式、特征和风格上也各不相同,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需要对语言形式进行适应性选择转换。[5]在语料库分析软件WordSmith4.0中,统计了形符(token)、类符(type)、类符/形符比(type/token ratio,TTR)、句数(sentences)和句长(mean(in words))。统计结果及对比情况见表1。

表1 《出师表》原文及四种译本词、句统计
形符是文本的总词数,类符是文本中的不同词数。随着形符的增加,类符增加并没有形符明显,所以通常以1000词来统计类符/形符比,称为标准类符/形符比(standardised TTR,STTR)。《出师表》原文及译文形符不高,类符/形符比便可以反映文本的词汇丰富度。从上表可以看出,罗慕士译本词汇最丰富,也最接近原文。由于原文为古文,语言极为凝练,所以译本类符/形符比与原文都有一定的差距。在句数与平均句长方面,罗慕士、邓罗与谢百魁的译文句数基本一致,都与原文有差距,但罗经国句数最多,与原文差距最大;四个译本的平均句长差距不大,且都接近原文。
《出师表》四个英译本整体上用词差异不大,都很好地做到了语言维的转换,保证了译文与原文意思一致。但罗慕士在语言维度的选词却更胜一筹,其余译者与其相比,用语略显平淡。详见表2。

表2 四译本语言维用词对比
“危急存亡之秋”中的“秋”,指某个时期(多指不好的),谢百魁、邓罗、罗经国都将其译为“moment”或“juncture”,但罗慕士译为“season”。“season”最常见的意思是季节,但也有时期的意思;“秋”最常见的意思是“秋季”,而文中取“时期”的意思。相比较而言,罗慕士的译文较好地保持了原语生态与译语生态的平衡,“season”一词构建了一个与原语生态颇为接近的生态环境,达到了更巧妙的语言维度的转换。
“小人”在文中特指朝廷上的坏人,所以邓罗的“mean people”与罗经国的“mean persons”只是传达了一般意义上的小人,没有做到正确的语言维转换。罗慕士和谢百魁指明了具体的人,也就是“courtiers”,因此这两个译文在译语生态里更富于生存的活力。
“临表涕临”,当诸葛亮看着这份奏表,内心突然汹涌澎湃。这个哭应该是心潮起伏,泪水模糊了双眼。罗慕士的“blind”一词非常形象生动,再现了当时诸葛亮眼泪模糊了双眼的场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完美地展现了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诸葛亮的忠士形象跃然纸上。
二、文化维转换
原语和译语是两种不同的语言,除了语言差异外,文化自然也存在千差万别。为了避免曲解原文,译者除了做到语言维度的转换,自然也需做到文化维度的转换。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需要有文化意识,将原语中的文化内涵传递给译语读者。《出师表》中有许多文化负载词,官职、自谦、尊称与禁忌语是其中主要四类。为了能更清晰地说明问题,四类文化负载词已做出统计,并选取部分具有代表性的示例对比分析各个译者在文化维度的适应性转换。表3为《出师表》原文四种文化负载词分布。

表3 《出师表》四种文化负载词类型分布
综观各译本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方法,主要有以下五种:音译加注(加注为音译时的一种翻译技巧)、直译、解释、套译、仿译。音译指用译语相同或相近的文字符号翻译原语;[6]直译指在词汇意义及修辞的处理上不采用转义的手法,在语言形式的处理上,允许适当的变化或转换,以使译文符合目的语规范;[6]解释与套译都属于意译,是意译的细分。解释法指解释性翻译,不用目的语的惯用语来替换原文;[6]套译也是一种解释,但是通过套用目的语的惯用语来实现的;[6]仿译不拘泥于原文,可能通过浓缩删减只译出某些信息,也可能通过增添扩充译出比原文更多的信息。[6]具体例子如表4所示。

表4 文化负载词翻译方法示例
从以上界定可以看出,音译加注、直译、解释、套译、仿译这五种翻译方法对文化的损伤依次递减。翻译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方法可以体现译者在文化维转换所做的努力。具体分布情况如表5所示。

表5 四译本文化负载词翻译方法分布
整体上看,罗经国译本在文化维的转换效果最佳,罗慕士和谢百魁次之,邓罗最差。但具体情况还需例证证明,因为同一种翻译方法,用词不同,则文化维转换的效果也会有细微差异。表6、7、8为部分具有代表性的示例。

表6 四个译本官职翻译对比
“侍中为正规官职外的加官之一,秦始置,两汉沿置。侍郎为汉代郎官的一种,本为宫廷的近侍。东汉以后,尚书属官任满三年称侍郎。”[7]显然这两个官职是有区别的,谢百魁与邓罗都将两个官职统称为ministers或the High Ministers,翻译得不明晰,可能误导读者,并且没有表达出原文两种官职的区别,没有给读者传递汉语中原汁原味的文化,中国文化味荡然无存。罗慕士与罗经国都分别翻译出来了,但罗慕士采取依归于译语生态环境的做法,将官职名用译语中的对应词表示,没有重复且达意,做到了文化维的转换,译语读者也容易接受。罗经国则是依归于原语生态环境,以拼音直接表示,加注释说明侍中、侍郎是一种什么样的官职,很好地保持了原语的文化生态。
根据史书《三国志》记载,蜀汉建兴五年(227年),诸葛亮创作《出师表》,郭攸之、费祎的官职是侍中,董允是侍郎。在译文中,罗慕士只是区分了两个官职,并没有指出对应人是谁;而罗经国指明了,但他犯了一个低级错误,误将费祎的“祎”拼成了Wei。原文并没有指出侍中、尚书、参军、长史是谁,但罗慕士和邓罗为了让译语读者了解当时情况,便补充了各自是谁担任该职务。但可惜的是,邓罗漏译了“侍中”一职,并且有一个语法瑕疵(在三者并列时使用“both”一词)。谢百魁依然使用minister指代这三个官职,这样的翻译可能使西方读者曲解文意。罗经国依然使用音译加注释的翻译方法,译文留下了原文的文化印迹。
从文化维度转换看,邓罗与谢百魁的翻译导致了中国古代官职文化内涵的部分丢失。罗慕士和罗经国都传递了原语的文化内涵,但各有利弊。罗经国的异化处理保留了中国文化的原汁原味,可能吸引读者的好奇心,传播中国文化,但读者可能不愿阅读繁琐的注释。罗慕士站在译语读者角度,直接归化了官职名,没有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文化,但读者阅读没有阻碍,十分流畅。

表7 四个译本自谦与尊称翻译对比
原文“愚以为”是自谦语,谢百魁译为“I think”,邓罗译为“my advice”,没有体现出自谦的语气,中国文化中的“谦虚”遭到了损伤。罗慕士译为“in my humble opinion”,“humble”一词则再现了原文的情感色彩,罗经国使用相反的手法,用尊称反向表达自谦,“I respectfully opine”,实为异曲同工之妙,他在第二处“愚以为”那里便使用了表示自谦的“humbly”。“庶竭驽钝”指的是“希望竭尽自己平庸的才能”,也是一种自谦的说法。除邓罗外,其余译者都用了表示自谦的词语,如“humble”,“inferior”和“mediocre”,罗经国更是将具体意象都翻译了出来。邓罗对原文中的文化生态的损伤是显而易见的。

表8 四个译本禁忌语翻译对比
“死”被认为是一种不吉祥的事情,人们总是选择主动避讳,不能避免时便用其它词语委婉表达。普通人的死亡都会委婉地表达,中国古代封建等级制度森严,对于皇帝的死亡那更是重中之重。皇帝去世不能直接说死,有委婉的说法,即“崩殂”。综观四位译者的译文,只有罗慕士采取了与中国文化最为贴合的用词。他没有直接用与死相关的词来表示,选择了含蓄委婉的“be taken from”。邓罗却直接使用了“death”,谢百魁和罗经国用词委婉程度居中。原文第二次出现“崩”,罗慕士也委婉地使用了“end”来表达皇帝的去世,而谢百魁、罗经国、邓罗没有做到文化维的转换,将原语转为译语时,原文的委婉程度被损伤了。“遗诏”指皇帝临终时所发的诏书。罗慕士的选词“last edict”最为委婉地避开了“死亡”,邓罗与谢百魁用词中规中矩,但罗经国却直接写明了“死亡”(death),没有避开禁忌语的出现。
三、交际维转换
“交际维侧重点在交际层面,主要关注在译文中是否体现了原文所要传达的交际意图。”[5]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译文的完整性与准确性必须得到保证,错译与漏译都没有做到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译文只有尽可能忠实完整地传达原文的内容、准确无误地再现原文的表达形式,用新语言的新面貌去传达原文的老形式和老内容,才能在“汰弱留强”的翻译生态中被广为接受、长久流传。译者最基本的责任就是将原语文章完整地传递给译语读者,出现了漏译,甚至错译,都损坏了原文的交际意图。四个译本都有不同程度的错译与漏译,具体分布情况如表9所示,部分典型范例如表10所示。

表9 四个译本错译与漏译分布

表10 四个译本错译与漏译对比
“臣亮言”为臣子上表的规范格式,罗慕士尽可能去芜存菁,最大限度地与原文保持一致,又不失古雅。邓罗漏译了这一重要格式。谢百魁译文则稍显啰嗦。罗经国译文与罗慕士不相上下,简洁明了。罗经国的译文表明“先汉”为“西汉”,“后汉”为“东汉”。实际上“先汉”“后汉”到底指什么,这也是一个不确定的问题。但罗经国认为“先汉”“后汉”分别为“西汉”和“后汉”,这显然有误。“西汉时王莽篡权、绿林赤眉起义”与“先汉兴隆”有悖,“东汉光武中兴”便不能称为“后汉倾颓”。[8]而罗慕士、邓罗、谢百魁都直译为“the Former Han”,“the Former Hans”或“the Earlier Han Dynasty”与“the Later Han”,“the Later Hans”或“the Latter Han Dynasty”,避开了语义处理。费祎这一人名则明显是罗经国的误译。“三顾”可以体现刘备的“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罗慕士漏译了这一重要信息。“夙夜”即早晚,泛指时时刻刻,邓罗模糊译成:“从那时开始就一直担心”。但谢百魁只翻出“at night”,丢失了“夙”这一信息。“不知所言”本不是大问题,罗慕士、谢百魁、罗经国三人都正确表达了出来。但邓罗可能当时误读了原文,译成了相反的意思。
四、结语
“翻译是语言的转换,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又是交际的沉淀。”[1]翻译与语言、文化、交际三者互相交融。一个译文要在译语生态环境长存,就需保持原文与译文的语言生态、文化生态、译语生态的协调平衡。当然,翻译不只是三维转换,只是这三维应该是最主要的。翻译过程中的适应性选择与选择性适应是多方面的,[1]这也是为什么虽然分维度比较四位译者的翻译,但每个维度又夹杂着其它维度。
合而观之,在语言维,罗慕士译本语言更丰富,与原文最为接近,在选词方面更为精当;在文化维,罗经国采用的翻译方法对文化损伤程度最低,但对于禁忌语的翻译,在同种翻译方法下,罗慕士的语言更能传递中国文化;在交际维,邓罗漏译最多,罗慕士和谢百魁分别有一个漏译,罗经国错译最多,邓罗有一个错译。通过比较分析可知罗慕士译本整合适应选择度较高,但也并非尽善尽美。
在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翻译是一种类似生物适应与选择的复杂活动。译文想要在“汰弱留强”的翻译生态中存活生长,就需要译者多维度地选择性适应和适应性选择,至少需做到语言、文化、交际维度的转换,从而使之与原语生态环境协调平衡,译语读者便可无语言障碍地阅读原语作品。[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