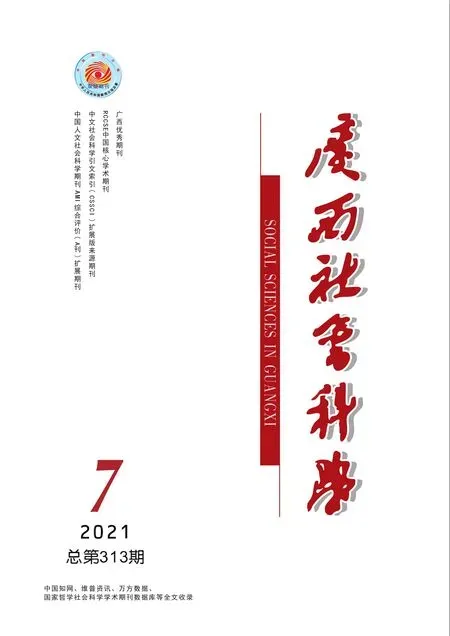浮现与消隐:花山岩画在越南传播的媒介反思
刘文军
(广西艺术学院 影视与传媒学院,广西 南宁 530022)
花山岩画位于广西崇左市左江流域及其支流明江流域,是壮族先民骆越人于春秋至东汉时期在石壁上绘制的岩画,据称被用于祭祀,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花山岩画雄伟壮观、神秘莫测,具有艺术性和考古价值,是骆越人留下的艺术瑰宝,并于2016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在古代中国,关于花山岩画的记载较少。目前已知的记载仅在《续博物志》(宋·李石)、《异闻录》(明·张穆)、《粤西丛载》(清·汪森)、《广西通志》(清·谢启昆)、《宁明州志》(清·黎申产)、《考辨随笔》(清·黄定宜)中可见。与此相反,越南古籍中却有大量关于花山岩画的记载。《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是由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和越南汉喃研究院于2010年合作编写的越南文献汇编,其中收录的文献记载了1314—1884年越南使臣在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交流经历,包含32份关于花山岩画的诗文和图画,是研究花山岩画的珍贵资料。这些越南文献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可以作为反观中国的“异域之眼”。
从2013年起,中国学者开始关注到《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中关于花山岩画的记载,并对其进行梳理和研究。黄权才在《明清两朝来华使节的花山诗篇》中列出他整理的16篇越南使臣书写花山的诗文,并按照时间顺序辑录及做简要的笺注[1]。张惠鲜等在《浅论越南使臣与花山岩画》一文中将相关文献扩充为32篇,其中包括绘画。在此基础上,论文从文献数量、文体、形成时间、描述深浅层次、花山岩画形成观等不同维度对32份文献进行详尽分析,并探讨越南使臣关注花山岩画的原因[2]。何永艳在《越南花山岩画文献研究》中基于32份文献的记述历程进行三个阶段的分期,并阐述了文献的艺术性与学术性[3]。同时在《越南使臣书写花山岩画的多重因素》一文中,何永艳在张惠鲜等人的研究基础上从地理、文化和利益三个方面阐述了越南使臣书写花山岩画的动因[4]。以上4篇论文开启了中国学界对越南使臣的花山岩画书写的研究。学者们从越南使臣的众多诗文和绘图中打捞起关于花山岩画的文献,并不断对其进行扩充、整理和分析,弥补了中国文献对花山岩画记载数量的不足,有助于还原花山岩画在古代社会中的真实面貌。但这些文献主要从文献学和艺术学两个维度对诗文与绘图进行梳理研究,缺乏其他学科视野的关照;同时,这些研究大多是对文献文本本身的研究,而没有跳出文献之外,将文献作为社会的标本,并分析其反映的社会生态与历史变迁。
针对32份越南使臣书写花山岩画的文献,结合历史与当下,有很多值得探讨的问题。比如,为什么处于中国的花山岩画在中国典籍中“消隐”,却在越南文献中“浮现”?花山岩画在古代越南受到越南使臣的高度重视,当下是否也被越南民众所关注?为此,本文试从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切入,以媒介变迁为视角,对比分析花山岩画在中越和古今“浮沉”的状况并分析其背后的原因。
一
花山岩画多次出现在越南使臣的诗文和绘画之中。从1597年冯克宽书写《过花山》开始,直至1882年裴樻撰写诗文、范文貯绘制《如清图》,前后历时近300年,总共26名越南使臣书写和绘制的32份文献提及花山岩画。越南使臣大量而持久的关注,和中国典籍“默不作声”状况形成鲜明对照。究其原因,与花山岩画的地理位置及越南使臣使用的交通工具有关。
花山岩画所在的左江流域处于中国西南边陲,广西虽然在秦朝时期就被纳入中国的版图,但其长期被认为是“南蛮之地”,因其偏远,而“距离是封闭和隔离社会的手段”[5],因此成为中原王朝流放犯人之地,著名文人柳宗元就曾因政治斗争而被贬为柳州刺史。广西左江流域又因为其江流曲折、两岸高山阻隔等地理因素而被“遗忘”在中原文人的视野之外,古代著名旅行家徐霞客曾游历广西,为上林县等众多地方留下宝贵的文字,但游记中却没有花山岩画的只言片语,其中就有可能是因为崇山峻岭“阻挡”了徐霞客的脚步。花山岩画在历史上可以说几乎被中原隔离和遗忘了。
花山岩画所处的左江流域虽然具有封闭性,但作为媒介的水路却让它同样具有开放性。高山造成“封闭性”,江流则带来“开放性”。左江发源于广西与越南交接的枯隆山,在越南境内的上游被称为奇穷河,在凭祥市边境平而关流入中国境内,进入龙州县城之后被称为左江。其后勾连崇左市和扶绥县城,最终从南宁汇入郁江,即百色段右江。而所谓的左江流域更是涵盖广泛的区域,因此,左江成为水路交通要道,长期发挥着重要的水运功能。作为沟通中越边境的要道,左江长期是越南使臣入关之后继续燕行的主要通道,久而久之便成为固定的朝贡路线。越南使臣曾以和当地州官冲突等原因为由请求更换线路,但都被清朝皇帝回绝,并将以水路为主的朝贡路线确定下来,不予更改[6]。因此,左江就像纽带一样,跨越中越边境,串联中越。“左江流域封闭却开放的文化地理因素为邻国越南成为花山岩画最早的异域之眼提供了‘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地缘优势”[7],花山岩画因为深处边陲的高山之中而向中原封闭,但左江却在峭壁间“铺开”水路,“万山中断一河奔”[8],使得花山岩画向越南开放,因此花山岩画虽然是不动的山体,但却游走在越南使臣的笔尖,入诗入画,在越南燕行古籍中多次浮现,明清两朝经久不衰。
水路犹在,但时过境迁,花山岩画在越南的传播于互联网时代衰落。通过检索越南语版的维基百科、YouTube、Google、Facebook等网站发现,与“花山岩画”(Các bức vẽ trên đá của Hoa Sơn)相关的文字音频寥寥无几,且主要以介绍地理位置、历史成因为主,点击量少。花山岩画在水路中浮现,却在网络中消隐。从水路到网络的转变是媒介变迁的重要问题,媒介环境学派的开创者马歇尔·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一书中以《道路与纸路》为题,分析了纸路从道路脱离之后的加速运动对中心—边缘结构的影响,“过去曾是中心—边缘结构的边缘区域的,如今成为独立的、建立在新兴的封建结构基础之上的中心”[9]。麦克卢汉选择媒介发展过程中的关键节点进行对比分析和论述,其实同一种媒介的方向转向也同样能够造成中心—边缘之间的动态关系的变动,继而造就帝国之间强弱盛衰的更替,如果仔细考察地理大发现时代威尼斯和马六甲在世界地理中的位置以及英法和西班牙、葡萄牙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位置,就不难发现水路航线的变动对地理中心和世界格局的深远影响。
中心和边缘的二元结构确实随着媒介变迁而相互转换,但麦克卢汉没有言明的是:中心—边缘结构不是单层和线性的,而是构成“中心—边缘链条”。比如藩交关系中的中越被置换到地理位置中,那么中国处于中心、越南处于边缘,越南使臣仪式性的朝贡是从边缘向中心的行进;而花山作为越南使臣必经之地和入关之后燕行的起点,是清政府都城和越南二元地理中的区域中心。因此地理层级并不仅仅只是中心和边缘之间的二元对立,构成“中国—越南”的地理关系,其间往往夹杂着区域中心,形成“中国—花山岩画—越南”的多层次地理关系。花山岩画在地理关系链条中身份本身是多元的:在中国的地理中,它是边缘的;在越南的朝贡线路中,它又是区域中心。也正是因为如此,花山岩画才会在越南典籍中“浮现”。
从水路到网络的转变自然带来中心—边缘动态关系的调整,“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不断加速超级内部连接的世界,一个‘全球性的世界都市’,充斥着激发着深刻复杂的文化转换和重新结构的传播互动和交流系统”[10],藩交时代的中心中国和边缘越南在互联网时代有更多联结,昔日的边缘越南虽没有转换到中心位置,但其作为独立国家在政治上具有与中国平等的地位。曾经在水路时代保持区域中心地位的花山岩画却在网络时代几乎被彻底遗弃和遗忘。水路左江就像一条金丝线一样,为越南使臣串起诸如花山岩画等文化景观的明珠,它的通路是线性的、独立的、唯一的,花山岩画成为越南使臣绕不过去的关卡;但网络正如一张节点众多的渔网一样,虽然花山岩画还是渔网上的一个节点,但渔网的通路是网状的、缠绕的、多元的,花山岩画只是越南民众擦肩而过的节点。
从水路到网络,花山岩画经历了浮现与消隐、连接与失联。在水路时代,花山岩画在中国典籍中消隐,却在越南典籍中浮现;在网络时代,原本在越南世界中获得连接的花山岩画再一次被动失联。媒介变迁不仅仅只是转换中心—边缘,其再造中心的同时也革除了麦克卢汉所没有关注的区域中心,花山岩画从水路到网络变迁背后的媒介转换自有其深意。
二
花山岩画在越南的浮现与消隐、连接与失联主要是交通工具的变迁所导致,除此之外,与此相关的语言文字的更替也在花山岩画的消隐和失联过程中产生了一定的作用。
花山岩画在越南古籍中的传播有赖于汉字在古代越南的广泛使用。秦朝时期,越南的北部归象郡管辖。973年,“大瞿越国”独立,丁部领请封于北宋,越南才正式改变藩属国的性质,形成中越之间的朝贡关系,直至1885年在西方殖民主义的冲击下,持续近千年的朝贡关系终结。宗藩和朝贡关系划定了中心和边缘,决定了文化高地和洼地,加之越南对中国科举制度的引进,使得越南社会精英能够熟练地使用汉语,并且汉字从西汉末年传入越南始到12世纪都是越南的官方文字。燕行使臣往往能够“娴熟地运用汉文撰述使程日记,书写往来公文,以汉诗咏叹摹写各地风光,并与中国朝野士绅文字交流”[11]。多次出使中国的阮攸家学深厚,和众多父兄形成“鸿山文派”,其出使中国途中书写的汉字诗集《北行杂录》收录132首,值得称道的是他将中国青心才人的小说《金银翘传》用喃字写成叙事长诗。足可见,汉语是越南使臣出使和游历中国、了解和书写花山岩画的基础。
越南使臣至少通过两个渠道了解花山岩画,而汉语在两个渠道中都是重要的沟通媒介。最为直接的知晓方式是问询。面对花山岩画,越南使臣向船夫、州官和其他人询问关于花山岩画的故事,比如阮攸有诗云,“远时拟问千年事,船户摇头若不闻”[12],诸如此类的询问被多次写入诗文,由此可见,对花山岩画的好奇心让越南使臣忍不住询问身边人,并因而得知花山岩画和黄巢之间的传说。询问和对答中汉语都是交流的媒介。同时,间接的方式同样重要,从已有的32份关于花山岩画的文献可知,共有26份文献提到了“黄巢”这一历史人物,花山岩画和黄巢传说相互裹挟,在越南汉文典籍中不断浮现和延续。特别是潘辉益和潘辉泳爷孙两人前后间隔60年分别出使中国,同样留下关于花山岩画和黄巢传说的诗文。由此可见,花山岩画以口头或书面的形式在越南传承;可以想象,每一位越南使臣在燕行之前都或多或少听说过关于中国的讲述,而仔细阅读之前使臣书写的使程日记、诗文和绘画,则成为他们了解中国的必备功课。越南使臣无论是和花山岩画直接对话,还是在口头传说和书面文字中与它偶遇,汉语都是必不可少的沟通媒介,由此花山岩画才得以被汉语记载、讲述和传播。
19世纪法国入侵越南后,殖民者用拉丁语创造新的越南文字;直至1917年,越南官方废除科举和汉字的传授,汉字在越南才退出历史舞台。汉语和越南语之间形成沟壑,阻碍了中越两国之间更为顺畅的沟通,从而切断了花山岩画和越南社会的联系,“砖石泥土埋葬”了花山岩画,后者在废墟中失联和消隐。如前所述,在Google中用越南语搜索“Các bức vẽ trên đá của Hoa Sơn”,出现的条目非常少,花山岩画淹没在互联网海量的信息之中。
语言文字是桥梁,也是沟壑。可以说,语言的相同将花山岩画和越南使臣勾连起来,花山岩画才能在越南古籍中被连接和浮现;而语言的不同则将花山岩画和越南民众隔离开来,花山岩画又在越南语互联网中失联和消隐。更有意思的是,如果仅仅只是搜索“Hoa Sơn”(花山),出现的第一条是越南语维基百科中的中国“华山”条目,其他众多网页信息都指向了华山。在汉语中,“花山”和“华山”除了声调不一以外,发音几乎是相同的;同时在书写中,虽然两者都共用“化”这一笔画,但实际书写出来的两个字因为偏旁部首的不同而呈现很大的区别:象形文字“花山”明显指向了山顶长有花草的山峦,而象形文字“华山”明显用“十”字底传达出了华山的险峻。但作为拉丁语演变形式的越南语是拼音文字,在越南语发音和书写中,“花山”和“华山”用了同样一个词,以至于在越南语版的维基百科对花山的介绍中,作者专门就名称问题强调“汉字‘花/华’,即‘花’和‘化学’。这座山的名称‘华山’中,‘华’这个词必须是‘化学’而不是‘花’”,以免花山岩画被混同到华山天险之中。然而这样的效果并不如人意:华山作为五岳之一,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又因为其山峦险峻,在中国的知名度远远高于花山岩画,因此在越南语版的互联网中,花山岩画的相关信息被淹没在华山的相关信息之中,花山被华山置换、替代和掩盖,除非用详尽的“Các bức vẽ trên đá của Hoa Sơn”(花山岩画)代替简单的“Hoa Sơn”(花山)作为关键词进行搜索。由此可见,语言的转换和文化的断续息息相关,花山岩画在文化的断续中浮沉。
当然,不同的语言不一定是阻碍沟通的坚不可摧的力量。虽然华山地处中国内陆,但并不妨碍它在越南的传播。越南语版的维基百科中,越南人为华山创建了专门的词条,内容详尽,包括华山的概况、名称、所处的位置、险峻的特点、类似游记似的华山生活简介、五岳的区别、华山照片、华山的小说化和两处华山的风景点等。而作者还特地强调“这座山本身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为华山画下“下划线”以表重要性。相比越南语版维基百科中华山的简介,花山岩画的简介简陋到只剩下三段话和三个链接,是关于花山岩画的历史和样貌的只言片语。通过维基百科的介绍可以合理推测,华山穿透语言的阻碍、在越南传播的原因除了它的历史地位和奇险地势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金庸小说对华山的诸多着墨。金庸小说中“华山论剑”情节的渲染到位,作为华山派的所在地,华山借着金庸小说在越南掀起“金庸现象”的影响而为越南民众所熟知。和华山借助金庸小说在越南传播一样,花山在越南使臣笔下的传播也是借助了黄巢这一历史人物。相传黄巢兵败,退走到左江流域,他将人马旗鼓形状的剪纸用妖术贴在山壁间,经过点化的剪纸可以化为神兵,没有经过点化的剪纸则留在石壁上,形成花山岩画。虽然现在关于花山岩画的传说有很多种,但越南使臣在近300年间书写花山岩画的过程中,有且仅有提到“黄巢”传说。这固然和黄巢在唐末起义的影响有关,黄巢起义使得越南趁唐朝国力衰弱之际谋求独立,因而越南精英阶层对黄巢了如指掌。花山岩画和华山在越南的传播可以说都借助了“名人效应”,借助于两个人物“扬名”,但二者知名度有较大区别,由此造成两者在越南传播的热度对比也明显不同。
从汉语到越南语,语言文字见证了花山岩画在越南传播过程中的浮现与消隐、连接与失联。语言的转换切断了花山岩画在越南古籍中的延续,变迁之后的越南语虽然不能完全剔除“花山岩画”,花山岩画在越南语互联网络中若隐若现,但语言具有呈现功能的同时也具有遮蔽的功效,可以说,花山岩画被语言藏匿在华山“巍峨的阴影”里。
三
花山岩画出现在左江流域已有数千年,随着交通工具和语言文字的普及应用而扬名八方。虽然花山岩画在越南的浮现和消隐与交通及语言的转换和变迁有关,但更为关键的因素在于身体在其传播过程中的在场和缺席。梅洛·庞蒂的现象学认为,我们的身体提供给我们面向世界的“开口”,“存在”于世的“载体”,以及与世界“沟通的手段”[13]。
“媒介是人体的延伸”,在麦克卢汉的“泛媒介观”中,交通工具和语言文字都是人体四肢和感官的向外延伸。顺江而下的舟船是越南使臣腿脚的延伸,被记载下来的诗文绘画是越南使臣口语的延伸,但无论交通和语言如何延伸人体,它们都永远无法替代身体。在越南使臣遭遇、凝视、吟诵和书写花山岩画的任一过程中,身体都不可或缺。甚至可以认为,越南古籍中沉淀的花山岩画诗文是越南使臣用身体和花山岩画相互碰撞的结果。身体作为媒介,始终参与了越南使臣对花山岩画的感知和书写。
首先,身体是越南使臣感知花山岩画作为神圣空间的媒介。花山岩画所在的左江流域是越南使臣入关之后的燕行起点,也是结束燕行、重返越南的终点,因此其不是一个空洞的空间,而是灌注了越南使臣的情感,从而承载了重要的地理意义和心理意义。简而言之,如果将越南使臣的燕行之旅当作一场仪式(许多越南使臣的燕行目的就是奉命贺寿和参加庆典等仪式性活动),而且越南使臣燕行回国之后往往得到嘉奖和升迁,因此燕行正如人类学家阿诺尔德·范热内普所说的“过渡仪式”,它是一场“从一境地到另一境地,从一个到另一个(宇宙或社会)世界之过渡仪式进程”[14],那么,作为这场仪式上的关键节点,花山岩画是涂尔干所谓的“神圣空间”,它具有切分燕行起止的作用。使臣的身体在花山岩画的神圣空间中往来,为后者所界定和转换。越南使臣张好合在《月中杂咏》中写道,“到处山光作远迎,似将景色媚华程”[15],中国的山光水色吸引了燕行的越南使臣的目光,只有亲身参与其中,才能感受神圣空间的意义。但网络上的“远行”使身体的感受被切分,仪式感被削弱殆尽。
其次,身体是越南使臣感受花山岩画作为禁忌之地的媒介。因为花山岩画的神秘性,外加黄巢传说附着于其上,使得花山岩画成为不可言说的禁忌之地。受到儒家传统“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影响,以及民间宗教的宣扬,花山岩画在中越两国的典籍中均是当地人避讳谈论的对象。张穆的《异闻录》中记载“舟人戒无指,有言之者则患病”,舟人船夫对花山岩画的恐惧传染给途经此地的越南使臣。除了上文提到的阮攸的诗句“船户摇头若不闻”外,李文馥在《黄巢城》中也叙述了他询问当地人的情景,“长牙(黄巢—笔者注)终古抛荒陇,残阵谁人部旧营。客欲停舟多一问,江流咽石作寒声”[16]。花山岩画因其神秘性,在口口相传的过程中出现各种传说,后者反而增添了它的神秘性,让其成为不可言说的禁忌,在空谷、寒声和孤火的感染中,禁忌反而能激起越南使臣知晓的欲望。欲望归属于身体,生理和心理的相互作用让身体成为感知花山岩画的媒介,但远离花山岩画,同远山近水、猿啸虫鸣相互隔绝的身体是“残缺”的,扶手椅上的身体仅仅只是眼睛和耳朵附属物而已,不足以感受花山岩画相关的禁忌所晕开的神秘性。
最后,身体是越南使臣思念家人和相互唱和的情感媒介。中国诗文讲究“触景生情”和“借景抒情”,因为文学的共通性和受到中国诗文的影响,越南使臣关于花山岩画的诗文中同样也体现了人和景之间的动态关系。除借花山岩画明志外,其还被用于抒发思乡之情,“别后关山思弟妹,望中岩岫见儿孙。日斜莫向花山过,怕有声声肠断猿”[17],身体经过日落时候的花山,勾起思乡之情,花山岩画成为身体和情感的催化剂。除了作为使臣和家人进行情感勾连的媒介以外,花山岩画还作为共同言说的对象,成为使臣之间的黏合剂。正使黎光定携副使阮嘉吉等人一同出使中国,途径花山岩画,两人兴之所至,各赋诗一首,一唱一和。黎光定作诗《花山塘记见》[18],阮嘉吉赋诗《花山晚泛次韵》[19],二者以花山岩画为媒,在异域他乡留下动人史话。在情感的唤醒和抒发的过程中,花山岩画都起到催化剂和黏合剂的作用,而其对象是能够感受、体验和言说的身体。情感是身体的本性,身体的缺席会导致情感大打折扣,正如兰德尔·柯林斯所言,“身体的聚集使其(相互关注和情感连带——笔者注)更加容易,但由远程的交流形成一定程度的关注和情感连带也许是可能的。但我的假设是远程仪式的效果会是较弱的”[20]。网络上缺席的身体可能唤醒情感,但无法保证情感的确切和稳定,因为扶手椅上的身体并没有离开家人,而与他人的一唱一和也是随机与滞后的。
身体的在场和缺席是一个亘古不变而又常辩常新的问题。从柏拉图开始,情感性的身体几乎一直被认为是理性思考的敌人,因此被贬低和排斥。媒介沿着麦克卢汉所谓“延伸人体”的方向一路高歌猛进,不断呈现莱文森所谓媒介进化的“人性化趋势”,因此媒介延伸、补足、修改、遮蔽甚至是替换身体。因为互联网是脱域的,从水路到网络的转换中,虽然“无形无象之人”在网络中穿梭和游移,但真实的身体却在花山岩画前失踪。媒介延伸身体,同时也截除身体,更为重要的是媒介重新调配身体感官的比例。花山岩画前在场的身体是一个完整的感知媒介,五官被同时调用;但互联网中缺席的身体却是一个“残破”的感知媒介,唯独视听觉被激发和放大。
身体的在场对于艺术的感知和传播非常重要。虽然彼得斯在《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中强调的是身体在场在人际传播中的重要性:与其“心连心”,不如“手拉手”共享不可复制和再生的触摸与时间。“触觉是人类最古老的感官,也许是最难得伪造的感官。这就是说,在同等情况下,互相关心的人会尽量到场见面。到场的追求未必使你进入对方的心灵本身,然而它的确可以使你接触对方的身体……亲临现场恐怕是最接近跨越人与人鸿沟的保证”[21]。但身体的在场对于艺术传播而言同样重要。感知的具身性要求身体在场,缺席的身体丧失感知的多元性。更何况花山岩画就是骆越先民身体和生活的延伸,它在骆越先民不在场的情况下替代身体,完成朝向时间的言说。很难想象骆越先民和越南使臣在身体同时缺席情况下的如何沟通,因此越南使臣的身体在场就显得尤为必要,它是在场的身体和延伸的身体间相互感知、凝视和交流的唯一保证。
综上,花山岩画在越南传播的过程中浮现与消隐、连接与失联,在中国古籍的“汪洋”中亦如是。其个中缘由是多元的,但媒介的转换和变迁在其中处于决定地位。从水路到网络的交通变迁使得花山岩画所在的空间被重新改造,中心和边缘被重塑,但作为区域中心的花山岩画却被革除;从汉语到越南语的语言变迁中断了花山岩画在越南的书写传统,同时越南语的模糊性让花山淹没在华山的叙述中;从在场到缺席的身体变迁改变了身体的感知比例,感知的具身性被离身性所取代,感官被截除的同时身体所感受的情感被隔离。交通、语言和身体的转换影响了花山岩画在越南的传播,三者的作用方式是殊异的,但身体被交通和语言所延伸,身体本身又是最完善的媒介,因此花山岩画在越南浮沉的问题可以被置换为花山岩画和媒介关系的问题。透过花山岩画在越南的浮沉,能够更为清晰地认识媒介的功能:它在呈现中遮蔽、在厘清中混淆,也在补足中截除,浮现与消隐、连接与失联都与此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