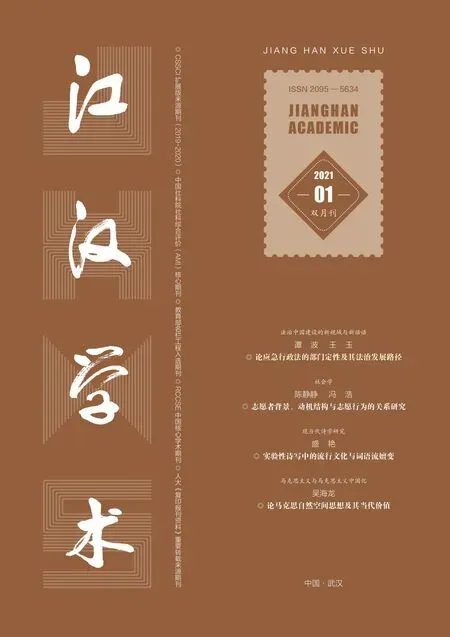《史记》中老子韩非合传原因之疏解
周 杰,林聪舜
(台湾“清华大学”中文系,台湾 新竹 30013)
一、《史记》老韩合传研究状况及其产生的社会背景
(一)合传研究状况简述
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将老庄与申韩合传,把“申子之学”归于“黄老而主刑名”,把韩非之“刑名法术之学”,也“归本于黄老”。如此处理引起了古今学者的兴趣,并产生了各自不同的辨析。如东汉班固在《汉书·艺文志》将先秦文艺书籍按诸子各派分门别类,以说明庄子、韩申分属于道法两家;唐代刘知几认为将老庄合传是《史记》中“舛谬”之“尤甚者”(刘知几《史通》卷四内篇《编次第十三》);而刘伯庄《史记音义》云:“黄老之法不尚繁华,清简无为,君臣自正。韩非之论诋驳浮淫,法制无私,而名实相称,故归于黄老”(司马贞《史记索隐》);宋代黄震认为“夫无为自化,去刑名……政教不施,则其弊不得不出于刑名;此太史公自源徂流,详着之,为后世戒也”(《黄氏日抄》卷四六);明代柯维骐认为司马迁的结论受其父司马谈影响,他说:“司马谈论道家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又云:‘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即史迁所论老子之说也。”(《史记考要》卷八)。清人梁玉绳则综合前代各家之说:“昔人以老、韩同传为不伦,《史通·编次篇》深訾之,小司马《补史》亦云不宜同传,宜令韩非居商君之末。然申、韩本于黄老,史公之论,自不可易,并非强合。况《韩子》有《解老》《喻老》二篇,其《解老》篇创为训注体,实《五千文》释诂之祖。安知史公之意不又在斯乎?前贤妄规之也。”[1]总之,古人对司马迁将申韩归于黄老的批判呈现两极化,要么强烈反对,认为老庄、韩非应分属道、法二家;要么同意此说,赞同合传。
现代学者对司马迁将申韩归于黄老的探讨更注重文本考释和史实考证相结合,更多倾向于对司马迁为何如此定论进行研究。如陈柱说:“老庄道家,申韩法家,以老庄申韩合传,以见法家源于道家也。此史公洞悉学术之源流处。”(《学术世界》1936年第1卷第12期)伏俊琏认为,韩非子继承并发展了老子“道”中无为、贵柔的另一个层面,其目的是为了实现个体在社会中的主体地位。司马迁高度重视《说难》,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强调了韩非子的《说难》《孤愤》,并在《韩非子本传》中附摘《说难》全文,而《说难》的主旨就是争取个体的主动性,实现主体性。[2]也有学者依据司马迁这一定论来看待西汉前期思想学术特征,即认为如此定论体现了西汉学术对先秦思想新的划分,《史记》将老庄申韩合传的理论基础,是基于稷下学宫的滥觞与汉初特定的社会形势相契合而发展为社会思潮的黄老思想[3]。台湾《史记》研究专家林聪舜在考察了司马迁所谓申韩思想归本于黄老的说法的各种疑点后,认为申韩“归本于黄老”的说法难以成立,而应当归于“老”[4]36-37。
无论古人还是今人,对司马迁合传进行各个面向的探讨都说明《史记》如此定论具有很大的学术意义,也可由此去探寻汉初思想家是如何对待战国末年至汉初思想学术的演化与发展,以及“学”与“术”是如何连接,即思想理论如何转向实践运用的。而司马迁把老庄申韩合传,并将申韩归于黄老的定论正反映了这一状况,展现了司马迁的学术洞见,也对研究战国时期各派思想的发展与相互关系及汉初的思想特征有着重要启示。
(二)合传的历史背景
司马迁作《史记》有其社会历史背景条件,包括政治形势、思想潮流,也与个人的学术修养和特殊的人生经历息息相关。那么汉初的思想政治情况如何呢?总体来说,其特征表现为:外在表现为政治上清静无为、休养生息,思想上推崇黄老思想,而暗下却是汉承秦制,法家思想依然被保留和运用。《史记》对汉初统治者好黄老之术,施行清静无为的统治方式多有记载,如《孝武本纪》《封禅书》《魏其武安侯列传》《儒林列传》《外戚世家》就多次出现窦太后“好黄老之言”“好黄老之术”“治黄老言”等,这说明汉初黄老思想已成为当时的思想潮流并赢得了统治者的喜欢,并为其政治所用。如《曹相国世家》反映:
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既见盖公,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参于是避正堂,舍盖公焉。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曹相国世家》)[5]515
这则材料反映了黄老之术已经成为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懂黄老之术的人会得到社会的尊崇与统治者的欢迎与重视。盖公所学黄老之术也非毫无依据,而是早有历史渊源,“其师号曰河上丈人,不知其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盖公教于齐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乐毅列传》)[5]617可见,老黄之术到汉初的盖公时期,已形成完善的学术流派,并对当时社会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汉代统治者在建立和治理国家的过程中,并非完全采用黄老思想的清静无为,而是也吸取了秦亡的教训,借鉴和吸收了秦制秦法的优势来巩固刚刚建立的政权:
于是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生、晁错明申、商,公孙弘以儒显,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太史公自序》)[5]839
萧何拟定“律令”,韩信规定“军法”,张苍制定“章程”,贾生、晁错更是主张效仿申不害、商鞅的法制思想,众所周知,萧何、韩信、张苍都是汉代统治者刘邦的功臣,属于早期政权的建立者;而贾生和晁错是文帝时期的重臣,属于汉初政权的管理和经营者。这说明在汉政权建立的初期并非独尊黄老之术,而是各家思想有所吸取,集众之长补其短,只不过仍需要一个主流思想来疗愈秦暴政以及汉初战争给人们带来的创伤,而黄老思想无可厚非地适合这一要求,而从政权建立与稳固而言,仅凭黄老之术来休养生息是不长远的,更需要法家的法制思想从根本上保障其统治的稳定持久。
因此汉初思想具有两面性:黄老清静无为与汉承秦制,即一面吸取秦亡教训反秦反厉法,与民安定、休养生息;另一面又承袭秦制,欲以法理的适度运用,来巩固政权。因此,在汉初不论是政治上,还是学术思想上黄老思想都极其流行,成为战后社会状态的表征;法家思想若隐若现,作为汉代政权支撑的根本保障;同时又呈现出黄老、儒家、道家、法家思想进一步融合,为“独尊儒术”作好了铺垫。由此推断,战国末期至汉初的思想家们的思想极大可能对“法”的思想有一定的理解。如贾谊、董仲舒属于儒法结合,刘安《淮南子》属于道法结合,当然黄老思想早就与法家思想有融合,或者从文献考证来看,法家应产生于道家之分流的黄老一派,在此不赘论。除此之外,司马迁本人实际受儒家思想影响较多,但受其父亲司马谈“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论六家要旨》)的影响对道家思想也有所涉猎,却不能忽略他的法家思想成分,如他在《史记》中就多处表现出正视法家思想,肯定法家合理部分与批判不足之处。实际上,司马迁肯定了法家思想对政治具有现实价值的功效。因此,司马迁把老韩合传,并将申韩归于黄老的论断产生于汉初的时代背景下,当时黄老派本身对儒、道、法等各家采取兼包并蓄态度,既丰富了自身理论体系,也对其他学派(尤其儒、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老庄、申韩合传原因检证前的几点说明
第一,“黄老”指黄帝老子,而连用最初应当始于司马迁《史记》(熊铁基先生对此有详细考证[6]),以至汉代以后,“黄老”出现次数众多。因此,黄老是否是一个思想学派或一种思想观点的代称,若是,其起源、流行何时都有待考证。
第二,老子后学、阴阳家等著作常会托名黄帝或老子之后,而法家似乎很难找出这样做的例子。此外钟肇鹏先生认为《黄老帛书》是《经法》《十六经》《称》《道原》四篇与《老子》合抄在一起的现象而命名的,也就是说《黄老帛书》是《经法》等四篇与《老子》的一个总称[7]。加之,此文献出土于长沙马王堆汉墓,墓主人死于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学界大抵承认此古佚书抄写年代应该在汉文帝初年,由于墓主人是汉代统治阶级,又和《老子》放置一起,说明当时黄老思想极为流行[4]38-39。因此,《黄老帛书》极大可能是战国末期至汉初的一种思想观点(“无为而治”“与民休息”)或一个学术流派的代表作。
第三,战国末期各家思想开始出现并杂,不可能出现单纯的某一家思想,同时各家内部分化分流,又吸收别家学说为我所用,“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庄子·天下》)。正如韩非子《显学》所论断:“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各派相融合,但各自的取舍和主张不一样而已。如此,就算黄老思想含有很大的法家思想成分,也难以此为判断,将韩非归于黄老。
第四,仔细阅读《老子韩非列传》文本,可以发现司马迁定论矛盾:在单人作传的时候,司马迁说“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其后又说“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然而明显不同于“太史公曰”的论断:“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故著书辞称微妙难识。庄子散道德,放论,要亦归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于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由此来看,论断一将申韩归于黄老,论断二实质上是将申韩归于“老”,而非黄老。从太史公曰句可以看出,司马迁将道家老子的学说的发展分为两派,一派是以庄子为代表继续发挥老子学说,“以明老子之术”;另一派则是申韩为代表的法家,“喜刑名法术之学”,但二者实质“皆原于道德之意”。从老子的“道”思想的解释来看,“道”在政治领域的作用显现出“无为而治”,其本身是一种王侯驾驭天下的手段,使人臣乃至万物感受到“道”的存在,而自动收敛性情。因此,老子后学有可能演变发展为司马迁所推断的两个方向:一是以庄子为代表的继承发展老子形而上的道,重在自然与人的精神领域里实现人生价值;另一流向则以稷下黄老学说为代表,偏重于发展了老子积极用世,重人生重人事,注重现实人生和政治的价值,而申韩就属于第二个流派,以道为法的根源,通过继承老子道有关柔术方面的思想而形成法家。
第五,依据《韩非子》中《解老》《喻老》为评判将韩非与老子合传,不足以说明法家起源于黄老。《解老》与韩非所著的《五蠹》《显学》等其他作品在思想内容上有很多不一致。容肇祖《韩非子考证》举了诸多例证。如《解老》中“重生者,虽入军无忿争之心”,而《显学》反对“重生之士”;《解老》“爱子者慈于子”,《六反》则说“父母之于子也,犹用计算之心以相待”等。此外,《解老》和《喻老》从文体形式、解说体例,到笔调、思想态度以及引用《老子》的底本等,都有很大不同[2]。
三、司马迁老韩合传原因试探
(一)黄老的形成与黄老中的法家思想倾向
黄老连用在《史记》中首次出现,但黄老思想并非单一指黄帝和老子的思想,也包括战国时期一些思想家对黄帝、老子思想的某些部分继续发挥与扩充。也许司马迁本人已经意识到各派思想融合形势,而他所称的“黄老”思想极具有这一特点,即融合儒、道、墨、名、法、阴阳等各家思想,但又坚持自己所主张的宗旨,将其他家思想加以改造为自己所用。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指出: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太史公自序》),几乎没有缺点,“立俗施事,无所不宜”,而且还灵活地“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吸取各家之长,进而在人事处理上会显得“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但需要指出的是司马谈所说的“道家”并非纯粹的道家,很可能是继承和发展老子思想中有关柔术、道术、法术的思想的老子之后学,即司马迁所说的黄老学派。
《汉书·艺文志》也对各家渊源有所解释,虽然其目的是要将各派著作分门别类,把各家各派分辨清楚,但各家分流前提是诸子在战国末期已经形成“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蠭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8]的局面,这也反映出战国末期诸子各家相互影响、吸收、融合的学术思想特征,一方面是“九家之术蠭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另一方面则各家“舍短取长,以通万方之略”,但最终目的不过是“取合诸侯”,在社会政治上发挥功效,实现各派学术价值。
因此,在学术混杂、思想观点没有严格区分的情况下,尤其是黄老之学更是融合各派观点,把黄老学派看成是道家的一个分支,或把法家看成是黄老的支流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正因为如此,司马迁才会在《老子韩非列传》出现两种不一致的定论。从论断二来看,他很可能看到了老子思想发展出的两个不同的支流:一个是以庄子为代表,“散道德,放论,要亦归之自然”,即继续发展老子“道”之“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思想;另一个则是以申、韩为代表的法家思想,发展了老子“道”思想的另一个层面,即“自守”“卑弱”是为了在人际社会关系中处于主动地位,并预测提防别人欲夺先与的居心,运用法术,在现实社会中谋求价值。因此,司马迁将老子放于庄申韩之前,并总概道:“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故著书辞称微妙难识”,然后分别介绍庄、申韩两个不同流派的思想特点,而最后再次总结道:“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可见司马迁知道老子思想之广阔与包罗万千的气象。
由上可以看出司马迁将申韩归于黄老的说法有待检证,虽然他看到了法家与黄老、法家与道家的特殊关系,但他很有可能因当时有关黄老的传说而对道家、黄老、法家三者之间的历史演变顺序不够清楚,加之,申不害与韩非的著作中的确存在着多处论述黄帝、老子的言论和思想,才会出现司马迁不统一的论断[4]36-37。
再看黄老之学的思想特征:主张道法结合,提出“道生法”的观点;重视刑名之学,如司马迁说申不害“申子卑卑,施之于名实”“主刑名”,又说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突出刑德观念,主张恩威并施以巩固政权;同时又兼采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的思想。可见黄老之学兼容并包,政治上主张“贵清静而民自定”“无为而治”,君主治理国家掌握政治要领即可,因势利导不要作过多的干涉;理论上持“道生法”的观点,即“道”是法、刑的根源和依据。当然,这些思想主张受到汉初统治者的欢迎,其原因是这种思想有利于汉王朝巩固刚建立的政权,加之吸取秦灭亡的教训,因此,汉初统治者都“好黄老之学”,施“无为之政”。而另一方面,汉初统治者也显示出喜刑名之学,《史记》也有记载“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儒林列传》)。汉初统治者的两面性正好印证了黄老学派存在道、法结合思想的成分。学者通常把《黄老帛书》当成黄老学派的代表著作,《黄老帛书》表现出了很多《老子》思想,尤其对“道”的阐释很大部分继承《老子》“道”的特性,即“道”的先在性、普遍性、永恒性,并作为天地万物的根据;进而发挥出“道生法”的观念,以“道”为“法”的依据和根源,并以“法”释“道”,建立了一套刑名之学和刑德观念,这和法家以法为中心,将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思想不谋而合。
《史记》中对黄老学派的传承最早可追溯到河上丈人,在《乐毅列传》中如是说:“乐臣公学黄帝、老子,其师号曰河上丈人,不知其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盖公教于齐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从河上丈人到盖公,传承有五代人,又根据“华成君,乐毅之孙也。而乐氏之族有乐瑕公、乐臣公,赵且为秦所灭,亡之齐高密”,可依据秦朝建立于前221年,而秦灭赵在前222年,推测乐瑕公、乐臣公生活的年代大致就在战国晚期,甚至到秦代,而且乐瑕公与乐臣公年龄相差不大;再看《田儋列传》曰:“通善齐人安期生,安期生尝干项羽,项羽不能用其策。已而项羽欲封此两人,两人终不肯受,亡去。”[5]671此段话最重要的一个字是“封”,即分封诸臣,“爵诸侯之土也。从之从土从寸,守其制度也”[9]。此时项羽有分封之权可见其地位亦很高,依据项羽年谱大致推断此时项羽随项梁起义约在前209年之后,而项羽出生于前232年左右,此时项羽大概有二十多岁。如此推测安期生活动时期略早于乐瑕公、乐臣公,而且根据古人寿命来看,安期生不会大于项羽一个世纪,因此,河上丈人的学术活动时间不会早于战国晚期,不可能如唐兰所推断在公元前四世纪的前期[10]。
(二)道家有关法的倾向分析
根据以上河上丈人的学术活动时期的推断,也不能完全说明黄老学思想兴起于河上丈人的的活动时期,即战国晚期。《史记》中的《孟子荀卿列传》记载:“慎到,赵人。田骈、接子,齐人。环渊,楚人。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论,环渊著上下篇,而田骈、接子皆有所论焉。”[5]595慎到、田骈、接子、环渊也同样受到黄老道德之术的影响,而这些人生活年代根据《田敬仲完世家》记载,他们生活在齐宣王时期,约公元前350年至公元前301年,差不多在战国中期。其年代和《庄子》成书时间相差不远,《庄子》的《天下》篇中将当时天下学派分为六组,其中将彭蒙、田骈、慎到归为一组,并认为他们“弃知去己,而缘不得已”“齐万物以为首”的思想学说与道家是相通的,可以归并为道家,但与庄子学派的观点还是有距离的,“其所谓道非道,而所言之韪不免于非。彭蒙、田骈、慎到不知道”(《庄子·天下》)。
同样在《荀子》之《非十二子》中说:“尚法而无法,下脩而好作,上则取听于上,下则取从于俗,终日言成文典,反紃察之,则倜然无所归宿,不可以经国定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慎到田骈也。”[11]这里有一个重要的信息是:慎到、田骈“尚法”。由此可推测,慎到、田骈的思想已经具备了道、法思想融合的特征,或者说道家内部已经演化出重视法的思想流派。
那么道家内部是否可能含有“法”的思想倾向呢?《老子》中于有关“法”的论述仅此一句:“法令滋彰,盗贼多有”,而且是反法思想的。但《老子》反法的根本目的是政治上的清静无为,由此演化出来“人君南面术”——帝王之学、治国之道、刑名之学、统御天下之术。通览《庄子》一书中发现其中反法思想也不少,如《胠箧》《天运》《天道》《在宥》等可以找到多处反法论述,但其反法的最终目的是为传承老子之“道德”思想的“无为”“无事”的一面,这无疑是继承了老子抛弃法术思想的一面,虽然《天下》篇也澄清庄子思想与老子思想也有所不同,但它从反面论证了至少在战国末期以前,关于法的思想已经流行,并且法理制度逐步建立与完善起来了。
关于“人君南面术”的法术思想何以产生呢?《老子》第二十五章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里的“法”乃“效法”“顺应”,并非后来法家的“法”,法家把“道”作为“法”的源头和基础,“法”演化为规范化的社会秩序和人世常理,并通过制定法制规章来对人民加以限制和规定,也是依据人的本性而顺应道的要求。这些“法”本应是“法乃道之法,对道的遵循可以使得天、地、人三界秩序井然,得以理治”[12],但老子本意却是认为圣人制定统一的规章制度却是不顺应“道”的规定、“德”的要求,不效法道的自然规律的表现。法家则将“法”的意义延展为法令、法刑制度。战国时期学术派别相互交错影响,并没严格区分,且一位思想家往往接受或者受到其他思想家的思想的影响,如老子后学可能有两种路线发展出韩非思想:由文子、稷下学宫之黄老学,而出现彭蒙、田骈并发展至韩非;也可能由受到老子思想影响的郑长者、田方子、申不害,直接发展出韩非子[13],这两种路线的老子后学对“道”“天”“人”“事”等概念的不同理解与发挥,按其思想脉络极有可能会继续对“法”的思想进行思考与阐释并完善道法理论,导致系统化与理论化的道、法、刑思想产生。
综观春秋至战国,尤其以战国中期以前的道家文献,如《鹖冠子》《管子》《列子》《文子》都有很多关于法、刑的思想的论述,但也为上述推断提供了参考材料。如《管子》之《七法》《法禁》《重令》《法法》等十多篇章论及道与法的关系。老子后学有文子、宋钘、彭蒙、田骈、慎到等思想家都有谈道与法、法与刑、礼关系,讲君臣之道、治理之论等思想,虽然庄子反对法、刑之治,但是这也说明关于法术思想最晚在庄子时期已经流行了。因此,法家一定会受到后来汉代所称谓的“黄老学派”思想的影响。
(三)韩非思想中的道家倾向的分析
韩非是法家集大成者,此时法家关于法的思想体系才得以完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韩非不但将商鞅之“法”、申不害之“术”,以及慎到之“势”集于一家,而且认为“申子未尽于术,商君未尽于法”(《韩非子·定法》)[14],即申、商二人不但没有把法与术结合,并“未尽于法”。因此,韩非的观点更加完善和进步,如韩非的“术”讲究“术以知奸”(《定法》),“法”要求“以刑去刑”(《饬令》),“势”讲求“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难势》)。第二,韩非继承和改造了老子的道的思想,并与法融为一体,构建了法家的学术思想。其“以道释法”(“援道入法”“以道护法”)方法非常巧妙地把道作为了法的合法依据,他认为“道”是万物产生的根源,具有先在性、决定性、普遍性等性质,有“道”才有天地万物,所以,“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万物之所以成也。故曰:‘道,理之者也。物有理不可以相薄,故理之为物之制。万物各异理,万物各异理而道尽'”(《解老》)。道不但是万物“之所然”,万物“之所以成”,“道亦为万物之理之所稽,为万理之统一与最普遍之理……为最高真理标准,故为人之行为修养之最高准则”[15]。如此有“道”才有“法”的产生,如《主道篇》曰:“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万物之源,治纪以知善败之端。”由此观之,韩非认为道生万物,理源于道,而万物从理尽道,而法是社会之理,因此法也是由道而生。
引“理”入“道”生“法”的思想,并非韩非首创,早在《黄帝四经》和《管子》四篇中就已讲到“道”与“理”的关系,[16]如《经法·四度》曰:“执道循理,必从本始。”[17]160而《经法·道法》曰:“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故执道,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废(也)。”[17]48《管子·心术上》曰:“故事督乎法,法出乎权,权出乎道。”可见韩非的道法思想实际上继承了早期的所谓“黄老学派”的“道生法”思想,由“道”生“法”最重要的作用是为“法”提供了哲学理论上的依据,使现实的社会法律制度具有了不可侵犯的权威性,其本质是为封建君主的统治找到了合理性,使人民服从法的形式的统治。
如果将这种思想运用到政治治理上,就表现为“以法为本”的尚法思想。认为实施“以法为本”(《饰邪》)的无为而治,可以达到法行而君不必忧,臣不必劳,而民守法的功效。可见刑名法术的根本就是强调君无为而臣有为,并通过法的制定和施行来保障社会秩序正常运行。国君治理国家,要想天下臣服于己,就必须做到“无为”的状态,表现出“无为而治”,而达到“古之全大体者”的依法治国的境界,即“寄治乱于法术,托是非于赏罚,属轻重于权衡”“不引绳之外,不推绳之内;不急法之外,不缓法之内”(《大体》)。
韩非通过吸收道家之“道”,将“道”解释成为天地万物中存在的事物生灭消长的自然规律和运行规则,即为“理”,并将这个原则运用到社会与政治治理中,就为他的法、术、势等政治思想找到了理论根据,由此,他认为“道不同于万物”“君不同于群臣”(《扬权》),因此“明君贵独道之容”(《扬权》),君主的权位、权势是要符合“道”的原则的,同样君主的统治手段与天地的统治手段也是要符合“道”的规律的,天地无亲疏,君主也应该对臣子无亲疏,从而使臣子人不谦职,官不谦事,君主虚静无为,深藏不露,神秘莫测,“若天若地,是谓累解”(《扬权》)。
总之,韩非的“重法”“任术”“重势”与道家思想在表面上看不出具体联系,甚至与道家所推崇的无为观念也相离甚远,但是其根源还是对老子道法自然、清静无为思想的吸收和发展,进而在政治上追求无为而无所不为,欲通过建立一套完整的法治理论体系来实现至善政治的最高状态。
四、司马迁以韩非《说难》自嘲
在《老子韩非列传》中司马迁附上了韩非子的《说难》原文,也是引起了不少学者的讨论。如汤谐认为司马迁“叙庄子、申子,简洁有致,而独韩子颇详,悲之也!非直为死于说难,意中言外犹有深悲焉,悲谗人之罔极也,韩子之智而不能自脱于谗也”[18]581,其认为是太史公悲伤于韩非的遭遇。曾国藩说:“以申韩为原于道德之意,此等识解,后儒固不能到。故其著书十万余言,大抵率寓言也。”[18]582李贤臣认为,附传作为《史记》体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史记》书法体例系统的整体原则[19]。
司马迁公正地评判了法家的历史地位,他既看到了法家的合理成分,后世必然有所继续采用的,如刑法不可废,法的公正平等性及其对汉初政治的稳定作用,但他又看到了法家公正性与平等性的逐渐丧失甚至“法家强调的严刑峻法带来的后遗症”[4]222-223即酷吏政治造成的人性残害和社会动乱。韩非之遭遇使他感同身受,司马迁说明了韩非著书的原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于外是因为当时政治腐败,法制混乱,“文乱法”“武犯禁”,名实枉曲,“廉直不容于邪枉”的现状,激起韩非关心政治得失的热情而作书;于内是因为“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太史公自序》),为抒发胸中的愤懑之情而创作。然而司马迁感叹韩非“韩非知说之难,为说难书甚具,终死于秦,不能自脱”。韩非明知说难之难,却依然“终死于秦,不能自脱”,司马迁借此问诘:因“李陵事件”惨受宫刑,这是自己的过错吗?作为人臣诚谏直言也有罪吗?以此暗讽汉武帝的昏庸残暴。韩非“终死于秦”,揭示了韩非的真正死因,并非韩非不知道危险和不知道秦皇昏庸听信奸臣谗言以及酷吏的陷害,其“不能自脱”才是根原,即韩非自己选择以身殉法。正如合传所说:“斯、姚贾害之,毁之”,而“秦王以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遗非药,使自杀。韩非欲自陈,不得见。秦王后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为此司马迁感叹:“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其实质,是借写韩非受害遭遇来表达自己对汉武帝的不满和酷吏对他非人折磨的愤懑,同时也表现他与韩非一样为了理想视死如归“殉道”的人格气魄。
司马迁巧妙地运用春秋笔法,微言大义,通过刻画韩非不幸的遭遇,含沙射影地批判了当时的历史现实以及统治者的昏庸以及对那些因法家“严法少恩”而蜕变出来的酷吏政治的深恶痛绝,并抒发了自己对天道正义丧失的深切悲痛。韩非之“不能自脱”的处境,也喻示着司马迁崇高的人生价值选择,他深切地感受到汉初政治虽然外黄老而内法,在吸取秦亡的教训,反秦反法的外衣下而继承秦制,同时也接受了酷吏政治的恶种,他将为了天道正义的重新构建而忍辱负重,“究天人之际”,“在历史中找寻出人类得以依循之法则,使人生与政治得到合理的安顿,使王道理想或人间正义秩序得以重现”[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