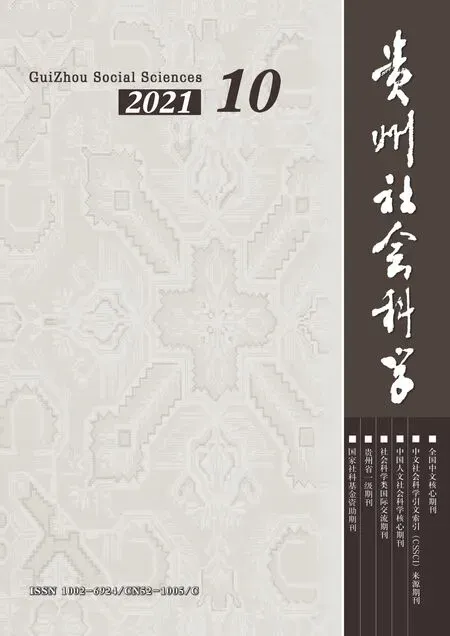基督教的政治学“启蒙”
——以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在中世纪的传播为例
田庆强
(山东大学,山东 济南 250100)
1260年,《政治学》由希腊语译为拉丁语是亚里士多德思想在中世纪西欧传播的标志性事件。此前拉丁语世界只有亚里士多德逻辑学作品流传。随着亚里士多德哲学著作的重新发现与阿拉伯哲学的传入,经院哲学家们围绕唯名论与唯实论争论正酣,忙于维护基督教信仰。总体而言,当时社会经济已大有改观,民族国家已显雏形,民族意识萌发,再加上大学的兴起,世界基督教帝国理论已不是铁板一块。在这样纷繁复杂的形势下,考察教会这一充满“集体智慧”的组织如何看待、吸纳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理论显得尤为重要。西方学者非常强调亚里士多德对中世纪西欧政治思想的影响,[1]154-169亚里士多德语言的形成[2]及《政治学》重新发现的深远意义等。[3]国内学者主要论及亚里士多德革命的影响以及由此带来的自然政治观与中世纪神学政治观的对立,[4]273亚里士多德革命如何促进中世纪王国实体性观念形成等。[5]学者们并未勾勒《政治学》在拉丁西方的传播、接受过程,基督教神学家对它的解读与借鉴,以及它对基督教产生的重要影响等。
至11世纪中叶,阿拉伯哲学家们已接触到除《政治学》以外的几乎所有亚里士多德著作。阿拉伯人最早有关亚里士多德学说的知识源自叙利亚人,以逻辑著作为主,他们并未知晓《政治学》。当时阿拉伯帝国涌现了以侯奈因·伊本·伊斯哈格(Hunayan Ibn Ishaq)为代表的翻译家,统治阶层亦设立了“智慧宫”(the House of Wisdom)等学术机构吸纳古典学术。但根据当时阿拉伯传统,知识被分为“理性的”与“传统的”,前者指源于希腊或其他异域的知识,后者则基本上包括写作技巧,与《古兰经》、传统、法理学及诗学相关的学科。[6]《政治学》显然是属于“理性的”。而对于《政治学》中出现的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等观念,阿拉伯帝国尚缺乏接纳这些新颖思想的土壤。阿拉伯人对译介《政治学》兴致寥寥,反而对包含自然哲学、数学乃至形而上学的理论哲学情有独钟。而且在阿拉伯世界不仅有亚里士多德学说,还有新柏拉图主义,两者存在竞争关系,但似乎后者略胜一筹:“柏拉图关于哲人王和立法者的观点,与达到完美宗教境界的先知这一穆斯林思想融为了一体”。[7]更有甚者,新柏拉图主义者截取普罗提诺(Plotinus)著《九章集》(Enneads)部分章节,并命名为《亚里士多德神学》(Theology of Aristotle),以混淆两种学问。《政治学》在阿拉伯世界的空缺逐渐被柏拉图的《理想国》和《法律篇》填充。
因此,亚里士多德著作由阿拉伯帝国传往拉丁西方后,基督教会顺势承担起《政治学》的译介工作。这要感谢大阿尔伯特(Albert the Great)的学生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阿尔伯图斯(即大阿尔伯特)是第一位诚心诚意地欢迎亚里士多德著作新译本的经院哲学家。……他还是第一位用拉丁语对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进行评注的人。”[8]在大阿尔伯特的悉心指导下,阿奎那对《政治学》的认识更深刻和全面,并为之注疏。之后阿奎那遇到了亦师亦友,同属多明我会的希腊语专家摩尔贝克的威廉(William of Moerbeke)。当时传入西欧的亚里士多德著作大都未能忠于原著,甚至掩盖了亚里士多德学说的“庐山真面目”。“《政治学》到达西方基督教世界时,已经满覆一个非基督教、有时反基督教文明的研究注疏。此外,《政治学》终于进入基督教世界时,基督教世界已经过保罗与奥古斯丁政治思想濡染,是一种与亚里士多德的国家论非常不同的政治思想。”[9]117有鉴于此,阿奎那请威廉依据希腊文原著订正乃至重译亚里士多德著作,这其中便包含《政治学》。
基于对《政治学》不同的立场,基督教会内部大致可以分为三派。以大阿尔伯特及托马斯·阿奎那为首的调和与改造派,意在发展基督教神学与哲学体系,以容纳《政治学》为代表的亚里士多德思想;以罗马的吉尔斯(Giles of Rome)及其政敌巴黎的约翰(John of Paris)为代表的论战派,认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把《政治学》作为教权派与王权派论争之工具;以但丁(Dante Alighieri)和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Marsilius of Padua)为代表的应用派,旨在把《政治学》应用于意大利城邦国家,为意大利的未来找出路。
一、托马斯·阿奎那的调适与融通
阿奎那采撷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并将其融入基督教神学之中。阿奎那继承并神化了亚里士多德关于人的社会属性观念。阿奎那模仿亚里士多德的口吻说:“人天生是个社会的和政治的动物,注定比其他一切动物要过更多的合群生活。”[10]44与其他动物相比,人没有大自然赋予的某些生存手段,如锋利的角、爪或者逃跑的速度等;当然,一个人也不能供给自己全部所需,人需要与同类在一起,相互协作以组成社会,因此他是社会和政治的存在。厄尔曼认为:“将人作为政治的动物,这种概念说明‘政治’已经进入了当时的词汇和思想过程。”[1]172然则人的社会与政治属性与基督教对人的定义相抵触,阿奎那便借用基督教教义来化解这一矛盾。在他看来,既然上帝是人和人性的创造者,那么他也是社会与政治权威的创造者与主宰者。如此,人的社会性披上了宗教的外衣,被阿奎那神学化了。
阿奎那基本上承袭了亚里士多德的自然主义国家观。阿奎那认为,由于私人利益的存在,社会中必须要设立某种共同认可的治理机构,由此产生了国家。[10]14-18国家源于人的社会性需要,这无疑体现了亚里士多德城邦的自然形成说。在奥古斯丁看来,国家源于人类的罪恶。但经过阿奎那的哲学改造,国家是自然本身发展的结果,因而具有自然性。同时人和人的社会性又源于上帝,因此国家又具有神性。阿奎那亦承续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认为国家目的是人类至善并谋取社会共同幸福。[10]45阿奎那虽然使“古代的国家思想在基督教中复活了,但这个国家本身不再是目的,而是实现神的宇宙计划最好的手段”。[11]439
阿奎那也效仿亚里士多德的政体分类学说。受亚里士多德正宗政体与变态政体分类的启发,阿奎那区分了正义政体和非正义政体:前者包括平民政治、贵族政治和君主政治,后者则包括暴君政治、寡头政治和民主政治。[10]46-47阿奎那与亚里士多德的政体分类基本是一致的,但两者标准不同:亚里士多德以统治人数多寡为标准,而阿奎那把政治目的作为首要标准。阿奎那认为君主制是最好的政体,因为“由一个人掌握的政府比那种由许多人掌握的政府更容易获得成功”。[10]48而亚里士多德最中意共和政体。[12]356作为经院哲学大家,阿奎那必然清楚君主制有可能变为暴君制,因此他只能希望君主能为公众谋幸福,倘若追求个人私利,倒行逆施,则会受到上帝的警告。[10]46-47这从侧面也反映了阿奎那坚持的王权必须服从教权的政治主张:“世俗权力之服从宗教权力,犹肉体之服从灵魂”。[10]140
阿奎那法的概念也受亚里士多德的影响。他认为法“不外乎是对于种种有关公共幸福的事项的合理安排,由任何负有管理社会之责的人予以公布”,[10]106这与亚里士多德法的定义如出一辙:“任何力量,只要它能通过共同的政治行动以促进和维护社会福利,我们就说它是合法的和合乎正义的”。[10]105以阿奎那之见,法的目的是公共幸福,而公共幸福即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共同的善”(Common Good)。阿奎那和亚里士多德都强调法的理性作用。亚里士多德指出,法律乃理性之体现,它可以“免除一切情欲的影响”。[12]172在《神学大全》中,阿奎那认为法是一种“理性的命令”或者“实践理性的某项命令”。[10]ix,106由于人的理性受上帝理性的支配,法自然被打上了宗教的烙印,体现上帝的意志。阿奎那对法作了宗教性阐释,使之神圣化。这也是阿奎那与亚里士多德有关法认识的不同之处。
托马斯·阿奎那顺势而为,全面认识并成功转换了以城邦为基础的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阿奎那把其中所蕴含的人的属性、国家观、政体分类以及法的概念等融入基督教神学框架内,以服务于属灵事业。“在政治学理论方面,他打破了中世纪典型的神学政治的‘话语霸权’……从而为人们用新的眼光观察和分析政治问题开了先河。”[4]304这不但丰富了以柏拉图哲学为基础的奥古斯丁经院主义传统,而且成为基督教的亚里士多德主义(Christian Aristotelianism)的重要源泉。
二、吉尔斯与约翰的教权和王权之争
13世纪下半叶,教俗之争已接近尾声,教权对王权取得绝对优势。教皇博尼法斯八世(Boniface VIII)与法王菲利普四世(Philip IV)围绕国家是否有权向教会和教士财产征税这一问题再起纷争。阿奎那的学生罗马的吉尔斯支持教皇,利用亚里士多德政治理论为教皇君主制辩护,是教权派的代表人物。吉尔斯认为,教皇是合法的统治者,对整个世界拥有最终裁决权。“他裁决万物,换言之,他会成为万物之神,且不受任何人的支配:亦即,没有人会成为他的神。”[13]巴黎的约翰早年加入多明我会并获得神学学位,曾担任过巴黎大学神学讲师。作为一名神学家,约翰却是不折不扣的王权派理论家,与教权派针锋相对,为王权合法性摇旗呐喊,是吉尔斯的论敌。以下分别简述两者对《政治学》的征引情况。
吉尔斯对亚里士多德学说的继承体现在《论公民政府》(On Civil Government)中。在该书第33章,[14]吉尔斯大量引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四卷内容,以说明为何中产阶级人数占优势时,王国便会秩序井然:(1)如果极富、极贫者多于中产阶级,则无人能过理性的生活;(2)王国或任何国家的居民之间缺乏相互尊重;(3)中产阶级是实现国家间必不可少的平等和公正的条件之一;(4)嫉妒与蔑视会毁灭王国。吉尔斯对中产阶级执政的政体分析过于简单,未能抓住亚里士多德学说之要义。具体而言,中产阶级执政的原因有三。首先,中产阶级所具有的政治特性。亚里士多德强调“中产阶级(小康之家)比任何其他阶级都更为稳定。他们既不像穷人那样希图他人的财物,他们的资产也不像富人那么多得足以引起穷人的觊觎。既不对别人抱有任何阴谋,也不会自相残害,他们过着无所忧惧的平安生活”。[12]209而且,与极富和极穷两个阶层相比,中产阶层最符合亚里士多德的中庸之道原则。再者,中产阶层执政能防止极端政体。“平民群众和财富阶级之间时时发生党争,不管取得胜利的是谁,那占了上风的一方总不肯以公共利益和平等原则为依归来组织中间形式的政体,他们把政治特权看作党争胜利的果实,抢占到自己的手中后,就各自宁愿偏向平民主义或寡头主义而独行其是。”[12]211-212中产阶层执掌的中庸政权就很少发生政权演变,产生极端政体,因为中产阶层执政实行的共和政体综合了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的优点,兼顾了贫富两者利益,有利于城邦的安定。
巴黎的约翰继承、借鉴了亚里士多德国家观和混合君主制等。有学者指出,约翰完全熟知《政治学》, 尤其是第一卷和第六卷。[15]xxiii亚里士多德认为,国家是人们依照其自然本性追求完美生活的结果,其存在目的是为了整个共同体的利益。他强调城邦的自然属性,以消弭人与政治共同体之间的对立关系,使人与城邦和谐相处。巴黎的约翰也完全认同国家的自然属性:“人类过群体生活是必要和有益的,最重要的是,人类能够生活在一个满足他们一生所需的共同体内,譬如国家或王国,尤其,他们应生活在以共同利益为目标的国王统治之下。这也意味着,这一统治起源于自然法,因为事实是,人在本质上是国家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动物。”[15]9显然约翰认为国家的自然属性源于人的自然本性,体现了古希腊的自然政治观。对继承亚里士多德学说衣钵的学者来说,城邦在中世纪的投射就是王国。对巴黎的约翰而言,从亚里士多德那里接受过来的“自给自足共同体”就是一个王国。[16]334约翰推崇一人之治的君主制。在《论王权与教权》(On Royal and Papal Power)的开篇,约翰便定义了君主制:“一个人为了共同的善对一个完善的群体的统治”。[15]7在谈到共同体生活时,约翰强调“人们应该生活在由国王治下, 以共同的善为目标的国家或王国”。[15]9约翰认为共同的善是共同体建立的目的,这与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开篇内容何其相似。尽管君主制有诸多优点,但约翰的理想政体是由贵族制和民主制成分相混合的君主制,而非上述纯粹的君主制,“因为,在一种混合的体制中,任何人都能参与政府。这样一来,人民的和平就有了保障,他们都会热爱并保卫这个政府,正如《政治学》第二卷陈述的那样”。[15]101
约翰在《论王权与教权》中借助亚里士多德自然主义政治理论,回击吉尔斯在《论教皇的权力》(On the Power of the Lord Pope)中支持教皇统领世俗权力的立场,力图使王国逐渐摆脱神学的羁绊,确立其实体地位。吉尔斯著述的目的是“为教皇争取最大的权力范围和对人类生活所有领域的管辖权”。[16]392约翰认为,王国是一个自然的政治共同体,而教会则是一个纯粹的神秘体,“神职是由基督授予牧师以向其信徒施行圣礼的精神权力”。[15]11教会与国家是不同性质的实体,国家源于人的自然性,受自然法则的规约;教会则源于上帝的神性,其目的在于引导信众走向彼岸,因此教会不能干预王国。这正与吉尔斯的主张相反。吉尔斯则区分了四种现实的权力,即自然之权、技艺之权、科学之权和统治民众之权。通过分析、考察自然之权,他认为在自然之权中,天国之权统治着所有其它的权力。[17]394“世俗统治者……都应该服从教会,世俗权力从属于教会权力,正如特殊从属于普遍,即低级权力服从于天国权力。”[17]399尽管吉尔斯的政治观增加了“自然”的色彩,但仍属神学政治体系。总之,吉尔斯与约翰的论战本质上是奥古斯丁神学政治学(吉尔斯曾加入奥古斯丁修会)与亚里士多德自然政治学之间的博弈。尽管约翰与吉尔斯分属王权派与教权派,但为了在论战中增加胜利的砝码,他们均引用新传入的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说,间接促进了《政治学》的传播。
三、但丁与马西利乌斯的沉思与探索
在基督教内部纷扰不断,王权派与教权派剑拔弩张之时,基督徒如但丁关心城市共和国命运,思考意大利的政治出路,欲恢复古罗马的荣耀,主张建立统一性的世界帝国;而有的基督徒如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则着眼社会现实,改造城市共和国。尽管旨趣不同,他们都借鉴《政治学》以论证各自的政治主张。
在《论世界帝国》(De Monarchia)中,但丁系统阐述了建立一统天下的世界帝国思想。全书通篇可见但丁对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说的运用。“与托马斯一样,他乃是在一个由若干原则组成的框架中阐释其世界共同体理论的,而这些原则乃是从亚里士多德那里推演出来的。……他的论证方式把传统上对帝国的理想化同种种新的亚里士多德的解释范畴奇妙地结合在了一起。”[16]311但丁认为,为了给尘世带来幸福,建立一个一统的尘世政体是极为必要的,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曾肯定这一说法。但丁采用层进式的推演,认为从物体到个人、家庭、地区、城市乃至国家(或王国)都要受“一统”的规约,惟有单一的政府、统一的政体方能给城市带来幸福,而相互攻讦、内部纷争往往导致毁灭、分崩离析。可见在为一统的“世界帝国”立论过程中,但丁沿用或模仿亚里士多德城邦优于家庭和村落的论证方式,以证明一统世界政体(世界帝国)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但丁说:“在那里,这位可敬的权威(亚里士多德)指出,每当几个物体结成一体,其中必有一个起调节和支配作用,其余则服从调节和服从支配。”[18]22但丁的论述进路无疑是聪明之举。13世纪,《政治学》由希腊语译为拉丁语,再经圣托马斯润色、调适而更加圆满,在欧洲大学等地影响日隆。但丁援引“可敬的权威”,使其论证更充分、厚重,自然有撼动人心之效,并力证亨利七世君临天下的合理性。但丁还认为,建立一个统一的政体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解决争执的需要。解决两个政体间的纠纷需要有第三者居中进行裁决。“因此,就有必要在这世界上建立一个世界政体。先哲亚里士多德也看到了这一点,他说‘事情最怕的是乱,而权威多了就会乱,因此,权威应该是独一无二的’。”[18]13
世界帝国思想源于但丁对当时政治现实的思考,体现了政治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但丁对其生活时代的政治给予了极大的关注。”[19]彼时因教皇与世俗君主争夺控制权,意大利陷入分裂与战乱。面对纷繁复杂的政治格局,但丁眷恋古罗马帝国,渴望其再现辉煌,因此主张建立以日耳曼皇帝为首,以意大利为中心的世界帝国,进而实现政治理想。时过境迁,他的罗马帝国情怀及所勾勒的政治图景注定难以实现,因此世界帝国思想具有空想性,但对当时四分五裂的意大利而言,他的和平、统一的主张具有进步意义。
作为但丁的同时代之人,马西利乌斯目睹了意大利的政治纷争。当时奥地利的腓特烈(Frederick of Austria)与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Ludwig of Bavaria)均被推举为罗马人的国王(king of the Romans)。之后路德维希打败腓特烈,在罗马加冕,但当时的教皇约翰二十二世拒绝承认其为国王,于是路德维希改立尼古拉五世为教皇。作为路德维希政治活动的见证者,加上他对意大利城邦国家未来命运的思考,马西利乌斯撰写了《和平保卫者》(The Defender of the Peace)。该书开篇即阐述了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理论,总论世俗权威与组织,为后面的论述奠定理论基础。
马西利乌斯认为国家是自然的产物,这颇受亚里士多德城邦起源论的影响。以他之见,国家(realm)由同一政体下数量不等的城市或省份构成,[20]11国家经过家庭、村落、社会团体(community)等阶段而自然形成。国家的目的在于提供“优良生活”——现世的和来世的。在论国家的构成时,马西利乌斯直接借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卷七,章七)的分类,认为国家由农民、手工业者、武装部队、有产阶级(部分)、教士团体以及裁决团体等构成,[20]22但各部分的价值并不相等。农民、手工业者价值远不如教士及士兵,他们也不可能享有同等的政治地位。马西利乌斯还强调国家形成与人自身弱点相关。[20]19-20人类天生的弱点及特质注定要过社会生活,而作为更高层次的共同体——国家则为人类的这一需求提供了保障。不管是借鉴亚里士多德的城邦自然形成之说,抑或对人类自然本性及弱点的剖析,马西利乌斯都证明国家学说的自然属性。
马西利乌斯的立法者概念受到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启发,却又是对它的背离。“‘立法者’(legislator),或法根本和真正有效的原因,是人民、公民团体或公民团体中的主要部分(prevailing part);在全体公民大会上,立法者通过选举或用演讲的方式表达意愿,并做出决定:作为公民,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违反者会被课以罚金或予以惩罚。这与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卷三章六(注:按现在编排方式是卷三,章十一)的陈述和忠告不谋而合。”[20]66-67尽管马西利乌斯声称其立法者的概念与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的论述如出一辙,但《政治学》(卷三,章十一)通篇并未出现类似“立法者”的字眼,亚里士多德在此讨论的是城邦最高治权(dominant authority)应该寄托于什么(或什么样的人)的问题。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的最高治权在于政体(宪法),[12]132然后宪法派生出法律,“法律必然是根据政体(宪法)制订的”,[12]151因此“当然不能叫政体来适应法律”。[12]181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既然政体等同于宪法,并且是法律之源,则法律问题归结为政体问题。但以马西利乌斯之见,立法者是法律权威的来源,法律反过来又控制政府的功能。因此“马西利乌斯国家政治结构与传统的中世纪国家概念不同之处在于,最高治权并不依靠体现终极价值或目的因的‘高级法’,而是依靠称为‘立法者’的积极的人类能动性(positive human agency)”。[21]167总之,亚里士多德认为法律源自政体(宪法),马西利乌斯认为法律、宪法均来自立法者。正如沃格林所言:“马西利乌斯的立法者译自亚里士多德的nomothetes(创制者),是授予宪法秩序以权威的世间能动者,在这种宪法秩序下,统治者可以执行其包括法规制定在内的职能。”[22]
马西利乌斯的公民定义来自亚里士多德。“据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卷三之1、3、7章,我把公民定义为参与公民共同体,根据其等级行使统治、协商与审判之人。”[20]67-68然而,但亚里士多德认为,其公民定义最适合于民主政体,生活在其它政体中的公民可能与这一定义相符,但不一定完全切合;公民兼有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属性,既能指挥而行令又能受命而服从;再者,公民身份还应考虑政体种类,能否具有公民身份取决于其所在城邦类型。相比较而言,马西利乌斯观念中的公民资格没有这般严格,他们无需具备成为统治者或制定法律所需知识以及深谋远虑的才干,如判别统治者理政之好坏和立法是否充分。[21]176
马西利乌斯的国家和立法者等概念都包含了亚里士多德《政治学》思想。但事实上,他并未拘泥于此,他修正乃至偏离了亚里士多德学说。马西利乌斯生活的时代,城邦早已面目全非,他的出生地帕多瓦只是神圣罗马帝国治下的意大利北部小邦,利用国王与教皇“鹬蚌相争”的局面,拥有一点独立地位而已。在这种背景下,他以帕多瓦人的身份研读亚里士多德,是要借他的学说,为独立的或即将独立的意大利城邦张目。[9]138在王权与教权的博弈中,“立法者”表达了人民权力至高无上的一元权力观,并否定了神权至上观念,为王权派也为世俗君主奠定了民权基础,开辟了新的权力源泉,促进了中世纪政治思想的发展。
四、《政治学》对基督教的“启蒙”
综上,基督教不同派系均借鉴了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的诸多概念。以这些概念为代表的理性对基督教信仰有一定的“启蒙”作用,以下略举一二。首先,《政治学》在人的属性方面对基督教有“启蒙”作用。基督教自初创之时便体现出神秘主义的特点,它是超越理性的,只有依靠信仰才能把握。作为理性载体的人只有被动信仰、接受。唯一体现人属性的痕迹在于有关基督二性,即神性与人性的分歧论战。人的“原罪”需要至善的化身上帝去拯救。因此宗教对人的定义淹没了人的政治属性,逐渐形成了圣保罗—奥古斯丁主义传统。上述学者中,阿奎那借鉴亚里士多德有关人的社会与政治属性的论断,马西利乌斯对人类必须过社会生活的认知都是基督教神学以前没有的概念。这可以被视为基督教对人的属性认识的扩大,对人类先天理性能力的承认。但基督教不会轻易让人的理性超越信仰,于是给理性设定一个天启的来源。如此,人的自然性、社会性与人的宗教属性融为一体,基督教确立了理性神学方向。
《政治学》的“启蒙”还体现在基督教对世俗政权(国家)及俗世政治的接纳。“凯撒的物当归凯撒,上帝的物当归上帝”(路加福音二十:25)及“我的国度不属于这世界”(约翰福音十八:36)说明基督教欲撇清它与国家的关系,对其敬而远之。这可能源于基督教最初遭受世俗政权迫害所带来的痛苦回忆。中世纪时,这种对世俗权力的警惕逐渐转变为两者一决高下。如前文所言,奥古斯丁认为人的“原罪”是国家的起源,是对上帝至善的一种忤逆;国家的建立及与之对应的俗世政治只是人类统治欲望的反映,[23]其本质不可能是正义的。这是一种消极的国家观。而自阿奎那至马西利乌斯无一不借亚里士多德之口,强调世俗政权的自然起源与属性,国家是人的社会性与政治性的必然要求,旨在促使公民过一种有德行的生活。再者,以奥古斯丁为代表的基督教政治神学认为,政治是“人类堕落后的‘惩罚’” ,[24]它是维系人类社会文明,解决冲突与混乱的一种制度或手段,它依附于宗教,因此被边缘化了。中世纪后期,基督教神学家融合了亚里士多德的自然政治观,认识到政治制度的目的在于实现至善,逐渐淡化奥古斯丁政治神学“惩恶”的理念,逐步提升政治的地位或确立其正当性,改变政治边缘化的状态。表面上看,基督教神学家是在吸纳亚里士多德学说,消除其威胁,实则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意大利北部城邦崛起,民族国家意识日渐增强,以法兰西王国为首的王权不断壮大,甚至一度让罗马教廷屈服,基督教会对世俗政权的控制愈发力不从心,教俗二元权力有倾向俗权的趋势。这都促使基督教会有识之士革新神学理论,以改变现状。而“神启”“惩罚”论等说服力日渐苍白,基督教神学疲态毕显,必须另辟蹊径以纾解这一危机。恰恰亚里士多德研究城邦所提出的一些概念为中世纪思想家提供了现成的分析“话语”。[4]277,373这些属于人类理性研究的范畴,并不受上帝神启的约束。既有此便捷、成熟理论可借鉴,神学家们自然取之、用之并改造之。
最后,“启蒙”还体现在神学家们对亚里士多德政体理论的借鉴。按照基督教教义,世俗政体是人性恶的体现,必挞伐、贬低,除之而后快。但中世纪后期,由于形势所迫,在亚里士多德共和政体最优的基础上,神学家们纷纷提出自己的政体观:阿奎那拥护君主政体,巴黎的约翰中意一人之治的君主制,但丁倡导一统天下的君主建立的世界帝国等等。《政治学》极大地开阔了基督教神学家的眼界,“启蒙”了他们国家自然起源的论断,给了他们更多宗教信仰以外的想象空间。这便是曾在数千年前有效的使城邦运转有序,使人与城邦和谐有致的一套机制,它在基督教神学家的论著中发出了耀眼的理性光芒。
五、结 语
中世纪后期,裹挟在教权与王权纷争,教皇与国王博弈漩涡中的《政治学》诸多要素,如自然政治观、法治、君主制与公民概念等,经托马斯·阿奎那、罗马的吉尔斯、巴黎的约翰、但丁及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等人的渲染、改造和吸纳,以巴黎、罗马等为中心传播开来。促使这一局面发生的因素有亚里士多德革命的警醒作用,更有基督徒自发译介《政治学》所引发的涟漪。尽管基督教神学家存在派别之争,传播《政治学》的目的迥异,甚至一度让它变成基督教派系间彼此攻讦的武器,但他们的最终目的是要把以《政治学》为代表的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说纳入基督教麾下,以修正奥古斯丁为代表的早期基督教思想,成功开辟出基督教神学—哲学中的“亚里士多德主义”。由此,基督教神学拥有了新的话语体系乃至新的理论基石。
作为一位颇具影响力的“异教徒”和文化权威,亚里士多德不再是基督教“危险的敌人”,而是成了基督教神学家们的“导师”。《政治学》的回归对基督教重新认识它的地位和作用,乃至审视自身组织内部架构都具有重要的“启蒙”意义。亚里士多德学说已势不可挡,作为拥有庞大、精致理论体系的基督教会也不敢等闲视之。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基督教会具有审时度势的应变之道、柔性和包容性等特点,很好地解释了基督教何以能够基业长青,绵延数千年。因此我们或许需要深化或改变已有的认识:宗教与以政治学说为代表的世俗学问并非永远对立,水火难容;在西欧中世纪,基督教成为传播亚里士多德学说的先锋和当时先进新思想的引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