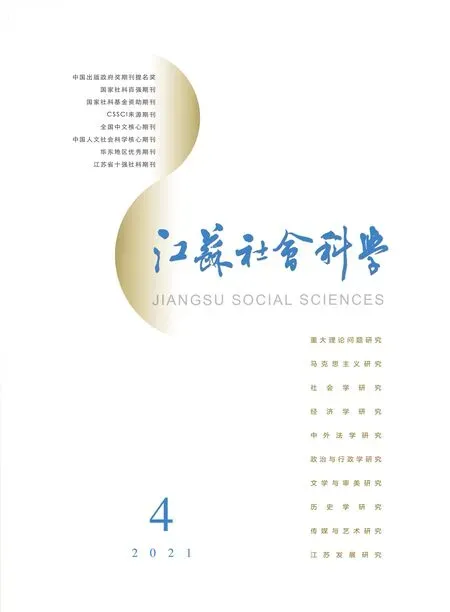当代批判理论的审美政治及其美学进路
—— 以阿甘本为中心的考察
王大桥 刘 晨
内容提要 作为当代批判理论的代表性作家,阿甘本以“装置”思考生命权力对个体感觉方式的钝化问题,推动了当代批判理论经由生命政治、感觉政治转向审美政治,感觉及其意义的社会发生机制是审美政治的深层逻辑。阿甘本以贴近生活形式的潜在性感知推动当代批判理论的审美政治转向,审美政治逐渐融入日常生活的经验语境,赋予审美参与并改写社会实践的现实介入性。当代批判理论下沉于生命基底之处的感觉方式,其审美介入性在权力治理等议题上具有激进的理论锋芒。
当代社会涌现愈发复杂的社会问题,恐怖主义、环境污染及资本的全球化危机等问题爆发,传统批判理论对此难以回应,现实问题推动批判理论在当代的转型。基于研究视域的不同,批判理论的划分包含多种方式。早期批判理论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主,立足现代社会的意识形态批判;后批判理论是批判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的转型,吸收后结构主义思想,关注社会边缘的文化群体;阿甘本、朗西埃和奈格里等当代批判理论秉持激进的理论锋芒,呈现对当代社会的强烈批判与重建[1]海科·费尔德纳(Heiko Feldner) 和法比奥·维吉(Fabio Vighi)的《批判理论与当代资本主义危机》(Critical Theory and the Crisis of Contemporary Capitalism)、达罗·斯科特(Darrow Schecter)的《21 世纪的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和瑞兹米格·基切扬的《左半球:图绘今日批判理论》等都提出批判理论发展的当代形态,其中包括朗西埃、阿甘本和奈格里等人。当代批判理论“Contemporary Critical Theory”强调在后现代之后,基于当代社会语境,对批判理论进路、范式和问题的反思与发展。。批判理论关注个体感知和认知现实的条件。个体日常的感觉方式与经验内容是特定社会现状存续的基础结构。批判理论的美学思想以感觉政治为进路,审美与政治经由感觉政治的问题逐渐交叉,审美政治成为批判理论发展不同阶段的重要问题。早期批判理论将审美政治安置于超越现实的审美乌托邦,以自律的审美艺术遥指政治问题;后批判理论将审美政治回归现实,强调现实生活中感知绝对的创造与生成;当代批判理论将审美下沉于日常生活的地平,回归生命经验的真实现场,以感觉方式的流动与停滞粘连社会政治的不同维度。阿甘本以生命政治指认当代社会权力对个体生命事实的渗透,生命权力以模式化的感知结构填充生命的生活感受,使生命的形态扁平化。他将生命解放的可能转向日常生活感知方式的变革,以生命潜能的感知方式,将审美政治的地基置于生活形式之上的潜在性空间。作为当代批判理论的代表性作家,阿甘本经由对感觉与政治关系的思考,参与和推动了当代批判理论审美政治问题的转换与美学进路的形成。
一、感觉方式:当代批判理论的审美政治视点
阿甘本政治美学的相关研究进路跨越多重学科。阿甘本早期关注语言与存在、诗与思的问题,后期以生命政治理论切入政治哲学问题,本雅明、居伊·德波、福柯和马克思等是他重要的理论资源。对阿甘本政治美学的研究基于不同的问题定位,后马克思主义、当代激进左翼与批判理论是重要的观测视点。后马克思主义基于后现代多元、破碎与差异的思想范式,持守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的反思立场。斯图亚特·西姆准确指认两者现实语境的转换,“后工业社会的新无产者构不成一个阶级,他们与工作世界是如此疏离,以至于它完全不会诉诸于阶级意识或团结意识”[1]〔英〕斯图亚特·西姆:《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吕增奎、陈红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0页。。墨菲与拉克劳以霸权理论审视马克思总体性的政治权力模型,以政治权力框架内多元的符号话语斗争回应阶级革命问题。他们将阿甘本归于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光谱,考察的是其政治美学思想在何种程度上拓展了经典马克思主义有关阶级、解放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思考[2]丹尼尔·麦克罗琳分析道,“如巴迪欧和阿甘本以忠诚的革命传统回应历史的终结,保持对权力话语的强烈批判,同时在经典马克思主义视野之外更新革命政治行动的理论范式”。Daniel McLoughlin, "Post-Marxism and the Politics of Human Rights: Lefort, Badiou, Agamben, Rancière", Law Critique, 2016(3), pp.303-321.。阿甘本接续的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激进的权力批判与政治解放立场,生命政治、例外状态与赤裸生命等概念是主要的研究对象,价值形式、资本权力和商品拜物教的概念一定程度嵌入生命政治理论,阶级解放的问题被纳入至高主权与赤裸生命的二元结构,权力展布的根基由资本的剥削转向个体生物性的生命事实。
将阿甘本置于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美学进路,则问题取决于研究对象在何种程度上突破了传统的审美反映论,不再囿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单向切分。德勒兹以欲望政治学审视马克思的革命理论,“现存的体系因此得以存在,不是因为欲望反映了统治秩序,而是因为统治秩序以肯定欲望的方式塑造欲望”[3]DeleuzeG, GuattariF, Anti-Oedip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London: Athlone, 2004, p.34.。德勒兹后马克思主义研究进路的重要维度在于分析权力与欲望机器的关系,而生命欲望生成与创造则不同于马克思的阶级革命论,转向一种文化政治学的视角,强调符号意义的表征与反抗。阿甘本接续的是居伊·德波和福柯等人的思想,以生命政治重新阐释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将商品价值形式的切分作为生命权力展布的装置,生命在景观社会中无意识地为生命权力构造的虚拟影像所捕获。在阿甘本看来,“景观即语言,即交流活动,或人类的语言的存在。这意味着,一种更为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式的分析,必须认真对待这样一个事实,即资本主义(或者你愿意给今天支配世界历史的进程其他任何一个名字)不止被导向对生产活动的剥夺,还被导向且在原则上朝向语言本身、人类的语言和交流天性”[4]Giorgio Agamben, The Coming Community, translated by Michael Hardt, Minneapoli: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7, p.72.。资本对剩余价值的剥削转为影像媒介对个体生命事实的填充,权力从生产劳动领域扩散到日常生活的个体经验层面,既定的语言系统、生活惯习与审美经验内嵌于生命权力的展布逻辑,传统的政治经济批判拓展至个体感性生命事实的异化。
批判理论与后马克思主义作为阿甘本政治美学研究的进路,共享相同的理论预设,即翻转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生产逻辑,后者尽管反思并回应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但总体理论范式仍囿于相关概念、问题和范式的思想边界[1]西蒙·托米与朱尔斯·汤森对此加以分析,“我们感兴趣的是那些曾经宣称存在马克思主义危机的人在正统学说崩溃,重新对其遗产进行思考,以重构理论的批判,后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中心元素是在马克思主义问题的轨道内”。Simon Tormey, Jules Townshend, Key Thinkers From Critical Theory to Post-Marxi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6, p.5.。后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视点很大意义上基于同经典马克思主义关系的勘定与发展。批判理论的审美政治进路则不同于后马克思主义,而是一种以感知方式把握并诊断社会病理的研究思路。早期批判理论面对的现实语境并非工人劳动的异化与生产关系的剥削,而是革命群体何以丧失能动性,自发嵌入资本权力秩序。阿多诺就指出了文化工业内在地侵蚀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主体性。阿甘本等当代批判理论进一步聚焦日常生活的情感经验与权力的隐性关联。海科·费尔德与法比奥·维吉即指出,当代资本社会的经济危机是现代理性的灾难性退化,阿甘本的弥赛亚主义补充了批判理论对根植于现代社会无意识母体的感觉形式的批判[2]Heiko Feldner, Fabio Vigh, Critical Theory and the Crisis of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London: Bloomsbury Publishing,2015, p.6.。
批判理论并非一种先验的社会蓝图,而以社会批判的形式,分析个体的情感、经验、感觉方式与社会进程的关联,正如将德勒兹置于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脉络,是基于生命欲望和强度如何拓展马克思的政治理论,“欲望不能被视为仅仅是上层建筑的效果,欲望应该被认为是意识基础的主要组成部分”[3]G. Deleuze, F. Guattari, Anti-Oedip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London: Athlone, 1984, p.34.。个体感觉方式的引导和塑造成为外在于资本剥削的权力核心,若置于批判理论的审美政治进路,则问题转向生命欲望的生成如何推动审美解放的问题。阿甘本在批判理论的美学进路内,以潜能、亵渎和生命形式等概念,让审美与个体切身的生活语境粘连,从具体的现实生活中发掘感觉方式激变的可能。施洛儿·特伦特指出:“批判理论作为一种思维形式的核心在于它能够看到思维和行为之间的内在联系,它预期解放性的感知、经验和思维转变的社会实践维度。”[4]Schroyer Trent, The Critique of Domination: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Critical Theory,New York: Braziller, 1973,p.31.现实语境的转换使阿甘本越过阶级革命与工人暴动的问题,关注权力对个体生活形式的异化。意识、经验和情感的结构化,固化了生命形式,隐秘地巩固了至高主权的神圣性。审美政治是批判理论的重要维度,它们不再将个体心理意识、情感经验作为消极的上层建筑,而视为权力斗争的先导因素,社会批判由特定的生产关系和身份表征的符号策略转向生命活动底层的感觉方式。
批判理论与激进左翼共同具有审美政治的维度,但前者经由感觉政治的问题思考审美政治。当代激进左翼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共同秉持对权力秩序的批判与个体自由的追求,但两者包含不同的理论进路,后者问题的展开逻辑主要基于资本关系对劳动生产价值的剥削,前者分析当代政治领域权力结构的转变,单极权力的资本盘剥分散为日常生活权力的微观治理。在此研究视域,阿甘本以生命政治透视当代社会的权力机制,权力由传统的司法逻辑转向个体生命事实的治理。科林·麦奎兰在激进左翼的政治理论框架内,考察了阿甘本关联文本意义的解读与生命政治问题的脉络线索[5]Colin McQuillan, "The Real State of Emergency: Agamben on Benjamin and Schmitt", Social & Political Thought, 2011(3), pp.96-97.,当代激进左翼根植于权力展布方式的转变,分析了权力渗透于日常生活的感性实践的具体机制。激进左翼与批判理论共同具有审美政治的维度,但两者审美政治的理论进路并不等同,当代激进左翼的审美政治指向全面生命政治化时代,个体的自由解放如何可能的问题,并不特指某种审美政治问题和进路。阿甘本、奈格里、埃斯波西托和朗西埃就分别从资本生产、国家主权与审美经验的角度,指出权力对个体日常生命事实的管控。在此意义上,他们都处于当代激进左翼审美政治的研究视域。而批判理论则以一种对情感-感知方式的研究,以感觉及其意义的生成机制分析政治权力的展布逻辑。阿甘本的政治美学思想可置于后马克思主义、激进左翼与批判理论的研究进路,但三者关注美学与社会现实的问题并不相同,将阿甘本置于批判理论的审美政治进路基于他的如何潜能、亵渎与形式生命等概念,这些概念推动了感觉方式介入社会政治的条件机制问题。
二、感觉政治:当代批判理论的美学进路
当代批判理论的现实语境并非劳动异化与生产剥削的问题,而是权力对个体日常生活的生命事实的全面殖民。早期批判理论即思考工具理性对社会生活诸多领域的渗透,使得个体同构于程式化的理性生活,阿多诺以“全面管理的时代”指认当代的垄断资本主义社会,它以大众媒介和文化工业为载体传播工具理性,内在而隐蔽地侵蚀无产阶级的革命主体性。福柯、德勒兹和阿甘本等人以生命政治进一步指认了这种政治权力构造的转换,单极国家权力对生命的死亡暴力转为日常生活领域对生命事实的异化。
生命政治的核心在于将人从一种开放性的生命降格为一种生物性的生命事实。至高主权与赤裸生命的二元结构是生命政治的显性逻辑,但进一步的问题在于生命何以自发嵌入这种二元结构,即“个体们的自愿被奴役与客观性的权力之间的触碰点是什么?”[1]〔意〕阿甘本:《神圣人: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吴冠军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 年版,第9页,第10页。那么,如何理解个体认同主权以例外状态将政治生命与生物性切分并排斥后者的逻辑?在阿甘本看来,生命政治的基本前提是生物性生命(zoe)和政治性生命(bios)的二元结构,生命权力以政治性生命建构个体虚假的生命形式,通过对既定的社会文化与生活方式的意义编码,以一种直接纯粹的生活事实塑造生命的经验、情感、想象与欲望,而生命形式的反面即人之质性的否定判断,它将一部分不可纳入生命政治范畴的群体驱逐。在此意义上,生命政治的问题从至高主权对赤裸生命杀戮的表层,转换至当代个体于社会生活中潜在地沦为赤裸生命的内核。正如克莱尔·科尔布鲁克的分析,“现代性为越来越多的生命政治充塞,人不再具有决断自我个性的能力……失去的是一种生命在现实中自我构成的开放性潜能”[2]Claire Colebrook, "Agamben: Aesthetics, Potentiality, and Life",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2008(1) , p.112.。生命权力展布的内核是生命个体全面降格为生物性生命的过程,“创造一个生命政治性的身体是至高权力的原初活动……通过把生物性的生命作为它的重点算计对象,现代国家实质上显露出了把权力同赤裸生命联结到一起的秘密纽带”[3]〔意〕阿甘本:《神圣人: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吴冠军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 年版,第9页,第10页。。权力通过预置的生命形式填充个体的生活事实,从日常生活领域完成了对个体的思维、行为与经验的赤裸化改造。生命的意义被安置于机械的生命形式内,它填充了个体的存在状态。而当生命丧失对生活事件自我反思与开放的可能性,让其生命鲜活的状态钝化并均质,也就自动接受了至高主权以保护生命的名义对一部分生命的降格,生命以社会部件的形式隐秘地嵌入了生命形式与赤裸生命的政治模式。
感知的钝化与经验的稀薄是当代批判理论思考生命政治问题的重要进路。早期批判理论关注到现实生活个体的感知方式与权力的同构,阿多诺以文化工业分析了现代个体审美经验的标准化;西蒙·马赛尔进一步指出个体心理意识的异化与权力的深层联结,“主体被还原为一种原子化的个体,作为理性的代理人,不断复制新自由主义资本的政治经济框架”[1]Simmon Mussel, Critical Theory and Feeling: The Affective Politics of the Early Frankfurt School,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17, p.7.。当代批判理论则明确论述感知与政治的一体化关系。阿甘本将生命权力指认为一种对生命的生活方式的“禁止”,它以生命形式预设现实客体的意义边界,生命权力“在同禁止(或弃置)的一个关系中来维持自己,从而将自身实现为绝对的实在性”[2]〔意〕阿甘本:《神圣人: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吴冠军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 年版,第71页。。既定的文化系统、生活方式与经验结构禁止生命逾越现实经验的边界,它规定个体感知的内容,将生活形式之于生命的意义浅表化。生命权力的展布机制在于对日常生活关系的装置化,它以纯粹的经验事实分隔生命与生活形式的关系,现实客体之于主体被划分为神圣与世俗、可用与不可用、可感与不可感。装置“在某种程度上有能力捕获、引导、决定、截取、塑造、控制或确保活生生之存在的姿态、行为、意见或话语”[3]〔意〕阿甘本:《论友爱》,刘耀辉、蔚光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年版,第71页,第26页,第17页。。装置即生命的主体化进程,它并非某种纯粹的生命观念,可以被还原为一种意识形态,而在于作为感知的支点,分隔个体生活空间的可能性,固化生命流动生成的经验内涵,锚定一切差异化的生命存在,从感知的基底之处将生命降格为均质、粗糙和可计算的生物性生命。阿米特支持了阿甘本的相关判断,“我们定位自身的存在方式基于情感的循环、调制和突变,人类多样性能力的衰退需从生命政治的角度理解,情感的循环意味着政治层面永久的紧急状态”[4]Amit Rai, "Here We Accrete Durations: Toward a Practice of Intervals in the Perceptual Mode of Power", Patricia Ticineto Clough and Craig Wiltse(eds.), Beyond Biopolitics: Essays on the Governance of Life and Death, Durham and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311.。生命权力通过将构成个体情感与经验的生成过程切割,将感知的运动降格为神经活动的刺激反应,这实际是一种对感知能力的调节与经验深度的压缩,它指向对生命的感觉强度的钝化。
批判理论介入社会批判的方式并非实在性的社会规划,而是一种主体与客体纯粹的感知关系,权力并非一种特定意识形态内涵或政治经济结构,而是对生活惯习、日常经验与感知方式的开放性的捕捉,这使得批判理论并非隅于特定的意义-表征机制问题,而在于思考钝化的感知再生产支配性权力关系的条件机制。阿甘本将装置指认为一种塑造主体化的“治理机器”,但这种主体并非基于特定的社会身份、生活方式与价值信仰,它坐落于装置的分隔性网络之中,指向对生命潜在性状态的捕获。“资本主义宗教实现了纯粹的分隔,纯粹到没有留下任何可分之物……对被完成、被生产,或被经验一切事物来说也如此。”[5]〔意〕阿甘本:《渎神》,王立秋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年版,第140—141页。阿甘本对生命权力的思考并非基于装置对主体形式的正面建构,装置恰恰是一种去主体化的关系网络,它并非实在性的观念内容,而是否定生命感知的创造性,将生命自由流动的经验还原为一种“惰性之躯”[6]〔意〕阿甘本:《论友爱》,刘耀辉、蔚光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年版,第71页,第26页,第17页。的生物性事实。当代批判理论将感知置于政治权力的底层逻辑,透视社会治理与生命异化的问题,不同于西方马克思对阶级意识的分析,而是考察革命阶级何以自发接受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葛兰西、卢卡奇等人以文化领导权、阶级意识与审美意识形态概念,强调统治阶级对大众心理意识的塑造,但并未深入解释社会个体为何自发认同服务特定政治结构和阶级群体的文化内容。而在批判理论看来,根本问题是个体感知方式和经验内容的异化。权力对社会的支配以异质性生命状态的整合为前提,这一过程伴随着权力生命经验的惯习化,它以稀薄的生活经验提高个体生命经验的阈值,淡化感知的强度。阿甘本将装置拓展为日常生活全部的经验关系,“包括笔、书写、文学、哲学、农业、烟、航海、电脑、收集、语言等一切物质要素”[7]〔意〕阿甘本:《论友爱》,刘耀辉、蔚光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年版,第71页,第26页,第17页。。生命权力对生命潜在的赤裸化正是基于对感知的持续刺激,它在日常生活中无差别地惰化生命的感知,将个体流动性的经验凝固为一种生活惯习,从而使生命降格为一种生物性生命,平滑地整合于生命政治的权力秩序之内。
批判理论特别关注“感觉与意义”以及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情感生成的社会机制,具体呈现为审美政治的维度。感觉方式的钝化是当代社会权力展布的首要条件,阿多诺在早期已经消极地指认工具理性全面渗透的现实,主体被降格为均质的社会构件,他“认为意识形态内容本身并不是不真实的,而是它理解现实方式的主张”[1]Adorno Theodor, Prisms: Culture Criticism and Society, translated by Samuel and Shierry Weber, Cambridge: MIT Press,1981, p.32.。阿甘本在相同的意义上指认装置对生命潜能的捕获,分析生命政治的底层逻辑,正如他将主体化与再主体化的内循环视为生命权力的运动过程,“个体永恒且不由自主地陷入并屈从生命权力对主体的不断定义之中”[2]Ulrich Raulff, "An Interview with Giorgio Agamben", German Law Journal,2004(5), p.116.。生命政治通过装置将生活空间压缩为可知与不可知、可感与不可感的禁止性结构,以客观的意义网络整合生活事实,生命形式在生命经验的发端即作为意义的支点,锚定一切感觉及意义的发生过程,生命在无质性变化的经验闭环中坍缩为赤裸生命。感觉政治中感知的钝化与经验的削平需下沉于感觉与意义发生的基底,让意义先于感觉活动,以一种预置的意义线索先验地排列、结构并编织杂多丰富的感觉碎片,感知的运动过程由此抽象为一组形式化的感知结构,而生命解放的可能则在于穿透固化的意义网络,恢复感觉及其意义的生成,让感觉方式重新锐化。感觉政治学作为批判理论的进路并不仅指某种意识形态的主张,而是权力塑造并传播的体制化的感知结构,它遮蔽生命经验的偶然与差异,维持既定的社会生活秩序的合理性;感觉方式的革命则让生命的意义重新流动并丰盈,拒斥权力以同质化的经验系统对个体生活意义的填充。
审美解放的问题根植于感觉及其意义活动不可穿透的神秘性。阿多诺以审美幻象对生活表象的增值,回应现实经验的全面异化问题,审美感知从既有的感知结构的裂隙溢出,客体的经验不再等同于稳定的意义结构,而呈现意义的盈余。阿甘本在此意义赞同阿多诺超拔的审美乌托邦,“实现哲学的时机错失了,就迫使哲学在不确定性中思考救赎的对象”[3]〔意〕阿甘本:《剩余的时间:解读罗马书》,钱立卿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第56页。。现实经验本身的装置化使感知的解放必然呈现“魔法之上的魔法”,客体需始终保持特定意义难以穿透的神秘性,使生命经验处于“仿佛如此(as if)”的潜在性状态,从而逃逸生命权力的展布逻辑。马苏米对感觉政治的分析旁及这种审美解放的内在逻辑,“情感不能包含于已然预置的文化意指系统,也不能被既有的认知思维捕捉,它受一种至今无法跨越的延迟所限制”[4]Brian Massumi, Parables for the Virtual: Movement, Affect, Sensation, 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28.。感觉的解放基于个体情感与庸常生活意指结构的间隔,其使经验内容处于一种不确定、运动中的事件状态。阿甘本由此以生命的“潜能”感知,思考生命一切皆可、一切皆无的潜在性状态。潜能感知回应的是“一种感觉何以可能在感觉缺失的情况下存在”[5]〔意〕阿甘本:《潜能》,王立秋、严和来译,漓江出版社2014 年版,第293页,第292页。的问题,即感觉如何突破既有的意义秩序,让经验不断生成。生命的潜能意味着悬置了特定的感知模式,“这个‘我能’超越所有能力,超越所有知识,这个肯定除了指称直面最为迫切经验的主体,什么也不意指”[6]〔意〕阿甘本:《潜能》,王立秋、严和来译,漓江出版社2014 年版,第293页,第292页。。感觉仅是从实在化的意义赋予活动回归的一种潜在性,保留主体与客体之间交融共振的无线可能性,而非实体化为既定的感知活动和生活事实。批判理论的审美政治指向主体与客体对象的交融互渗的感知关系,丰富的客体不再被当作主体以特定的意义模式削平,而是在两者之间的互动过程中让意义开放,颠倒和倾覆既有的生活形式和经验表象。
当代批判理论的审美政治问题最终指向一种多重层叠的生命形态,它以意义的无限可能拒斥一切权力秩序的规约,这种抵抗不是传统政治经济学意义上被压迫群体的外部斗争,而是一种社会个体的存在方式的差异化表达,而这种政治主体的形成需要沉降于生命的基础性的经验活动中展开。只有当生命的感知方式不再同步于现实的意义表象,让主体与异质性客体处于不确定的关系,才能诞生一种权力难以公约的生命状态。正如阿甘本以生命经验的“剩余状态”,强调生命所处的无可划分的混沌状态,经验的剩余并非以多元的经验内容抵制整一的感知模式,而是一种不可被任何实在的经验形式所填充的意义的潜在性,他以任意的经验意义抵制一切生命权力对感知方式的分隔。而一旦生命以普遍的知识、思维与意义作为其经验的坐标,其也就随之丧失自身的神秘性,经验内容的透明与可穿透会使一切生命存在均质化,丧失跳脱既定生活方式和社会秩序的能力,权力得以单向完成对消极的个体生活事实的灌输。因此问题的核心不在于革命群体被虚假意识欺骗,而需从宏观的文化领导权、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概念下沉至个体经验的基底,从感觉与意义的关系问题切入。
三、审美介入:当代批判理论的实践品格
早期批判理论的审美政治呈现审美对现实的超越与救赎,当代批判理论的审美政治则强调审美介入并改造现实的实践品格。阿多诺以“全面管理的时代”指称当时的社会现状,现实经验异化为工具理性的单向表达,艺术一旦与异化的现实产生对象化关联,则会沦为现实世界的同一性表达,这使早期批判理论的审美政治必然转向一种超拔于现实的审美乌托邦。南森·罗斯指出,“艺术呈现一个自主表象的领域,正是这种能力使其展开对工具理性和意识领域的激进批判”[1]Nathan Ross, The Aesthetic Ground of Critical Theory: New Readings of Benjamin and Adorno, London: Rowman &Littlefield International, 2015, p.25.。早期批判理论的审美救赎并非坐落于现实社会,而以“谜一样”的特质存在于现实之上的审美世界。阿多诺以客体优先的原则,强调无限庞杂的客体对主体感知的超越,其粉碎并击穿既有的经验表象,审美政治被置于一个现实经验难以靠近的彼岸世界。阿甘本由此批判阿多诺的审美乌托邦,他使任何个体的经验经由对现实意义的纯粹否定,退化为丧失任何潜在性的非现实。不同于阿多诺以超拔的审美感知与现实完全切割,阿甘本认为弥赛亚时刻源于生命与生活此时此刻的亲密与张力,“已存在事物之救赎正是弥赛亚事件准备的迫切性领域”,这也就是阿甘本尽管赞同阿多诺将审美政治指向“魔法之上的魔法”,以救赎异化的现实经验,但又认为“对阿梅利与阿多诺来说,一切主张高举魔法的姿态全都是空洞的”[2]〔意〕阿甘本:《剩余的时间:解读罗马书》,钱立卿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第57页。。审美介入现实的方式并非以无法感知的方式彻底摧毁既有的经验内容,朝向一个绝对神秘的审美乌托邦。阿甘本据此将潜能的感知呈现为对既有生活形式的亵渎,它并非彻底脱离现实的意义结构,以不可感知的审美救赎自上而下地演绎现实,而是以去目的化的姿态,回归生活经验本身的潜在性空间,将流动的生命状态安置于感觉与意义共振的现实结构中。早期批判理论预先以感觉的绝对生成脱离了既有的意义结构,生命主体的存在被安放于绝对不可认识、难以靠近的客体,这种审美政治策略难以产生事实上的政治介入效果。无尽的审美幻象脱离现实经验的地基,感知方式的革命在松动现实时,也预先偏离了个体真实切身的生活事实,这使审美政治先验地预置了一个理想的生命状态,与大众庸常的生活经验割裂,很大程度囿于自律的艺术哲学,难以真正进入具体的社会政治问题。
批判理论在20 世纪60 至70 年代经历后结构主义转向,后工业社会形成了复杂的社会群体。后批判理论审视审美乌托邦的神秘化倾向,重新勘定生命与生活的关系,让个体既有的生活模式碎片化并不断组合与生成,发掘平滑的现实表层之下意义的层垒。德勒兹以一种欲望政治学,将生命解放指向一种现实中感知的解域化运动。尽管审美解放进路将感觉方式的变革指向现实生活,但仍脱离个体实际融入的日常生活语境,正如米歇尔·菲奥拉的质疑,“福柯的自我艺术需要我们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创作出一种尚不存在的东西……对于那些聚焦于社会空间中的规范问题的读者来说,这个命题包含了重要的歧义,即在怎样的情况下,我们规范性的生活现状才能是绝对的创造”[1]Michael Feola, The Powers of Sensibility: Aesthetic Politics through Adorno, Foucault, and Rancière, Evanston: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18, p.46.。差异性的感知革命最终指向并非是总体共享的社会行为,而是少数个体自我艺术化的生活方式。阿甘本与德勒兹共同强调生命感知的潜能,但两者走向的进路并不相同。德勒兹以感觉的分子式革命,将一切现实稳固的经验肌理击穿,长久渗透于个体生命历程的记忆、想象与情感的经验组织被粉碎,取而代之的是空无的内在性平面之上感知永恒的生成与创造[2]汪民安、郭晓彦主编:《德勒兹与情动·生产》(第11 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7页。。阿甘本则以“亵渎”的概念,限定生命的潜能。亵渎是基于生活形式之上的自由创造,其通过触摸生活经验的肌理,将既有生活空间作为经验延展的基座,并非绝对地钝化生命的感知。而德勒兹则以无形式羁绊的纯粹生命,将理想的生命安置于一个孑然孤立的内在性平面之内,这种撕裂一切生活形式束缚的感知仅作为一种追求生命纯粹性的浪漫化想象。
当代批判理论下沉于个体真实经历的生活空间,切入大众普遍共享的生活语境,审美与政治深度粘连,这赋予其审美政治介入并改造现实的实践品格,具有推动并改写既有社会生活的实际可能。德勒兹对生命稳定熟悉的经验活动的撕裂,使后批判理论的审美政治难以被不同生活空间的个体共享,也难以对接既定的社会生活语境。德勒兹以内在性概念“触写那个超越(或先于)一切意识观念的一个前个体的、绝对非个人的区域”[3]〔意〕阿甘本:《潜能》,王立秋、严和来译,漓江出版社2014 年版,第412页。,其以先验的形式回应欲望机器对生命经验的辖域化,它切断并超越个体连续整一的生活意义,以感知的绝对生成将一切先在的意义网络穷竭,并以无形式、无内容也无意义的感觉颗粒重组并创造世界。但阿甘本在生命解放的问题上却采取了不同的审美进路,他以亵渎来拆解装置。当装置全面渗透于日常生活的基底时,我们该采取何种审美进路逃离生命权力对生命形式的捕获?“我们力求达成的,既不是简单地摧毁它们,也不像一些天真的建议那样,去正确地使用它们。”[4]〔意〕阿甘本:《论友爱》,刘耀辉、蔚光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年版,19页。生命的亵渎行为并非对感知分隔的超越和废除,个体的切身经验与情感倾向的变化必须基于既有的生活语境,我们难以如德勒兹一般以解构的姿态清空一切惯常的符号秩序与意义空间,日常生活的共同约定俗称的生活记忆与文化系统是经验生长的地基。这也使阿甘本的审美解放最终指向贴近生活形式的形式生命,而生命解放的可能也正在于感觉与既有的经验意义空间的共振与交融,个体生存其中的社会空间与庸常的生活语境是生命解放的坚实地平。
当代批判理论以审美介入的范式,深度参与治理、平等、解放与共同体等多个社会政治问题的思考。贝斯·汉德尔、维瑞德·迈蒙等人指出,“当代前卫艺术比任何时候都关注集体性政治的探索……朗西埃的审美共同体与南希共同体思想的交流有力补充了这一维度,通过‘感觉共同体’这一术语,试图开辟集体政治的可能性”[5]Beth Hinderliter, William Kaizen, Vered Mal Mmon, Jaleh Mansoor, and Seth Mccormick, "Introduction: Communities of Sense", Beth Hinderliter, William Kaizen (eds.), Communities of Sense Rethinking Aesthetics and Politic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2.。阿甘本则以生命共通的潜在性状态,探索了一种持守个体意义之可能性的“来临中的共同体”。他以共同的感觉方式思考当代社会的社群关系。阿甘本以装置概念透视生命政治的治理维度,其渗透于日常生活,包含语言行为、审美鉴赏与商品消费等一切模式化的感性活动,治理问题由塑造情感倾向与生活惯习的文化治理转向钝化感觉方式的审美治理,其以实在的感知形式分隔生命经验的潜能,潜在完成对生命的赤裸化改造。朗西埃则以可感性的重新分配,质疑既有的审美分配体制,通达一种歧义碰撞的感知逻辑,回应了当代社会的伦理平等问题[6]Jacques Rancière, Dissensus:On Politics and Aesthetics,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Steven Corcoran,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2010, p.178.。当代批判理论对生活语境的回归使其不再以现实之上的审美乌托邦改造现实,而是贴近既有的感觉及意义的发生机制,让生命的感觉活动与先在的意义结构彼此共振,在日常生活的基底处撬动现实秩序。
当代批判理论的审美介入范式包含多重异质的理论进路。阿甘本认为在生命全面政治化的时代,去创造、去生成即意味着被权力捕获,这使其以非现实的潜能将感知导向不做、不为后生命溢出的可能。奈格里不同于阿甘本以感知的不确定性,拒绝进入现实生活,止步于现实之上的潜在性空间,他从生命政治的母体内发掘审美解放的可能[1]Antonio Negri, "The Ripe Fruit of Redemption-Review of Giorio Agamben's The State of Exception", https://www.generation-online.org/t/negriagamben.htm, 2021-7-9.。奈格里贴近当代社会“非物质生产”的事实,分析个体之间情感的交流与沟通所具有的政治能量[2]〔美〕迈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年版,第36—37页。。基于当代社会生产方式的变化,他认为情感、趣味与欲望的交流可以孕育政治潜能,这使得他将生命的潜能指认为一种创造的动力,促使生命去构建并生成自我的形式。奈格里接续德勒兹对生命的纯粹内在性的思考,以感知于现实的生成创造探索一种集体性的政治抵抗行动。阿甘本则受海德格尔影响,以存在的不可言说性,使存在本身成为空无,通过让生命从现实生活实在性的符号秩序中回撤,将解放的承诺指向不做不为的形式生命[3]Antonio Negri, "The Ripe Fruit of Redemption-Review of Giorio Agamben's The State of Exception", https://www.generation-online.org/t/negriagamben.htm, 2021-7-9.。当代批判理论尽管持守不同的审美政治理论,但他们作为一个理论群体,共同以感觉方式的激变介入社会生活,将审美政治的视域沉降于日常生活的语境,俯身于大众细微琐碎的情感经验的地面,强调理论介入并改造现实的实践品格。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共享独特的审美介入品格。
审美介入下沉于个体日常生活行为的基底,这赋予当代批判理论介入并批判社会的激进锋芒。批判理论与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共同强调美学对社会现实的介入,但后者的介入性依凭既有的文化意指系统,以文本意义的解码与编码,关注边缘群体、性别和族裔的文化身份。托尼·本尼特以特定情感倾向对个体生活行为的管理,强调审美的治理性,“治理策略的本质是通过把共同体组织成情绪投入和情感认同的焦点而运转,目的在于使它们可成为自我治理的集体,能管理好它们成员的行为活动”[4]〔英〕托尼·本尼特:《文化、治理与社会》,王杰、张东红译,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版,第483页。。审美治理是对个体文化习性与生活情感的隐秘控制与塑造,以巩固特定的政治组织形式。尽管托尼·本尼特切断了美与某种超验价值的联系,指认审美自律作为权力治理的幻象,但他回答美学何以被权力渗透的条件机制不同于阿甘本,这是基于批判理论与文化马克思主义在审美介入现实问题上理解的差异。
文化马克思主义对美学介入的思考基于共有的文化惯习框架,意义产生于具体的文化交流与沟通行为,他们更多地关注不同时期的意义生产与权力表征的联系;而当代批判理论则认为权力治理的核心是感知的压缩与经验的板结,其审美介入的底层逻辑是感觉及其意义的运动机制,并不囿于回答何种文化系统的意义生产机制建构虚假的文化身份以及压制边缘群体的身份意识的问题。不同于托尼·本尼特对文化政策和博物馆的分析,阿甘本认为博物馆并非隐秘地输出特定的社会记忆、情感结构和生活惯习,而是“定义人们生活的精神之潜能”,“‘博物馆’并不是某个既定的物理空间或场所,而是一个分隔的维度,那些一度被感觉为真实的、坚定的东西现已被移到此处”[5]〔意〕阿甘本:《渎神》,王立秋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45页。,博物馆的治理功能在于将客体对象窄化为可展示、可鉴赏的艺术价值,以先在的感知方式架构、填充并凝固经验。阿甘本由此在托尼的基础之上,将后现代艺术、语言行为等一切日常感性实践指认为审美装置,其或是将生活的可能性消解为一种纯粹“否定的无”,或以均质的审美消费与语义系统将生活形式固化,它们实际都拔除了个体建构自我生命形式的可能,以既定的感知模式阻滞意义的流动。由此,审美治理并非是权力对文化文本的特定意义阐释模式,而是一切生活实践对感知方式的钝化。托尼·本尼特的文化治理并未穿透文化符号系统的表层,回应治理何以顺利发生的根本原因,即个体为何自发地被整合入既有的文化意义模式。文化、习性和情感倾向稳固的前提实际都以生命感知的僵化为前提,生命的意义基于个体即时即刻与生活空间的偶然遭遇和生成,一旦感觉方式钝化,则生命也就潜在地成为了一种可识别、可分割的文化主体。
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学者以文化的编码与解码理论,参与实际文化政策的制定。这种文化批判模式的前提在于某种程度承认既有话语结构的合法。托尼·本尼特分析了特定历史时期意指阐释与权力群体的关联,而阿甘本对生命治理的思考则深入生命权力的底层逻辑,从社会约定俗成的文化意指系统转向个体私密的感觉方式。当代批判理论不同于文化政治学批判,其审美介入展开的基座并非某种社会群体内部的文化表征系统,而是生命无差别的感觉方式。正如特蕾莎·艾伯特指出,文化的介入性呈现为“对词语和陈述的连贯意义的符号震荡”[1]Teresa L. Ebert, The Task of Cultural Critique,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9, p.x.。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政治学的核心在于将文化表征作为一个意义摇摆和身份置换的协商场域,它既是权力对边缘群体的文化身份的强制表征,也是底层大众在特定文化行为实践中对意义的再阐释;而当代批判理论并非对既有文化文本的分析,他们聚焦前反思、前认知的个人化的生活感受,使其对审美政治问题坐落于惯常的符号层面之下,从理论的根底处松动稳固的文化意义模式。从日常文化语境的个体沉降于生命基础层面的感觉,以感知的生成与变动激活均质化的经验现实。这使其理论脱离了惯常的文化环境,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性,在解放、治理和共同体等多个问题上拓展了审美介入现实的深度与广度。
结 语
当代批判理论基于社会形态的转换,聚焦权力对个体生命事实的渗透,以感觉政治建立了美学与政治的联系,感觉及其意义的发生机制成为分析政治问题的底层逻辑。审美政治问题从先验的审美乌托邦逐步下沉于日常生活的具体语境,审美与政治深度粘连,以审美治理、审美解放等多种形式凝聚了美学介入并改造现实的政治能量。当代批判理论的审美介入并非以修辞形式传递特定的意识形态内容,塑造个体的文化观念与生命价值,也不再囿于文化政治学视域符号意义的生产与表征,而下沉于生命个体感知方式的基底,指向社会政治的基本结构的变革,其审美政治问题呈现激进的理论锋芒。政治转向是当代美学的重要问题,当代批判理论以感觉方式的分配与经验意义的构造参与了政治问题的讨论,拓展了当代美学的审美介入品格。
当代美学的政治转向包含多种进路,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以文化的表意实践,思考文化的发展对大众和社会生活的影响;詹姆逊、大卫·哈维等美国晚期马克思主义从审美与社会生产方式的角度,讨论政治变革的美学维度。批判理论从感觉及其意义生成的角度,分析了权力的展布与个体感知方式的关联。朗西埃以“感觉的分配”指认审美与政治的一体化关系;奈格里聚焦当代“非物质生产”的情感交流性,在信息、符号与经验的生产活动中发掘政治解放的可能;朗西埃、巴迪欧、奈格里与阿甘本等共同推动了当代批判理论的审美政治转向,当代批判理论共同关注感觉的运动与经验的延展,他们的核心诉求在于以差异性的感知方式切入权力展布的核心,参与并改造具体的政治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