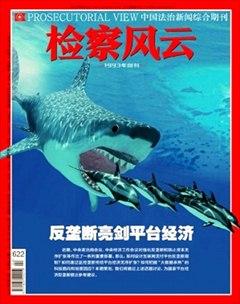叶与花
陈超群

左:铁冬青 中:菩提叶 右:豌豆花
铁冬青
是鸟儿指引我看到了鐵冬青那诱人的红果。
这是校园中僻静的一条路,两边长满了竹子和澳洲鸭脚木,配以低矮的龙船花。我经过时,树丛里窸窸窣窣的,枝叶被压得上下跳跃,我知道一定是鸟。南方进入秋冬季后,本土留鸟和北方来的候鸟在此聚会,到处都是鸟。我憋住气,悄悄走近,鸟儿们却得知了最微妙的信息,扑啦啦像风一样飞走了。松一口气,定睛一看,一颗颗闪着珊瑚般光泽的小红果挂在枝头,掩映在浓绿油亮的树叶中。原来这里还有一棵铁冬青树。铁冬青的果子红了。
在满目绿色中遇到这样精致的小红果是令人欣喜的,这是多么美丽的红果啊,我想起梭罗在《野果》中写的,野生的冬青果“红得像酒鬼的眼睛”“也许在所有的浆果中,这是最美的一个——细长的枝条上长满精致的叶子,冬青果就挤在这些叶子里,摇曳在枝头”。我相信梭罗的感觉,它们应该是最美的浆果,就像是鸟儿们飞走时,把灵性留在了枝头。
和爬山虎、海芋诱人的浆果一样,铁冬青的红果也是人类不食用或不可食用的,但它们是鸟类的美食。这犹如上天特意地安排。对自然的观察总会让我想到自然界中万事万物的相互联系,其精密巧妙令人敬畏。
在网上看到了一些铁冬青红果的摄影,大多果实累累,红果密密麻麻、层层叠叠缀满枝头,有的甚至是满树红果,几乎没有绿叶,映得四处红光一片,那是植物在秋冬的狂欢,是民间热闹喜庆的色调,但我觉得都不如我在校园中看到的那一枝惊艳——果实不多,却格外洒脱,也许是鸟儿的轻盈给我了这样的暗示。
也有让我心动的照片,比如白雪覆枝后的铁冬青红果。背景虚无,色彩极简,纯净的白雪,欲滴的红果,冷而艳,仿佛静谧天地中一声声的心跳,是极美的。广东没有下雪天,无缘看到这样的铁冬青红果。如此美景,留待念想吧。以后若是冬天往北走,我想我应该会留意到铁冬青。
虽然上天将美丽的红果分给了鸟类,却把铁冬青身上其他的妙处给了人类。铁冬青是植物中的“药王”,根和树皮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祛风利湿等功效,民间称之“救必应”。
菩提叶
在《此时众生》“秋时”第一篇里,蒋勋写道,“曾经去过印度菩提迦耶那棵大树下静坐,冥想一个修行者曾经听到过的树叶间细细的风声。或者,树叶静静掉落,触碰大地,一刹那心中兴起的震动”。蒋勋承认,喜欢菩提叶“或许与传说里佛的故事有关”。然而接着笔锋一转,“冥想尽管冥想,这片叶子其实可以与故事无关的”。
下面是他和一名植物学者脱离了宗教故事框架的对话。他赞美一片菩提叶,用诗句去歌咏,用色彩、线条和质感去展现;然而植物学者却有不同的解释——叶蒂纤细,却非常牢固,因为要支撑整片叶子的重量。他形容菩提叶“像一颗心形,尤其是拖长的叶尖,使人觉得是可以感受细致心事的人类心脏的瓣膜”;植物学者却仍然有更为“科学”的回答——许多植物的叶尖是用来排水的,“尤其在热带,突如其来的暴雨,大量积存在叶片上,叶片会受伤腐烂败坏;久而久之,植物的叶子演化出了迅速排出水分的功能,形状其实是功能长期演化的结果”。
惊艳的是最后的对话——“要多久才能演化成这样的形状?”“上亿年。”这让蒋勋陷入沉默,他写道:“美是不是生命艰难生存下来最后的记忆?美是不是一种辛酸的自我完成?”至此,蒋勋感悟到的,是文学艺术和自然科学在美学上的终极融合。这片叶子可以与故事无关,它本身就是美。
德国植物学家和水彩画家合著的《植物的象征》一书中提到,有些花卉可以“纯粹以其辉煌美丽而成为象征”,不需要故事。花卉如此,树叶又何尝不是如此。蒋勋细腻入骨的观察和体会,为我们欣赏菩提叶提供了一种“纯粹”的方式。这种方式是回归自然、回归初心的,即抛开那些故事框架,进行一场只是人和植物之间的感应。
我的校园有一棵菩提树,夏季,我采了两片菩提叶,把它们夹在书中,等待它们干燥后做成书签。每当翻书见着它们,总能让我的心多一份宁静。这份宁静不仅来自宗教的启示,更是对于美的领悟。
豌豆花
在野外邂逅豌豆花,是前些天我在一项“拯救食虫小草锦地罗”秘密行动中的意外收获。那日中午,我和小伙伴(也是植物爱好者)进入预先定位好的某建筑工地,我们像“摸金校尉”那样,按照地图的指示一路探寻,却误入一处农田,看见了两架豌豆正开着花,一架淡紫配酒红的花,一架纯白的花。
我欢喜地跳进田垄里,满足地沉浸在豌豆特有的清脆气息中,豌豆花在我身边轻轻摇曳。淡紫配酒红的豌豆花俏皮,纯白的豌豆花淡然,各有各的美。置身花丛中,我还发现,淡紫配酒红的这种豌豆花开过了之后,会变成纯净的天蓝,安静地退在一旁,也是极为好看。
我看看这朵,摸摸那朵,无比快乐,只觉四周出奇的安静,安静得我听到了风吹过时豌豆叶互相摩擦的沙沙声和我自己的心跳声。这大概就是传说中的“物我两忘”吧,真是妙不可言。这种美妙是可遇不可求的,在我看来,只有在自然中偶遇才能获得。
汪曾祺说过,美,多少要带有一点偶然。
是的,我爱看植物,却不是为了看植物而看植物,我想在自然中“遇见”它们。比如,在校园的落羽杉树下捡到一块散发着松香的油脂,即便它很小,里面也没有小昆虫,却比在古玩市场看到一大堆琥珀令我兴奋多了。又比如,爬山时转过一个山头,忽然看见对面山腰上一棵野生桃树开着满枝的花,虽然无法触及,却比在公园看到一排排整齐栽种的桃树开花,令我兴奋多了。在野外看见这两架豌豆花,当然也是最美妙的体验。
仔细看豌豆花的样貌,它的造型不是大多数花朵那样的对称形,而是半边型,恰好像一只舒展着翅膀驻留在草尖的蝴蝶。如果逆光看,花瓣上的条纹脉络清晰可见,像蝴蝶翅膀上精致纤巧的斑纹。内层小一些的花瓣则厚实地紧裹着深藏在中心的更小的花瓣,像极了蝴蝶灵活小巧的身体。
虽然卢梭在《植物学通信》中对豌豆花的造型给予了更加科学的描述,说它的“花瓣分为旗瓣、翼瓣和龙骨瓣”“旗瓣像一把大伞覆盖在其他部分之上;翼瓣长在旗瓣下面的两片侧翼上,生得结实;龙骨瓣护卫着花朵的中心部位,庇护着豌豆花的幼嫩果实”,我还是更愿意用非术语来形容豌豆花,就说它像蝴蝶,从头到尾都像。
豌豆花的确总是被比喻成蝴蝶。我想起了经典的儿童绘本诗集《蝴蝶·豌豆花》,其中就有一首这样的诗:“一只蝴蝶从竹篱外飞进来/豌豆花问蝴蝶/你是一朵飞起来的花吗?”图画也配得很有童趣——热闹的豌豆花藤和欢快的蝴蝶,两者神形皆似,蝴蝶低着头,豌豆花仰着“头”,仿佛真的在对话。
关于豌豆花像蝴蝶,我还看过一句绝妙的话,说豌豆花的旗瓣像蝴蝶张开翅膀一样高高耸起,这样不是招蜂引蝶,而是占山为王,仿佛向真正的蜂蝶宣告了这朵花的主权。这个说法有点意思。事实上,豌豆花是闭花授粉的,不像那些需要借助风或者小动物传粉的花朵,豌豆花在花苞没有张开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了授粉。张开的旗瓣,可不就像是宣告主权了嘛。蜂蝶光顾开花以后的豌豆花,说白了做的都是无用功啊。
说到这里,可能很多人会想起高中生物课遗传学知识中的孟德尔豌豆实验。孟德尔选用豌豆做遗传学实验,是因为豌豆既自花传粉,又闭花授粉,在自然条件下,一般是纯种,相对性状易于区分且能稳定地遗传。
蝴蝶与豌豆花的故事是很适合讲给孩子听的,孟德尔的豌豆实验也能激发好奇心,那将是极好的诗意教育和科学教育,但不是睡前躺在床上讲。我想,最好是在野外,在和孩子一起偶然发现满架豌豆花的时候。
在邂逅豌豆花之后,我们在博物圈朋友的帮助下找到了锦地罗,在不远处挖掘机隆隆的噪声中,我们小心挖掘了一些带回到深圳大学城校园。现在,我们带回的锦地罗逃离了被挖掘机铲掉的命运,每天都能在深圳大学城呼吸着塘朗山下西丽湖畔新鲜的空气,晒着太阳,也像当日我看到的豌豆花那样悠然自得了吧。
编辑:沈海晨 haichenwowo@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