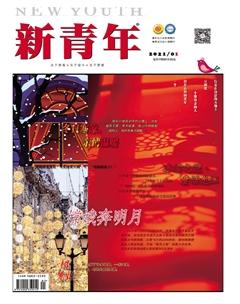郝婆的葱包桧
孙丹
一口乌黑扁平锅,一张春卷皮子裹着半根油条,煎、压,翻面,烤得表皮金黄,香气扑鼻。
郝婆用锅铲“当当当”敲着锅沿,用杭州话脆生生喊:“来,葱包烩好哩,葱包烩吃哩!”
食客们围过来:“郝婆,烤焦点!”“油条新不新鲜?”“甜酱哩?辣酱太辣了。”
郝婆笑著,递过去一个个葱包烩。
说起杭州风味小吃葱包烩,有个历史典故。抗金名将岳飞以“莫须有”罪名被害后,杭州百姓十分痛恨秦桧夫妇。一家卖油炸食品的店主王二,捏了两个人形面块比作秦桧夫妇,将他们揿到一块,用棒一压,投入油锅里炸,嘴里还念道:“油炸烩吃。”这就是油条的来历。王二有时油条炸多了,卖不出去,而冷了以后又软又韧,味道不佳。王二把烤熟的油炸烩同葱段卷入拌着甜面酱的春饼里,再用铁板压烤,烤到表皮呈金黄色,油炸烩“吱吱”作响。烤完后王二一吃,觉得葱香可口,取名叫“葱包烩”,一直流传至今。
郝婆做葱包烩30多年了,春卷皮子自己烙的,油条自己炸的,连招牌酱料也是自己做的。郝婆把红尖椒拔去蒂头,晒干搅碎,把碎辣椒渣子灌到瓶子里,拌上盐,浇上一层油封好。做酱时,就倒出一点点放到锅里煮,加上水、糖和味精,等辣椒糊不稀不浓的时候就做成了辣酱。做甜酱关键在香料,郝婆把茴香、桂皮、香叶、香果等煮成香料汤,和着面糊就一起煮,等煮成稀糊时,特制的甜酱就出锅了。郝婆的辣酱辣到好处,不伤胃,甜酱也甜而不腻,吸引着大批忠实食客。
别看郝婆年近七旬,可手劲儿好着呢。一个铁板上下左右地压,鼓着的油条烩儿就泄了气,包着的春卷皮儿裹紧了卷个边儿,截成长段儿的青葱一夹进去就“嘶哩嘶哩”地冒着香味儿。
食客们递过钱,烫着手,接过葱包烩,涂抹酱,是吃葱包烩最大的乐趣,每人有自己独特的涂法。食客们把葱包烩折得两头贴牢,一点点地把溢出来的酱舔掉,大口地咬下去。蜜甜的酱里滑过几分辣,香喷喷,甜丝丝。喜欢辣的,抹满辣酱,吃得直冒汗,不住赞:“够味,够味。”
葱包烩制作虽简单,但郝婆选材好,用心做,丝毫不马虎。生意好的时候,一天可以卖300多个。
郝婆命苦,丈夫生病早早过世,自己又下了岗,在街口摆了摊,靠着卖葱包烩,硬是把独养儿子拉扯大。儿子小时候一放学就坐在妈妈摊前的小桌上写作业,天黑才独自回家,葱包烩常常就是娘俩儿的晚饭。
郝婆很欣慰,儿子大学毕业后进入省城某机关工作,又成了家。虽然这几年儿子很少回家,但总打电话来让郝婆上省城享享福。听说儿子混得不错,掌握了一定实权,郝婆不想沾儿子的光,继续在街口卖她的葱包烩。
国庆节一大早,儿子一家开车来到郝婆摊前,郝婆正在忙。
儿子让郝婆歇一会儿:“妈,如今儿子经济宽裕多了,养得起您老。”
“妈知道你孝顺,”郝婆边说边招呼顾客,“妈现在还做得动。”
郝婆拿起一个葱包烩,涂上酱,递给儿子,“辣,太辣。”儿子咬了一口,“您知道我吃不了辣的啊。”
郝婆笑了,“我就是要让你尝尝这辣的滋味,不好受吧?”
“你的钱若是来路不正,就像秦桧一样,被人唾弃一辈子。”郝婆下面团炸油条,正色对儿子说,“你看这油条,油少煎呢,不会熟。煎过头,就变成老油条,硬邦邦,咬不动,成废料喽。”
知子莫若母,从儿子眼神里,郝婆明白儿子定是遇到棘手的事不好选择。儿子不说,郝婆也不讲明。
儿子把剩下的葱包烩吃了下去,两眼辣出泪水,盯着母亲炸的油条,若有所悟,说了句:“那我回去了。”便开车走了。
“来,来,好吃的葱包烩哩,来吃哦!”郝婆依然把扁平锅敲得“当当”响,回荡在周边,久久不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