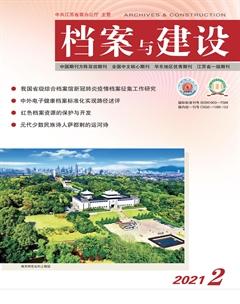参与式档案管理中社会力量参与权力的来源与实现研究
杜璇宇
摘 要:参与式档案管理逐渐受到档案界的关注。虚拟空间、关系网络和数字技术成为社会力量参与档案管理的权力来源,但社会力量参与权力的实现受权力主体权利意识淡薄、权利保障缺乏、权利行使途径有限等的限制。档案专业权力主体应与社会公众权力主体协同努力,开展主体培育,完善制度保障,丰富参与途径。
关键词:参与;档案管理;权力来源;权力实现分类号:G270
Research on the Source and Realization of Participating Power of Social Forces in Participatory Archives Management
Du Xuanyu
(Department of Library, Information and Archives of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Abstract: Participatory archives management has gradually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the archives community. Virtual space, relationship network and digital technology have become the source of power for social forces to participate in archives management, but the realization of social forces participation in power has been restricted by the weak awareness of power subjects rights, lack of rights protection, and limited ways to exercise rights. Therefore, the subject of power of archival specialty should make concerted efforts with the subject of public power, develop the subject, improve the system guarantee, enrich the participation channels.
Keywords: Participation; Archive Management; Power Source; Power Realization
信息技術革命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新的组织与管理模式应运而生,档案机构也在不断适应并进行管理与服务方面的转型。其中,参与式文化受到档案工作者的关注,档案学语境下的“参与”研究逐渐增多。档案是权力建构的产物[1],在参与式档案管理中,社会力量的参与权力由何而来,又如何运行从而实现多方权力主体的共赢,应当受到学界的合理审视。
1参与式档案管理研究现状
“参与”这一概念在中国档案学研究语境中呈现出多样性及复杂性的特点。有学者从“参与媒介”这一角度出发,探索如何利用社交网络扩大档案信息服务社会化的范围,增强用户与档案专业主体的交流与互动。[2-4]也有学者将“参与”视为社会公众与档案专业主体共同处理某类档案事务的方式或途径。如徐海静将目前城市记忆“参与式档案管理”实践活动分为档案部门主导型实践、学会组织主导型实践、公众主导型实践、机构协助型实践四个类型。[5]又如加小双等对数字档案资源建设中的各类参与式实践进行分析,认为有参与式数字档案资源建设和参与式社区建档两大类。[6]在这类解读中,“参与”体现为档案实践活动的一种特征。还有部分学者将“参与”解释为一种有别于传统档案工作的新兴模式,认为“参与”不再是档案专业主体解决某一问题的方法,而是成为一种中心理念融入档案信息服务系统运作。在这种观点下的档案参与研究多是结合时代产生的新事物进行讨论,如社交媒体或者Web2.0等。[7-9]
不论从哪一种角度解读“参与”概念,学者们基本都立足于数字化的时代背景。我们可以这样总结,数字技术的发展为社会力量参与档案管理提供了渠道和工具,并且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基于此的模式化的参与式档案管理也正逐步向我们走来。实际上,“参与”也代表着一种新的权力关系,在参与式档案管理中,社会公众不再只是被动的服务接受者,而被赋予一定的权力,可与档案专业工作者共同处理档案事务。总体而言,社会公众的参与权力从何而来,又如何得以实现,学界暂未给出答案。
2参与式档案管理中社会力量参与权力的来源
权力从来都不是凭空产生的。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权力的来源有着与时代相融合的驱动力。如君主专制时期“君权神授”的权力来源观,法国大革命时期权力来源的契约学说,后现代时期米歇尔·福柯认为权力通过话语和规训来表现和渗透,迈克尔·曼认为权力来源于意识形态、经济、政治和军事的互动网络[10]。数字时代,网络空间被开拓,关系网络进一步交织,数字技术提供了丰富的对话渠道,社会力量参与档案管理的权力来源日渐清晰。
2.1空间赋权:网络空间提供权力博弈新场域
福柯指出:“空间在任何形式的公共生活中都极为重要;空间在任何的权力运作中也非常重要”。[11]数字时代创造出了相对于现实空间的网络空间,在网络空间内,原本地理意义上的空间限制被打破,甚至由时区分布带来的时间限制也逐渐消失,人们的交往空间得到拓展与延伸。同时,个人表达权利意识苏醒,使“人人都有麦克风”。网络空间的产生带来话语权的分散,对中央集权式的信息传播模式造成冲击。言论多样性和思想多元化进一步发展,原先档案专业主体独有的叙事权力与记忆建造权力被分散。独立性主体自我身份认同的意识逐渐觉醒,在档案权力场中,个人权力不再由国家权力分配,这表现出权力主体间的竞逐与权力关系的改造。换言之,网络空间为档案权力主体的竞争与权力关系的重塑提供了新的场域。
不仅如此,网络空间的开放性与包容性还带来身份的隐匿以及行为的随意,人们的责任、义务等意识容易淡化,这随之加大了人在网络空间内行为的随意性与破坏性。如果说以前政府治理的问题是“空间的”,对象是地理意义上的国土和属民,那么当今治理的问题就是“社会的”,对象不再限定于地理空间,而是包括了网络空间内的社会现象。数字时代,很多新的“空间—社会”问题诞生,例如个人信息的泄露与窃取、虚假信息的传播等。为了更好地解决网络空间内的伦理问题,原先“自上而下”的国家主体权力进行自我调适,分权于社会公众,期望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在档案领域内这表现为档案利用者与档案专业工作者就档案事务进行平等协作,二者权力在档案领域开展竞逐与博弈。
2.2关系赋权:关系网络加强个体权力凝结
数字时代不仅创造出新的虚拟空间,也对关系网络造成改变。福柯认为权力是一种关系,是“众多的力的关系,这些关系存在于它们发生作用的那个领域……在任意两点的关系中都会产生权力”。[12]数字时代,关系网络的去中心化特征愈发明显,人与人的交往可以通过统一的互联网直接进行,每个人都可以是网络中独立的一个节点,以开放式、平等性、扁平化等为特点的关系网络逐渐生成。在关系网络中,传统权威力量、官方机构和垄断渠道失去了原有的中心地位与控制力,社会基本单位由组织降解为个体[13]。去中心化的关系网络使话语表达的聚光灯不再聚焦于传统权威与官方机构,而是分散给每个个人主体,普通社会个体的力量能够通过自身的行为活动影响整个社会关系的建构进程。不仅如此,个体力量还可以通过网络凝聚成群体的力量,扩大其影响。以微博为例,每一次转发、评论或点赞都造成了关系的连接与共同观念的表达;而当连接不断增多,一个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关系网络就此织成,将个体的声音汇聚一齐,强化话语权与行动权的表达与实现。关注到这种关系网络的赋权后,参与式档案管理模式由此被提出,认为不能绝对化拘泥于传统管理方法,而应广泛吸收个体与群体的智慧与力量,使社会公众参与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工作,协助档案管理,并不断扩大档案信息服务的范围。因而档案界越来越呼吁培育社会力量,以实现从档案管理走向协同治理的转变。
2.3技术赋权:数字技术提供工具性支持
如果将虚拟空间与关系网络比作参与式档案管理中社会参与权力的蓄水池,那么数字技术就更像一个连接水道,将充满活力与智慧的社会力量灌入档案管理的池塘,为档案管理工作的提质增效与升级转型提供动力。数字技术为社会力量参与权力的运行提供手段,以实现社会公众的技术赋权。数字技术发展背后隐含的是资源获取、信息传播的问题。在传统档案管理模式下,社会公众对于档案信息的获取基本上只能依靠国家权力主体即官方档案机构的决策,由官方机构决定档案信息服务的信息内容与服务方式;借由数字技术发展而被提出的参与式档案管理,使公众获取档案信息资源的途径增多,甚至自身就能参与进档案信息资源的建设当中,随之反馈渠道和反馈机制也进一步得到拓展与完善。因此,可以说技术为社会公众参与档案管理事务提供了工具性支持,增强了社会力量对于档案管理的影响力。
技术作为工具手段为社会力量参与档案管理提供了多种途径与方式,而途径和手段的增多会带来主动性的增强,技术的赋权体现为一种行动过程。社会化媒体的发展使得自主性主体的多元身份认同得以实现,身份认同与自我价值的肯定带来参与积极性的提高。社会公众在档案领域内不再扮演沉默的大多数,原本的档案信息服务接受者转变为积极的信息传播者与社会记忆构建者,主体能动性被不断挖掘与激发,档案专业主体与社会独立主体互相学习、对话与交往,各自的知识、经验与技能共同在档案管理活动中发挥作用。
3参与式档案管理中社会力量参与权力的实现困境
认识到权力的来源并不意味着权力实现的顺畅无阻。权力的实现在权利价值与功能的指导和规制下完成,权利的不断实现与满足推动和促成了权力的实行。对社会力量参与档案管理活动而言,社会权力主体的参与权利意识淡薄、权利保障缺乏以及权利途径有限,致使参与权力运行面临着一定困境,我国社会参与式档案管理未能达到理想状态。
3.1社会权力主体参与权利意识淡薄
权利是一种价值判断,被认为是正当的权力。“正当的权力”通过某种价值观念以及相应的社会规范将自身的正当性反映出来,从而将一般的权力关系转化为一种既具有强制性,又具有正当性的权利关系[14]。从这一角度而言,只有当社会公众意识到自身所具有的參与权利时,才能将意识转化为行动,并行使权力。参与式档案管理是档案专业主体将部分管理档案及档案信息工作的权力让渡给个人、机构、学术组织、非官方档案机构等社会公众力量,使他们秉承自愿的意志并通过志愿的方式参与档案事务管理。因此,社会公众的档案责任意识与参与权利意识对于参与式档案管理而言十分重要。但长期以来,我国档案管理具有一定封闭性,档案利用者仅是作为信息接收方看待档案管理工作。近年来虽然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与档案信息服务水平不断提高,档案用户提供反馈信息的渠道增多,但本质并没有改变双方在档案管理模式中被固化的身份,档案利用者与档案工作者仍是一种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如此,我国社会公众对档案管理的参与权利意识不强,没有意识到个人力量对整个档案工作及社会记忆构建的影响。
意识决定行为,薄弱的公众参与权利意识,一方面导致个体参与行为的消极,另一方面分散、微弱的个体力量难以聚合产生影响相当的社会效应。档案专业主体对档案管理的话语权看似被数字技术分散给普罗大众,但“沉默的大多数”使得个体声音表达有限。最终,档案信息资源开发、提供利用的话语权仍牢牢掌握于档案专业主体手中。
3.2社会权力主体参与权利缺乏保障
制度约束权力,在使权力不至于无限膨胀而损害其他权力主体的利益同时,为权力的实行提供保障,维护权利正常被行使不受侵犯。参与式档案管理同样需要制度的规范,保障社会权力主体权利的正常表达以及权力的规范化使用。制度根据其存在形式可被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前者包含的内容主要为法律、法规、政策、行政管理措施等成文性规定,后者主要为道德文化、价值理念层面的行为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