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源何处寻
荣智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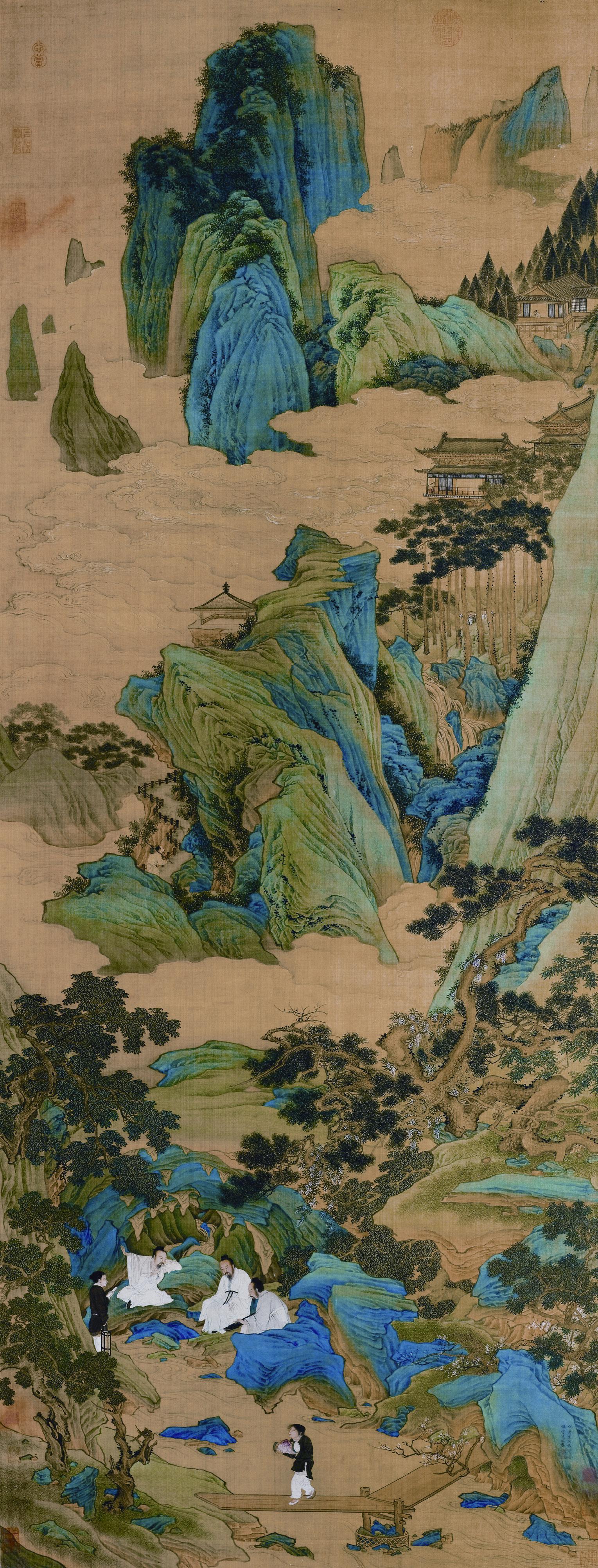
历史往往令人不安。而在历史中有一种沒有历史性的东西—桃花源,构成了一个超越不安的意义网:不受权力的控制,也不受制度的挤压,长期承载着可信的经验、恒定的价值和冷静的期待。
自陶渊明开启“桃花源”意象,王维、韩愈、王安石的“同人文”,也在不同的历史语境里重构了“桃花源”的内涵。传统知识分子的视角从“渔人”和“桃园中人”之间来回转换,暗示了往返乌托邦的可能性。元清两代诗人的桃源作品,当代话剧《暗恋桃花源》的经久不衰,则反映了人们“失去”历史、“不复得路”的追寻和迷茫。
儒家乐土
“桃花源”是陶渊明在《桃花源记并诗》中描述的一个“异世界”,它和外界隔绝,宁静古朴,如海上仙山一样不可复现。作为极具神秘性的文学主题,“桃花源”在后代反复出现,并由于时代和作者的差异,呈现出不同的想象图景。
汉末到魏晋,世道离乱,能带来心灵慰藉的山水诗大盛,“乐土”也出现了。
刘敬叔的《异苑》里有个故事,写道“元嘉初,武陵蛮人射鹿,逐入石穴,才容人。蛮人入穴,见其旁有梯,因上梯。豁然开朗,桑果蔚然,行人翱翔,亦不以怪。此蛮于路砍树为记,其后茫然,无复仿佛。”几乎是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并诗》的另一版本。
《桃花源记》结尾说南阳刘子骥云云,《太平御览》卷五百四引用《晋中兴书》:“刘驎之,字子骥,一字道民。好游于山泽,志在存道,常采药于名山,深入忘返。见有一涧水,南有二十囷,一囷开,一囷闭。或说囷中皆仙方秘药,驎之欲更寻索,终不能知。”余嘉锡在《世说新语笺疏》里说,“此叙驎之所见,颇类桃花源,盖即一事而传闻异辞。陶渊明集五桃花源记,正太元中事……”
也就是说,陶渊明的“桃花源”故事,很可能根据晋、宋之间流传于荆、湘一带的某种南方传说改编而来,用以寄寓自己的社会理想。
然而,陶渊明的理想,究竟归于儒家,还是归于道家,历来众说纷纭。陆九渊说,“李白、杜甫、陶渊明皆有志于吾道。”真德秀说,“渊明之学,正自经术中来。”沈德潜称陶渊明为“圣门弟子”。朱熹却说“渊明所说者庄老”。
这场纷争不能小看,因为这一结论决定了陶渊明“桃花源”理想的立足点。如果是儒家的,那么桃花源意味着一个“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的大同世界。如果是道家的,桃花源就更多代表着“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业”的“小国寡民”模式。
要看透陶渊明的理想社会,不能只看《桃花源记并诗》,《陶渊明集》里有更多的线索。像“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与老子“虚其心实其腹”大不相同。《桃花源记》“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与老子的“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亦迥异。
特别是“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一语,可以说是对理想社会的提纲挈领式总结。这样的社会,一是充满了儒家仁民爱物的精神内核,一是带有极强烈的悲悯色彩。也就是渔人待在桃花源这一昼夜里,悲天悯人的怀抱才能得以安慰。
渔人待在桃花源,本属于“避世”,怎么就能做儒者?其实儒家也讲避世,孔子说“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这四个“避”(辟通避),实际上就是儒者精神“逃避”的指示牌。陶渊明对晋宋易朝,始终耿耿于怀,而体制内部的精神压迫,也异常令人痛苦。对于知识分子而言,以暴力反抗暴力并不现实,以带着希望的“避世”反抗暴力,才是一条心灵的出路。
唐宋“同人”
陶渊明的“桃花源”很快成为经久不衰的题材。唐宋诗人尤其做了不少“同人文”,和“桃源”相关的诗歌,不下百首,其中最具讨论价值的,是王维、韩愈和王安石的作品。
清代的王士禛评论:“唐宋以来,作《桃源行》最佳者,王摩诘、韩退之、王介甫三篇。”
王维写《桃源行》时只有十九岁,但全诗风度雍容,气象自在。王维的“桃花源”有两个特点,一是把陶渊明的隐藏的“渔父”视角,转换为“桃源中人”视角,如“初因避地去人间,及至成仙遂不还。峡里谁知有人事,世中遥望空云山”;一是把儒者避世、退而独善其身的做法,转换成对仙境的追寻。这两点也可以结合在一起,桃源中人的成仙隐含着王维的自我期许。
诗人的精神超越之旅,始终围绕着远游—追寻—回归(或迷失)的秩序展开。
把桃花源“改造”成仙境,道教做得比较早,一方面也有其受到唐代皇帝遵奉的缘故。较早的记载有刘禹锡的《游桃源一百韵》,表明唐代朝廷已经将桃源视作神仙洞府,列入祀典,诗中说“皇家感至道,圣祚自天锡”,而且此处还有“白日飞升”的事迹,“如今三山上,名字在真籍”。
唐末康骈的《剧谈录》记载:“渊明所记桃花源,今鼎州桃花观即是其处,自晋宋来,由此上升者六人。”宋张君房《云笈》引用司马紫薇的《天地宫府图》说桃花源是“白马玄光天”,由一位谢真人主管。这些都可以看作是尚未成为“隐士”的王维创作背后的长期社会背景。
中唐时代的韩愈,一上来就在《桃源图》中说,“神仙有无何渺茫,桃源之说诚荒唐”,以“世俗宁知伪与真,至今传者武陵人”作结。发起古文运动的韩愈,致力于抨击佛教和道教,因此他既反对桃花源的“仙境说”,也反感小国寡民的解读。
韩愈从陶渊明那里独取了一句“先世避秦乱来此”,铺陈了“大蛇中断丧前王,群马南渡开新主。听终辞绝共悽然,自说经今六百年”从秦亡、汉兴又到晋立的历史遗迹。而且,现实主义的桃花源,有着“月明伴宿玉堂空,骨冷魂清无梦寐。夜半金鸡啁哳鸣,火轮飞出客心惊”的奇崛景色,和韩愈一贯喜欢描摹的厉怖世界相关。“人间有累”的现世,对比渔舟之子的“离别”,这个桃花源不免带着乐土崩坏的无尽失落。
到了北宋王安石笔下,桃花源又“回归”了陶渊明意义上的儒家政治乌托邦的寓意。主持了轰轰烈烈变法的王安石,在诗歌里强调了桃花源的两个特点,一是无苛政—“儿孙生长与世隔,虽有父子无君臣”;一是无战乱—“重华一去宁复得,天下纷纷经几秦”。
“重华”指的是虞舜,《书·舜典》“曰若稽古帝舜,曰重华,协于帝”,常常被儒家用来当作累世升平的治世的代名词。而“秦”正是舜的反面,王安石慨叹秦虽速亡,继秦而起者,无非暴政。圣人之治,一去而不可复得。“天下纷纷经几秦”,和谭嗣同所言“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判断相近。一治一乱,寄托的是王安石的抱负,这也是后人误会他为法家时需要注意的一个地方。
从诗人的视角来看,陶渊明是渔父视角,王维是桃源中人视角,韩愈和王安石更像是抽离出来的评论者。从桃花源的内涵来看,其坐标在政治乌托邦、仙境和现实之间不断滑动。如果将这两个角度放在一起,不妨说,诗人的精神超越之旅,始终围绕着远游—追寻—回归(或迷失)的秩序展开。

“不复得路”
元代和清代的诗人,处在多元种族和多元文化复合的体系中,不免怀有一种“国仇家恨”和“文化失根”之感。
和唐宋时期的个人化阐释不同,元代的桃花源成为诗人群体性的精神寄托—可以令人忘记“亡国”的理想邦国,仿佛历史分裂出了一个平行世界。像方回的《桃源行序》就把桃花源比喻成亡国者的归隐之地,在陶渊明原作“避得虎狼秦”的基础上,增加了更为明显的对抗现实政治的属性。
元代的桃花源文本,還有一个特殊之处,其往往暗示了一个隐秘的情欲王国。像散曲《仙吕·寄生草·春》里,彩绳、罗裙、垂柳和武陵溪、桃花纷落如雨组成了对照性的审美关系。《南吕·一枝花·孤闷》,则把“桃源洞山谷崎岖”“阳台路云雨模糊”的景象相结合,又和“东墙女空窥宋玉,西厢月却就崔姝”形成互文。
桃源路、渔舟、武陵溪等经典意象,在元代都带上了旖旎的指涉意味。这一方面显示了元代文人世俗愿望的落空,一方面也隐喻着异化家国里无可排遣的认同的丧失。
清代,特别是晚清,乌托邦小说大量出现。传统的桃花源和西方式的生活世界,经由杂糅和编译,奇异地组合在一起。虽然桃花源的意象不再明显,但一种考察现实制度、批判政治时局、介入民主科学的蓝图建制,成为这一时代独具特色的乌托邦方案。
每一个时代的桃花源话语的建构和接受,都可以视为是当时的新的文化想象。
吴趼人的《新石头记》,旅生的《痴人说梦记》,杞忧子的《苦学生》,都从百科全书式的框架里搭建出一个“新学”境界。如果从中国三次制度革命—商周之变、周秦之变、现代中国之变的角度去看,这些寓桃花源理想在内的乌托邦小说,实际上正试图处理“现代中国之变”的文明碰撞问题。
而赖声川于1986年执导的话剧《暗恋桃花源》,毋宁说有意处理“现代中国之变”的后果。这个象征着一九四九年两岸分治、台湾解严后追求身份认同的故事,通过《暗恋》和《桃花源》两个文本“剧中剧”式地同台演出,展现了一个荒谬、错乱、断裂的历史空间。
剧中,“暗恋”和“桃花源”是两个不相干的剧组,他们都与剧场签订了当晚彩排的合约,双方争执不下,谁也不肯相让。由于演出在即,他们只好同时在剧场中彩排。
古典和现代、大陆和台湾、记忆和遗忘、死亡和再生等元素,都以某种混乱的方式拼贴在一起。曾经的远游—追寻—回归(或迷失)的心灵秩序,以新的历史面目再度出现。赖声川曾说,《暗恋桃花源》的成功,在于它满足了台湾人民潜意识的某种愿望:台湾实在太乱了,这出戏便是在混乱与干扰当中,钻出一个秩序来。
每一个时代的桃花源话语的建构和接受,都可以视为是当时的新的文化想象,它不仅承载着集体的共同意识和共同符码,也象征着某种文化共同体对乐土或乌托邦的强烈诉求。除了对无阶级、无战争、无苛政的治世的期待,中国文人也创造出了一个富有文化意味的记忆空间,桃花源既是历史的,也是非历史的,它随时向人们开放,被填充进新的情感、经验和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