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盯中国,美国会迷失自我
雷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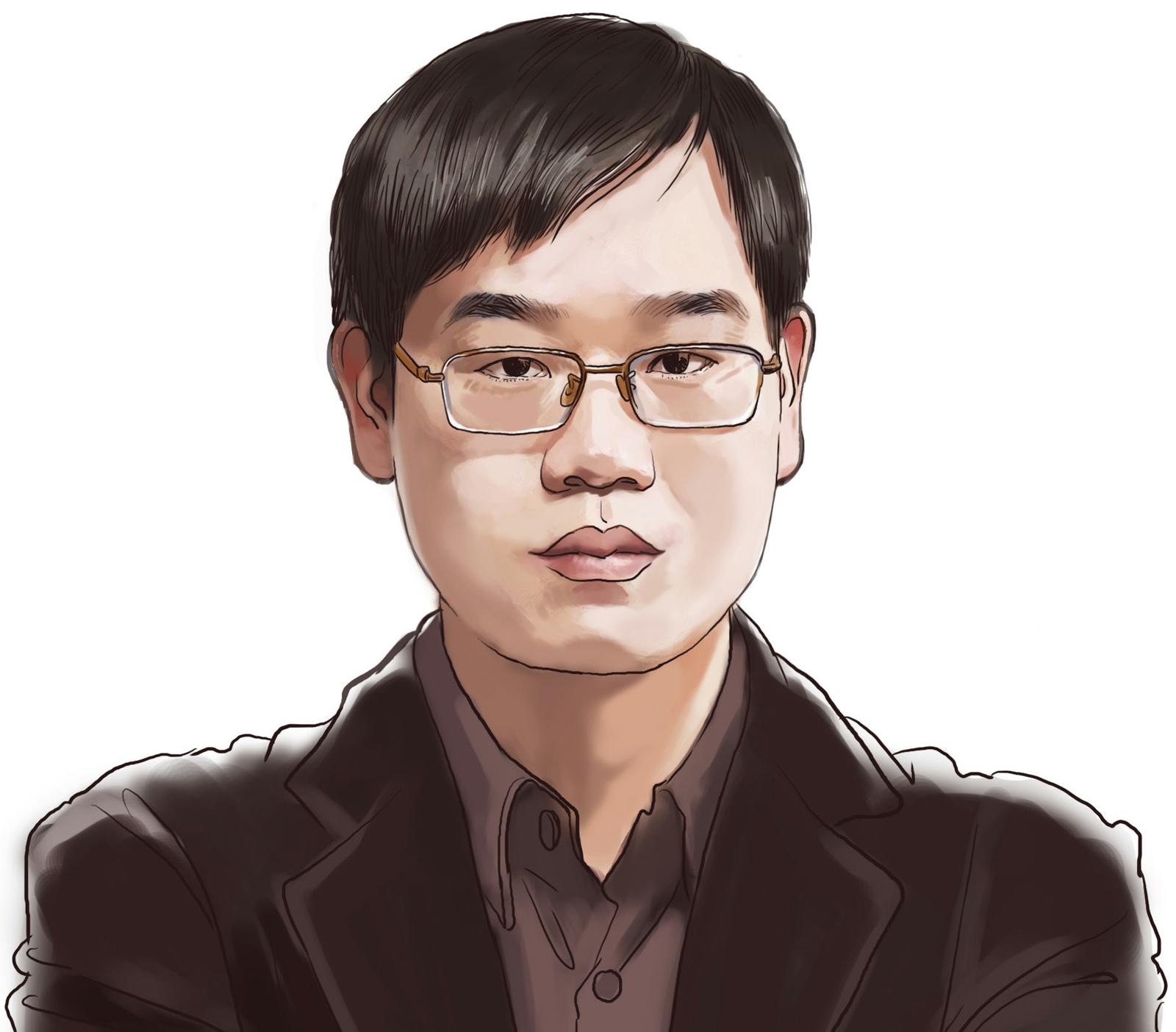
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已轮廓出现。总的目标是重新领导世界,重点关注对象是中国。
3月3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了上任以来首次外交讲话。他在阐述拜登政府外交政策时,列出了八大优先事项,分别是结束新冠疫情、振兴国内外经济、恢复民主、移民改革、重建联盟、应对气候变化、确保美国在技术上的领先地位,以及应对中国的挑战。
美国新任国务卿阐述新一届政府的外交重点任务,乍一看没什么特別之处。但是,回顾冷战后美国外交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这是美国政府首次在外交中把单一的国家—中国,单列为“外交优先”。
3月1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了《2021年贸易议程报告及2020年年度报告》。这份308页的报告,提到中国多达467次,频次史无前例。这样的年度报告,带有总结过去、规划未来的意味。有美国媒体注意到,中国是唯一被特别列为“拜登政府将应对”的国家。
拜登的外交将紧盯中国。目前来看,他的政府不仅这样说,还打算这样做。
这不是外交智慧,能否如其所愿还很难说。拜登外交为何会紧盯中国?
此前的文章中,我多次提到,拜登的对华外交带有极强的焦虑感。这一届总统任期干完,拜登已年逾八旬。作为浸润美国政坛半个世纪的老政客,这是他“青史留名”的最后机会。在拜登的逻辑中,美国能否重新领导世界,中国因素是最大的变数。
拜登有焦虑感。他的外交政策团队,也有焦虑感。布林肯2019年谈到中美战略竞争时曾说,“目前中国已经比我们处于更优势的地位。”事实上,在整个美国战略界,都有“美国一直在输给中国”的情绪。
某种程度上说,在对华政策上,拜登圈内的美国政治精英们有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
美国在世人眼中不再那么“美”,所有这些都不是中国的“错”。与中国“极端竞争”,还可能导致美国的自我扭曲。
但是,基于焦虑制定的政策,很容易滑向非理性。这是常识。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情绪化、非理性正是特朗普对华外交的突出特征。拜登在谈到中美关系时,用了“极端竞争”(extreme competition)这样的表述。拜登如何用这种带有满满情绪的表述,来区别他与特朗普的政策不同?
特朗普政府曾极力营造中美新冷战氛围。拜登明确否认过中美将陷入新冷战,强调与中国的关系也有合作的一面。但他“极端竞争”的对华外交,如何能产生竞争与合作的连接点?
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如果拜登真的希望与北京展开合作,与特朗普的做法有所不同,那么拜登的首要任务就不是‘极端竞争,因为这听起来像是特朗普时代的升级再次升温。”
拜登的就职演说,主要谈的是如何“治愈美国”。这说明,他与他的政策团队非常清楚,美国的最大挑战,以及所有挑战的根源,在美国国内。
美国政治的部落主义、极端化趋势,美国民主的式微,美国经济优势的减弱,美国社会的撕裂和不宽容,美国在世人眼中不再那么“美”,所有这些都不是中国的“错”。与中国“极端竞争”,不仅无助于解决这些问题,还可能导致美国的自我扭曲。
某种程度上说,拜登政府对华外交的焦虑感,是其国内焦虑感的向外投射。我们不能完全寄望于美国政治精英们找到情绪的平衡点、回归理性,但我们也应该清楚,对于中美关系,目前的中国比两国建交以来任何时候,都更有影响和塑造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