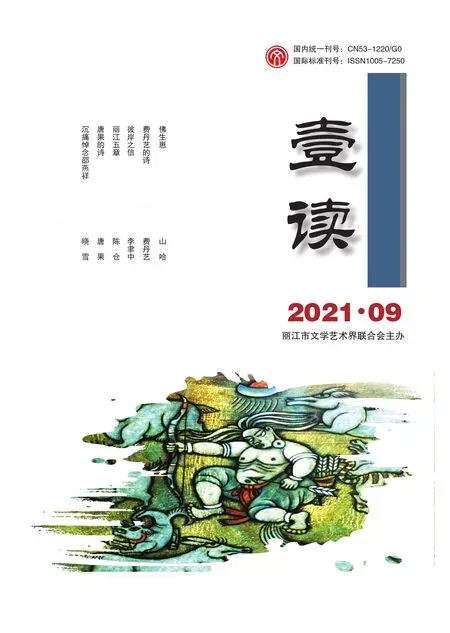历史与现在
◆何建安
迁徙的民族
古越人来到河谷的时候,是一个风和日丽的秋天。红河水经历了漫长的雨季,涨潮、暴怒、失控、沉浮,渐渐回归到回落与平静,它由夏天铺天盖地的水域,沉落到秋冬里汪在河滩里的一条线,历经了哀牢山起伏跌宕的时光。但这并不影响河水的力量,毕竟,这是一条纵横千里的国际性河流。当南迁的人一眼看到这条河的时候,一条扯不断的命运之绳牵引住了他们极度疲惫的双脚。古越人停下仅存一点的蹒跚的力量,身躯像破落而下的枯叶,紧紧贴在河风吹硬了的冰冷的岩石上,他们矗立在砾石破碎的山丘,一条越远越细的大河,明晃晃金波荡漾。
这是一个山脉相夹的坝子,山坡上长满了栗树、松树、大大小小交织如荫的灌木,宽阔的坝子也被绿阴匝地的植被覆盖,热带特有的榕树、木棉、酸枝树、凤凰树、清香木就像施肥了的庄稼绿满坝心,和风吹拂,鸟鸣云淡,水色苍穹,波光乍现,不知是落魄还是激动,面对群山中的美景,很多人都流下了眼泪。
这大约是距今两千二百年左右的事。
公元前后,云南北部陷入旷日持久的战乱,汉朝与滇国,汉朝与哀牢国几乎同时发生了战争,这时的大汉帝国吹响了统一南方的号角,当滚滚而来的战马一轮又一轮地冲击后,位于滇池湖畔的滇国和位于永昌郡(今保山市)的哀牢国(史书里也叫乘象国)就像撕裂的蛛网分崩离析,君臣纷纷倒戈,死的死,降的降,而大批被冲散了的臣民,落魄到楚雄、大理一带,沿江南下。
从滇池湖畔的滇国或哀牢国盘踞的昌宁至楚雄、大理,再来到今日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境内的红河谷,并一直沿江往南走,要经历千万里的跋涉,路途迢迢,得把家园抛弃,把器具抛弃,把千丝万缕抛弃。如果没有活的信念,重重阻隔的山川,就是古越人消失的墓衣。那是什么让一部分南逃的人在今天的戛洒江一带河谷住下来?相传是河谷里自生自灭的野芭蕉。一些南逃的队伍,他们在长途跋涉中渐渐掉队了,来到戛洒江河谷时前方的队伍已不知去向,惶恐中这部分人在江边发现了被大队人马经过砍断的芭蕉树,抽出了长长的树心。于是,这部分人误认为前方的大队人马已经去得很远了,不可能追上,饥寒交迫的队伍便决定在这个宽阔的坝子里留下来。想不到,他们这一留,就是二千二百年的漫长岁月。
戛洒江河谷西面是岿巍的哀牢山,东部是高耸迤逦的迤岨山,河谷下切,坝子海拔仅有七八百米,炎瘴之地,疟疾盛行,单是生存,就不好对付。远道而来的先人们与脚下这片土地融合着,并要接受来自各方力量的对抗和命运猝不及防的挑战。在漫漫岁月的征途中,古越人一步一步建立起了属于自己的生命空间和精神家园,就像河谷中枝繁叶茂的大榕树,一枝一蔓,一丝一根,一叶一芽,慢慢生成,然后在岁月的磨砺中变化成长。
醉美之河谷
不得不说,这是一个迷人醉心的河谷。
一条自北而南的江从山谷中穿过。清晨的朝阳,沐浴着出山的热气,它从东部的迤岨山巅冒出来,金灿灿的光线,首先打在对面的哀牢山主峰上,然后渐渐地往河谷底部走,越走越低,越走越远,最后走过哀牢山脚下的戛洒古镇,并一古脑儿地照到古镇脚下的江面上,刹时,红河谷中便腾起一道明晃晃的金光。河水伏在山谷里,它是静止的,不要说是早晨,即便是在秋夜里,人们也无法在小镇上听到它奔腾的脚步声,即便来到宽阔的河床,也听不到河水本应发出的轰轰的声响。戛洒江太宽阔,太平坦了,不到它身边,你看到的红河就是一条在山谷里的睡龙,它匍匐着,又像仰面朝天,给天地束上一条七彩的腰带。
灵动河谷的是一种水鸟,它羽毛是白色的,个头鹌鹑大小,红腿短,黑嘴长,眼睛位于头部的后方,它机灵地在江面上盘旋着,转动着幽灵般黑亮亮的大眼睛四下搜寻着江面的小鱼,沙地上的昆虫,如若发现周围一有动静,就会飞入随风浮动的草丛再也见不到踪影。还有一种漂亮的鸟儿,羽毛呈黑白两色,头顶前部及脸上的羽毛是白色的,余下的是黑色的,它喜欢在白色的沙地上快速地走动,也喜欢停歇在江岸边的大石头上上下有节奏地摆动尾羽。它的叫声是悦耳的,飞翔的姿势就像夏天洪水飞溅的波浪。它能走能跳,能飞能跑,当地的群众叫它白鹡鸟。但最吸引人注意力的还是常见的鹭鸶,它身子硕大,颈脚细长,它们群飞时就像江面上移动着纯白色的晨雾,它们没有其它水鸟那样灵敏,但正是这样悠长的飞翔,为很多远到而来的摄影师留下了美好一生的瞬间。
河谷里还有大象,它们甩动着粗大的鼻子,吹动着响鼻,它们在沙地上来回走动,并三五成群地走过河面,四肢就像浇灌江河的泥柱。不过这是南迁时先祖们看到的情景。但密林里的绿孔雀仍然还栖居在江畔周围,它们常常会在夜间出没,成群结队地觅食树梢坠落的果实。
我分别在春夏秋冬,到过哀牢山下红河谷畔的戛洒。
在哀牢、迤岨两山之间,一条大河就像鬼斧神工,摧枯拉朽般劈出一条宽阔的江坝,高处山峰列列,低部红河蜿蜒而去,一个繁盛的戛洒古镇,就兴建于哀牢山脚下的江边。古镇四周,傣乡梯田平平整整,层层叠叠,硕大的芭蕉林环绕着密密的村寨。芭蕉,亚热带特有的名片,不但人喜爱,过去大象也喜爱,不同的是这儿过去是野芭蕉林,而现在却发展成为地方产业,外面的老板进来承包、流转,一次就是成千上万亩。路上来往的都是附近村寨里的花腰傣人,他们就是遗落在红河谷的古越人的后裔,滇国皇室的后代。男女都穿自织自染的土布衣服,女人服饰鲜艳,镶金坠银,因腰部缠绕着一条长长的花腰带,现代的人就叫他们为花腰傣。
在戛洒坝的乡村道路上,不论朝哪个方向走,流动的都是花腰傣的气息。这儿的村寨,家家户户都是土基砌墙、田土擀成的平顶土掌房,一改版纳、德宏傣族的干栏式尖顶建筑风格。房屋宽大,窗户很小,不过土房通透通风,冬暖夏凉。从古镇穿衣戴帽,欣欣向荣的派头,看得出这个集镇一直发生着大的变化。上世纪70年代,这儿还是从草皮滩上兴建而起的江边集镇,沙滩上的街子,就是傣语“戛洒”的意思。而今集镇越来越大,已向西延伸到山脚。像小镇永远膨胀的欲望,一直在向四方延伸。
春天的戛洒,是最灵动的,梯田里流动着山泉水,春光荡漾。开春了,花腰傣人男耕女织,在插秧。他们编织的梦,也是中国梦。很多人一直想不明白,镶金坠银的那支古滇国皇室队伍,他们从驻扎在荒无人烟的戛洒那天,是怎样一步一步走到现在,从学会自己生火,自己做饭,自己建房,自己开地,点播庄稼,再走向和各民族的相交相融,他们的泪水,他们的欢笑,他们的生,他们的死,在口耳相传的古歌谣里还能找到。
一个黄金一样的季节,是秋天的戛洒。梯田里吹来的和风,杂糅着稻穗的香味,一群群不同种类的鸟,在村寨上空盘绕,在江雾上方迂回穿梭。有花腰傣人在成熟的稻香里收割,他们的身影往梯田的前方移动着,身后就会出现铺路般不断扩大谷茬的旷野。从前的傣乡,是一个农业区,每到秋夜里,平整的土房顶上就会晒满金黄饱满的谷粒,天上不来雨,这些谷粒一直要在房顶上晾晒到稻穗收割完成,那时,房顶上的金黄,才会像褪色的金属慢慢地消失。
哀牢山岿然而险要,险要的高处,耸立着一座城堡一样的土司府。民国时镇守新平、双柏、镇沅、墨江、景东五县的最高联防指挥官,号称“滇南一柱”的大恶霸、大土匪李润芝的城堡就高高地建在那里。李润芝祖籍陇西,始祖李尚忠,明初祖父宦游来滇,落籍新平。李润芝继承家父祖业,他来到哀牢山,带来了战争,同时也带来短暂的安定。但任何人都明白,这种君主的辉煌是短暂的,只有人民才是永恒。现在,高踞峰顶的城堡门前冷落,要不是当地政府把它修缮一新,变身旅游景点,它大约早被哀牢山雨后春笋般的荒草所湮没。
游客与沙滩街子
现在,许多游客都像我一样,不断来到戛洒镇。
不论是坝子中的河谷、集镇、街道、村寨,还是山峰之上、密林公园,在戛洒漫游,我经常要遇到一些操着南腔北调的游客,有开着小轿车来的,有为登山来的,有为采风来的,还有为观日出来的,从装束和设备,基本就能判断他们的目的和身份。
戛洒对游客的诱惑,主要有三:一是来感受花腰傣风情;二是来体验茶马古道文化;三是吃戛洒汤锅。来的人都要完成这三部曲,不然就白来戛洒了,或者就根本算不上来过戛洒。
从新平召开了首届花腰傣国际文化学术研讨会后,花腰傣就火了。许多专家学者就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眼睛盯上了戛洒。大多数专家们认为,居于红河谷戛洒江畔的花腰傣,就是古滇国皇族后裔。因为有太多的文化符号,和滇国之地晋宁石寨山出土的青铜器、江川李家山出土的青铜器文化无比一致。当然,也有一部分专家认为,花腰傣是哀牢古国的后裔,以永昌郡为核心的哀牢国,主体就是傣族,而且当时国家的势力范围,东部就包括现在的红河谷戛洒一带。历史是一个谜,就像大起大落的江水。也像日月的光影,明明暗暗斑斑驳驳。当然,大多数游客来到戛洒,并不是为考证花腰傣历史,花腰傣服饰艳丽、高贵典雅,风情浓郁、饮食奇特,再加上红河谷长期处于封闭半封闭状态,因此它保留了较为完整的原初文化,游客是来体验民族文化的丰富多彩。
很多人都成为了花腰傣的弟兄、朋友,成为戛洒汤锅的座上客。
戛洒,这个沙滩上的街子,自古就是商贾云集的地方,茶马古道的中转站。建于唐、兴于宋、辉煌于明清,衰落于民国的茶马古道,曲曲弯弯,四通八达,盘亘于哀牢山的崇山峻岭之中,并从戛洒集镇经过。
门前长着梭椤树,门后长着马缨花,马蹄声踏碎千家水,打铁声惊走山中鸟。埋藏在戛洒镇耀南山十里河原始森林中的茶马古道,宽约1至3米,长度难于估算,目前保存尚为完好。苍茫的古道旁,古老的千家寨遗址、营盘遗址、红河古渡口、东磨古渡口、明清战壕掩埋在水渠腐叶之间,是辉煌,也是破落,是故事,也是慨叹,是明灯,也是暗流,是喧嚣,也是沉寂。是一部书,可惜已少有人翻阅。
密林中的千家寨,有酒店、客栈、马店、烟馆、铁匠铺、赌场、炼铁厂。辉煌时曾有过千户人家,相传寨头杀猪,寨尾都无法听到猪叫。南来北往的客商、马帮过山时都要在这里歇脚,修整后再进山,下普洱。或出山,下戛洒北上省府昆明,每天有800多匹骡马要过哀牢山和红河谷,摆渡的船来回于江面,就像万里横渡长江的舟船。
清同治年间,有当地人在戛洒十里河开矿炼铁,铁矿在距离千家寨十多公里的地方。民国时期,“陇西氏族”世袭土司后人李润芝的父亲李国宝投资开采十里河铁矿,冶炼生铁铸铁锅和铁器;1958年大炼钢铁时期,人们又在这里开矿炼铁。炼铁炉高约2米,宽1.5米,进深4米左右,一窑挨着一窑。现在,青藤缠绕,落叶纷飞,岁月是踏破古道的一枚马牙石,是暖风送来的陈年旧梦。千年哀牢茶马古道经历了蛮荒、原始、艰险、苦难,见证了人们熟知和不熟知的一切,人们来到这里,似乎是在找寻一片让灵魂得以栖息的安静之地。
抗浮锚杆是抵抗建筑物向上位移的受拉杆件,适用于基岩或土性较好的地段,具有埋深浅、受力合理、造价低廉的优点。抗浮锚杆一般采用高压注浆工艺使浆液渗透到岩土体的空隙及裂隙中,使锚杆侧壁阻力增加。抗浮锚杆自由段的防腐蚀要求较高,且锚杆受力会产生较大的变形,不利于结构稳定。
江面已远去的渡船,不断下落的水和消失的炎瘴的天气,说明醉美之秋已来到河谷。沙滩就像贪婪的魔鬼,不断地赶着河水往河心里走,河水就像弱小的蚯蚓,不断地拉长身子,缩小身躯。等河谷上露出了大片的沙地,河岸上就会摆起了一长溜的汤锅市场,有卖羊肉汤锅的,有卖狗肉汤锅的,有卖牛肉汤锅的,当地的群众用土基或三个江石垒成灶,支一口铁锅在上面卖肉汤锅。中午,江边的市场上人越来越多,本地的,外地的游客都有,人们坐在芭蕉叶垫起的江石上喝酒,形成一幅壮美的南国风情图。市场越来越繁荣,汤锅市场也跟随着沙地赶着江水往里走,市场越走越大,最后市场占踞了江南岸的半个沙滩。芭蕉叶铺满了整个河滩,这就是红河谷有名的沙滩街。但这样的繁闹市场只能持续半把年,雨季就来了,宏大的河水一夜暴涨,天亮时就淹没了整个裸露的河床,变成了一条发怒的龙。龙身上不时漂浮起上游冲涮下来的木块,“啪啪”击打的浪涛吞噬着岸边上红色的沙页岩层。这个时候,夏天又来到了红河谷了。
水淹没了河床,戛洒的街子,仍然搬回到街面上赶。汤锅铺会搬到街道附近关竜寨子的稻草垛下进行,南来北往的游客和商人依然如故,坐在歪斜的四方桌前和江石上大碗吃肉,大口咂酒,芭蕉叶上的碗传达着丰富的信息,铁锅下的火依然很旺,锅里的肉冒着热气,或翻滚着,这个由沙滩过渡到乡村的街,依然没有因河水的发涨而影响了人们的生活。
花腰傣的服饰
在哀牢山下的红河谷,最明亮的风景之一,是经常会看到花腰傣穿着华丽的服饰在田间地头劳动,插秧、种菜、收割、拿鱼,这种平常老百姓所做的苦力活计,本来并不奇怪,但对一身皇族般高贵的花腰傣女人来说,着实会让人有些无比惊艳。
劳动,本来是针对全人类的,不论你是达官显贵,还是一介布衣,一个人具备了人的功能属性,你在世间就得参加劳动。只不过劳动的方式会因人而不同。而作为古滇皇室后裔的花腰傣,他们在迁徙中丢掉了皇族所掌握的一切荣贵,世世代代仅延袭了一件穿在身上的服饰,这是多么珍贵的历史记忆啊。
在沁凉的花腰傣平寨村的榕树下走动,哀牢山白花花的流水翻滚着浪花冲刷着高高的石槽,“唧唧”的织机声不时会从傣家的房间里传出,让人突然就有了一种回到农耕时代的古韵。临窗下,73岁的刀元珍老人安静地推拉着古老的织布机和梭子,织布机和她一样历经沧桑,见证了美丽与衰老的变迁;旁边几位年龄不等的绣娘低头忙着手中的绣品,一边聊着我听不懂的闲话,她们身上的花腰傣服饰,见证着她们曾经的青春年华。她们穿着巧手随心剪裁出的衣裙,在小村里美丽着自己的人生,也使一门古老的技艺得以源头活水,生生不息。
我在小组长的引荐下来到了绣娘刀梅的家。刀梅正在赶制和外商签订的订单。看见刀梅的第一眼,我第一印象就是觉得她长得太美了:婀娜多姿的身材,粉红白嫩的皮肤,润湿可人的小嘴,微微上翘的眉。在哀牢山,人人都说花腰傣姑娘长得最美,看来一点也不假!
当然,这大约也跟她们的皇室血统有关。
刀梅见到我,忙放下针线活,站起身为我添茶倒水。我在她堆满织品和布匹的房间里坐下,我们开始交谈。
刀梅说,一到年关就很忙,田地里都忙不得去,下半年接了许多订单,都要在年前交货。
我说,有生意不是很好吗?只要有事做,有钱赚。
刀梅笑笑说,何大哥,你不知道啊,刺绣的活计是一针一线,一点也快不起来。交不出货,我急了睡不着。
我宽慰着她。一边打量起她家来,只见宽大的墙上全部挂满了她和协会做的针织品,有花腰傣女子服饰,也有花腰傣男女挎包、背衫、餐布和各种用于生活装饰的绣片,绣片上的刺绣结构细密有致,色彩搭配鲜艳,绣制的图案多为表达傣乡特色的四叶菜、八角花、薄荷、鱼尾、凤凰花、槟榔叶等大自然中的花草树木、飞禽走兽,也有表达山川河流的彩色线条,还有表达青年男女恋爱的心字图案等,每幅图案中,都融入了绣娘无尽的遐思,寄托着傣乡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在新平,花腰傣的服饰被称为穿在身上的艺术,绣在身上的历史。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花腰傣人一直延袭着古老的纺织技艺,衣服全是自织自染土布,缝合的衣服再绣上精美的彩线和图案,配钉上琳琅满目的各式银泡,搭配上精制小巧的秧箩饭盒,这是多么美的盛装!还有部分傣族女子喜欢缝制红绿相间的锦缎上衣,华丽高贵,神采夺目。上世纪九十年代,一套华丽的花腰傣服饰在法国卢浮宫展出,惊艳世界,从此,花腰傣服饰美名传扬,许多到哀牢山来的游客都喜欢买一套花腰傣服饰,作为礼品回去送亲人,特别是小孩子服饰,供不应求。
“男人看田边,女人看花边”,花腰傣女孩六七岁就能舞针弄线。一代代花腰傣女子,都把最美的刺绣穿在身上。刀梅说,她小学毕业就跟随着母亲学刺绣。这也是傣家女孩子人生的必修课。刚开始,虽然针脚粗笨幼稚,但机灵的她在边玩边学中,初步掌握了傣绣的基本要领。
高中毕业后,刀梅外出打工,城市炫目快节奏的生活让她有些茫然,每天为生计辛苦奔波,却一点也不踏实。2008年,她回到了家乡,重新拾起了绣花针,开始像祖辈一样用织机和针线描画自己的花样年华。在她的带动下,平寨村成立了刺绣协会,全村120多名妇女加入了绣娘的行业。大家互相帮助,现在她们的手艺都能变成商品。她们到街面上开铺子,逢年过节到集市上摆摊位,当地妇女们带着自己的绣品去卖,一年下来,都能赚上万元钱。而新平刺绣协会统一订做的绣品,还远销新加坡、香港等地。
在哀牢山戛洒,我看到刺绣已为花腰傣服饰文化锦上添花。这种源生于宫廷,在社会生死变迁中仍然坚守,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刺绣技艺,通过女子灵巧的手指展现在衣裙上,傣族男女美丽的情思也是通过精美的针线传达。傣家女子身着自己做出的彩衣与心爱的人约会在大青树下,款款而来,婷婷玉立,摇曳的裙裾飞舞旋动,花腰带如她们绣织的彩线一般艳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