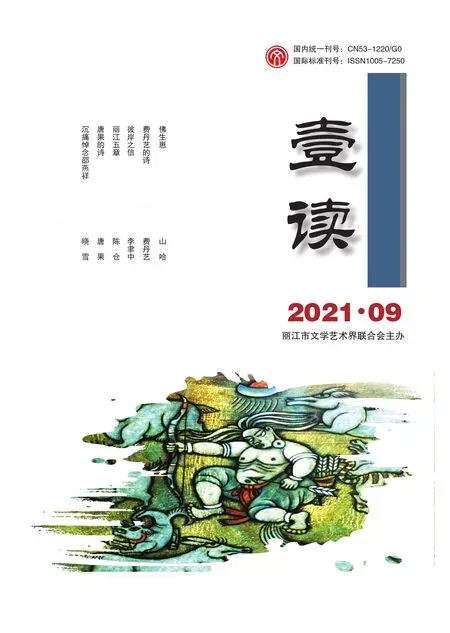费丹艺的诗
路过的信
【致离者】
与你同行的人
有的走着走着竟停下
有的 又自然朝别的方向去了
你总是四处张望
更改了路线的人
你默读他们的背影
回头瞧停下的人
笑起来指着前面 叮嘱你看路
想起 无数个深夜
你与他们分享的月光
越亮 越凉
流离在你心边儿上的城墙
墙头的枯草都觉着缺氧
你看着他们 一点点变作你身体里
沸腾着的蓝黑色血液
像是 海底的火山
梦亦是梦 醒亦是梦
青山漂流而去 江河静止
春花落下 秋月就立刻升起
极光在赤道的上空斑斓
扑火的蛾子安心回到茧里
他们还是顺着你的眼光
徐徐向你走来
你痴恋地不肯眨眼
瞪到眼泪变得鲜红
大地也跟着你龟裂
你一跺脚 又一次宣布
你要走了 你要忘了
你可以端着茶杯 拈来笑谈
你转身 面向前方的阳光
你激动地朝理智招手
时间却对你摇了摇头
【离者回电】
你该怎么办呢 我们的宝贝
你盛着泪水望我们
望得模模糊糊
睁大我们曾千万次吻过的
你的眼睛 瞧个清楚
我们呀
有的走倦了
互相牵着 手背上扎满荆棘
一两句话落在地上 就成了悬崖
有的 被路中间长出的高墙挡开
这唤作距离 时间 误会的高墙
月亮升起 最后只剩一句晚安
有的 已经走到了终点
所有的承诺和不舍
就只能永远站在这里 目送你成长
离别是一日的三餐 人间的四季
我们是去往另外的世界
还是别人身边
你都要相信同行时
予你所有的赤诚与坚定
不要再掐着手呜咽
也别让回忆如海啸般埋住自己
我们已是你命里淡化的光阴
你看柳暗之后的花明
芳香混在阳光里变得恬静
蝴蝶追着岁月向前飞去
你也得去
你要去找找谁始终与你一起
谁无言为你疗伤
把你的热泪和珍重统统给他
你还要去未来碰见不弃你的人
乘上地铁 转了公交
淋着大雨走很远 都要来见你的人
答应我们
莫要怀念 只留下零星的纪念
快点上前去
去紧紧地拉住他们
里外城墙
在我 企图不顾一切的时候
总有一切来顾我
从一粒芝麻开始
然后便是数不清陨石
或小或大的 无故坠入脑海
可能这是我的特质
口头无所不能的同时又排斥自我
由内而外地 仰慕着想象
是种种 种种的元素
寻找话题时的刻意
挥手的刻意
用力撇清自己与夜晚的刻意
以及巴望终点的刻意
致我的脸上布满厚厚的老茧
我曾一次又一次拒绝梦见
梦里都狠下决心
把某个背影揉碎在无数次的回眸里
后来懊丧攒够了 质变成生活
我们害怕悲剧
而顺序倒置的悲剧 有更深的忧愁
当你意识到起初之拥有
才会为你现在呆滞的目光添一滴泪
我们需要情感
当一滴泪变成涌泉
才会再次渴望欢愉时不假思索的笑靥
周而复始
只有我们这样热爱生活的人
才能发觉生活最爱讲的玩笑话
只有摘下假面的此刻
才能耐心地解释给你听 它的幽默
“离离原上草 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得尽 春风吹不生”
钥匙
很长一段时间里
我把自己塞进锁孔的凹凸处
找不到任何一把对的钥匙 甚至一根稻草
被称不出重量的弹子压得动弹不得
真就是这样 弹子把我压得动弹不得
我在锁孔里不见天日
也把自己锁在日夜往返线路相同的小路
锁在几乎没有意识的凝视
锁在不动声色的躯壳里
在锁孔里的生活中
我不抱怨闹钟是何时响起
半夜抑或午后 我只是醒来而已
我不在乎几点吃上饭
大脑抑或是手 我习惯着饥饿的状态
可我懒得进食
我不怕疼
无非就是被上天需求一道划痕 一些暖流
放在身体里也会变冷
再刺痛也比不了灌进心口的风
事实上我也看不懂别人看不懂的眼神
对于我的锁孔
我没有办法出来也不想出来
更没有人在外面接我
因此被迫我接受生活的号令
若让我静 我可以在长凳上坐一个世纪
若让我动 我可以环游到新的星球
在长凳上 我的大脑里
你看 这就是生命之鸿毛 就像弹子
我撑不起来 跨不出去
也许是偶尔 也许锁孔就是一个世界
明夜无风
不止明夜无风
以后每天的夜色都没有风了
怎样的暗涌都将被摁住
举头望月时 少缕云丝
平静的是空 更是注视着空的眼球
夜半小院里 只有你和树的影子
枝丫相缠 胡乱交错
就像你的血管
每一阵风吹过 就战栗 颤抖
你想把它们从身体里抽出
却无奈就像这树影
感受得到 却改变不了
你会念起曾经踏进泥泞
陷入苦尽甘来的圈套
陷入抿嘴浅笑 戚戚然的酒窝里
每一阵风划过 都剔除一层傲骨
如今不仅形单影只
更薄如纸片般的易散
又一阵风
赶快裹紧了外套 转身进屋
所以以后要在阳光最好时出门
忘记老山一万年才积一次的雪
忘记那只不守约的海鸥
欣喜却难得的 我们得忘记
给朝天的唢呐蒙上红盖头
拔掉罂粟 种上稻谷
终于到了明夜
一切会安然无恙吗
会的 你看
他说要浪迹天涯
又用马换了一壶酒
以北河山
当 晨昏线的光晕将思绪引向天际
以北以北 裹紧大衣
生性怕冷又生性好奇
着陆的风沙划过鞋底和眼底
脚跟踏下 碾碎了年华
指尖 春风混在朔风里
四月素尘 又添新痕
东山再起的严寒刺中眉心
提醒我牢记我眼见为实的
白雪莅临戈壁 狭路相逢
赤脚驻足冰冷的漠上
大自然的野心穿透身体
孤勇之花在头顶盛开
挥挥衣袖 挡开八方决骤的猛兽
任由青丝鞭挞脸颊
指点鹰驰雁舞
事实我怕极流动的固体
迷失 沦陷在四周相同的景象
人不可能永恒矗立 至高无上的
所以我需要崎岖来告诉我实质
清清楚楚地告诉
在疾风掠过后
嗅到萦绕口鼻处的硫磺沙土
这时候细腻也戛然而止
举头危崖无草木
垂眸深谷无江湖
徒步再向荒原
荒原里的积水 像极哑巴的眼泪
塞上牛羊也要压榨致干
牵马人的手皲裂一如脚下的旱地
跨马上的游人却嫌震荡不堪
而来之不易的辽远苍穹
分明可以细数星宿的眼睛
只看见了夜的深邃
以北以北
这是九州版图上的虬髯客
不羞小节而精于气概
剑气挽成凹凸壮阔的地标
戳破鸳鸯蝴蝶梦
偶尔哽咽 目送红拂
所到之处苍茫 将天地留给自己
我没有否认这一方水土
只是我来时初见的颓然
又割开了断肠
忆起前年的同时
我在南国望着窗 落英正缤纷
夜尤短 墙也暖
所以愿下次再见
风吹草低见 你温润的双眸
以北大地
我离开的时候 枯木尚未逢春
我回头的时候 青岸霸占黄塬
只可惜我心胸太小
装不下这大山大水
门前的一寸雪 扫干净足矣
头顶的一片瓦 摸得到月光足矣
壶中有茶 屋后有井
足矣
分明四季
趁我现在还记得起
这次要用最直白的语言告诉自己
避免衰老后再读到时的颤抖
甚至无法自我翻译
如同回首 拨不开的雾霭
看不清来路 茫然而无措而恼怒
那时春
我的生活还无霾无沙无柳絮
纯粹是触手可及
是脸上的雀斑 是淡淡的蛾眉
是我烦腻的单眼皮
干干净净 一尘尘都不染
干净到我想把它扔进泥潭
那时夏
我嫌头顶的太阳太辣
我想跑到没有一丝阳光的地方
我嫌家乡的土地太烫
我想躲到没有人认识我的汪洋
我总是想着如何逃窜
逃窜不成就大哭一场
那时秋
落日落叶落落寡合
不曾完整观看某一次余晖
不曾全心投入某一次散步
将心事归结于微凉的空气
是呼吸把烦懑灌入身体
每一个细胞 都如同落日 落叶
落落寡合
那时冬
我猛然开始怀念春夏秋的岁月
快速穿梭其中的我
自以为聪明地把朗朗书声
比作青春的修罗场
直到最后一片红叶落下
变成了隔绝过往的香扆
或者说是成长
来时孟婆汤 忘却了前世苦
没做想今生还有千千杯御寒的烧酒
冲淡今世吞咽的苦胆
为寇
跌跌荡荡多年 绕不出心里的结
让人放心的无非是换了一个款式
死结变成蝴蝶结
扎在心上看似留有了余地
命运之手系上 谁也无法解开
这结或许是那双手的错
无法解开却是我自己的错
错误总是以不变的姿态环环相扣
扣得我只能冷眼旁边 自我的境遇
而天命带来的不甘
随之掩埋在向生活屈服的不甘里
两种不同的不甘
不甘人下和不甘自弱
生活还是带来了升华
我说过有些人生于罗马
却也不能说自己差之千里
升华的意义
便是让我跌倒在去罗马的旅途里
矛盾 凹凸 冰冻住的焰火
我以不作为作为对境遇的抵抗
甚至不知若是逃出这里是否还有气力
就连写下的诗句 都少了莫测的寓意
若是无人看懂怎么骗得一个知己
连执念都妥协
其实只是懒得去找寻的惰气
举头三尺有神明
我的天地受限于三尺之内
我要在这三尺天地里活得喜乐张扬
一边嬉笑积极 团结友爱
我又要在这我的天地里挂念头顶的神明
一边伤春悲秋 汲取着回忆撑到明天
或明或暗都是我 你若爱我
便无需爱我的全部 胜者为王
不要长大
又要向北去
路过那些拒绝好奇的站台
当眼前出现一览无余的平原
与毫无难度的丰收
高山起伏 被抛在身后
自由的天空也越来越远
不要回头
你只能往前看
用余光打赏夕阳
用发丝去感受严寒
你告诉自己 家乡
那冗长的白昼和刺眼的太阳
在窗上呵出水汽印上手掌
再见
不要眷恋
无法挽留的许多事
促成了真正的生活
就像被铁丝网勾住的毛衣一角
以及离家的车票
成年后的世界
除了几句操蛋
再少有卯足气力的反抗
连诗歌都变得简单
不要呐喊
顾·元谋县江边小学
孩子们 我什么也不是
你们却让我别走
你们叫我老师 向我行礼
孩子 你们的心上没有围墙
你们不会明白
我为何惶恐与战栗
因为我 什么也不是
对不起 我的钟表太小
我的行囊只够装下结果
我自诩辛勤的蜜蜂 飞舞 采蜜
盘旋在你们当中
在你们无瑕的笑容当中
居然是我那些被世俗所包裹的企图
是的 惶恐与战栗
你们干净得让我羞愧
我唯有不知所措地笑着
双脚长进了水泥地里
你们叫嚷 蹦跳 欢闹
我愣在原地
看着笑声打破了冰封着我的壳
你们 闯了进来
如此
世间最纯洁的生灵围绕着我
极致的幸福让我变得麻木
我承受不起这份最纯粹的被喜欢
我记得你们每个人的样子
刻在我的每一根睫毛上
眨眨眼睛 全都是你们
“老师 别走”
你们又一次轻声祈求
闪烁在黑夜里的眼睛 凝望着我
我却不得不退到更黑暗的地方
等星星泛起困意
你们也睡了 睡了
不要梦见我 我只是一个过客
未有光
我从未进入的那个世界
慢慢钻进我的鼻腔
好呛 好暗
出租房的楼道褫夺目光
好像裹进积满灰尘的被子
梦里是我不想揭开的答案
我懦弱 我怕梦境是真
我怕眼见如听闻
我怕十几平的房间里 竟然住了四个人
推开门 梦境是真
灶台紧挨三个孩子的书桌
缤纷的催费通知在桌上呐喊
生满锈的双层床
这间房里放了两张
老父亲吱呀坐在小木凳上
我忽然就想起 我晒太阳的那个飘窗
周家唯一的窗户 照不进阳光
老父亲还握着钥匙
他手中 钥匙比钢筋还重
他也笑 在妥协中认真地笑
想起他的兔唇男孩和双胞女孩
他在每一个夏天挡住雨
又在每一个冬天拦着风
他将孩子读过的每一本书都整齐收藏
是全然相悖于这间出租房的异象
孩子们也笑 在忘却中简略地笑
十一二岁的孩子 熟练地运用菜刀
十一二岁的孩子 说养活自己就好
说梦想是望着天马行至半路
在空中燃烧
我望向他们和他们心中湮没的天马
却只能记下这个世界
我望向这个无尽的灰色世界
望向窗外紧邻的另一栋出租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