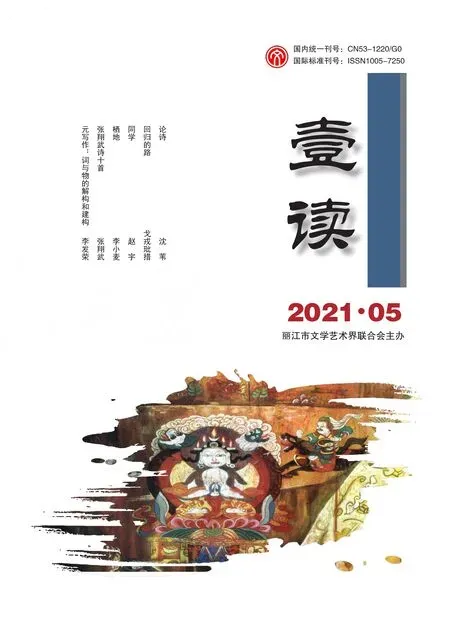让生命在诗歌里沉醉
——麦芒诗歌品读札记
◆张家鸿
这不是一个写诗的时代。普罗大众早已远离诗歌,视诗歌为古化石,视诗人为特殊的人群。然而,对写诗的人我常常是高看一眼的,因为身处物欲膨胀的时代背景与处境,诗歌写作更显不易。写出名噪一时的佳作,麦芒做到了。写出让人喜欢的诸多作品,麦芒做到了。我以为,这都不是最难的,亦或者说,这都不是他诗歌创作的目的。我以为,麦芒的目的是让文学拥抱生活,让生活为诗歌创作提供永不枯竭的源泉。如果说生活是一个浑浊与清澈交织的湖面,那么缪斯之光投射在湖面上,总会散发出异样的神采。如此一来,写出诸多佳作、让读者心生喜爱,必然是水到渠成之事。正如麦芒在《关于诗的诗》的倒数第二节写道的:“诗人不会消亡/诗歌永远年轻”,这句话不正是他的自我简介吗?他写的,何尝不是他自己?
饱含浓郁的人道主义情怀是麦芒诗歌鲜明的精神特质。世相纷繁,人是万变不离其宗的核心要素。不管是六行诗、三行诗、四行诗、五行诗,抑或是别的形式的诗歌,其中最耀眼夺目的当属这些以“人”为主旨的作品。
他的目光既向上,也向下。何为向上?即关注的视线延及历史上的名人、伟人,这些人身上体现出来的“上”不是权力、地位、名气,而是他们身上散发的精神光芒是耀眼的、灼热的,让人一咏三叹。“一曲《广陵散》/昂扬了一千七百多年/——嵇康犹在!”这是在颂扬人心的壮美,古人的铁骨铮铮至今动人心魄。“二十四岁,二十四级阶梯/二十四岁,一座高耸入云的碑。”这是《想起聂耳》中的诗句。用短暂的一生树立起一座音乐的丰碑、艺术的丰碑、历史的丰碑,聂耳当仁不让。生命的价值与意义从来不取决于其长度,只取决于其厚度与宽度。《大夫林巧稚》中写道:“平生最喜爱孩子/却没有自己的孩子/年轻产妇的微微一笑/是她最大最高的奖赏/一双纤纤小手/托起五万颗太阳”·微笑源于小生命的第一声啼哭,这是医者的仁心,是天使般的大爱。虽无一儿半女,林巧稚却有许许多多的孩子。
我尤其喜欢麦芒的《端午节感怀》:“叫鱼儿去吃粽子/叫鱼儿去追龙舟/让他尽情地倾诉/让他静静地思索/好一个三闾大夫/楚国的一根骨头”。后来人的粽子与龙舟,全在于表达对屈原的敬意,为的是还他一片宁静。倾诉也许是自言自语的,思索也许是于事无补的,可是这不正好还原出屈原最本质的身份——思想者吗?真正的思想者岂会奴颜媚骨?他的刚烈与耿直,是后人享用不尽的精神财富。他审视自我时的严苛与人格追求的高洁,让多少死去的人与活着的人相形见绌?
何为向下?即麦芒的目光同时也聚焦于身边的普通人。他们平凡、普通,充满俗世的烟尘气息。然而他们的悲喜,同样给予诗人感动与启迪。这些人有血有肉、有神有魂。
“带着绿色的双眼/从城里来到大山/一来就是十三年/盯着黑颈鹤旋转/妻子走了孩子散了/鹤儿们哦越叫越欢”。这是赞颂黑颈鹤志愿保护者的一首诗。他,不对,是他们付出的代价可谓沉重,精神可谓高贵。把鹤视为子女,已然不是众生平等之意,而是视如己出。通常来讲,唯有对待自己子女,方能够全心全意、无微不至。“欢”的背后倾注的是常人无法付出的艰辛。写街头素不相识的小贩时,“不分四季,走街串巷/把一丝丝温暖和乡音/奉送到你我手上”,在有情人眼里,小贩卖的不仅仅是小商品、小物件,是给予他人的体己的帮助,是一种不绝如缕的乡愁。小贩不是卑微的,渺小的,还是温暖的。他与别的人一样,是丰富的个体。
为什么同学缘最深、同学情最真?原来不管是李是桃,都是“一棵树上的花”。一棵树上的花不正是一家人吗?一家人的感情,岂有掺假之理?这是让时常置身于同学处境中的我,心生反思的一首诗。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我会不会对待同学不够真?我是否已经把一部分同学情遗忘在岁月的最深处?
向上是观照历史,向下是瞩目现实。麦芒也抨击,也鞭笞,也控诉,也指斥,但是他最震撼我的是关于美好人性的讴歌、高贵品质的颂扬、人间温情的赞叹:黄万里的信念与风骨、陈寅恪的巍峨与高耸、外祖母的呵护与温情、艾青诗心的永远年轻、故人的诚挚与热心肠。这些难以用三言两语来转述的美好,更多地给人带来希望,让人不自觉地向着真、善、美靠拢。钱穆先生在《谈诗》中说过:“我们学做文章,读一家作品,也该从他笔墨去了解他胸襟。我们不必要想自己成个文学家,只要能在文学里接触到一个较高的人生,接触到一个合乎我自己的更高的人生。”
基于这样的阅读体验,我尤其关注麦芒诗歌中写到的一个个人。说到底,“人”才是生活的核心字眼。放眼浩荡漫长的文学史,与人相关的一切才是让文学作品摇曳多姿、错落有致的关键要素。我以为,麦芒关于人关于生命的审视与省思,眼光是独到的,意义是深远的。
在品读诗歌的时候,我一直在思索着:文学,于麦芒来讲究竟意味着什么?他在《文学就是马拉松》中写道:“文学就是马拉松/一步一步朝前冲/缺血少钙者,让开/怕苦怕累者,让开/谁能坚持到最后/谁就笑得最好最酷!”文学于心灵有益,文学于世俗无益,正因为如此,麦芒深知坚持文学创作的不易。马拉松对人的毅力要求最高,有血有钙者、能吃苦耐劳者方能抵达终点。对不同的写作者而言,同样的文学马拉松并不是等距离的,终点必然因人而异。然而,不管到达哪个终点,笑得最好不是意味着与他人的作品相比写得最好,而是与自己的过去相比写得更好,同时已然写出最真实的感受。笑得最酷就是笑得最灿烂、最敞亮、最有感染力。由此我深知,在某种程度上讲,文学抑或诗歌对麦芒来说就意味着生活。
“你终于从画梦里走来/来到我新迁进的房间/一排排站立着的兵士/随时等待主人的调遣/有你和缪斯女神做伴/即若皇室我也不稀罕”,这首诗虽以《写给我的书柜》为题,表达的却是对文学的钟情。有文学相伴相随的人生不仅是幸运的,还是幸福的。麦芒便是如此。他回报以文学的便是孜孜不倦的动力、乐此不疲的热情。书籍出版、作品发表、获奖多少、各种名头于他来讲,都是外来的,不是内发的。每天都可以写着、写多写少、写好写不好,凭借一己之心,不管如何,都可以制造出独享的快乐。我以为,这就是麦芒。如他在《诗痴》中写到的:“一见到好诗便醉了/从夜晚到天亮/月光,好香!”把“见到好诗”改为“写出好诗”不也可以吗?
生活中的一切都是诗歌创作的源泉。对麦芒而言,文学是无处不在的。体坛明星、旅游景点、身边亲人、政治小丑、文学大师、日常所见、都在写作范围之内。凡事皆可入诗,凡物皆有触动灵感的可能。因此他的诗歌是平和温顺的,平易近人的。这样的诗歌注定不是关在象牙塔里的自娱自乐,而是积攒着打动普通人的巨大能量。以人为核心的书写,自有温度存在。
无论夏日炎炎还是刮风下雨,校门口停满的车、挤满的人,让人感受可怜又可敬的天下父母心。如云一样四处漂泊的文友,最后的理想是一间拥有诗书的茅草房和一张固定不动的小木床。在这里他可以休息,可以吟诗。地理老师与音体老师的各种人生际遇,在大时代中如一粒微末的沙子被裹挟着,载浮载沉身不由己。挚友,是夏日里的一盅矿泉,是冬天里的一盆火焰。挚友之间的心与心是没有距离的。
麦芒的诗歌字简、句精,恰合于生活中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倾吐与流露。这不是随意的日常口头陈述,而是经由提炼、浓缩后的升华与飞扬。不难想象,麦芒于日常生活中凝神思考的画面,时而眉头紧皱,时而眉眼舒展,这是一个热忱地拥抱缪斯女神的人。因为热忱的投入,便与世俗的嘈杂树立起一道屏障,因而获得冷静审视的空间。这种精神层面上的寂寞,并不是人人可得的。“文学这个古老的东西,最初是一个人在寂寞空间里展开的手工。”我以为,张炜的这句话用于麦芒身上是合适的。
写着一个个人,支撑起的是写诗的这个人。他的善意、宽厚、执着、热情、自省,无不是人身上本该拥有却被很多人漠视的品质。钱穆先生还说过:“所以作诗,先要有作意。作意决定,这首诗就已有了十之六七了。作意则从心上来,所以最主要的还是先要决定你自己这个人,你的整个人格,你的内心修养,你的意志境界。有了人,然后才能有所谓诗。因此我们讲诗,则定要讲到此诗之情趣与意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