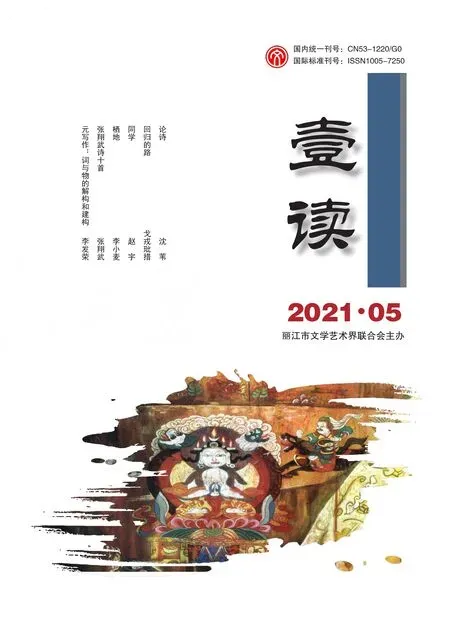栖地
◆李小麦
车子才驶进岔科地界,南方小镇特有的村庄气息便扑面而来:红褐色的土地,逶迤连绵的群山,错落有致的村庄,茵绿的麦苗,一切都在重复着记忆中儿时村庄的模样。小镇很普通,街道两旁的商铺、简易小摊摆满了琳琅满目的形色商品,油盐酱醋茶、糖食果酒米、服装鞋帽等乡民日常所需的生活用品五花八门。林林总总的商铺中,偶尔也夹杂着几家不大不小的饭馆、理发铺、台球室、录像厅等餐饮、生活及娱乐场所。这个小镇汇聚了岔科乡民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大部分内涵,它在宁静的小镇中显得热闹、真实、平常。我去时天已渐暮,由于天气清冷,街上行人稀疏。冬天的夜晚来得特别早,在小镇逛了没多久天便黑了。真是多少年都不曾偶遇的机缘巧合,这竟是一个漆黑的停电之夜,在浓稠的夜色中,烛光星星点点地在农舍里闪烁起来。夜色昏幽的街巷,行人若轻若重的脚步引来几声隐隐约约的狗吠。街口有一家卖烧烤的小店,客人稀廖,在这样凄清的冷夜,店主仍固守着心中一份微薄的希望。走进小店时,店主人没像城里的生意人表现出过份的热情,只是简朴地招呼:吃夜宵啊,坐,坐。烤盆里的炭火红红的,像熟透的红柿子。男主人沏来还冒着热气的山茶水,依然简朴地招呼:天冷,喝水,喝水。女主人在烤盆上方坐下来,她扒开盆中红红的炭火。炭火映着她的脸,她的脸健康红润,是我进岔科时在路上见到的红土地的颜色。一杯茶水的工夫,烤架上的烤菜已经熟了,发出滋滋的响声。女主人把烤熟的小瓜、洋芋、牛肉放进一个小碟,有一搭没一搭地向我介绍着岔科的山水、风情、人文,冬夜的小店弥漫着一股浓郁的温暖。不自觉间,夜色已深,遂起身向店主告辞。小镇的四周漆黑一片,黑暗浓得像化不开的墨汁笼住了我。来时星星点点的烛光已随着困顿的主人沉入酣梦,只有忠诚的、不知疲乏的狗吠声随着忽轻忽重的脚步依然清晰可闻。
入住的小酒店建在集市旁,它有一个大大的落地窗,这个窗正对着阳光充沛而喧嚣的集市。我搬了个靠椅坐到窗前,感受一个阳光下的小镇的世俗和日常。集市上,一个扎着红头巾的卖包谷的青年妇女,正和一个穿件黑色小马褂的中年彝族男子讨价还价,他们的声音很响亮,以至像是有仇恨般在互相争吵攻击。集市的一个角落里,拴了一头黑黄相间的毛驴,它是宁静的,在我注视它的一小段时间里,它始终一动不动地保持着一头驴最优美的姿势。一个孩子,两岁的模样,在她母亲旁边的空篮子里沉睡着,年轻的母亲把一把陈旧的蓝格子雨伞绑在篮子上,孩子小小的身子因此躺在一片荫凉里。有牛车在集市上慢悠悠地走着,有背着背篓的妇女结伴欢笑着进了一家杂货店,还有一个扎了块绿头巾的彝家大婶,不知为了什么事,气呼呼地站在大街正中对着一个满脸络腮胡的男人破口大骂。
这样的集市,这样的乡村,这样的阳光,这样喧嚣中的宁静,对我来说太熟悉了。这种熟悉来自我对乡村深刻的记忆,它们让我想起了我的村庄,想起了乡村上空的炊烟,裹了脚的外祖母,还有挂在老家那斑驳墙壁上的红辣椒和金黄色的玉米。我还听到了乡村里的鸡鸣狗叫声,听到了一位母亲呼唤她外出玩耍孩子快快回家的声音,还有一个年轻农妇做饭时锅碗瓢盆清脆的撞击声,以及一个熟透了的桃子落在地上的闷响声。我又想起闪烁在城市夜空里的霓虹灯,在大街上肆无顾忌乱窜的狂劲的摇滚乐和的士高,川流不息的车流和熙熙攘攘的人流,各形各色的红男绿女,花花绿绿的钞票,一幢连一幢的钢筋水泥房,尖尖的高跟鞋,形形色色的时尚服装。
清早走进一个叫双见峰的村子。这里的土坯房用红土砌成,房顶堆着圆锥形的草垛,村里的老人零散地坐在自家门口或做针线或聊天或剥豆子,偶尔有老农牵着黄牛走向田野。在一条不起眼的小巷,伫立着一座古建筑。这是建于明朝晚期的一座老戏楼,经过今人的改造,现已成为岔科民居中一座普通的乡村庭院了。两层楼的木质结构紧凑结实,小院中种有几株美人蕉,葱葱郁郁,充满了生命的蓬勃生机。一字排开的老戏台显得空阔绰余,人走在上面,隐约发出几声空洞而沉闷的响声。当年,这里曾是岔科小镇一个车马喧嚣的热闹场所,人间或悲或喜的戏剧曾一幕幕在这里上演。拂去覆在历史长卷上的那层薄灰,可知现在的岔科是古时通海、昆明通往阿迷(现开远一带)的重要通道。离小镇十余里外的风月桥,便是古驿道旧址。我去时是黄昏,冬日的残阳把风月桥和这条昔日的古驿道映衬得苍茫荒芜。青石铺就的桥身,被四棵古树不偏不倚地成四方形围绕着。作为连接通海、昆明到开远一带的一条重要古驿道,岔科在其中的位置可想而知。那时的古驿道,马啼声声,铃铛悠扬,马帮里赶马的汉子合着褡裢的节奏,想媳妇儿时哼曲软绵绵的《出门调》,饥渴难耐时扯开嗓门吼一曲《走帮口》,热了累了在风月桥上小憩一会儿。如遇天晚赶不了路,在岔科小镇的某个小客栈,赶马人卸下一身的风尘与疲惫,在酒足饭饱之后,一头倒在异乡的客栈里酣然进入梦乡。那时的岔科小镇,是赶马人温暖踏实的家,是如媳妇儿一样贴心的小棉袄。但和家人聚少离多的漂流生活,让赶马人倍尝了生活的艰辛与孤独。如遇街口的老戏楼开戏,栖身在岔科小镇上的赶马人的夜生活必然增添了一些丰富的内容。或许在花旦小生缠绵悱恻的歌舞和歌妓们的脂粉味中,他们会让自己放浪形骸地醉倒在异乡的温柔梦里。只是曲终人散、热闹尽褪再回到小小的客栈时,望着客栈门庭上悬挂着的红灯笼散发出的惨淡暗光,赶马人心里的落寞与愁绪会不会更深一层?
桥叫济生桥,横卧在阎把寺段的泸江河上。我不知它历经了多少岁月,但它确实已经很苍老了。桥栏已经残缺不全,桥面已是坑坑洼洼,有一种破败的凄凉。倒是桥的名字,让我感受到乐善好施之流建造济生桥时美好的衷愿。桥名既为济生,应有普济众生之意。事实上,从桥修建至今,济生桥确实也在普度着芸芸众生。很多年前的泸江河,水流湍急,如遇雨季,水位暴涨,如果没有济生桥,过河的险恶可想而知。和风月桥一样,济生桥也是古时建水通往开远一带的古驿道,开远与建水之间的贸易往来就是经过这条古驿道实现的。当地人传说,明末旅行家徐霞客徒步旅行到临安时,看见阎把寺村风光秀美,人杰地灵,便往阎把寺而来。后来经过济生桥,直往颜洞而去,并在颜洞题下了“我到此旅游,观风看景,人和水好”的句子。徐霞客是否来过阎把寺村,是否经过济生桥而到达颜洞,关于这种行走路线,无史可考,但这个传说却给济生桥增添了一层美好的人文情怀。徐霞客来过建水并游过颜洞是千真万确的事。资料记载:“霞客由黔西入滇,首次抵昆明并南下临安,游颜洞。徐霞客游罢颜洞,当天到距后洞十里外的漾田歇息。”这段资料里所提到的漾田,是距阎把寺村不远的一个村庄,徐霞客既在漾田歇过,那么他到过阎把寺并留迹济生桥的说法虽无史可考但也是可能的。桥无语,古人早已遁去。事实上,徐霞客留迹济生桥与否,又能表明什么呢?桥还是济生桥,河还是泸江河,而村还是阎把寺村,所有这一切并不会因为徐霞客来或没来过有所改变。但桥却是实实在在普济着芸芸众生,村庄也日复一日地迎送着春来秋往。我选择了一个阳光灿烂的中午登上了这座古桥。灿烂的阳光与败落的古桥显得非常不协调,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恍惚感。在古与今的时光交错中,似乎听到了马帮行走在古驿道时沉重的叹息,透着为养家糊口远离妻儿的无奈。桥下的泸江河水静静流淌着,似乎远去的岁月,一去不复返。只有河堤两旁几棵高大的木棉树,亘古不变地伫立岸堤,火红的木棉花开得热热闹闹,璀灿夺目。桥上有村民散散落落而过,吱吱呀呀的牛车在桥面辗下一个个并不清晰的印痕。破败的济生桥在村民的生活中突现出一种浓浓的烟火味。看得出,济生桥已经融入到阎把寺人的生活中,成了村民血肉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还没看见泉,便听到哗哗的水声。循声而去,一股清洌的泉水没头没脑欢蹦乱跳而来。沿着流水而上,不知这样的好泉出自哪里。源头在山肚子,仿佛龙口,汩汩地向外吐着水,源源不断。同行的田社长说,这龙潭是有灵性的,2005年东南亚国家发生海啸前一夜,泉水曾有预警。村民说,当时,仿佛有股巨大的魔力在操控着龙潭,汩汩流淌的泉水突然出现倒流现象,全部被吸进山肚子,黑漆漆的龙潭口一下子裸露出来,过了几秒钟,泉水才从山肚子里复流出来。这样的奇异现象在短短几分钟里重复了三次。第二天,各大媒体便纷纷报道了东南亚地区发生海啸的事件。龙潭所发生的奇异现象与东南亚海啸是否有必然关联,这涉及到地质学原理,需要得到地质学家进一步证实。但因为这件事,龙潭在村民们的心目中变得神秘起来。但龙潭是世俗的,它既生在村庄,便和村民有了血浓于水的感情纠葛。村民以龙潭水为生活饮用水,每个村民的血液里,都有龙潭水在流淌。
绕过龙潭,要去的洞叫南明洞,本地人称之为仙洞。仙洞坐落在万象山的山顶,像山的一只眼睛。去仙洞的路并不好走,崎岖蜿蜒,颠颠簸簸。很快便到了仙洞的洞口。洞口很小,仅够一人出入。入洞后,经一条窄窄的天然过道,眼前豁然开朗,呈现于眼前的是一个可容纳数百人的大洞,这是仙洞的内洞。内洞的洞顶生有一个直径约十多米的露天天窗,阳光从窗口照射入洞,使得洞内光线充足,这和其他溶洞“非列炬不可入”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差别,使得仙洞成为颜洞洞群中的佼佼者。仰头看向天窗,一束阳光斜射进来,几棵苍翠的树木环绕在天窗四周,一片云朵恰巧从天窗上空悠然而过。大自然鬼斧神工,在仙洞的洞顶造就了如此卓绝的窗口,即便身在洞内,洞外的气候变化依旧可以透过天窗知晓。洞内有许多塑像,或许普度众生的使命使然,他们的表情圣洁悲悯。洞内飘散着浓烈的香火味,那是香客供奉的香火,寄存了香客们美好的衷愿:或祈求姻缘美好,或祈求人畜兴旺,或祈求人寿物丰,或祈求财源广进,或祈求仕途顺畅。如此种种美好的祈愿,最终实现也好,没实现也罢,对人们来说,也算是心理上有了安慰罢。
站在牛滚塘的乡村公路遥望对面乌梅大山上的玛琅村。那是一片保存完整的土掌房,依坡而建,形状像中国图地,黄色的土坯在夕阳的斜射下发出熠熠的金黄色光芒。现在的玛琅村已经是一座空城,因山体滑坡,村民安全受到威胁,所以全村倾巢而动,选新址建了新房,遗留下这片土掌房形成玛琅村旧址。因为是一座空城,大老远便感受到了村庄的沉寂。因为进村道路被封,我只能站着远远观望,猜测着村庄里一切有可能发生的细枝末节,那种因无法涉足而想一探究竟的好奇,让我对散落在乌梅大山上的这片土掌房展开了丰富的怀想,怀想一个村庄曾经的鸡鸣狗吠和现在人去屋空的沉寂。但脚下的牛滚塘村却生动得多。春天的气息扑面而来,梯田里蓄满了水。田里那满满当当的水,让一切跟幸福有关的事情都有了发生的可能。牛滚塘的先民大智若愚,村庄的命名,通俗得像村里的大爷给二叔取的小名二狗一样顺溜,却暗藏福祈。在牛滚塘,该绿的树都绿了,比如棕树、芭蕉。该开的花都开了,比如桃花、梨花。在这些越冬而来的桃树、梨树之间,牛滚塘小学的孩子们跋山涉水正从几里之外的家赶来,小小年纪,已经学会了独立和坚强。这些孩子,像田野里的花儿般,绽放得无声无息。沿校园大门外一道缓坡缓缓而下,是一大片土掌房,被炊烟熏得泛黑的墙壁,大门墙头上长着一丛丛瓦沟花。村头一株榕树下,流淌着一股清澈的泉。这是一个能让人的灵魂回归家园的村庄,一个能让人陶醉在岁月纵深处的村庄。它的沧桑,它的宁静,它斑驳的墙壁,它铺着青石块的泥泞小道,它袅娜的炊烟,以及那些淳朴的彝民,都是。当我在这个土掌房的村庄里行走时,我的灵魂忽然撞击到了某种让我疼痛的物件,我意识到,我身上流淌的血液和土掌房怎样的一脉相承,我远去的童年和土掌房有着怎样千丝万缕剪不断的联系。是的,离家太久了,以至快忘了我的祖先是一个被汉人喊作倮倮的民族,快忘了我的童年曾和小伙伴在家乡那连成片的土掌房上留下多少难忘的记忆。今天,在土木建成的土掌房里,我看见了那位面容苍老但和蔼可亲的彝家老阿妈。她静静地坐在屋檐下,插着红色别花的黑布包头,穿着领口和袖边绣碎花的对襟服和大筒裤,以及尖尖的黑布鞋,像一株长在大地上苍老枯槁的乔麦,我的心抽搐了一下。土掌房算是我的第二个衣胞之所,自从我离开母体来到人世,我的一生便和土掌房有了割舍不断的联系,在饥饿、寒冷和贫困交织的童年时光,我的人生和土掌房交织出无数个漫长的春夏秋冬。现在,我的灵魂和躯壳终于回到了童年的土掌房中,虽然我知道这种回归已经不可能永远依附在我的灵魂深处了。我没和这位彝家阿妈搭话,我只是定定地站着,她恬静地看着我。我知道在她心里,我是一位从外而来的客人,我知道城市这个立体空间已经让我变得很苍白很浮华了,我曾经健康红润的脸庞现在已经失去土地的质感,我的衣服时尚但缺少生命的律动。彝家阿妈,我该如何洗去这满身的铅华,让浮华的生命重新回归宁静?
转几个弯,从一个长长的斜坡下去,是乍拉古渡。说是古渡,却没有留下古老时光的痕迹。乍拉古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并不长,但在有记载之前,它确实很早就在发挥渡口的作用了。作为一个优良的天然渡口,乍拉古渡一直起着交通南北、联系两岸的重要作用,是出入江内江外的交通要道。历史上,无论是出于军事方面的考虑,还是出于商道逐利的意图,乍拉古渡都在其中充当着重要的角色。对于曾以官厅为统治中心、地跨三江八里、在历史上存在长达五百年之久的彝族纳楼土司来讲,乍拉渡口显得尤为重要。我眼前的渡口安静,寂寞,只有三三两两的渡客和渔民。渡口码头的右边种了很多芒果树,树冠遮天蔽日,树根深深浸在红河水里,如是闷热的夏天,划只小船到树下避暑,该是一件美妙的事。靠近芒果树的地方,泊着几艘捕鱼的渔船。码头的左边建了些简易的住所,几位傣族阿妈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一些我们听不懂的家常话,沉静的乍拉渡口显现出了一种世俗的家常味。乍拉渡口所显现出的世俗的家常味,是有渊源的。在渡口平静的水面下,曾经有一个古老的傣族村寨,这里曾炊烟袅袅,鸡犬相闻,高大的芒果树、香蕉树、荔枝树、酸角树等热带植物应有尽有,这些果树或成林成片,或遮天蔽日,散落其间的傣家竹楼在绿树丛中若隐若现。这个曾经的傣族村寨,现在沉睡在乍拉渡口的河底深处。当古老的红河犹如一条红色的丝带蜿蜒曲折地从远方奔涌而来,在这里转了一个弯后,奔涌的红河水变得平缓起来。由于河水滞流,水势减缓,河面宽阔,便形成了一个天然的优良渡口。为了拓宽河床,使乍拉渡口更好地发挥其摆渡功能,紧靠渡口而居的傣民被整迁到新建的住房,曾经的傣族村寨也随之永远沉睡在乍拉渡口的河床深处。河岸的浅滩上,被河水冲洗得圆润光溜的鹅卵石躺在银白色的细沙上,一棵经年的酸角树倾斜着身子伫立在水中,累累的酸角果挂了满树。几个渔人已经打鱼归来,小小的渔船上装着满满一篓罗非鱼和几条十多斤重的白鲤鱼。由于是旱季,红河水显得特别温顺,绽放着清澈和碧蓝的光,在阳光下粼粼而动。宽阔的河面,不时有渡轮从对岸驶来,发出突突的沉闷声。渡轮靠岸后,渡客拿了从江外带回来的货物,不紧不慢从渡轮下来,然后朝家的方向而去。也有驾车的司机直接把车驶上渡轮渡到对岸,省去了驾车在红河谷的崇山峻岭中跑来跑去的大把光阴,省时省事又省钱。从古至今,乍拉渡口在交通两岸、促进两地商贸往来方面发挥着的作用是不可小觑的。看着现在风景宜人的乍拉渡口,我总是想起沉睡在水底的那个古老的傣族村庄,寨子里曾经的鸡犬相闻的世俗日子,但河面上不时传来的突突的渡轮声,以及渡轮抵岸后人们卸载货物的景情,又把我的思绪从回忆中一次次拉回来。
才踏上通往苍台的山路,绵绵细雨便来了。薄雾一直如影随形,从车窗外望去,烟雨笼罩下的山谷犹抱琵琶半遮面。耳边一直萦绕着忧伤的加拿大情歌《红河谷》,红河就奔流在这群雾笼罩下的山谷中。雾让整个山谷都湿漉漉的,车到苍台村时,雾更浓了,整个村庄在云遮雾绕中若隐若现。村庄里的雾不似山谷中的雾那般有着女子的温顺,倒像是年青的后生小伙,它们长了长长的脚,在苍台村的土掌房间肆意地奔跑。我才一下车,便和雾撞了个满怀,它鲁莽地撞我一下,之后逃得无影无踪。我走在烟雨中的苍台里,感觉迷路了,一时不知该走向何方,出路究竟在哪里。我只看见成团成团的雾气在我的眼前来了又去,去了又来,我看到的一切随着雾的来去时而清晰时而隐约。村里的路并不好走,和天气一样也是湿漉漉的,并且有些泥泞,我几乎是深一脚浅一脚在村庄里行走的。雾却不管这些,它像长了大大的翅膀,始终以一种飞的姿态在村庄里游来荡去。雾把绵绵细雨也一并带来了,烟雨中的土掌房,应该属于已经凝固了的古典音乐,在不久的将来,这样的音乐将被强劲的的士高和摇滚乐所代替,而我们又有什么理由阻止社会的发展规律在这个村庄里停滞下来呢。
在苍台的一间土掌房里,我看到了毕摩,他是官厅苍台村最具威望的长老。他穿了一身黑绸缎的法衣,头上戴了顶藤和篾混编而成形似斗笠的法帽,左手执一根顶端有人头面的法杖,右手握一卷羊皮制的经书。他坐在那里,嘴微翕着,并没有因为我的闯入而表现出不安。他把传承了几辈的羊皮经书摆在面前的方桌上,然后用右手慢慢翻开,揣摩了一会儿后用手指着经文一字一顿地诵唱起来,神情虔诚庄重,像在举行一场隆重的古老仪式。他念的是一段《哭丧经》,时缓时扬的音调透出一种古老而遥远的音律之美。他的手形色枯萎,像一截枝枯,在经书上随着诵唱的音律上下移动着,历经近一个世纪的岁月与沧桑。他在经文里唱到:那些漂流在外的灵魂啊,不要在外面游荡了,沿着祖先迁徒的路线,回到彝族部落的老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