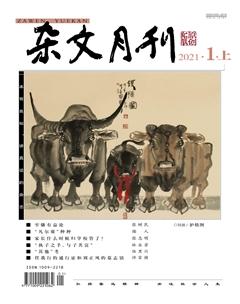窗口
杨闻宇
我们常见的门窗,在悄无声息地变化着。门发展到今天,美观之外,讲究结实、防盗。窗呢?不时听到某项创新是对外展示成果的窗口,这里所说的窗口则属于隐喻,与流传下来的窗口是两码事。
人们起初打窑洞、盖房屋时,置窗于顶部或壁上,为的是通气、透光,后来的车轿、舟船,所设置的窗口才有了朝外窥视的意向。
小时候,我家房屋的窗口朝向东方,面对着开阔的田野。春天的早晨掀开窗子,满眼是麦浪汹涌,波波荡荡,形同瀚海,我们小小的村庄,仿佛是浮在海上的一座孤岛。农家窗底,多为土炕。这类土炕,对于农家小伙子来说,天亮时分的睡眠最为香美。个别小伙儿贪恋早晨的回笼觉,生产队长会从屋外敲着窗棂,大声喊叫:“日头晒红屁股了,你个懒熊,还不下地啊!”
后来,我离开家乡去外地求学,从书本里,在旅途中,才渐渐发觉,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经见广博,对于窗口的接触与感受,并不像小时候农家生活那样的简单,直白。
苏轼的“彩索身轻长趁燕,红窗睡重不闻莺”,描述怀春少女的天真活泼,本性天成;而他在妻子去世10年后,于宦途坎坷、风霜奔走之中写下的“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却是梦里相逢,情怀难叙,这22个简朴平实的家常文字,重温远逝已久、相亲相爱的夫妻生活,自成绝唱。
李商隐是河南沁阳人,旅居巴蜀时,给妻子写了首《夜雨寄北》: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人啊,离乡愈远,情思愈重。秋雨之夜,设想与妻子他日重聚时剪灯夜话,回忆这孤寂而难熬的落寞情景,情思凝重,期望殷切,也是罕有的一曲绝唱……生活里习见的大同小异的窗口,太平凡了,似乎是不值得一提的,可被李商隐移用在这里,妙趣天成。窗口因为被赋予了文化内涵,就连这“西窗”二字,也惹得后人产生出情思绵绵的无限联想。
品读古代诗词里的窗口,翻回头也勾引我重温儿时农村的生活片段。农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岁月是单调的、艰辛的,然而,每当春节来临时,老老少少笑逐颜开,身上的衣裳尽都是里外三新,千门万户洁净明亮的窗纸上,全都剪贴上色彩鲜艳的、象征“人寿年丰”的窗花,精巧雅致而各具特色的喜庆图案,尽是当家女人们巧慧心灵的产物。窗户连襟,窗与门历來是对应着的,这窗花与门口新贴的大红对联交互辉映,闪耀于漫天飞舞的雪花之中,形成天地间浩大质朴、圣洁美好的迎春图画。
常言道,物离乡贵,人离乡贱。而在感情上,人一旦离乡,反倒能迸溅起灼热的珍贵的火花。苏轼、李商隐,俱是在远离故乡而情怀寂寞的时候,才记起了家乡熟稔的窗口。我那村庄,现在已经因为城市化而彻底消失了。步入老年,我在数千里外的异乡回忆起60年前的景象,怀恋的心口仍是热乎乎的。
社会发展迅捷,当今的居住条件大为改观。高楼巍列成阵,居室的窗口也日益开阔,采光透风的功能自不待言。而新闻里所说的某某创新乃是向外展示成果的窗口,这样的窗口自然不同于生活里真实的窗口了。每见到这样的新闻,我便记起杜甫在“安史之乱”后回到成都草堂时的那首七绝: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西岭指成都之西的岷山,东吴泛指行程万里外的江南。同样是普通的门窗,却与那些催成清泪、惊魂孤梦的忆念情境大相径庭,杜甫身在草堂,视通万里,襟怀万类,胸次开阔,思接千载。
尘世中没有绝对静止的事物。寂静的窗口,随着社会发展,逐渐被赋予了新的含意与活力。添进活力的窗口,仿佛更接近于人身上的眼睛。作为眼睛,当今的窗口向外界所展示的,是自身强劲的生机与蓬勃的活力,是善于广取天下之优长,以补己身之所短胸怀,从而让前行的步伐更稳健,也更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