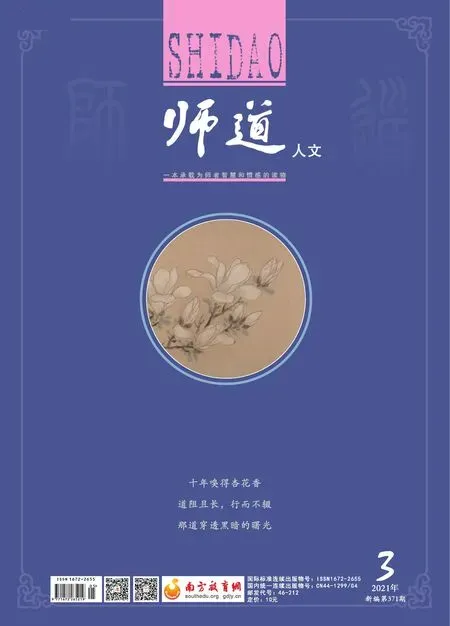迷失在雪中的城市
成旭梅

这个冷夜, 我在远离乡土之地。 没有父亲母亲在身边的年节,总是失去方向。
我走出家门, 去看那些被风吹得迷失了灵魂的道路, 是不是还笃定地停留在生长它们的路基之上。我在我的家里, 我想, 路也应当在他们该待的地方。
可是路, 总把我们带到人群里, 好像路就是他们铺就的。 我们总在他们给我们约定的时间里, 来到那些路的终点, 与他们见面, 说他们想听的话, 带着他们想要看到的我们的样子。
但是并非这世上所有的人, 都渴望走上一条通往人群的路。
卡尔维诺说:
“那个早上是寂静把他叫醒的。打开窗户: 整个城市不见了, 被一页白纸所取代。
电车因下雪而停驶, 马可瓦多只好走路去上班。 沿途, 他自己开辟出他的通路, 感到前所未有的自由畅快。 在市区路上, 人行道与行车道的区别都消失不见了, 车辆不能通行, 而马可瓦多, 虽然每走一步就陷入半截小腿, 雪水也渗入袜子, 但他游走在马路中央, 踩踏着花坛, 任意穿越路口, 东摇西摆地前进。 他是自己的主人。
事实上他的脚步正把他带往每天工作的地方, 等走进大门口, 这位搬运小工惊讶地发现自己站在一成不变的墙内, 仿佛那些让外头世界消失的改变, 独独漏掉了他的公司。 在那等着他的, 是一枝铁锹。
铲雪并不是一件轻松的差事,尤其对那些没吃饱的人而言, 可是马可瓦多却觉得雪就像一位朋友,撤消了禁锢他生命的牢笼。 于是他发奋工作, 一大铲一大铲的雪花由人行道上飞向路中央。”
卡尔维诺浪漫昏了头, 一个连吃饱都成问题的实利社会里底层——准确地说是体力工作者, 一个搬运小工——决计难有这样高迈的境界。 管子很诚恳地告知我们,“仓廪实而知礼节, 衣食足而知荣辱”, 这才是人性真实的逻辑。
卡尔维诺当然知道这个逻辑,于是他把一个正常人拉到了我们面前:
“失业的西吉斯蒙多对雪也充满了感激, 他在那天早晨被市政府征召成为铲雪工人, 终于眼前有了几天确定的工作。 不过他的这种感情, 不同于马可瓦多模糊美丽的幻想, 而是精确的计算, 要清出这么多平方米的面积就必须铲掉多少平方米的雪; 他把目标锁定在能够成为小队队长, 然后——这个志向是一个秘密——再直上青云。”
我走在路上, 看到西吉斯蒙多在走, 来来回回地测算这条路——也是他今后的人生之路。 此时此刻大马路归他管——“管” 这个词是非常奇妙的, 带了一种权力意味在里面的词, 都是非常奇妙的, 它让西吉斯蒙多刹那间一扫那数月以来因为失业而黯沉的晦气, 春风骀荡起来。
在这条铺满了雪的路上, 卡尔维诺比对着精神力的 “强” 与“弱”: 在同样的困境里——贫困、饥寒、 职业危机、 价值理性等——马可瓦多与西吉斯蒙多谁更不幸?谁更强大?
这是一个后修辞时代的隐喻性文本。 以互联网的出现为标志的现代传播技术革命正在引发一场重大的修辞变革: 修辞主体全民化和交往形式网络化; 背后潜藏的, 是运作方式、 传输手段、 修辞语境和修辞心理等修辞的全方位深层次变革——这种变革, 继后工业时代之后, 将现代人置于 “群体性孤独”之中。 特克尔如是解释这种富于修辞意味的 “群体性孤独” 的特性:“我们似乎一直致力于赋予物体人性特质, 同时却一直满足于用物化的方式看待彼此。” 是的, 卡尔维诺正是逼迫我们直视物化世界中的人的根本处境: 当物质从我们身边抽离, 当我们一无所有, 当世界给我们以寂静冰冷, 我们将何去何从?
然而, 我们无非教书而已, 教书也者, 除却谋生部分的意义, 本身就是一个与物质化相去甚远的概念; 而且, 世界那么大, 会放不下一张平静书桌?
然而我们早已步入时代的另外一个陷阱。 这个陷阱用另外一种方式将 “教师” 修辞化、 神圣化,“高举心中的圣旗, 走向罪恶的深渊” (伏尔泰), 从而将具体的“个” ——个体的特殊性、 自由精神、 独立人格等——迫离, 使面向现代性教师群体的话语场成为的“奴役之路” (哈耶克)。 而在这个“‘我们联网’ 和 ‘情绪 联 网’”(徐贲) 的互联网时代, 在 “社会证明” 的驱使下, 人们将 “标签”奉为圭臬, 以绝对怀疑或绝对肯定的姿态奉行网络时代的犬儒主义,对被标签者投以盲目的期待——继之以未能达成这群体期待的不满,由此, 对教师职业理想价值的完美主义预期本质上成为修辞化 (异化) 教师的过程; 甚至成为滋生矛盾与阉割人性的暴力场域。
关于工业社会中非资本群体的存在状态的问题, 早在本雅明的笔下得到过意味深长的阐释。 在 《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 里,本雅明对第二帝国时期的巴黎 “渐次熄灭的煤气灯、 把人固定在土地上的住房牌号、 日渐堕落成商品生产者的专栏作家” 发出挽歌式的哀叹。 面对这种现代社会的异化和新型的奴役, 他深刻地指出: “当波德莱尔谈到 ‘大城市的宗教般的陶醉’ 状态时, 商品可能就是这种状态的莫可名状的主体。” 而 “一个人, 他越意识到那种生产制度强加给他的生活方式, 他就越使自己无产化, 就越紧地被冰冷的商品经济攫住。 一切商品的魅力是以市场为基础的, 这些魅力也变成了同样强权的手段。”
“文人市场” 的生活方式, 本雅明这样来命名一个商品化社会之下的非资本群体的基本生存境况。他指出: “文人的真实处境: 他们像游手好闲之徒一样逛进市场, 似乎只为四处瞧瞧, 实际上, 却是想找一个买主; 甚至, 经常把某种人, 首先是他自己, 比作娼妓。”
这种在商品化与神圣化的撕裂关系中存在的状况, 也是今天教师最真实的生存状况。 今天, 教师这个资本世界之外的群体, 正经受着尊严的双重考量: 一方面是世俗生存的必要的资源, 那些俗世生活的名与利; 另一方而是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内在道德。 这正是本雅明通过对波德莱尔作品的具体分析所着重研究的价值: 非资本群体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特殊的生存方式与生活态度。
本雅明把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诗人 (文人) 称作 “游手好闲者”(或曰 “城市闲逛者”)。 这种命名意在指出: 真正的文人是那种虽然生活在文字的世界里, 但却不去职业性地著书撰文, 而且往往与秩序、 规范格格不入的自由作家。 在拥挤不堪的人群中, 在深陷的最堕落的感官世界里, 漫步、 张望和沉思成了他们的生活方式, 这种方式将他们带入一片充满神性和灵魂气息的理想境界, 并可能由此引发出那许许多多思想深邃的寓言和尖锐、 犀利的文字。 他们力求在一切方面保持 “自由然而孤独” 的权利, 力求以自己冷静的思考来充当社会的良心。
但是, 人很难走出万千人群共在的那条路, 那条已然泥泞不堪的路, 以精确的计算, 以直上青云志向, 如同西吉斯蒙多, 也如同鲁迅笔下的豆腐西施。
我常在想中国古代文人们那些跟 “路” 相关的隐喻, 充满了革命性与破坏性意味的那些修辞。 我在想他们是经历了怎样一个生命的过程才会写下那些在后世引起许多共情的文字。 比如柳宗元要去那 “千山鸟飞绝, 万径人踪灭” 的 “万千孤独” 之境, 去到水的中央 “独钓寒江雪”, 究竟他的身体多能承受而他的心对这尘世又有多冷; 比如李白 “蜀道之难, 难于上青天” 中的书写张力, 那来自于与神话世界的比对的巨大空间所产生的伟力所投射出的个体的渺茫与渺小, 是那样森森的叫人刺痛; 比如苏轼 “人生到处知何似, 应似飞鸿踏雪泥”慨叹, 充满了对生命历程的怀疑和生命偶然性的觳觫, 最终在赤壁找到了“唯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这“吾与子之所共适” 的万古存在。他们的路, 都铺着或深或浅的雪。
当人间无路可走, “登高” 就成为一种 “姑且” 的行为的修辞。谁人不知 “高处不胜寒”? 但东坡仍欲 “乘风归去”; “万里悲秋常作客”, 缘何不往那温暖灯火的家里取一取暖, 杜子美却要挣扎着“百年多病” 之身 “独登台”; 辛幼安那一句 “少年不识愁滋味, 爱上层楼。 爱上层楼, 为赋新词强说愁” 何尝不是经年沧桑历尽滋味之后的笑谈——“登高” 原出于人间不能承受之痛, 故要立上高台让自己看清自己; 让自己从人群拥挤的囹圄之地走出, 站在天地之间, 自由呼吸: 这些, 哪里是年轻的心灵所能感同身受的啊。 毛喻原今说“精神在高处”, 或可与那深远时间里的 “登高” 互文。
这是一种深重的无奈与慨叹:拥有着飞翔于真正的自由之境的心灵, 但却无法真正 “飞去”。
我终于明白: 这一席的人间烟火呵, 明灭之间, 才是盛宴!
我也终于明白, 为何木心将这一路走成了 “冷冷清清的风风火火”。
这不是 “姑且”, 而是直面,是 “面向实事本身” (胡塞尔) 真诚地想与做。 这大约就是钱理群先生所讲述的民国时期的那一群知识分子: “那一代人, 无论做学问、讲课、 做事情, 都是把自己的生命投入进去的。 这样, 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会使他自身的生命不断获得新生和升华, 从中体会、体验到自我生命的意义、 价值和欢乐。”
于是又回到开头卡尔维诺的那个问题: 我们是更像马可瓦多还是更像西吉斯蒙多。 卡尔维诺的意思很明白, 我们普遍的生态, 不是马可瓦多, 就是西吉斯蒙多, 没有第三选项; 而作为一种形式即内容的隐喻性的写作, 卡尔维诺不再将西吉斯蒙多探讨下去这叙事的断裂,本身即宣告对其存在的价值的否定, 及对马可瓦多这另一种 “城市闲逛者” 的命运的关注。 通过对马可瓦多的紧密关注, 卡尔维诺呈示了 “人在现代性的逼仄空间里如何自处” 的存在之问, 并让我们看到马可瓦多身上所蕴涵着的无穷的可能性 (诗性): 物质的有与无, 并不能决定我们的整个世界。
我突然明白, 在这个被风吹黑了天地不辨牛马的无边无际的世界里, 卡尔维诺其实告诉我们的, 是一个关于空间与时间的故事: 空间是眼之所限; 而时间, 则是无可限之心灵。 “人生的所有行走, 无非是走成一个有趣的魂灵。” (钱钟书) 空间 (物质) 形式的多变与偶然, 无非取决于你在时间里历练成的美丽心灵。
你看那一个从城市 (物质空间) 的格式化里叛逃的张岱, 有着多么传奇而趣味盎然的一生: 以富贵之身而降世, 以江淹之才而落第, 以仕宦之家而向穷, 以亡国之名而流离——可谓半世凄凉。 但中国古代的士人成就文化的基本轨迹相类, 在褪去前半生的浮华之后,张岱终于有了空寂的时间, 去做实利社会看不上的 “无益之事”。 后半世, 张岱隐居四明山中, 坚守贫困, 潜心著述, 在破旧的茅草屋中写下 《陶庵梦忆》, 写下 《夜航船》, 写下他对一蔬一饭的深情切意; 康熙四年撰写 《自为墓志铭》,向死而生; 于康熙二十八年与世长辞, 享年约九十三岁。 张岱在功名成空、 富贵如梦的安静生命中, 努力留住了那一点人间烟火的暖意。
那个写 《闲情偶寄》 的李渔与张岱相类, 也是出身于富庶之家,也是遭遇了一个烽烟突起的时代,也同样并不借势谋生, 同样走上一条 “人间大隐” 之道。 由此, 李渔创立了较为完善的戏剧理论体系,成为休闲文化的倡导者、 文化产业的先行者。 李渔在给礼部尚书龚芝麓的信中说: “庙堂智虑, 百无一能; 泉石经纶, 则绰有余裕……托之空言, 稍舒蓄积。” 足见其文艺修养和生活情趣。
真喜欢走在中国古时间里的士人们的这种熨帖而简单的生活风格, 他们总是把一个又一个迷失于雪夜望不见来路也分辨不清去路的怅惘幽昧痛得喘不过气来的故事讲述得干净而美好——黑布鞋, 白布里, 简简单单, 干干净净; 走在那鞋里的, 却一定是个满腹经纶的书生。
——也是, 在这样一个 “我们生活在众声喧哗的第一人称叙述的现实中, 我们从四面八方听到多音杂音” (托卡尔丘克) 的时代,“若复不为无益之事, 则安能悦有涯之生” (张彦远 《历代名画记》)。
也是在这个雪的季节的那一条条奔向迷茫的雪路上, 我看到我的父亲母亲, 在完全丧失了方向的泥泞里, 坚定又清晰地把童年的我驮在自行车上, 走向一个又一个的村庄, 去给我的祖辈长辈们叩头拜年。 他们不知道路在何方, 只默默地认为那就是应该的路向, 最后,他们总能把路走到温暖的地方……他们并不知道, 当年伴我走过的那一条条雪路, 那一个寂静而温暖的自由世界, 引我走成了 “老师”。
——以短篇小说集《马可瓦多》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