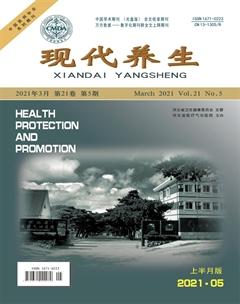器识与文人
鲍安顺

器识,指人的器度与识鉴。
丰子恺推崇恩师李叔同,继承其思想精髓并总结出一个观点:“先器识而后文艺。”这种文艺观,是“首重人格修養,次重文艺学习”。换句话说,就是要做一个好文艺家,必先做一个好人。事实上,李叔同平日致力于演剧、绘画、音乐、文学等文艺修养,同时更致力于器识修养。他认为一个文艺家倘没有器识,无论技术何等精通熟练,亦不足道。所以他常劝诫人:“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
唐代刘晏总结孔子等人的教育思想时明确提出:“士先器识,而后文艺。”常言说:“为文先为人”“人品决定文品”“文如其人”。说的也正是人品至上,文品与文章次之的道理。学者王国维总结说,三代以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人,如果没有文学天才,就凭着他们的人格力量,也足以流芳千古。可以,世界上如果没有高尚伟大的人格,就不会有高尚伟大的文学者。
司马迁著书《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被鲁迅称颂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可是,他为了写成此书,以极大的勇气选择了被视为奇耻大辱的宫刑,隐忍苟活。在太始元年汉武帝改元大赦天下时,时年50岁的司马迁出狱后任中书令。中书令是掌管宫里诏诰答表等机密文书,设在宫内,由太监担任。实际上,司马迁接受了这个职务,等于向世人宣布,他就是个太监。汉武帝是在继续污辱他。后来,司马迁在家中写《史记》时,有人在他家门上贴了大字报侮辱他:“鱼跃龙门变成龙,还看鲤鱼雌与雄。假若非雄也非雌,跃上龙门也非龙。”遭此侮辱,司马迁对他的朋友说,不进宫怎知宫廷秘史?不和帝王将相打交道,怎知他们灵魂善恶?不应招,史书又怎生去写成?
对文人而言,器识就是看他们的性情、胸怀,如何宽广博大,与众不同。据说张居正13岁时考举人时,本来是通过的,可是主考官不让其中举人。原因是,主考是为了保护他,不能让他养成少年得志的轻狂自大,将来难成大器。因此,我想起了唐伯虎与蒲松龄,他们两人都是少年得志,春风得意,却在后来的仕途误入了歧途。虽然一个成了书画天才,另一个成了中国文坛的文学泰斗,那是发挥了才情的文艺之幸,几乎与器识无关。
伟人毛泽东谈古代文人参政言政时,也倡导器识为先。他读《明史》时,颇为欣赏教书先生朱升,将他在朱元璋召问时务时建议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策略,于1972年改提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现实战略。毛泽东读宋代一些散文大家的史论和政论文章,评价普遍不高。即使对政治改革家欧阳修也一样,在读《朋党论》时的批注是“似是而非”。欧阳修在《为君难论》中提出历史上的一些失败现象,原因在于“乐用新进,忽弃老成”。毛泽东却说,看什么新进,况且老成之人开始的时候皆新进。毛泽东在读曾巩的《唐论》时批注“此文什么也没有说”,读苏洵的《谏论》认为是“空话连篇”、“皆书人欺人之谈”,读苏洵的《六国论》中提出六国如果联合起来“并力向西”就不会为秦国所灭的议论,便批注“此论未必然”,因为“凡势强力敌之联军,罕有成功者”。
毛泽东爱读古代文人史论、政论文章,却不喜欢他们抽象说教、言不及义的书生意气。可以说,书生意气和政治器识之间,毕竟隔着一道深不可逾的心灵鸿沟。 编辑:修远 xdyszzsb@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