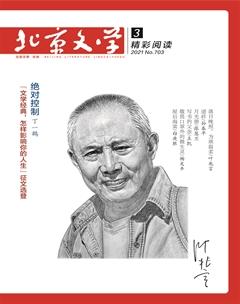美味佳肴(散文)
彭喜媛
一
我二十岁那年,得了场急病。父亲不知从哪儿打听到一个专治此病的医师。
翌日清早,他便带我去相隔三十里远的一个镇上,逢人就打听那个医师的诊所。三十元钱一包的中草药,捡了七包。我心疼得要命,平时一分钱恨不能掰作两分钱花的父亲,将钞票叠得整整齐齐,双手恭恭敬敬地递给那个须眉皆白的老医师。那神情,与寺庙佛陀脚下虔诚的供奉者无二。
回家后,风尘仆仆的父亲脸都顾不上擦一把,平日很少进厨房的他,亲自为我熬药。我见他坐在灶膛前的蚂拐凳上,腿长腰长的他,虾躬样地屈着膝,抻着颈,两眼不错珠地盯着药罐子。为了怕药汁溢出来,鼓着腮帮子,一口接一口地吹气,半个小时后,将二两切成指头般粗的生猪油放进去再熬……一个时辰后,父亲便大功告成似的,叫我喝药。
我敢打赌,这世上,再没有比这种更难吃的中草药了!一层厚厚的,浓得化不开的油腥子堆积在药汤上,闻着那味儿,人都要腻歪了。
我心里一百个不情愿,磨蹭了半天都不愿张口。父亲在一旁温和地催,好崽,快喝了吧,良药苦口利于病,喝了病就好了……
我心里一暖,倏忽感觉病去了几分。病中真好,全家人都让着你。可以开小灶,可以吃零嘴儿,可以在父母面前撒娇。不管你几岁,病中的你,在父母眼里都是需要精心呵护的。孩子病了,父母比自己得病还要着急上火。他们宁愿自己病痛,也不愿意孩子有一丝一毫的闪失。自从不穿开裆裤后,父亲便呼我名字,从不叫“满崽”了。人活一百岁,都愿自己是父母掌心里的宝。
写到这儿,不禁想起一件趣事。我大姐的儿子三岁那年犯了个小错误,大姐倒拿鸡毛掸子要抽小家伙的屁股。谁知小家伙猴子样钻进床底下,大姐握着鸡毛掸子左挨不着,右捞不着,最后无可奈何地说,超,快出来吧,出来就不打你了。小家伙却躲在床底下提要求,你为什么不叫我“满崽”呢?叫我“满崽”就出来。
也真是奇了,服完那几服中药,我的病竟奇迹般好转起来,只是身子尚弱。
二
记得那是一个阳光慵懒的下午,我在卧室门外葡萄架下的竹椅上午休,醒来睁开眼时,发现父亲站在我身旁慈爱地瞧着我,神秘地朝我笑笑说,到厨房来……
众所公认,四姊妹当中,我是秉承父亲遗传因素最多的一个。
我以为父亲要同我讲一件什么悄悄事。一言不发地跟进厨房,母亲正在灶台上收拾,水缸木桌上墩着碗堆得冒尖的燉猪肚。
要知道,那个年代的农村,即便在大年三十晚上,平常人家的年夜饭不一定看得见猪肚这道美味佳肴。这不年不节的,父亲突然炖了猪肚子来改善伙食,我摸起了后脑勺。
快吃!父亲压低声音命令我。
我吃?!我拿眼睛瞟瞟门外,用手指指着自个儿鼻尖。
父亲从灶膛前端起那条蚂拐凳,用手掌在上面抹了抹,放在水缸桌边,又从筷子筒里抽了双筷子塞到我手里,朝我使了个眼色,按着我的肩膀坐下,严肃地说,你大病刚愈,身子弱,需要补补,听话,莫让了,快趁热吃!
母亲也走拢来劝我,你爸专门做给你一个人吃的,他在我面前哝了几回,心疼你瘦了……
举箸在手,感觉重若千斤!我是个无用之人,病中的我,拖累了全家,平日里享受父母贴心巴肉的疼爱,已令人柔肠百结,没料到父亲还为我如此破费。
也许,对于富贵人家来说,别说一个猪肚,就是一头全猪全羊都不屑一提,可于我们家当时而言,那是前所未有的奢侈啊!
由于我们家建起了红砖楼房,外头还欠着债。为了补贴家用,父亲凌晨五点钟起床,挑担箩筐,打着手电筒,去我们乡圩扯猪腿收猪皮子再去县城卖,从中赚几块钱差价。有时乡圩没货了,便要再步行二十里路到镇上去,为了节约一个铜板,父亲通常舍不得吃早点。为了节约五毛钱车费,父亲一根木扁担担着百八十斤的货物,一步一步吃力地行走在崎岖的山路上。右肩痛了,换到左肩,左肩红了再换到右肩。贴心的白棉背心常常是湿了又干,干了又湿。一天累死累活下来还挣不到几块钱,回来时箩筐里便多了些洗衣粉、肥皂之类的日常用品。如果多了一袋苹果或梨子之类的水果,表明那天生意稍微好一点儿。长年累月下来,父亲的双肩被扁担压得凹进去,脚板心长了个厚厚的鸡眼丁,却从来舍不得花一分钱去治疗。有一次疼得难受,叫母亲拿火柴来烧,母亲素来胆小,划燃火柴后怎么也下不了手,他一把夺过来,将火柴头往鸡眼上一戳,屋里顿时漫起一股焦煳味……
多美的猪肚汤啊!
肚片脆而嫩,汤汁鲜而甜。知我怕油腻,这么大一碗肚片居然连一片指甲大的肥油都没有,就在我酣然午睡时,父母在厨房是如何紧张忙碌,一丝不苟地煲这一锅“爱心汤”哦!
见我动了筷子,父亲像卸下一副石磨,搓了把手,走出厨房,轻轻咳嗽一声,坐下来开始卷他的 “喇叭筒” 旱烟。
三
儿时,在饭桌上,父亲讲了个故事,说的是一对朋友,为了见证友谊,甲割了自己一只耳朵。乙呢,拔了自己一根头发……
若干年后,我私下认为,总觉父母就是那个故事中的甲,做子女的便是乙。
然而,我这个做女儿的甚至还来不及扯根头发表示,上天已不给我什么机会了。
2008年初冬的一天早上,我撇下一切事务,从菜市场买了一只乳鸽回家,一向不擅厨事的我,胡乱地抹了些姜丝、葱末,手忙脚乱地将乳鸽清蒸了,装进保温壶,骑上小电驴来到本市一家肿瘤医院。
朝阳打在我身上,我的心却沉浸在冰窖里!
住院部转弯抹角的,每走一步我都腿如灌铅。
有几个病人无声无息地躺在院子里的长椅上、草丛中,闭着眼佯寐。他们趁被送进冰冷的土地深处前,多一点儿享受这温暖的跳动着的阳光。那是对生的渴望,对死神的恐惧……
这时,从化疗室迎面走出来两个病号,脚步踉跄,骨瘦如柴,面部用红粗笔画了个醒目的“十”字,头上因化疗而“寸草不生”。
死亡的气息在这个寂静而阴森的院落里飘荡……我的手臂上顿时耸起一层鸡皮疙瘩。
我疾步走进503病房,父亲穿着病号服,侧身坐在病榻上,正同隔壁病友聊天,见我来了,他清癯的脸颊立刻绽开了笑容,就连眼睛也似乎亮了一下。
爸,给你蒸了点东西,也不知弄什么给你吃。
哎呀,你这个崽,天天围着我转,自己的事忙不过来,还天天换花样给我炖补品,水里游的,天上飞的,都弄给爸爸吃了。
母亲正在洗手间洗衣服,走出来拧开保温桶的盖子,默默递到父亲手上……
我注意到,病中的父亲,精神尚好,倒是母亲,眼眶都凹进去了!自父亲住院以来,日夜守护,从未要做儿女的陪过一次床!
“哎呀,这乳鸽好香!我这哪儿是来住院,分明就是来疗养的嘛!”
父亲捧着保温桶,深深地嗅着,然后头向后仰,微眯了眼感叹。
我鼻子一酸,转过脸去,面朝窗外。父亲一辈子卷的是“喇叭筒” ,喝的是劣质酒,死神早就窥视他这种没有生活质量的人了,但他一直“负案在逃”,不肯进医院请医师“降妖伏魔”,逃呀逃呀,逃到六十五岁那年,终于筋疲力尽,死神不费吹灰之力逮捕了他。
忆起十七年前父亲精心给我烹制的“爱心汤”,足以温暖我一生一世!
如果“美味佳肴”能延长父亲的生命,我愿意为他做十次、百次……
可是,父亲当年给予我的是再生,我送给父亲的却是向死。
写到这儿时,手机音乐刚好响起满文军唱的《懂你》:“你静静地离去……在我忽然想你的夜里……把爱全给了我,把世界给了我……从此不知你心中的苦与乐……”行文中,我几度伏案,泪崩……
责任编辑 师力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