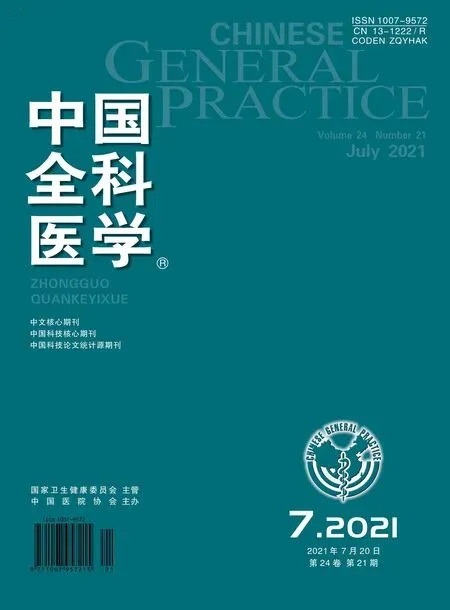新型生物制剂在炎症性肠病中的临床应用:现状与未来
王英德
在过去的十余年里,抗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制剂等生物制剂在炎症性肠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IBD)治疗方面的应用逐年增多。临床研究表明,抗TNF-α制剂治疗克罗恩病(Crohn's disease,CD)的4周临床应答率为64%,黏膜愈合率为33%[1],提示抗TNF-α制剂治疗CD可以获得较高的临床应答率与黏膜愈合率。然而,也有研究表明,约1/3的CD患者采用抗TNF-α制剂治疗后会出现原发性[2]和继发失应答[3-4]。此外,抗TNF-α制剂还能够增加患者罹患机会性感染(如肺结核)、恶性肿瘤(如非黑素瘤皮肤癌)等不良事件的风险[5-7]。因此,抗TNF-α制剂的临床应用存在一定局限性。
随着新型生物制剂不断涌现,IBD的治疗进入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生物制剂时代。目前,国内外用于治疗IBD的新型生物制剂主要包括抗黏附分子制剂、抗白介素12/23因子制剂及JAK抑制剂等。新型生物制剂具有疗效好、安全性高、给药方便等优点。近年来,我国相关部门陆续批准了多个新型生物制剂治疗IBD的适应证,国内外相关指南亦以较高证据等级推荐其用于IBD的一线或二线治疗。本文就包括抗黏附分子制剂、抗白介素12/23因子制剂及JAK抑制剂在内的新型生物制剂在IBD中的应用现状、作用机制、疗效、安全性及应用前景进行评述,以期为新型生物制剂在IBD患者中的规范、合理应用提供参考。
本文要点:
自从2006年首个生物制剂——抗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制剂英夫利昔单抗在我国获批用于治疗克罗恩病(CD),国内炎症性肠病(IBD)患者临床缓解率、黏膜愈合率均明显提高,但在治疗过程中患者继发性失应答率及机会性感染、恶性肿瘤等不良事件发生风险升高,临床应用存在一定局限性。
随着新型生物制剂陆续在国内获批上市,IBD的治疗进入到生物制剂时代。维得利珠单抗是唯一具有肠道高选择性的新型生物制剂,可作为包括溃疡性结肠炎(UC)和CD在内的中重度IBD患者的一线治疗药物,并处于新型生物制剂“安全金字塔”的顶层;乌司奴单抗起效快、安全性高,可作为中重度CD患者尤其是伴有肠外表现及全身表现的活动期CD患者的一线治疗药物,且给药方式为首剂静脉滴注、之后皮下注射,有利于增加患者长期用药依从性;JAK-1抑制剂托法替布为口服小分子制剂,对于UC也有较好疗效,但在国内尚未获批上市,而由于其可增加患者血栓栓塞症及疱疹病毒感染发生风险,因此国外指南仅推荐其作为UC患者的二线治疗药物。
可以预见,随着国内用药经验不断增加及药物价格不断下调,新型生物制剂在临床上将被广泛应用,甚至会取代传统治疗药物而成为IBD药物治疗的主体。
1 新型生物制剂在IBD中的应用现状
1.1 抗黏附分子制剂 抗黏附分子制剂可特异性地与淋巴细胞表达的整合素结合并阻断其与黏膜血管地址素细胞黏附分子1(mucosal addressin cellular adhesion molecule-1,MAdCAM-1)相互作用,进而阻止淋巴细胞从血液向炎症组织迁移和归巢,最终达到抑制肠道炎症的目的[3]。维得利珠单抗是抗黏附分子制剂的代表药物,具有肠道专一性,能够特异性拮抗肠道α4β7整合素异源二聚体,但其起效较为缓慢,达到临床应答的时间至少为2周。FEAGAN等[8]研究结果显示,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UC)患者采用维得利珠单抗治疗第6周临床缓解率为47.1%,黏膜愈合率为40.9%;SANDBRORN等[9]研究结果显示, CD患者采用维得利珠单抗治疗第6周临床缓解率为14.5%。上述两个临床研究表明,维得利珠单抗治疗IBD起效较慢,其原因可能与维得利珠单抗的作用机制有关:维得利珠单抗虽可特异性地结合α4β7整合素异源二聚体[10-11],但作用靶点为炎性反应上游信号通路,对已经归巢的淋巴细胞及其分泌的细胞因子无抑制作用,因此无法在短期内发挥抗炎作用。然而,也正是因为上述作用机制,才使得维得利珠单抗的抗炎作用较为持久。此外,维得利珠单抗是唯一具有肠道高选择性的新型生物制剂,对于病变局限于肠道的中重度IBD患者具有更好的临床治疗效果,且诱发机会性感染的风险极低。
FEAGAN等[12]研究结果显示,既往未接受过抗TNF-α制剂治疗的UC患者使用维得利珠单抗和安慰剂第6周临床应答率分别为53.1%和26.3%〔相对危险度(RR)=2.0,95%CI(1.3,3.0)〕,第52周临床缓解率分别为46.9%和19.0%〔RR=2.5, 95%CI(1.5,4.0)〕;经抗TNF-α制剂治疗失败的UC患者使用维得利珠单抗和安慰剂第6周临床应答率分别为39.0%和20.6%〔RR=1.9,95%CI(1.1,3.2)〕,第52周临床缓解率分别为36.1%和5.3%〔RR=6.6,95%CI(1.7,26.5)〕。上述研究结果提示维得利珠单抗对于经抗TNF-α制剂治疗失败的UC患者仍有效,且既往未接受过抗TNF-α制剂治疗的UC患者短期临床应答率及长期缓解率明显高于经抗TNF-α制剂治疗失败者。
在安全性方面,维得利珠单抗处于新型生物制剂“安全金字塔”的顶层。COLOMBEL等[13]通过综合分析6项临床研究发现,采用维得利珠单抗治疗的2 380例IBD患者在用药期间及52周随访过程中仅18例(<0.1%)发生恶性肿瘤,发生梭状芽孢杆菌感染、脓毒血症、肺结核等严重感染者占比亦很低(约为0.6%)。
总之,维得利珠单抗作用持久、安全性高,国内外相关专家共识/意见均推荐其作为治疗IBD的一线药物,而最新的欧洲克罗恩病和结肠炎组织(European Cron's and Colitis Organisation,ECCO)及美国胃肠病学会(American College of Gastroenterology,ACG)指南均推荐其作为治疗中重度IBD的一线药物。
1.2 抗白介素12/23因子制剂 研究表明,白介素12和白介素23不仅存在于肠黏膜组织,而且存在于全身多个器官系统,并能够通过刺激辅助性T细胞(Th)1和Th17细胞增殖而发挥促炎作用[14]。乌司奴单抗是抗白介素12/23因子制剂的代表药物,能够阻断白介素12和白介素23的生物学功能。此外,由于乌司奴单抗对肠道及肠外炎性反应均具有抑制作用,因此其对伴有肠外及全身表现的中重度CD患者的治疗效果优于其他新型生物制剂。FEAGAN等[15]进行的UNITI-1研究结果显示,741例对生物制剂失应答或出现不良反应的中重度CD患者使用不同剂量乌司奴单抗(130 mg/kg或6 mg/kg)治疗第6周临床应答率分别为34.3%、33.7%,均明显高于使用安慰剂者(21.5%)(P≤0.003);UNITI-2研究结果显示,628例经传统治疗药物(激素、免疫抑制剂)治疗失败或出现不良反应的中重度CD患者使用不同剂量乌司奴单抗(130 mg/kg或6 mg/kg)治疗第6周临床应答率分别为51.7%、55.5%,亦均明显高于使用安慰剂者(28.7%)(P<0.001)。LEE等[16]研究表明,23%的CD合并肛瘘患者在使用乌司奴单抗治疗1年内肛瘘愈合。
SANDBORN等[17]研究结果显示,儿童及青年CD患者使用乌司奴单抗治疗36周期间严重不良反应发生率为17.1%,与使用安慰剂者严重不良反应发生率相似。BAR-GIL SHITRIT等[18]通过为期24周的随访发现,106例CD患者使用乌司奴单抗治疗期间不良反应发生率仅为2.8%,提示乌司奴单抗安全性亦很高。
乌司奴单抗起效快、安全性高,除可作为中重度CD患者尤其是伴有肠外表现及全身表现的活动期CD患者的一线治疗药物外,也可作为其他新型生物制剂治疗效果不佳时的转换治疗药物。荷兰的一项前瞻性临床试验结果显示,经维得利珠单抗治疗失败的中重度CD患者转用乌司奴单抗治疗第52周临床缓解率为46%,明显高于使用维得利珠单抗者(27%)(P=0.004),提示经维得利珠单抗治疗失败的中重度CD患者转用乌司奴单抗的疗效可能更优[19]。
一项随机、双盲、Ⅲ期临床试验共纳入961例中重度UC患者以评估乌司奴单抗诱导和维持治疗中重度UC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结果显示:不同剂量乌司奴单抗(130 mg/kg或6 mg/kg)诱导治疗(8周)的临床应答率分别为51.3%、61.8%,明显高于使用安慰剂者(31.3%)(P<0.001);在维持治疗阶段,使用乌司奴单抗(90 mg/12周或90 mg/8周)第52周患者临床缓解率分别为38.4%、43.8%,亦明显高于使用安慰剂者(24.0%)(P=0.002、<0.001),证实了乌司奴单抗治疗中重度UC的有效性[20]。一项真实世界研究发现,采用乌司奴单抗进行挽救治疗的19例难治性UC患者中10例达到临床缓解标准[21]。因此,乌司奴单抗可作为伴有肠外表现及全身表现的IBD 患者的首选治疗药物,也可作为经其他新型生物制剂治疗失败的IBD患者的挽救治疗药物。
需要指出的是,乌司奴单抗的给药方式为首剂静脉滴注、之后皮下注射,有利于增加患者长期用药依从性。目前我国批准的乌司奴单抗的适应证仅为CD,相信随着临床研究的不断深入,乌司奴单抗在不久的将来亦能获批用于治疗UC。
1.3 JAK抑制剂 JAK共有4种亚型,即JAK-1、JAK-2、JAK-3、酪氨酸激酶2(TYK-2)。JAK抑制剂是一种全新的小分子口服制剂,可通过阻断细胞内炎症通路而发挥抗炎作用[22];严格意义上讲,JAK抑制剂不属于生物制剂范畴,但学界习惯将JAK抑制剂与新型生物制剂一起探讨。目前上市的JAK抑制剂主要包括托法替布和非戈替尼,其中托法替布主要抑制JAK-1/JAK-3,而非戈替尼则选择性抑制JAK-1[23-24]。关于托法替布的Ⅲ期临床试验结果显示,1 139例中重度UC患者使用托法替布(10 mg/次,2次/d)治疗第8周临床缓解率为18.5%,明显高于使用安慰剂者(8.2%)(P=0.007);在维持治疗阶段,随机给予对托法替布有临床应答的593例中重度UC患者两种剂量托法替布(5 mg/次,2次/d或10 mg/次,2次/d)治疗44周,结果显示其临床缓解率分别为40.6%、34.3%,均明显高于使用安慰剂者(11.1%)(P<0.001)[25]。
WINTHROP等[26]根据托法替布剂量将1 157例UC患者分为高剂量组(10 mg/次,2次/d,n=196)和低剂量组(5 mg/次,2次/d,n=198)并分析其治疗1年内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结果显示:高剂量组患者中出现带状疱疹者占比为5.1%(10/196)〔每100例患者年带状疱疹发病率(IR)=6.64,95%CI(3.19,12.22)〕,明显高于低剂量组的1.5%(3/198)〔IR=2.05,95%CI(0.42,6.00)〕和安慰剂组的0.5%〔IR=0.97,95%CI(0.02,5.42)〕。此外,托法替布用以治疗UC患者还存在发生严重感染、血栓栓塞、心血管事件、胃肠道穿孔、血脂异常及恶性肿瘤等风险[26-27]。由上可知,虽然托法替布对中重度UC有一定治疗效果,但不良反应较多,且不良反应发生率与其剂量呈正相关,因此不建议将其作为UC的一线治疗药物。另外,已有研究证实JAK抑制剂对CD疗效不佳[28],但JAK-1选择性抑制剂非戈替尼对CD可能有一定疗效[29]。
目前,部分国家已批准托法替布用于治疗UC,但我国尚未批准JAK抑制剂用于治疗IBD。因此,JAK抑制剂治疗IBD患者的临床疗效还需进一步深入研究。就IBD患者依从性而言,托法替布和非戈替尼均为新型小分子口服生物制剂,是需长期维持治疗患者较为方便的选择。
1.4 其他新型生物制剂 研究表明,SMAD7蛋白可通过与转化生长因子β1(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1,TGF-β1)结合而抑制下游炎症通路、引发肠道炎症,因此,肠道炎症的发生也可能与SMAD7基因过表达有关[30]。孟格森(Mongersen)是一种新型反义小链寡核苷酸口服制剂,可通过有效降解SMAD7转录产物mRNA而抑制SMAD7蛋白的表达,进而发挥抗炎作用。一项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Ⅱ期临床试验结果显示,活动期CD患者分别接受10、40、160 mg/d的孟格森治疗28 d后临床应答率分别为37%、58%、72%,明显高于使用安慰 剂 者(17%)(P=0.04、<0.001、<0.001)[31],但由于之后的Ⅲ期临床试验证实该药对活动性CD疗效不明显,因此对该药的进一步研发已停止[32]。虽然SMAD7蛋白及TGF-β1介导的肠道炎症通路还有待进一步探讨,但以上研究无疑为治疗IBD的新型生物制剂的研发提供了新思路,而小分子口服靶向药物或将成为新型生物制剂未来的研发方向。
2 小结与展望
随着关于IBD的基础及临床研究不断深入,尤其是近年来生物制剂的广泛使用,IBD的治疗目标逐渐从“临床缓解”向“黏膜缓解”和“透壁愈合”“组织学愈合”转变,近期有学者提出将“改变疾病进程”作为IBD治疗目标[33]。IBD的治疗策略强调综合性及个体化,涉及药物治疗(包括5-氨基水杨酸、糖皮质激素、免疫抑制剂、生物制剂等)和非药物治疗(包括白细胞吸附治疗、粪菌移植、营养治疗等),而新型生物制剂仅是IBD药物治疗的一部分。与糖皮质激素、免疫抑制剂等传统治疗药物相比,新型生物制剂因作用于特定靶点、具有不同抗炎机制而能够有效降低IBD患者住院率及手术率,具有疗效好、不良反应发生率低、安全性高等优势。目前,新型生物制剂在国际上的应用已日趋成熟,国内相关用药经验也在不断增加,相信随着国内药物价格的不断下调,新型生物制剂将在临床上得以广泛应用,甚至会取代传统治疗药物而成为IBD药物治疗的主体。
本文无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