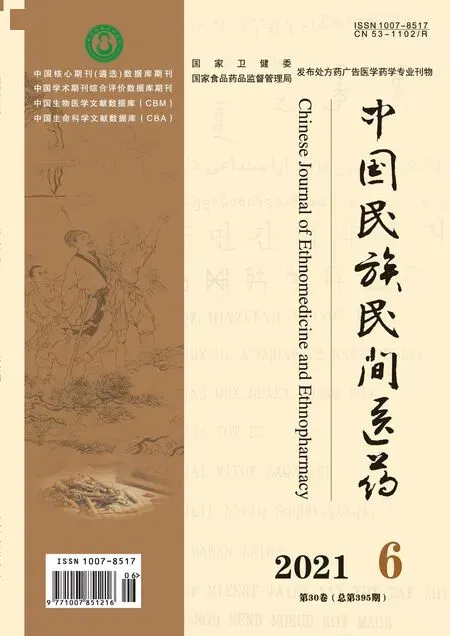黄恒青教授治疗福建地区湿热痰阻型胃脘痛临证经验
张晓钰 郑泽宇 林秀珍 黄恒青
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人民医院,福建 福州 350001
胃脘痛,祖国传统医学简称“胃痛”,是常见的中医内科病。临床中表现为上腹胃脘部近心窝处的疼痛,可伴有上腹胀、嗳气、反酸、恶心、呕吐等[1]。本病近似于西医的急慢性胃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功能性消化不良等疾病。
黄恒青教授从事临床脾胃病研究30余年,擅长于中医脾胃病的诊治。对于福建地区胃脘痛有独到见解。黄恒青教授认为,胃脘痛之病因、证型纷杂多样,在胃脘痛的治疗原则上,当注重地域特点,把握整体观念,加以辨证施治,同时兼顾后期饮食调护,则效如桴鼓。就福建地区而言,湿热痰阻证较为多见,症状突出表现为胀痛、嗳气、反酸等,常伴有口干苦、纳呆、大便黏腻、舌苔黄腻等。临证中,黄恒青教授常以温胆汤化裁辨治福建地区胃脘痛,取得满意疗效。笔者有幸师从黄恒青教授,现将其治疗福建地区湿热痰阻型胃脘痛经验总结如下。
1 病因病机
胃脘痛常见病因有外邪、饮食、情志及素体脾胃虚弱。早期胃痛多考虑实证,责之外邪、饮食、情志,后期胃痛以脾胃虚弱为主,常夹瘀、夹湿等。胃脘痛主要病位在胃,与肝、脾关系密切,当辨寒热虚实,在气在血。黄恒青教授认为,福建地区因其特殊的地域特点及当地居民平素饮食特色,湿热痰阻型胃脘痛多见。福建地处我国东南沿海,气候温暖湿润,易于外感湿热之邪,加之恣食肥甘厚味、生冷海鲜之品,湿浊内生,外湿和内湿相合,阻滞中焦,纳运失健,水液无法正常输布而凝聚成痰,阻滞气机,胃失和降,则胃脘胀痛、嗳气反酸、纳呆食少;湿热蕴脾,上蒸于口,津液耗伤,则口干苦、口中黏腻、舌苔黄腻;湿热下注,阻碍气机,大肠传导失司,则大便黏腻不爽。
2 辨证论治
现代大多医家认为胃脘痛辨证分型主要有寒邪客胃证、饮食伤胃证、肝胃不和证、脾胃湿热证、寒热错杂证、瘀血阻胃证、胃阴亏虚证、脾胃虚寒证等。当以“通”为治疗原则,以“和胃止痛”为基本治法[2]。黄恒青教授认为,针对于福建地区而言,胃脘痛主要是湿热痰阻证多见,同时可兼见其他证型,总治则为理气化痰、清热化湿、和胃止痛。其余治法随兼证加之。例如:兼食积证,可兼见不思饮食、嗳腐吞酸、恶心欲呕等,治法兼有消食导滞。兼表寒证,可兼见遇冷痛重、头痛恶寒等,治法兼有温胃散寒。兼肝郁证,可兼见嗳气频作、喜叹息、两胁胀满等,治法兼有疏肝解郁。兼血瘀证,可兼见胃脘刺痛、入夜尤甚、舌质紫暗等,治法兼有化瘀通络。兼气虚证,可兼见胃脘隐痛、乏力气短、舌淡苔白等,治法兼有补气健脾。
3 用药经验
3.1 用温胆汤为主方化裁治疗 对于湿热痰阻型胃脘痛患者,黄恒青教授擅用温胆汤化裁治疗。黄恒青教授认为温胆汤是治痰之良方,可化一切有形、无形之痰,化痰理气,气畅则湿自除。温胆汤,见于唐朝孙思邈所著《备急千金要方》中,药物组成为生姜、半夏、橘皮、竹茹、枳实、甘草。其后在陈无择的《三因方》中药味有所增减,在原方基础上加白茯苓、大枣,将生姜减量。后世大多沿用的是《三因方》中的温胆汤[3]。温胆汤经过历代医家的演化,增减得当,其类方有黄连温胆汤、柴芩温胆汤等。温胆汤中以半夏为君,祛痰化浊、降逆和胃,以竹茹为臣,专清热痰、开郁宁神,佐以枳实破气消痰、散结除痞,陈皮理气燥湿化痰,茯苓健脾渗湿,姜、枣和中培土。再者甘草为使,益气和中,调和诸药。随湿热痰阻证兼食积、兼表寒、兼肝郁、兼血瘀、兼气虚等之兼证不同,随方加减药物亦不同。
3.2 胃脘痛早期用药 黄恒青教授认为福建地区胃脘痛之早期以湿热痰阻居多,故早期多先治标,祛除实邪为主,并在湿热痰阻证下细查兼证后用药可有诸多变化,临床患者若热重于湿,舌苔偏黄,常加黄连3~4.5 g、茵陈9~12 g、黄芩6~9 g 等清热利湿;若湿重于热,舌苔偏厚腻,常加厚朴6~9 g、苍术6~9 g等燥湿除满;若不知饥、纳差,常加炒莱菔子12 g、神曲9 g、山楂9 g、鸡内金6~9 g等消食导滞;若兼见恶寒、头痛等,常加藿香9 g、紫苏叶6 g等疏散风寒;若伴有反酸,常加瓦楞子15~30 g、锻牡蛎15~30 g等制酸止痛;若大便偏干,常加柏子仁20 g、瓜蒌仁12 g等润肠通便;若寐欠安,常加琥珀3~6 g、茯神12 g等宁心安神。
3.3 胃脘痛后期用药 叶天士认为胃脘痛“初病在经,久痛入络,以经主气,络主血”,“通字须究气血阴阳,便是看诊要旨矣”[4]。故胃脘痛其本在气血,黄师重视气血的调和。从整体观念出发,后期当治本,补益脾胃之气,气血同调。久病气血郁滞不畅,脾胃虚损,易于积滞痰湿,血络瘀阻,故后期多为脾胃虚弱夹湿夹瘀,治以调养气血,补益脾胃,兼顾化湿活血逐瘀。随临床患者兼证变化用药,若乏力、气短,常加党参12~15 g、太子参12 g等益气健脾;若喜嗳气、叹息,矢气得舒等,常加玫瑰花6 g、郁金6~9 g、香橼6~9 g、佛手6~9 g、香附6~9 g、檀香3 g、砂仁3 g、薤白9 g等疏肝理气、行气止痛;若舌质暗、有瘀斑,常加赤芍9~12 g、丹参12 g、没药9 g等活血化瘀。本病之治,黄恒青教授不仅注重辨证论治、结合患者个体差异精准用药外,还强调后期的“养胃”,注意饮食调护,忌辛辣刺激、生冷油腻之品。
4 验案举隅
患者林某,女,62岁,福建福州人,形体偏胖,平素思虑过多、性情急躁。2019年11月13日初诊。主诉:反复胃脘胀痛10余年,刻诊:胃脘胀痛不适,伴嗳气,偶有反酸,口干口苦,不知饥,纳少,咽部堵塞感明显,不影响进食,寐欠安,日4小时,易早醒,小便黄,大便黏,日1次。查体:舌淡红暗苔黄厚腻,边齿痕,脉弦细数。辅助检查:(2019年5月31日福州市第八医院)胃镜:慢性萎缩性胃炎;胃体息肉(体小,已钳除)。病理:体小:胃底腺息肉。HP:(-)。中医诊断:胃脘痛病,辨证为湿热痰阻证,先予清热祛湿、化痰理气,方予黄连温胆汤合半夏厚朴汤加减。处方:黄连3 g、陈皮6 g、茯苓12 g、姜半夏6 g、甘草3 g、枳实9 g、竹茹9 g、茵陈 15 g、苍术9 g、厚朴9 g、瓦楞子15 g(先煎)、紫苏梗9 g、炒莱菔子12 g。14剂,日1剂,分2次服,早晚饭后半小时温服。
二诊(2019年12月4日):胃脘胀闷疼痛较前明显减轻,次数减少,偶有嗳气,嗳气后舒,无反酸,稍口干,无口苦,知饥,纳可,时有咽部不适,情绪郁结,夜寐欠安,易早醒,小便淡黄,大便偏干,日1次。查体:舌淡红暗苔薄黄,边齿痕,脉弦细数。前方去黄连、茵陈、苍术、瓦楞子、炒莱菔子,改茯苓为茯神12 g,姜半夏加至9 g,加丹参12 g、郁金9 g、薤白9 g、瓜蒌仁12 g。7剂,日1剂,分2次服,早晚饭后半小时温服。
三诊(2019年12月11日):偶有胃脘胀闷疼痛,无嗳气,无口干口苦,情绪不佳,知饥,纳可,无咽部不适,稍感乏力、气短,寐可,小便淡黄,大便偏稀,日1次。查体:舌淡红稍暗苔薄白,边齿痕,脉弦细。前方去薤白、瓜蒌仁,改茯神为茯苓12 g,加檀香3 g(后下)、砂仁3 g(后下)、玫瑰花6 g、党参15 g、赤芍12 g。7剂,日1剂,分2次服,早晚饭后半小时温服。嘱患者注意饮食调护,除忌辛辣刺激、生冷油腻之品外,还需忌食豆腐、土豆、地瓜、芋头、板栗等易胀气之品。此后上方基础上加减,续服2周后,症状基本消失,随访2月,未见复发。
按语:患者久居湿热之地,平素饮食失常,湿热蕴结中焦,纳运、津液输布失常,痰湿阻滞气机,发为胃脘痛。该患者湿热痰阻明显,当以温胆汤加减治之,考虑热象稍显,酌加黄连、茵陈清热利湿,苍术燥湿健脾,瓦楞子软坚散结、制酸止痛,炒莱菔子消食导滞,以黄连温胆汤加减为主方治之,再加半夏厚朴汤加强理气化痰。二诊时,中焦湿热减轻,可考虑标本兼顾,调和气血。去苦寒败胃之黄连、茵陈及温燥之苍术。改茯苓为茯神,增强宁心安神之效。加丹参活血祛瘀、郁金开郁通滞、薤白行气导滞、瓜蒌仁润肠通便。三诊时,诸症皆减,主方仍为温胆汤,加丹参饮、赤芍理气活血,玫瑰花、郁金理气解郁,党参益气健脾。黄师认为该患者兼有肝气的郁结不舒,故需加重理气、行气药物的使用,“气血冲和,万病不生,一有怫郁,诸病生焉”,以郁金、玫瑰花、檀香、砂仁等疏肝理气、行气止痛,气行则血行,瘀血去则新血生。同时,黄恒青教授认为胃病三分治七分养,故后期饮食调护亦是关键。黄恒青教授常常嘱咐患者注意胃病后期的饮食调护,以减少胃脘痛的复发。
5 体会
黄恒青教授针对福建地区胃脘痛的治疗,着眼“湿热”及“痰浊”,常以温胆汤加减治之,治以标本同治,同时强调个体的后期调养,固后天以养先天,以使正气生而邪自去,疾病乃愈,机体得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