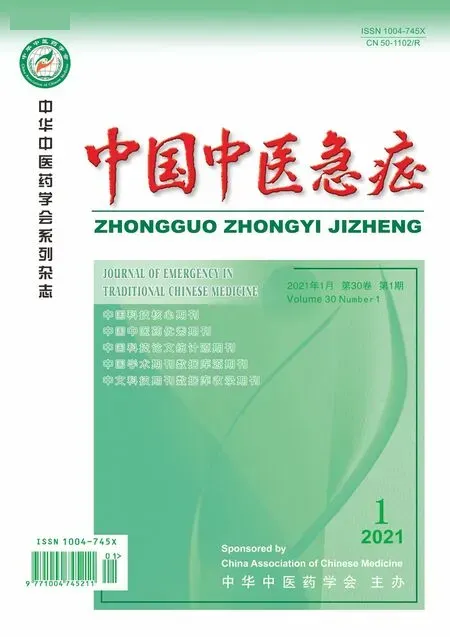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中医证治中若干问题的思考与体会*
崔 翔 毛 娅 郭 薇 刘玲兰 江自成 黄辉红 王晓玲△
(1.陕西省安康市中医医院,陕西中医药大学第七临床医学院,陕西 安康 725000;2.陕西省安康市中心医院,陕西省安康市传染病医院,陕西 安康 725000)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传染性强烈,属于中医学“疫病”范畴。病因为感受疫疠之气,病位在肺,基本病机特点为“湿、热、毒、瘀”[1-2]。笔者在疫情救治实践的基础上,深入探析COVID-19发病特点和规律,并结合现有文献,就COVID-19证治中的几个基本问题,与同道探讨,以期对本病证治提供参考。
1 COVID-19病因为湿浊疫毒
疫疠之气,也称疫毒,是存在于自然界中一类具有强烈传染性的外邪,形成和流行多与气候反常相关,致病特点包括:传染性强;发病急骤,病情危笃;一气一病,症状相似。《温疫论》指出“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黄帝内经》言“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吴鞠通曰“温疫者,厉气流行,多兼秽浊,家家如是,若役使然也”。《回生捷要》载“疫证者,乃感四时不正之气也……其之中人,多从口鼻而入,蕴久而发,绝似伤寒,第所感系秽气,当以解秽为主”[3]。综上,COVID-19的病因兼有湿浊和疫毒的特点,可概括为“湿浊疫毒”。就其属性而言,湿浊疫毒相合并无截然寒热之分,但湿浊在本质上属阴邪。
2 COVID-19病性与病势多取决于患者禀赋体质
湿浊疫毒在COVID-19的发病中起主导作用,而疾病的寒热属性及病势与感染者体质差异密切相关,也受地域、气候的影响。正如《医宗金鉴》言“人感受邪气虽一,因其形藏不同,或从寒化,或从热化,或从虚化,或从实化,故多端不齐也”。笔者临证发现,感染者以轻症和普通型占主体,多表现为寒湿郁肺证。这不但与患者体质有密切相关,也与本病发病节气在大雪、冬至之后,气候寒湿有关。
3 COVID-19病位:肺脾两脏同时受邪,以肺为主
根据最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六版)》[2],结合我们掌握的临床资料和文献报道[4-5]来看,本病常见症状为乏力、倦怠、发热、干咳(鼻塞、流涕相对少见)、肌痛、胸闷,重症病例常伴有呼吸困难。同时,很大一部分患者常伴有腹胀、食欲不振、恶心、腹泻等消化系统症状。《灵枢·经脉篇》曰“肺手太阴之脉,起于中焦,下络大肠,还循胃口,上膈属肺”。肺与大肠、胃均有经络上的联系,湿浊疫毒,来势凶猛,自口鼻而入,肺为娇脏,肺气郁遏,宣降失司;脾喜燥而恶湿,湿浊困脾,阻遏中焦气机,脾运失职;故可以出现发热、咳嗽、胸闷、气短等肺系统疾病的证候表现及纳差、纳呆、恶心、痞满、腹泻、肌痛等脾胃系统疾病的证候。故本病病位首在肺,次为脾,危重患者病情进展恶化,变证丛生,病位涉及心、心包、肝、肾。
4 COVID-19病机为气机郁遏,痰瘀速生,痹阻肺络
COVID-19属中医学“疫病”范畴,由感受“湿浊疫毒”所致,湿浊与疫毒相合传染性极强。在隔离病房,穿戴防护衣和多层橡胶手套,很难准确把握患者脉象,同时温病重视验舌,故临证应舍(轻)脉从舌。从笔者采集的舌像资料和相关资料分析[6],患者无论老幼,舌质总体偏暗,舌苔以腻(垢)为主,以舌中部、根部为著。基于对本病病因和四诊信息的掌握,笔者认为“湿浊毒痰瘀”是贯穿始终的基本病机要素,其基本病机为湿浊疫毒,口鼻而入,直中肺脾,气机郁遏,肺失宣降,脾困失运,痰瘀速生,痹阻肺络。
湿浊疫毒之邪,因感染者体质的差异,或从寒化或从热化,平和质、气虚质、痰湿体质等易从寒化,易表现寒湿郁肺证,而湿热、阴虚体质多从热化表现为热毒闭肺证。少部分体弱虚羸者,疾病易急剧进展恶化,出现逆传心包、邪陷心营,内陷血分等危候。寒湿郁肺多为轻症和普通型,占绝大多数;而热毒闭肺证多表现为重症,相对较少。据WHO报道,中国1.7万例新冠肺炎病例,传染性虽远高于SARS,82%轻症感染,3%极危重[7]。进入恢复期,邪去正虚,患者常有两种证候:一是肺脾气虚证,常表现乏力、气短、纳差呕恶、口淡无味、痞满、便溏等症状,多由寒湿郁肺证转归而来;二为余热未清,气津两伤证,表现为低热微汗、气短乏力、咳嗽痰少、纳差等表现,多由疫毒闭肺证转归而来。
5 证治要点
基于对本病基本病因和病机的认识,治疗上总以宣上、畅中、通腑、解毒、辟秽、活血、化痰为基本原则,芳化湿浊,辟秽除疫,解毒化痰,分消走泄多途径分化湿浊疫毒。《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六版)》[2]给出了包括辨证、分期、分型、方药在内的详细方案,具备很强的指导性和实用性。在国家方案和基本治疗原则的指导下,我们在本病的临床救治中应重点把握以下证治要点和临证细节。
5.1 宣肺醒脾,宣畅气机 本病病位主要在肺,次为脾,故治疗上应治肺为主,兼顾脾胃。着眼于“湿浊疫毒,郁遏气机”病机的始动环节,首当宣畅上中二焦气机,气机顺,则湿浊去,疫毒散。肺气被遏,宣降失司,治宜宣、宜降。治上焦如羽,非轻不举,药用轻灵、轻清透泄之品。根据病情轻重辨证,酌选桑菊饮、银翘散、麻杏甘石汤等。其次,针对湿浊困脾,应醒脾行气,酌情配伍广藿香、苍术、厚朴、紫苏、白芷、豆蔻、木香、砂仁、槟榔、石菖蒲、苏合香等芳香化浊,辟秽解毒的药物。需指出,此时不宜轻易使用或重用补剂,以免壅滞中焦,不利于湿浊外泄。
5.2 解毒化痰,忌过苦寒 湿浊疫毒郁遏气机,重在宣畅气机,用药早用或过用苦寒之剂,以免伐脾,徒伤中气,招致邪毒内陷。对于邪毒痹肺证,热毒与痰浊胶结,邪气乖张,病机复杂,应统筹全局,既不可单纯重用苦寒清热解毒化痰,又忌片面强调清热燥湿,以免苦寒冰伏留瘀,敛遏湿浊疫毒。治当清热解毒,化痰辟秽,宣畅气机,分消走泄多法合用,多途径给邪以出路,可仿柴胡达原饮、三仁汤、甘露消毒丹、连朴饮、黄芩滑石汤之旨。对于逆传心包、邪陷心营、内陷血分之危证、变证,应中西医结合协同综合救治,遵《黄帝内经》之旨“热淫于内,治以咸寒,佐以甘苦”,选方用药可仿清营汤、清宫汤、犀角地黄汤之意,清营解毒,辅以养阴,不忘透邪,可酌情选用麦冬、玄参、生地黄、竹叶、连翘、银花等品以顾护阴液,透热转气。
5.3 化瘀通络,谨防生变 活血通络在疾病早期往往最容易被忽视,湿浊疫毒,来势凶猛,直犯肺脏,阻遏气机,短期内可致瘀痰速生,与疫毒相合,痹阻肺络,也是病情进展的关键环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六版)》[2]中指出重症患者多在1周后出现呼吸困难和低氧血症,严重者快速进展为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脓毒症休克、难以纠正的代谢性酸中毒和出凝血功能障碍。肺实变是本病肺部的影像学严重表现,而湿浊瘀痰毒互结,痹阻肺络是发生肺实变的中医病机基础。既病防变,在早期应尽早介入活血化瘀药物,必要时可酌情选用虫类药活血逐瘀,以截断扭转,防止进展逆传心包,深陷营血。活血药物的使用对于改善微循环缺血、缺氧,防止肺实变加重,以及防治后期肺间质纤维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5.4 通腑泄浊,顾护肠道 肺与大肠相表里,在多版方案中疫毒闭肺证的处方均包含了宣白承气汤,笔者在临床中应用也取得了良好的疗效。以泻代清,对于改善发热症状,预防肠源性内毒素血症,抑制炎症风暴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自《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四版)》[8]中开始推荐使用肠道微生态调节剂,维持肠道微生态平衡,预防继发细菌感染。因此,SARS-CoV-2感染与肠道黏膜屏障的关系及中医药的干预作用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5.5 瘥后防复,综合调治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六版)》[2]指出,患者体温恢复正常3 d以上、呼吸道症状明显好转,肺部影像学显示炎症明显吸收,连续两次呼吸道病原核酸检测阴性(采样时间间隔至少1 d),可解除隔离出院。湿性黏滞,湿浊疫毒相合,更难速去,邪去正虚,尤其是重症患者,虽达到出院标准,但肺部可能还存在未吸收的病灶,尤其是危重患者经治疗出院,应特别警惕复发或转为肺间质纤维化等慢性疾病。这类患者常伴有余邪未尽,正气虚损的表现。因此,在恢复期应特别重视中医药方法的连贯性,这也是全程介入中医治疗的要求。通过综合调治,一助正气,二清余邪,可以改善患者后期症状,促进损伤组织的修复。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中医药管理局2月23日印发《关于印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恢复期中医康复指导建议(试行)的通知》[9],建议除了服用中药外,一些传统的中医理疗方法也有助于增强自身抵抗力,如膳食疗法、艾灸、针灸、太极拳、八段锦、呼吸六字诀等。
6 中医药防治新冠肺炎的临床与研究动向
中医药参与疫情防控的临床、科研有两个动向:一是在疫情暴发初期,采用以辨病为主、病证结合的方法,全国各地根据实际情况采用辨证论治的模式。二是随着临床经验的积累、确诊病例的激增,出于疫情防治的现实需要,通用方的筛选攻关研究及临床推广应用成为主要方向,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以临床“急用实用效用”为导向,紧急启动治疗COVID-19“中医药有效方剂筛选研究”专项,筛选出“清肺排毒汤”,3 d总有效率可达90%以上[10-11]。基于此,该方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六版)》[2]中单列推荐。此外,广东、四川、陕西等省启动新制剂应急审批程序,已报道“透解祛瘟颗粒”“清肺排毒合剂”“益肺解毒颗粒”“清瘟护肺颗粒”等制剂应用于本省疫情救治。中医是一门实践医学,理论来源于实践,并在实践中丰富完善,在疫情防控救治一线开展中医药防控与科研攻关,可以更好地总结疫情的发病、证候演变及证治规律,提升当前的防控救治效果,同时也能为中医药应对类似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积累经验。中医药参与一线防控和科研攻关,应本着因地制宜,分层实施的原则,即疫情中心区以通用方为主;疫情高发区以辨证论治和通用方结合开展临床对照研究;而在疾病散发地区,应在国家方案的框架下,采取三因制宜,个体化辨证,精准施治的策略。疫病流行在病因、病性、病机、证候演变上都存在一定的规律性,同时也要考虑到不同的地区受地理气候及人群体质因素的影响,也存在特殊性和个性。
综上,笔者通过分析本地收治的确诊病例资料,结合对湖北省及全国其他地区资料和报道分析,就本病的几个基本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但限于病例资料有限,且重危病例少,局限性在所难免,有待在临证中进一步总结并完善。
致谢:承蒙课题组共同承担单位安康市中心医院(安康市传染病医院)的大力支持。特别感谢湖北中医药大学周艳萍教授、周玲博士,湖北省中医医院何堂清医师,湖北省武汉市第一医院杜念龙博士,湖北省襄阳市中心医院陈立博士,湖北省十堰市人民医院吴曦博士对本文提出的宝贵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