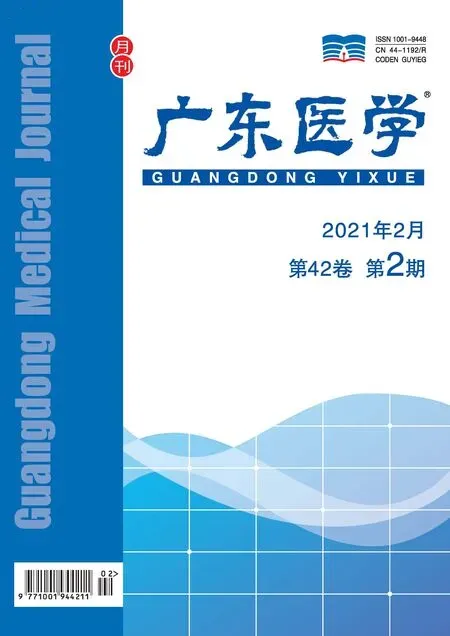术后镇痛对肺癌患者免疫功能影响的研究进展*
陈志明,丁登峰
暨南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深圳市人民医院麻醉科(广东深圳 518020)
肺癌的发病率与病死率均位于恶性肿瘤首位,手术切除是其主要的治疗方式[1]。肺癌手术创伤大,疼痛剧烈,使得术后急性疼痛高发。疼痛抑制自然杀伤细胞(natural killer cells,NK cell)活性,诱导免疫抑制[2]。完善的术后镇痛不仅减少肺癌患者不愉快的主观感受和情感体验,还可以保护患者免疫的功能,在降低肿瘤转移及复发风险方面有重要意义[3]。既往单一的镇痛药物及镇痛方式常出现镇痛不足、呼吸抑制、恶心呕吐等不良反应,而且抑制肺癌患者免疫功能。随着麻醉药物和麻醉技术的发展,不同的镇痛药物及镇痛方式用于临床,在减少不良反应的同时,改善患者的免疫功能。本文就不同镇痛药物及镇痛方式对肺癌患者免疫功能的影响进行综述。
1 围术期肺癌患者免疫功能状况
NK细胞、T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均参与调控肿瘤免疫,其中NK细胞、辅助T细胞1(T helper cells1,Th1 cell)以及 CD8+细胞毒性T细胞(cytotoxic T-lymphocyte,CTL)发挥抗肿瘤作用,抑制肿瘤生长,而辅助T细胞2(T helper cells2,Th2 cell)、调节性T细胞(regulatory T cell,Tregs)、肿瘤相关巨噬细胞(tumor-associated macrophages,TAMs)则抑制抗肿瘤作用,促进肿瘤生长[4]。
不同种类免疫细胞影响肿瘤免疫机制不一,NK细胞分泌γ干扰素(interferon-γ,IFN-γ)、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TNF-α),直接杀伤肿瘤细胞[5]。研究表明,肺癌根治术后NK细胞数量减少,且对肿瘤细胞的杀伤能力减弱[6]。Th1细胞分泌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IL)-2、IFN-γ等细胞因子,激活NK细胞与巨噬细胞活性,并增强CTL的杀伤能力。CD8+CTL可通过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Ⅰ类(major histocompatibility complexⅠ,MHCⅠ)肽复合物途径直接识别和杀伤肿瘤细胞。Th2细胞通过分泌IL-4、IL-5、IL-10等细胞因子抑制机体抗肿瘤效应。机体Th1/Th2是相互制约的平衡关系,Th1/Th2失衡将影响患者的免疫功能,增加肿瘤的发生率[7]。与健康人相比,肺癌患者Th1相关细胞因子水平下降,而Th1相关细胞因子水平上升,Th1/Th2明显失衡[8]。TAMs不仅能抑制肿瘤微环境CTL活性,还能释放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并产生基质金属蛋白酶-9(matrix metalloprotein-9,MMP-9),促进肿瘤血管的生长[9]。在肺癌的进展过程中,TAMs可能诱导肿瘤细胞侵袭和增殖,导致患者预后不良[10]。Tregs通过分泌转化生长因子-β(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TGF-β)、IL-10、IL-35等细胞因子抑制CTL对肿瘤细胞的杀伤作用,导致肿瘤的转移、侵袭[11]。Phillips等[12]比较肺癌患者与健康人外周血免疫细胞数量,结果发现肺癌患者外周血Tregs显著增加,且分离出的Tregs对原始T细胞有抑制作用。
由此可见,肺癌患者术前已经存在免疫抑制,肺癌术后患者疼痛剧烈,而术后疼痛进一步抑制患者免疫功能,增加术后肿瘤复发或转移的风险,因此肺癌患者应做好术后镇痛。
2 镇痛药物对肺癌患者免疫功能的影响
2.1 阿片类镇痛药 吗啡是经典的阿片类镇痛药,可激活μ阿片受体(Mu-opioid receptor,MOR),刺激原始T细胞蛋白激酶C-θ(protein kinase C-θ,PKC-θ)蛋白磷酸化和转录因子GATA3表达,诱导T细胞向Th2细胞分化,降低Th1/Th2比值,抑制免疫功能[13]。吗啡还可抑制核因子-κB(nuclear factor kappa B,NF-κB)信号通路,降低免疫细胞微小RNAs的表达,且这种抑制作用呈时间和浓度依赖性[14]。除了MOR,κ-阿片受体(kappa opioid receptor,KOR)亦通过抑制NK细胞的细胞溶解功能参与细胞免疫[15]。动物模型中,不同种类阿片类药物作用于巨噬细胞表面阿片受体,从而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免疫抑制效应(吗啡>羟考酮>丁丙诺啡)[16]。芬太尼类药物是人工合成的阿片类镇痛药,Ma等[17]等发现芬太尼剂量依赖性下调NF-κB的活性,抑制T淋巴细胞活性,但临床剂量芬太尼用于术后镇痛不影响患者NK细胞毒性。并非所有阿片类药物对机体免疫都有抑制作用,研究显示,阿片受体激动-拮抗剂地佐辛通过提高CD8+细胞增殖和细胞毒性,抑制肿瘤转移[18]。
阿片类药物对机体免疫系统随着药物种类、剂量及给药方式不同而产生不同影响,一项回顾性研究发现,术后96 h内阿片类药物的剂量增加与5年内肺癌复发率增高相关[19],因此,肺癌患者术后镇痛需谨慎选择阿片类药物。
2.2 非甾体类抗炎药 炎症在肿瘤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使用抗炎药可降低肿瘤的发病率和复发率,抗炎药可能是一种新的肿瘤治疗策略[20]。非甾体类抗炎药(non-steroidal anti-inflammatory drugs,NSAIDs)是一类主要抑制环氧化酶(cyclooxigenase,COX)活性从而减少前列腺素(prostaglandin,PG)合成的化合物,这类药物通过减少细胞迁移、抑制血管生成、诱导细胞凋亡、增强细胞免疫应答等作用机制,发挥抗肿瘤作用,降低肿瘤复发[21]。
上皮-间质转化程序的异常激活使癌细胞具有转移性,非选择性NSAIDs阿司匹林通过抑制上皮-间质转化程序的激活,阻滞高侵袭性K-ras表达肺癌细胞的转移[22]。阿司匹林还通过下调血小板源性COX-1/血栓素A2途径,阻止转移性血管内环境形成,使癌细胞保持在血管内,减少肺转移[23]。程序性死亡-1(programmed death 1,PD-1)是一种活化T细胞表达的小分子,抑制T细胞介导的抗肿瘤免疫。临床研究显示,肺癌术后PD-1升高,而非选择性NSAIDs氟比洛芬酯在术后72 h内抑制CD8+T细胞术后PD-1水平升高,改善肺癌患者术后免疫功能[24]。另一项临床研究发现,氟比洛芬酯提高肺癌患者术后长期生存率[25]。
研究显示,COX-2在肺癌中高表达,其水平高低与预后有关[26]。COX-2抑制剂塞来昔布不仅通过内质网应激诱导肺癌细胞凋亡[27],还诱导肺癌细胞细胞间黏附分子-1(intercellular adhesion molecule 1,ICAM-1)上调,增加肿瘤杀伤细胞对癌细胞的溶解,发挥抗肿瘤作用[28]。另一种COX-2抑制剂帕瑞昔布降低吞噬和细胞运动3(engulfment and cell motility 3,ELMO3)的表达,抑制肺癌的生长和转移[29]。由于COX-2抑制剂提高机体对肿瘤的反应性和生存率,减少癌细胞的增殖和诱导癌细胞凋亡,因而有学者指出,有必要进行更多的临床试验,评价选择性COX-2抑制剂在肺癌防治中的作用[30]。
NSAIDs主要通过COX依赖机制参与抗肿瘤作用[31],COX-1、COX-2在致癌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肺癌患者选择NSAIDs用于术后镇痛,需综合考虑COX-1、COX-2抑制剂的抗肿瘤作用及其所致的并发症。尽管COX-2抑制剂选择性更强,但其他分子靶点是否具有同样的效果,也需进一步研究。
2.3 α2肾上腺素受体激动剂 右美托咪定是一种高选择性α2肾上腺素受体激动剂,它对α2受体的亲和力是可乐定的8倍。右美托咪定可抑制炎症反应、减轻应激反应、减少麻醉药物用量、提高术后镇痛质量,而炎症、儿茶酚胺释放、麻醉药物及疼痛对抗肿瘤免疫产生不利影响,因而围术期使用右美托咪被认为对肿瘤切除的患者特别有益[32]。一项系统性回顾研究显示,与对照相比,围术期使用右美托咪定的患者NK细胞、B细胞和CD4+T细胞数量以及CD4+/CD8+和Th1/Th2的比例明显升高,CD8+T细胞数量减少,可保护手术患者的免疫功能,提高临床疗效[33]。研究发现,右美托咪定用于胸腔镜手术,可减轻围术期的免疫抑制[34]。
虽然右美托咪定通过间接作用改善肺癌患者围术期的免疫功能,但其直接作用的效果可能与此相反。体外实验显示,右美托咪定通过肺癌细胞中α2肾上腺素受体的信号传导促进肿瘤细胞的存活[35]。体内实验也发现,右美托咪定增加肺癌小鼠体内肿瘤细胞的存活和转移生长,这种作用也通过肾上腺素受体实现[36]。临床研究发现,右美托咪定通过诱导肺癌患者术后单核髓源性抑制细胞促进肿瘤转移,该细胞群具有较强的促血管生成能力,对患者远期疗效产生不利影响[37]。由于基础研究缺乏可靠实验模型模拟人类肺癌,且右美托咪定用量远大于临床用药,难以为右美托咪定对肺癌患者远期疗效的影响提供明确依据。目前临床研究集中于右美托咪定对围术期肺癌患者免疫功能状态的影响,虽然其间接作用有利于肺癌患者免疫功能的恢复,但其直接作用促进肺癌细胞存活和转移仍不容忽视,因而未来的研究有必要明确右美托咪定肺癌患者长期预后的影响。
2.4 非阿片类中枢镇痛药物 曲马多是一种非典型的阿片类药物,除作用于阿片类受体外,它还能阻止5-羟色胺(5-hydroxytryptamine,5-HT)和去甲肾上腺素的再摄取,主要用于中重度疼痛的治疗。由于曲马多对阿片受体作用弱,因而其所致的不良反应比经典阿片类药物少[38]。曲马多在急慢性疼痛治疗后均未引起免疫抑制,急性给药还对正常动物的NK细胞、淋巴细胞增殖和细胞因子产生等免疫指标有明显的增强作用,这种作用与其所致的5-HT活性增强有关[39]。研究发现,曲马多可激活NK细胞活性,防止手术引起的NK细胞活性抑制,明显抑制肺癌术后转移,而同等剂量的吗啡则无此作用[40]。因此,曲马多对肺癌患者围术期的免疫保护无疑起到正向作用,但肺癌术后疼痛剧烈,曲马多镇痛作用有限,剂量过大容易导致恶心呕吐,因而在选择时需充分评估。
3 术后镇痛方式对肺癌患者免疫功能的影响
3.1 患者自控静脉镇痛(patient-controlled intravenous analgesia,PCIA) PICA是治疗术后疼痛的有效方法之一,以阿片类药物为主的PCIA在临床应用广泛。但阿片类药物不良反应多,其抑制免疫功能的作用对癌症患者产生负面影响,目前针对肺癌患者的PCIA多联合应用其他药物,在减少不良反应的同时,保护患者免疫功能,延缓肿瘤术后复发[41]。
3.2 胸段硬膜外镇痛(thoracic epidural analgesia,TEA) TEA是公认有效的胸科术后镇痛方式。研究显示,与静脉镇痛相比,TEA可减缓围术期CD3+、CD4+、CD4+/CD8+比值和NK细胞下降,使患者术后72 h各项指标恢复至麻醉前水平,对免疫系统干扰小,患者恢复快[42]。但一项回顾性研究发现,肺癌术后2年和5年无复发生存率与TEA或PCIA的镇痛方式无关[43]。
3.3 区域神经阻滞 椎旁神经阻滞(paravertebral block,PVB)是一种与TEA镇痛效果相似而并发症较少的神经阻滞[44]。PVB抑制肺叶切除术后血浆MMP-9水平升高,有利于患者术后迅速康复,减少术后肿瘤复发[45]。但也有研究认为,与PCIA和TEA相比,PVB不降低肿瘤复发率,但增加术后总体存活率[46]。近年来,随着超声技术的发展,肋间神经阻滞(intercostal nerve block,ICNB)、前锯肌平面阻滞(serratus anterior plane block,SAPB)、竖脊肌平面阻滞(erector spinae plane block,ESPB)等区域神经阻滞相继用于胸部手术的术后镇痛,在减少麻醉药物用量、改善术后镇痛质量、减少术后并发症方面取得良好效果[47],但目前有关区域神经阻滞对肺癌患者免疫功能影响的研究较少,尚无研究观察这些神经阻滞对肺癌患者远期复发率和生存率的影响。
3.4 多模式镇痛 多模式镇痛是一种采用不同麻醉药物和麻醉技术,作用于疼痛传导的不同靶位,减少单一药物和技术的不良反应,以达到完善镇痛质量的镇痛方法。对肺叶切除术患者,多模式镇痛限制阿片类药物的不良反应,改善疼痛治疗,促进患者快速恢复[48],理论上有利于肺癌患者免疫功能的保护。但手术方式、患者病情、麻醉医生的选择及治疗费用等因素限制了多模式镇痛标准流程的制定[49],使得多模式镇痛的组合种类繁多,因此多模式镇痛能否提高患者免疫功能,减少术后肿瘤复发,不同研究结论不一[50]。
4 展望
围术期免疫功能的抑制,将促进肺癌术后微小残留病灶和循环肿瘤细胞生长,导致肿瘤复发和转移。如何改善肺癌患者围术期的免疫功能,降低肿瘤复发和转移风险,一直是临床研究的重点。诸多研究表明,良好的术后镇痛能提高患者围术期免疫功能。以往肺癌术后镇痛方式单一,PCIA是主要的镇痛方式,因而相关研究多观察不同镇痛药物对肺癌患者免疫功能的影响,但很多镇痛药物存在缺陷,如阿片类药物和右美托咪定直接抑制患者免疫功能、NSAIDs使用禁忌多、曲马多镇痛作用弱等,对临床指导作用有限。近年来,随着超声技术的发展,不同方式的神经阻滞被用于肺癌手术,使肺癌术后镇痛方式有了多种选择。神经阻滞所用局麻药吸收入血缓慢,且局麻药可抑制肿瘤细胞生长,因此今后的研究可着眼于不同术后镇痛方式对肺癌患者免疫功能的影响。此外,肺癌术后复发率和生存率是反映肿瘤复发转移及治疗效果最直观的指标,但目前研究主要观察围术期患者免疫功能变化,缺乏对远期疗效的评价,未来的研究需弥补这方面缺陷,为肺癌术后镇痛方案的制定提供更有力的临床证据。最后,围术期免疫功能受麻醉、手术、护理等多方面因素影响,设计有关术后镇痛对肺癌患者免疫功能影响的临床研究时,需要制定严谨的试验方案,排除其他干扰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