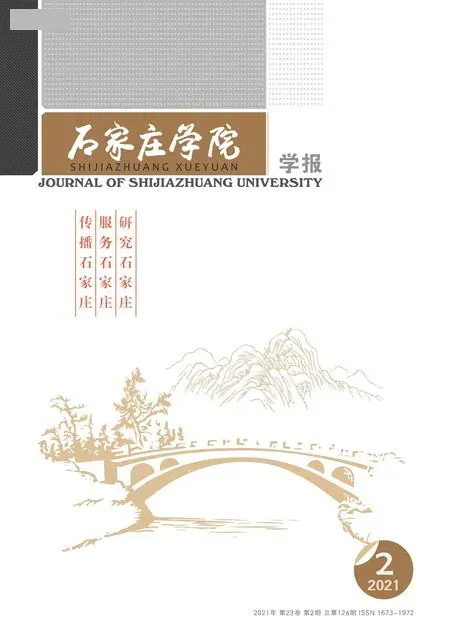语音系统性与语音演变的关系
——读《语音学教程》
陈沛莹
(南京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210046)
语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有了语音形式作为载体,人们才能接受到彼此的语言信息从而进行沟通交际。语音学是描写语音的科学,语音的描写和研究可以有共时和历时两个维度。历史语言学重视语音历史演变的研究,关心一个语音现象从过去到现在的状态的改变;结构主义语言学则关注语音的共时结构特点,研究一个语音单位在整个音系结构中的位置及功能。这两个维度看似不同、各自独立,但实际上有相通之处。语音的演变有其规律性,这种规律往往与其共时结构系统有关。而要解释其系统分布特征,就不得不探究语音作为物质材料所依赖的发音规律及生理基础。
《语音学教程》(以下简称《教程》)是美国著名语音学家彼得·赖福吉(Peter Ladefoged)所著的一本关于语音学知识的基础教材。《教程》第七版由美国凯斯·约翰逊(Keith Johnson)补充,中译本由张维佳、田飞洋翻译,朱晓农、衣莉审校,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出版。
《教程》在介绍语音知识时按照由点到面、由具体到一般的逻辑顺序。全书分为三编:第一编,介绍语音学的基本概念,分别从语音学和音系学的角度介绍语音学的相关研究内容和方法;第二编,以英语这一具体语种为对象,从音节学的角度介绍英语音段中的辅音、元音各组成成分以及各自的具体音位形式,并介绍音节基础上的词语和句子中的超音段音位以及动态语流中发生的音变;第三编是普通语音学,讲解人类语音的一些普遍规律。人类发音基于大体相同的生理基础,因此存在一些具有普遍性的基本规律。在这一部分作者介绍了气流机制和发声类型、辅音音姿、声源/滤波理论等声学语音学基本原理、音段特征和超音段特征等普遍的语音学知识。最后一章归结到“语言学的语音学”,充分表达了作者的思想观念,即语音学应为语言学问题服务。
《教程》有几个突出的特点:第一,将纷繁且看似相互独立的诸多音素用几个核心的概念贯串起来,如最后一章用特征的层级系统将诸多的语音特征进行整理,使它们被归于喉上、喉和气流这三项具有关键意义的发音部位和物理项目,这样就使语音项目的展现更具系统性,也体现了发音时的内在机理。第二,介绍了气流机制和发声类型这两个较为前沿的语音问题。这是其他语音学教材较少涉及的内容。气流机制指的是发音时的能量来源,这里涉及到音、内爆音等一系列非肺部气流音;发声类型指发音时的不同声门状态产生了不同类型的声音,着重介绍了气声、哞声、嘎裂声等。上述我们今天一般称为发声态,因为都属于广义的“发声活动”。第三,将语音学的内容置于音节学的框架之下,从音系学的角度组织安排各种语音因素,如最后一章将“气流启动”“喉部发声”“喉上声道(口鼻)调音”这些语音发音要素都归结到“音段”这一音系学框架之下;而本书对各项辅音、元音的介绍也是基于音节学的框架来进行的。第四,赖福吉提倡“语言学的语音学”,强调“语音学应为语言学服务”。赖福吉认为,“语音描写必须与音系学相关”①原文为“The phonetic description of a language must be related to the phonology.”(“Features and parameters for different purposes”,LSA paper,引自赖福吉的网页),转引自朱晓农《为音节学服务的语音学——赖福吉〈语音学教程〉中译本序》,载《东方语言学》2010年第1期。,因此本书最后一章将语音学放置在语言学的大框架下进行介绍。[1]
传统的语音学关注语音事实,即对于语音的定性描写和语音演变的内容和形式。由于有了实验的手段,语音的定性和定量研究都更加直观化和精确化,同时由于人们对发音的生理机制了解得更为深入,对于语音系统的整体框架及其互动规律更为清楚,所以对于语音演变原因的研究也就变得更加深刻。因此,通过《教程》对语音要素和语音规律的展示,我们发现了语音具有系统性,并且这种系统性常常成为语音演变的动因。这将是笔者接下来所要重点探讨的问题。
一、语音的产生是系统运作的结果
语音的产生本身就具有整体性,它是一个涉及了生理、物理和心理三方面因素的过程。
从生理上讲,发音机制包括气流过程、发声过程、调音过程和口鼻过程。气流过程指的是为发音提供能量的气流排出方式。大多数气流过程都是伴随着呼吸一起由肺部提供的,肺部提供的气流,或撞击声带发声,或在喉上声道(口鼻)中受阻或共振发声。但世界上还存在着部分非肺部气流音,这种气流机制上的区别是赖福吉比较新颖的一个观点。《教程》中举了内爆音作为例子。内爆音是通过降低喉头,用气流内入的喉头机制来形成的塞音。赖福吉以信德语为例,对内爆音ɓ的发音过程进行解说:“在我们所考察过的所有内爆音里,先是调音部位的闭塞——双唇合拢,接着喉头像一个活塞向下运动,这会引起口腔中的压力下降……当发音闭塞解除时,可能会伴随着缩气的动作,把气流吸进口腔”[2]148,所以伴随着缩气动作的内爆音,人们也称为“缩气音”。有些语言的内爆音成独立音位,有些则只作为常态浊音的音位变体。但不管是肺部音还是非肺部音,气流都是语音产生最基本也是必要的动力。
发声类型主要以声带状态来命名的。声带振动形成浊音,声带不振动形成清音。发声过程对应的生理部位是喉部,对于气流来说喉部相当于气阀的功能,决定着气流是否从声门通过,而这也决定了声带是否振动。当声门关闭,气流受阻而撞击紧闭的声带,声带振动发声;当声门敞开,气流从声门的缝隙中逸出,声带不振动发声。赖福吉认为,发声过程“只有两种可能”,但其实这只是两种最基本的形态,声带不是简单的条状,其上下片的不同开闭组合方式和内外片的不同厚薄程度的结合,使其开闭状态有了非常复杂的变化[3]83-85,在声门的开和闭之间,还存在着许多中间态,并且不同的单一状态和多种状态的组合,会形成多种发声态,如气声、紧喉嗓音等。汉语方言吴语中的清音浊流,其实就是赖福吉所说的浊音和清音的结合,因为发气声时声带的状态是一部分闭合振动、一部分敞开气体逸出,所以其性质是两种不同音的综合。发声态是如今比较前沿且热门的问题,《教程》在第六章介绍发声类型时,提到了气声、哞声等,并对它们相应的声门状态和声学表现形式进行了介绍,这在当时的语音学教程来说已是非常具有前瞻性了。对于大部分语言系统来说,清音和浊音相对来讲在音系中都具有系统性意义的特征。
调音过程和口鼻过程共同构成我们现在常说的声腔共振过程。口、唇等调音部位的不同状态引起声道形状的改变,从而改变了一个声音的音色。假如说发声过程提供了一个声音的模子,那么经过口唇等声腔共鸣之后声音就得到了修改,于是获得了自身独有的音色。口鼻过程决定了气流是从口腔呼出还是从鼻腔呼出,口腔中的软腭是连接着两个共鸣腔的中介,其升降控制着鼻腔通道的打开与关闭,因此是决定一个音素是否具有鼻音音色的重要因素。就大多数的人类语言来讲,按鼻腔是否参与发音以及参与的程度,语音主要可分为鼻音、口音和鼻化元音。发鼻音时软腭下降,鼻腔通道打开,气流主要从鼻腔通道流出,纯鼻音都是辅音;发口音时软腭提升,鼻腔通道关闭,气流主要从口腔通道流出,口音主要有非鼻辅音和口元音两种类型;发鼻化元音时鼻腔通道处于半开启状态,气流同时从口腔和鼻腔两个通道中流出。
人的发声包括喉部声源发声和共鸣腔调制,这样的发声程序在物理上可以类比声源/滤波原理。喉部声门的开启为发声提供了气流作为声源,声带振动产生了带有一定频率的基音,这个基音在经过口、鼻、咽喉等共鸣腔体时,部分频率段的声波因引起共鸣而得到增强,部分频率段的声波则因阻尼的影响而被削弱,这样就产生了频率、强度都不同的丰富的陪音,也就是声学上所说的谐波。以同时兼有声源发声和共鸣腔调制这两个完整发音过程的元音为例,一个元音同时包含许多不同的频率,其中最基本的是由声带振动所产生的基频,每个元音的产生都需要振动声带,因此每个元音的基频频率都是一样的,基频的声学表现为语图上的浊音杠。元音之间音质的区别来源于其陪音结构的不同,不同的陪音频率赋予特定元音独特的音质。这些陪音结构在声学上以共振峰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声源/滤波模型中,声带是声音能量的来源,声道则相当于一个频率滤波器,改变了声带发音的“材质”。而声音在声道中产生共鸣的过程,又可以类比管道发声的原理。元音发音的关键在于舌位位置的前后高低,舌位位置的不同实际上是使声道的形状受到改变,当舌位位置靠前时共鸣管道长度较长,反之则共鸣管道长度较短,管道长度的长短不同导致了振动频率高低的不同。口腔发音和鼻腔发音的区别同样可以用管道原理来解释。单纯的口音发音只有口腔一个气流出口通道,而鼻音发音则相当于有分支的管道,鼻腔和口腔会发生耦合作用而产生零点,因此不同于普通音素的全极点模型,鼻音发音对应零极点模型。
一个声音产生之后需要被交际的另一方接收才算完成交际,接收端的心理因素占有很大作用。言语感知至今仍有很大的未知空间等待探索,《教程》中对这方面的介绍较少,只在书后最后一章从宏观的角度谈了一点听话人角度的感知区分原则,处于对立关系的两个音位,为了感知区分的需要,应是在区别特征上保持一定的感知距离。
语音从产生、传播到接收,是一个完整、系统的过程。不管是言语交际双方的互动还是发声方的声音创作过程和声音的物理传播过程,这些环节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声音产生系统,其各自的实现也是需要内部各系统的共同配合的。
二、语音的系统性
对于特定言语社群来说,语音系统本身是一个有规律、相互联系紧密的组织结构,其系统性体现在以下两方面:第一,纷繁而各自独立的诸多音位可以用几项物理参数分门别类地贯串起来;第二,呈现出互补的分布格局。
(一)特征层级系统
《教程》在最后一章介绍了一个特征层级系统,以对诸多的语音特征进行整理,其原理是:“在最具体的层面,语音特征可能和特定的发音动作或声学特征联系起来,也就是说‘双唇’这个特征不仅说明调音部位在唇部,而且还是双唇。特征是以层级形式排列的,每个层级的节点都和更具体的特征有关。”[2]279语音最基本的应用单位是音节,音节由音段构成,因此在特征层级系统里,处于最顶层的结构是音段,而最主要的语音学特征有喉上特征、喉部特征和气流机制。在此基础上,喉上特征又可以分为(调音)部位、(调音)方式和可能的鼻化和边音性等。
调音部位可分出唇、舌、喉等几个最基本的部位,这些都是我们定位辅音时最基本的发音部位。由调音方式特征所统辖的则有空隙度、拍音和颤音。空隙度是指气流通过的间隙的大小,按照间隙由小到大可分出塞音、擦音、近音和元音。从这个视角来看,这几种原本分属辅音和元音的音素就通过一项特征被整合到了一起。辅音是受阻碍的音,但元音发音时舌高点与口腔上壁事实上也形成了一定的空间,只是比起辅音缝隙来说这个距离要大得多而已。也就是说,擦音、近音和元音事实上只有量的区别而并无质的区分,只是出于感知和学习研究等的需要,才将他们分别范畴化,形成辅音和元音这两类相互独立的音。塞音和擦音的区别在于一个是阻塞音,而另一个是阻碍音,也就是气流所穿过的缝隙大小一个为0,一个大于0。但这仍然是停留在类的层面上看待两者的区别。我们还需要从一个更加微观的层面来分析它们。辅音的形成包括成阻、持阻和除阻三个阶段,从这三个阶段来看擦音是没有变化的,气流始终匀速通过阻碍的缝隙;而塞音则经历了一个从闭塞到瞬间打开的变化过程,那么在塞音发音的后半段,也即除阻的阶段,闭塞区的打开同样形成了一定开度的缝隙以供气体流出,从而爆破成声。那么,塞音的后半段跟后面的几类音也可以说是相同性质的。
喉部位不仅充当着为发音提供能源动力的阀门的功能,其声带的不同状态本身就能造就多种不同的语音特征。赖福吉将与喉部相关的特征分为喉头开闭度、喉头开闭时和喉头运动三种。喉头开闭度说明声带之间的距离有多大,不同的喉头开闭度导致多种发声态的产生,如清化、气声性、常态浊化、嘎裂声性、喉闭态等;喉头开闭时导致送气、不送气不同特征的产生;喉头或提升或压低时不同方向的运动则产生了喷音和内爆音等。[2]284喉部由于关系到上述诸多项特征,因此在语音演变时时常充当枢纽部位的作用,这一点笔者会在后面语音演变的系统性时展开论述。
对于气流特征,赖福吉认为在其统辖之下的有肺和软腭两项特征,气流来自肺部的音是常态浊音,气流撞击软腭就形成了音。
从以上内容看,赖福吉是从音系学的角度对各种语音因素进行的整理。目前的语音学和音系学将语音要素音段和超音段分为两大范畴,赖福吉将发音三过程“气流启动”“喉部发声”和“喉上声道(口鼻)调音”都归结到“音段”下,这对英语等以口鼻调音结果——音段——为主的语言来说是合适的,但是对于亚洲南部等以口鼻调音和喉部发声并重的语言来说,除了产生音段的调音活动之外,还有产生发声态的发声活动。[1]这是近一段时期语音学的新领域,朱晓农对赖福吉的这个框架进行了调整,增添了发声态的内容,将总的框架调整为“调音—发声”两大类,并著《语音学》一书,书中以专章对发声态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二)互补的分布
语音的系统性体现在特定音系的共时分布呈现互补的特征。最典型的例子便是音位变体。音位变体是处于互补关系中的一对或一组相似音素,这些音素可以归并为一个音位。《教程》举了英语的l作为例子。英语中lip(嘴唇)和pill(药片)两个词中的l,不仅所处的音节位置不同,其具体发音也有差异,甚至可以说一个是辅音,一个是元音。当l出现在音节开头时,其发音特征是舌体下降,以舌尖接触龈脊从而发音;而当l出现在音节尾时,整个舌体在口腔中向后上方抬起,舌尖不再接触龈脊。严格来说,这个音在英语中不是龈辅音,而更像是叠加了一个像后高元音[γ]那样的发音,因此这个变体叫作“元音化”的/l/,这种现象被称为“软腭化”。[3]64软腭化可以通过附加符号[~]来表示。l的这两种发音形式的分布模式为互补分布模式。常态发音的l都处于音节开头,软腭化的l都处于音节尾,音节尾的l之所以软腭化,可能是受了前面元音协同发音的影响。因为按正常发音舌位动程较大,处在元音后面时要从元音调整过来比较费力,所以采用了“元音化”的读法。
汉语的唯闭音和英语软腭化的l情况有共通之处。现代汉语音节一般是辅音1+元音+辅音2的结构,能充当辅音2的只有鼻音m、n、ŋ。但是在现代汉语方言和古汉语中,清塞音p、t、k同样可以充当辅音2,也就是作为韵尾出现在音节中,如粤语的叶读[jip3]、室读[sɐt5]、角读[kok3]。这些处于音节尾的塞音与处于音节开头作为辅音1的塞音,其发音存在细微的区别。常态塞音的发音经历了成阻、持阻、除阻三个阶段,然而当位于韵尾位置时,除阻的动作则消失了。这种只停留在成阻和持阻阶段而不爆破的塞音被称为唯闭音。这种唯闭音产生的生理机制是什么,我们还不清楚,但是英语中有类似的情况,也即塞音在位于音节尾时其塞音性(持阻)往往不那么明显,甚至会完全消失,和这种弱化现象有关的音素之一是重音,倾向于弱化的元音和辅音一般都位于非重读音节中。这其实也是协同发音所导致的。
还有很多种其他类型的音位变体,有不少情况是由协同发音产生的。可见共时的分布格局往往隐藏着音变信息,而这个音变过程,往往与音节内部诸要素之间的互动有关,这种互动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语音的系统性。
三、语音演变的原因
(一)生理机制
生理器官构造是发音的物质基础,许多语音演变都可以在生理机制上找到解释。上面主要介绍了协同发音的例子,下面笔者将对协同发音的生理基础进行介绍。
协同发音的产生在生理上有动作交叠和次要动作的“转正”两种机制。语音看起来是一个线性的序列,是一个个相互独立的音素先后排列而成的。但是,我们应该将每一个发音看成是一种连续的运动,而非若干静止部位的机械拼合,音素之间存在着交叉关系,甚至一个主要发音动作还“内包”着另一个附加的发音动作,尽管这个附加的动作不被赋予音位价值,但有时它们会在语音演变中转而成为“主角”。《教程》在第三章介绍了英语中出现的音姿交叠的现象,在第九章介绍了次要音姿及其引发的音变现象。音姿交叠指的是一个音和另一个音的发音姿态交相叠加在一起。[2]71比如一个送气音跟一个元音相接时,送气段会与元音的初始段结合在一起,发送气音时声带处于打开状态以供气体流出,这样的状态还未结束,口腔中就已经摆好发元音的舌位位置,口腔共鸣实际上已经开始。这时我们就可以看到辅音和元音的发音姿态呈现交叠的关系。音姿交叠的结果是我们常说的顺同化和逆同化影响。汉语普通话音系中鼻辅音在音节中的位置最为灵活,因此我们以鼻辅音与元音的互动为例,观察两者之间所发生的顺同化作用和逆同化作用。普通话的元音系统不存在口元音和鼻化元音的对立,元音的鼻音度都低于汉语鼻化元音的普遍标准40%,①数据来自时秀娟《汉语语音的鼻化度分析》,载《当代外语研究》2011年第5期。也即都是口元音。但是当口元音与鼻辅音相接时,会受鼻辅音的同化影响而带上鼻音色彩,具体表现为鼻音度达到鼻化元音水平,不管这个鼻辅音是作为鼻音声母还是作为鼻音韵尾。并且,鼻音当韵尾时对元音的影响比其当声母时对元音的影响要大得多,鼻音度的升高幅度也更大。②鼻音度指的是发一个音时鼻音能量在口音和鼻音总能量中的占比,鼻音度越高,鼻音色彩越浓。原词为Nasalance,时秀娟团队翻译为鼻化度,表示“语音发音时鼻音化的程度”。笔者认为,鼻音度高不一定是“被鼻化”的结果,汉语部分方言中系统性地存在不与鼻音结合但本身鼻音度就很高的音。因此,主张将带有互动义的“鼻化度”改为中性义的“鼻音度”。参见陈沛莹《汕头市区话复合元音的鼻化与非鼻化——基于普通声学数据和鼻流计的研究》,载《南方语言学》2018年第1期;时秀娟《汉语语音的鼻化度分析》,载《当代外语研究》2011年第5期。
然而,鼻辅音和元音的这种互动关系,是有条件的。对于不同的语言或方言来说,具体情况可能有差异。以闽南方言汕头话为例,汕头话是一种口元音和鼻化元音成系统性对立的方言,也就是存在不与鼻辅音相接而其鼻音度就已经达到了汉语鼻化元音的普遍标准,并且听感上能被感知为与口元音相互对立、彼此能区分意义的两类音。汕头话的口元音与鼻音声母相接时,同样会受鼻声母的顺同化影响而被鼻化;但是当其与鼻音韵尾相接时,则不会受鼻韵尾影响,仍然停留在口元音状态。表1是汕头话各口元音分别与鼻声母、鼻韵尾或者同时与两种鼻辅音相接时的鼻音度情况,可见:与鼻声母相接时,鼻音度提高至鼻化元音水平;与鼻韵尾相接时,鼻音度无质的变化;同时与鼻声母和鼻韵尾相接时,则因受了鼻声母的影响而提高到鼻化元音水平。

表1 汕头方言元音鼻音度与鼻辅音的关系
同化作用的产生还有音理上的条件。这种互动大多发生在两个相邻的音素之间。汕头话的鼻声母会对后接元音产生顺同化影响,但是当两者之间插入了其他音素成分时,这种影响则不会起作用。汕头话有一类以浊塞音为主要音位成分而同时以鼻音为附加成分的鼻冠音,作为音位变体形式,这类音的鼻音成分并不一定出现。但是,即使鼻音成分出现了,其后接元音的鼻音度仍然停留在口元音水平而并没有被鼻化。表2展示了同部位的鼻音、鼻冠音和清辅音各自的后接元音鼻音度情况,可见鼻冠音组的元音鼻音度与清辅音组更为接近,而与鼻音组不在同一个鼻音度水平,前者低于口元音和鼻化元音的分界线40%,而后者则高于这个分界线。“语音间的协同发音总会使声道某些部位受到很大影响,而其他部位所受临近音影响较小。逆同化的程度取决于两个目标音所确定的调音器官位置,协同发音的程度也取决于两个音之间的间隔。”[2]74这种规律看起来是有生理机制作为基础的。
次要动作的“转正”也是协同发音产生的一种重要机制。这种音变与发音时的次要音姿有关。次要音姿(或者叫次要发音)是一种在主要元音音姿上同时带有轻微持阻的音姿,也就是在主要发音动作之外还伴随着另外一个附加的发音动作。《教程》第九章对介绍了四种次要音姿的类型,分别为腭化、软腭化、咽化和唇化。

表2 汕头话m、n、ŋ与mb、ndz、ŋg与p、s、k对照组后接元音鼻音度
“腭化是在一个音姿上加入前高舌位音姿。”[2]242汉语语音史上发生的腭化运动,本质上是起因于一种次要发音,也即叠加了前高元音[i]舌位的发音动作。舌根音见组和舌尖音精组在与舌面高元音[i]相接的过程中,因为主要音姿向硬腭区靠拢,而在历时音变中逐渐叠加了一个像前高元音[i]那样的发音,进而发音部位逐渐向硬腭区靠拢,这个次要发音渐渐地“喧宾夺主”而成为了主要发音,原本的舌根音和舌尖音也就渐渐变成了硬腭音,于是完成了腭化的过程。腭化首先是一个次要音姿,这个次要音姿在一次次发音的强化中逐渐转为主要音姿,因而实现了音变的过程。
(二)物理因素
语音传递的过程同时也是声波传播的过程,一些物理因素和物理环境同样会对语音产生影响,甚至进而导致音变。前面我们提到鼻辅音会使相邻口元音鼻化而变成鼻化元音,Ohala提出:发音与声学—听觉事实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其中,清擦音和送气塞音等发音时产生的高气流会导致元音的声学性质受到改变,这种转变使它在声学特征上与鼻化元音相似,听感也像鼻化元音。这就可能使听者模仿而转述为实际生理上的鼻音。[4]可见,物理环境上的细微变化会通过误导听音人而在习得时产生偏差,从而导致真实的音变。
容易引发鼻音听感的不仅有特定辅音,还有特定的元音。据研究,高元音容易引发鼻音增生,因为高元音容易产生“颤噪效应”。House和Stevens研究指出:只要有少量的鼻流,就会修改高元音([i]、[u])的语图,而低元音不会产生这样的现象。如果说话人在发[ti]、[ɡu]这样的音时,在不经意之中鼻音度稍微增大一点,听者就容易产生鼻音感的错觉。因此,虽然根据时秀娟的研究,元音越低鼻音度越高,[5]但是要在听感上达到非鼻音听出鼻音的效果,却是低元音要远远难于高元音。[4]
(三)心理因素
从上面的分析不难看出,一些物理现象和规律也能成为推动音变的动力,而在这个过程中,起最直接作用的是听话人对这些物理现象的接收和对此作出的反馈,这样才能导致音变的产生。Ohala将这样一种机制称为听者启动的音变原理,强调听觉感知在语音演变中的作用。可见,听话人的心理因素同样会导致语音演变的产生[4]。
心理因素对语音演变的影响还可以体现在句调方面的语音演变。连读变调的产生除了最基本的语音方面的原因之外,有些方言的连读变调和句调的语音演变还与语法、语用等说话人的心理因素有关,这个时候的语调变化是说话人为了实现一定的信息聚焦目的而在词、句中的重音侧重的变化。闽南方言的连读变调十分复杂,至今仍未被研究透彻。有学者对闽南方言汕头话的连读变调进行了研究,认为汕头话之所以呈现出如此复杂的变调规律,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汕头方言连读变调规则绝不仅仅局限于语音层,在语句中,当连读变调进入动态的运行时,可以看到词汇、语法、语气、韵律各层都有规则在起作用”[5],也就是说,除了一般方言所常见的语音条件之外,汕头话的连读变调常常还用来区别语法结构、表示语法意义和实现某些语法功能。那么在这里,说话人对于交际目标的把握,调控着语调的演变。
四、语音演变的系统性
语音是一个内部平衡的系统,语音演变的实质是区别特征的转移或音素的流转。汉语语音史上浊音清化的过程就是经典的辅音清浊特征转移为声调特征和辅音送气不送气特征的案例。
浊音清化指的是中古的全浊声母字到了现代汉语普通话失去了浊音的区别性特征而成了清音。我们知道,以切韵音系为代表的中古音系是清辅音和浊辅音成系统地严整对立,既有塞音全浊声母,也有塞擦音、擦音全浊声母。塞音、塞擦音的全清、次清、全浊三位对立与全浊擦音、全清擦音二位对立是中古汉语典型的音系特征。可见从中古到近代,浊声母中只有次浊声母明m、泥n、来l、疑ŋ保留了下来,而三十六字母中的全浊声母並、奉、从、邪、定、澄、床、禅、群、匣母十个母,则分派到了上述的21个清声母中,也就是清化了。清化时按照特定的语音条件,如“平送仄不送”便是官话全浊声母清化时所遵循的规则。
全浊声母清化的语音现象得到了当今大多数汉语方言实例的支持,现今的汉语九大方言中,除了吴语和老湘语之外,几乎其他的各大方言都不复保留中古的全浊声母。就连公认的存古性最高的闽语和粤 並语,、奉、从等全浊声母也都已清化成了相应的清声母。而对于今天最系统地保留了浊音的吴语来说,其浊音事实上也显示出了清化的趋势,而不是完全、完整地保留了浊音。据学者的研究,吴语中的古全浊声母字在今天的上海等一些方言点,实际上是清音浊流的读法,而非常态浊音。也就是说,即使是在全套保留古全浊声母的吴语里,其全浊声母事实上也已经迈出了清化的步伐。上海话中的全浊声母字,只有在动态语流中才保留其浊的特征,而在其他环境下,事实上属于“清音浊流”的属性①,而这个“清音浊流”,其辅音特征实际上是一个清音,只是在元音部分增生了气声的特征。
对于清音浊流,一开始很多学者将其理解为是一种辅音特征。赵元任是第一个以“清音浊流”这样的名称来指称吴语中的浊音,他的描述是,“吴语的浊音单念时并非真正的带声,而是‘清音浊流’”,并将这类音记为pɦ、tɦ、kɦ等,即清辅音音标加上一个代表浊流的送气音ɦ。①详见赵元任《现代吴语的研究》,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后来,随着实验语音学的发展,在新技术及仪器的辅助下,人们更清楚地了解了吴语这种清音浊流的真正声学性质。任念麟[6]、曹剑芬[7]、陶寰[8]、陈忠敏[9]等提出,吴语清音浊流是元音的特征,辅音实际上已经完全就是个清音了。清辅音后面接着一股浊气流,这个浊气流从元音开始一直贯穿整个音节,此时元音的状态实际上是一个气声。气声是一种声带闭合大约2/3的发音类型,发音时声带大部分闭合振动,小部分敞开从而使气体逸出,进而造成一种“浊流”的听感。这个浊气流发生在后接元音的前半部,人们在感知上把元音的浊送气误认为前面的声母是浊的,因此早期将清音浊流误以为是辅音问题。这样看来,对于现代吴语来说,其古全浊声母实际上在上海等一些语言接触较为频繁、语音变化较快的地区,已经是清化了的状态,只是残留了一些浊的辨识特征嫁接在元音上面。可见浊音清化大体是将清浊特征的对立转移为声调区别的对立。
在辅音清浊和声调互动过程中,送气不送气特征也作为一个附加特征参与了这个演变过程。浊音清化时伴随着送气不送气特征的分配。中古浊辅音本无送气不送气之分,但是汉语官话大多数方言在清化之后,按声调条件古平声字变为同部位送气清音,古仄声字变为同部位不送气清音,这两批字产生了送气不送气的区别。可见,在这个过程中,辅音系统的清浊特征转移为送气不送气特征。这里体现了语音系统的平衡性趋势:一项区别特征的取消,可能伴随着另一项区别特征的产生,这样才能继续保持两批字的对立。区别特征的转移是有条件的,从这里来看,应该是以相邻的特征优先,也即遵循就近原则。浊音清化的过程中辅音的发音部位并没有发生改变,因此特征转移只能从发音方法开始。现代汉语的两组发音方法一个是清浊,另一个就是送气不送气特征。由此,为了浊音清化,将清浊特征转移为送气不送气特征提供了音理上的可能。声调演变时,古平声按照辅音清浊的原则平声送气仄声不送气,也呼应了上述规律。从音节结构的角度来看,辅音清浊与声调演变的这种互动演变,也是可以得到生理上的解释。汉语音节结构为辅音+元音+(辅音)+声调,其中声调属于超音段音位位于音节层次的第二层级,覆盖辅音+元音+(辅音)的音段音节,当辅音为浊音时则全音节覆盖,当辅音为清音时则只覆盖元音。在这样的音节结构中,辅音的清浊特征属于嗓音特征,也就是由声带进行声源发声而不需要经过口腔调制,声调也是嗓音特征。人的完整发音包括声带作为声源的振动发声和声音信号经过口腔时受口腔共鸣体形状调制而音色得到修改,这两部分的内容。浊辅音和声调都是单纯的嗓音信号,是不需要经过口腔腔体的调制就可以形成的声音,在生理上比同时需要声源发声和口腔腔体的调制才能形成的元音更为接近,因此浊辅音和声调在演变中的互动更为活跃。由此可见,辅音和声调的互动演变也展示了区别特征转移过程中的就近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