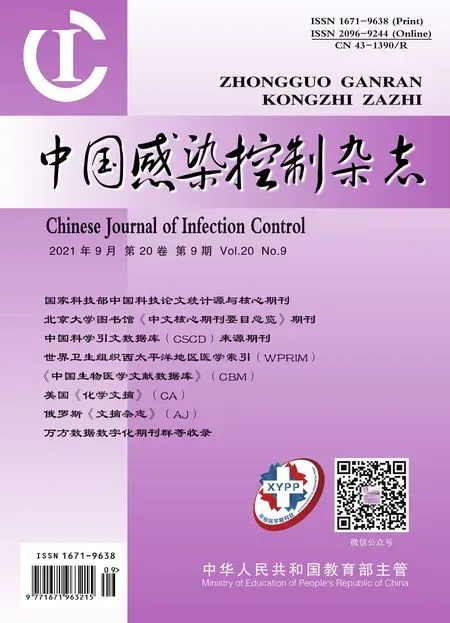国外血液透析机构医院感染暴发的研究现状:1987—2021年
张 慧,宗志勇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医院感染管理部,四川 成都 610041)
血液透析(以下简称血透)患者常合并糖尿病、高血压、心血管疾病,且需要长期留置导管,是感染的高风险人群。血透患者不仅可能发生经血传播病原体的感染,如乙型肝炎病毒(HBV)和丙型肝炎病毒(HCV),还可能发生细菌、真菌和其他病毒所致的感染,尤其是细菌所致的血流感染。血透操作过程复杂,多种原因可导致感染暴发,诸如布局流程不合理、制度不健全、设施设备的清洁消毒不彻底、无菌技术和手卫生执行不到位等。近二十年来,血透医院感染暴发事件在国内外以及部分发达国家时有发生,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我们应该不断地从这些暴发事件中吸取经验教训,更多地从系统层面关注和解决问题,推动医院感染防控措施的真正落实,减少医院感染的发生,从而保障医疗质量安全。因此,本文通过在PubMed上检索血透暴发事件相关的文献,总结分析1987年至今国外血透机构医院感染暴发情况,以期为今后的血透医院感染防控措施的制定和监管提供参考。
1 经血传播病原体医院感染暴发
1.1 HBV 终末期肾病患者因暴露于血液制品和免疫状态受损有感染HBV的风险,定期筛查、隔离对维持安全的透析环境至关重要,但血透人群细胞和体液免疫的改变却导致疫苗接种效果不理想[1]。研究[2]显示,透析患者对乙肝疫苗缺乏免疫应答与年龄、糖尿病、HLA-DR3状态、较短的透析时间、较低的营养状况、 较低的血红蛋白、较低的甲状旁腺激素水平和较低的透析充分性有关。因此,尽管感染防控措施的实施和乙肝疫苗的使用,促使血透患者的HBV感染率有所下降,但必须继续保持警惕,以防止这种强大的DNA病毒的传播。我国近年发生的一起青岛市城阳区人民医院血透患者感染HBV事件,暴露出当事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对血透室医院感染管理工作部署落实不力、医院感染管理不到位等问题[3]。相较于国内,国外近二十年前已有相关文献报道。
1.1.1 墨西哥[2]Zaidi-Jacobson等[4]报道墨西哥一所血透机构的HBV感染暴发事件,5个月内4例患者感染(发病率为14.8%)。因无全国性的血透患者HBV感染监测系统,研究者认为患者和工作人员的实际感染率可能更高,并强调了实施血清学筛查、加强透析机和透析单元环境消毒、预防血液和体液污染、患者和医护人员接种疫苗的重要性。
1.1.2 日本 Tanaka等[5]报道,1994年9月9日—10月3日,在东京某透析病房进行维持性血透的5例患者相继感染HBV,其中4例死于重型肝炎。该病房每周8个班次,181例患者每周分别透析3次。5例患者与其他27例患者(包括2例HBV携带者)在同一班次透析,其中1例HBV携带者造成了HBV感染的暴发。
1.1.3 美国 Hutin等[6]调查1995年12月—1996年5月美国某县慢性血透患者HBV感染暴发情况。该县有两个透析中心(A和B)和一所医院(C)。6例患者分别在两个中心进行透析,均于1996年1—2月在C医院住院。患者1通常在A中心透析,于1995年12月转阳,其他患者于1996年3—4月转阳。研究者开展了两项队列研究:一项在A中心透析的患者中进行,以确定传播发生的地点;另一项于患者1住院期间在C医院透析的患者中进行,以确定与感染相关的因素。结果显示,A中心有4例(15%)发生HBV感染;患者1在C医院住院与HBV感染相关(P=0 .002),因患者之间经常共用物品和多剂量药瓶,为传播提供了机会。该研究提示,慢性血透患者住院期间需要透析时,应复查乙型肝炎表面抗原(HBsAg),不得共用仪器、物品和药物。
1.1.4 巴西 Lewis-Ximenez等[7]在巴西一所血透机构HBV感染暴发期间,对患者进行了血清学病毒标志物和疫苗免疫应答状况评估。结果显示,26例患者感染HBV,其中HBsAg阳性20例,阴性6例,但核心IgM抗体(anti-HBc)和HBV DNA阳性。主要感染源未明确,但其中2例患者疑似为传染源。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抗-HBs滴度低和疫苗免疫应答反应低下是HBV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检测到的高HBV感染率(31%)和观察到的疫苗免疫应答反应低下(53%)都强调了标准预防措施在控制HBV感染方面的重要性,同时应重视抗HBc检测在血透机构HBV常规筛查中的价值。
1.2 HCV 我国2003—2010年发生多起HCV感染暴发事件,卫生管理部门高度重视,于2010年先后颁布《医疗机构血液透析室基本标准》和《血液净化标准操作规程》[8-9],但暴发事件仍时有发生。在国内外近期的暴发事件中,引起广泛关注的是新加坡中央医院的HCV感染暴发事件,但很多暴发事件并未上报或进行文献报道。从现有的文献报道来看,暴发原因主要包括:手卫生不当、环境和物体表面清洁消毒不到位、不安全注射、共用透析机等。
1.2.1 美国 在美国,血透患者中HCV感染的流行率比普通人群高5倍。Niu等[10]报道,1987年1月—1988年10月,美国一所血透机构有35例患者血清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升高,提示为非甲、非乙型肝炎。该机构对所有透析患者和工作人员进行了三次(间隔9个月)抗-HCV酶免疫检测,对患者家属和性接触者进行了一次抗-HCV检测。结果显示,HCV感染发病率为5%,35%(27/77)的患者抗-HCV阳性,工作人员、患者家属和性接触者抗-HCV为阴性,82%的很可能病例、44%的可能病例、44%的可疑病例和12%的非病例中发现抗-HCV阳性(P< 0.01)。这些病例既没有共同来源,也没有直接的人传人记录,但感染控制措施落实不到位,如未按要求使用手套,未及时进行手卫生。
Rao等[11]调查了8例新发HCV感染的门诊血透患者。流行病学调查和基因测序结果显示,传播可能发生于经常在同一或相邻透析机同一或连续班次治疗的患者之间。另外,感染控制措施执行不到位,如胃肠外用药的准备、处理、给药等环节,因此应加强对所有工作人员的感染控制教育和培训。
2012年11—12月,费城6例血透门诊患者被诊断为HCV感染[12]。进一步调查发现,自2008年1月1日—2013年4月30日在该诊所确诊18例患者,发病率约为16.7%。此18例患者和既往感染患者在同一班次的相邻透析机接受治疗,或连续两班在同一透析机接受治疗。通过一种法医学化学发光剂评估环境清洁效果,发现诊所的多个物体表面都有可见和不可见的血液。感控措施也存在不足,如员工在不同机器间操作时未更换手套,或在接触机器后未进行手卫生,未明确标注干净水槽和污染水槽,静脉配药和给药不规范,擦拭机器表面不彻底等。
1.2.2 法国 Delarocque-Astagneau[13]等调查了法国一所平均收治90例患者的血透病房HCV 2a/2c基因型的传播途径。该研究选取了在1994年1月—1997年7月HCV基因型2a/2c血清转化的患者,并且在发病前3个月内曾在该病房接受透析治疗。结果显示,HCV血清转换与同抗-HCV(基因型2a/2c)阳性患者在一台机器或同一房间进行透析相关。还观察到患者回血的外部压力管的传感器保护器潮湿,可能导致血液污染透析机的压力传感端口,且无法进行常规消毒。该病房自加强感染控制和更换传感器保护器以后,未发生其他病例感染。
Savey等[14]研究了法国一所血透机构HCV感染暴发期间病毒的传播模式。结果显示,2001年收治的61例未感染HCV的患者中,有22例(36.1%)于2001年5月—2002年1月发生HCV感染,发病率为70 / 100患者·年。聚类分析确定了4个不同的HCV组与1例病例有相似的病毒。如果护士“刚好之前”或“接触一例患者之前”曾连接过HCV感染患者的透析机,则会增加HCV感染的风险,提示HCV主要通过医护人员的手传播。直接观察还发现,血液会涌入动脉压测试管组的双过滤器接口处,提示由于内部部件可能受到污染,不能排除HCV通过透析机传播。
1.2.3 德国 在德国,HCV感染在血透患者中的患病率为15%~30%。Grethe等[15]报道了1997年在一所血透机构暴发的HCV事件。采用聚合酶链反应(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方法从19例患者血清中扩增出HCV高变区1(hypervariable region 1, HVR1),并直接测序。14例新感染患者与2例感染数年的患者HCV分离株密切相关。该研究强烈推荐对非感染患者和新入患者进行反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T-PCR)分析,以早期发现和预防HCV。
1.2.4 西班牙 2001年,西班牙雷亚尔市的一所血透机构发生一起18例患者HCV感染暴发事件。随后调查显示,1998年1月1日—2001年9月30日,有86例患者在血透机构接受治疗,其中在2001年1月3日前HCV感染27例(31.4%)。自1998年以来,只有一例血清转化被记录在案(1999年)。所有病例均为4d基因亚型,在西班牙不常见(占3%),提示所有病例均有共同的初始来源,由相同的病毒株引起。既往HCV感染病例多为1b,3例为4c/4d,1例为1a。IgG活动性研究表明,并非所有病例均为同时感染,可能是由于患者之间的二次人传人所致。透析轮班是感染的危险因素,在星期二-星期六-星期四轮班接受透析治疗的患者中,无一例感染[16]。Bracho等[17]分析了2002年西班牙卡斯特罗一家私人诊所3例患者HCV转阳的暴发事件。该研究明确至少存在两个独立的传播事件,涉及两个不同的感染源患者和三个血透患者,也提示彻底修订血透的操作程序非常必要。
1.2.5 意大利 Spada等[18]报道了意大利一所血透单位暴发的HCV感染事件。在2003年4—10月,4例患者抗-HCV血清转阳,均是在原有入院时抗-HCV已经阳性的10例患者的基础上增加。对这14例患者进行HCV RNA和HCV基因检测,结果显示4例新感染患者均携带2c基因型HCV,而在原有10例患者中,2例也检测出2c基因型HCV。进化分析表明,所有新感染 HCV-2c 的患者都携带密切相关的病毒分离物,且与其中1例 HCV-2c 慢性感染患者有关。进一步调查发现,4例新感染患者中,有3例与该例慢性 HCV-2c 感染患者在同一日和同一班次接受了透析,但使用不同的机器。另外1例HCV-2c新感染的患者和上述3例中的1例在同一日不同班次接受透析,但使用同一台机器。暴发可能是由于感染控制措施落实不到位,但不能排除通过其中1台相关的透析机传播。
1.2.6 越南 2013年,越南的一所血透机构有11例患者抗-HCV转阳[19]。调查发现,所有患者均重复使用透析器且共用血透机,有一复用处理系统用于冲洗透析器。静脉注射药物和清洁用品的准备区毗邻血标本处理区和重复使用透析器的存储区。在11例病例中,1例可能是通过共用透析机传播,其余10例可能通过间接接触传播。而共用血透机不是本次暴发的主要危险因素,最可能的原因是环境污染。该暴发提示配备专用的透析器再处理系统和严格遵守感染控制预防措施以防止HCV交叉感染尤为重要。
2 细菌引起的医院感染暴发
除了经血传播病原体,血透患者还常发生细菌所致的医院感染暴发,常见的有洋葱伯克霍尔德菌、黏质沙雷菌、铜绿假单胞菌等。暴发的主要原因不仅与手卫生依从性低有关,还包括废液处理系统不合格、水处理系统不合格、皮肤消毒剂不合格等。
2.1 多种细菌 Arnow等[20]报道了在美国一所大学附属医院的两个慢性血透中心8个月内发生了29例16种病原菌引起的血流感染暴发事件,导致21例患者入院,23根透析导管拔除。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所有感染患者均有导管,且在星期一、三、五接受治疗,并使用同一台严重污染的透析机。培养和模拟试验表明,血液中的病原体存在于近期安装的用于处理使用后的启动盐水附件中,并可在透析器启动和组装期间直接或间接进入血管通路导管。该中心针对附件采取措施后疫情得到控制,提示在血透设备的设计和使用中,应考虑微生物的重要性。设计设备时需要重点关注处理透析废液,因其中含有平衡盐、碳酸氢盐、葡萄糖和膜后有机溶质,可支持细菌生长到浓度为108CFU/mL。
美国丹佛一所医院对该中心接受透析的患者进行了回顾性队列研究[21],发现1999年1月—2000年1月基线期血流感染(BSI)发病率为0.7/100患者·月,而从2000年2月—2001年4月,BSI发病率上升至4.2/100患者·月。该暴发为多种微生物感染暴发,约有30种。75%的BSI与中心静脉置管(CVC)相关,原因是2000年1月该中心因所有权变更,预先包装的CVC敷料包和每两周一次的感染控制监测被中断。因此,从2001年5月开始,对工作人员进行了CVC培训,用氯己定代替聚维酮碘进行皮肤消毒,用纱布代替透明敷料,CVC出口部位停用含聚乙二醇的抗菌软膏,并对CVC患者进行健康教育。干预期结束后,截至2001年10月,BSI发病率降至不到1.0/100患者·月。该研究指出,正确进行皮肤消毒和通路护理是预防血透患者BSI的关键,感染控制程序、工作人员和患者教育以及使用最佳的抗菌剂或预先包装的工具包都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
2.2 革兰阴性菌 Beck-Sague等[22]报道,1988年4月4—20日,11例复用透析器的患者中,9例发生发热反应,5例发生革兰阴性菌血症。复用透析器的患者与不复用透析器的患者,发热反应或菌血症的发生率分别为4.5%和0(P=0.03)。透析器采用2.5%的伦拿灵消毒剂进行消毒后复用。在暴发期间,储存的12个复用透析器中伦拿灵浓度变化较大(0.9%~4.2%);内毒素浓度中位数为0 ~ 246 ng/mL,伦拿灵浓度≤1.0%透析器的内毒素浓度中位数高于较高伦拿灵浓度的透析器(P=0.01)。采用一名技术人员提供的稀释方法,制备容器表面至底部的伦拿灵浓度为1.4%~3.5%。上述研究表明,稀释时未能充分混合伦拿灵可能与透析器中消毒剂水平低、细菌和内毒素水平高以及透析患者中发热反应和革兰阴性菌血症的暴发有关。
Humar等[23]回顾性分析1993年3月4日—6月28日10例颈内静脉置管的革兰阴性菌血症血透患者。结果显示,预冲的废液收集袋长时间未清空,定量培养出>200 CFU/mL的革兰阴性杆菌,包括血培养中分离的菌种。在启动期间,透析管路和连接器被浸泡在废液收集袋中,在连接患者之前,管路未进行消毒。采取控制措施后,包括每次使用后清空废液收集袋和每日消毒,所有的透析管路在连接患者前均需消毒,未发生新病例。
Jackson等[24]报道,美国一所血透中心的11例患者中发生了6例革兰阴性菌血症和7例热原反应。调查发现,透析用水、复用用水以及透析液中细菌和内毒素浓度超过了医疗器械进步协会(AAMI)推荐的允许浓度,且透析机未每日进行热消毒。
1997年2—9月,在以色列耶路撒冷的一所血透单位发生了8例无临床证据来源的革兰阴性菌血流感染[25]。所有感染都可以追溯到13台正在使用的透析机中的3台。流行病学调查发现,透析机的废液处理系统是感染的来源,停止使用废液处理系统后暴发停止。
2.3 黏质沙雷菌、铜绿假单胞菌和阴沟肠杆菌 黏质沙雷菌可自水、土壤、人和动物的粪便中分离出,在机体免疫功能降低时,可引起肺炎、泌尿道感染和败血症。铜绿假单胞菌也广泛分布于水、土壤、空气、医院环境,可通过污染医疗器具及医护人员手引起医源性感染,感染多见于皮肤黏膜受损部位,也见于长期化学治疗或使用免疫抑制剂的患者。血透患者不仅免疫力低下,且长期留置静脉导管,为阴沟肠杆菌侵袭血管通路提供了机会。
Sanchidrián S等[26]报道在西班牙医疗机构发生了因抗菌溶液细菌污染导致隧道导管血透患者发生黏质沙雷菌血症。Pereira等[27]报道了一起印度某血透机构暴发的黏质沙雷菌血症事件。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也调查了一起在3所门诊血透机构暴发的革兰阴性血流感染事件[28]。2015年7月—2016年11月在A、B或C机构接受血透的患者中,58例发生革兰阴性菌血流感染,其中48例(83%)需要住院治疗,主要病原菌为黏质沙雷菌(21例)和铜绿假单胞菌(12例)。调查发现,在透析液组件和透析处理站内排水管道连接的嵌入式壁盒处有废液汇集和回流现象。环境采样从壁盒采样标本中分离出黏质沙雷菌和铜绿假单胞菌。通过脉冲场凝胶电泳和全基因组测序,发现壁盒中分离的黏质细菌与病例密切相关,因此推断可能因壁盒的废液通过医护人员的手污染中心静脉导管。
Arenas[29]也报道了西班牙阿利坎特的一所血透机构长期使用隧道血透导管的患者在2个月内发生11例次菌血症,9例为铜绿假单胞菌。调查结果显示,水龙头可能导致铜绿假单胞菌感染,患者是感染源,通过人传播到导管。
Wang等[30]调查了一起美国马里兰州一所血透中心1996年12月1日—1997年1月31日暴发的菌血症。通过回顾感染控制措施、水系统和透析机的维护和消毒程序,对水和透析机进行培养(包括废液处理器,一个排污口,患者透析之前用于冲洗透析器的盐水),采用脉冲场凝胶电泳对分离株进行比较,结果显示:94例患者在27台透析机上进行透析,其中10例(11%)患者出现革兰阴性菌血症。致病菌为阴沟肠杆菌(6例)、铜绿假单胞菌(4例)和大肠埃希菌(2例),2例患者为多种微生物感染菌血症。与革兰阴性菌血症发生相关的因素是CVC和3台透析机,从透析机中培养出阴沟肠杆菌、铜绿假单胞菌或同时存在这两种菌。26台机器中有8台(31%)出现了废液处理器阀门故障,其中包括与病例患者流行病学相关的3台机器中的2台。该研究表明,废液处理器瓣膜功能不全和由此产生的回流是透析管路和患者CVC交叉污染的来源。因此,在更换有故障的废液处理器阀门和加强透析机消毒后,暴发终止。
2.4 洋葱伯克霍尔德菌、无色杆菌 导管维护不当是血透机构感染暴发的重要原因之一。国外有多篇文献报道了因消毒剂导致血透患者发生洋葱伯克霍尔德菌和无色杆菌菌血症的暴发事件。洋葱伯克霍尔德菌是一种环境中广泛存在的革兰阴性杆菌,与医院感染有关。该菌易在供水系统、滤膜和消毒剂中生长。西班牙马德里阿尔科本达一所血透中心就因使用污染的洗必泰导致洋葱伯克霍尔德菌感染暴发[31]。Rolón Ortiz等[32]也报道,2014年巴拉圭某血透单位暴发洋葱伯克霍尔德菌感染事件。R Bellazzi等[33]报道意大利20例血透患者因洋葱伯克霍尔德菌引起CVC感染而暴发的菌血症。由于该菌存在于血液、中心静脉导管的生物膜、供水分配系统中均有过记载,此点和其他混杂因素影响其感染源的明确。最终,从一次性无菌包内用于皮肤消毒的氯化铵溶液中分离出完全相同的菌株。Kaitwatcharachai等[34]报道泰国一所血透机构9例患者发生洋葱伯克霍尔德菌血症。采用随机扩增多态性DNA分析发现,患者和消毒镊子(锁骨下静脉导管换药时用于夹取棉球和纱布)的洗必泰稀释液中分离的菌株一致。该研究表明,洗必泰消毒剂细菌污染是9例患者发生感染暴发的细菌来源。2014年1月,加的斯一所血透中心发生洋葱伯克霍尔德菌菌血症暴发[35]。该中心对患者和环境采样,结果从7例患者的血培养、3个导管封管液和2瓶洗必泰消毒剂中均分离出洋葱伯克霍尔德菌。利用脉冲场凝胶电泳和多位点序列分析发现,暴发由同一株菌引起,提示可能有共同的传染源和人传人的二次传播。
木糖氧化无色杆菌是一种罕见的菌血症致病菌。Tena等[36]首次报道了由木糖氧化无色杆菌引起的中心静脉导管相关菌血症暴发事件。在西班牙的一所血透机构,2周时间内4例长期留置导管的血透患者血培养中分离出木糖氧化无色杆菌,从一瓶含2.5%洗必泰的喷雾剂中培养出木糖氧化无色杆菌,且该洗必泰消毒剂曾用于皮肤消毒。采用脉冲场凝胶电泳分析,前3例患者分离菌株和喷雾剂检出的菌株一致,第4例患者分离菌株比引起暴发的菌株多6条带。停用喷雾剂后,无新增病例。该研究认为使用稀释的洗必泰喷雾剂用于静脉导管护理达不到消毒效果,可引发感染,应引起重视。Vázquez等[37]也报道了墨西哥首次因血透患者中无色杆菌引起的菌血症暴发。
2.5 嗜麦芽窄食单胞菌、皮克蒂尔氏菌 接受血透的患者发生血流感染通常与污染供水、水处理、分配系统或再处理透析器有关。巴西一所大型血透中心因嗜麦芽窄食单胞菌(21例)和洋葱伯克霍德菌(例)引起血流感染暴发,导致3例(7%)患者死亡,其中2例是嗜麦芽窄食单胞菌引起的菌血症,另1例为洋葱伯克霍尔德菌感染。该中心从血透系统的不同部位采集水标本进行培养和分型。通过PCR-RAPD和脉冲场凝胶电泳进行基因检测,结果在透析用水中发现了相同的基因型,并在水分离株中鉴定出多个基因谱,表明污染严重。该中心在实施了标准控制措施后,菌血症病例依然存在,表明管道系统已被微生物生物膜污染。最后,在更换整个管道系统后暴发结束[38]。
皮克蒂尔氏菌是一种非发酵革兰阴性杆菌,常存在于潮湿的医院环境中,特别是水源,如牙科用水、医院供水和工业超纯/高纯水,易在塑料工业水管中形成和维持生物膜。May等[39]报道了一起因非发酵革兰阴性菌导致的血透暴发事件,其中有4例患者感染皮克蒂尔氏菌和3例患者感染嗜麦芽窄食单胞菌。分析发现,透析器重复使用和水处理设备是造成感染风险的原因之一。通过加强一般消毒程序、维修和更换水处理系统的旧部件以及暂停重复使用透析器,暴发得到控制。
2.6 甘露醇罗尔斯顿菌 甘露醇罗尔斯顿菌是一种革兰阴性细菌,是医院获得性感染中一种新出现的条件致病菌,主要影响免疫功能低下的患者。2016年10月—2016年11月,班加罗尔曼尼帕尔医院门诊血透室发生了一起感染暴发事件,5例患者感染甘露醇罗尔斯顿菌,其中1例为感染性心内膜炎。感染暴发后,血透室立即进行了环境微生物学采样,包括治疗室的家具、电子设备、血透设备、导管和药品推车、皂液、洗必泰、用于静脉配药的无菌水和生理盐水。结果发现,无菌水培养出甘露醇罗尔斯顿菌。感染控制部门要求弃用整批无菌水,并且对透析用水进行加氯处理和室内消毒后,暴发得到控制[40]。
2.7 艰难梭菌 2012年10月—2013年3月,美国密歇根一家血透诊所的37例门诊血透患者中,6例患者出现艰难梭菌感染,5例随后发生[41]。所有病例均为社区发病,其中3例为医院感染,且来自同一所医院。一名工作人员在照顾第1例有症状的患者后,也检测出艰难梭菌。暴发事件发生后,该血透诊所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包括指定3台透析机作为所有艰难梭菌感染患者的接触隔离区域,直到抗菌药物治疗结束后2周。工作人员在护理这些患者时,要求穿专用的一次性隔离衣和戴手套,操作结束后用皂液和水洗手;对患者进行治疗后,使用1∶10稀释的漂白剂消毒透析区域的环境表面,并确保消毒剂在物体表面有足够的停留时间;加强手卫生检查。截至2013年6月,无新发感染病例。
2.8 无乳链球菌 侵袭性B族链球菌(Group BStreptococcus,GBS,无乳链球菌)疾病在成年人中呈上升趋势。GBS已从人类直肠、阴道、宫颈、尿道、皮肤和咽部的培养物中分离出来。在健康的年轻男性和女性中,定植率可能分别高达20%和34%。侵袭性GBS疾病可能与社区或医疗保健相关。Baraboutis等[42]报告了一所血透机构暴发的GBS导管相关菌血症,有2例患者感染,时间间隔数小时。该血透机构对所有与两例GBS感染患者在同日治疗的患者以及所有医护人员均进行详细的问卷调查及拭子培养。同时,审查医疗和护理记录,追踪感染控制和导管护理实践。结果显示,所有患者及工作人员的肛拭子或阴道拭子培养均未见GBS阳性。近期热病的进展与是否使用血透导管(P=0.028)和在最后两次透析期间由特定护士护理超过30 min有显著相关性(P=0.007),因此推测GBS菌株是通过医护人员的手在患者之间传播。
2.9 肺炎克雷伯菌 Welbel 等[43]报道,6例慢性血透患者在11 d内发生血流感染,感染的肺炎克雷伯菌具有相同的血清型和相似的质粒谱。6例患者可能在第4班次接受透析治疗并且复用透析器。调查发现,1例动静脉瘘患者在第4班次感染肺炎克雷伯菌。透析器复用人员在治疗区接触患者和其透析器间未更换手套,在第4班次结束后继续处理患者的透析器。血透室在修订透析器复用流程和强调手套更换后,无新发血流感染。
2.10 结核分枝杆菌 Kobayashi等[44]报道,在日本一所血透机构发生了泛耐药肺结核(XDR-TB)暴发。原发病例为一例51岁男性血透患者,7年前曾患结核分枝杆菌感染。患者经异烟肼(INH)、利福平(RFP)、乙胺丁醇(EB)治疗后完全恢复,无耐药性,后于2006年6月因肺结核复发而住进另一所医院。起初,该患者接受了HRS治疗,但在8月依据药敏试验结果改为INH、EB、左氧氟沙星和卡那霉素治疗。由于肺结核复发和痰培养转阳,患者于2007年6月再次入院,且检出泛耐药结核分枝杆菌。之后,血透机构的5名工作人员和患者的1名家庭成员被诊断为XDR-TB。感染的工作人员在同一间透析室工作,所有病例均出现耐药,3例发生耐药基因突变。关于肺结核暴发的原因,首先是对结核病再次恶化的诊断延误了4个月;其次,在病例2中,患者在首次诊断为哮喘后发展为喉部和气管支气管结核,结核病诊断延迟;第三,病例2的痰涂片呈强阳性。
2.11 成团泛菌 Borrego等[45]报道了一起在圣塞西里奥大学医院血透室发生的因成团泛菌引起的菌血症暴发事件。
3 真菌引起的医院感染暴发
3.1 单胞瓶霉属 霉菌是透析患者中一种罕见的播散性感染致病菌。Clark[46]分析了美国一所三级医院附属血透中心发生的因霉菌(单胞瓶霉属)引发的导管感染聚集事件。通过回顾性分析监测和临床微生物学结果,对所有患者进行血培养,发现4例患者感染,其中3例表现为真菌血症,1例表现为人工血管感染。对21例患者的观察研究发现,血管穿刺部位消毒时间不充分。对透析中心的水处理、透析设施、供热、通风和空调系统进行环境评估,结果在暖通空调系统鼓风机下的冷凝滴水盘水中采样培养出菌株。
3.2 热带念珠菌 真菌血症暴发在血透患者中并不常见。Boyce等[47]调查一起热带念珠菌引起的血流感染暴发事件,8例患者在3个月内发生感染。调查发现,盐桶是用自来水冲洗,未进行常规消毒,并且水管允许与盐桶中的溶液接触。从患者、盐桶和其他环境标本中分离的热带念珠菌具有难以分辨的脉冲场凝胶电泳图谱。对盐桶进行常规消毒后,暴发终止。
4 其他病毒引起的医院感染暴发
4.1 甲型H1N1流感 2016年3—4月,巴西一所私立医院血透室发生甲型H1N1流感暴发事件[48]。该科有15台透析机,仅为62例患者提供血透治疗,但12例患者确诊。透析组的工作人员包括6名医生、4名护士、18名护理技术员、1名营养学家和3名接待员,其中4名工作人员被发现感染。感染者最常见的症状是发热(92%)、咳嗽(92%)和流鼻涕(83%)。该科对有症状的患者采用奥司他韦进行早期经验性抗病毒治疗,并采取了一系列感染控制措施,包括工作人员减少接触、在同一组感染患者中对无症状患者进行抗病毒药物预防、辞退疑似感染的工作人员,最终暴发得到控制。
4.2 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 血透患者传播COVID-19的风险增加,部分原因是难以保持身体距离。加拿大多伦多一所血透中心,尽管遵循了基于症状的筛查指南,但还是发生了COVID-19疫情。该中心使用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T-PCR)从237例患者和93名工作人员的鼻咽标本中检测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结果发现,有11例患者和11名工作人员检测阳性,而这22例中有12例在检测时无症状,7例在随访期间无症状。1例患者在感染SARS-CoV-2时住院,另外4例检测结果呈阳性的患者随后住院,2例患者需要进入重症监护病房。随访30 d后,无患者死亡或需要机械通气,无血透人员需要住院治疗。在疫情暴发期间,感染SARS-CoV-2的血透工作人员,无论症状如何,都要进行家庭隔离;而SARS-CoV-2感染患者,包括无症状者,在SARS-CoV-2 RT-PCR检测结果阴性之前,均采取飞沫和接触隔离措施。通过分析,该暴发事件由2例病例引起,随后在透析机构内和到透析机构的共用班车中发生院内传播[49]。
比利时一所血透中心也发生了COVID-19疫情。2020年3月6日—4月14日,62例患者中有40例(65%)检测出SARS-CoV-2,26名医护人员中有18名(69%)检测出阳性。25例(63%)感染患者住院,平均住院时间为8 d(IQR:4~12 d),11例(28%)患者发生COVID -19相关死亡,症状出现至死亡的中位时间为9 d(IQR:5~14 d)。在18例发生感染的卫生保健专业人员中,13例(72%)出现症状,2例(11%)住院,无死亡[50]。
2020年3月12—26日,意大利伦巴第的一所大型血透机构10名(33%)护士和1名医生被诊断为SARS-CoV-2感染。209例血透患者中有55例(26%)鼻咽拭子SARS-CoV-2阳性,伴或不伴症状。188例无症状血透患者中有33例(18%)鼻咽拭子SARS-CoV-2阳性,且这些阳性患者与拭子阴性患者一起在房间接受血透治疗。从3月26日起,在实施预防措施(升级个人防护用品、所有血透患者进行鼻咽拭子检测、阳性的无症状患者在专门区域分组治疗)后,未发现新增伴症状的感染患者[51]。
综上所述,血透患者医院感染暴发的种类繁多,且因血透操作的复杂性和人可能犯错的必然性,暴发仍然可能会发生。事实上,国外血透暴发事件远不止上述文献报道。国外针对暴发事件,尤其是发达国家,主要采取了以下处置和管理:一是尽快查明导致暴发的根源(如消毒剂、复用透析器、废液处理器、手卫生等);二是根据暴发原因制订有针对性的感染防控措施并落实;三是有专业的团队指导开展工作,这些均充分体现了暴发调查和防控的能力。因此,预防和控制血透暴发事件的发生,不仅要防止人力、物力、财力阻碍医院感染防控措施的实施,加强患者和医务人员的培训教育,促进安全文化的建设,更重要的是血透机构要不断完善、持续改进,同时建立一支专业能力强、能胜任暴发调查的专家团队和实验技术支撑,为暴发事件的控制提供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