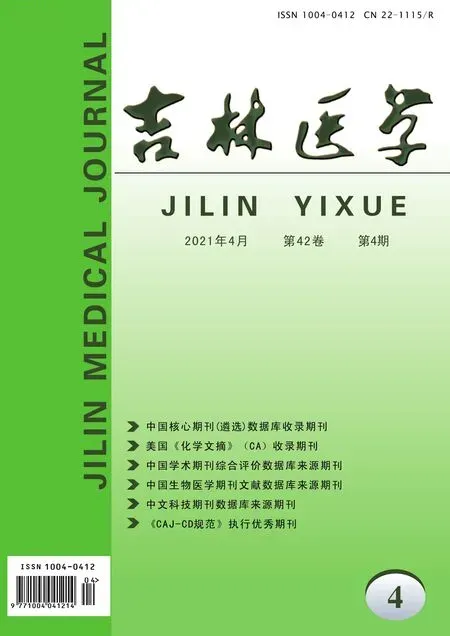表观遗传修饰在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中的作用
陈子毅
(杭州医学院,浙江 杭州 311399)
视网膜病变是糖尿病的重要并发症之一,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是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所以对两者关联性的研究十分迫切。现在的研究对高血糖如何影响视网膜病变的机制仍不明确,不过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结果显示,不仅是先天遗传因素,后天高糖环境中出现的表观遗传修饰对于调节该病变也有重要作用。对表观遗传修饰的研究,已经成为研究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方向的热点。下面从表观遗传修饰方向对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影响的研究进展作综述。
1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DR)概述
糖尿病会对全身微循环造成损坏,在眼部可表现为视网膜病变。临床分为背景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PDR)与增殖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NPDR)[1]。在背景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阶段,体循环中葡萄糖过高,导致滋养视网膜的微小血管受损,引起微小血管和微动脉瘤的出血等。若不加以控制,疾病可能发展为增殖性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阶段,此阶段涉及视网膜新生血管的形成,然后从视网膜循环的静脉侧形成新的脆弱血管,并可能进入内界膜进入玻璃体房,最终导致视网膜脱离和失明。这种复杂疾病的发病原因仍不明确,有些发病者的生活环境、生活习惯差异较大,这说明遗传因素与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2 表观遗传修饰对基因调控的作用
表观遗传学领域是近年来研究较多,发展最快的领域之一。表观遗传学与许多疾病的发病因素有关,基因与环境发生复杂作用,在不改变基因序列的情况下可遗传地改变基因的表达。至少有三种主要的表观遗传修饰,包括DNA甲基化、组蛋白修饰和非编码RNA。通过这些途径来调控基因表达,以达到适应环境的目的。
胞嘧啶甲基化为5-甲基胞嘧啶是被研究最多的表观遗传修饰。在真核生物中,CpG序列(5mCpG)处核DNA的胞嘧啶甲基化通过染色质结构的改变来调节表观遗传。最近有研究发现胞嘧啶的表观遗传修饰可微调i-基序DNA的稳定性[2],这些结构是表观遗传修饰的潜在位点,可能是表观遗传修饰影响基因表达的因素。有些研究分析了CpG岛中不同甲基化水平的DNA结构参数的行为。证明了高水平的甲基化与非甲基化的情况相比,甲基化可能会诱导协同作用,该协同作用强烈地改变了DNA骨架的扭转参数,从而改变了螺旋度,调控基因表达[3]。在线粒体DNA中的影响有所不同,这种作用尚不清楚,有研究认为5mCpG的出现可能会影响TFAM-DNA的识别[4]。线粒体转录因子A(TFAM)既是线粒体DNA(mtDNA)核苷酸中的主要DNA紧缩蛋白,也是转录的起始因子,而TFAM发挥作用必须在mtDNA中结合数百个CpG。甲基化由此在线粒体中通过影响转录因子结合的方式作用于基因表达。
染色质由组蛋白和核酸构成,组蛋白乙酰化是最常见的修饰之一。组蛋白乙酰化是指在相关酶的催化作用下,乙醜基被选择性地添加到组蛋白相关位点的过程。组蛋白翻译后修饰(PTM)的染色质调节原理是由于庞大的组蛋白修饰施加的空间和机械限制,导致染色质功能状态的潜在改变。这种修饰所改变的基因表达可能与生物适应环境有关,生物学意义与其他表观修饰方式类似。有研究认为植物组蛋白翻译后修饰特性会受环境胁迫的影响而改变,启动相关胁迫应答基因表达,或者充当胁迫应答转录因子的下游参与调控转录活动[5]。还有研究显示,肠道微生物与宿主的相互作用也会涉及组蛋白修饰,这种调控不仅影响宿主的免疫力,而且还影响代谢健康和抗癌能力,这种相互作用的主要决定因素是微生物衍生的短链脂肪酸(SCFA),SCFA对组蛋白脱乙酰基酶(HDACs)的抑制是引起该调控的关键[6-7]。
非编码RNA包括微小RNA与长链RNA,其中的微小RNA(miRNA)被认为可以影响基因表达。miRNA与mRNAs的3′非翻译区的互补序列结合,并切割mRNA,影响蛋白质的翻译。
3 表观遗传修饰与糖尿病
根据上述研究,表观遗传的发生与细胞环境有着密切联系。这种可遗传的变异可以成为引起糖尿病和其他慢性病有吸引力的靶点。这也可以解释传统思维上持续的高糖环境会引起一系列代谢异常。胰腺β细胞的保存是2型糖尿病发病和发展的重要因素。笔者已经知道DNA甲基化会引起2型糖尿病发病率增高,有研究以仔鼠为模型,发现妊娠期糖尿病可能通过CDKN2A/B启动子甲基化对后代胰腺β细胞产生不良影响[8]。CDKN2A和CDKN2B基因附近的CpG位点的低甲基化异常可能与β细胞功能障碍和糖尿病有关。有研究发现给早期2型糖尿病小鼠给予达格列净治疗后,有助于胰腺β细胞团的保存,Agr2、Tff2和Gkn3的表达明显上调。这种上调的基因表达可能为胰腺β细胞团的保存存在联系[9]。 在对1型糖尿病(T1DM)的研究中,与没有神经病变的T1DM患者相比,患有神经病变的T1DM患者在第一个NINJ2轴突中显示出明显增加的甲基化,在BRSK2的第一个内含子区域以及CLDN4 5'UTR区中显示出较低的DNA甲基化水平[10]。这启示我们,对于不同区域来说,均发生甲基化上调或下调所产生的效益可能是相反的。
4 表观遗传修饰与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高血糖和胰岛素抵抗都通过对内皮细胞造成损害最终影响患者的视力。不过,与常规作用不同的是,表观基因组的修饰可能存在代谢记忆的基本机制或者已经形成新的异常血管,从而导致即使在糖尿病患者中实现血糖控制后,炎性反应和细胞功能障碍的基因表达仍会持续[11]。越来越多的证据说明两者之间存在联系,有研究将DR患者白细胞中5-甲基胞嘧啶的含量与无DR患者作对比,前者的指标明显偏高[12]。CpG位点DNA聚合酶γ(POLG1)调节区的高甲基化可能通过影响线粒体DNA转录,导致线粒体DNA复制系统紊乱,导致视网膜毛细血管细胞凋亡[13]。 关于组蛋白修饰的研究,主要是组蛋白甲基转移酶和乙基转移酶。在高血糖状态下,组蛋白甲基转移酶可能在核因子κB(NF-κB)的启动子处增加,该启动子与其转录增加相关,激活的NF-κB途径可增加糖尿病患者视网膜毛细血管细胞的凋亡[14]。 miRNA水平的改变在视网膜血管病变和血管生成相关疾病的病理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有研究通过激活血管生成途径,识别可能参与DR发病的miRNA。眼内注射前miR-31、miR-150和miR-184可显著减少视网膜新生血管的形成[15]。
5 总结与展望
现在这一领域许多作用机制仍不明确,许多结论仍待考证。已知的修饰途径只是冰山一角,是否有更有效、更直接的修饰途径存在?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而应对这种并发症的治疗选择也会逐渐增多,这对于人类健康事业具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