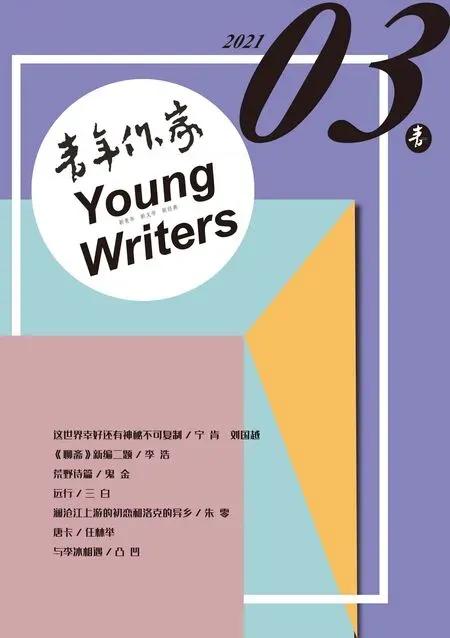父亲好的这一口
田 耳
今年九月初我来宜宾,才意识到是头一次来宜宾。对它的熟悉当然是在酒里,说到五粮液,顺口就有“宜宾五粮液”,这地名是随着酒的味道一块飘香的。且四川陈醴佳酿太多,各占据一块地界,五粮液虽为川酒之首,也从不抢别人风头,所以,它用不着叫成“四川五粮液”,“宜宾五粮液”就好。
我第一次来这,却也不陌生。西南天空大都没有例外,阴沉的颜色为主,天的边际又翻涌起白光,直观地让我体认,这是离家不远的地方。山城我是熟悉的,车穿过宜宾城区去向酒厂,随着路的高低起伏,城区疏密有致地排列,有几处街头,忽然见着久违的熙攘,再往前走,很快复归于平静。也许,山城就应该有这种动静相宜的布置和铺排,爱热闹与享清静的人怡然相处,各得其所,但我去过的山城大都逼仄,过于拥挤而难觅清静。所以,城区随处可见的“宜人宜宾”标语招贴,也是掂量以后对自身中肯的评定。
街巷也是差不多的格局,只是宜宾不大的一片老城区隐藏了诸多老酒坊。这些年去到各地,热衷于逛荡老城区,里面都能找见丝缕的童年记忆,甚至老城区的光线,也是在高耸的楼群中难以寻觅的。因是酒城,宜宾老城区的古酿酒坊都得以完好保存,巴掌大一片地方,藏着“长发升”“利川永”“天锡福”“听月楼”等八家古酿酒坊,古窖池近两百口。进入这片城区,当我想找一找儿时片段,却有浓郁的酒香浸润、干扰,俨然和记忆区分。
记忆中我老家的老城区,主街也是沿袭了河流的走势,狭窄的道路两旁都是板房,许多倾斜将塌,但用木柱强撑,木柱一端砸入硬木桩头,人依旧住里面。街道即是菜市,混乱无序中透着热闹,但也不乏脏乱,我外公和父亲每天喝酒,经常拎着胶壶去沽酒,沽来的不论苞谷烧或者高粱酒,都叫成壶子酒。那些商户卖的酒都是从郊区或者乡镇酒坊贩来,酒坛酒瓮一例捂得严实,生怕跑气漏财,只给酒客吸一鼻子尝一嘴,品判优劣。记忆中的老街,酒坊里丝缕酒气都要换钱,行人自然闻不到酒香。我们来到宜宾老城,走近最大的一处古酿酒坊“长发升”,六百多岁的老酒坊,酒气从砖缝和泥地板中渗漏出来,每一处小小的渗漏又汇成漫溢,酒香得以扑鼻而来。泥地板,还有老建筑中特有的黑白光效,能让人瞬间穿越。漫长的时光里头,酿酒师在这一片窖池中安然地劳作,时光黏滞,六百余年缓缓流淌却又这么从容地过去。酒体无色透明,甚至近乎晶莹,但诸种粮食谷物的滋味都诚实地揉到了里面。酒坊尽头的屋顶有天光涌入。我记起以前的房子采光不足,还没接上电灯,又被柴火熏染,白日的光源主要是靠屋顶的几片明瓦。我又看到了明瓦,老酒坊完好保留着这些细节。我走过去,让光柱直接落到我头上,这是小时候玩过的游戏,我看见光柱里浮游的微尘。我曾用很长的时间思考这个问题:到底是光映亮了微尘,还是微尘的浮动构成了光?
带着一丝由童年横亘至今的恍惚,我在那道光柱底下侧过头去,看见旧时的酿酒师和劳工,光着膀子(必然是光着膀子)劳作的情形。他们周身找不出一丝赘肉,黑得发赤,那赤色显然是酒精浸染出来,醉而不酲。每日的工作,在这黑白光线的显影中,肢体熟练地重复每一个动作:蒸粮、踩曲、下窖、起槽、拌和、上甑、摊晾、撒曲、封窖……有点漫不经心,但也不窝工,就像酒本身也是宜缓不宜急,每一口滋味,都是漫长的时间在其中纵横捭阖。
有时我会羡慕久远的生活,物力稍有艰难,他们只要思考吃穿用度。那时候所有的异地都是远方,他们被封存在某一个地方,一辈子干一件事。酿酒师和劳工都是终身职业,酒坊生意稳定,所以每家都留存数百年,他们每天品尝刚蒸制而出的头曲原酒……又一个恍惚,我看见古代的某位酿酒师,脸上忽然现出我父亲喝酒时的神情。但我知道,这种羡慕只是出于历史现场还原能力的缺失,我们哪能进入久远的生活。我们又何尝真的想回到过去?只在酒里品一品陈年的味道,是最好。
这里古酿酒坊都有自己名号,还都是三个字,结体稳定,声音铿锵,老字号通行的格式。不过这些名字没有广为传布,它们全都汇入了“五粮液”。“五粮液”三字直白痛快,也收敛了文气,收敛了古意斑驳,但它的其来有自,是具体可观的。一座座老酒坊仍戳在老街老巷,重新修整,像一尊一尊镀金菩萨。几百个年头挺过来,它们配得上任何高级别的待遇,甚至窖泥也是古董,成为国家博物馆的藏品 。
我记忆中的老街,酒坊都是无名,也不是前店后厂的坦荡格局。小酒坊酿酒质量不稳,一坛清一坛浊,一坛清冽一坛却烧锅味重 ,价格都是一样,起初几角一斛,慢慢涨至三五块。喝酒的人不能断顿,父亲经常去酒坊尝酒,有经验,遇有口感不错赶紧多打几壶存下来。偶尔碰到烧酒师傅超常发挥,或者是父亲人品突然爆发,一坛酒酿得沁人心脾,父亲便有感慨,说这有点五粮液的意思了。
五粮液这个名字,听到应该是八十年代中期的事。此前家里人大都是喝壶子酒,慢慢开始有了瓶子酒,听来一些酒的名字,大体知道五粮液和茅台是最好,但是难弄到。第一次见到五粮液,是外公过生日,母亲找关系从副食品公司弄来一瓶,酒瓶上还贴有销售小票。外公和父亲一喝自然停不下来,一瓶酒见底,晚上睡觉前床头柜各摆一大搪瓷缸凉白开。那时喝酒,最易干渴,经常半夜渴醒了找水,所以一旦喝得不少,晚上床头备水,是习惯性动作。次日醒转,床头的水一点没动,一觉睡得沉实松快,便对这酒又一顿好夸。那以后,“五粮液”就经常挂在外公和父亲嘴上。
外公外婆生日前后差几天,酒席一块办,姨家舅家拎酒来我家,也不挑剔。舅舅通常是拎五粮液,那些年在我们县城,五粮液比茅台贵,大家喝得也更勤快。父亲从不过生日,他有个说法,说上面还有老人,自己就不能过。也不知道是哪得来的说法,父亲认定了,确实就一直坚持,这是他性格。其实,父亲只比外公小一轮,而外公外婆长期跟在我家住,不去舅舅家中。父亲做了一辈子年龄小一轮的儿子,七十多岁,还要照顾着两位更老的老人。一七年,外公外婆几乎同时离世,父亲头顶上已经没有长辈,他自己差一岁也整八十。待我说要给他好好庆贺一下八十寿辰,父亲说,我已经习惯了不过,还是不过吧。我说,按你自己的规矩,也应该过。父亲想了想,说不要办酒,自家屋里弄一弄,你和你弟陪我喝五粮液就行。我说,我弄茅台怎么样?父亲坚持,说买五粮液,我就好这一口。我说,茅台更贵哩。父亲的回答令我意外,他说,茅台卖到两千的时候,是不是比卖一千口感翻倍?
这是父亲一贯的思维,凡事究个底,拧干了水分,再拿出来摆明立场。事实也是如此,即便朋友送我茅台,父亲也叫我留着应酬,场面上有时候不能少。他自己喝,五粮液当是最好,也不能当成口粮酒,现在价格也已飙高。但每年逢他生日,我都是买五粮液,和弟弟陪着他,一家人静悄悄地喝。去年他心情好,八十二岁的老人,一高兴还喝了整一瓶。
在宜宾老城,我不免想象,如果自家就居住于此,很久以前打壶子酒喝,父亲和外公也不会半夜渴醒。在这座酿酒之城,容不得劣质酒的存在。那又是怎样的一种幸福?老人身体会否更好?去到五粮液酒厂,工人赤膊劳作,仍然是古老的姿势,我们进去也不用鞋套口罩,显出与大多数酒厂不一样的坦率。他们和他们的父亲还有爷爷以及更远的先祖一样,用不着遮遮掩掩,数百年前店后厂的格局,使得他们早已适应在别人的目光中劳作,怡然自得。这肯定是时下酒店“明厨净灶”的源头,进店沽酒,看着酒是怎么做出来,买卖双方自会更多一些信任。当天,我们作为游客,也可以操起大铲装填酒糟,待有新酒出糟,高度的原酒下喉竟也喝得出绵柔口感。
这次来五粮液酒厂参观,获赠一瓶五粮液特酿,想必蕴蓄了最正宗的滋味。收到这件礼品,我首先想到的,是父亲的生日忽然又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