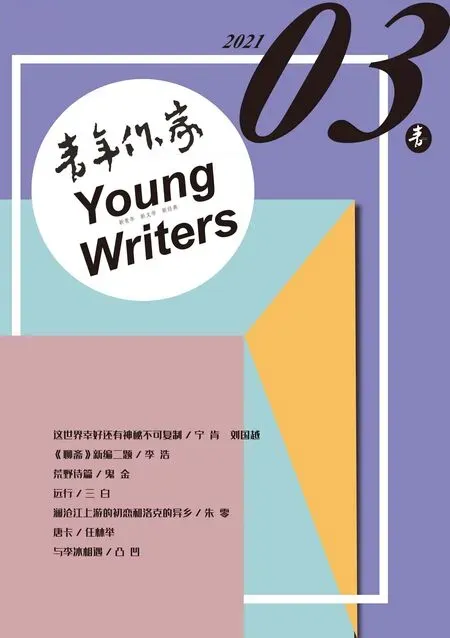评论者说 主人公可以死,但最好死有所值
向祚铁
三白这两篇作品有个共同特征:主人公都被写死了,故事也随之结束。
作为一个基本常识,小说总得有个开头,也总得有个结尾,再长的小说,也不可能无休无止地唠叨下去。单从结构形式上来衡量,以主人公的死亡来结束故事,的确是种行之有效的手法。不过,爱惜羽毛的作家不会滥用这一手法。否则,岂不是在“草菅人命”?
在小说里,主人公可以死亡,但读者希望,主人公之死能给作品带来足够的文学价值,具有足够的文学信服力,而不是仅仅让作者得以借机收尾。现在,我们来谈谈三白这两篇作品里的主人公,他们死有所值吗?或者说,从文学的角度来看,他们的死亡能成立吗?
《远行》的主人公,没有名字,在小说里自始至终以第三人称代词“他”来出现。不知作者是有意如此呢,还是无心之举,反正,这带来一个阅读效果:主人公作为一个人,变得有些抽象,像一个符号。故事发生地巴黎,也是符号特征鲜明的城市。它是时尚之都、奢侈品之都,它也是文艺之都、革命之都。前者是物质的、保守的,对应着主人公的妻子依依;后者是精神的、激进的,对应着主人公的情人Lena。
先看依依。依依出身良好家庭,热爱名牌,思想贫乏,也没啥文化,以为白金汉宫在法国,是个典型的“傻白甜”式女孩。小说里暗示,她回国和主人公结婚后,从没上班挣过钱,就是一种被养着的生活状态。——“依依”这个名字就有种小鸟依人的味道。这次来到巴黎,依依和主人公游览卢浮宫、凡尔赛宫等名胜后,身心疲倦,然后在老佛爷百货商场大肆采购名牌衣包化妆品,这让她的生命活力恢复过来。当夫妻俩在旅馆里说到准备生孩子后,她立马兴奋起来,开始筹划再去老佛爷采购小孩衣物。如果顺利发展,过一两年她会生下一个孩子。她会给孩子起个很“萌”的小名(比如“小汤圆”之类),还会用各种名牌衣物将其打扮起来,美得像个洋娃娃,然后给自己的这个“作品”拍下各种照片,发到朋友圈,等着亲友们点赞。
从世俗的角度来看,依依家境好,安静听话,喜爱孩子,能踏踏实实过日子,是个不错的结婚对象。我们的主人公,一个有着留美学历、在帝都北京驰骋职场的青年才俊,估计也这么认为,所以他选择了依依做妻子。当然啦,依依也有缺点,性格温吞,没啥见识。换作其他人,应该会包容这位妻子吧?可惜,曾经沧海难为水,我们的主人公和依依这朵白玫瑰在一起之前,还有过另外一朵红玫瑰——Lena。
Lena,是个在北京出生长大的姑娘,我们一直不知道她的中文名叫什么。她生命的根儿就不属于北京这“四九城”,她属于全世界,——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Lena 这个名字,简净,明了,全球通行,发音有几许性感。给Lena 取名这个细节,作者处理得很好,很符合Lena 的本质特征,她独立,有思想,有激情,敢于行动,具有全球化人格气质,Global girl。Lena 真心地认为依依是个好姑娘,可也毫无心理障碍地把依依的丈夫带到自己家里一夜激情。像她这样的姑娘,大都在纽约波士顿伦敦巴黎柏林东京等北纬四十度左右的国际一线城市出没(近些年,北京也开始进入她们的眼界),偶尔也出现在香港和新加坡这两个低纬度城市。如果得到某个基金会资助,Lena 们会冒着生命危险去中东某个动乱国家拍纪录片,然后在某个国际会议上慷慨陈词;抑或表情严肃地去往非洲,将镜头对准苦难的非洲儿童和女性。和安分的依依相比,Lena 是危险的,可这种危险的乐趣,却吸引着我们的主人公,这种吸引力一直没有消退。
依依和Lena,主人公感情世界里的白玫瑰和红玫瑰,表面上看她俩完全相反,实则拥有相同的本质特征:都是某种意义上的“符号消费者”。依依所进行的,是物质上的符号消费,如各种名牌衣包化妆品;Lena 所进行的,是精神上的符号消费,尤其是具有“白左”特征的符号,她带着主人公去左岸咖啡馆,还带着主人公去参加黄马甲街头运动,还先后两次完成了扔警察砖头的“壮举”并安全撤离。在此,笔者不由得想起了在文艺青年中广为传播的一部电影《戏梦巴黎》,电影结尾,女主人公在巴黎街头抗争中把砖头扔向警察,然后冲了上去。不客气地说,Lena 消费街头革命的行为和依依在老佛爷商场消费名牌衣包的行为,两者没有本质区别。
可以说,和主人公纠缠的这两位女性,分别在物质上和精神上进行着高端的符号消费,并投射到了主人公身上。我们的主人公看似纠结于选白玫瑰,还是选红玫瑰,其实,他只是想做个“全都要”的高端符号消费者。有一句诗正好能形容他的本质特征:我的心是一颗不甘心。他纠结来纠结去,不过是对鱼和熊掌不能兼得的“不甘心”,如此而已。
这种“不甘心”,让主人公的感情生活处于一种“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分裂状态。他选择依依作婚姻伴侣,内心里却一直渴慕着Lena。“身”“心”分离,是他情感世界的本质特征。当他和Lena 度过激情一夜,回到宾馆,发现宾馆遭遇窃贼,妻子一个人呆在宾馆房间等他回来,楚楚可怜,他的内心似乎“觉醒”过来。他决定忘掉Lena,要和妻子好好过日子,要跟她生一个她企盼已久的孩子,自己还要努力把握住晋升的机会,挣更多钱。他租好了车,和妻子拉着行李来到街上,准备离开巴黎这一“是非之地”。看来,主人公摆脱了多年来的情感困扰,他从此会“身”“心”合一,即将获得新生。
假如故事到此结束,好像也不错。乔伊斯在小说集《都柏林人》里,就多次以主人公的某种“日常生活中的觉醒”来结束小说,且广受称誉。但是,三白在这里展示了不凡的洞察力。在三白心里,早已看清主人公的“小布尔乔亚”人格,并且坚信,主人公的所谓“觉醒”,其实只是某种“小布尔乔亚”性质的心理冲动而已,用不了多久,他又会故态萌发,恢复“身”“心”分离的情感状态。
所以,就在主人公即将“身”“心”合一地陪同妻子离开巴黎之际,三白出手了,安排如下情节来做结尾:在隔街传来罢工游行的声响中,主人公那一直被忽略的心脏病发作了,他猝死于巴黎街头。他的身子留在了Lena 所在的巴黎,那颗心则追随着走在前面的妻子想要离开,——依然“身”“心”分离。真是讽刺啊!在这里,主人公之死更像一个充满象征意味的符号。这个符号提醒着读者:在主人公的情感世界里,“身”“心”分离是其本质特征,他改变不了这一点。
实话说,一个中产男人纠缠于白玫瑰红玫瑰之间,这种男女情感的三角关系,已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戏码。如果没有主人公的猝死,三白的《远行》不过是众多已略显俗套的“白玫瑰红玫瑰”故事中的一个而已,但结尾处的主人公之死,无情揭示出他精神情感世界的本质特征——这,给作品赋予了别样的文学质感!
下面谈谈另一篇小说《鬼》。在笔者看来,《鬼》是个黑童话,无情揭示了儿童友谊里潜藏的可怕的暗黑属性。
整个小说从“我”的视角来展开叙述。小学二年级时,“我”由于父母工作的原因,从国内转学来到美国纽约的一所学校,不用说,班里的同学五颜六色,各色人种都有。小说里,“我”是个有些内向的小女孩,在班上一直没有朋友,过得比较封闭、自卑。半年后的一天,数学老师在黑板上写出5+4=?“我”不加思索地说出了“9”,被旁边的小女孩听到了,兴奋地说She knows it!老师点名让“我”作答,“我”说了答案,受到赞许,也收获了班里其他同学的掌声。
我和那个小女孩——故事的主人公Paula,当天就成了好朋友。彼此也是对方唯一的朋友。Paula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父母都是墨西哥裔,估计是非法移民来的美国,处于社会底层,父母还离了婚,母亲带着Paula 兄弟姐妹四五个小孩艰难度日,不难想象,Paula 在家里很难得到关爱,穿的裙子脏兮兮的,“点缀着番茄汁和芥末酱”。Paula 戴着一副紫色框架怪里怪气的眼镜,让眼睛显得很大,而胳膊和腿又非常细小瘦弱,结果,她看起来就像一只苍蝇。Paula的外貌已如此“出色”,加上她学习成绩又很差,上课不好好听讲,总在本子上乱写乱画。很自然地,她被班上同学当成了“怪胎”,被孤立,被隔绝,被恶意对待。在这个班集体呆了一年多,她连一个朋友都没有。
“我”和Paula 成了朋友,当天一起午餐,故事似乎将向光明美好的一面发展。可就在这第一次交往中,暗黑的东西开始出现了,Paula向“我”大谈特谈她家乡一个“真实的故事”,——玛丽亚杀死自己孩子的故事。她仿佛被魔鬼控制住了似的,连续两天都在谈这个故事。接下来的日子,她和“我”在一起时,一有机会就说这个鬼故事。她处于一种狂热之中,讲得绘声绘色,充满细节。她比划着玛丽亚的指甲有多长,上面滴的全是小孩的血。而且,在不同的环境,她总能“天才”地做些改编,“如果我们在操场,孩子就是从滑梯上摔死的,如果在饭厅,那(孩子)就是被人用土豆泥噎死的”。有一天,Paula 和“我”上厕所,她又灵感大发,指着一个久已未用、放置拖把的厕位隔间,说那就是玛丽亚在厕所里吊死孩子的那间屋子,“我”当时狠狠地讥笑了她。
说实话,任何一个正常人,碰上这么一个朋友,很快就会感到厌烦吧?是的,“我”很快就厌烦了这段友情。此时,我开始融入整个班集体,甚至受到了“上流圈子”的接纳,班上成绩最为出色、高挑壮硕、“像个姐姐”的Caron 开始邀请“我”和她一起玩。而Paula 呢,依然只有“我”这一个朋友,依然在讲玛丽亚弄死自己孩子的鬼故事。——不久前,“我”和Paula 还“同是天涯沦落人”,可现在,两人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呀。
接下来,班上去哈得逊河那里春游,由于Paula捣乱,“我”新买的睡美人午餐包掉到桥下,被汽车轮胎撞到了河里,丢失了。“我”借此由头,中断了和Paula 的友谊,不管Paula 怎么道歉,怎么求老师出面说情,都不管用。Paula失去了她短暂拥有的唯一朋友。她再度茕茕孑立,形单影只。班上的捣蛋鬼们又开始嘲笑和戏弄Paula。而“我”在班里的“社会地位”则更进一步,加入了以Caron为核心的读书团。“我”虽然是个小孩,但也像成年人一样,遵循着“人往高处走”这条处世原则。
Paula 就像溺水者想抓住一根救命稻草,想把“我”这个唯一的朋友牢牢抓住。她央求“我”跟她来到那个厕所,拉开那个此前放着拖把的隔间的门,说:“求求你,你闭眼,大声数到三十,然后把门打开!”Paula 在干什么呢?她在隔间的墙上拴了根绳子,她要把脖子套进去,装成被玛丽亚吊死的孩子。也许她这么想,当“我”打开门看到眼前的这个“鬼”,就会相信玛丽亚杀死自己孩子的故事是真的,从而恢复两人的友情。——这可真是又诡异又令人心酸啊!按照Paula 的请求,“我”站在厕所里数数,数到24 时,Caron 在厕所门口叫我去阅览室读书。Paula 的请求怎么能和Caron 的邀请相比呢?很自然地,“我”跟随Caron 走了。此时,因为操作不当,Paula 被绳子勒死了。——如果“我”如约数到30 就去打开隔间的门,也许来得及把Paula 救下来?但我已追随Caron 来到阅览室,正在阅读经典名著——鬼故事《鄂榭府崩溃记》……
三白在《鬼》这篇作品里,以敏锐的触角,探索儿童友谊暗黑的一面。而Paula 的死,极大地强化了这一主题,作品的文学感染力也大大地得到提升!在《鬼》中,如果没有Paula 之死,那就像燃放一个充满炸药的炮仗,最终却放成了哑炮。——这话有些残忍,可的确如此啊。
《远行》和《鬼》这两篇作品,单从技艺来看,都体现出了三白的良好写作素养。但《远行》里的三个人物,主人公“他”、妻子依依、情人Lena,都属于典型的中产阶级,“小布尔乔亚”。——是的,Lena 本质上也是中产阶级,尽管她的生活看起来很前卫,其实依然是一种俗套,一种看起来比较高端的俗套。这样的人物,在已有的文学人物长廊里,并不罕见,他们仨的纠葛则更显普通。但《鬼》里的Paula,这个人物形象无疑是新颖的,小说主题也很具探索性,故事也写得“抓人”。可以说,三白成功塑造了Paula 这个令人耳目一新的文学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