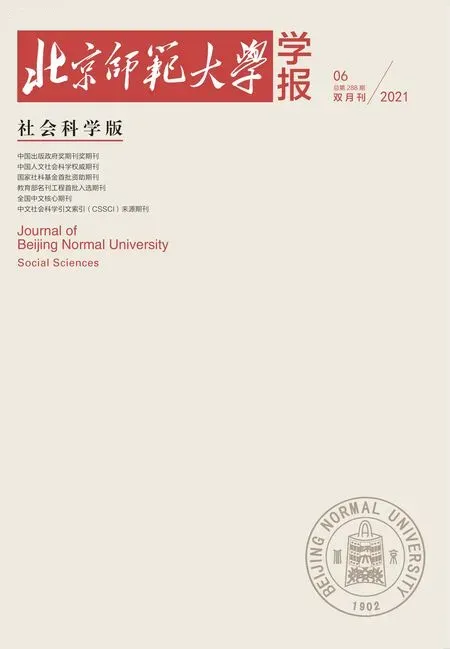论20世纪英国史学家屈威廉的乡村保护事业及其意义
梅雪芹
清华大学 历史系,北京 100084
在英国,屈威廉(1)全称乔治·麦考莱·屈威廉(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1876—1962),亦译特里维廉、屈勒味林等,本文简称屈威廉。不仅是家喻户晓的史学家,而且是颇负盛名的乡村和自然美景保护者。作为史学家,他所撰述的许多历史著作已成为畅销书,获得了极大的社会效益;作为保护者,他因积极参与乡村和自然美景保护活动,赢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同。因此,屈威廉的成就和贡献远不止于作为学术事业的史学领域。他本人曾在致朋友的信函中解释说,他一生主要关注两方面的事情,第一是“历史和文学”(history and literature);第二是“国民信托基金会(2)它的全称为“国民保护历史名胜或自然美景信托基金会”(National Trust for Places of Historic Interest or Natural Beauty),1895年由英国社会改革家奥克塔维亚·希尔(Octavia Hill)、教士哈德威克·罗恩斯利(Hardwicke Rawnsley)以及律师罗伯特·亨特(Robert Hunter)共同发起成立。参见宋俊美:《为国民永久保护——论1895—1939年英国国民托管组织的环境保护行动》,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和乡村保护”(the National Trust and country preservation)(3)参见David Cannadine,G.M.Trevelyan:A Life in History,Hammersmith,London:Harper Colins Publishers,1992,p.179。。不过,他第二方面的关注在一段时间内并未得到学术界的重视,1962年7月21日他去世后英国皇家学会所发的讣文中对此只字未提(4)Edgar Douglas Adrian,“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1876—1962”,https://royalsocietypublishing.org/doi/pdf/10.1098/rsbm.1963.0017,2021年1月25日。。
30年后,任教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英国史学家戴维·伽纳丁(David Cannadine, 1950-)出版了有关屈威廉的传记作品(5)David Cannadine,G.M.Trevelyan:A Life in History,Hammersmith,London:Harper Colins Publishers,1992.,描述了他的丰富事迹,刻画了他的多重形象。在伽纳丁的笔下,屈威廉不仅是“自由的国际主义者”(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ist)和“辉格派宪政主义者”(the Whig constitutionalist),而且是“乡村哀悼者”(the Rural Elegist)。在此书中,伽纳丁还特别梳理了屈威廉参与的乡村保护活动。然而,伽纳丁所刻画的屈威廉的“乡村哀悼者”形象,在某种程度上却又模糊了人们对其乡村保护意义的认知,以至其相关重要事迹一直未能得到凸现,继续淹没在他论述英国国民信托基金会发展历程及其乡村和自然保护活动的著作之中(6)Jennifer Jenkins and Patrick James,From Acorn to Oak Tree:The Growth of the National Trust 1895—1994,London:Macmillan,1994.这部著作涉及屈威廉在国民信托基金会的工作及其乡村和自然保护事迹,但很不醒目,必须仔细研读才能发现他在这方面的作用。,这使学术界和世人难以明了屈威廉在史学领域之外的工作和贡献。
在我国学术界,不少人对屈威廉颇感兴趣。早在民国时期,著名法学家钱端升即已译介屈威廉的《英国史》,对其推崇备至(7)〔英〕屈勒味林:《英国史》,钱端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33年;2008年和2012年东方出版社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先后再版这部译著。。近年来,屈威廉论述光荣革命的作品也得到译介(8)〔英〕G.M.屈威廉:《英国革命(1688—1689)》,宋晓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而他关于社会史是“除了政治什么都有的历史”的界说亦为学者所熟知。不过,迄今我们对于屈威廉的了解仍局限于他作为一位专业史学家的层面,而他自己所说的第二方面的事情还鲜为人知。有鉴于此,本文基于对相关研究成果的搜集和研读,尤其是对屈威廉本人有关著述的挖掘,试图深入其思想语境和实践之中,专门系统地分析、探究屈威廉热衷于乡村保护的缘由和宗旨,以便在当代更好地认识他作为史学家而开展乡村保护工作的意义(9)笔者曾对此作过简约的讨论,参见梅雪芹:《史学家的学术研究和现实关怀》,《光明日报》,2018年2月12日,第14版。。
一、“我们为什么应该拯救英格兰?”
上文提及,屈威廉一生都关注乡村保护之事。为什么如此?毋庸讳言,这与他的出身和个人喜好息息相关——这是首先必须具体说明的。
屈威廉于1876年2月16日生于沃里克郡(Warwickshire)靠近埃文河畔斯特拉福的维尔康姆大宅(Welcombe House,Stratford-on-Avon),宅子和庄园为他外祖父罗伯特·菲力普(Robert Needham Philips)所拥有,他外祖父是兰开夏郡的一位富商和伯里市的自由党议员[the Liberal Member of Parliament (MP) for Bury](10)G.M.Trevelyan,An Autobiography and Other Essays,London,New York:Longmans,Green and Co Ltd.,1949,pp.5,2-3.。1889年屈威廉的外祖父去世后,他的父母继承了维尔康姆大宅,并把它作为冬季度假胜地(11)G.M.Trevelyan,An Autobiography and Other Essays,London,New York:Longmans,Green and Co Ltd.,1949,pp.5,2-3.。屈威廉家族则“是影响了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英国公众和文化生活的知识贵族的主要成员”(12)Laura Trevelyan,A Very British Family:The Trevelyan and Their World,New York:I.B.Tauris & Co Ltd.,2006,pp.23,25,36.,家族大宅子是英格兰北部诺森伯兰郡(Northumberland)的沃林顿府(Wallington Hall)。这座富丽堂皇的宅邸矗立在开阔的乡间,为屈威廉家族享有乡绅和知识分子的地位奠定了根基(13)Laura Trevelyan,A Very British Family:The Trevelyan and Their World,New York:I.B.Tauris & Co Ltd.,2006,pp.23,25,36.。而沃林顿所在的地方位于英格兰和苏格兰交界处的偏远荒野,虽不壮观但却非常美丽;这栋房子则与周边风景融为一体,不可分割(14)Laura Trevelyan,A Very British Family:The Trevelyan and Their World,New York:I.B.Tauris & Co Ltd.,2006,pp.23,25,36.。
可见,无论从母亲还是从父亲世系来看,屈威廉皆来自上层社会。这一阶层“由实业界人士、迅速扩大的专业人员和官僚阶层及早先的乡绅和贵族聚集而成”(15)Martin J.Wiener,English Culture and the Decline of the Industrial Spirit,1850—1980,2nd ed,Cambridg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11;David Cannadine,G.M.Trevelyan:A Life in History,pp.144-145.,作为其地位和财富象征的乡村大宅与庄园领地,既是屈威廉出生和成长的环境,也是他直接接触英国乡村和大自然的场所。关于这一点,屈威廉在自传中有如下记述:
……在孩提时代和年轻的时候,我大都在莎士比亚故乡沃里克郡居住,漫步。住宅很舒适地掩映在维尔康姆幽谷底部的树木和丛林中,鸟儿在上面大量筑巢……往北往西是大片的林地,我常去那里在报春花丛中漫游……近处,埃文河要么在树木繁茂的岸下蜿蜒,要么在碧水茵茵的草地穿流。埃吉山(Edgehill)包住了东边的地平线;天气晴好的时候马尔文山(Malvern)清晰可见……总之,这对一个男孩来说是命中注定的极好的东西;这个男孩很快就认为诗歌、历史以及在乡间独自漫步,是一生中最美好的三件事。(16)G.M.Trevelyan,An Autobiography and Other Essays,p.3.
这样,对乡村及其自然美景的热爱,于屈威廉可谓自然天成,由此也让他养成了在乡间漫步的天性与喜好。
屈威廉十分喜欢在乡间独自漫步。他认为,在新鲜空气和宁静景观中进行这种锻炼,对健康大有益处。他还写过一篇题为“漫步”(Walking)的文章,在其中生动地描述说他有两个医生,即左腿和右腿;“当身体和精神都不正常的时候……我知道我只要请我的医生来,我就会好起来的”(17)G.M.Trevelyan,Clio,A Muse and Other Essays,Literary and Pedestrian,London,New York:Longmans,Green and Co Ltd.,1914,pp.56,57.。当他的灵魂(他认为是精神和身体的结合体)“被不好的想法或无用的烦恼阻塞”时,他的治疗方法就是“漫步”(18)G.M.Trevelyan,Clio,A Muse and Other Essays,Literary and Pedestrian,London,New York:Longmans,Green and Co Ltd.,1914,pp.56,57.。他相信,漫步是一个人在与自然神圣结合中恢复自己灵魂的最好方法。
因此,屈威廉对乡村自然美景的热爱和保护的确有他自己的需要,这既可以陶冶性情,也可以助益身心。但必须指出的是,他对乡村自然美景的热爱和保护,并非只是出于个人喜好,一定程度上也是一个受热衷于“公共事务”家风熏陶的学者,在面对所处时代的社会需要时的积极反应。
热衷于“公共事务”,具有“公共精神”,履行“公共责任”是屈威廉家族的一个传统。19世纪以来,这个家族有多人担任公职。屈威廉的祖父查尔斯·爱德华·屈威廉(Charles Edward Trevelyan,1807—1886),是第一代沃林顿从男爵(1st Bt of Wallington),出任过文官,主持过文官制度改革(19)Laura Trevelyan,A Very British Family:The Trevelyan and Their World,pp.59,182.;父亲乔治·奥托·屈威廉(George Otto Trevelyan, 1838—1928),是一个自由党政治家,也是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大哥查尔斯·菲力普·屈威廉(Charles Philips Trevelyan,1870—1958),在1924年和1929—1931年系工党内阁成员(20)Laura Trevelyan,A Very British Family:The Trevelyan and Their World,pp.59,182.。史学家及政治家托马斯·马考莱勋爵(Lord 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是他的舅姥爷。因此,屈威廉自幼受家族的公共精神的熏陶,对于自己所处时代的社会现实非常关注。
屈威廉生活在19世纪末叶到20世纪上半叶。这一时期,英国社会最突出的特征是城市化。在这一过程中,英国的乡村“因汽车和大型游览车、新郊区扩张和带状发展、半独立式住宅和度假别墅”(21)David Cannadine,G.M.Trevelyan:A Life in History,pp.151-152.而受到前所未有的影响,这不仅意味着乡村景观的变化,也意味着污染和噪音等公害的大范围扩散。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屈威廉于1922年写的《19世纪英国史》强烈地表达了对乡村保护的关注。这部著作开篇就唤起了人们对“18世纪被机器摧毁之前的静谧的古老英格兰”的回忆(22)G.M.Trevelyan,British Histor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1782—1901),London,New York,Toronto: Longmans,Green and Co.,First Edition,1922;Ninth Impression,1930,p.viii.,生动地描述了“主要是破坏性的”工业革命(23)G.M.Trevelyan,British Histor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1782—1901),pp.xvi,158-159,230,398,xiii,405.,并明确表达了其内心深处的关切。他看到,男男女女被残忍地“从古老的乡村生活的虔诚和联系中驱逐出来”(24)G.M.Trevelyan,British Histor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1782—1901),pp.xvi,158-159,230,398,xiii,405.,与自然脱离,被赶到丑陋肮脏的城镇;在那里他们被迫忍受“经济困境、贫穷、饥饿和阶级不公”(25)G.M.Trevelyan,British Histor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1782—1901),pp.xvi,158-159,230,398,xiii,405.。更糟糕的是,他说“工业革命从未结束,从未结束,只要人们不断地发明创造,每一种新形式的经济生活几乎在它尚未成型之前就开始被另一种取代”(26)G.M.Trevelyan,British Histor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1782—1901),pp.xvi,158-159,230,398,xiii,405.。他甚至看到,“在每一代人中,新的经济生活差不多都会擦掉稍早一点的经济生活的痕迹”(27)G.M.Trevelyan,British Histor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1782—1901),pp.xvi,158-159,230,398,xiii,405.;当时的英国被大城市和工厂的丑陋主宰,它的居民是在日常大量接触日报、廉价杂志、中篇小说、足球比赛和音乐厅长大的。对于屈威廉来说,作为维多利亚后期地主阶级的一员和一名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者,他担心世界将发生深刻的转变,而走向“一个大城市而不是乡村的世界,一个更多地通过科学和新闻而不是宗教、诗歌和文学来表达自己的世界”(28)G.M.Trevelyan,British Histor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1782—1901),pp.xvi,158-159,230,398,xiii,405.。
同时,屈威廉也见证了英国传统的社会结构被大大削弱的现实,1918年之后尤其如此。因为一战夺去了723,000英国人的生命,其中包括20名上院贵族、49名上院贵族继承人和更多的贵族子弟,这就使许多家庭失去了原定的爵位和财产继承人(29)阎照祥:《英国贵族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28页。。结果出现了所谓的“土地持有革命”(revolution in landholding),许多大贵族的地产被分解,四分之一的英格兰土地被推向市场。
在这样的时代和现实背景下,屈威廉对乡村保护的必要性有着系统的思考认知,这集中体现在他于1929年提出的一个问题及对它的解答之中。是年,他代表国民信托基金会发表了一份题为“英格兰的美景是否注定要毁灭?”的答辩书(30)G.M.Trevelyan,Must England’s Beauty Perish? A Peal on Behalf of the National Trust for Places of Historic Interest or Natural Beauty,London:Faber & Gwyer Limited,24 Russell Square,1929.。在答辩书中,他提出了一个涉及英格兰乡村保护的问题,也即“我们为什么应该拯救英格兰?”(Why should we save England?),并进行了颇为全面的思考与回答。在他看来,拯救英格兰意味着至少要保留它的一些自然美景。他认为这是值得花费金钱并投入精力去保留的(31)G.M.Trevelyan,Must England’s Beauty Perish? A Peal on Behalf of the National Trust for Places of Historic Interest or Natural Beauty,p.18.。为什么这样说?他从三个方面解答了这一问题。
首先,屈威廉指出了其中最浅显的理由,即钱财考量。他说道:
如今,自然美景是值钱的。到英国来的游客,尤其是那些美国人,来品味这座绿岛的花园般魅力,而他们自己大陆上的壮阔景色中却没有这种魅力。如果我们破坏了我们的岛屿,他们的后代就没有什么兴趣来参观了。而且,正如该岛的自然美景是整个国家的财富和荣誉的源泉,每个郡和每个地区的自然美景也是当地居民的财富和荣誉的源泉。(32)G.M.Trevelyan,Must England’s Beauty Perish? A Peal on Behalf of the National Trust for Places of Historic Interest or Natural Beauty,p.18.
于是他认为,如果德文郡(Devon)或萨里郡(Surrey)的人们因为对他们个人没什么直接好处而任由他们郡的特有美景遭到破坏,那么他们就是一群不善经营的人。他还进一步指出,城市居民失去了熟悉的自然美景,渴望得到自然美景,并在度假时寻找自然美景,因此会有大量合法的交易来满足他们的需求。为了这项交易的蓬勃开展,哪怕只是作为一种商业资产,也必须保留自然美景。他还批评了英国一些地区的居民,因为他们喜欢在自己最美丽的地方建房,这无异于“杀鸡取卵”(33)G.M.Trevelyan,Must England’s Beauty Perish? A Peal on Behalf of the National Trust for Places of Historic Interest or Natural Beauty,p.18.。
第二,屈威廉从“精神价值”(Spiritual Values)角度提出了拯救英格兰的理由,强调拯救英格兰不只是甚至主要不是钱财考量,而是关系到全体人民的幸福和心灵健康的大问题。
在屈威廉看来,自然美景曾是英国国民生活中的基本要素,它无时无刻不滋养着他们,启发他们从事伟大的文化创造。他说道:“昔日,英国人生活在大自然之中,每时每刻都受到大自然的影响。于是我们的祖先被唤起灵感,在宗教、歌曲、艺术和手工艺中产生了他们伟大的创造——这是精神上生机勃勃的全体人民的共同产物。”(34)G.M.Trevelyan,Must England’s Beauty Perish? A Peal on Behalf of the National Trust for Places of Historic Interest or Natural Beauty,pp.19,19,19,19,20,19,19,20,20,20-21,21,19.然而在他所生活的时代,大多数人“被流放”到城市,这对他们的想象力、灵感和创造力产生了有害的影响。“但是有些人仍然住在乡下,有些人仍然会到乡村度假,如饥似渴地畅享自然美景欢愉,而后精神焕发地回到城镇。”(35)G.M.Trevelyan,Must England’s Beauty Perish? A Peal on Behalf of the National Trust for Places of Historic Interest or Natural Beauty,pp.19,19,19,19,20,19,19,20,20,20-21,21,19.因此,保护自然美景是一项与“努力维持理想标准和健康生活的各方人士”密切相关的事业。这项事业赢得了宗教界、教育界、爱国者、社会改革家、旧时代的怀恋者、文学和诗歌爱好者、艺术家和音乐家、鸟类爱好者和动物学家的普遍支持;所有这些人都有最强烈的动机,为了共同支持这一事业而忘记一切恩恩怨怨;因为“如果自然美景消失,宗教、教育、民族传统、社会改革、文学和艺术都将被剥夺生命和活力的重要源泉”(36)G.M.Trevelyan,Must England’s Beauty Perish? A Peal on Behalf of the National Trust for Places of Historic Interest or Natural Beauty,pp.19,19,19,19,20,19,19,20,20,20-21,21,19.。
可见,屈威廉十分注重从英国人的精神需求和民族文化发展角度强调保留自然美景的意义,乃至称之为今日英国的“精神经济体系”(the spiritual economy)(37)G.M.Trevelyan,Must England’s Beauty Perish? A Peal on Behalf of the National Trust for Places of Historic Interest or Natural Beauty,pp.19,19,19,19,20,19,19,20,20,20-21,21,19.。针对人们有时认为的保留自然风景的愿望源于情感上对树木和植物自身生命的高估,他明确指出,“但事实并非如此。究竟是否应该为了其自身利益而保护树木或动物,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人们对此可能持不同的意见。不过,保留英国自然风光和野生动植物的理由,可能基于仅仅考虑人类福祉的目的;而我在这里要提出的就是这些理由。为了人类的精神福祉,需要保留乡村的鸟类生命;对其中的英国人尤其如此,他们观鸟,听鸟鸣,从中找到了快乐。”(38)G.M.Trevelyan,Must England’s Beauty Perish? A Peal on Behalf of the National Trust for Places of Historic Interest or Natural Beauty,pp.19,19,19,19,20,19,19,20,20,20-21,21,19.因此,不能听任“现代发展的冷酷犁头继续肆意破坏这岛国每一处美丽之地”(39)G.M.Trevelyan,Must England’s Beauty Perish? A Peal on Behalf of the National Trust for Places of Historic Interest or Natural Beauty,pp.19,19,19,19,20,19,19,20,20,20-21,21,19.;如果有什么事业值得人们投入金钱、工作和生活,那就是保留自然美景的事业(40)G.M.Trevelyan,Must England’s Beauty Perish? A Peal on Behalf of the National Trust for Places of Historic Interest or Natural Beauty,pp.19,19,19,19,20,19,19,20,20,20-21,21,19.。
第三,屈威廉从“自然与历史”(Nature and History)维度阐述了保留自然美景和历史名胜的动机,即是要“在我们的人民身上培养历史意识,清晰地理解祖先以及本岛从前所有居民的生活;这是在脑海中钟情地描绘的某个实体,而不仅仅是历史书中的抽象读物”(41)G.M.Trevelyan,Must England’s Beauty Perish? A Peal on Behalf of the National Trust for Places of Historic Interest or Natural Beauty,pp.19,19,19,19,20,19,19,20,20,20-21,21,19.。
屈威廉看到,在他生活的时代,人们“参观古罗马人的遗址、原始的土方工程、城堡、教堂、庄园和古时村庄的热情日益高涨;对老房子越来越感兴趣,渴望修复它们并在里面住住”(42)G.M.Trevelyan,Must England’s Beauty Perish? A Peal on Behalf of the National Trust for Places of Historic Interest or Natural Beauty,pp.19,19,19,19,20,19,19,20,20,20-21,21,19.;认为参观历史名胜和建筑已成为最鼓舞人心的现代教育方法之一。而且,在民族主义日益高涨的时代,保留英格兰的文化景观变得越来越重要。譬如,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游客参观国民信托基金会所属的博迪亚姆古堡(Bodiam Castle)这样的地产。通过这种方式,在现代城市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男男女女对其祖先截然不同的生活深表同情,这对他们的精神面貌和想象力都具有非常宝贵的改善作用。而“当‘历史名胜’建筑矗立在‘自然美景’之中,这种效果最为强烈。比如,草地和树木环绕的博迪亚姆古堡、浪漫树林中的切德沃斯古罗马人别墅(Chedworth Roman Villa)以及古老荒僻之地上的巨石阵(Stonehenge),都会产生这样的效果。”(43)G.M.Trevelyan,Must England’s Beauty Perish? A Peal on Behalf of the National Trust for Places of Historic Interest or Natural Beauty,pp.19,19,19,19,20,19,19,20,20,20-21,21,19.
屈威廉甚至指出,英国一些没有任何建筑的地方都有可能是“历史名胜”。这些地方包括英格兰南部的“唐斯丘陵”(the Downs),它讲述了早期人们在高地上的生活;埃文河畔(Avon banks),是纪念莎士比亚的最佳场所;还有原始森林或古老公园里的树木,在悄悄谈论罗宾汉(Robin Hood)、猎人赫恩(Herne the Hunter)以及过往的其他时代。“的确,在自然荒野的深处,一个人可以感到与他的祖先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为在那里,他可以从现在这个嘈杂的时代抽身片刻,与大自然独处,就像他的祖先在同样的绿色景象和静谧中独处一样。”(44)G.M.Trevelyan,Must England’s Beauty Perish? A Peal on Behalf of the National Trust for Places of Historic Interest or Natural Beauty,pp.19,19,19,19,20,19,19,20,20,20-21,21,19.这样,在他看来,虽然没有从严格意义上说自然美景对个人精神生活和道德生活的影响“难以计算”(incalculable),但它确实是巨大的。因此,他在答辩书中明确指出:“没有美景,人就会颓废;没有自然美景,英国人在精神上就会颓废”(45)G.M.Trevelyan,Must England’s Beauty Perish? A Peal on Behalf of the National Trust for Places of Historic Interest or Natural Beauty,pp.19,19,19,19,20,19,19,20,20,20-21,21,19.。
由于屈威廉对自然美景之于英国人的健康及其文化和历史影响的深刻见解,他也非常清楚破坏自然美景所造成的不可估量的损失。然而,现实中许多人对这一情况及其后果却不以为然,对此他用了一个比喻加以说明:
出售大英博物馆和国家画廊(National Gallery)的珍宝给一个疯狂的百万富翁,他想在特拉法加广场(Trafalgar Square)将它们全都烧掉,这一行为不会比听任英格兰西南海岸线或湖区被开发者一点点地破坏更糟糕。然而,虽然出售大英博物馆的珍宝被认为是不可想象的,但许多人似乎认为破坏英格兰最美的风景是不可避免的。(46)G.M.Trevelyan,Must England’s Beauty Perish? A Peal on Behalf of the National Trust for Places of Historic Interest or Natural Beauty,p.21.
屈威廉指出,如果不仅仅是审美利益,而且经济、社会和文化利益也会受到威胁,“那么为什么要允许这个岛国上的自然美景被破坏呢?它不啻是剥夺了无数未出生之人的生活乐趣,并使民族的精神萎缩”(47)G.M.Trevelyan,Must England’s Beauty Perish? A Peal on Behalf of the National Trust for Places of Historic Interest or Natural Beauty,p.21.。这样,在他看来,“自然美景保护”(the preservation of natural beauty)是一个关系到英格兰未来的重要问题,因为他亲眼目睹远离自然而埋首于大城市的英国人与其他任何国家相比要多得多,英格兰这个小岛国被破坏性的现代发展之手触碰的地方比其他任何国土要大得多。对一个自然与文化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国度来说,自然美景的丧失就意味着文化的衰落。
屈威廉从上述三方面对“我们为什么应该拯救英格兰?”问题的回答,反映了他对保护乡村的内涵及其重要性的基本认知。在他眼里,拯救英格兰也就是保护这个岛国的乡村世界,保护乡村则意味着保留其自然美景。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屈威廉是一个乡村哀悼者,他哀悼的则是自然美景被破坏和丧失的现状。之所以热爱乡村自然美景并哀悼它的丧失,当然并非只是出于他个人的喜好,更是因为它是英国及其各地金钱财富的一大来源,是英国国民身心健康和精神富足的源泉,也是英国文化和历史的根系所在。
二、“为自然美景鼓与呼”
出于对自然美景重要意义的深刻认知,以及对自然美景丧失后果的急切忧虑,屈威廉一直积极投身于乡村保护事业,因而有着较长时间的乡村保护实践。对于屈威廉的乡村保护实践,不妨概括为“为自然美景鼓与呼”(The Call and Claims of Natural Beauty)。这是他于1931年10月在伦敦大学所作的讲座的题目,也是他几十年积极参与乡村保护活动的写照。
屈威廉对乡村自然美景的保护,并非只是他个人的战斗。在英国,至少从19世纪60年代伊始,保护乡村及大地上的万事万物即已成为一项有组织的公民自治活动,相关组织层出不穷,至一战前,依成立时间先后主要的保护主义者(preservationist )组织有:公地保护协会(Commons Preservation Society,1865)、凯勒协会(Kyrle Society, 1876)、古建筑保护协会(Society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Ancient Buildings,1877)、德温特湖和博罗代尔峡谷防护委员会(Derwentwater and Borrowdale Defence Committee,1882)、湖区防护协会(Lake District Defence Society, 1883)、全国人行道保护协会(National Footpaths Preservation Society, 1884)、塞尔伯恩联盟(Selborne League, 1885)、鸟羽联盟(Plumage League, 1885)、鸟类保护协会(Society for the Protection of Birds,1889)、制止滥用公共广告协会(Society for Checking the Abuses of Public Advertising, 1893)、国民信托基金会、帝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Society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Wild Fauna of the Empire,1903)、大英帝国博物学家协会(British Empire Naturalists’ Association,1905)和自然保护区推广协会(Society for the Promotion of Nature Reserves,1912)等(48)Jeremy Burchardt,Paradise Lost,Rural Idyll and Social Change in England since 1800,London & New York:I.B.Tauris Publishers,2002,pp.93,94.,这份名单显示了一战前即已建立的英格兰保护主义者组织的数量和范围。虽然各组织的具体保护目标和对象各不相同,从乡村景观、有价值的古建筑到野生动植物等等不一而足,但它们同样都致力于保护活动,甚至还通过领导成员相互紧密地联系在一起(49)Jeremy Burchardt,Paradise Lost,Rural Idyll and Social Change in England since 1800,London & New York:I.B.Tauris Publishers,2002,pp.93,94.。其中,国民信托基金会则将上述那些目标综合起来。屈威廉的乡村保护活动一开始即与之相关联,日后他更积极地投身其间,甚至在其中起到了核心作用。
屈威廉的乡村保护活动最早可追溯到1912年。是年6月11日,他致函《泰晤士报》(TheTimes)主编,支持国民信托基金会筹集4,000英镑,以获得并保护位于温德米尔湖源头(the Head of Windermere Lake)的安布尔塞德的古罗马要塞(the Roman fort at Ambleside)。他之所以要这么做,是因为该要塞面临着当地建设开发造成的威胁。这在他看来是一个拯救温德米尔湖源头的问题,而温德米尔湖岸对于英国人是十分重要的,“这里是英帝国各地各阶层成千上万的人进入湖区的最重要的门户”(50)G.M.Trevelyan,“The Head of Windermere Lake”, The Times,15 June,1912.。翌年10月21日,他再次致函《泰晤士报》主编,抗议在湖区斯科菲尔峰(the Scafell peaks)修建汽车公路的提议(51)G.M.Trevelyan,“The Styhead Road”, The Times,22 October,1913.。像这样,致函《泰晤士报》或公开呼吁,以明确自己对于某一美景的保护立场和态度,成为屈威廉参与乡村保护的一种方式。
之后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屈威廉对乡村保护的积极性有增无减。他不仅通过撰述历史著作来表达对乡村的感情(52)这期间屈威廉所撰述的《19世纪英国史》和《英国史》(Illustrated History of England,1926)皆鲜明地表达了对工业革命所摧毁的乡村世界的怀念。,而且进一步投身于国民信托基金会所开展的乡村保护事业。其中一个典型的案例发生在1925年秋天。那时,屈威廉居住在赫特福德郡(Hertfordshire)西部“令人愉悦的乡镇”伯克姆斯特德(Berkhamsted),其住所位于阿什里奇庄园(the Ashridge estate)边缘,这里靠近尚未丧失原有自然美景的乡村,附近有美丽的丘陵、荒野、山毛榉林和公园。然而,那座庄园则因主人布朗洛伯爵(Earl Brownlow)在1921年去世而陷入将被出售并用作住宅开发的险境。这不禁令周围的居民十分担心,他们试图通过国民信托基金会发出呼吁,以购买和保留这片地产及其附近的自然美景。屈威廉说,这事碰巧让他与国民信托基金会建立了联系(53)G.M.Trevelyan,An Autobiography and Other Essays,pp.40-41,41.。他与老朋友、英国著名的文学批评家、时任国民信托基金会主席约翰·贝利(John Bailey)以及其他人一起,向公众发起募捐呼吁,很快募集到50,000英镑。后来在这一年的10月20日,斯坦利·鲍德温(Stanley Baldwin)、拉姆齐·麦克唐纳(J.Ramsay MacDonald)、牛津勋爵阿斯奎司(Oxford and Asquith)和法洛顿的格雷(Grey of Fallodon)等政治要人联名致信《泰晤士报》主编,紧急呼吁为了公众利益向国民信托基金会捐赠以拯救阿什里奇地产(54)The Times,20 October,1925.。结果,在1925年到1926年之交的冬季,该组织获得了1700英亩的阿什里奇地产,包括一些荒野、山丘和林地(55)The Times,15 July,1927.。1927年7月14日,屈威廉本人致信《泰晤士报》主编,表示国民信托基金会通过购买所获得的阿什里奇地产的面积在增大,这里作为一个公众游乐场所受欢迎的程度每年都在增加(56)The Times,15 July,1927.。因此,虽然从受托人手里购买这片地产的事情颇费周章,但正如屈威廉本人所说的,“这件事有着很好的结局。到1926年至1927年,阿什里奇得救了”(57)G.M.Trevelyan,An Autobiography and Other Essays,pp.40-41,41.。
显然,屈威廉在保护阿什里奇地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伽纳丁甚至认为,这一事件标志着屈威廉作为一名积极的保护主义者和国民信托基金会最具影响力的成员崭露头角(58)David Cannadine,G.M.Trevelyan:A Life in History,p.154.。而基于其丰富的历史知识、对乡村的热爱以及在公众中的声望,屈威廉于1926年被选入国民信托基金会的理事会。从那时起,他就一直代表该组织工作,在其理事会任职到1961年。这期间的1928年至1949年,他任该理事会地产委员会主席;1929年至1946年任该理事会执行委员会副主席,由此成为了负责该组织事务的核心人物,从而得以更好地致力于乡村及其自然美景的保护工作。
作为该组织理事会地产委员会主席,屈威廉实际上负责管理该组织的所有财产。从上文提及的答辩书来看,到1929年,国民信托基金会拥有的财产种类繁多,分布在英格兰各地,包括环伦敦郡县(Home Counties)地产、湖区、其他地区的乡村地产、海滨景观、自然保护区、建筑物及纪念建筑物、纪念碑和土方工程等(59)G.M.Trevelyan,Must England’s Beauty Perish? A Peal on Behalf of the National Trust for Places of Historic Interest or Natural Beauty,pp.37-63,37-44.。其中,仅环伦敦郡县地产的数量和规模就十分可观,不仅有阿什里奇附近面积大约2,000英亩的壮丽的丘陵、荒野和森林,还有萨里郡(Surrey)小镇莱瑟黑德(Leatherhead)附近大约330英亩的公地,萨里郡著名的可俯瞰多尔金山谷(the Dorking Valley)壮丽景色、总面积达652英亩的博克斯山丘(Box Hill),以及肯特(Kent)、白金汉(Bucks)、埃塞克斯(Essex)等郡的许多地产(60)G.M.Trevelyan,Must England’s Beauty Perish? A Peal on Behalf of the National Trust for Places of Historic Interest or Natural Beauty,pp.37-63,37-44.。它们或通过私人直接捐赠,或通过募捐购买的方式,先后成为国民信托基金会的财产。对于它们的获取和保护,屈威廉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此后,屈威廉继续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为扩大对英国乡村保护的范围和加大保护力度而努力奔走、呼号。1930年,他说服新成立的朝圣者信托基金会(the Pilgrim Trust)提供大量的捐款,使国民信托基金会获得并保护了英格兰内陆和海岸的许多财产。不久,他又代表该组织正式接受了不少捐赠礼物,如1931年接受了位于英格兰中部峰区(the Peak District)的700英亩龙肖庄园(Longshaw estate),六年后又接受了位于汉普郡(Hampshire)南唐斯丘陵的纽廷伯山丘(Newtimber Hill on the South Downs)(61)David Cannadine,G.M.Trevelyan:A Life in History,pp.155,156,155.。屈威廉对国民信托基金会的保护事业非常感兴趣,在他最钟爱的湖区尤其如此。
上文述及,在20世纪早期屈威廉即已关注湖区的开发与破坏状况。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他更加关注对该地区日益陷入困境的自然美景的保护。他不仅像早期那样经常致函《泰晤士报》,强烈地表达需要保护当地的自然美境,而且投身于要求保护湖区山谷和山峦的请愿活动。例如,他抗议在凯斯维克山谷(the Keswick Valley)修建输电塔的提议,还反对修建一条通往上埃斯克代尔(Upper Eskdale)的主要道路的计划。他总结说:“将纳税人的钱花在这样一件令人愤慨的事情上,是完全无视人们的精神需求”(62)David Cannadine,G.M.Trevelyan:A Life in History,pp.155,156,155.。1928年他父亲去世,他得到很大一笔钱款,他动用这笔钱购买了位于湖区朗代尔山谷(Langdale)顶部以及其他地方的几座农场,将它们全部捐给了国民信托基金会(63)G.M.Trevelyan,An Autobiography and Other Essays,p.41.,由此可见他亲自投入英国乡村和自然美景保护的情形。
在1929年至1937年间,屈威廉又先后购买和捐赠了更多的土地,使之并入国民信托基金会持有的阿什里奇庄园地产(64)David Cannadine,G.M.Trevelyan:A Life in History,pp.155,156,155.;1937年,他还说服大哥查尔斯捐赠了自家的沃林顿宅邸及其周围的13,000英亩的田产。查尔斯捐赠的惟一条件是,“他的妻子儿女在有生之年能继续在那里居住。之后,国民信托基金会可以自由地将之出租给任何最适于为公共利益而维护它的人。”(65)Jennifer Jenkins and Patrick James,From Acorn to Oak Tree—The Growth of the National Trust 1895—1994,p.93.
此外,因心系故乡所在的英格兰北部的诺森伯兰郡,屈威廉不忘敦促人们努力保护和维护坐落于此的哈德良长城(Hadrian’s Wall),还买下了豪斯特兹要塞(Housesteads Fort)旁边的农场,为此立约将其捐给了国民信托基金会,并公开反对皇家空军(RAF)使用诺森伯兰郡海岸进行轰炸练习。作为剑桥大学钦定现代史教授(Regius Professor of Modern History,1927年始任),他帮助建立剑桥保护协会(the Cambridge Preservation Society),整合力量将该城西侧从格兰切斯特草地(Grantchester Meadows)到麦丁利(Madingley)的未被破坏的区域从开发商手里保护下来。作为国民信托基金会事务的资深人物,他还被吸引到与其相似的组织即英格兰乡村保护委员会(Council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Rural England,1926年成立)的工作之中,定期在其年度会议上发言。作为著名的保护主义者,他支持伦敦绿化带计划(the London green belt scheme),反对1931年的《土地税法案》(LandTaxBill),欢迎1932年《城乡规划法》(TownandCountryPlanningAct)的通过(66)参见David Cannadine,G.M.Trevelyan:A Life in History,p.156。。
屈威廉也曾为英国的青年旅舍协会(the Youth Hostels Association, YHA)贡献力量。1930年,他成为该协会的第一任主席,其名字给这个新生组织带来了莫大的威望。这是他投入公众健康教育的又一个例子。他在1931年1月21日的讲演中解释道,该协会的目标是帮助收入有限的人特别是年轻人,获得“更多的关于乡村的知识和关爱”,并改善他们自身的健康、休息和教育(67)“Address by Professor G.M.Trevelyan,O.M,The President of the Association,on the wireless,January 21st 1931,” pp.1-4,6.转引自David Cannadine,G.M.Trevelyan:A Life in History,p.157。。该协会则计划为这类游客提供廉价、简朴的住宿,旅馆之间大约相隔15英里。屈威廉认为,“为了与自然融为一体”,到乡村旅游的游客必须步行或骑自行车,他们一次可以在乡村停留数日(数夜)。他还为青年旅舍协会的内部杂志《背包客》(TheRucksack)撰写了一些相当轻松愉快的文章,譬如有一篇文章曾这样写道:“现在我们吃过早餐,穿上靴子,上路了……”(68)David Cannadine,G.M.Trevelyan:A Life in History,p.157.。屈威廉之所以看重这个组织,是因为他认为“能够从根本上反对非利士人(the Philistines)(69)形容那些没有接受过大学教育,缺乏文化修养并鄙视文化的人。而捍卫‘宜人景致’(amenity)的惟一力量,即是到尚未丧失原有自然美景的乡村度假的民主运动,其中‘青年旅舍协会’的勃兴是一个象征。”(70)G.M.Trevelyan,An Autobiography and Other Essays,pp.41,92,94,41.
还应该明确的是,由于屈威廉是英国人家喻户晓的史学家,他本人第一关注的事情也是历史和文学,因此,他在代表国民信托基金会从事乡村保护事业的时候,能够很娴熟地结合英国历史和文学知识,阐释乡村和自然美景保护的必要性和意义,由此更能赢得公众的理解和共鸣。他的这一特长,不仅在上文述及的1929年的答辩书以及致《泰晤士报》主编的多封信函中反复得到体现,而且在后来的一些公开演讲和交流环节进一步发扬光大。其中,1931年10月26日他在伦敦大学所作的“为自然美景鼓与呼”的演讲,是最为典型的一例。
为什么作为史学家的屈威廉会被邀请到伦敦大学作这样的主题演讲?这不免令人困惑,但细究起来,又不难理解。原来,屈威廉是在伦敦大学“里克曼·戈德利讲座”(Rickman Godlee Lecture)上作这个演讲的,该讲座由戈德利夫人创办,以纪念夫君。戈德利曾是伦敦大学学院和大学学院附属医院的杰出学者和外科教授,其兴趣广泛,热爱自然,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野外植物学家,退休后在牛津老家致力于自然研究,写过《泰晤士河畔的一座村庄》(AVillageontheThames),书中探究了这一地区的古物、自然历史及其美景(71)G.M.Trevelyan,An Autobiography and Other Essays,pp.41,92,94,41.。据该讲座主持人说,请屈威廉来作有关自然美景的演讲,是对戈德利的特别合适的纪念,因为屈威廉已提出,“为了英格兰人民的快乐,要永久地保护大片大片非常珍贵的美景”(72)The Third Rickman Godlee Lecture,The Call and Claims of Natural Beauty,Delivered by Professor G.M.Trevelyan,O.M.,G.M.,p.5.。这表明,其时在英国,屈威廉因积极投身乡村自然美景保护事业而赢得了盛誉。
讲座伊始,屈威廉稍作寒暄后旋即直面现实,他说道:“有两种情况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对我们这个岛国来说尤其如此。这就是对自然美景的自觉欣赏,以及对自然美景的急剧破坏。毫无疑问,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因为破坏的速度太快了,所以欣赏的意识也就十分强烈。当你爱的人要在你眼前被处决时,你当然会失声痛哭。‘同时,不管我多么爱他,我发现现在我已失去了他。’”(73)The Third Rickman Godlee Lecture,The Call and Claims of Natural Beauty,Delivered by Professor G.M.Trevelyan,O.M.,G.M.,pp.7-8;G.M.Trevelyan,An Autobiography and Other Essays,p.92.紧接着,屈威廉反复援引英人祖先对自然美景的喜爱以及各个时代文学诗人留下的赞美自然的诗篇,陈述自然美景对于英国历史文化发展的巨大影响。由此,他十分忧虑地表示,如果不能至少挽救一点英国的乡村之美,那么英格兰诗歌或者与它有渊源关系的思想感情和愿望抱负都将没有发展前景(74)G.M.Trevelyan,An Autobiography and Other Essays,pp.41,92,94,41.。
这样,通过多种方式,屈威廉一直活跃在英国乡村保护事业的第一线,成为最重要的积极分子之一。在屈威廉和国民信托基金会几任主席、秘书以及其他人等“一群兄弟”的共同带领下,20世纪上半叶英国的乡村保护事业欣欣向荣(75)G.M.Trevelyan,An Autobiography and Other Essays,pp.41,92,94,41.。据统计,截止二战前的1939年,国民信托基金会已拥有了58,000英亩的地产,还以契约的形式保护了27,000英亩的土地;它用于地产保护的金额已高达500,000英镑,其会员人数也增加到7,100人(76)Jennifer Jenkins and Patrick James,From Acorn to Oak Tree:The Growth of the National Trust 1895—1994,p.115.。
三、“为世人永久保护”
由上可知,20世纪上半叶,作为史学家的屈威廉不仅系统地阐释了保护英国乡村及其自然美景的必要性,而且身体力行地以多种方式积极参与乡村保护实践。今天,我们又当如何认识他的这项工作的作用或意义?
毋庸讳言,屈威廉及其所代表的国民信托基金会等组织开展的乡村保护事业,看上去似乎带有英国文化的某种倾向,即“反工业价值观”(anti-industrial values)。这种文化为人所诟病,甚至受到了批判,这在1981年美国史学家马丁·威纳的《英国文化与工业精神的衰落》中有直截了当的表达(77)Martin Wiener,English Culture and the Decline of the Industrial Spirit,1850-1980,New W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威纳认为,英国文化中存在一种较为普遍的对企业家精神(the entrepreneurial spirit)的排斥,乡村保护主义(rural preservationism)是其组成部分,而企业家精神对于工业资本主义经济的蓬勃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英国没有资产阶级革命,在政治和经济上仍然由土地贵族统治,虽然商业和金融是贵族可以接受的财富创造形式,但工业在其眼里是肮脏的。结果,反工业的价值观仍稳居英国文化的核心位置,对各阶层都产生了影响。有学者评论说,在威纳看来,“乡村保护主义证明了一个国家对自己的未来失去了信心,并试图通过将前工业化时代的遗迹奉为其文化皇冠上的宝石,来支撑垂死的社会秩序”(78)Jeremy Burchardt,Paradise Lost,Rural Idyll and Social Change in England since 1800,pp.94,95-96,99,100.。
这样,威纳将20世纪英国的衰落与英国文化中存在的对企业家精神的排斥倾向直接勾连起来,他的这种论点很快在史学界引起了争论。一方面,对威纳论点持赞同态度的史学家进一步放大这种主张,从而特别“关注与乡村主义(ruralist)态度和保护主义组织相关的保守或倒退特征”(79)Jeremy Burchardt,Paradise Lost,Rural Idyll and Social Change in England since 1800,pp.94,95-96,99,100.;另一方面,有些不赞同威纳论点的史学家认为,“保护主义”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促进国家认同建设的一股重要思潮,因此“将它描述为一种本质上的倒退力量是误导人的”(80)Jeremy Burchardt,Paradise Lost,Rural Idyll and Social Change in England since 1800,pp.94,95-96,99,100.。实际上,英国一流的保护主义者在政治上并不保守。“相反,维多利亚晚期的保护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自由主义者主导的;在较小程度上还有社会主义者……作为一种政治力量,保护主义的内涵确实具有潜在的激进性。保护主义的核心理念是,当私有财产权威胁到自然美景或人造美景时,它们应该向整个社区的利益让步。”(81)Jeremy Burchardt,Paradise Lost,Rural Idyll and Social Change in England since 1800,pp.94,95-96,99,100.这些人还认为,至少在1918年之后,威纳所假设的乡村主义价值观和反现代主义之间的等式不再成立。
姑且不论英国衰落是相对还是绝对,也不论造成其衰落的原因有多少重(82)参见〔美〕马丁·威纳:《英国文化与工业精神的衰落(1850—1980)》,王章辉、吴必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译者序”。,需要思考的是,仅仅着眼于经济发展、国家兴衰等层面来认识和讨论英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历史是否完全足够并合理?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还需要从其他哪些方面来认识发展的目的和意义?或者英国社会普遍推崇乡村休闲生活这种情感、看法和价值观是否值得重视?尤其是在“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全球共识的当代,我们该如何对待之前时代各种保护的努力及其遗产?这些问题显然都值得一番深思和讨论。
在屈威廉生活的时代,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和社会的着力点,这在很长时间内也一直是人们讴歌的对象。而那个时代发展的内涵,正如美国环境史学家J.唐纳德·休斯(J.Donald Hughes,1932—2019)所注意的,“它被视为一种毋庸置疑的好东西……即使‘发展’没有定义,但很明显它的意思就是由技术发展所推动的经济增长。虽然世界史教材描述了艺术和科学的成就,但它们所认为的发展目标显然不是比《荷马史诗》更好的文学作品,比拉斯科岩洞壁画更胜一筹的绘画,甚至物理学中超越爱因斯坦理论的发现,而是工厂、能源设施、金融机构的创建,以及为了人类的目标而不断增强对地球资源的利用。至于环境,发展的故事大都忽视了生物和非生物世界。一个国家要想在发展中取得成功,就必须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将森林转化为木材,将煤炭和铁矿转化为钢铁。在这一过程中,空气会受到更严重的污染,河流也会因侵蚀和废弃物而变得更加不堪重负。”(83)J.Donald Hughes,What is Environmental History,second edition,Cambridge,UK:Polity Press,2016,p.99.休斯所注意到的这种发展及其结果,不啻是英国所开创的工业化发展道路及其结果的写照。
在这种发展观的主导下,许许多多的东西被碾碎、被破坏,当然包括乡村田园景致的破坏。1926年,屈威廉出版的《英国史》中有不少涉及乡村场景被破坏的段落,其中一段如下:
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英格兰那片未曾开垦的林地荒野上,至今仍栖息着上帝所赐的各种各样的美丽鸟兽,它们仍在树木和花朵的丰饶中嬉戏,这一定是个十分美妙的地方;而现代人,对其最好的传承漠不关心,他已经完全破坏了它,而且还在继续破坏它;新的破坏工具及方法的发明有多快,破坏就有多快。(84)G.M.Trevelyan,Illustrated History of England,London,New York,Toronto:Longmans Green and Co.,1926,p.87.
这段文字描绘了英格兰乡村曾经繁盛的景观,以及现代发展造成的破坏,其描写带有明显的苦乐参半的感觉。《英国史》在1926年甫一出版即成为那个时代销售最好的教科书,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英国人,甚至激发了他们复古的热情。
虽然我们并不完全认同屈威廉的立场和认识,但是他的文本描写和社会实践至少表明,对于现代发展及其成就和结果不仅要历史地看,而且要现实地看;不仅要从经济方面看,也要从文化、自然方面看。其时,英国社会的确形成了一种崇尚乡村生活的风气,那些保留了传统英格兰色彩的古老乡村宅邸在人们眼中也变得越来越可爱,但濒临破坏的它们却还没有得到政府或民间机构的应有的关注。因此,许多人士开始督促政府和社会对其进行有组织的保护,以阻止那些要把美丽的乡村庄园变成丑陋的建筑用地的破坏行为,并防止宅邸内收藏的大量无价之宝的流失。而屈威廉所从事的乡村和自然美景保护的确是一项有组织、有目标、有原则的事业(85)Laura Trevelyan,A Very British Family:The Trevelyan and Their World,p.299.,因此就需要跳脱个人喜好,从更大更长远的角度加以认识。我们可借用国民信托基金会保护工作的主旨,将他的事业的目标概括为“为世人永久保护”(For everyone,for ever)(86)参见https://www.nationaltrust.org.uk/features/about-the-national-trust,2021年1月25日。。唯其如此,才能把握屈威廉参与的乡村保护事业的作用及其重大而持久的意义。
应该认识到,在屈威廉及其代表的国民信托基金会的努力下,英格兰大量的历史名胜或自然美景得到了保护,它们是有形的物质财富,也是丰富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有着多方面的价值,尤其有助于满足城市化时代英格兰公众的需要。
正如上述1931年10月伦敦大学那次讲座的主席在给屈威廉演讲的书面版本所写的导言中提到的,屈威廉教授提出“为了英格兰人民的快乐,要永久地保护大片大片非常珍贵的美景”(87)The Third Rickman Godlee Lecture,The Call and Claims of Natural Beauty,Delivered by Professor G.M.Trevelyan,O.M.,G.M.,p.5.,这即是屈威廉参与的乡村保护事业的一项原则。它也可以简洁地表达为“为了公众”(for the public)。对此,屈威廉曾在代表该组织发表的答辩书中已经提及。一位听众问到:“当我们‘永久地’拥有我们的地产时,我们如何处理它们?”屈威廉回答说,有两个主要原则“指导我们的行动”:“(1)使这些地产尽可能地保持我们接收它们时的状态;(2)向公众开放这些地产”(88)G.M.Trevelyan,Must England’s Beauty Perish? A Peal on Behalf of the National Trust for Places of Historic Interest or Natural Beauty,p.25.。屈威廉在担任国民信托基金会地产委员会主席期间完成的保护地产并向公众开放的工作,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他的保护目标,由此使自然美景发挥了作为城市居民休闲娱乐空间的作用,它们对于缓解城市生活的问题并恢复城市化时代人类与自然的和谐交融是不可或缺的。
屈威廉保护乡村的言行及其投身的乡村保护事业,也代表了他所属的社会阶层的作用的变化。正如伽纳丁所评论的,这表现在他们不再是排他性的土地所有者,而是代表整个社会成为了乡村的保护者(89)参见David Cannadine,G.M.Trevelyan:A Life in History,p.156。。在屈威廉生活的时代,英国正在经历快速的城市化,这极大地改变了城市和乡村的关系,也改变了特定社会群体的角色,特别是贵族,他们以前是乡村地主。屈威廉处在了这一变化的交叉点上,代表了一种重新定位贵族角色的努力,同时也重新定义了乡村:它不再只是农田/庄园,还是作为游客的城里人前去消遣和放松的地方,这赋予了自然和文化遗产某种治疗能力。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些年里,大批英国城镇居民涌入乡村,要么是为了一日游,要么是为了度假,要么是为了永久居住。这表明,与1914年之前相比,乡村成为了国民认同的中心(90)Jeremy Burchardt,Paradise Lost,Rural Idyll and Social Change in England since 1800,pp.99,100.,进而在城市化的英国社会形成了崇尚乡村生活及其体现的传统的风气。
即便如此,在屈威廉等奉行保护主义的领导人物中,很少有人会接受他们的目标是倒退到过去的评论。屈威廉强调说:“我并不是在辩论一般的相对得失问题,或者在寻求平衡”(91)G.M.Trevelyan,An Autobiography and Other Essays,p.95.,因为在他那个时代,城市生活在许多方面都比过去的乡村隐居生活更可取,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所以,大多数主要的保护主义者认为他们的活动主要是为了改善未来,而不是将过去神圣化。保护主义的确利用了它从过去所感知到的价值来批判现在,但它这样做的目的是培育一个更美好的未来(92)Jeremy Burchardt,Paradise Lost,Rural Idyll and Social Change in England since 1800,pp.99,100.。在回顾过去的时候,保护主义并不是要逃避现在,而是要为现在树立一面镜子,让它的缺陷变得更加明显。
还值得注意的是,屈威廉在投身乡村及自然美景保护的过程中,对于自然本身及其与人类关系的认知有一种从人类中心视角向生态整体认知的推进,这从1929年和1931年他的两次公开演讲的内容比较中可窥见一斑。1929年的演讲,也即上文述及的他代表国民信托基金会进行的答辩,他在其中对“我们为什么应该拯救英格兰?”的问题作了回答和阐释,其着眼点主要在于英国人的身心健康及其历史感的培养上,因而体现了明显的人类中心视角。1931年的演讲,也即前文提及的是年10月26日屈威廉在伦敦大学的演讲“为自然美景鼓与呼”,他在其中不仅描述了英国乡村面临的威胁,以及城镇居民恢复他们与自然长期断绝的联系的需要,而且重申了对人与自然世界关系的重要性的认识。从两次演讲的主旨来看,他的思想变化是清晰可辨的。
在1931年的这次演讲中,屈威廉从英国历史和文学中挖掘出了一种自然观念,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一种天然的兄弟般的爱”:
但并不是只有在春天我们才能感受到对生长万物的爱。我们对树、对花甚至对草都有一种天然的兄弟般的爱;对岩石、对水也可以是这样。从字面上讲,我们和它们都是地球之子,因为正如科学教导我们的那样,我们已通过无数代从地球中进化而来。从字面上讲和用比喻来说,我们都是一个家庭的兄弟姐妹;而当一个美丽的审美形态被赋予我们的树木兄弟,或者被赋予穿过我们岩石兄弟的我们的水姊妹时,我们从它们以及它们跳动的生命中感受到亲情与欢乐,这种依恋之感比单纯的审美乐趣更强烈,尽管审美乐趣确实占了情感的很大一部分。(93)The Third Rickman Godlee Lecture,The Call and Claims of Natural Beauty,Delivered by Professor G.M.Trevelyan,O.M.,G.M.,p.16.
这段文字所表达的对自然万物的“天然的兄弟般的爱”,是人类历史文化中普遍存在的一种自然生态认知。虽然这种认知通常并非自觉的思考,但屈威廉相信,它是人类对自然的冲动的核心,并认为英国诗人乔治·梅瑞狄斯(George Meredith)的诗歌,如《山谷里的爱》(LoveinaValley)和《冥王之女降临的日子》(DayoftheDaughterofHades)等,最明确地表达了我们人类与地球和自然的家庭关系这一观念(94)The Third Rickman Godlee Lecture,The Call and Claims of Natural Beauty,Delivered by Professor G.M.Trevelyan,O.M.,G.M.,pp.16,15,15-16.。
屈威廉还认为,自然的体验因地而异,自然的魅力由多方面组成。一方面是美感,或者形式和色彩之美;另一方面是“自然的召唤”,是生命的意义,这种意义常常作为寓言和现实体现在春天的永恒轮回之中。“当一个人在漫漫长冬过后眺望花园,依据一些迹象,看见意志坚定的大地老母(Old Mother Earth)‘再次苏醒’,是多么的高兴啊!”(95)The Third Rickman Godlee Lecture,The Call and Claims of Natural Beauty,Delivered by Professor G.M.Trevelyan,O.M.,G.M.,pp.16,15,15-16.屈威廉甚至声称:“在万物复苏之时,这种喜悦对所有动物、大母神(the Great Mother)的所有子女、地球上所有居民都是自然而然的;人是其中的一员——除非他把自己关在城市里,不再是自由的、有形的自然的一部分。”(96)The Third Rickman Godlee Lecture,The Call and Claims of Natural Beauty,Delivered by Professor G.M.Trevelyan,O.M.,G.M.,pp.16,15,15-16.
因为有这样的生态整体认知,所以我们看到,屈威廉领导的国民信托基金会强调对多种类型的土地以及在自然美景中栖息的其他生命的保护。这包括大量可耕种但经济效益较低的土地,以及涵盖丘陵、荒野、悬崖、草地、树林和小山等未开垦的土地,屈威廉说到过它们——“我们拥有的大部分是未开垦的土地,我们的目标是保持其自然状态”(97)G.M.Trevelyan,Must England’s Beauty Perish? A Peal on Behalf of the National Trust for Places of Historic Interest or Natural Beauty,pp.28,28-29.。除此之外,还有“鸟类保护区和自然保护区”,这是国民信托基金会拥有的一种特殊类别的地产,公众进入是受到限制的。譬如,斯科尔特黑德岛(Scolt Head)、布莱克尼海角(Blakeney Point)、维肯沼泽(Wicken Fen)以及法恩岛(the Farne Island)等,国民信托基金会是为那些在其他地方濒临灭绝的鸟类、植物和昆虫而保护它们的(98)G.M.Trevelyan,Must England’s Beauty Perish? A Peal on Behalf of the National Trust for Places of Historic Interest or Natural Beauty,pp.28,28-29.。而对这些类型的地产和其他生命的保护,显然最能体现屈威廉投身的乡村保护事业除了为公众健康着想外也着眼于未来的主旨。
结 语
毫无疑问,屈威廉是那些以对自然的感知和历史知识来关心乡村和自然的历史学家的先驱。因此,正如在政治史和社会史领域他受到特别的关注一样,在环境史领域他也值得研究。屈威廉的乡村保护是有思想指导的、理性的、积极的实践,他并非“乡村哀悼者”,而是“自然美景的守护者”,其乡村保护事业在英国环境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页,在强调可持续发展的当代具有世界性意义。屈威廉乡村保护的言与行可能会启发我们这些专注于环境历史研究的历史学家思考,如何在当代社会的环保工作和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或许可以想象,正是因为有了屈威廉和他的同事及学生们的努力,剑桥大学附近的乡村美景,尤其是格兰切斯特草地在20世纪20年代末面临被开发而毁灭的危险时,才得以被拯救下来,中国诗人徐志摩(1897—1931)也才有可能在1928年创作著名的诗歌《再别康桥》。这样,我们也才能欣赏到如此美妙的诗句:“软泥上的青荇,油油的在水底招摇;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寻梦?撑一支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99)徐志摩:《再别康桥:志摩的诗》,郑林选编,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第213页。